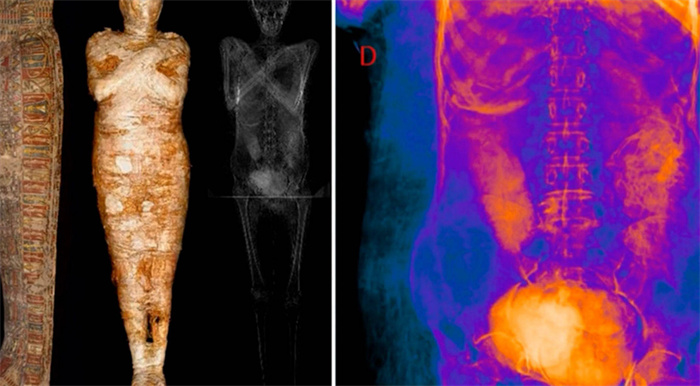卫聚贤与万泉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掘
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是民国时期山西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亦是卫聚贤对家乡所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本文试析遗址发掘之因缘,对已发现遗迹及出土器物进行梳理,借此来怀念卫聚贤这位对中国考古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万泉荆村(今万荣县万泉乡)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处峨眉岭北侧,其西南近邻孤山,北拒汾河,东北逐次下降,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平缓坡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性质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存的遗址。1965年,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民国时期山西籍考古大家卫聚贤首次发现的,遗址发现后几年,卫聚贤等人先后在万泉县西杜村(今万荣县皇甫乡)阎子疙瘩汉代遗址、荆村瓦渣斜新时期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二者相比,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时代早,发现遗迹及出土器物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且绵延时间较长,它无疑是山西地区发掘时间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1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始因
卫聚贤早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书时即认真听取过李济先生讲授考古学,后来看到一些考古类书籍,随后又到清华地质调查所历史博物馆参观实物,方才明白石斧等物为何形状。受考古学家李济、袁复礼发掘夏县西阴村并将新石器时代器物带回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响,卫氏携带着李济先生的三种陶片作为标准,于1927年2月回到老家山西万泉,在其侄儿卫月盛的陪同下,前往北吴村枣堰地、南吴村药王庙前后、袁家庄东沟西沟、荆淮村沟楞、荆村瓦子斜、南涧村涧薛村沟沿、秦王寨、城内东城濠、县党部后院、南门外沟沿、北门外文庙附近、西门外老母洞北等多地进行发掘,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迹的存在。这些遗迹分布范围南北长十余里,东西宽二三里,孤山东麓黄土坡上沟壕两面尽是。
在发现这些遗迹的同时,卫聚贤把在万泉采集、购买以及发掘出来的部分石器,带到清华地质调查所进行鉴定,经过与历史博物馆所藏石器仔细进行比较对照,发现他所带的正是同类石器。有此重要发现,卫聚贤很是兴奋:“既得新石器时代遗址,于是又参考考古学书籍,有疑难处,请教于李济之先生,我的考古学兴味,从此日隆。”这些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成就感,促使卫聚贤提高了从事考古事业的兴趣。通过在山西地区调查,卫聚贤还发现:“山西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推万泉,次为文水,如有专家往勘,当于这两处加以注意。”这正是卫氏发掘首推万泉之深由,展现了卫氏以学术为主的学人精神。
以上种种便是近代以来万泉孤山周围从事考古活动的开始。可以这样说,孤山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便是卫聚贤等人最终确定较大规模发掘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内因。而卫氏等人发掘山西地区的具体过程,据发掘者之一的董光忠(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代表)说,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三方签订合约专做山西考古发掘,先进行了西杜村阎子疙瘩汉代遗址的发掘,而后卫聚贤(女师大代表)、董光忠、山西公立图书馆等三方又重新签订合约发掘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本校(女师大)有鉴于此,蓄意于斯项工作者良久,适幸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开发万泉汉汾阴后土祠之际,同时而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址,且于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占据面甚广,极有继续发掘之必要,与期图更得进一步之重要供献之可能,该二机关遂于本校另订合约,为彻底考察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而作长期较大规模之发掘。”
关于瓦渣斜遗址发掘之经过,据董光忠描述:“爰于民国20年(1931年)春,由三方组织团体,实地在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大施发掘,此即本校与山西公立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三方订立合约发掘山西万泉县石器时代缘起与经过也。此次之发掘,亦于斯年(1931)四月一日开工,五月十五日停工,于工作期间,除因风雨停止工作两半日外,余日均自上午七时开工,至下午五时停止,中间于十二时至一时休息。开工伊始,只用十余名工人,嗣后依发掘情形,随时而增添工人,最多时则有四十余人工作云。”
综上所述,万泉县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可以进行并顺利完成发掘是种种内因外缘所促成的。
2发现重要遗迹、器物及其相关研究
2012年秋,笔者有幸与本省有关考古专家前去荆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耳提面授,聆听教诲之余,在专家悉心指导下,看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灰坑、弦纹及绳纹陶片等遗物,特别是在瓦渣斜遗址看到了多种彩陶片,这些重要遗迹遗物都足以说明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之发掘,在山西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影响很大。
(一)出土发现遗迹、器物
关于荆村遗址发掘的情形,据卫聚贤回忆:“万泉县城东临一大沟,沟两旁及其南尽为其遗址……”。可见遗址面积之大,实属罕见。而卫氏等人未全部发掘,仅发掘了瓦渣斜这一块七亩大之地。通过发掘发现有地穴、炉灶、屠宰处等遗迹以及众多器物,包括有:石器、骨器、粗陶器(鼎、鬲、甗、尊、罐、盆……壎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彩陶(为黑白红三色,黑色最多,白色次之,红色少见,黑色多涂于红底上,其花纹多点、线、三角形、鱼形、蝉形、蛇形的有二块)、骨等数种,董光忠还发现有四五种蚌器。
(二)发现遗迹及研究
1.地穴
在荆村瓦渣斜共发掘七亩地,遗址中发现地穴有二十余处,穴桃形平底,深约五六尺至丈余不等,宽亦如此。有一穴深约丈五尺,宽约一丈,距底约三尺处有一隧道,通至地面,隧道有五个阶段而成,其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故其隧道向东北,穴顶开口宽约三尺;又有一穴,其隧道口尚有扶樑栽柱的遗迹。
2.炉灶
在同一地点发现炉灶共有三处,灶是用泥做成,分上中下三部,下部有一圆洞,洞口向东南,为通风口;中部为施柴(燃料)处,底有许多孔,为洩灰通风用,旁的左右后三面高约一尺三寸厚约五寸的墙,墙顶湾内为悬空,为置鼎鬲处;由地层观察,当日此灶设在地面,今已埋入土中约五尺,在地穴中未发现灶,而此灶相连在地面上,似尚存共食遗迹。
3.屠宰处
距炉灶东北方向约一丈有余,有用火烧过的硬土坑,深约五寸,宽约一尺五寸见方。坑旁血迹尚多,应为屠宰处。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也丈夫认为,此“遗迹分布范围达600平方公里,在这里发现了贮藏谷物的竖穴(窖)和烧造陶器的竖穴(窖)。”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此次发掘“发现了‘窖穴、灶址等遗迹……’发掘者不仅准确发掘出单个和相互打破的袋状灰坑,而且清楚的认识到,‘如此交错之二窑或多窑,在古代当不能同时挖窟以住居。’”亦有学者研究,还在此地“发现了粟和有可能是高粱的壳皮,尽管关于高粱的真假问题尚有争论,但这无疑是除仰韶村外,发现的另一处新石器时代栽培作物遗迹的重要遗址。”
(三)出土器物研究
通过分析出土器物,董光忠认为:“瓦渣斜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品;陶器中间的花纹有划刺之花纹和物体之象形;陶制品塑态之艺术非为美饰之用意,盖寓有某种之情义;它的彩绘之艺术色料选址之精良,花纹描绘之细致,诚有为后人所不及者。”他又说:“ 经此一次发掘,除认为各石器时代遗址所出最普通之各种石器、骨器及粗糙印纹陶器在瓦渣斜均有发现且较繁夥外,他如瓦渣斜所发现带彩之红地黑花及三色花纹之陶器,有与仰韶西阴所出甚为相似者,有为工艺高超二处绝无者,诚为欲试做石器时代遗址之发掘者之最大贡献也。”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也丈夫调查山西古物时在省立太原博物馆看到了荆村出土的陶器后写道:“遗物以陶器为主,其中的彩纹陶器引人注目。”有一件“陶器的色彩是橙色,壁极薄,品质出色,器身肥阔,器口略为收敛,呈一钵形。器底很小,下收幅度很大,边口外翻很多,彩纹为黑色,边口上是条黑线,器身上是带状的花纹。带状花纹围绕着偏椭圆形的中心,呈紧绷开的三角巾状,也就是所谓的涡卷文。这是中原黄河流域常见的彩纹陶器,这种器型和这种独特的涡文,代表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特征。”
除这件器物外,日本学者也还注意到荆村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他们按照“前期涡纹发达,后期涡纹退化”的观点把荆村出土的彩陶划分为彩陶的前期制品和后期制品,另外还发现有一件制作精湛的薄胎黑色陶器:“这件陶器呈青灰色,颇为坚硬。陶器肩部突出,颈部束狭,可以认为属于黑陶系……可以认为,在荆村存有继于彩陶期之后的黑陶器的器物。”而这些彩陶与黑陶器物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所体现的特征。
3荆村遗址发掘带来的思考
荆村遗址发掘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是民国时期山西地区较早的、重要的新石器遗址发掘地之一,而且它是继李济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之后其弟子卫聚贤在山西境内的又一次重要考古活动,卫聚贤也由此跻身中国考古大家之行列,成为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通过此次发掘,它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1.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及其出土丰富多彩的器物填补并丰富了山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内涵。关于荆村遗址发掘情况,迄今为止,仅有当年发掘的当事人之一董光忠先生的《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正式发表过,另外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小史》中亦详细总结了遗迹及遗物,但这个遗址较为重要的发掘报告却因种种原因未正式出版。据卫月望所说:“此批古物,据传当时路经太原时,即被山西当局扣留,现在的山西博物馆尚陈列的有许多件,其下标签上均写‘万泉荆村瓦渣斜出土’。由于发掘报告未能发表,以致这一重要遗址的情况未能正式批露于世,”父子二人均感到发掘报告未正式出版一事确为遗憾,无疑给我们后世学人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虽然报告未正式出版,就单从荆村遗址发掘出土器物来看,其对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性仍是不容质疑的。
2.荆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如果放到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河三角洲区域来看,意义似乎更为重大。关于荆村遗址的文化特色,据董光忠所说:“由瓦渣斜所发现之新石器时代带彩之陶器,而欲研究其与他各古代文化区有无文化相似之处,能否用归纳方法而研究各区相演之文化系统,俟瓦渣斜发掘报告宣布于世后(约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出版),读者自能一目了然。且易知其与夏县之西阴村(视李济先生所著之《西阴村史前之遗存》),渑池县之仰韶村(视阿尔纳氏所著之河南石器时代之著色陶器)所出陶器代表之文化实为近似。”据上可知,荆村遗址与仰韶、西阴等文化,及其这些文化所覆盖的黄河三角洲区域在续写着人类文明史新辉煌,荆村遗址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3.“二重证据法”及实际工作中运用的“多重证据法”是考据观点成立的重要方法。从事考古及器物研究,任何一种观点的成立与否,证据的价值与多寡是关键。找到充分证据进行论证,无疑是笔者梳理荆村遗址出土器物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卫聚贤早年对荆村遗址发掘之后,直至现在,对出土器物的研究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草就此文,通过今后不断去深入研究,在此领域开花结果,这无疑是纪念卫聚贤这位山西籍学者的最好方式。
作者:吴鹏程
作者单位: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吴鹏程《卫聚贤与万泉县西杜村汉代遗址之发掘》 ,《华夏考古》 2017年第4期
[2]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民国22年(1933年)版
[3]卫聚贤《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经过和见解》,《东方杂志》1928年第二十六卷第四号
[4](日)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李广洁、谢鸿喜译《山西古迹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版
[5]董光忠《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师大月刊》第3期(1933年)
[6] 赵换《卫聚贤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
[7] 卫月望《卫聚贤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九辑》第一版,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黄雪芮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