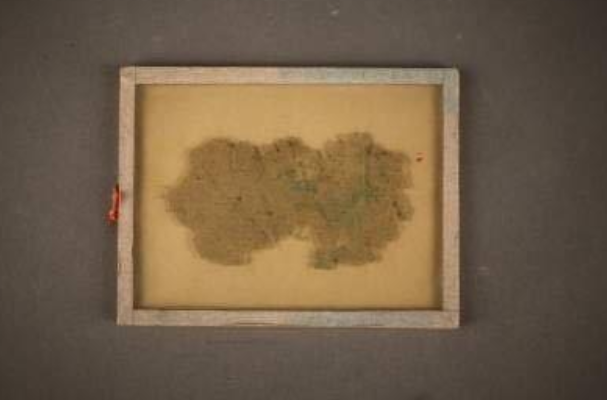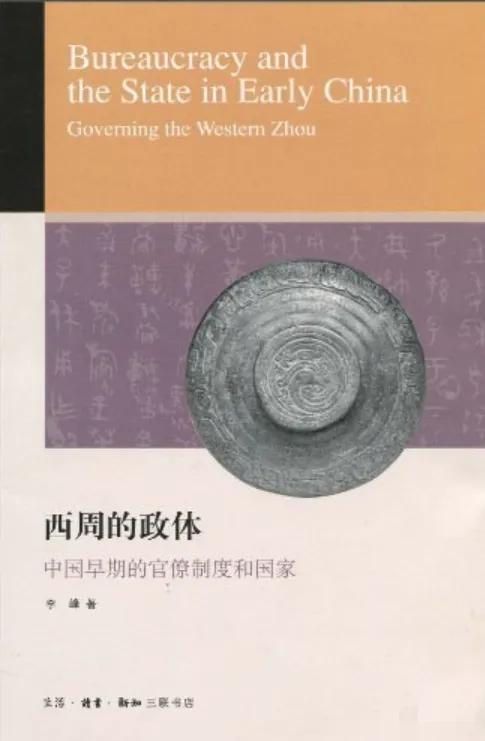“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安金槐先生访谈录
12月2日,安金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郑州举行。
安金槐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纪念安金槐先生从事考古工作50周年时,北京大学的师生送了安先生一幅字:“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安先生不仅是河南考古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还是河南省文博战线的一面旗帜,曾先后主持发掘郑州商城、郑韩故城、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密县打虎亭汉墓等数十处大型古遗址及墓葬。他提出了原始瓷起源于商代观点,将中国瓷器起源的历史由东汉提早了1500余年,改写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他撰写的《中国考古》教材培养了一代中国考古学人。
在其5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其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吃苦耐劳、勤奋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成就,对河南省乃至全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图片来源:河南日报)
“文博中国”本期特别推送,《考古与文化续编》中安金槐先生专访一篇,致敬“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
采访时间 / 2001年1月5日 下午
采访者 / 曹兵武、方燕明
采访地点 / 安金槐先生家中
1954年,河南的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安金槐和新中国河南的考古也就自然从郑州的建设开始……
问
先生今年已经80岁了,近来身体可好?忙些什么?
答:我自己觉得近来身体已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忙来忙去,始终还是围绕我的那个老问题: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报告。从1953年到1985年,全部经过我手的材料,我都要有个交代。这些年,几次开始又几次放下,这一次是彻底了,刚刚脱稿,过几天就送到北京。也算是了结了我平生的一件心事。
问
回顾您的一生,主要都做了哪些工作?
答:就考古来说,主要只做了两件大的工作:郑州的商城和登封县的王城岗。其他遗址也挖了一些,比如新郑的郑韩故城,我开了个头,最后由别人继续做。当时是1964年,国家文物局点名让我去做。那时候的发掘不轻易批,批了也就30、50 个平方米,不准多挖。当然,要论投入的力气,还是郑州商城最多,开始挖的时候也比较作难,不认识器物。王城岗发掘是在挖郑州商城后,眼光逐渐看得远了,想找夏代的东西,才开始做的。
问
能不能谈谈郑州商城具体的发现、发掘和认识过程?
答:1950年,二里冈被发现。52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三家举办考古培训班(按:即后来所说的考古黄埔四期),第一期就选择这里实习。培训班结束后,河南的同志接着在这里发掘,53年成立了省文物工作队,我被任命为副队长,还是接着挖。当时郑州铁路枢纽和郑州市的基建如火如荼,而我们只知道二里冈,所以,整个工作队的任务就集中于此。为了培养河南的考古力量,53年和54年还在郑州开了两届自己的培训班。当时设在郑州的文物队是双重领导,省里和国家都很支持。郑州离北京比较近,一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国家文物局的同志就来了,王冶秋局长一年能来个两叁趟。我们在不少地点比如北边的白家庄都发现了二里冈式的商文化遗存,但还不知道有城。54年发现了南关外和北郊的铸铜工场、制陶作坊等。
当时的发掘还不能叫主动发掘。那时候基建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处都是出土文物的线索,多少挖几条探沟,确定一下发现而已。当时的文物考古工作讲双利,中央文物工作的方针是“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配合基本建设是主要的。专业考古人手很感紧张,所以我从北京参加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三家举办的考古培训班后,接着就办省里的培训班,现学现用,现炒现卖。不过那时候发掘的经费不用愁,国家文物局会给,王冶秋、夏鼐、裴文中等领导都是专家,也是培训班的老师,对这里的发掘是很重视的。裴文中先生把自己的书带到工地,让大家学习。王冶秋说,人手实在不够,可以让华东(当时包括七个省)文物队的同志们来,每省抽两三个同志。南京博物院的曾昭橘、尹焕章都来了,他们在当时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郑州的文物队被改名为河南文物队一队,曾昭橘、尹焕章都被任命为副队长,我仍然兼任副队长,没有队长。工人的事不用愁,各派出所可以抽派,而且可以挑最好的。
那时候考古队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大家很团结,但是业务的力量确实有限,各省来的也不全是内行,不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实习锻炼的。我自己也是被逼上梁山,一天到晚都泡在工地上,常常是早上4、5点钟就起床。任务重的时候,一、二十个工地同时干,我是每天必到。工地的工作制度也比较严格,地层要分清楚,大家共同研究以后再往下挖。
问
挖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挖的是商代的东西?怎么跟商对得上号?
答:知道。殷墟发掘已过很多年了。我们这里53年发掘,54年就开始整理资料,都知道是商代的。只是刚开始只知道二里冈,慢慢地才知道还有早晚的区别。54年发现了作坊,也只是小挖了一下,基建快得很,不等人啊。
55年发现了城,是10月份,说起来是偶然的很。55年进行清干(按:清理干部队伍),我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上的是资产阶级办的河南大学,出身又是地主,自然是清干的重点对象。8月份让我停职检查,各省来的同志也陆续离去,考古发掘工作非常不好开展。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宿舍楼东侧(在当时城内东北高处)破土挖沟准备埋设水管,我照看工地(也没有叫我负责),发现了夯土,面积很大,形状很长,不像是墓葬。开始时认为是河堤,但越挖越长,心想可能是城墙,钻探了两个月,跟郑州的小城接上了。56年才开始对夯土进行发掘,发现夯土被商代的墓葬和房基压着,因此,定为商城是可靠的。
不久我恢复了工作,认为应该写出商城的发掘报告。开始时我叫同志们写,但大家都害怕当白专典型,写出来后挨批判,担风险,不愿写。只有我胆大,我觉得自己不是考古科班出身,犯错误、丢脸没关系,硬着头皮写了。报告出来了,果不其然,一些人认为安阳殷墟尚且没有城,郑州二里冈比殷墟早反而有城,这不是胡来吗?《文物》和《考古》杂志上都有批评的文章。其实,我心里也很打鼓,稿子57年就写出了,一直不敢拿出来,还是王冶秋到郑州看了稿子,才拿走要发表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试论郑州商代城址——敖都》,公布了商城的发现和我对其性质的认识。这些本来应当包括在报告里,但是,当时关于该城的争议颇多,意见一时无法统一,为了及时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我只得以个人名义著文,文章在61年发表。
问
什么时候对商城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答:1972年,国家要办出国文物展览,王冶秋提出应给郑州商城画个图,但北京仍然有专家不承认有这个城。于是,在72年的9月(?),我们找了个叠压关系比较复杂的地方挖开,请专家们到现场来看,大家才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承认了商城的存在。
因此,商城的发现是有很多坎坷的。
郑州商城争争吵吵了十多年,终于得到大家的承认。80年代河南偃师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大型宫殿遗址和同等规模的商城的发现,才使得对郑州商城的深入认识有了参照的对象,直到最近殷墟外围洹北商城发现以前,二里岗商城一直是中国前文字时代最大的城址,而被安先生论证的二里岗商城的原始瓷器,一下子把中国这个瓷国瓷器起源的年代上推了一千多年……
问
郑州商城著名的原始瓷器是怎么回事?
答:郑州发掘中发现有商代的瓷器和瓷片,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应该是原始的瓷器,一种认为还是属于过去叫的釉陶。59年,为了向国庆献礼,我们对历年同志们发掘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编写报告或简报,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所谓商代的“釉陶”产生了一些看法,6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从胎骨为高岭土、釉质化学元素和早期瓷器已比较接近两个方面,结合商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认为它们已经属于原始的瓷器。文章当时也是不敢发,这一次是叫陈滋德(按:原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看见了,拿去发在《文物》上。文章当时没有多少影响。1974年,英国人李约瑟写了本中国科技史方面的书,陶瓷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候谷牧同志在国务院分管文物工作,比较重视,上海的硅酸盐研究所提出也想搞中国自己的陶瓷史,与故宫的冯先铭先生联系。他们因为是急着搞,所以就采取全国动员,在北京开了个大会,夏鼐先生也参加了,我也去了。当时一般的看法是中国的制瓷是起源于汉代,而我60年就提出起源于商代,区别确实是太大了。
后来,硅酸盐研究所通知我到浙江开会,说是同意我的观点,让我也写一部分,就是夏商周的陶瓷。我说过去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写不了。他们说你不写,别人恐怕更不行。在浙江会议上,我的观点被批了一通,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文博系统的同志基本上都支持我的观点,他们说再不参加这样的会议了,书还是由陶瓷研究所自己去写吧。
会后,有同志把情况说给谷牧同志听,谷牧同志反而同意我的意见,因此,最后我还是参加了陶瓷史的编写工作。
问
看来学术上的创新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70年代以后,郑州商城的考古有什么重要的进展?
答:郑州商城基本上得到承认,接着很快又在城内找出了宫殿区、铜器窖藏坑,还发现了更多的作坊工场,郑州的考古至此算是平安无事。要说新的的进展,比如后来还发现了井,其实,以前已经碰到,没有弄明白,有些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挖到底,后来继续挖下去,认识到这种遗迹原来是井;还发现了更大的外城,也是在53年时就碰到的,当时没有认出来。这是考古学的进步。72年—85年,断断续续的工作仍在搞,但我的主要工作已经不在商城,不过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我很关心这里任何新的发现,我是人离心不离。
问
是不是去了王城岗?为什么要挖王城岗?
答:商代有了原始的陶瓷,夏代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时研究夏文化已是被提上了日程,重点当然还是在河南省,因为传说夏人活动的主要区域都在这里。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选择了河南,河南省自己也要搞。考古所选择了二里头,两家何必争?我们就选了王城岗。算是与北京考古所的一个分工。
王城岗是有历史记录的,我们挖这里,抱着两手打算,就是要看一看有没有城址,有和无都无所谓,如果有城,无论是龙山时代还是夏代都无所谓。
工作是在75-77年的上半年开展的,没有多久就发现了夯土。我们在郑州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对夯土很熟悉,所以,一碰上就认出来了。当然,对夯土的认识同样是有争论的,争了很长时间。77年,我们到北京汇报,决定下半年在王城岗开个现场会,现场鉴定一下。夏鼐先生领队,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还有各省文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这个会开得很重要,肯定了夯土和城的存在,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大家认为城还是太小了,实际上是两个城并列,东边的那个被洪水冲毁了(按:后来方燕明和刘绪等先生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又发现了大城)。后来隔河发现了战国的阳城,出土的器物上有“阳城”、“阳城仓器”等字样,证明这个地方在战国时还叫阳城,阳城就在登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禹居阳城”,这是很古的记载。
在王城岗一直发掘到1980年,考古报告也很快就写好出版了。
问
对王城岗这个城怎么认识?
答:王城岗的城是龙山时代晚期的,通过王城岗的发现,可以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是夏代不成啥问题。全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些,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很单纯,龙山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时期嘛。包括良渚文化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当然也存在很多的争论。不过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上还是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是夏文化的。
总起来说,我这一生也就是围绕着三个问题:郑州的商城、王城岗的阳城、原始瓷器。你看我的文章,大多与这三个问题有关。三个问题在学术界都有过争论,但我是都写了报告,也写了文章,公布了资料,表达了观点,于公于私,基本上是问心无愧。
前不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纪念安先生从事考古工作50周年时,北京大学的师生送了安先生一幅字:“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似乎想以此对安先生的成就进行一次全面的概括……
问
除了自己的学术成就外,安先生实际上还是河南考古工作的奠基人,由于您这么早就开始了考古工作,现在人才辈出的河南文博界的很多专家都是安先生手把手地带出来的,您怎么评价您这个从业的过程。
答:我只是来的时间早,50年组织上就让我来做这个工作了,原因是我是学历史的。其实学历史对考古学是很外行的,因此我一直很努力,夯土、台基,我都是亲自动手、辨别,因此,自称是一个老技工倒是很合适的。工作不敢瞎指挥,自己动手,别人说对说错心里有数。
对于年轻人,我的观点是只要你愿意学,有培养的前途,我不管你是谁,都无私心。自己家里的事情我是基本上不管,最困难时也一样,一年有七、八个月是在外边搞考古的。
问
龙山时代的晚期是夏文化,夏商周又是华夏传统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但是现在不少人认为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不如其他地区比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发达,您一直在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工作,对这个矛盾怎么看?
答:龙山文化是个关键,夏与商之先都在这个里边,龙山文化代表了一个时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试论河南的龙山文化与夏商文化》。就河南来说,豫东与豫西就不一样,所以我叫它们河南的龙山文化,目前的工作和研究都还很不够。
没有做过真正的老师,但通过培训、扶持年轻人和一本教科书式《中国考古》,今天在文博界同样是桃李满园……

问
您写的《中国考古》影响也很大,与你前面讲的这些事情有没有联系?
答:这本书也是很经过一番作难才弄出来的,是国家文物局多次找、多次催的结果。50年代在郑州发掘时,王冶秋局长就认为全国考古人员的知识太少了,提出让我编一本中国考古的书。当时我知道的也不多,全国的知识有一点,但没有亲自摸过。不过当时还真是写出了一本,王冶秋鼓励我大胆地写。但是,写出来后,我却没有胆量交稿,文物局的人催过多次,我都没有交出去。80年代,张柏同志主持教育处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在郑州办培训班,他又提出想编几本教科书,大概计划有七、八本吧。张柏直接对我说,考古就由你编了。我说北京的考古所人才济济,应该由他们编。过了没多久,国家文物局在山东长岛开会,讨论编书的事,果真通知让我去,并要求带4-5个同志一起去,我就带了4-5个人去了,基本上是河南人,为的是工作起来好协调。长岛是个好地方,水产多,会议开得好,我们是吃也吃了,住也住了。回到河南,我很快忙于王城岗的报告,而计划中的青铜器这一本由马承源主编很快就出版了。国家文物局要求连续地出下去,于是就不断地催,张柏此时已到办公室当主任,由教育处的同志接着来催我,我只好召集大家分工,其中夏商周的部分由我写。后来是越催越急,上海出版的款项都拨了,还能不写吗?没有退路了,不就是多收集些材料嘛。郑州大学的匡瑜老师也参加编写了,他没法写,就把自己的讲义拿出来了。但是其他的同志也是成天催也不动手,最后,我是谁也没有指望了,北京是催我不催他们。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动手。84年,王城岗报告的初稿完成后,我是全力投入这本书了,一年时间,一下子写了80万字。原想找专家审一审,但那边催得太紧,没有时间了,就自己直接寄到上海。上海的出版社说,一本书没有给多少钱,80万字太多,不给出,要求减到50万,我只好又亲自跑了一趟上海。在那里,别人对我说,老安啊,像这种书以后再不能编了,真是又苦又累,出力不讨好,比编一本考古报告还要作难。
这本书署名确实是我一个人。书出来后,就有人提意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王仲殊所长说,像这样的书应该是500万字,哪里是50万字可以说得清楚的。
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就是编《中国陶瓷》,也是这套教科书中的一本。主笔是冯先铭,前一部分最后也是落到我身上。情况也是一样,别人都不动,我又被逼上了。
不过,这书出来后卖得还不错,重印不少次,台湾已出了繁体字版,最近还要出修订版。
我这人一辈子不跟别人生气……胆大、冒失,才干了一点别人不愿或者不敢干的事……编考古报告要有点吃亏的精神,发掘时那么多人搞,轰轰烈烈的,最后谁来收底……
问
这些事情是当时有争论,现在基本上已成定论,影响都是很大的,你自己从中有何心得?
答:可以说我这个人就是胆大、冒失、不计较,才干了一点别人不愿或者不敢干的事。我说这些,你最好不要发表,捎带了一些人。不过我这人一辈子不跟别人生气,不跟别人计较,该干的事,别人不干,我是一定要干的,电报在催着,我说我是走错了路,但也得走下去。文革中,我被定为这个、那个,过后我没有与任何人计较。
问
这是不是可以集中精力做点事情的原因之一?
答:对对。我这个人跟北京的老同志、老领导都混得很熟,单位的同志都对我也不错。我也当了几十年的单位领导,班子里没有一个同志不舒服。搞业务也是这样,商代考古不能一个人研究完,再加200个人也不多。今天你们到我这个家,我住在这个地方不想走,给了很好的新房子也没有走,就是想离单位近些,不想离开这个老地方,当年买地皮盖房子我都参加了,有感情啊。没想到现在因为环保不让老房子用暖气,才觉得受不了。
问
能不能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完稿的商城报告的情况?
答:不算图一共有80多万字,分两本。考古报告的出版是个大问题,我的想法是凡经我手的都要出来。编一本考古报告是要费大劲的,这一本已经几十年了,弄弄就搁那儿了,现在基本上结束,后天稿子就到北京的出版社。还有的文章本来也想写,最后都搁下了,现在也不想写了。所以编考古报告要有点吃亏的精神,发掘时那么多人搞,轰轰烈烈的,最后谁来收底?大家都怕吃亏,都盯着新材料新发现,挖完一个遗址再去挖下一个,那报告就完了,再好的材料也就没有了。象《密县打虎亭》,谁去弄?你挖了,情况清楚些,有这个义务。
问
最近还有什么工作要做,还有啥打算?
答:老了,不能动了,我现在是连门也不出了,外边的消息不太灵通,也不想写啥了,报告交出去,心里很坦然,基本上不打算做啥了。
问
看不看《中国文物报》?
答:每期必看。省文物局给订的,我还是他们专家委员会的人。你们扩版了,内容丰富多了。
谢谢您接收我们的采访。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化续编》 曹兵武/著 )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0000
- 0000
- 0005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