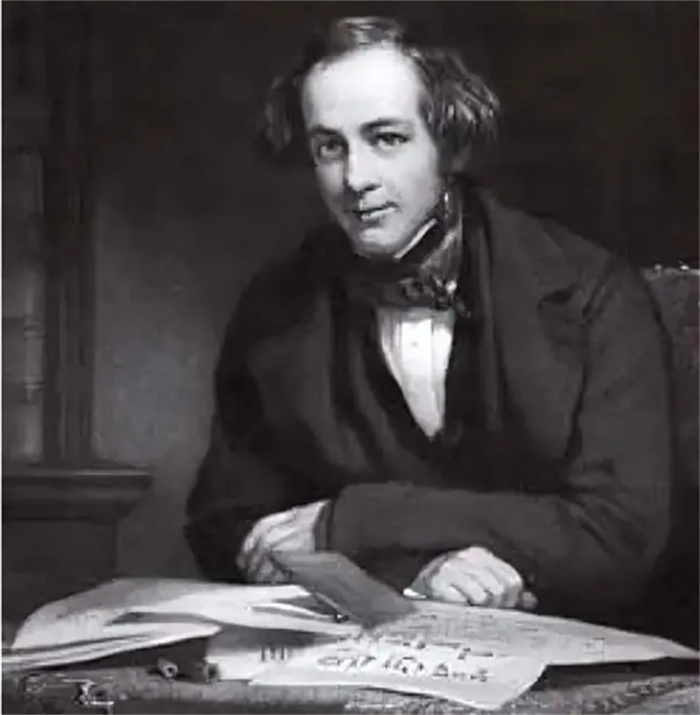张越|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
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 说,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 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
就史学而言,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 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纪传体,与其说本于《史记》,不如说本于《汉书 》;编年体,与其说源于《春秋》,不如说源于《左氏》;政制史(以往目录家称为政 书类),与其说始于刘秩《政典》,不如说始于《周礼》六官;学术史(以往目录家分隶 于子部各家),与其说源于《史记》的《孔子世家》、《儒林传》,不如说本于《汉书 》的《艺文志》、《儒林传》;《左氏传》、《周官》以及《汉书》不是古文经典以及 受古文派学说支配的史学著作吗?”(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 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史书体裁如此,在史学 观点、史学方法诸方面,经学的影响也可说是无所不在。经学对于史学的种种影响,有 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刘家和先生从史料的角度论及经学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 时,指出经学对史学有提供资料、提供对古代文献的解释、提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等 三种意义。(注:刘家和:《史学与经学》,见《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7-225页。)这是从积极的方面而言。直到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将经纳 入史的范畴,在经史关系上,史似有反被动为主动的倾向。但章氏的提法本身就存在经 学派别纷争的色彩,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经尊史卑”的局面也不可能 被完全扭转。
鸦片战争以后,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由复兴到昌盛,至戊戌时期,康有为等人将 今文经学发挥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今文经学以公羊学说为代表,一时风靡海内。19 世纪末年,西方的进化论观点经严复的转译传入中国,着力倡导“公羊三世说”的今文 学家迅即接受了进化论的见解。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说:“南海先生读大著 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 :‘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 版,第108页。)康著《孔子改制考》(1897年)与严译《天演论》(1896年)成书时间相近 ,由上引梁书所言来看,康氏似对进化论学说知之更早。可以认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 今文学家的公羊学说,即融入了西方外来的思想观点,这在经学史上是一个重要变化, 今文经学结合于西方进化论,其结果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言:“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 一幕,夕照辉煌,晚霞满天,预示着新世纪行将到来。”(注:陈其泰:《清代公羊学 》,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这同时也预示着,经学时代即将走向终结。
晚清以来对诸子学说的研究逐渐发展,形成了诸子学的复兴局面,把孔孟纳入诸子学 的范畴,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诸子之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经学的独尊 地位。
从经学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晚清时经史地位的变化已见端倪。钱穆指出:“晚清康 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盖经学之至于是已坠地而且尽。”“《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此两书者,非 研经,乃辨史。显以由经学而转为史学矣,此亦途穷思变,为大势之所趋。”(注:钱 穆:《经学与史学》,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册,华世出版社1 976年版,第136、135页。)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今文家崔适撰写了《史记 探源》,从经学的角度探讨《史记》一书,认为,《史记》属今文经学的性质,中就有 与古文说和《汉书》相合的,是经过了刘歆的篡改他的另一部著作《春秋复始》认为《 谷梁传》也是古文学,是经过刘歆伪造过的。崔适的这两部著作,“反映了这时今文经 学在经部范围之内,无论分经的或综合的研究,都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于是转而治史。”“说明‘经师’式的研究,已陷末路。”“‘经’的可信范围越缩越小,‘经’的可 疑程度越来越大。‘经’的地位动摇了,二千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终结了。”(注: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3-364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史学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 》(1901年)、《新史学》(1902年)为代表,“新史学”的口号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划 时代的标志。梁氏运用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的有关思想结合进化史观解释历史进程;夏 曾佑在其重要著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中讲到了今文 学说与进化论的关系。这就表明,一方面,今文经学再次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 内在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史学家已经有了用西方进化论学说解释历史而有条件地排斥 经学思想束缚的较为明确的意识。
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的古文经学,并未因今文经学的再倡而销声匿迹。晚清章太炎、 刘师培等人的思想和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为学术界不可忽视。章太炎主古文经学而力 斥今文经学,矛头直指康有为,引申及政治思想则宣传“排满”、“革命”,较之康氏 的“保皇”、“改良”更为激烈,也更为激进。然而此时的章、刘等人却也接受进化论 的学说。如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尽管前后变化不一,但对于历史进化之理却一直有着深入 的思考。在1902年,章氏曾计划修撰《中国通史》,认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 清尘翳而已,已既能破,亦将能立。”(注:章太炎:《訄书》重刻本《哀清史 ·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力求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注: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 版,第167页。)章氏是一代经史大家,他希望撰述新的中国通史,并积极借鉴西方学理 ,其史学主张同样是“新史学”思潮的重要内容。
前言信奉今文的夏曾佑运用进化论的原理撰述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 了热烈的反响。就在同一年(1904年),信奉古文的刘师培也出版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科 书》,这部书出版后也风行一时。表面上仍势同水火的经今、古文学两派,在使用进化 论撰述中国历史这一点上却取得了一致。这个现象很可以说明西方进化论学说在当时产 生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经学与史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关系的些许变化。
二、经学走向终结与史学的独立意识
五四时期,经学走向终结,史学则开始了其新的发展历程。
范文澜认为经学趋于灭亡的原因有二,一是外部原因,缺乏统治者的强有力的支持;二是自身原因,“它有夺取对方武器的传统本领,虽然新民主主义的武器(民主)欢迎任 何人去采用,可是阶级性质限止了它,使它没有勇气去夺取或采用。”(注: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 269页。)换句话说,经学已经失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存在的可能。所谓新的历史 条件,就是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 店的呼声使经学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而民主与科学是不可能被经学用来“充实自己 改造自己”的。陈寅恪在1935年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的序中说:“近二十年来 ,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 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金明 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史学的转变若此,扩言之,经学 的衰落和终结标志着进步,标志着理性的觉醒。
经学走向衰落,使得史学有可能挣脱经学的羁绊;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深入人心, 则促使史学以主动的姿态要求学科的独立。史学独立的条件首先是史学研究应超越功利 目的和利害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反对“通经致用”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五四 时期史家所刻意强调的。章太炎在20年代称,“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 ,先于求是。”(注:章太炎:《说求学》,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0页。)章氏本意显然是主张求是应先于应用之学。王国华述 及其兄王国维的学术时说,“并世贤者,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俱不外以 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注:王国华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顾颉刚 强调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 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 ,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 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 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注: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其实,希求史学研究完全超越现实政治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史学摆脱经学羁绊的过程中,摒弃片面的通经致用是必要的。总之,学术研究中 求是大于致用、史学研究中求真大于致用,科学原则取代经学的说教,史学与经学的关 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虽然在主观上有意识地走出经学的羁绊、努力摒弃经学的派别与门户之分,但这并不 是说,经学已经销声匿迹,或者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便不存在。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具有 上述认识的人并不普遍。一些人因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师承渊源关系,还有着很明显的经 今古文的派别之分,如章太炎,因谨守古文学派家法而多有意气之论,梁启超就认为:“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甲骨文,治 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 9年版,第70页。)周予同回忆说,五四运动以后,“文史学的情况仍然落后于现实,更 其表现在高等学校和出版企业中。当时文史学界有四派:一派是超‘经学’、否定‘经 学’而转究史学,虽然如何否定、如何转变还没有正确的方向,但在当时已算是‘前进 的’。一派是根本不知道‘汉宋学’的异同,而只是抱残守阙,‘汉’‘宋’乱用,在 当时虽是‘落后的’,但情况却相当普遍。其余两派,或继承孙诒让、章炳麟的学派, 坚持‘古文’;或宣扬廖平、康有为的论点,专主‘今文’。这两派在当时势均力敌。”(注: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后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4页。)不过,这些“ 否定经学而转究史学的”少数人,代表的却是一种发展方向。
以往经史混同,史学主要表现在成为经学的附庸;如今经学式微,史学却也与经学并 非毫不相干,两者的关系千丝万缕。关键性的转变表现在主观认识上。五四时期的史学 家对于经学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对于经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诸如梁 启超、王国维等人,在五四前后已将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入史学,其论学已少有经学色彩 。梁启超“由经师弟子转变而为新史学家。”(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22页。)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 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 注: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1997年版,第132页。)
再观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家,对于经学,特别是今古文之争,大都能够保持 一种超然的态度,从一个更高的起点看待之,所得的收获反而更有价值。胡适就曾表示 ,“我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顾颉刚以为他作于1922年的《<诗辨妄>序》、《郑 樵著述考》、《郑樵传》等几篇文字“建立了经学革命的旗帜。”(注:顾颉刚:《192 2年2月2日与俞平伯信》,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69页。)一方面,他“始知道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 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以至“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 了”,另一方面,“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注:顾颉刚:《自序》,《古 史辨》第1册,第26、43页。)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 代的顾颉刚,一直在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古文说与今文说的是非异同,避免盲目陷入某一 家说,但却积极地从双方的学说中吸取有用的成份。将经书以及子书摆到与史书平等的 地位,明确地把经学的材料看作是历史材料,不能不说是五四时期史家的一个卓识。顾 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和“古史辨”派的出现,就是史学走出经学羁绊的直接后果。
1921年,吕思勉在《论经学今古文之别》一文中指出:“吾辈今日之目的,则在藉经 以考见古代之事实而已。夫如是,即‘发生今文与古文孰为可信’之问题。予谓皆可信 也,皆不可信也。皆可信者,以托古改制之人,亦必有往昔之事实,以为蓝本,不能凭 空臆造;皆不可信者,以其皆为改制之人所托,而非复古代之信史也。”(注:李永圻 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06页。)吕氏所论已不再纠缠于 今文、古文的孰是孰非,而是涵盖了今古文双方“皆可信皆不可信”,其立意在于史学 ,即“藉经以考见古代之事实。”
50年代,顾颉刚在回顾当时的经史关系时总结道:“窃意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 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惟如 何必使经学消灭,如何必使经学之材料转变为史学之材料,则其中必有一段工作,在此 工作中我辈之责任实重。”他认为经学在当时已到了结束的时候,把原为古史料的经典 ,恢复其古史料的原貌,是史家的重要职责。他接着说,“然清之经学渐走向科学化的 途径,脱离家派之纠缠,则经学遂成古史学,而经学之结束期至矣。特彼辈之转经学为 史学是下意识的,我辈则以意识之力为之,更明朗化耳。”(注:顾颉刚:《顾颉刚读 书笔记》卷4,转引自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 0、11页。)清代学者用考证学的缜密方法研究经学,客观上已经造成了“经学遂成古史 学”的后果,但彼时的“下意识”与五四前后的“以意识之力为之”,性质又有不同, 后者的结果,不仅促成经学的终结,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史学的独立和史学的转型。
吕思勉也同样主张,经学终衰已不可避免,但经学典籍作为“最古之书”,对它的研 究仍然是有意义的。
另一位学者钱玄同所表示的对经学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 ‘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 奴的陋见。”(注: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 2年6月。)五四时期史家对待经学的态度,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三、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与史学对经学的承继
随着经学的走向衰落,在五四前后,史学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人们更愿意把这种 转变看作是史学取代了经学,或者说成是由经入史。但从本质上而言,经学与史学的性 质毕竟不同。正如金景芳教授所言,“经学、史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各有各自的领域 ,各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目的。”(注:金景芳:《经学与史学》,《历 史研究》1984年第1期。)顾颉刚指出,“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 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怀疑的“圣道”和有碍于客观研究的“家派”特征,使其不能成为 “科学”(注: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经学的终结是其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史学作为人 文学科的一支,其过去和未来都是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经学的衰落并不一定意味着史 学必然兴盛,反之,经学的兴盛也不是说史学完全无地位可言。因此,简单地将经学的 兴衰类比等同于史学的沉浮并不恰当。经学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因种种原 因与史学产生了密切关系的一门学问。正是由于中国史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经 学的支配与束缚,所以在经学走向终结之后,其对于史学的影响在短时期里却不会随之 消亡。并且,这种影响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依然值得重视。在五四时期,表面上经学衰落 与史学独立的趋势十分明显,实质上二者的关系并非由经入史般的简单转化。
经学对于史学的客观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时仍是左右中国史学发 展的内在因素之一。就史家个人而言,对待经学的不同观点,既影响到他们的治学旨趣 和治史方法,也影响到他们对经学及相关学术的记述和评价。譬如,范文澜“显然倾向 古文经学,赞同‘六经皆史’说。”“即使到后来,范老的经学史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 ,但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内,仍然对今文经学持否定态度。” (注: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2页。)从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仍不可忽视经学的曾 经存在和仍然发挥潜在作用的客观现象。譬如,有人将现代史学分为史观派和史料派, 较之以阐释微言大义为主要特征的今文经学和以训诂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古文经学,其两 种截然不同的治学路数对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顾颉刚曾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 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其最显著 之一例)。此实存舍难趋易之心,以经学纠纷太多,不易了解,更不易处理也。然此不 可能。盖如不从辨别经学家派入手,结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从家派中求出其条理 ,乃可各还其本来面目。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始可以见古史之真相。所以,这番功夫 虽苦,却不是劳而无功的。惟有做了经学的工作,方知真正古史存在的稀少,同时也知 道现有的古史中经学家学说的丰富。”(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转引自 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第89-90页。)范文澜就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经 学本身已无丝毫发展的可能,古史研究的新道路却由新汉学的成就而供给丰富的材料。”(注: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68页。)刘家 和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经学在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已经走向衰落,中国史学终 于摆脱了经学的思想和义例的束缚。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大变革。当然这种变革并 不排斥我们对于学术史的反省,相反,我们应当分析中国史学与经学关系密切的传统, 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注:刘家和:《史学与经学》,《古代中国与世界》,第216 -217页。)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经学作为传统学术遗产的一部分 ,其有价值的内容,不仅不应当被完全摒弃,反而应当得到继承。
史学是一门与现实、特别是现实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观点 、史学方法都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五四前后传统史学遭到了抨击,走出经学羁 绊的新史学豁然感受到了挣脱束缚后的开阔视野,如期而至的各种西方的思想理论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经学终结后的理论真空。19世纪末传入的进化论,到了五四时期仍 然为多数史家所信奉。不同的是,他们此时更加重视科学对于史学的意义。史学求真、 史学独立无不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目的。“今古文之争,早已成为陈迹,但对于现 代史学界的发展颇有重大的影响。”(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10月。)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汉 学、宋学中辨伪、存疑、考证等方法,被五四时期史家敏锐地抓住,并结合西方的治学 方法,称之为“科学方法”而大加阐发。五四以后的数十年间,历史考证学成为当时史 学研究的主流,与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羁绊、但又在治史方法中有意识地承继治经方 法有很大关系。
至于经学,吕思勉认为,“清儒治经之方法,较诸古人,既最精密;则今后之治经, 亦仍不能无取于是,特当更益之以今日之科学方法耳。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 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希祖)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 开拓之地也。故居今日而言分别今古文,亦只以为治学之一种手段,与问者斤斤争其孰 为孔门真传者,主意又自不同。”(注: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106、10 8页。)抛开今文古文之争,以科学方法治之,其中的意义又不一样。所以周予同说,“ 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注: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 选集》,第622页。)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被人们普遍提及,是由于把“六经”看作 史料,蒙文通进一步强调“经学的精深卓绝处乃在传记、经说,其价值在六经之上。” (注: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版, 第72页。)若再辅以治史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治经其实也就是治史了。
现代史学建立的前提之一就是走出经学的羁绊,用史的观点和方法对待经学,而不是 用经的思想和义例束缚史学。五四以来,史家主观上对于经学的看法已渐平实,但经学 在客观上对于史学的深层次的影响却还时隐时现。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经史关系虽已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仍然是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之一。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