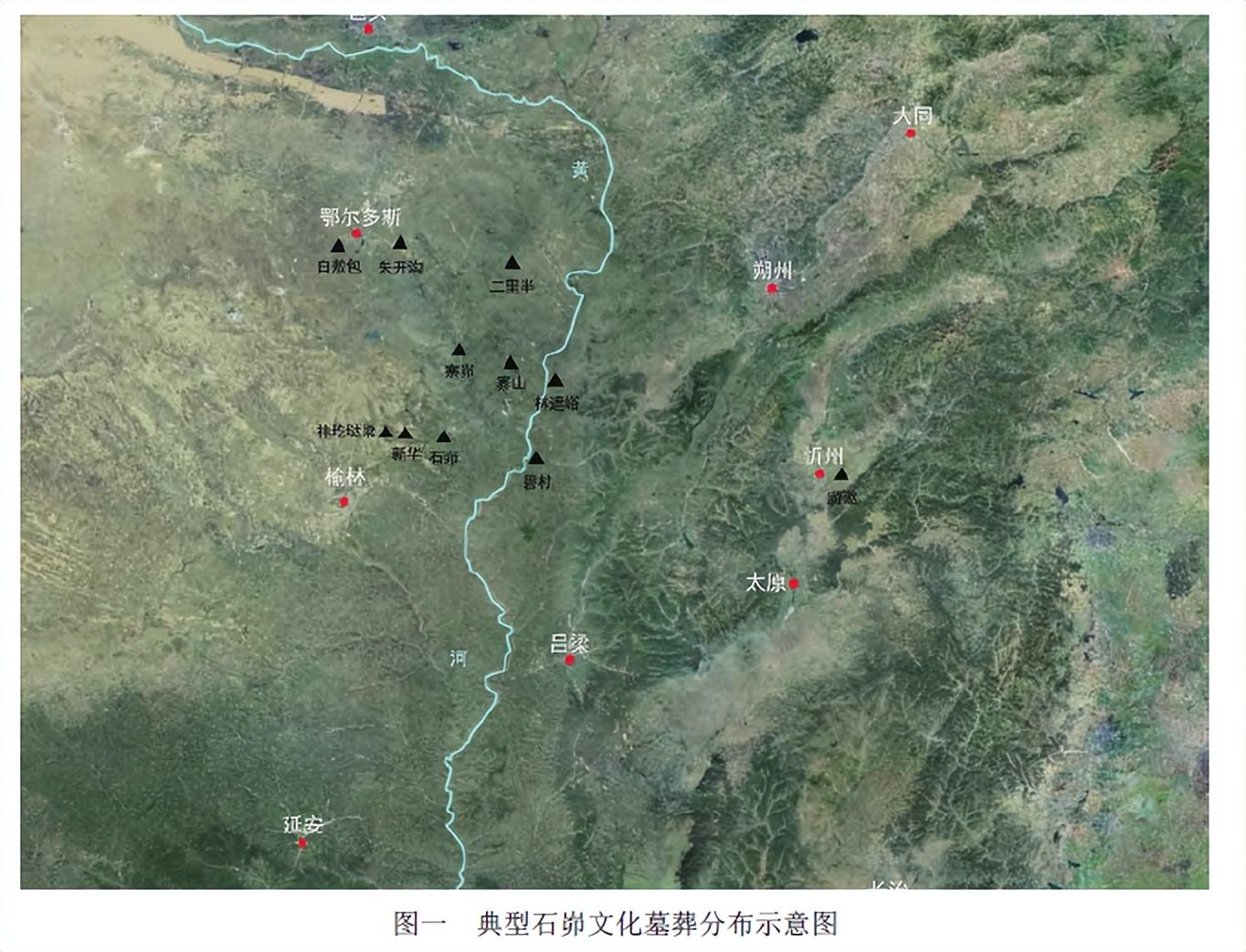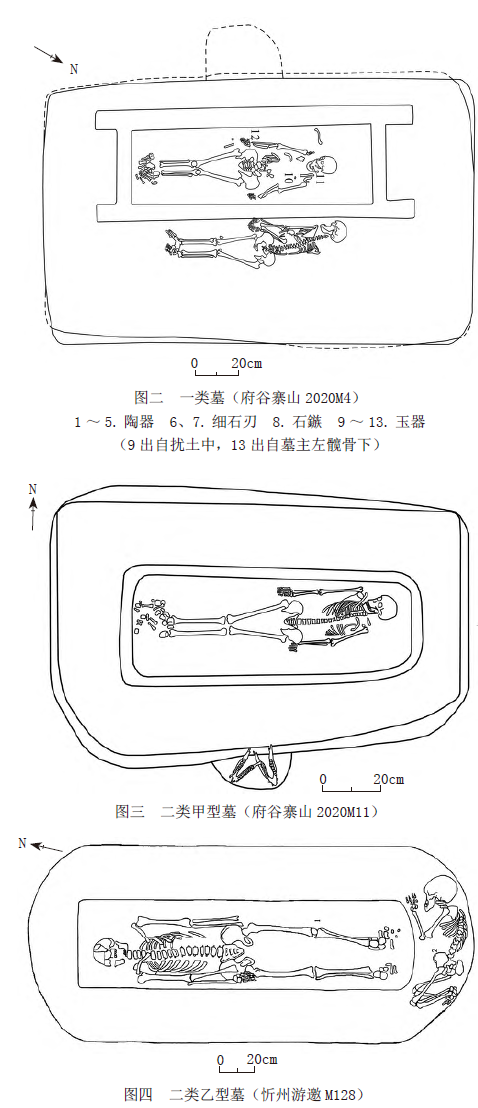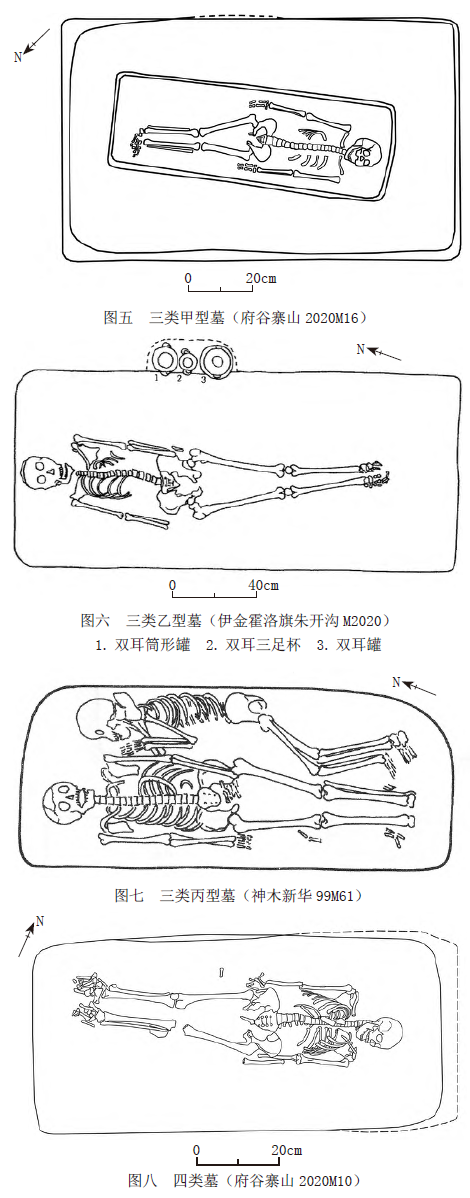王巍: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与展望
一、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回顾
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考古学,其产生、发展、繁荣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其同国际考古学界的联系相伴随,也与国际考古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孕育期(1899~1920年):列强涌入,争先恐后;文物遭掠,民族之殇。
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商代甲骨文,揭开了通过出土遗物系统研究商代历史的序幕。1900年,敦煌藏经洞古代文书等遗物被发现。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现引起了世界关注。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物古迹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垂涎,各国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仗势欺人,争先恐后地派人到中国的新疆、甘肃、内蒙古、东北等地开展探险、考古调查与发掘,这些探险和考古活动虽然使一些遗址和古迹的内涵得以为世人所知,也使国内外知识界开始重视对这些古代遗迹和遗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的获取和研究①。但是,包括敦煌文书、石窟佛造像和壁画在内的大量极为珍贵的文物被劫掠至国外,特别是一些缺乏起码文化良知和道德的外国人为了获取壁画和佛像等文物,不惜采用损毁其周边文物的破坏式获取手段,使大量珍贵文物古迹被损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可谓民族之殇、文明之祸!许多披着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外衣的外国人大肆劫掠中国文物,其罪恶行径令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一般不把外国列强派人来我国从事考古调查和文物劫掠活动纳入中国考古学史的范围。
(二)初创期(1921~1949年):科学发掘,考古开端;学子归来,奠基创业。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协助寻找矿藏。1921年,他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仰韶遗址,随即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陶器、石器等遗物②。这次发掘通常被作为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发端。就在这一时期,第一批留学国外学习考古学的年轻的中国学者(包括李济、梁思永、裴文中等)陆续回国,把他们在国外学到的考古学知识运用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开始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③、河南安阳殷墟④、北京周口店⑤等重要遗址的发掘。这些发掘有的是国外机构出资,由中方学者实施的。而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的发掘则是由中国考古研究机构第一次独立组织实施的,具有特别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李济和梁思永先后主持了殷墟的发掘。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由下至上的地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解决了此前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这几种文化遗存孰早孰晚的问题⑥。以殷墟、周口店、城子崖等一批重要遗址的发掘为代表,中国考古学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各地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断。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转移到四川和云南等大后方,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尽其所能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例如1945年夏鼐在西北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在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的陶片,从地层关系上解决了两者的相对年代问题⑦,就是突出的一例。1930年,梁思永用英文撰写、发表的一篇介绍中国考古学的文章,是当时中国考古学家为数不多的对外介绍中国考古学进展的成果⑧。
(三)初步发展期(1950~1966年):独立发展,体系初建;对外交流,比较稀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新生”。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负责主持和指导全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195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在文化部的领导下,合作举办了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面向全国,培养考古学的专门人才。梁思永、夏鼐、裴文中等著名考古学家领导了培训班的教学活动。前后四期的培训班为新中国考古工作培养了数以百计的考古专业人员。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中国各地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西周的都邑丰镐、汉唐时期的都城长安和洛阳等古代都城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各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的轮廓逐步清晰,在一些地区,开始初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序列。
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很少。据《夏鼐日记》的记载,这一时期,他每年仅有数次接待或参加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其中有一部分来访者还不是考古学者。1957年5月,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接待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接见了代表团成员,足见对该代表团来访的重视和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合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朝鲜联合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在辽东半岛南部发掘了岗上、楼上等青铜时代遗址;在黑龙江宁安县,发掘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遗址和墓葬。这次合作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外国考古机构合作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发掘。
(四)基本停滞期(1967~1976年):考古工作,基本中断;重要发现,偶有所见;对外交流,极为稀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冲击。考古学的发展同样受到干扰,各地的考古工作基本上限于停顿,大批考古工作者或“下放”到农村,或在单位参加“运动”。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等。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交流基本上中断。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级或省级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极少数考古学家,偶有机会与外国考古学者进行有限的交流,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考古学。此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帮助阿尔巴尼亚修复羊皮书是为数不多的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对外合作项目。
(五)全面恢复期(1977~1989年):考古工作,全面恢复;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人才培养,形成规模;对外交流,逐渐活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因“十年动乱”而陷于停滞的中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各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在中国考古学领域表现得十分充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各省区内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开始主要由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独立承担。多所高等院校相继创办了考古专业,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新三届”(七七、七八、七九级)大学生以及此后几届的学生们得以比较系统地学习考古学知识,并积极学习外语,为日后开展与国外考古学同行的交流打下了基础。这几批大学生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加入,极大地缓解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考古队伍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局面。目前,在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大学学习考古学,很多还有国外留学研修经历。
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大量涌现,彭头山、牛河梁、良渚反山与瑶山墓地、陶寺墓地、三星堆祭祀坑、新干商代大墓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重要的考古发现,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格局和文明进程的轮廓逐渐清晰。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开始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中国考古学亦然。1982年,夏鼐率领中国考古学家代表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商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派出的首个完全由考古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可以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登上国际学术舞台的代表。
1983年在北京和西安召开的、有12个国家的学者参加的“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是在中国首次承办的国际考古学的会议,标志着中国考古学重新回到国际考古学的大家庭之中,使外国考古学者得以近距离地了解中国考古学。我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夏天,夏鼐先生陪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参观我正在发掘的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贵族墓地的情景。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考古学家应邀到国外进行学术访问逐渐增多。例如夏鼐先生和王仲殊先生都曾应邀到美国和日本访问,并做学术讲演,介绍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夏鼐先生在日本所做的学术讲演,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出版⑨。王仲殊先生在美国所做的学术讲演,以《汉代文明》(Han civilization)和《汉代考古学概说》为题,先后在美国和中国出版⑩。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和外国互派考古学留学生。以北京大学为首的我国各高校先后接收了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考古学留学生。我国也开始派遣经历了较为系统的田野考古训练,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年轻考古学者到欧美、日本等地留学和研修。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成批的“走出去”留学,使他们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外国考古学界的新理念、新方法。其中绝大多数学成回到国内后,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栋梁,在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这一阶段中外考古学界的交流,不能不着重提到的是美籍华人、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张光直先生。张光直教授身在海外,一直心系祖国。我国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就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六场学术讲座,使得与国外隔绝多年的中国大陆学者如沐春风,得以了解国际考古学界近数十年的发展变化以及最新的学术动态,他的讲演内容后来汇编成《考古学专题六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1),至今仍是考古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六)成熟期(1990~2004年):考古体系,日趋成熟;国际交流,显著发展;中外合作,硕果累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考古学日益成熟。绝大多数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逐渐完整。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古国、方国、帝国理论,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逐渐深入人心。中华史前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研究课题逐步开展并取得了突出成果。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考古学国际化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
国家文物局于199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使我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合作有了明确的方针。此后,中国考古界的国际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于1993年开始正式实施,持续了数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较早开始进行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揭开了中外合作在中国开展考古发掘的序幕。国家级和一些省级考古机构以及高等院校,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考古学者进行了包括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项目。合作研究涉及的地域相当广阔,遍及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合作研究的时代范围也相当宽泛,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和铁器时代的汉、唐、宋、元、明时期;合作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史前聚落、古代宫殿、池苑、佛寺、墓地、农业、手工业、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与环境的关系、铜和盐等重要资源的供给、丝绸之路古代遗迹的研究等。在国家的统筹规划和管理之下进行的这些国际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深化了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缩小了我们和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考古学的差距,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合作研究,中国考古学家得以亲身了解国外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外国考古学家也通过开始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了解了中国考古学家们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这些都为中国考古学更好地融入国际考古学的大家庭打下了基础。
在中外合作研究中,中外考古机构合作在中国各地开展的大规模区域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值得特别提及的。较早开展中外合作区域调查的是1995年山东大学与美国学者开展的鲁东南地区区域考古调查(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河南安阳殷墟开展的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13),直接导致了洹北商城的发现。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等合作开展的伊洛河流域聚落考古调查(14),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共同与美国的考古机构合作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聚落调查(15)等,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通过这些合作开展的区域调查,使中国考古工作者掌握了区域聚落考古调查的理念和方法,对聚落考古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得到深化;从注重对一个遗址内部各类遗迹的分布状况的研究,发展到在此基础上对某一区域内不同聚落或聚落群之间关系及其所反映社会结构的研究。
在大量的中外合作研究项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投入经费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开展的前后历时15年的合作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对汉长安城桂宫(16)、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17)、汉魏洛阳城宫城等都城重要宫殿遗址进行了发掘,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中日两国考古学界的交流,也为东亚地区古代城市的发展及其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通过与国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使中国考古学家开阔了眼界,得以掌握并逐渐熟练地运用国际考古学界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也使国际考古学界得以对中国考古学的近况有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了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国内开展考古工作经费的紧张,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
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展,中国学术界对国际考古学界的了解日益增多。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以及诸多外国考古学论著的编译出版,使中国考古学者得以了解几十年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要流派,诸如“新考古学”、“社会考古学”、聚落考古”等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围绕如何对待这些理论和方法,它们是否适合于中国?在中国考古学界曾引起了一场争论。但最终争论的双方实际上达成了共识,任何理论与方法都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去加以检验和创造性地运用。
这一时期,在国内举办了越来越多的围绕某一考古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或某一遗址发掘成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多的外国考古学家通过来华参加学术会议和参观考古发掘现场,直接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对中国的考古学有了直接的了解。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家意识到不能仅仅知道本国的考古学,而应当知己知彼,了解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并研究古代中国与其他区域古代文化的交流。王仲殊、乌恩、林沄等许多考古学家致力于古代中国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和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研究,并取得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使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只知自己、不知他人的状况有所改变。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展,中国考古学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请进来”,还日益重视“走出去”。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考古学家参加国际学术界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应邀组队赴香港参加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内地考古机构赴港澳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序幕。此后,国家级和多个省区的考古机构和大学相继赴香港和澳门开展考古工作。通过香港、澳门这一特殊的窗口,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大陆考古工作者的风貌。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者越来越重视外国同行们在境外从事的考古工作,并试图以各种方式直接了解国外同行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方法。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10位青年学者赴德国,参加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体验了德国同行开展考古工作的方法。虽然这次“走出去”只是参加德国同行的发掘,带有体验的性质,但这毕竟是中国考古机构第一次组队赴国外参加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2004年夏季,吉林大学组队赴俄罗斯阿穆尔州,与俄罗斯考古机构联合发掘了特罗伊茨基唐代靺鞨墓地,清理墓葬30座,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金属器(18)。虽然这次发掘仅仅历时一个多月,发掘面积也只有250平方米,但这毕竟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真正“走出去”,派队赴国外开展合作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中具有开端意义。
(七)蓬勃发展期(2005年以来):考古体系,日臻完善;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赴外考古,逐渐增加。
近10余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对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投入的增加,使中国考古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多学科结合深入人心。包括科学精密测年、DNA技术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效果显著。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与外国研究机构的合作发掘仍在国内继续开展,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对汉魏洛阳城宫城的合作发掘等,但数量大幅度减少。这一阶段中国考古机构与国外考古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合作,不再单纯以合作发掘为依托,而是转向主要以合作研究项目为主。
这一阶段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派队赴国外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开始,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等考古机构合作,实施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一直持续至今。先后发掘了回鹘的方形墓园和契丹及柔然的墓地,填补了蒙古高原地区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诸多空白(19)。此项发掘也是在迄今中国赴国外发掘的诸项目中,开始时间较早,持续时间最长的。2006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的考古机构合作,对越南北部永福省义力遗址进行了为期数年的合作发掘(20)。
2006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以及2016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送来了东风。各考古文博单位认真领会、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奔赴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开展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了热潮。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时期。
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对肯尼亚东部沿海地区的遗址和近海的水下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中国明代的瓷器等遗存,极有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21)。湖南省考古研究所2014年以来在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寺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了解了该组建筑的布局与结构(22)。从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费尔干纳盆地的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修建年代相当于我国汉代、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之一,很有可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古国——大宛国的遗存(23)。西北大学近年来在中亚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24),并于2015年对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中部的古代墓葬进行发掘,出土了一批随葬品。南京大学于2015年对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古代冶铜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25),并在伊朗开展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工作。故宫博物院对印度喀拉拉邦沿海地区遗址进行了调查,对奎隆港、帕特南遗址出土的中国文物进行了整理(26),并将实施对奎隆港的发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局及哈佛大学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掘了一处保存基本完整的玛雅文明高等级建筑群址和高级贵族墓葬(27)。这项发掘是中国考古机构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存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界“走出去”的决心和实力。
我国文物保护队伍赴国外开展工作,要比赴国外考古工作开始得更早。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从1996年便开始了对柬埔寨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程,一直持续至今(28)。该单位还对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希瓦古城、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蒙古国科伦尔巴的古塔、缅甸蒲甘佛塔等古迹进行了保护修复,他们的精湛技艺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国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考古文博机构在境外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古迹维修涉及的国家已达10多个,开展工作的区域不仅包括与我国相邻的北亚地区俄罗斯、蒙古国,中亚地区诸国,西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国,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还包括距中国万里之遥的中美洲洪都拉斯和非洲肯尼亚等国。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和印度对埃及文明和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并进行中华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的项目获准立项,正在积极筹划派队伍去埃及和印度实施合作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16年秋季在北京举办了埃及考古系列讲座,邀请世界著名的从事埃及考古的权威专家做报告,为即将开展的赴埃及考古进行知识储备和人才培训。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进展,还表现在参与国际考古学界的学术研究活动方面。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中国考古学家参加已经是司空见惯,中国考古学家组织专场学术研讨也已是“家常便饭”,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最能够体现中国考古学国际地位提高的是分别于2013年8月和2015年12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和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局和上海大学等单位承办的国际学术论坛。
世界考古论坛的宗旨是:(1)加强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为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学者增进相互了解、开展合作创造条件,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展;(2)提升全世界范围内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水平,促进对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时代文化和社会面貌的了解和历史进程的认识;(3)借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持,以及城市化、全球化、人口迁徙和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4)促进考古学与公众的互动,提升公众对考古学研究之重要性的关注和认同,有效保护全世界的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
世界考古论坛的主要内容有三项:(1)评选前两年度世界范围内的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论坛聘请世界各国考古学及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约200位知名学者组成咨询委员会,40位世界著名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多为世界各大洲考古研究的学术权威,其中大部分为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类似机构的成员,包括剑桥大学科林·伦福儒勋爵、斯坦福大学伊恩·霍德教授、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查尔斯·海曼教授等。评审委员来自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埃及、南非、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希腊、以色列等16个国家;从他们主要研究的区域来看,包括非洲4人,北美洲3人,中美洲3人,南美洲2人,欧洲2人,近东、西亚和北非6人,地中海、南欧2人,欧亚和中亚3人,太平洋、东南亚4人,南亚2人,东亚9人。咨询委员向论坛推荐过去两年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评审委员从各约50项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题名中投票选出各10项作为论坛获奖项目。(2)每届论坛设置一个主题,邀请本领域的世界顶级学者围绕该主题发表学术讲演。首届论坛的主题是“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是“文化交流与文化多样性的考古学探索”。(3)邀请数位世界知名考古学家面向公众举办公共考古讲座。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每届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约80位评审委员和咨询委员前来参加。中国作为论坛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评审委员和咨询委员的聘请、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的评审、论坛主题的确定、主题论坛和公共考古论坛主讲者的遴选等,都是由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论坛秘书处负责与各国的评审委员商议并组织实施,当选为论坛评审委员和咨询委员的中国学者也成为论坛秘书处的后盾。
二、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展望
(一)中国考古学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1)缺乏整体谋划和组织,各个单位的“走出去”都是各自为战,缺乏整体的谋划和布局;(2)缺乏稳定的经费支持;(3)还存在对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模糊认识。
虽然中国多个考古机构在实践着“走出去”,但无论是在学界内部还是社会上,对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必要性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有些人认为,中国考古学自己国内的考古工作还做不过来,何必还要分散精力去国外考古。还有些人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文物保护的工作经费短缺,何必还要花经费用于国外开展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是大势所趋,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一直与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接受外来的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如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等都是在大约距今5000~4500年间从西亚经中亚地区传入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联动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了解外国的历史和考古学资料,就难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在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特质的时候,由于不了解其他古代文明,没有开展相互比较的基础,也使我们认识自身特质时遇到严重困难。因此,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需要。
由于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和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化发挥的作用,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有利条件
1.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政府大力倡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增强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2016年6月22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习近平主席专门接见了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西北大学的学者,他还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工作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出色工作。
2.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 对于中国考古“走出去”,国家各个部委都给以了大力支持。商务部近年已经对在蒙古和肯尼亚的发掘给以了经费支持,缓解了相关单位涉外考古经费方面的困难。2017年夏季,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了涉外考古工作汇报会,已经开展涉外考古的单位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和成果,交流了经验,并就今后的涉外考古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与会的各个部委的代表经过认真讨论,达成共识,今后将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涉外考古,国家文物局将对各个单位的涉外考古工作进行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导。
3.科研机构和学者参与的热情高涨 已开展的涉外考古所取得的成绩,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使全国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倍受鼓舞,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加入到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洪流之中。201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希望在加强国内各考古机构“走出去”的沟通和协调方面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预见,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迎来一个新的高潮。会有更多的中国考古机构加入到“走出去”的队伍之中,在更多的国家可以看到中国考古队伍的身影,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将会得到不断的提高。中国考古学家将会更多地活跃在国际舞台,更好地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0001
- 0000
- 0001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