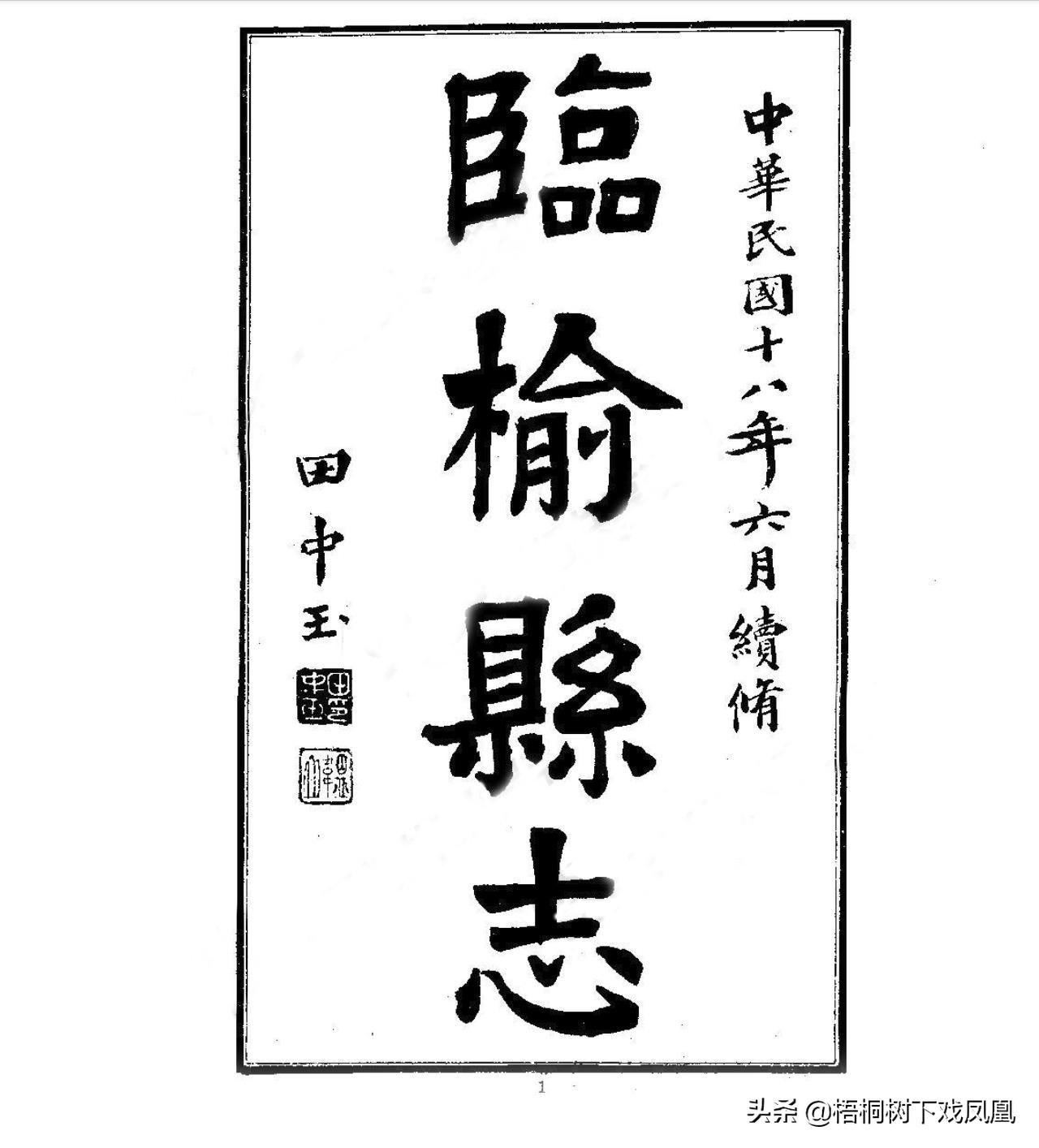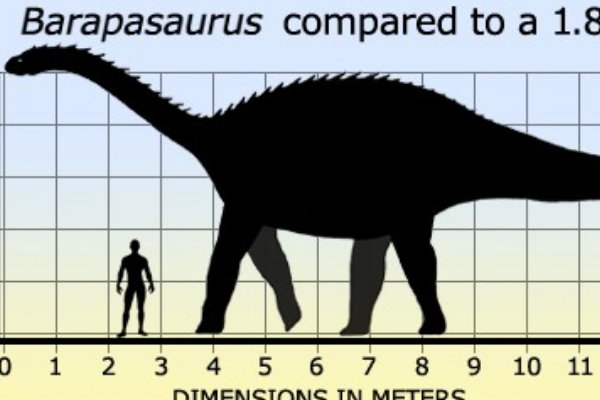周振鹤: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近代文献述略
引言
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历来重两头,一头是古籍版本目录研究,一头是现当代出版物研究,而对夹在古代与现代当中的近代文献则研究相当薄弱。近代文献甚至一度处于目录学不讲、藏书家不重、图书馆不收的境地②。然而近代正是传统古籍向现当代文献变化的重要过渡阶段,无论从出版物的内容、形式、种类以及印刷方式、印刷技术、出版过程、出版理念与资本运作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忽略或轻视这一时段的印刷出版史研究不但将使整个中国印刷出版史显得残缺不全,而且实际上无法理解中国印刷出版事业的现代化过程。本文试图从近代文献这个概念出发,分析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以及近代书籍与报刊的分类,强调近代文献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则是从目录学的角度指出普查与编纂近代文献目录的急迫性与重要性,为书写有深度的近代印刷出版史打下基础。
一、传统图书分类的困境与近代文献的概念
中国的古代典籍自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四部分类的思路,自《隋书·经籍志》始,即明确实行四部分类的方式,将所有传统及当时的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个分类不能说很合理,因为前三种是以书籍的内容而分,最后一种是以文章编排方式来分。但这个分类行之一千余年,从雕板印刷术发明之前一直到雕板印刷术极其鼎盛时期均可从容应对,即便晚明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华撰写及翻译的西方神学与科学的著作,也以传统的线装书形式出版,并多能纳入子部类的各分目当中去,而不致发生很大的困难。但近代以来印刷出版的文献却出现了无论在书籍形式上,印刷方法上以及内容分类上无法与传统图书分类相榫接的情况。
首先是内容上的不纯粹,使得经史子三部都无法容纳,例如期刊报纸一类,就难以归类。其次印刷方式已经从雕板印刷与木活字(极少数是泥活字或其他材质的活字)发展到石印与铅活字形式,同时书籍的装订形式也开始有洋装方式(包括平装与精装),文献载体也从单一的书册形式变成报纸的单张或多张的不装订形式。出版周期的概念也同时出现,过去典籍的出版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但近代以来则有连续出版物的形式行世。再者,这些出版物还有以外文形式或中外文并存的形式出现(古代文献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例外),这一切使得原来的四部分类显得捉襟见肘,起先的弥补的方法,是在四部之外,另加一个新学部,以包容近代与西方文化有关的文献。另外在出版形式上也加了一个丛书部,以包容将多部单独的书籍合在一起出版的新思路。同时也有一些个人或单位打破了旧的分类法,编制了如《西学书目表》、《古越藏书楼书目》、《南洋中学藏书目》等目录,打破了四部分类的传统,但上述补苴的方式有时只能是削足适履,方凿圆枘,或只是局部可行,并不能与近代新型文献的大量出现完全合宜。因此新的图书分类法很快就在清末产生,但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的目的只是要由此引出一个近代文献的概念。
所谓近代文献并不是学术界目前已经存在共识的一个学术概念,正像“古籍”一词至今亦尚未有严格的定义一样③。近代文献大致是指在近代产生的,在印刷出版方式与古代传统典籍有别,或者虽然还是以传统形式出版,而内容则完全出新的文献。这样一些文献由于在内容上与传统文化有本质的不同,甚至有些被视为离经叛道,同时在印刷出版方面,商业性的利益考量超过艺术鉴赏性的需求,再加上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而使出版数量大幅度增加,结果为时人所不重,以致今日有些距今不过百年的文献成为极为罕见的境况④,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编辑全国善本古籍目录,甚至正在编辑全国古籍目录,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出版总书目也早已问世,但于近代图书目录却付之阙如,尤其是1800—1900年间的图书没有完整目录可言。然而近代文献在当今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重要依据,在一些重要图书馆,近代文献已经被视为与珍稀文献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将近代文献作为一项学术概念予以提出,并加以重视。以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编成全国近代文献总目录,将其作为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以便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
近代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印刷出版史上也可视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如下数端:一是文献范畴的扩大,其中以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的登场为最大的亮点;一是印刷术的革命,石印技术的产生与照相排版的出现以及铅印技术的推广;一是印刷文献的动力由人力到机器的转变;一是出版机构由官刻、私刻、坊刻等形式的小规模生产转变为公司经营的大规模的商业出版。这几方面的变迁在具体而微的方面都有过不少研究,尤其是对印刷技术的研究更是印刷出版史的重镇,但对于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对近代文献作一概观式的研究,则一直存在空白。由于对近代文献尚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因此以下我们不妨从时间性、内容上以及印刷出版特点方面来进行初步的解析。
二、近代文献的时间段概念
对近代的时间段概念目前没有统一的认识。传统上以鸦片战争为始,因为自此以后国门大开,出现过去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但若深究中国自身发生的变化以及外来影响之始,有人以为可以将近代上伸到从19世纪初年起。在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之末的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双方实行自由贸易,虽然这一使命宣告失败,但该使团却将中国的虚实探明,为以后的侵华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接着在世纪之初的1807年,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入华,开启了另一轮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虽然初时影响较弱,却具有标志性作用。至1815年,有两件与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有关的事情同时出现,一是在澳门开始出版马礼逊的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的第一部分《字典》的第一卷,这部词典是第一部中英对照词典,也是第二部正式印刷出版的中文与欧洲语言的对照词典⑤。另一是在马六甲出版第一种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后者不在中国本土出版,但对象却是华人,包括在东南亚以及在大陆的中文读者。因此如果我们以印刷出版史为本位,不妨可以将这一年当成近代文献产生的开始。至于下限,如果按传统的说法,历史时期的近代结束于1919年,这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但如果仍以印刷出版史为准,则不妨以新文化运动开始,即以《青年》(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为标志创刊的1915年为止,亦即从《新青年》出刊之后,大致可以表明另一个出版时代的起始。所谓近代文献的范围正在1815—1915的百年之间,或者也可以大致定为1800—1919年间。
当然也有将近代下限延至1949年者,如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已经有一个近代文献联合目录,时间段为1900—1949年,共收2万多种。虽然这个下限亦可自成一说,但上限则显然断得太晚。原因不在别的,正表明1900年以前的近代文献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研究。即使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重镇,其建馆伊始至1911年间的出版目录至今还留下许多空白⑥,遑论其他。我们今天于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籍与报刊大概有个基本的目录,尽管还很不完善,但于1900年以来的晚清出版物则没有完整的目录可以检索,在这方面甚至还远不如对古代典籍的了解。至于专注于近代出版物的版本学与目录学著作更是几乎不见,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印刷出版史中的近代文献作为一个专门的重点来研究。
三、近代文献基本范畴的扩展
从历史研究的眼光看来,凡触目者无一不是文献。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宽,文献的概念与范围也不断扩大。可以大致地说,从鸿文巨册到笔记便条,凡是形成文字记录的无非文献。进一步而言,则凡是形成图像纪录的也是文献。这其中可以包括正史、实录、起居注、奏章以及一切的公私著述,如档案、如碑铭墓志、如函札日记、如宗教经典、如家谱稗乘、如杂志报纸、如闱墨硃卷、如账本地契、鱼鳞图册、地图照片、日历年画、词典教材、广告招贴、唱本歌词、邮件请柬(莫理循甚至保留袁世凯请客的菜单),不管刊刻复制印刷出版发行与否,无一不可作为文献使用。正如韩愈所比喻的:牛勃马溲,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文献的载体则从甲骨、吉金、玉帛、简牍、纸张,直到今天的电子形式。文献一般应该有文字,但在当代范围扩大以后,以图证史功能明显重要,现在也已经归入文献类。
近代文献的基本范畴虽与古代文献相比有许多后者所无的特点,前面已经提及,举其大者有两方面,一是文献形式的增多,除了传统的图籍以外,产生了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其次是文献的载体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汉字(以及少数的满、蒙、藏等文字)外,出现了欧洲文字与汉字并存或单独以欧洲文字及日文等其他文字印刷的出版物⑦。近代文献当然还有其他别于传统文献之处,但就以这两项特征最重要也最显著。
中国历史上非无连续出版物,如邸钞、塘报、京报都是,但近代化的,具有社会新闻与科学艺术报道的定期出版物则到晚清才出现,正是新教传教士将这一形式引进中国,因这种文献形式在西方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当然起初引进时,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是先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而后才进入广州,北上上海,最终并分成报纸与期刊两大类,而进入现代。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马礼逊等人亦无法将monthly或magazine译成简易的中文对照词,如月刊或杂志之类,而只能称之为“每月统纪传”。而且由于起先报纸、期刊在出版形式上没有根本的分别,名称叫做“报”的其实可能是杂志,如晚清流行的多种白话报即是如此,以至于迟至1929年,戈公振写作第一部中国新闻史时,还不得不将其称作《中国报学史》,以“报”来包揽报纸与杂志两大类连续出版物。
外文文献与中外混合文献的出现。在中国,将中文与西文并处于一种正式出版印刷的文献中,应该是由中西语言对照词典最先实现的。虽然1813年小德经所编纂的汉法拉对照词典开了先河,那并不在中国出版。两年后,马礼逊的《华英词典》在澳门开始出版可算是在华出版的最早中外混合文献。完全以西文出版的报纸杂志应以1827年《Canton Register》(《广东纪录报》)为始,直到1851年在上海出版《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已经相当成熟了。中文报纸出版晚于期刊,要迟至1850年才出现,起初多是附在英文报纸后面出版的,香港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如此,《上海新报》亦如此。
中外混合文献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形式,即坊间所刻的“红毛番话”一类洋泾浜英语或“澳门番语”一类洋泾浜葡萄牙语读本,虽然内容的实质是英文或葡萄牙文与中文的对照,但其中并没有西文原词形,而是以中文的谐音形式来代表。这一类文献过去从未被注意,更未被纳入学术研究范畴,现在则是珍稀文献了。
正式的系统的文献之外的零星散碎的非正式文献,也应该引起重视。例如广告海报之类。
虽然今天近代的报刊内容已被认识到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好材料,但对其中的广告注意者仍然不多。十几年前影印全套《申报》时,据说有人为了节省篇幅,打算不印广告。好在这个提议未被采纳,而且也实行不了(大量广告非专页),否则就要损失许多有用史料了。大而言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各派政治势力刊登的成立某组织以及召开各种大会的广告,活生生地显示了当时的政治场景;小而言之,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私人设英语学塾者不在少数,由他们刊登的招生广告便约略可睹。当然也有始终不知道可以广告来作为史料的例子,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目录的编纂至今离完善还很遥远,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从广告中去寻找线索。商务早期的出版物现已佚散严重,不要期望有搜集到全部原件的可能,因此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新书广告,与各种现存书籍前后所附的广告便是重要的史料。可惜这些材料未被利用过,由于一般人所看的《东方杂志》都是删去了彩页广告的影印本,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该杂志有那些广告存在。
四、近代文献在内容方面的出新
近代形成的文献,当然有相当数量是对古代文献的翻刻重印,还有近代学者阐释古代经典而形成的文献。这点毋庸赘述,也不是我们要谈的内容。近代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就是其内容的出新。这些出新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
中国在前近代没有发展出科学观念来,自晚明以来,西方科学通过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兴趣。传教士的本意是要传教,但必须借助传播科学为工具或先导,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说取得了成功,至少我以为晚明的徐光启、李之藻与杨廷筠的皈依天主教是与震惊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有密切关系的。也因此,新教传教士采用同样的策略,在传教的同时也要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即使在科学内容相对较少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可以看到,更不用说后来科技成份较多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以及《六合丛谈》等早期期刊了。对于这些期刊杂志对国人的影响,至今并无专门的研究,因为资料太少,但却也不是无迹可寻。我在早稻田大学找到的《西域水道记》的徐松自笔修订本上就注意到夹有一张字条,上写“《每月统记传》谓生于陈宣帝太建元年……”云云⑧,使我大为吃惊。如果说上述杂志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话,那么,到了傅兰雅受聘在江南造船厂译学馆专门从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时,这个影响就相当大了。过去对近代文献中的科技资料注意得并不够,例如通常都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记录为中国最早的气象资料,但其实在早期英文报纸中就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气象记录了。
二是中西方语言的接触资料。晚明天主教传教士在中西语言接触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既编写了大量西方语言与汉语的对照词典,也写了许多汉语语法著作,但前者无一单独出版成书,后者则虽然有专门著作,但却不在中国境内出版。大量的中西语言对照辞典在1815年之后出现,而且不但有官话,而且有各地方言与西文的对照辞典。与此同时,西方人还对汉语方言的语音、语法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层出不穷。在正规外国语言著作或教本之外,中外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洋泾浜语言,也有多种坊间刻本,而且被大量翻刻,这方面在过去也受到忽视。
三是西方人文科学著作的引进。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从来不觉得有引进西方文化的需要,充其量只会引进西方的“奇技淫巧”与声光化电。但在近代中国对列强屡战屡败,甚至败于日本人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怀疑日渐加深,于是在19世纪末西方人文科学的引进成为近代文献重要的内容。二十世纪初甚至经由日本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不需等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四是国人本身的新式著述。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之一是“述而不作”,所尊崇的只是古代经典,历代以来的学者多只是祖述阐释前圣之著作,而鲜有自己的创造,也少有条件接触西方经典。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则是取源于西方的地理学著作,加以自己的创意,不但在国内,而且在邻国日本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自此以后,此类著作渐次增多,至于十九二十世纪之际而大盛。
五是国人对传统经典阐释的通俗化。传统经典均用文言书写出版,其中的特殊情况也有,如为了让“愚夫愚妇”能了解皇帝的教导,对康熙的上谕十六条与雍正的《圣谕广训》有不少人用方言俚语作过阐释。到了近代时期,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也这样做过,一些士人也开始用白话来解释经典,尤以解释四书,尤其以《论语》最为突出。这些白话文献是研究中国汉语史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源,实不待胡适等人于新文化运动才提倡。
六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西洋文学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以至后来梁启超有小说革命这样的话头产生。第一篇西洋小说的翻译是《昕夕闲谈》,此后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清末而有欧美名家小说丛刊这样的系列翻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再后则有说部丛书、林译小说等等。
七是汉语方言文献的大量涌现。此点与传教士来华关系极大。汉语方言种类多,彼此差异很大,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对汉语方言进行认真记录与深入研究,既形成不可多得的文献本身,又从域外的视角以及西方语言的角度进行学理方面的研究,写成数量颇夥的专门论著,同时又利用方言翻译圣经与书写布道著作,结果在近代形成一大批难得的汉语方言文献。
还可以举出更多内容,这些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例证而已。近代文献在中国文献史上有太多的第一,过去一直被人所忽视,值得我们去进行文献意义上的考古发掘。
五、近代文献对传统印刷出版技术的传袭与革新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雕板印刷技术长期被沿用,即使传教士出版的许多刊物,从1810年代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1870年代的《小孩月报》都是使用传统的印刷工艺技术。即便在上海开设的中国第一所近代化印刷技术的墨海书馆,也仍然用雕板印刷,只不过不用人工刷印,而以畜力带动机器印刷。由于雕板印刷历史久远,刻印技术高超,甚至连西文字母与科技插图最初也照用不误。但毕竟西方的先进印刷制板技术更加有利于西方文字与艺术、科技图画的传真,所以很快得到风行,而且是从上海开始进行了印刷革命。至19世纪70年代前后,上海的印刷技术在亚洲显然处于第一流的地位,连日本的《和英语林集成》(按:即日英词典)最初的版本都是由上海美华书馆承印的。现在这些内容虽新而印刷仍然传统以及初期的内容与印刷皆新的近代文献都属于比较罕见的出版物了。中国的传统印刷技术还有由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但应用得不如雕板普遍。这一技术后来雅称为聚珍版,近代京师同文馆有过一些重要的出版物都以此种形式行世,如《万国公法》、《法国律例》、《英文举隅》等。
石印技术在1843年后进入上海,先由传教士印刷宗教宣传品,后1874年土山湾印刷普通读物。节省劳动降低成本减少错误,开本任意,图像制作与西文再现容易。自清末到民国,我国出现的大、小石印书局多达百余家,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1874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始设石印印刷部,开始印制教会宣传品;1876年,创设申报馆的英国人E.美查在上海开设了点石斋石印局,开始石印图书和期刊,出版了《考正字汇》、《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随后中国人徐裕子、徐润等于1881年先后开设了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专印古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此后李盛铎创办的蜚英馆、凌陛卿开设的鸿文书局等许多石印书局也相继出现。石印在当时一度十分时髦,内页要写上仿西法石印的字样,以广招徕。但在传统的藏书家看来这种石印本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的,并且是学术性的研究,同时图书馆对此类图书的收集也从不措意,以致当时印刷数量颇大的一些石印本书籍,现在有时也难觅踪影。这一方面尤其要提醒近代文献的研究者予以注意。
六、近代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重要性是随着人们的认识提高的,如正史上五行志的遭际即是如此。过去正史虽被当成最重要的史料,但其实并非正史内的所有内容都被充分利用,如其中的五行志,就因为借灾异现象来解释人事祸福、政治变迁,历来为史家所不齿,曾被梁启超讥笑为“邻猫生子”式的史料。但今天灾害史的研究兴起,只要除去那些天人感应的无稽之谈,所有气象灾害、天候异常的记录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不但可以作为数千年气象史的基础,而且可以为预测将来的长时段的天气趋向作参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编制《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和元代以前气象资料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些史料。
对于近代文献的认识也一样要经过一段长时间。当然对于近代史研究者而言,近代文献一直是受到重视的,但也不见得所有近代文献都能受到青睐,当近代史研究只注重于政治史、军事史时,所体现出来的就是认真整理最主要与最常见的史料而成为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十一个专题,从《鸦片战争》直至《北洋军阀》。在经济史方面也有《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近代中外贸易史资料》等一系列可资利用的文献汇编出现。在思想史方面也勉强见得有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那样的汇编,但如果从与社会史、文化史相关方面而言,恐怕还有大量近代文献未受到重视,以下只能以举三方面的例子作简单地说明。
近代一大批与语言相关的文献过去从未引起注意。直到上一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研究中国近代学术用语的形成以及更为广泛的中西语言接触课题的出现,这些文献才受到广泛的注意。但究其实,不但是研究中外语言接触史,而且研究中国语言也需要域外学人所撰写的有关文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用西方近代的语言学来写中国语言学,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许多方言难以全用汉字表达,于是用罗马字记音的辞典或专门的方言著作,以及方言圣经,方言传教报刊就成了极为重要的汉语方言研究资料。这样的资料数量相当大,值得加以收集与研究。另外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与研究,近代文献里也有不少,足以填补多项空白。
而即使对于政治史与外交史而言,近代文献的开发力度也是不够的。比如说,外交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但于外国的档案利用却相当薄弱。最近美国外交档案解密数量不小,广西师范大学已经影印出版了近代中美来往照会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档案等数大套文献,于近代中美外交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对近代外交档案的保存情况并不理想,比较完整的是外务部的档案,但已经迟至二十世纪以来了,而国外的保留情况较佳,因此除了应该重视国内的近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利用之外,对国外所保存的与中国有关的近代文献也应该积极搜求。我自己有个经验,即多次到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读档案,因而对近现代中国新闻史有些本土以外的重要补充知识。因此海外近代文献的开发利用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各国的外交史料馆或档案馆应被视为中国近代文献的一个重要渊薮,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更进一步而言,即使从来未被看好的近代的闱墨、硃卷一类材料,其实也大有用途,从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一般士人思想演进的轨迹。光绪庚子年改革后的乡试与会试的第二场考的是各国政治艺学策,每场考试由主考官出五道问策,而由考生作答策。两科会试共10道问策,两科乡试各省合共170道问策,由问策体现出来的主考官员的世界与中国的意象是否真正反映了历史真实,答策又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考生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以及对世界情势的认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世界认识得越深刻,等于是对中国认识得越深刻。所以各国政治艺学策这样的官方考试,无异于正式号召普通知识分子关心世界历史的进程,从而在客观上让应试的举子们了解到中国的弊病所在,无论对改革对革命都准备了思想基础。但清末保留下来的这些问答文字似乎从未有人好好利用过,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虽然考生的答策并不全是在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而是要迎合考试的需要,也就是在力争中式的前提下写出的急就章,所以必定要揣摩问策的意向,使答策能得到考官的认同。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精彩答策,体现了在社会转型期相对丰富的思想内涵。当然有些问策迹近可笑,答策也很幼稚敷衍,但正是这样良莠不齐的一问一答,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变化的真实。
举一例而言。山西壬寅年乡试有这样一道策问:中学西学互有体用。西人中如培根之讲求实验,笛卡尔之专务心安,未尝不与中学通。今普通学堂兼取西人所长,补我所未逮,何以不病迂疏,不涉诞妄,义理明而格致精,体立用行,以备朝廷任使策。
能出这种题目已经说明考官对新思潮有相当之注意,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群既想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不想触动中国原有文化与政治体制的高官的基本主张,但这个思路被严复所批评,严认为中学自有中学的体用,西学自有西学的体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此由这个题目首先可见考官已经认可了严复的思路,尽管接下来的问题又回到老路上去。晚清因为受到西学的冲击,国人自信心大受挫折,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挑战,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追寻自身文化光荣的一种心绪排遣(或曰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或者退一步,提倡中学西学有兼通之处,如本题首先就预设培根与笛卡尔的思想与中学是相通的,为考生定下框框。而具体要考生作答的是题目的后半部,亦即询问考生怎样才能使兼取西学的新式学堂能够避免迂疏诞妄的毛病,而达到体立用行,让朝廷得以利用。改革后的第一场科举考试是考中国史事论,但有些论题出得相当之超前,甚至与策问相去无几了。如壬寅年湖北乡试的论题即有一道问:“关中称西北隩区,长江为东南天堑,其物土之肥瘠,形胜之险夷,试以历朝陈迹证之近今大势,博考精求,为讲习政治地理学之一助论。”这里不但出现了我至今所知的“政治地理学”一词的最早出处,而且此论所问,其实已经与策问相去无几了。
顾廷龙先生主编《清代硃卷大成》,大约就是认为硃卷还有其上述所列的无用之用,这是极有见地的工作,只可惜所缺甚多,尤其是江浙两省以外所缺更为明显,如果能够动用全国公私藏书之力,应当能够补充得更为全面。
对近代文献的重视是随着学科领域的扩展与学术研究的深入而逐渐为人所认识的。即使极其重视文献的前辈学人张元济与郑振铎,他们由于研究的侧重点有区别,观念就有不同。前者极其重视古代文献,而后者则古、近并重。一直到今天还有古籍研究者对近代文献不屑一顾,实在有点遗憾。其实近代文献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有识者的重视,美国学者韩南与中国学者李欧梵,分别研究不同领域,前者重在古代文学,后者专攻现代文学,结果双方不约而同都分别伸展到近代。所以另一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王德威说:没有晚清,哪来五四?正是说明了近代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近代文献自然而然也就逐渐引起重视,近代小说等文学形式也日益受到重视,日本的樽本照雄首先以一己之力广搜资料,编纂了近代小说目录,最近更有传教士创作小说研究这样的专著出现,说明近代文献受重视的程度已经与日俱增,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蔚为风气。
七、注意近代文献的珍稀性
由于近代去今不远,加以传统认识上以古籍版本为珍贵,于是近代文献的搜集、庋藏与整理保护从来乏人注意,至于文献目录的编纂更是无人问津,以致造成一些近代文献十分稀缺的情况,有些重要文献甚至比古籍善本还要珍贵,这在国内最近的古籍拍卖市场上已有所体现。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上海图书馆要算是对近代文献的收藏最为注重的了,但即使在该馆你仍然查不到《华英通语》、《英文话规》这样的书籍。历来的藏书家只讲宋元版本,至不济也是明清佳椠,稿本,批注本。石印书铅印书没有人看得起。目录学亦只讲四部,此外不讲。当其时,图书馆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学书应接不暇,对闱墨之类敲门砖的书则因看不起而不收,而至今不少藏书机构与出版单位对近代文献仍不十分重视。对古籍善本的收集不遗余力,对古代文献不断翻印,近代却很少翻印复制。中文早期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中华书局翻印了,但《遐迩贯珍》与《六合丛谈》都是日本先印,中国再复制。至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外新报》一类则还没有出版社看上。更往后的报刊,如上海出版的《益闻录》看似容易收集,但恐怕现在亦难收集到一套全的。范约翰在1890年即为该年五月份以前行世的中文新闻报刊编制了一个目录⑨,包括中国传统的《京报》在内,一共有76种,这76种报刊现在大多已经搜集不到全帙。就连中国历史最长的连续出版物《京报》,现在能够复印再现的也只是光绪以后的一小部分,光绪以前的只有零星存世,至于马礼逊等外人曾经译为中文的嘉道年间的《京报》,则无中文原版可寻矣。
英文刊物最近已经复制了Chinese Repository,这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还有《广州纪录报》、《北华捷报》这种动态性比较强时效性比较快的报纸,其中有些保留了中文文献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复制出版,未免让人觉得可惜,前者还有胶片可读,后者则只有原纸质报纸可用,但因为纸质保存不易,已到了必须抢救的岌岌可危的程度了。近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复制珍稀的近代报刊了。
近代文献还有其唯一性,就是一直只以手稿形式留存的文献,这方面可能注意的人较多,但也仅注重如盛宣怀档案这样的重要文献,至于许多不成体系的,不那么显赫的人物的日记函札,大量堆积于各图书馆或者散落于民间,也都有重视的必要。即使显赫人物的有关文献有时也不容易一时获得,如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的日记一直到前年底才正式出版,于敦煌文物流失过程有切实的记录,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或许有人会认为手稿并非印刷出版物,但我们不妨视之为待刊之出版物,因为讲古籍版本学的人,一样要讲稿本抄本,严格说来这些稿抄本也还没有成为版本。
还有一些近代文献起初以为易找,其实不然。杨家骆的《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保存了许多重要近代文献,功不可没,但这一工作还任重道远,因为该汇编中还有些近代出版的文献并非第一手或并非初版本。如郭连城的《西游笔略》初版本,该汇编就未曾收入,而以其民国版替代。这个初版本我在法国的沙畹文库里偶然发现,才交由上海书店出版,有兴趣者不妨与民国版作一比较。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百多年的东西就容易找,其实大大不然。关于近代珍稀性的例子还有许多,不能遍举,只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万一你看到某一种文献觉得从未见到,你就不妨加以收藏,因为可能那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
八、重视建立近代文献目录学
既然近代文献还不是被广泛使用的正式学术术语,也因此至今还没有正式、遑论完善的近代文献目录⑩,但是从晚清起到民国初年却出现一系列的西学、东学与新学的书目,这些书目实际上属于近代文献书目的范畴,也是近代文献总目录的基础。自从晚明艾儒略写作《西学凡》以来,西学就成为一个正式的名词,只是在当时使用频率还不高,到了晚清西学就成了士人皆知的一门新学问了。大凡是从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过来或介绍、引述、引申、重构、改写的西方的科技人文思想与成果的中外人士的著述也被称为西学。19世纪40年代以国人摘译改写的《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为代表。50年代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译《全体新论》、《代微积拾级》等书;60年代,同文馆、上海广州广方言馆成立,编译外文书籍,重要者有《万国公法》、《法国律例》等;7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兴起,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江南制造局设译学馆,翻译科技书籍近二百种;90年代以后,在西学之外又加上东学,即从日本舶来的西学,不久以后,二者合称新学。戊戌维新前,新学书籍已经大量出版。庚子年后,新学成极时髦学问,非但日常需要,即科举改革考试中国史事论与外国政艺策,非新学有基础即考试不能中式。因此为了士人的实际需要,以及学术方面的内在需求,西学以及新学书目开始出现,摘其重要流行者有以下这些:
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
1897年沈桐生《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读有用书斋(尚有《东西学书录》未出版)。
1898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大同译书局。
1898年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
1899年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902年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
1901年赵维熙《西学书目答问》。
1903—1904年通雅斋同人编《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
1903年中国学塾会编《中国学塾会书目》。
1903年王景祈《科学书目提要初编》。
?年《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
1909年陈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
1934年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杭州金佳石好楼。继徐、顾所著之《增版东西学书录》作,收1902—1904年续得知见之新学译著(11)。
但是这些正式出版的书目还远远没有囊括所有的新学著作,更不必说完全不及未成书的单篇重要学术论文。上面提到的一些珍稀著作,就有好些未被收入以上书目。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两类书目,一是营业书目(包括《贩书偶记》一类,但该书不及新学),一是公私机构的藏书目录。首先将营业书目收入自己的藏书中的是郑振铎先生,这是独具只眼的行为。因为营业书目可能包括时人所不重而今天却是珍稀文献的书籍。晚清成为书籍出版的营业书目最初要以《申报馆书目》与《续书目》最重要,后来,商务印书馆也有历年的书目出版,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完整的一套可供利用。至于以单幅广告形式出现的营业书目今天更是难觅,我所编辑的《晚清营业书目》只是纳入自己所藏书目而已,自然是挂一漏万。这样营业书目还需多方搜求,以便能按图索骥,进一步丰富近代文献的收藏。还有一些营业书目是存在于已出版书籍的附页或封面封底,或在报刊当中,搜集起来更为麻烦。
晚清以还,公共与私人图书馆渐次出现,这些机构也往往编写一些藏书目,过去也不为人所重,例如在浙江图书馆建立以前,有《浙江藏书楼书目》,其《乙编》所载就全是新学书籍。像这类书目就容易被忽视。再者,基督教新教在晚清特别致力于中文传教书籍报刊与传教文献的出版,上面提到的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就收入来华新考传教士首次大会上,但由于新闻史研究者过去忽视教会与英文文献,所以直到二十多年前,还不知道百年前就有这个重要目录存在,由以上所述,可见在近代文献目录学方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九、几句结语
近代上承古代,处于改革之中,下启现代,焕然一新,历史地位极其重要。近代文献正是我们理解西学如何进入中国,东学如何引起重视,新学如何成为时髦,寖假而成为革命动力来源之一,以至引起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过程。学问的追求原本不全在于实用,好奇心(而不是实用性)是西方科学观念得以产生的关键性原因,恐怕也值得人文科学界的深思。近代文献浩如烟海,从史学的角度曾经出版过的《近代史资料》100多辑,还恐怕只是沧海一粟,但即便这一《资料》也由于出版社的变更,出版周期的过长,至今还很少有图书馆收齐的。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有长期规划,将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进行认真的规划,那将不但是印刷出版史的福音,也是整个学术界的愿景。近代文献由于去今不远,数量还很庞大,但正由于此,所以重视的人还不够多,尤其是青年学者往往不容易判断所见文献是否重要或珍稀,有时不免就将值得重视的文献遗漏掉。爱好文献的同道,不妨以近代文献的搜求与研究作为一种志业,努力提高研究近代文献的能力,积以年月,必定会有可观的收获。同时于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也是一项极大的贡献。
- 0001
- 0002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