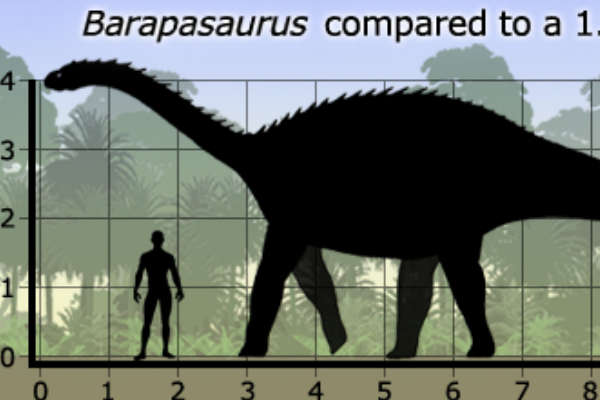谢保成: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的八字概括:“从考古到史学研究”①。这一道路决定了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治学方法是注重综合研究的。
一
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深受着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
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就曾明确表示:
三十年代,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后,就很自然地吸引着我。从此,我就逐步进入古代社会研究这个阵地了。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当时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感受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都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是减低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动向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这时候,正迫切地要求着这一问题的解答。”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锋利的文学手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像打了一针强心剂”②。从这时起,先生就在郭沫若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道路”,1931年6月发表《关于社会分期问题》。1945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发表,先生身居延安,在《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庆《群众》杂志随即转载。经周恩来往返重庆——延安,转达彼此的著作,先生同郭沫若建立起了长达30多年的深厚友谊。1949年北平解放,先生才见到郭沫若,“得到了面受教益的机会”。此后,“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直到郭老去世。”对于受郭沫若的影响,先生有这样的自白:
在相当时间里,在我虽说是从事具体的考古发掘,但由于郭老的影响我始终尽最大可能读了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应当说,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了。③
梁思永对先生的影响,史学领域似乎注意不够。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在北京病逝, 4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会,院长郭沫若出席纪念会,副院长陶孟和致悼词,先生在会上以《悼念梁思永先生》为题报告了梁思永生平学术活动和成就。报告中追述说:
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思永先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之于田野的调查和发掘的考古工作。
正是这几年,先生一面系统学习近代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发表评论《考古学研究法》的书评,一面参加安阳殷墟和后冈遗址、浚县辛村西周墓地和大赉店遗址、安阳侯家庄南地遗址和西北冈殷陵、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而其中的许多发掘都是由梁思永主持和领导的。先生的第一篇发掘报告《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④,“得龙山与仰韶两者的堆积关系”。进而,完成“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虽然这一报告“已成十分之九,未完稿存历史语言研究所中”⑤,未得发表,但梁思永仍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区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⑥。
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先生重写于南京鸡鸣寺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综合当时新石器遗址发掘的考古事实,得出结论:“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在河南北部确知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⑦。这篇论文的写作,反映着梁思永对先生的直接影响。在《悼念梁思永先生》中,先生这样评价梁思永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谜底戳穿了。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⑧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正是以梁思永参加、主持、领导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坚实基础,准确地运用梁思永关于“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这把“钥匙”,经过缜密论证得出确论的。⑨先生此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是以此为基点而逐渐深入并理论化的。1939年冬在延安蓝家坪写成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不仅“梁思永先生在病中曾仔细看过,且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⑩,还特别强调“一九三一年春,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阳的后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贡献”(11);文章论述昂昂溪文化反映“以渔猎为基础的氏族制的社会”所据材料和结论,更是引自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1955年8月《中国新石器时代·后记》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的补充,就是梁思永先生提出的意见。他本来希望我插在那篇里面,因为那篇写得较早,不便大动,所以就附在后面了。现在梁思永先生已去世一年多了,我谨以这册书的出版永志思永先生的热情。(12)
《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不仅“永志”先生对梁思永的深厚感情,同时永远记录下先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与梁思永的学术渊源。
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决定先生必然走出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从 1931年发表《关于社会分期问题》、参加河南殷墟发掘到1983年病逝,先生的治学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31-1937年,步入考古领域,即获重要创见;1938-1943年,把新石器时代考古推进到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方面,考古与史学研究初步结合;1944- 1953年,从事出版与教育组织工作,基本中断考古与史学研究;1954-1966年,肩负全国历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学科建设重任,从事历史学理论、考古学理论探讨,考古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此后,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长时间的理论思考。
二
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
(一)突破安特生的错误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先生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新石器时代》是其代表。
在延安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先生很快恢复了中断两年多时间的新石器时代研究,把1937年以前发掘所得比较可信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审慎地找出各种文化遗存的先后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各种文化遗存的具体内容,1939年冬在延安蓝家坪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论证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序,肯定昂昂溪文化是当时所知“代表着前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论述“以农业为基础的氏族制的社会”,分别考察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明确指出:“安阳后冈的发见,使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了仰韶、龙山和小屯这三种文化的时间先后顺序了。”仰韶文化遗存——在下层,属于后冈期;龙山文化遗存——在中层,属于辛村期;小屯文化遗存——在上层,属于殷代后期。(13)进而,以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的论断推测出龙山文化 (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初步确立。
15年后的1954年冬,当看到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朱家寨遗址》(1945年)、《河南史前遗址》(1947年)及其同事比林—阿尔提《甘肃齐家坪与罗汉堂遗址》(1946年)之后,发现“安特生在这些新的报告里,对于分期问题的意见,只是过去的见解之继续发展而已;其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他的旧说在我国的影响尚未清除,其新著却又在我国一部分历史学者中发生了影响”,“还在使用着以至传播着他的理论”。于是, 1955年4月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针对安特生新著中的观点,重点考察了先前未及深入的不召寨、齐家坪的遗存。文章第三部分“从不召寨和仰韶村遗址的再分析说到安特生分期的基本论点”所得结论是:“不召寨是纯粹的龙山文化遗址;仰韶村遗址里有龙山文化的墓葬。河南西部有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遗址的存在。大体上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那么,安特生所假设的‘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的基点就站不住了,他为这一错误论点所作的辩护也就不攻自破了。”(14)文章第四部分“关于齐家坪遗址及其它”作出的结论是:“齐家坪遗址确属另一系统的文化遗存,不得和仰韶文化混为一谈”,“它晚于仰韶文化。安特生把齐家期放在仰韶期前面是错误的”。最后强调:“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5)同年8月,先生将此前所写有关新石器时代的文章汇集在一起,请郭沫若题名“中国新石器时代”,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1962年6月以后,先生“重温了搁置已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行业”,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综合起来”的“全国范围内三千多遗址的丰富内容”为基础,“忙里偷闲,深夜捉笔”,到1963年4月写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初稿。在中央党校报告后,又广泛征求考古学界的意见进行修改,10月正式发表。这一长篇论文,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根据新的发现、新的问题,提出尚待深入钻研的学术问题,论证了“怎样前进”的诸多方面, “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16)。
1979年《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增订为《新石器时代》出版,成为先生致力于“探索新石器时代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的代表作。
(二)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氏族制度在我国发展序列的研究,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原始社会,是先生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自觉紧跟其后以唯物史观对史前社会、秦以前的古代社会作出系统的专题研究的是吕振羽、侯外庐。而专论史前社会的则是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40年12月修订改版为《中国原始社会史》。几乎同时,1939-1941年,先生依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观点,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1939-1940年9月,完成全书的主体部分,即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当时“国内外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这两编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17)
为了论证“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出(来)的,并不是由他处移植过来的”,批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东来”或“西来”说,1940年1月写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过程、从金文甲骨文中证明的古代传说之真实性两个方面展开论证,批判了当时“西欧和日本的学者”的各种“臆说”,以“西来”说为重点。(18)7月写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殷代后期是氏族社会末期“这种说法始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后来他所写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考释》两书都是围绕着这种观点写的”(19),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和其附近的考古发掘,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批最有价值的史料”,“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20)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强调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同时指出“目前所出的报告太少了,它们只是殷代遗址的部分的事实,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21)
三个单篇作为第三编《补编》,与上述第一、第二编于1942年8月结集付排,当年10月作“校后记”,1943年4月写“跋语”,5月由作者出版社出版,扉页作《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他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著。这部论著,集中反映出梁思永、郭沫若对先生的双重影响。第一编第一篇利用先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写成,第一编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就是1939年冬在延安蓝家坪写成、后来单独成篇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的内容,“费力最大”,前面已经说到,梁思永“在病中曾仔细看过,且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第一编第三篇《在崩溃过程中的中国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分经济结构(农业、牧畜、狩猎、工艺、贸易与交通)、社会组织结构(氏族组织、战争、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发生、国家的初期形态)、意识形态(宗教、历法、文字、艺术)的写法以及引用的基本史料,则是依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考释》并“借重”“彦堂先生的成果”完成的。(22)“校后记”声明:以原始社会崩溃“大约是在殷代后期,这并非自造,而是吸收了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的意见,加以研究和补充所得到的”(23)。
《中国原始社会》这一论著,既是先生沟通近代考古与“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标志,又是先生“正式研究原始社会的起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生浓厚兴趣的开端”(24),更是先生“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三)在将“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的最后历程中,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这一长篇论文之后不久,先生的“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经过十年浩劫,先生更加注意“对我们的史学理论状况认真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强调面对新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去探索这些新课题,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25)为着科学地总结我国史学理论的现状,先生认为应该从我国史学发展状况入手,一是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作出认真总结,一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状况进行全面了解。1977-1978年,先生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短短几年的时间,研究室形成规模,研究队伍不仅老、中、青年龄搭配适当,而且研究范围自先秦至20世纪前半段前后衔接。
1982年,先生与研究室成员讨论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编写原则这样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经过大约一年时间,初稿基本完成。尽管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主编工作,但全书是遵循先生确定的编写原则和审阅部分初稿的有关谈话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基本完成于这一期间,因为是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没有能够作为书序。(26)编写组在书前“编者说明”中这样写着:“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尹达同志史学生涯的一个纪念。同时,也寄托着我们的缅怀之情!”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先生故乡,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六编,下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前苏联学者勃·格·多罗宁认为《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项成果是“当前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27)惋惜的是,先生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状况进行全面了解的意愿未能得以实现。
分看三本代表作,分别代表先生在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纵观三本代表作,则清晰地展示出先生“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历史足迹和治学道路。
三
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工作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早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初期,先生的这一治学特点就为梁思永所赏识。西北冈发掘,先生被梁思永“点将”主持“最复杂”、“墓室面积也最大”的1001号大墓。据夏鼐回忆:
梁思永喜欢尹达,说他的工作认真、细致,说他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有综合研究的能力。(28)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写作,即已显示出先生这方面的特色。文章将最初17年间“发掘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作以系统清理,按其内容分析,含有龙山文化遗存的有11处,含有仰韶文化遗存的有10处,进而“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层位关系”的5处堆积情况,即后冈、侯家庄高井台子、大赉店、刘庄、同乐寨,将“许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最后作出结论。同时,对仰韶村遗址堆积进行新的估计,强调“安特生最初命名的‘仰韶文化’,实有加以纠正的必要”(29)。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运用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批评安特生“犯了不可宽恕的错误”:
安特生在那些“根本不同的文化”的各个地带的遗址中,找到了“那唯一相同之点”,即片面的加以比较……我们研究任何问题,一定要多方的全面的去把握所研究的对象,要从普遍的大量的现象中寻求问题的核心所在;绝不应强调个别的部分的现象,而忘掉全局。安特生在方法论上正犯着这样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剧。
我们……绝不应将一个整体割裂为几个单独的部分,然后将这被割裂的部分孤立的作为这个整体的代表;安特生拿仰韶文化的彩绘花纹和安诺、苏萨作部分的比较,正犯了这样的不可宽恕的错误。(30)
当先生总结自己学术道路,说到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时,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逐渐认识到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研究,就不可能使这一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现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同时还体会到,根据片面的个别的材料,就海阔天空的侈谈什么理论,除了制造混乱外,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以矜慎为名,把精力只放在个别孤立的事实上,而不去作全面的综合性的考虑,同样也会阻碍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这两种偏差应当说是没有正确解决好考古理论同考古资料的关系。(31)
1941年前后从事原始社会研究,在运用考古材料方面,同样强调应当避免“着重片面的事实,而忽略了大量的现象”,认为有的作者“就是这样”,因而不能够同意他们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结论。(32)
1955年《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结集出版之际,《后记》依然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33)
1963年,在系统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之后写成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谈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怎样前进”时,着重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考古学、史学及其相互关系,二是综合研究、科学发掘及其相关诸问题。
关于考古学、史学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指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过往的历史,而不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了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祖国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历史,而不是其它。这就为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者规定了明确的科学目的性。”为了这一目的,必须严格遵守应有的几道科学的工序:“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有计划的科学发掘,确切的发掘报告,认真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必须把三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分别开来。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是“最根本的基础工作,也是第一个重要环节”;“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是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进一步的深入,“它将从考古学的理论的高度,分析考古资料中所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两个阶段内,“把考古学上所存在的问题基本解决”。从事氏族制度的研究,“就要以最大的可能把考古学中的术语翻译为历史的社会生活中所习用的语言,使之更加具有人的气氛、生活气氛和社会气氛;在可靠的科学根据上,把残缺的遗物遗迹复原为完整而生动的社会历史的资料”,使氏族制度的历史面貌有可能重现出来。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工作,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不可机械分割。(34)
在论述综合研究、科学发掘及其相关诸问题时,有这样一段带总结性的论述:
综合研究和发掘工作之间应当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关系。不在科学发掘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学术成果;不在科学的综合研究指导下进行发掘工作,往往会处于盲目状态,忽略其应当注意的重要现象,从而失却其可能解决某些学术问题的机会。这是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35)
这是先生“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积累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既是先生个人的经验总结,又是整个新石器时代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验积累!这一经验或方法,不仅仅限于新石器时代研究领域,实在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
当谈到多学科协作时,先生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它迫切需要史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物理、化学等等学科的大力支援,从这些学科中吸取必要的营养资料。”(36)直至晚年,依然不忘“把史前考古、民族学、历史学以及各个有关学科的学者们密切地联合起来”,以“推进史前社会历史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37)。先生的这一愿望,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
注释:
①详见《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母校河南师大的谈话》,《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第372—382页;《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350-360页。
②上引见《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前编),《中国史学集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 159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尹达集》所收此篇,个别文字与最初发表文字稍有不同,这里引用最初发表文字。下同。
③上引见《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续编),《中国史学集刊》第1辑,第167页。
④发表在《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1936年8月),署名刘耀。《尹达集》,第7-27页。
⑤《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页注②。下引《新石器时代》,均为此版。
⑥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英文),《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会志》第4本(1939年),第 69-79页。中文译文(“根据原作,忠实地译出”),刊于《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⑦《新石器时代》,第117-118页。
⑧《尹达集》,第398-399页。
⑨这篇文章1947年3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杂志》2卷1、2期同时发表。《中国考古学报》刊载此文署名“刘耀”,《北方杂志》发表此文署名“伊达”。《中国考古学报》刊载此文无副标题,《北方杂志》发表此文增加副标题“中国原始社会资料研究之一”,《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增订版《新石器时代》收录此文改副标题为“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中国考古学报》刊载此文前列五个部分的标题,《北方杂志》发表此文前有1946年10月21日所写336字的小序,说明十年间文章辗转抄寄、图版照片流落以及这次发表稿子“只更动了个别的字句,所有的意见和布局都不曾变动”的情况。
⑩《新石器时代》,第244页。
(11)《新石器时代》,第7页。
(12)《新石器时代》,第245页。
(13)《新石器时代》,第72-73页。
(14)《新石器时代》,第138页。
(15)《新石器时代》,第142页。
(16)《新石器时代·再版后记》,《新石器时代》,第254页。
(17)《中国原始社会·校后记》,《中国原始社会》,作者出版社1943年版(下引《中国原始社会》,均为此版),第 172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222页。
(18)《中国原始社会》,第138-147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301-318页;《尹达集》,第245-262页。
(19)《中国原始社会》,第149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319页;《尹达集》,第263页。
(20)《中国原始社会》,第150、151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320、323页;《尹达集》,第264-265、268页。
(21)《中国原始社会》,第162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340-341页;《尹达集》,第285页。
(22)《中国原始社会·跋语》,《中国原始社会》,第174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226页。
(23)《中国原始社会》,第172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223页。
(24)前引《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母校河南师大的谈话》。
(25)上引《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母校河南师大的谈话》。
(26)《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系由笔者根据先生讲课笔记于1983年1月写出,送先生审阅并经有关部门审定,作为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论文”印发。因写作时间仓促,先生让修改好再正式发表,或作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书序。当年7月1日先生离去,文稿成为一篇未完成的遗稿。《河南师大学报》改版为《河南大学学报》,再三希望将这篇文稿交由他们正式发表。在征得历史研究所领导同意后,又作了一次修订,篇前加按:“尹达同志这篇遗作,曾作为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论文’印发过。此后,又作过修改。现按照修改稿发表。”文末附言:“此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保成同志整理惠寄”,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收入《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尹达集》时,由于编辑方面的原因,篇前按语、文末附言均未保留。文章基本反映先生晚年关于中国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至于系统性、个别观点、文字表述等,则未必完全符合先生的本意和风格,特此说明。
(27)Б·Г·ДОРОНИН: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Раэ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远东问题》1988年第2期)。中文摘译,参见〔苏〕多罗宁:《现阶段中国史学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9期。
(28)夏鼐:《悼念尹达同志(1906-1983年)》,《考古》1983年第11期。
(29)《新石器时代》,第108页。
(30)《新石器时代》,第72页。
(31)前引《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母校河南师大的谈话》。
(32)参见《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中国原始社会》,第162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341页;《尹达集》,第 285页。
(33)《新石器时代》,第243页。
(34)《新石器时代》,第220-224页。
(35)《新石器时代》,第225页。
(36)《新石器时代》,第239页。
(37)《衷心的愿望——为史前研究的创刊而作》,《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450页;《尹达集》,第6页。
来源:《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