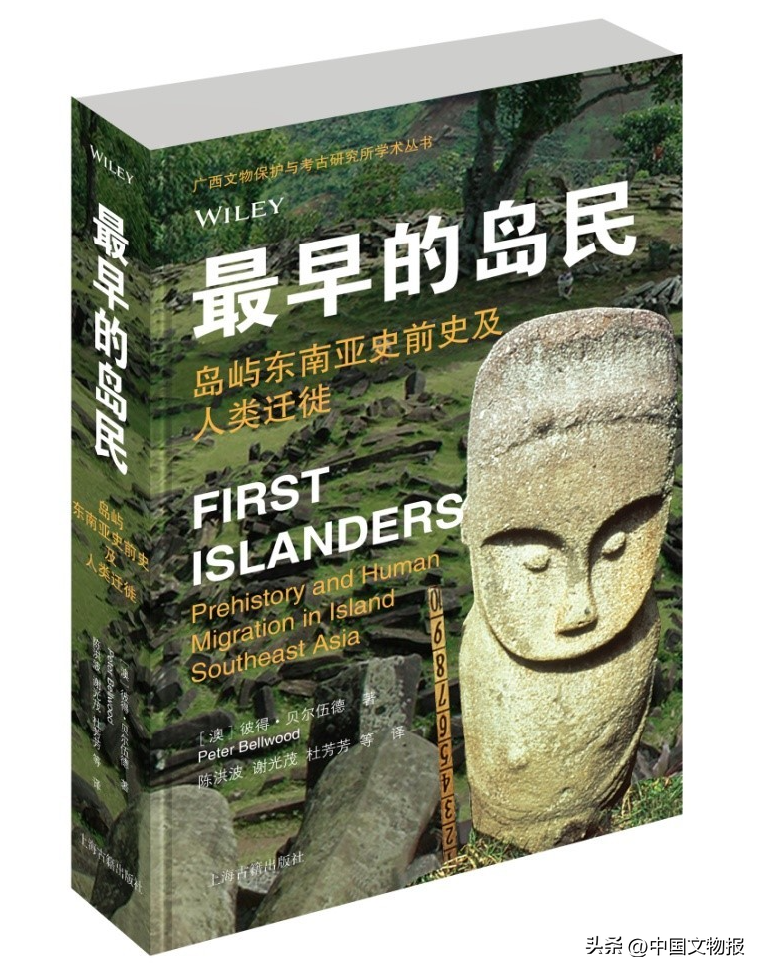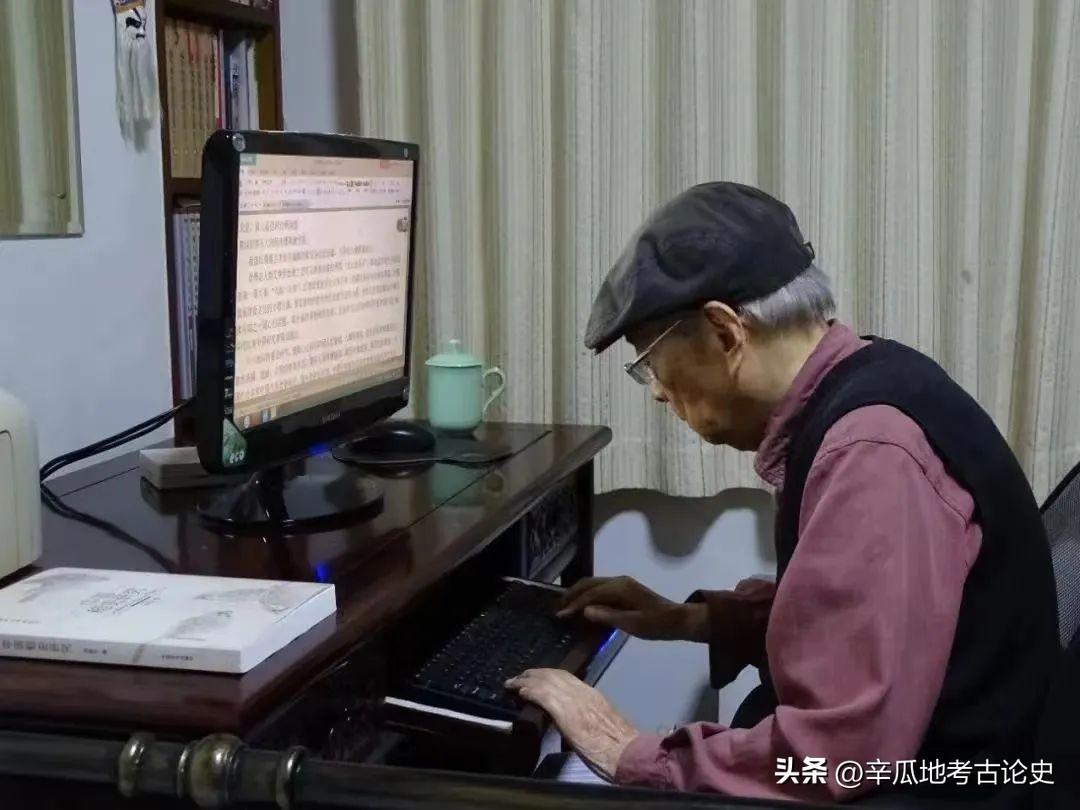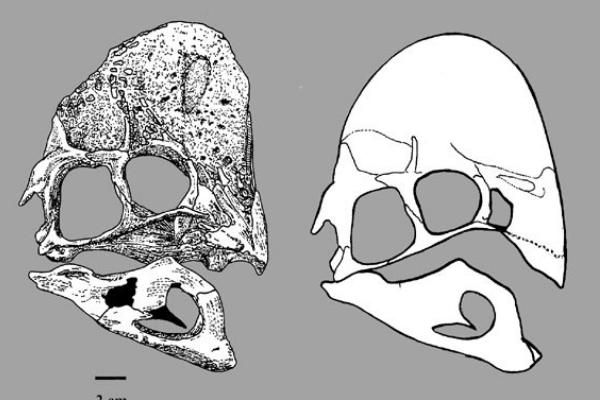林沄:说“貊”
古籍中的族名“貊”,也写作“貉”。东汉郑玄注《周礼·肆师》“祭表貉”说:“貉读为十百之百”,可见貊和貉本是同音字。但貉字的读音分化颇甚,所以本文取貊字作为该族的正式称谓。
传世古籍“四书”除《大学》之外,都提到过貊。汉代以降的文献中仍用这一族称来称呼当时实际存在的民族集团。所以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可是古籍中貊的记载多为片言只语,且互相矛盾。历代注家对它的解释也很分歧。现代民族史论著对这一族称更是新解叠出,莫衷一是。也有人试图从考古学角度来解决这一疑团,但考古资料的运用要以有关该族的文献记载为基点,在对纷纭的记载有不同取舍和不同理解的前提下,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反又增加不少新的纠葛。
古籍中有关非华夏族的记载往往是零星、片断,甚至互相矛盾的。只凭一两条史料立论,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使是收集了有关某一族的全部史料,之所以仍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一、对不同记载形成年代的先后和可信程度未加充分的考虑。二、同一族称的实际含义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注家,对同一族称的理解也有差异。这一点更是往往被忽视了。所以,面对纷纭的文献记载,一定要作必要的历史性的分析。否则,一视同仁地引用各种异说,一味调和,只会陷入迷魂阵而难以自拔。
因而,本文想对有关“貊”的文献记载,作一番历史性的梳理和分析,希望对重新考察先秦时代的这一重要古族的历史真相,能有所帮助。
一
提到貊的先秦古籍有十多种,但大都是貊和其他族并举的。单称的貊,只有以下两例有较具体的内容: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诗经·韩奕》)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
《韩奕》是西周晚期的作品。诗中说韩侯的先祖便已受周王之命统治貊和追,而为北国之伯(颇有似文王曾为商之“西伯”)。韩侯的都城为燕国的军队所建。则诗中所提到的貊,其地亦当近燕。其存在之年代当可追溯到周初。所以,传世的西周早期的貉子卣铭:“王令士道归貉子鹿,貉子对扬王休。”“貉子”有可能是貊族中的首领人物。
关于这个周初以来近燕之貊,还可参照以下的记载:
“(周)王使詹桓伯辞於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貊的假借字),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
“史伯对曰:‘……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也是貊的假借字)。’”(《国语·郑语》)
貊、亳、蒲古音都是铎部唇音字,故可通假。这个近燕的貊,故地大概在战国时被北扩的燕国所占领,所以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按:疑“燕”字下原有重文号,传抄时脱去)。”这条记载虽错入《海内西经》,所云“汉水东北”也未必可靠,但在燕国史料很贫乏的情况下,还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能印证貊故地近燕并被燕所占的,是燕国又被称为“燕貊之邦”。齐国陈璋在破燕所虏获的方壶和圆壶上都刻了“内(入)伐郾(燕)亳(貊)邦之获”,燕国被蔑称为“燕貊”和楚国被蔑称为“荆蛮”相仿。《汉书·高祖纪上》“四年,……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也是貊、燕连举,可作参证。
《孟子》的记载,一方面表明战国时的貊人尚未建成与中原同一水平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证明它们已经有了“二十取一”式的公共积累制度,至少应该出现了“准国家”(或“酋邦”)。从“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来看,他们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种植业。但据《战国策·秦策》“大王之国,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可谓貊人也养马。据《水经注·河水》引《竹书纪年》,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举记述为“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或可以推论貊人在服装特点上和善骑射的胡有一致性。所以,把貊人的生业设想为亦农亦牧亦猎的多种经济,是比较妥当的。
另据《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可知貉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族群,内部还可分为多种分支。《周礼·司隶》所属有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各百二十人。其中貉隶除和其他诸隶一样“守王宫”、“守厉禁”外,还专门从事“养兽而教扰之,掌与兽言。”这也许反映了貉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开发程度较低而野兽众多。这和《韩奕》诗中专门描写“孔乐韩土,川泽许许,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以及“献其貔皮,赤豹黄罴”,可以互相印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说“貔,豹属,出貉国。”“鲜,鲜鱼也,出貉国。”
此外,西汉杨雄《方言》:“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也许是先秦貊人所创。《说文解字》:“繜,薉貉中女子无绔,以帛为胫空,用絮补核,名曰繜衣,状如襜褕。”“

,水虫也,薉貉之民食之。”如果许慎说的“薉貉”是指薉和貉两族,也可以视为有关貊族的民族志记录。
二
在先秦文献中,常见“蛮貊”连举。如:
“至於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诗经·閟宫》)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论语·卫灵公》)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
“汤武置天下於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育蛮貊四夷。”(《大戴礼记·礼察》)
显然,以上的“蛮貊”是用一南一北两个有代表性的族名泛指一切非华夏族人。《閟宫》中的“淮夷蛮貊”实际所指是淮夷,要翻成现代汉语,应是“淮夷这样的异族人”。所以毛传解释这句时只说:“淮夷,蛮貊而夷行也”,不再对蛮貊另作说解。至于《礼察》中的“蛮貊”下面又加了“四夷”,其实是同义重复,是为了和上句中的“禽兽草木”一样凑成四个字。像“四夷”一样泛指一切非华夏族的“蛮貊”,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很流行,成为固化的合成词。伪古文《尚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就是典型的例子。
和“蛮貊”连举略有不同的,还有《墨子·兼爱中》引古传中周文王告祭泰山文的“以祗商夏,蛮夷丑貉”。“丑”为众多之意,即是用蛮、夷、貊三者并举来泛指一切非华夏族。晋张湛注《列子·汤问》“性而成之”引先秦慎到之言:“治水者茨防决塞,虽在夷貊,相似如一。学之於水,不学之於禹也。”,则是用“夷貊”并举来泛指一切非华夏族。总之、夷、蛮、貊都可用来代表其他异族。所以“蛮貊”、“夷貊”和“蛮夷”都是同义的。只是“蛮夷”后来最流行,“蛮貊”次之,“夷貊”则不大流行。这三个族也可以单举一名便代表一切非华夏人,如前引《韩奕》中用“百蛮”表示一切异族。《汉书·礼乐志》:“奸伪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是用“四貉”表示一切异族。后来最流行的则是用“四夷”泛指一切异族。
但是,古人既然用“蛮貊”、“夷貊”、“四貉”指称一切异族,毕竟表明了貊是在中原人心目中很有份量的异族。
三
先秦文献中还每见貊和胡(包括代、狄、戎等)并举的现象。
“古者禹治天下,……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之民。”(《墨子·兼爱中》)
“虽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墨子·非攻中》)
“(秦)北与胡貉为邻”(《荀子·强国》)
“大王之国,北有胡貉代马之用。”(《战国策·秦策》)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伤害。”(《宴子春秋·谏下》)
“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赏罚弗能禁。”(《吕氏春秋·义赏》)
“干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大戴礼记·劝学》)
胡和貊连举是在较晚的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现象,是因为都处于北方而相提并论。《墨子》中除胡、貊外还提到了燕、代,这和第一节中已提到的貊故地近燕是一致的。
战国开始流行的“胡貊”并举,到汉代更加流行,也固化为一个合成词。而且几乎成为“胡”的同义词。这是因为中原的文人对北方各族缺乏实际知识,把一切北方民族都想象为同一经济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大族团。如西汉初年晁错上书言边事:“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贪戾而欲广大也。……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汉书·晁错传》)其中的“胡貉”显然是说的匈奴,所以文中又把“胡貉”省称为“胡”。由此可知,《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李斯从狱中上书的“……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胡貉”其实也是指匈奴。又如《汉书·天文志》;“中国於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其中的“胡貉”也是指胡而言。如误以为胡貉之间可以加上“、”号,就会错把貊族安到西北方去了。
而且,汉人有把“胡”扩大到泛指一切北方民族的倾向。如《汉书·天文志》在谈到破朝鲜时说;“元封中,星孛於河戍。占曰:‘南戍为越门,北戍为胡门。’其后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朝鲜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把朝鲜半岛也归入“胡之域”了。无怪乎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东夷传·秽》中写道:“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以后胡、汉稍别。”把该地的非汉族都称为“胡”。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时,引汉末应劭之说有“胡真番、朝鲜胡国”、“古句丽胡”等提法。另一方面,汉人也把“貊”(包括戎、狄)笼统地理解为北方异族之称。例如:
《诗经·韩奕》毛传:“追、貊,戎狄国也。”
《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郑众之说:“北方曰貉、狄。”
《孟子·告子下》赵岐注:“貉在北方。”
《说文解字》:“貉,北方貉。”
所以,“胡貊”(或“戎貊”)一词便有了泛指一切北方民族的性质,不一定非指匈奴不可。
本来是并举的“胡貉”之固化为和“胡”同义的合成词,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像《荀子》说秦国的北方有“胡貉”,也可能是战国时人已经开始把“胡貉”和“胡”混用。未必可用以论证战国时貊确实向西分布到秦国以北。至于《秦策》说秦国之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因代的分布实际在燕赵之北而并不在秦之正北,所以连举的貊也不见得必在秦之正北。《史记·匈奴列传》有“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史记·赵世家》中保存的一则神话故事提到,赵襄子得到一只竹筒,剖开后发现其中有朱书:“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也许可以此推论赵国和貊相邻。但这两条记载中的“胡貉”和“貉”也可能已泛指北方异族,所以并不能使人确信貊曾分布到赵国以北。
四
汉代以后的文献中仍有单称的“貊”,专指高句丽及其“别种”。
“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於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尉(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貊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今岁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城。……’於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汉书·王莽传中》)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力气,习战斗,沃沮、东秽皆属焉。又有小水貊。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太平御览》七八三引《魏略》略同)
《汉书·王莽传》表明高句丽被称为“貉人”。所以《后汉书·东夷列传》抄录《三国志》对高句丽的记述时,在“……沃沮、东秽皆属焉”后,插了一句“句骊一句貊耳(耳字可能是衍文)”,这可以使下一句“又有小水貊””更便于理解,是加得不错的。《后汉书》中还有其他用“貊”来指高句丽的例子。如《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五年“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和帝纪》和《耿弇传》元兴元年“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貊人寇郡界,夔追击”,与《东夷列传》高句丽条对照,可确知都是指高句丽的。
大水指鸭绿江,叆河尖古城出土“安平乐未央”瓦当可确定为汉时西安平,因而小水是叆河,都是汉代貊人分布区的自然地理标志。《三国史记》中还有三处提到“梁貊”。故不少人认为梁水(今太子河)也有貊。但这样晚的书中出现的“梁貊”是否可信,有一定疑问(注:《三国史记》为南宋时高丽史官金富轼监修,多取中国史书的记载改写。其卷十三、十六、十七均有“梁貊”。卷十七“东川王二十年,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毌丘俭将万人来侵。王将步骑二万人,逆战於沸流水上,……又战於梁貊之谷,……”,显然与《三国志·毌丘俭传》所记“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有关。但裴松之对“梁口”注曰:“梁音渴”,其实梁字历来无读渴音者,所以疑是它字之讹。因而《三国史记》的“梁貊之谷”也不能无疑。)。
汉以来被称为“貊”的高句丽,和先秦时近燕且被燕所灭的貊,是什么关系?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说周初近燕的貊就在鸭绿江流域颇难令人信服。因为周初的燕的都城在房山董家林古城,西周燕文化的影响只到达大小凌河流域,鸭绿江流域还没有发现和西周燕文化接触的任何证据。可以设想三种假说:一、周初貊人分布很广,在大小凌河流域或更西南的地区和燕相邻。到战国燕国疆域向东北扩展后,才缩小到只局限于鸭绿江流域的一隅之地。二、先秦貊人起初在以大小凌河为中心的地区,战国时原地被燕国占领后,一部分不愿丧失独立的人迁移到东北方的山林地区。成为后来高句丽的重要组成成份。三、高句丽和先秦的貊并无人种和文化上的联系,只是醉心于复古的王莽时代的人们把古代族称“貊”硬派给高句丽而已(注:此说曾见于三品彰英:《濊貊族小考》,《朝鲜学报》4,1952年。)。要弄清真相, 只有靠东北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的充分开展了。
五
汉代文献中出现“秽(或作“濊”、“薉”)貊”连举的现象。除上举的《汉书·王莽传》外,还有:
“(冒顿时)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
“(元封四年),汉东拔秽貉、朝鲜。”(《史记·匈奴列传》)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史记·货殖列传》)
“彭吴穿秽貉、朝鲜,置沧海郡。”(《汉书·食货志》)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高句丽蛮夷。”(《汉书·地理志》)
“孝武皇帝躬仁政,厉威武。……东定薉貉、朝鲜。……”(《汉书·夏侯胜传》)
应该指出,秽本是个单独使用的族称。
“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汉书·武帝纪》)
“(安)上书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汉书·严安传》)
“

,

鱼也,出薉邪头国。”“

,

鱼也,出薉邪头国。”(《说文·鱼部》)
“其(按:指夫余)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三国志·东夷传》)
1958年在平壤贞柏洞土坑墓中出土“夭租薉君”银印(注:此印文朝、日、中学者过去都读为“夫租薉君”,其实据原篆看,“夫”应改释为“夭”才对。详见拙文《夫余史地的再探讨》,不日将在《北方文物》发表。),应为汉夭(沃)租(沮)县境内的秽人之君。沃沮是单单大岭(今狼林山脉)以东的七县之一,可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的“自领(岭)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是可信的。如果相信《逸周书·王会》是先秦文献,则其中的“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是秽人最早的记载。《吕氏春秋·恃君》“非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也提到过秽。所以,以上各例中的“秽貊”,其实都可以点读为“秽、貊”,秽可理解为夫余以外的秽人,貊可理解为高句丽或其别种。
单称的“秽”分布于邻近高句丽的广大地区。夫余在高句丽以北,其印文为“秽王之印”,故城名“移城”,表明高句丽以北原为秽的分布区。岭东七县的秽则在高句丽以南。《汉书·武帝纪》记当时“东夷薉君南闾等”共有二十八万口,合五至六万户。比《三国志》记高句丽以南的秽“户二万”,多出很多。故推想秽人的分布本来不止上述两区。汉代人“秽貊”连举,乃因两族相邻甚至交错分布所致。
本为两族的“秽貊”连举,也逐步变成一个合成词,被用来泛指东北方各族。试举例如下:
“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於瓯骆;左将军伐朝鲜、开临洮,燕齐困於秽貉。”(《盐铁论·地广》)“秽貉”显然泛指秽、貉、朝鲜等异族。
“移檄告郡国曰;‘……故新都侯王莽,……西侵羌戎,东摘秽貊。”(《后汉书·隗嚣传》)“秽貊”实际主要指高句丽。
“是时孝武,……东攠鸟桓,蹂辚秽貊。”(《后汉书·文苑列传》引杜笃《论都赋》)“秽貊”包括朝鲜在内。
“六国擅权,燕赵本部。东限秽貊,羡及东胡。强秦北排,蒙公城疆。”(杨雄《冀州牧箴》)追述战国时代冀州以东有“秽貊”,所指颇宽泛。
“鲜卑、秽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后汉书·东夷传》转述汉安帝诏书之语。)此为高句丽归还所掳生口后下的诏书,“秽貊”显然主要指高句丽。
“乃祖慕义迁善,款塞内附。北捍

狁,东拒濊貊。”(陈琳《为袁绍拜乌丸三王为单于版文》)“濊貊”和西周古族名“

狁”对仗,虚指东方异族。
“秽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曹丕《典论自序》)这里的“秽貊”其实是“貊”的代称,以求在修辞上和“燕代”构成对偶句。
所以,以上各例的“秽貊”不宜用“、”号隔开,正是“秽貊”逐渐固化为合成词的先声。
《三国志》中“秽貊”已固化为一词。陈寿主要用它作为秽的代称。《乌丸鲜卑东夷传》秽条中说“秽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但在高句丽和沃沮条中却说“高句丽……南与朝鲜、秽貊……接。”“东沃沮……南与秽貊接。”用“秽貊”取代了“秽”。在夫余条中,则在“其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之后,紧接着就说:“盖本秽貊之地”,也是说“秽”即“秽貊”。《三少帝纪》“(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丽,夏五月,讨秽貊,皆破之。”按本纪中的七年讨高句丽,《毌丘俭传》作“六年复征之”。集安的毌丘俭纪功刻石上也记“六年五月旋”。而《鲜卑乌丸东夷传》中所记“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秽属高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正好和毌丘俭复征高句丽是同一年。《毌丘俭传》在总结他的战功时说的“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即兼及不耐侯举邑降。可见《三少帝纪》中的“讨秽貊”其实就是指伐秽之役。但是,《文帝纪》“延康元年……三月,……秽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此“秽貊”似难以解释是高句丽以南的秽人,因为秽人好像没有独立朝献的政治地位。究竟是借以指高句丽,还是别有所指,待考。
南朝宋人范晔写的《后汉书》中,“秽貊”的含义很混乱。他一方面学陈寿把“秽貊”作为秽的代称,如《后汉书·东夷列传》秽条中说“自单单大岭已东,沃沮、秽貊悉属乐浪”,记述辰韩时说“其北与秽貊接”,“秽貊”都显然是指秽。但他在该传开头所说“於是秽貊倭韩万里朝献”,似乎也可以点读为“秽、貊、倭、韩”。该书转引前代文献时,“秽貊”更有不同含义。所以,在读他写的本纪部份时,就颇难确定他写的“秽貊”究竟是何所指了。和高句丽、马韩并举的“秽貊”大概是指高句丽以南的秽。但是和乌桓或鲜卑并举的“秽貊”,就很难说是指高句丽还是其他族了。
在魏晋以来文人的观念中,“秽”、“貊”和“秽貊”其实都混同为指称东北异族的概念。颜师古注《汉书·严安传》“略薉州”时引晋人张宴曰:“薉,貊也。”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海内西经》的“貊国”时说:“今夫余国即秽貊故地”。而唐人李贤在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时说:“貊人,秽貊国人也。”颜师古在注《汉书·高帝纪上》的“北貉”时说:“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皆貉类也。”总之是把东北各族都搅成一锅粥了。在高句丽把夫余、沃沮、秽等古族都熔铸成新的民族统一体后,对于已经成为纯历史名称的“秽貊”,不同的学者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里再举宋代的两个例子比较一下:
《新唐书·渤海传》说“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认为秽貊故地只有渤海的一个府大。但《武经总要》却说“渤海,……本秽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则认为整个渤海都是秽貊故地。《新唐书》因被奉为正史而信从者较多。其实,东京龙原府是现今珲春的八连城,其属下的盐州是现今俄国滨海州南端的克拉斯金诺古城,都已是学术界的定论。而《新唐书》所说的“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目前虽不能确指其地,却必须在朝鲜半岛上,方能合于它是“新罗道”的作用。这样,《新唐书》所说的沃沮故地竟在秽貊故地之南,和《三国志》、《后汉书》记秽貊在沃沮之南正好相反,可见欧阳修的这种见解貌似精确,却并不足信。
总之,我们不能把汉代以来文献中习见的“秽貊”一词当作一种有确定含义的族称,只能说它是一个内涵一向不稳定而可以泛指东北地区异族的族称。
六
最后,着重分析一篇容易使人误入岐途的文献。
《管子·小匡》有记述齐桓公武功的大段文字,其中三处提到“貉”,“於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南据宋郑,征伐楚,……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束马,踰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

柯、……”其中“卑耳之貉”,《国语·齐语》作“辟耳之谿”,《说苑·辨物》作“卑耳溪”,《管子·封禅》作“卑耳之山”。足证《小匡》的“貉”实为“刜”字之讹,非族称,可置而不论。而“胡貉”和“秽貉”同见于一篇,是罕见的现象。
这段文字明显和《国语·齐语》的如下文字有关:
“(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南城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帅诸侯而朝天子。”
从对比可以看出,《小匡》所述实由《齐语》衍成。《齐语》所述和《春秋》、《左传》多不合,如对东南用兵“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等等,均显属夸诞之语。而且既渡西河,又逾太行,和实际地理相矛盾。所以不能视为春秋时代之史实。《小匡》不但袭取《齐语》的内容,又增加新的夸诞之辞。其中“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就是《小匡》新增。“北至於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等语中的“秽貉”是《小匡》作者凭空添加,“拘秦夏”由西征之文中窜入。所以其史料价值还不如《齐语》。《小匡》中有“南至……

柯”,据《华阳国志》,“楚顷襄王时,遣庄蹻伐夜郎。……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椓船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则此地名要到战国晚期才出现。而《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要到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才听说南越西北有牂柯。然后才有“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才“平南夷为牂柯郡”。《小匡》篇的作者能编造齐桓公到达牂柯的事迹,其时代不可能早于战国晚期,很可能是在汉开牂柯郡之后。因而他在编造齐桓公战功时,不但用了战国时已有的“胡貉”之称,还有汉代出现的“秽貊”之称。我们决不能据此以为齐桓公时代真有这两个族称,并据以考证它们的地望。
以上,我们把古籍中有关貊的记载全部梳理了一遍。可以看出,先秦的貊一定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个重要的族,但要弄清先秦的貊主要分布在何地,及其历史真面貌,还需要在东北南部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然而目前已可以断言:过去有的学者因为没有考察“胡貊”连举的实际历史,便断言貊曾远布于西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还有不少学者对汉代才出现的“秽貊”连举现象未作充分的历史分析,便信从东北自古以来有所谓“秽貊系”民族或“秽貊系”考古学文化的谬说,这一迷信是亟需破除的。
来源:《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 0001
- 0001
- 0004
- 0000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