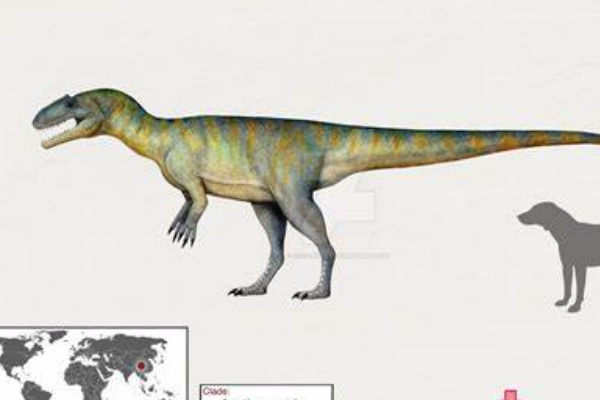李晓东:百年埃及学研究综述
埃及学在18世纪末已经开始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历程。当时入侵埃及的拿破 仑军队跟随了许多学者,这些学者此次跟随军队远征的直接成果是发表了《埃及记述》 (Description de l' Egypte),为整个欧洲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外部世界对埃 及这个神秘文明的兴趣由来已久,古代的一些经典作家就曾在自己的记述中描述过大量 的埃及文化生活的历史和传说。埃及学诞生的标志是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破译埃 及象形文字。然而,埃及学真正取得重大成果,成为一门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学 科还是在20世纪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完成的。20世纪埃及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考古挖掘和 材料的整理以及历史疑团的解决上。
一、考古挖掘
埃及学诞生之前的考古大多是掘宝性质的滥挖,结果造成了遗址和有价值材料的巨大 破坏。当时很多在这些挖掘者的眼中无价值的东西就都被随手扔到了一边。遗址当地的 居民成了挖掘者,使得后来的学者不得不从这些人手里购买文物。19世纪拿破仑入侵埃 及开始的埃及考古的发展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也仅限于对这些通过掠夺得来物品的 收集整理上。
阿斯旺大坝的工程,打响了20世纪埃及文物挖掘整理的第一枪。开始时,埃及政府对 文物的即将被毁并没下大决心来拯救。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与了筹集资金记录将 被淹没的努比亚遗址,但没有大规模的抢救行动。直到1958年,埃及任命了一位新的文 化部长,才有了改观。他意识到,这个工程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于是,他发起了一 场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大规模的抢救运动。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承担 这项工程,四十多个考古队伍参加。其中最大的两项是举世注目的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 拉美西斯二世在阿布·西姆波的神庙的整体搬迁提高工程和菲莱(Philae)岛上的伊西斯 神庙在阿及祁亚(Agilkia)岛上的重建。还有一些小的神庙被抢救挖掘出来,其中一些 被埃及政府送给了美国,因为美国在这次抢救挖掘中投入最大。丹杜尔(Dendur)神庙就 成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的一件藏品。但埃及在20世纪最重要的 挖掘还是在帝王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影响最大的是图坦哈门墓的发现和发掘。提 到图坦哈门墓的发现就不能不提及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C.W.西拉姆(C.W.
Ceram)在他的《神祗·坟墓·学者》一书中称他是“考古学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能够找到神秘的图坦哈门坟墓不是偶然的。他从小就对埃及有着很大的热情,17岁就 远离开英国,来到埃及记录和复制坟墓墙壁上的景物。白天工作,晚上就伴着蝙蝠睡在 坟墓里。后来接受了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的指导和训练。190 8年与卡那封(Carnarvon)勋爵合作,开始了寻找图坦哈门墓穴的工作。根据当时发现的 各种各样的关于图坦哈门墓的线索,卡特翻遍了帝王谷。在久寻未果之后,于1922年末 开始了最后一次的挖掘。挖掘从11月1日开始,三天之后,挖出了一个台阶的上半部, 三周之后,整个台阶被挖掘出来,图坦哈门墓穴的正面的石膏石块展露了出来。11月26 日,第一块石膏石块被撬开,填充走廊的碎石被清理干净,第二块石膏石也准备移走。大约同一天的下午4点钟,卡特打破了第二块石膏石,20世纪的一个重要发现,图坦哈 门坟墓被找到了。图坦哈门墓的发现,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埃及国王墓葬完好无损的范例 。后来,霍华德·卡特在他的《图坦哈门墓》(The Tomb of Tut·Ankh·Amen)一书第 二卷的前言中说:“不像帝王谷其它都遭到完全掠夺而只有很少家具残片留存下来的王 室陵墓,这个陵墓除了早期几个偷窃金属的盗贼的劫掠之外,实际上未被触动过。在这 一点上,我们的巨大惊喜与好运是应得的。如果底比斯伟大法老们的陵墓都以同样的状 态被发现的话,图坦哈门陵墓比较起来就不会这么重要了,只有这一时期的艺术能保持 其突出的特点。”[1](Preface,viii)图坦哈门墓的发现为我们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一些疑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材料,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图坦哈门 头骨上的窟窿,很可能是这位年轻发老早逝的原因。那么,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蓄谋的 结果,现在还是个悬念。
1925年,乔治·安德鲁·瑞斯那尔在吉萨发现了赫特菲瑞斯(Hetepheres)墓。这在20 世纪埃及考古及历史研究中无疑是一个不小的事件。乔治·安德鲁·瑞斯那尔(George Andrew Reisner)是现代科学考古的始祖之一,一个名望很大的埃及学家。这个出生在 美国的德国人的后代,将后半生的生命都投入到了埃及的考古挖掘中。19世纪末,瑞斯 那尔的挖掘主要集中在纳加·艾德-迪尔德(Naga ed-Deird)的大墓地和库伏特(Quft)、 迪尔·艾尔-巴拉斯(Deir el-Ballas)的遗址上。到了20世纪初,他的挖掘转向吉萨
(Giza)三座大金字塔周围的古王国墓地,之后又转向努比亚(Nubia)。
赫特菲瑞斯是第四王朝第一位法老斯诺弗汝(Snefru)的王后和法老胡夫的母亲。关于 她的材料我们所知甚少,但其夫其子的显赫足以让后人不会轻易将有关她的材料从眼前 溜过。她的这个陵墓没有地上建筑,而墓中最为重要的遗存女王的木乃伊也不知去向。整个陵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个仓促的再葬,原来的陵墓很可能是在达赫述尔(D ahshur)法老斯诺弗汝金字塔附近,由于遭到破坏而再葬于吉萨。不见了的赫特菲瑞斯 的木乃伊很有可能是在她原来的陵墓遭到破坏时给毁掉了[2](P164)。
这个墓葬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奠定古埃及文化丧葬习俗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提供了直 接的材料。古埃及木乃伊的丧葬传统到了第四王朝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从第四王朝开 始,死人的内脏不再和死人一起裹入木乃伊,而是剥离出来,用四个荷鲁斯神四个儿子 的胸罐盛起来放在石棺的外头。这里面充满了古代埃及人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和总的观 念。这种做法的最早发现就是赫特菲瑞斯墓。尽管在这个墓的石棺中没有发现赫特菲瑞 斯的木乃伊,但装有她内脏的胸罐却在其墓室西墙南部尽头的神龛中发现[3](P277)。
之后,重要的墓葬发掘还有皮埃尔·蒙太特(Pierre Montet)在塔尼斯(Tanis)挖掘的 第二十一、二十二王朝的国王和王室墓葬,为这两个没有太多资料留下来的王朝提供了 非常珍贵的资料。皮埃尔·蒙太特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曾先后在斯特拉 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erg)和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任教的蒙太特 的第一次挖掘是在比布鲁斯(Byblos)——现在的黎巴嫩的侏贝尔(Jubayl),这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一直有人居住的城镇之一。这个古代港口城镇对于我们了解远古时代的文化交 流极为重要。古埃及的很多朝代都与这个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埃及缺少木材,从埃 及统一以来这里一直是埃及木材的最重要的来源地。黎巴嫩雪松以及其他埃及所缺少的 东西都是通过这里运往埃及的。埃及的物品从埃及第二王朝(约公元前2890年到前2686 年)开始就在这里多有发现。他的考古挖掘,对埃及和亚洲地区年代学的互相印证提供 了可能。埃及中王国文化对那里青铜时代中期的统治者影响巨大,许多王室成员墓葬中 发现的东西上都刻有埃及第十二王朝国王阿蒙尼姆赫特三世(Amenemhat Ⅲ,公元前185 5到前1808年)和四世(公元前1808到前1799年)的名字[4](P57-58)。
1939年、1940年和1946年,蒙太特先后在塔尼斯进行了重要的考古挖掘。塔尼斯这个 位于埃及三角洲东北部的遗址曾是晚埃及时代(公元前747年至前332年)下埃及第十九诺 姆的都城。这里进行的大的考古活动19世纪就有过两次,一次是1860年到1880年奥古斯 特·马利特(Auguste Mariette)的挖掘,另一次是1883年到1886年弗林德斯·皮特里的 挖掘。20世纪这里的考古活动主要是法国考古学家在进行。蒙太特1939年二十一和二十 二王朝皇室陵墓的发现本来是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 发现没有引起本应该有的注意。所发现的六个陵墓全都是用泥砖和从别的建筑上拆下来 的石块修建的地下陵墓,其中很多陵墓中刻有铭文。有两个陵墓的主人尚不可知,但其 余四座分别是普苏森尼斯(Psusennes)一世、阿蒙尼姆普(Amenemope,公元前993—前984 年)、奥索尔康(Osorkon)二世(公元前874—前850年)和沙尚克(Sheshonq)三世(公元前8 25—前773年)的。皮埃尔·蒙太特的挖掘收获颇丰,发掘出了很多金属制品,让我们了 解到当时这个地区叙利亚人的影响。在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有一个银棺和一个金面 罩很引人注目。这个金面罩和其他从塔尼斯墓地发现的器具是我们了解第三中间期(公 元前1069—前747年)皇室丧葬习俗最为重要的材料。作为塔尼斯挖掘的研究成果,1947 到1960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塔尼斯皇室墓地》[5](vol8,P285)。
虽然在这个遗址发现了很多古王国和中王国以及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 )的浮雕和雕像残片,但所有这些早期的遗存都是被人再次使用过的。蒙太特相信拉美 西斯遗址雕塑有理由让我们推断这个遗址应该是古时候的皮拉美西斯(Piramesse),塞 提(Sety)一世(公元前1294年—前1279年)和拉美西斯二世建立的新都城。但是,后来在 太尔·艾尔-达巴(Tell el-dab'a)和堪提尔(Qantir)的考古证实了那里才是皮拉美西斯 的真正遗址。塔尼斯最早的有记载的建筑是第二十一王朝普苏森尼斯一世(公元前1039- 前991年)时期建造的,他建造了环绕阿蒙神庙的巨大泥砖围墙(430m×370m)。二十一和 二十二王朝后来的统治者在这个神庙建筑群上又添加了很多建筑,第三十王朝的奈克塔 尼波(NECTANEBO)一世(公元前380—前362年)也在这里进行了修建,从沙尚克五世(公元 前767—前730年)和普萨美提克(PSAMTEK)一世(公元前664年—前610年)的神庙建筑中拆 下石头用来建造他的“圣湖”。在遗址的西南,神庙围墙的后面,是一个小的姆特(MUT )和泓斯(KHONS)神庙,有意思的是,亚洲的女神阿斯塔尔特(ASTARTE)也在这里受到崇 拜。这个建筑后来在托勒密(Ptolemy)四世(公元前221年—前205年)期间又进行了重建 。皮埃尔·蒙太特之后,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考古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着这个遗址[4](P2 82)。
W.B.艾莫瑞(W.B.Emery)和W.P.克万(L.P.Kirwan)1931到1934年在努比亚发现了属于巴 拉纳赫(Ballanah)文化的陵墓。这些发掘都是在阿斯旺大坝第二次升高之前的完成的。在这之后,世界考古界把目光都集中在埃及和努比亚地区来,纷纷前来挖掘。这是1970 年阿斯旺大坝完成之前20世纪50和60年代埃及考古挖掘的主要工作。下努比亚现在是世 界上一个考古挖掘做得最为完善的地区。那里的神庙,或者被迁移到了高处,或者被迁 移到了其他地区,如阿布·西姆波和菲莱。这一考古挖掘的世界行动对于文物保护和在 考古中科学地挖掘方法的引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论在挖掘方面还是在记录方面,都 引进了新的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大大提高了考古的水平。
除了上埃及的考古外,20世纪埃及考古在其他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孟斐斯( Memphis)古城墓地萨卡拉(Sakara)、萨拉匹斯神庙(Sarapeum)的新区域又有很多新的发 现。古代孟斐斯遗址在20世纪的系统考察,以及它与尼罗河古河道的位置关系的确定, 城市人口居住区的头一次被详细研究都是20世纪埃及考古工作的重要成就。
墓葬遗址的发掘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居民遗址的考察。有两个重要遗址最为引人注意 :艾尔-阿玛尔那(El-Amarna)和迪尔·艾尔-麦地那(Deir el-Medina)。这两个遗址的 发掘都不是20世纪开始的,但却都吸引了不同国家的考古学家到那里去做长时间的考古 挖掘。19世纪80年代阿玛尔那楔形文字泥板被发现之后,伍尔班·鲍日安特(Urbain
Bouriant,1849—1903)就在那里工作并写出了一部名为《太尔·艾尔—阿玛尔那的两日 挖掘》的著作出版。接着来的是我们都熟悉的皮特里(1891—1992),尽管他在这里没呆 多长时间,但很有成效。可很快他的成果就被由路德维格·鲍尔查特(Ludwig
Borchardt,1863—1938)率领的德国考古队的成果所淹没,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雕塑家图 特摩斯(Thutmose)的房间,里面有非常著名的内芙尔提提(Nefertiti)的胸像和许多杰 出的作品。20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了几个季节的挖掘和研究,对 埃及十八王朝晚期的历史及这个短命首都的研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 ,这个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迪尔·艾尔—麦地那是整个19世纪埃 及发现的一个重要源泉,在20世纪初意大利考古队也来到了这里,之后,乔治·米勒
(Georg Moeller,1876—1921)1911年到1913年也率领德国人前来。1917年,开罗的法国 东方考古所开始了他们在这个遗址的发掘,中间尽管有中断,但还是一直持续到现在, 几乎完全挖出了工人村和临近的墓地[2](P28)。
二、语言研究及年代学的发展
埃及学的两大支柱一是考古,二是语言。考古挖掘为埃及学提供材料,语言的研究为 埃及学研究解释这些材料提供武器。古埃及语言的研究自1822年商博良成功地破译了埃 及象形文字,经过了埃及学家们180多年的不懈努力,其语言和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在商博良之后的近60年里埃及语言的研究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1880年厄尔 曼(Erman)对晚埃及语的分析研究才开始了让埃及语研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他的研究 为埃及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奠定了埃及语言研究的坚实的基础。进入20世纪以来,语言的 研究走向了系统完备和科学之路。
埃及语研究在20世纪最突出的成就是埃及语研究的成型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 个阶段。阿多尔夫·厄尔曼(Adolf Erman,1854—1934)和柏林学派(包括K.塞特,1869 —1934;G.斯坦多尔夫,1861—1951),得到了英国学者B.甘(Gunn,1883—1950)和阿兰 ·伽丁内尔爵士(Sir Alan Gardiner,1879—1963)的支持。他们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取得 的成绩大多都是在20世纪完成的。阿多尔夫·厄尔曼和赫尔曼·格拉泊(Hermann
Grapow)在柏林出版了《埃及语词典》(Woeterbuch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一部几 乎穷尽埃及象形文字的大型词典。到这个阶段后期,古典埃及语法已典籍卓著非常系统 ,这阶段的第一个顶级之作是伽丁内尔的中埃及语语法(1927年第一版)。这是一部涉及 数千个例证的埃及语法结构大全式的著作,几乎每一种语法结构都囊括在内了。尽管在 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但作为奠基式的著作对埃及语言研究的发展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特别是在词法的完备上。
汉斯·雅阁布·普劳次基(Hans Jakob Polotsky,1905—1991)和他的学派的研究成果 构成了在第一阶段研究基础之上的发展,被称作埃及语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古 典埃及语动词句法的“标准理论”的提出。普劳次基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44、1965和19 76年。
普劳次基的“标准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动词的名词化,二是句法上的对 仗理论。在普劳次基之后,语法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如何对待他的理论的问题。是融合、 取代,发展还是干脆无视它的作为一个掌握了古典埃及语法全面模型概念的实用性。一 些学者想要证明它的错误或者提出取代它的方法,这些人中就有像J.P.阿兰(J.P.Allen )、J.F.鲍阁霍特(J.F.Borghouts)、M.克里雅(M.Collier)、J.约翰森(J.Johnson)和T.瑞特(T.Ritter)这样的学者。其他人则正好相反,支持“标准理论”,试图让这个理论 的实用性扩展到更大的领域,这些人中有L.德普伊特(L.Depuydt)、F.容格(F.Junge)、 F.卡摩哲尔(F.Kammerzell)、H.斯特辛格(H.Satzinger)和W.申克尔(W.Schenkel)。此 外,还有许多人试图走出“标准理论”语言结构的局限,创立新的方法来理解古典埃及 语的句法,尝试一条结合语意和语用学的词—句法的道路,这些学者中有J.F.鲍阁霍特 、M.克里雅、F.容格、A.罗普瑞诺(A.Loprieno)、P.维尔那斯(P.Vernus)、T.瑞特和W.申克尔。
“标准理论”和以前的方法之间的争论焦点是句法的问题。阿兰·伽丁内尔爵士假定 埃及语基本上属于闪语语法,因此,他根据这个假设断定动词词法和句法的大多数重要 的方面表现了时态,就是说,一些动词形式是“完成时”,而另一些则是“未完成时” 。这个方法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让人们据此完美而通顺地翻译了大量的埃及文献,但因 为它没有解释埃及语法的一切方面而遭到一些学者的抵制。其实,H.J.普劳次基作为“ 标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从来没有创立自己的标准的埃及语语法体系,但他却将他 的理论要点论述得极为清晰。其中一个要点是光凭借词法不足以据此完全正确地理解句 法,接着提出要根据句法研究词法。词法的变化只有在句法的框架内才能正确地理解, 而不是句法在词法的框架内来理解。很明显,这是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趋势,这个方法在 方法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标准理论”的中心是它的转换体系,根据这个规则,动词 被转换成名词、副词和形容词。根据习惯的观点,这个转换不仅是一个动词偶然的用作 名词、副词和形容词,而是认为这个动词就是名词、副词和形容词的一种特殊形式。这 个转换系统认为,一些词法上很容易看到的形式仅出现在特殊的句法中。然而,尽管人 们作了很大的努力,至今仍没人能够证明这个假定条件形式的真实。此外,许多动词形 式在转换理论中充任了其他角色而不是分派给它们的角色。埃及象形文字不记辅音,所 以,词形的变化在文字中很难显现,这对普劳次基的理论是一个潜在的困难。
1994年,沃尔夫冈·申克尔(Wolfgang Schenkel)出版了他的《图宾格尔古典埃及语言 与书写入门》(Tuebinger Einfuehrung in die klassisch-aegyptisehe Sprache und Schrift)的第二版,这本书没有采用普劳次基的理论,但却把伽丁内尔的理论同后来的 理论结合了起来。申克尔认为,理解埃及语传统语法的概念不断处于变化当中,没有哪 一个单一的理论能够宣称为正统。他在著作中详细地讨论了句法,特别是动词的句法结 构。
在历史学方面,德国学者爱得华·梅亚(Eduard Meyer)、厄尔曼(Erman)和克特·塞特 (Kurt Sethe)、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卢埃林·格里非特(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 和阿兰·伽丁内尔爵士以及捷克埃及学家加罗斯拉夫·切尔尼(Jaroslav Cerny)进行的 研究工作建立了古埃及历史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一开始,埃及年代学也取得了一个重要 的成果,其标志是1904年,德国学者梅亚发表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埃及年代学的 专著《埃及年代学》(Meyer,Eduard,Aegyptische Chronologie,Abhandlungen der K.
Preuss,Akad.Der Wiss,Berlin,1904.)。梅亚的埃及中王国及以后的年表直到现在仍然 是古埃及的标准年代学框架。1926年,法国学者威尔(Weil)在巴黎发表了《埃及年代学 的基础、方法和结果》,其结果是形成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原始框架。之后,著名年代 学家帕克尔(Parker)于1950年发表的他的《古代埃及历法》,1971年又出版了《埃及的 遗产》一书,其中详尽地阐述了古埃及年代学的材料、框架和研究方式,为埃及年代学 研究奠定了基础。70年代以来,年代学家就有争议的历史时期的年代学问题继续进行探 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三、中国的埃及学诞生发展于20世纪
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尽管中国人对埃及的接触可以追溯很早,两个文明 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但仅限于域外见闻的记录。真正的对埃及进行科 学的研究,我国第一人是夏鼐先生。夏鼐先生是浙江温州人,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19 35年去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 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 名誉所长等职。他在英国读书期间曾跟随英国考察队在埃及进行过考古挖掘工作,之后 又在开罗博物馆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学习古埃及语言的博士。
尽管夏鼐先生比较早地进入了埃及学领域的研究,我国解放后也有自己的学者,如刘 文鹏先生多年对古埃及的研究,但真正建立起这个学科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林志纯(日 知)先生于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开始的。1985年,我国史学界 三位老先生周谷成、吴于廑和林志纯鉴于我国在一些学科的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发出了填补我国埃及学、亚述学和赫梯学等学科空白的呼吁,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 《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的文章。接着又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Changchun)用英文发表了此文。从此,埃 及学作为一个真正跟世界接轨的以埃及象形文字和考古成果为基础的科学的埃及学学科 在中国建立了起来。东北师范大学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埃及学的研究者。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吉林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也先后有由东北师范大学培养的学者所开辟的埃及学教 学和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Howard Carter.The Tomb of Tut·Ankh·Amen,volume Ⅱ[M].New York,1963.[2]John Baines and Jaromir Malek.Atlas of Ancient Egypt[M].Oxford,1980.[3]Salima Ikram and Aidan Dodson.The Mummy in Ancient Egypt[M].Thames andHudson,1998.[4]Ian Shao and Paul Nicholson.British Museum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M ].British Museum,1995.[5]The New Encyclopadia Britannica[M].Chicago,1998.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 0002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