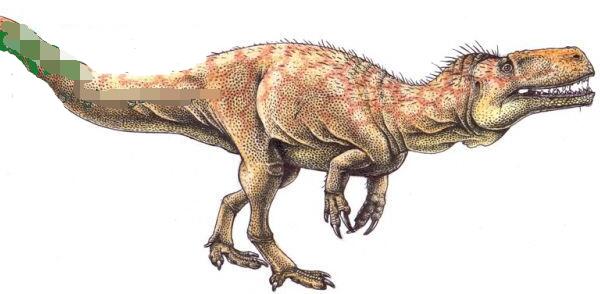邓聪:澳门半岛最古老的文化
一 澳门半岛的早行者
现代人类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因此,考古学与未来学同样是21世纪最令人神往的学科。一个地区人类文化历史起源的探索,往往是有相当吸引力的。1999年3月公布澳门最新的面积, 为21.45平方公里。澳门尽管很小, 同样无法避开本地人文历史肇始的重大问题。这篇短文试图讨论澳门半岛范围内现知最古老的文化。
有关最早期澳门半岛人类活动的情况,如果从文献史料入手,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第一:如据17世纪冒险家平托(F.Mendes Pinto)在1614年出版《远游记》(Peregrincao )中谓:“澳门从前是个荒岛,我们的商人兴建价值三四千克鲁扎多的房屋把她变成一个高贵的居民点。”(注:Fernao Mendes Pinto, Peregrinacao, Lisboa,Publicacoes Europa-America,1998,vol.Ⅱ Pp.342-343.转引自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页33。)平托的澳门荒岛说,与稍后英人来香港时所提及“香港岛上只有石头,无一处房子”(注:W.Meacham.Archaeology inHong Kong, Heineman Asia.1980.p.3.秦维廉氏亦曾批评此观点。)的说法,基本相似。两者同样出于欧洲外来侵略者之口,均故意无视两地原居民的历史。这样的荒岛说是别有用心,不必深究的。另一方面,澳门历史的工作者,又如何讨论澳门半岛最早人类的活动呢?1991年出版《澳门史纲要》中1277年一条,记述“端宗赵昰和张世杰等军民在澳门地区出海,遇飓风袭击,上岸栖居,并凭借澳门妈阁山和路氹高地击退元军。从此澳门逐渐有人居住”(注: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如果此说属实,则澳门半岛地区,迟到宋代才有最早人类的活动。最近有些学人蠡测,明代“闽人成为最早的澳门开发者”(注:徐晓望《福建人与妈祖文化渊源》,《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页33。)。此外,据文献资料记载,明嘉靖《香山县志》中“山川”一条,有“九澳山,其民皆岛夷也”,记叙了九澳地区可能已有居民。看来,根据文献资料,澳门半岛地区人类的活动,就只能上溯到明末。在宋或以前记载半岛上人类活动的说法,都并不可靠。当然,以上的讨论并不意味澳门半岛迟到明代才有人类的活动。如果我们从物质的资料入手,以考古学的角度考虑,对认识半岛上人类活动的历史,就可能有很大的改观。不过,物质资料或者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前提,往往极依赖古代遗址的保存情况。究竟半岛古代的遗址在这现今世界人口可能最密集的都会中,还能有幸存留下来吗?这又是半岛史前考古学发展中最大的难题!
二 半岛史前遗址厄运
澳门半岛的面貌,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在1840年,半岛的面积只有2.78平方公里。1991年半岛面积已超过6平方公里, 填海增大半岛面积达1.5倍。现代机械的怪手在半岛土地上不断移山填海, 半岛的古代遗址受到严重的威胁。
随着澳门半岛的都市化, 原来的古代遗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据1794年澳门半岛的地图观察,半岛的南湾及黑沙环尚保留有极其美丽的海湾。特别是半岛的南湾,清印光任《南湾浴日》诗尚有“海岸如环抱,新潮浴渴乌”之名句。过去南湾地理形势与路环岛著名的黑沙考古遗址极为近似,均为东北向西南伸延,朝东南面开口。估计昔日南湾海岸长度超过1000米,生态环境与黑沙也可能相当接近。这使我们推测过去南湾可能同样是一处内涵很丰富的考古遗址。然而,在1863年的前后,南湾沿岸一带由于填海等土木工程,沙堤已被夷平,可能存在的史前沙丘遗址,荡然无存。
此外,半岛的黑沙环沙堤,在地貌上亦具备史前考古遗址的因素。迟至1980年,现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杨耀林先生在珠海拱北一带考古调查,发现数量相当丰富的文物,出土遗物的时代横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据杨氏的研究,拱北遗址分布较广,南北长约1.5公里, 由北部的老虎沟至水涧山的南坡,向南到西瓜铺菜地、银海新村工地和拱北与澳门交界的关闸口。可以想见,这一条于《澳门记略·形势编》所提及的莲花茎,理应就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的大型考古遗址(彩版肆:4)。杨氏的调查中又报道:现拱北边防检查站附近地面尚有陶片和石器分布,在关闸口发现一件磨制精良的长条形石斧和一件青铜斧。(注:杨耀林、徐恒彬《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33~337。)90年代珠海拱北一带原有的遗址,亦被新填海及都市发展所湮没。澳门关闸至黑沙环一带迄今未发现过古代的文物,肯定只能归咎于缺乏考古工作所致。
澳门半岛地区的南湾和黑沙环两处有潜质的史前遗址,可能很大部分都在过去数百年间都市发展过程中被破坏。当然,半岛内是否所有的史前遗迹都已荡然无存,需要现代考古很精细的调查工作去证实。数年前,葡籍考古工作者,在半岛大三巴的附近,发现了一些早期人类文化的线索,为认识半岛神秘的古代,带来了一线希望。
三 大三巴出土石器
1998年4月18日笔者幸蒙邀请,出席澳门博物馆的开幕典礼, 获赠由澳门博物馆所编制的《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专刊。随后通过学习考古学者Clementino Amaro有关圣保禄神学院和大炮台的发掘报告,知悉在神学院的走廊范围的下层,曾发现一些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房子的柱洞遗址。按已发表的彩照考察,房子遗迹内发现有3至4处的柱洞。柱洞形制规整。柱洞的间隔有适当的距离。同时,报告中报道了发现的两件燧石石器。原葡文报告的中译本译文如下:“早于宗教综合体的文物方面,我们收集到了两件燧石手工艺品,是澳门半岛上首次发现的,因此我们计划将之向公众展出。其中之一是燧石核;长距离的搬运使之具有很高的磨圆度。第二件有用于加工植物纤维的一个碎片切口。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先生提出的概念,这两件物品属于所谓的‘台湾文化’。”(注:Clementino Amaro著,曾永秀译《圣保禄神学院和大炮台,考古挖掘和解读》,《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澳门博物馆,1998年,页114~157。)
这段文字在葡中翻译上,有若干处可待商榷。尤以其中所指笔者提出的“台湾文化”,应是“大湾文化”之误译。大湾是位于香港南丫岛西面的遗址,笔者于1990年及1996 年两度主持大湾遗址的发掘工作。1994年笔者与黄韵璋在第二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中发表了《大湾文化试论》,提出“大湾文化”之概念。

图一 广东及澳门出土打制石器
1.深圳小梅沙 2~4、7~8.广东西樵山 6.澳门路环村 5、9.澳门大三巴(均为1/2)
1999年3月8日间,笔者有幸于澳门博物馆内,直接观察及记录了上述大三巴出土的两件燧石石器(彩版肆:1、2;图一:5、9)。
澳门大三巴出土的两件燧石石器,均为打制石器。第一件MM2974,据Clementino Amaro指出,这件石器是石核。原葡文之中译为“长距离的搬运使之具有很高的磨圆度”。据曹晋峰的译文,葡文之原意为:“由于长距离(长途)搬运,该物已呈球状,并有从中剥取石片的痕迹。”按笔者的观察,此石器是以磨圆度较大的小河砾石作素材,石器之背面仍然保留有原河砾石之自然面,表面光滑。而腹面的破裂面一方,上面有清楚的打击点,沿边有连续性细微的剥离痕。这些剥离痕,很大部分可能是由于砾石在被流水搬运过程中,相互间无数次撞击而形成的。在破裂面左边的细微剥离面较集中,不排除此部分的剥离痕是制作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可能性。此件石器的带打击点剥离面边与背面间未形成典型的台面,或可称之线状台面或零台面。按石器的腹背两面特征显示,此件器物应称为石片更合适,而并非Clementino Amaro所说是“石核”。从石片打击点的打瘤并不发达,剥离面的波纹较密集等石片剖面形态分析,此件石片可能是两极技术的产物(注:邓聪《石器工艺学研究之一——两极法初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7卷,1986年,页19~56。)。第二件石器MM2975明显是一件石片,背面保存有较大面积的自然面,同样应为采自河川的砾石。背面有横向的剥离疤痕,估计是石核作业面旧剥离的痕迹。由于背面剥离方向与石片剥离方向相交错成直角,说明石核体在生产石片过程中不断转动,转换台面以剥离石片。台面呈三角形,由两次以上的剥离面构成,腹面为破裂面,打瘤发达,打面对边有若干细微的剥离痕,形成一处似凹口的形状。腹面左边有非连续性的细致剥离痕。这件石器可称为刮削器。严格来说,此件石器之二次加工痕迹并不明显。Clementino Amaro谓此石器用于切割植物纤维(注:Clementino Amaro著,曾永秀译《圣保禄神学院和大炮台,考古挖掘和解读》,《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澳门博物馆,1998年,页114~157。),这个判断涉及石器使用对象的研究。在未进行科学的石器使用痕的鉴定及从石器上检出植物痕迹以前,Amaro的说法只能是一种推测。
四 综合分析
燧石是一种脆性较大的岩石,破裂的石片边沿呈比较锋利的刃部,是一种优质的石器材料。史前人类比较常用燧石加工成工具。大三巴出土的两件燧石石片,素材均为河砾石。从两者自然面的差异判断,可认识两件石器来源于不同之河砾石,是由两个母岩生产的石片。两件石片都未见明显之二次加工痕迹。从制作技术而言,一者可能是两极法生产(Bipolar technique ), 而另一者则以徒手加击技术打成(Free -hand percussion flaking technique)。大三巴范围内发现打制石器及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房子柱洞遗迹,但由于石器并非发现于房子遗迹范围内,又不见较易辨别时代特征之陶器,这对大三巴地区所发现的遗迹及遗物年代的确定,确实是有一些困难。如果从澳门半岛本身来说,由于过去尚未发现过同类的石器,因此无从对比。笔者1995年在澳门与澳门大学中文系郑炜明氏所共同发掘的路环黑沙遗址,未见出土燧石石片工具。1999年3月1日至6日间, 笔者考察澳门艺术博物馆内所藏黑沙历年出土的文物中,未见有燧石制作的石器。按笔者目寓所及,路环的路环村附近,曾采集过一件燧石石器。1972年7月15日至16日, 香港考古学会一些业余考古爱好者在路环一带调查,在路环村附近修路范围内,采集到不少夹砂粗陶和几何印纹硬陶片。此外尚发现一件残石英环和玉髓刮削器(chalcedony scraper),后者长宽为5×2厘米。据原报告者W.Kelley分析,此件刮削器的周边均有细致二次加工。Kelley从加工技术考察,认为此件石器可能早于新石器时代(注:W.Kelley"Coloane,Macau." 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vol.Ⅳ,1973,Pp.12~18.)。1998年2月6日, 笔者与日本国学院大学加藤晋平教授在前澳门博物馆筹备室内,详细观察了此件石器(彩版肆:3;图一:6), 并由加藤晋平教授亲自完成该石器的实测图。原报告者将此石器的石质定为玉髓(Chalcedony),据笔者对实物的观察,此石质破裂面带油性光泽,与我们一般所称燧石较相似,即英文、法文及葡萄牙文“Silex”一词。这件燧石石器的周边, 除了好像是连续二次加工的特征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石器的刃部均被敲击成钝角。这种石器更像是一件加击其他石器或其他道具的特殊工具(picker)。笔者过去未见此实物前曾推测此石器为环玦素材,似未能作定论。
大三巴及路环村两者出土的燧石石片工具,在石质上有一定的相似。而路环村的石器与史前时代一些陶器可能是同时期的。ClementinoAmaro主张大三巴出土的两件燧石器, 属于笔者所主张“大湾文化”的范畴,亦不无道理。据现今所知的大湾文化,其年代距今6000年前后,广泛分布于环珠江口沿岸一带(注:邓聪、黄韵璋《大湾文化试论》,《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 395~450。)。然而,过去大湾文化中的燧石石器并不多见。其中如1980年深圳属于大湾文化时期的盐田小梅沙遗址内,除发现特征鲜明的大湾式彩陶盘、夹砂陶、刻划戳印纹陶外,亦在同文化层深2.4 米处出土一件燧石的刮削器,为三面刃,长3.2,宽2.3,厚0.6厘米(图一:1)(注:深圳博物馆编《深圳市先秦遗址调查与试掘》,《深圳考古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页53,图三。)。此件燧石器大小与大三巴出土的石片亦较接近。除此以外,1980年初笔者在西樵山考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广东西樵山的发掘,其后于西樵山遗址一带,采集到较多的燧石石片加工的石器(注:邓聪、盖培《中国旧石研究の新动向订正补遗——考古学シゼ—ナル283,1987》, 《考古学シゼ—ナル》,290期,1988年,页27~28。)。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曾骐教授曾研究西樵山的细石叶石器群(注:曾骐《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其中就有不少是由燧石加工(图一:2~4、7~8)。只可惜目前对西樵山出土燧石石器的年代并未得到最后的确定。曾骐教授主张西樵山的石器年代属于距今6300年前。现在环珠江口地区“大湾文化”或西樵山文化内都包涵有燧石石器,两者年代可能都在距今6000年前。大三巴出土的燧石石器及房子的柱洞遗迹,很可能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今后还需要更多科学的资料去论证。
大三巴出土的两件燧石石片,是迄今澳门半岛所知最古老的文化。饮水思源,感慨万千。此种思古之幽情,在1999年重新探讨大三巴出土史前的文化遗物,就有着格外的价值与意义。
幸蒙澳门博物馆惠示所藏石器资料,曹晋峰先生教示葡中翻译,谨致衷心感谢。
来源:《文物》1999年第11期
- 0002
- 0002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