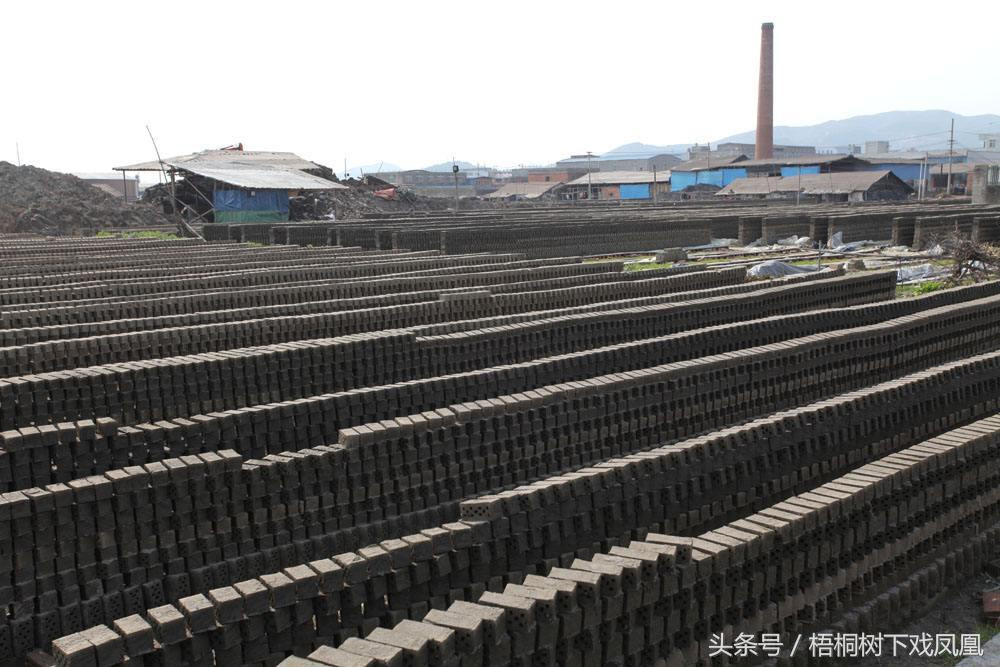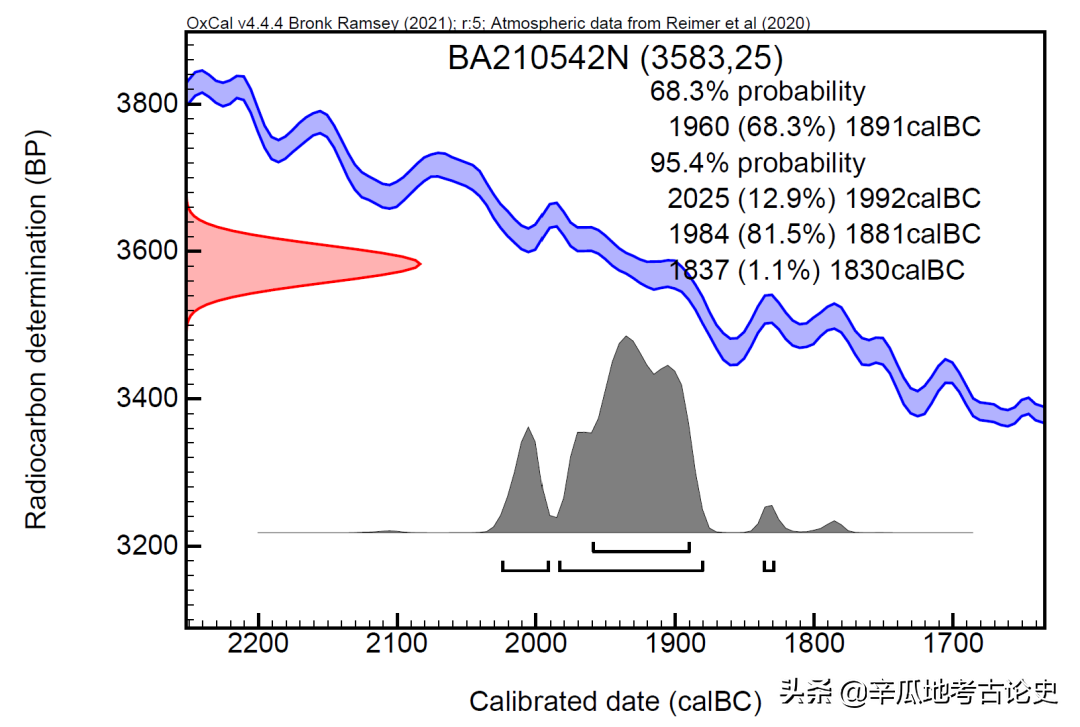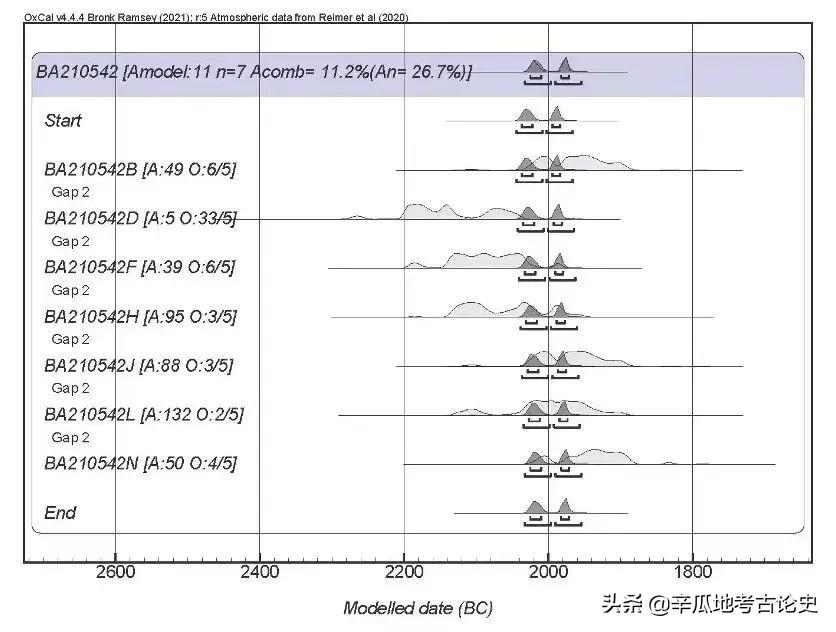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
有的学者把当前考古学的主流派,称为“传统考古学”,自称“新考古学”。他们的主张,曾有过变化,现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学者新近发表的论著,继摒弃了“类型学顶多可以说成是方法,层位学只能是技术”,以及“把层位学与类型学归为考古研究的中间理论”的观点之后,也已认为层位学与类型学同为考古学的方法论了。看来,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有些趋同。这是好的现象,令人高兴。不过,重要的分岐,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他们又提出了“超新考古学”的新识。
本文,就他们新近提出的论点,归纳如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问题
考古是广义史学中的一个学科。透物见人,研究历史,是考古学区别于狭义史学的主要之处,也是在这点上,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存在着某些原则的区别。
可是,“新考古学”或者“新阶段的考古学”(为简便起见,这里有时称为“新段”)则主张要“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看待考古学文化”,说“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极普遍意义的概念,它进入某一学科,常常变成一种认识工具,使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客体可以有更好的把握。文化这一概念进入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文化的领域,使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作出整体性的思考,这正是科学进步趋势的一种表现”。用意可嘉。实际怎样,却可商榷。
什么是人类学的文化。它在人类学中,是一庞杂的概念。当今包括“新考古学”者在内的中国“新段”学者,推崇的《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美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说:“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点和态度”。作者还同时认为动物后天所习得的行为,亦属“文化”。“新段”论者对人类学的“文化”的任何定义不作说明的情况下,即以为其范畴应包含物质的(或称技术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或称意识的、观念的)三个方面,考古学家应当研究具有这种含义的文化的进化发展过程”。实质上,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形式的表达。这从来是狭义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考古学“研究工作的全部目的是重建已逝生活(彼特里)”。如何“重建已逝生活”?正如“新段”论者所说,是通过“陶器、工具、武器、装饰品、房子、墓葬形制及死者葬式等等一系列形态特征及其组合的”变化,“了解人们群体的发展、迁徙和相互影响”。这当然要涉及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个方面,亦即人与自然、人和人以及为了实现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制度及意识形态,和表现生活及感情的艺术。可见,“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来看待考古学文化”,并未给他们称之为“传统考古学”增加什么新的内容。
人集结为群,或人的群分,人是以群或人、群为单位进行活动,创造历史。狭义史学有地区史、国别史及世界史之分,民族学似村社、社区、民族和族群,或以氏族部落、宗族、部族和民族划分人群,考古学则以考古学文化区分人类的不同群体。此理自明,均是从自身研究对象出发,以达到具体地客观地研究客体,以便在坚实的基础上,从微观进入宏观,即对人类作总体的考察。正如不能以识别民族的标志当成研究民族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一样,考古学也从未以识别考古学文化作为它研究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这是“新段”论者理当明白的。然而,他们在不顾忌自己文章中指出的“他们研究工作的全部目的是重建已逝生活(彼特里)”的同时,硬将识别考古学文化的标志,说成是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显然,这是把“新考古学”描绘成巨人的时候,先得把“传统考古学”打入小人国。
为此,他们还惊呼:“在很长时间内,陶器的分类,即其分型、分式、分期几乎占有考古学研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陶器的类、型、式与期,是不同的概念。陶器的分类不等于型、式与期的划分,因此,“即其”两字,似乎使用得不确切。至于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扣在“传统考古学”头上的一顶帽子。将陶器作类、型、式、期的区分研究,是划分考古学文化、探讨考古学文化谱系和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必须进行的工作。不如此,岂不是把研究对象搞成一锅粥!其实,学术研究的地位,是相对于资料的积累程度及所可能吸取的信息而言的。可以说,对陶器进行的区分类、型、式及期的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站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总之,考古学是广义史学组成的一个部分。它的任务是研究历史的,而历史自当包含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个方面,或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内容。因此,“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来看待考古学文化”,不仅未能给考古学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而且,由于它舍弃了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标志,则将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混乱。至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进入某一学科,常常变成一种认识工具“这种把研究对象可变成认识研究对象的工具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同时,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那样,考古学只能研究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且,也永远难以全面地揭示这一侧面,在这一现实面前,作乌托邦式的追求,只能有害于科学。
(二)“新考古学”到底新在哪里
我在1992年接受《东南文化》的采访中,已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意见。现在他们把对古代居民进行的环境研究及聚落研究,以及对考古学所见的人工或自然遗存进行的计量研究以及进行的测试及鉴定,说“是在60年代以后考古学新阶段中出现的”,并把至世纪中叶,或60年代以前的考古学,称之为“传统考古学阶段”。所谓“考古学新阶段”,实际上是他们以往鼓吹的“新考古学”的别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径直地言之为“新考古学”了。
同时,他们又说“对于传统考古学和以后的新阶段的考古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能够准确表述其理论、方法特点的专门名称,表明考古学的理论思考尚不成熟”。既然如此,划分“传统考古学”与“新阶段的考古学”或“新考古学”的标志是什么,又为什么要作此划分呢?
“‘层位论’和‘形态论’,则是传统考古学的两大方法论支柱”,“文化论”类似于考古学理论中的本体论”,“既有本体论,又有方法论,从而构成了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框架”。这是他们提出的新认识。据此,又如果将“文化论”中被他们改造的那部分剔除的话,那么,被他们称之为“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思考,并非“尚不成熟”。事实上,正是依赖被他们称之为的“传统考古学”,使考古学成了广义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改变了狭义史学某些领域的面貌。看来,“尚不成熟”的只是“新考古学”了。
且看他们说的“考古学新阶段”的那四论吧!首先,运用自然科学手段鉴定、测试考古学发现的人工及自然遗存,无疑,给考古学研究增加了不少信息,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信息,从而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但是,是否称得上考古学上的方法论,很值得怀疑。
其次,考古学的环境研究和用科技手段鉴定、测试古代人工及自然遗存,均非起始于六十年代,同时,包括论者所说的计量、研究在内,又不受制于层位学与类型学,或者其结论及价值,仍需接受层位学及类型学的检验与评估。更值得注意的是,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的严文明,本人就是反对“新考古学”的。至于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则根本扯不进聚落研究,因为他讲的是文明的起源、形成以及走向专制帝国的道路问题,那里是“聚落论”所能涵盖的。
再次,论者所提到的那四论,是包容于“传统考古学”之中的。没有一项对中国考古学的进程,产生过基本性的影响。看来“传统考古学”并未成为传统,难以成立的只是“新阶段的考古学”或“新考古学”。
众所周知,六十年代初,我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其时,仅有的三大考古杂志,不是停刊,就是出不满期,肚子刚刚吃饱,又得接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不但缺乏搞学术研究的宽松的政洽环境,甚至停止了一切学术研究。事实上,他们列举的被认为属于“新阶段的考古学”的成果,除少数一、二种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外,绝大多数都是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那么,他们认定“新阶段的考古学”于60年代就开始替代“传统考古学”的说法,不仅缺乏根据,而且也太不顾忌时代了。像他们讲的那样的好事,岂能始于这个年代!不过,他们这样说是自有目的的。恕我直言,无非是和路易斯宾福德挂上钩,把中国考古学的过程,说成和美国一样。这就太不考虑中国的实情了。事实上,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的,既不是宾福德,也不是“新阶段的考古学”,而是夏鼐和苏秉琦。
(三)走向未来的道路
有人说,考古学的未来,是“全息考古学”。
物理学认为宇宙是个磁场。气功师接过这话,说人是万物之灵,是这磁场的一部分,经过气功修炼,就可认识这磁场,发现宇宙的规律。其中的道理是,“部分可以映射整体,时段能够映射发展过程。”跨出真理一步,就是谬误。
不过,“全息考古学”论者,是在探索科学,敢持谨慎态度,说“现在提出的关于全息考古的认识,只能算作是有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启示,只是一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理论或思想”,“并非在于它的现实可操作性,而是它的思想前瞻性。”
言到“前瞻性”,似乎还应该说,“全息考古学”的出现,是现代考古学,甚至当代的整个科学消亡之时。但是,依哲学中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说,人们的认识,只能接近绝对真理。所以,“全息论”仍不能全息。
让我们从神话般的世界回到人间。
“考古学是科学,但也可理解为艺术。”前句话是对的,后一句话,值得商榷。
“说考古学也可当作艺术,还在于其研究对象又往往是艺术的。”依论者的表现主观愿望,在事物的分类中,则属于艺术,这对艺术的界定,则对象制约研究,限制研究者的自由表现,难以实现论者所称的表现主观愿望的艺术。艺术史归之为科学,就是这个道理。“如把考古学解释,看作是追求科学性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其中既有客观性的东西,也有主观性的内容,那也就不能排除其艺术性的成分。”如此说来,一切含解释性的科学,都“可理解为艺术”。把“考古学研究当作艺术的自由创作”只能导致谬误。这是科学工作者力求回避的歧路。受研究对象限制产生解释性的错误,或因主观能力而出现的解释性的错误,往往是科学工作者力求避免而又难以避免的现象,但这都是在客体这一舞台上进行的活动,则不能归之为“表现主观愿望”的艺术。
应拒入“艺术论”为谬误启开的方便之门。更不能倒退到文艺复兴时代。因为,考古学走出了艺术史的窄径,早已迈进了史学的原野。
什么是考古学?简单地言之,就是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依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又高于自然界。相互之间,存在着关联;运动规律,却有区别。以自然规律替代考古学对象运动规律的研究,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有害于考古学的发展。
衡量科学水平之高低,在于对同一现象吸取的信息量及阐释之深、广程度。
层位与类型是遗存的自存形态。依据层位与类型,才能正确地揭示遗存,从中获取遗存的基本信息。科技能帮助考古学者从遗存中取得仅据层位及类型难以得到的消息。人们对遗存的揭示、解释是否正确,以及研究和评估科技从遗存中吸取的信息,均受制于层位学与类型学。层位学与类型学贯彻于揭示、研究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矛盾的始终。科技的巨大进步,将助动考古学的发展,然而,考古学的未来革命,最终取决于对考古学对象运动规律的把握与运用程度。
透过遗存层位与类型,方能探知考古学对象运动规律。考古学前进的必由之路,是深化层位学与类型学的研究。
层位学与类型学,同考古学的实践,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方法、理论对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实践却是方法、理论生长、发展的土壤。在揭示、研究遗存的考古学实践中,应不断推动层位学、类型学的发展。只有从考古学实践中探索、推进层位学、类型学的发展,并用进步的层位学、类型学指导考古学研究,同时,对科技及其它学科持热情态度,敞开大门,吸引它们参与探索人工及自然遗存乃至遗存主人的奥秘,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已经形成的轨迹,中国考古学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健康地走向未来。
来源:《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24日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