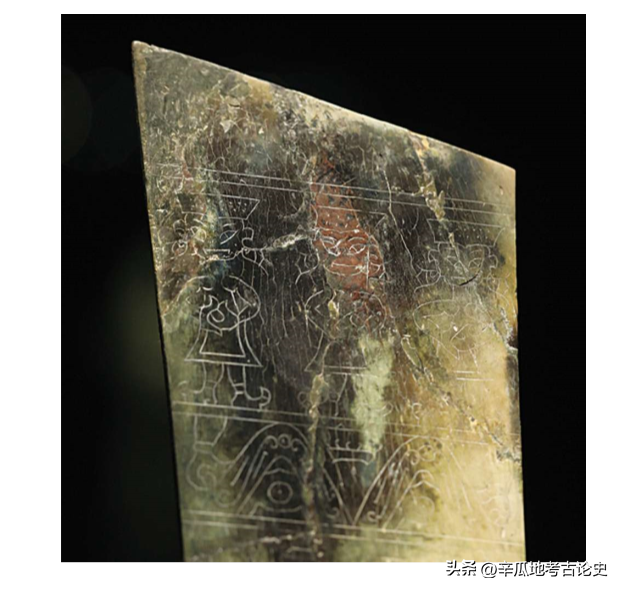裴安平:当代中国考古学学科重点的转移与考古学文化的整体研究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讨论已引起整个学科的瞩目,它表明这个学科正处在新的历史变化时期,并促使人们对现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对未来进行积极的探索。
一 中国考古学史的简要回顾与当代学科重点的转移
任何学科之所以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相应的生命力与价值,都在于它有逐渐逼进学科终极目标的能力。
中国考古学以一切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存为基本研究对象,以阐明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规律为最终目标。但就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言,因受不同时期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局限,将会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自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揭开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序幕以来,本学科已走过了70周年的历程。作为这段历史的结果,无论具体发现与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对世界考古学的兴起与成熟,中国晚出了半个多世纪。因此,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人们既可看到不同时期国外先进技术、方法与理论思想影响的烙印,又可感受到本国学者致力探索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1921-50年代初,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中国考古学几乎全盘引进、消化、吸收了关于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以及有关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具体研究目标则是发现考古学文化,重点解决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梁思永先生“后岗三迭层”的发现,夏鼐先生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苏秉琦先生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与《瓦鬲之研究》,都是当时这种工作的代表。又基于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深厚,中国考古学初创伊始,就开始了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的学科倾向。不过,那时侯这种研究多数并未跳出“证经补史”的“金石学”窠臼。
50年代中—70年代中,这时期考古学新鲜资料大量涌现。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实践空前活跃,不同时期、地域、面貌的考古学文化迅速覆盖中国境内的主要地区,整个学科对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与性质的辨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国际考古学界肇始于30年代对传统考古学研究目标的反思,尤其是“考古研究所”这一名称在苏联的再度复出,深深地激励着年青一代考古工作者,学科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见物不见人”倾向的批判。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将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作为学科的终极目标,并促使人们深入地思考如何将具体的考古学研究导向历史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科开始了将器物型态学研究引向对考古学文化发展系统的考察,将墓葬器物组合的研究引向对社会组织状况的探讨。同时,还开展了关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
70年代中—80年代中,这是学科史上第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由60年代初的萌芽,经酝酿走向成熟。它与稍后不久“文化因素分析法”的提出一道,表明关于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辨析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整个学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考古学文化体系的构筑之中。与此同时,许多关于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著述也陆续刊印,又表明在经过长期探索与发展之后,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中国特色业已初步形成,并与上述二种理论和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国自己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论体系。
以上三个时期,各自的研究互有侧重,大体过程是:年代序列→文化性质→文化体系。这是学科研究不断深入与发展的轨迹。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具体阶段的目标实质上都是围绕考古学文化物质形态面貌的揭示与认识而展开的,使用的方法则是地层学、类型学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理论。正因此,这些时期又可统一归纳为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如与世界考古学史相比照,它的工作大致相当30年代以前传统考古学的范畴,即以资料的分类整理作主要内容的基础研究阶段。又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积极影响,在重点从事传统考古学作业的同时,学科的总体思维与实际工作并没有都停止在那个基础上,而是一直在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事实上,构筑考古学文化体系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文化关系的认识,也包含了开辟历史研究途径的意义。然而,基于学科重点的局限,那方面的工作一直并未占有支配地位。
80年代中期以后,学科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要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可概括为三点。
第一,以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为标志,表明学科的基础研究已大体告一段落。尽管遗留的工作仍然相当艰巨繁重,进一步普及地层学、类型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工作的总体性质已不再是学科的主要任务,而属于填空补漏,且永无止境。因此,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学科研究重点转移的时机与条件均已成熟。
第二,自二次大战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客观世界整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大量与考古学结缘的新学科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领域中的运用,使考古学获得了摆脱地层学、类型学垄断研究资料的能力。关于古代人类生活的信息量成倍增长,从而又为学科研究重点的转移提供了保障和可能。
第三,不满于学科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认为尽管已经在历史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无论方法还是思维模式都已落后。而且还由于过分强调物质型态研究的重要性,使得许多本来可以探索的课题和方法的运用受到扼制,延误了时间,扩大了与当代世界考古学整体水平的差距。这些认识又因近年国际上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新进展、新思想逐渐为国人所知,而日趋强劲,成为要求学科加速研究重点转移的内趋力。
由以上原因共同促成的变化现已日渐明朗,其核心内容是由过去对“物”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关注。不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尽一致的发展趋势。
第一,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
它以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变与问题,并进而概括历史发展的宏观规律为特点,着重解决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课题。在辽东“女神庙”遗址发现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工作,即标志这种研究的实践活动已拉开帷幕,而不久前展开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则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二,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学
目前,它更多的还只是表现为一种舆论准备。它是对“见物不见人”现象强烈不满的产物,并试图借鉴国外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可取之处,为改变学科的现状探索道路。其主要思想是,呼吁以人类社会的具体生活为研究重点,并要求为此而加强以聚落为纽带的人类文化行为的研究。同时,它也希望把遗物的类型学研究引向对人类行为意义的揭示,希望大量利用自然科学手段来更多地获取人类的行为信息,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在以上二种趋势中,前者的具体目标显然比之后者更为宏观,而且更贴近当代中国考古学已经奠定的资料基础与研究方法。它以人类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事变为核心来组织研究的思路,也与狭义历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这种研究的初期,通过已有的遗迹遗物即可获得一定的具体认识,更容易使人对它产生理解和共鸣,感受到它的意义。
后者的目标对于习惯于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事变过程的人来说会感到某些捉摸不定。这一方面是因为表现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行为是多方面的、具体的,有些也不一定能直接作用于历史事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与以往直接由类型学研究上升为历史研究的传统模式相违背,而在“物”与“史”之间增加了一个中间环节。尽管中国考古学对这种研究或许并不陌生,但那只是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为不够,更没有上升为重要的阶段性目标,这种目标的潜台词实际是主张以“人”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主张由“人”见“史”,而不是由“史”见“人”。
究竟在未来发展中,学科会倾向于哪种趋势尚难预测,但是,这二者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历史的重大事变及其反映的规律实际是历史科学的永恒主题,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它的意义。然而,从认识的过程而言,则会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我国考古学基础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们互为基础或发展。这就说明,要真正廓清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形式、过程,不同地域的不同差别,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制定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否则,任何课题的讨论都将流于形式,难有深入的结果。
纵观学科以往历史研究的状况,几乎所有重大事变都已不同程度地被涉及过了。但是,引向深入的过程总给人步履维艰的印象。
或许资料的局限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然而,资料总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在资料面前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并把全部研究课题的提出与讨论都寄托在某些具体遗迹遗物发现的基础上。似乎没有墓葬的大小分类,随葬品的多寡、同穴男女墓葬式的区别,就无缘提及阶级的产生。没有城堡、青铜与玉制礼品、甲骨文、庙坛冢,就无力确定文明的起源。当然,要说明问题确实需要典型的资料,这是考古学的基本特点。但单纯的依赖这种资料则无异于对“宝物”和“宝迹”的看重,轻视必要与深入的基础研究。以前,为了搞清楚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实际主要是陶器的面貌,我国曾发掘了数以百计最好的遗址。但是,在这些发掘中,大量与那个目的无关的宝贵信息与资料则失之交臂,以至新的课题被提出时,又不得不再次掀起新的发掘高潮。这种仅限于单独目的的工作传统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前不久告一段落的文明起源讨论已证明,少数典型遗存充其量只能提供一种现象,一些线索,要真正理解它、说明它,还需要更好地利用那些曾被忽视过的遗存。可是,在这方面,我国至今尚缺乏一种有助于各种信息与资料全面提取的机制、指导思想和课题中心。因而也就不能促使所有的考古工作者都主动地去利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主动地考虑改造传统方法,使之满足新的信息获取的需要,
与“被动”获取信息联袂的研究方式是只注意遗迹遗物表面特征的揭示与概括,它是长期主要从事类型学研究产生的负效应之一。由于类型学的最大特点是只揭示区别,不探讨原因,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学科历史研究中导致了普遍的“大手笔”、“大写意”与具体认识的“模式化”倾向。不久前,有人在撰文讨论洞庭湖平原与长江三峡境内大溪文化时期遗存的性质时,就简单地套用生产工具数量、种类愈多,个体形态愈大,生产力水平就愈高的模式,得出三峡地区经济较前者发达的结论。实际上,它仅仅表现了当地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增长,与生态条件优越的洞庭湖区的生产力水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那里两岸阶地狭窄,土壤贫瘠,花岗石基岩风化严重导致地表大量含砂,农业规模受到多种制约。又由于山高林密近水,石料来源充足,渔猎活动频繁,遗址常见厚几十公分的渔骨堆积与大量石器。此外,为了砍伐森林,并适宜砂质土的挖掘作业,又造成了工具的大型化倾向。这样,工具就有了门类齐全、数量众多,大小配套的特点。由此一例不难说明,在具体遗迹遗物与历史问题的探讨之间,必须插入一个了解人类生活、行为及其与环境关系的中介环节。否则,就很容易形成正确的类型学比较结论与错误的历史认识之间的矛盾。同时,它也说明,为了克服这一矛盾,现在,更需要注意的是把那些物质遗存都返回到人类实际活动的研究中去,而不是急于将它们在类型学比较的基础上擢升为一种历史证据。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国外考古学积极变化的影响,我国也开始提出了要“复原历史”的问题。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复原”已经失去了平衡,具体表现是只侧重经济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并将所有遗迹遗物的信息提取都纳入这种研究的轨道。凡动、植物残骸与工具,首先考虑的是由其反映的生产门类与生产能力的大小;凡村落布局、房屋建筑与墓葬,主要涉及的则是社会等级分化与组织形式。至于各种遗存所反映的文化传统、观念、信仰、与外界的交流、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等等,均在研究中处于从属地位。如能兼顾,不失锦上添花;若无力涉及,也与上述研究无妨。仰韶文化“人面鱼纹”所以较长时间被看作渔猎经济的象征,就是这种“复原”模式的写证。
正因此,基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学科研究活动的现状与实际需要,并为了实现学科的终极目的,使学科最后成为真正的“历史学”的考古学,目前,完全有必要首先成为“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学。历史是人的历史,只有真正理解了人的具体社会活动及其文化,才能理解历史,重建属于人,而不属于任何理论与模式的历史。
二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整体研究
对考古学文化进行整体研究,这是近年因学科重点转移,以及考古学文化本身研究走向深入,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
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早已成为全部考古学研究的关键与基石,它的概念在实际研究活动中更起着影响全局的理论导向作用,并直接影响考古学对人类活动与人类历史的研究。然而,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仅是一个遗存的分类学单位,而且包含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理解。正因此,目前,这个概念又在经历变化,要么维持以往的“一元结构”,要么逐步过渡为“二元结构”。
所谓“一元结构”,就是强调它的物态性,把它只当作一种纯净的物质文化。“二元结构”,在承认具有物态外貌的前提下,更强调它是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的统一。二者的进一步区别还在于,前者割裂了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的有机联系,使它们之间除了“反映”与“被反映”之外,别无其它。这种类似“镜子”与“物体”般的单向关系可描述为:
反映
物态文化─→非物态文化
后者把物态文化看作是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尽管对非物态文化的认识要受到物态文化的某种制约,但非物态文化不是被动无为,而是在物态文化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中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它们的关系可描述为:
反映
物态文化─→非物态文化
作用
长期以来,那种“一元结构”的认识一直在考古学中居主导地位。有关的权威性阐述是1959年由夏鼐先生总结提出,并于80年代中再度重申。他指出,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考古学文化”条,对此更有具体解释,“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地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即可以称为一种‘文化’”。
上述概念从提出至再度重申与解释的时间恰好与我国考古学以基础研究为工作重点的主要时期相吻合,这就说明,那种概念和认识与当时整个学科的发展背景、实践活动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既是那个阶段实践的需要,又是那个阶段实践的总结和反映。
5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田野考古资料的大量涌现,学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基于我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多源性与多样性,分类整理更显其极端重要。可以说,没有分类就没有中国考古学。根据分类学的原理,分类标准的可比性必须与事物某方面的特点或共性相联系,且标准要明确、简要、便于掌握。虽然物质遗存本身含有多方面的性质,但所有的性质无一拥有直观、具体的特点。在这里,分类标准的相对性构成分类的合理性。因此,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及其要点对于统一分类标准,规范实际操作过程就有了十分明显的意义。事实证明,在长期利用类型学进行的分类研究中,我国考古学所总结的,包含“典型器物”、“典型组合”等概念在内的“典型因素”分类法,其学科的理论依据即源出于此。
此外,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科内部曾存在一种倾向, 以为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只需以具体的实物为其资料,或以实物为其立论的根据。然而,这种割裂整体与部分的联系,孤立片面地将具体考古资料与历史问题挂钩的认识和方法,实际并不了解考古资料的真正特点,因而其作用只能是“证经补史”,根本不可能升到“阐明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正因此,以往那个概念中所指出的“共同体”的整体性给予人们重要启迪。它把孤立分散的各式“古物”联结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实体,从而使考古学对历史的研究获得了客观基础,有了学科自身的立足点。为此,立足考古学文化研究历史现已成为学科的普遍共识。
然而,任何科学概念都是相对的。随着学科的进一步,“一元结构”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也逐渐显出了相对过去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它制约了考古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助长了致力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倾向。
虽然国内已有的考古学专门著作都曾对学科的性质与宗旨有过明确的阐述,但研究者更多地还是凭自身的体验来理解和确定工作内容。长期以来,由于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考古学文化的物态性,一方面又在实际工作中大量从事这种物态性的研究,遂使许多考古工作者很容易就在它们的引导下,将具体遗迹遗物的形态与组合分类、排比当作了全部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并把考古学文化的发现、识别与划分看作学科的基础研究,把文化的年代与谱系看作是历史研究。即使今天,仍有一些考古工作者由于过去工作形成的惯性,看不到整个学科研究重点正在转移,而一再强调物质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研究物质文化的排列组合才是考古学的本来目的。实际上,考古学研究物质文化及物质文化史都只是一种手段和途径,不是目的。
其次,它妨碍了考古学文化与文化性质的正确划分和认定。
由于不承认非物态文化对物态文化的有机作用,并在实际研究中依赖遗迹遗物的表面形态与组合特征,从而使大量考古学文化与文化性质的正确划分和认定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讨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里头文化本身只有四个期别,但关于这些期别文化属性的意见却多达5种,已将各种可能性涉及无遗。对此,人们不能不对引出众多相左意见的理论依据提出质疑。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在同地区前后文化的交替阶段,同时期几种文化的交错地带,以及同时期同地区并存几种文化且势力互有消长的各种遗存性质的研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学科内又出现了各种遗存竞相“升级”的趋势。即原本属于同一个“类型”下面的遗存,现又分化出好几个更细小的“类型”,而以往的“类型”则晋升为“文化”,“文化”则晋级为“系统”。这或许可视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表现。但问题是,围绕各种形态与组合差异进行的这种排列组合研究,究竟以什么作为固定级差的客观标准。显然,在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差异”既是线索、依据,又是标准。这样,它就使上述各类问题的解决都陷入了无力自拔的“怪圈”。“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毗邻的二处遗址,甚至同遗址的不同地域,同一遗址的上下两个堆积层位也无例外。因此,物质形态的排列组合如果再不引进人类的社会生活,一味只注意它的“差异”,那么这种研究不仅永无休止,也没有任何意义。这说明,利用物态文化的本身来认识物态文化,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并难以在复杂的历史与各种人类活动频繁的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二方面使问题都得以廓清。
与以往概念局限性逐渐显露的同时,作为它的一种响应,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在许多考古工作者的实际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实和扩展,形成了“二元结构”。
洛阳地区发现的东周墓葬,部分可以烧沟为代表,部分可以洛阳中州路东、西工段和王湾为代表。前者,器类组合工整,器物形体大,制作精细,泥质为主,烧成火候高,器表打磨光滑,常见暗纹,器体外部仿铜附件式样精致繁多。后者,不仅器类组合与前者有较大区别,组合规律性差,且个体小,烧成火候低,极少暗纹,多素面,几乎不见仿铜装饰附件。对于这些墓葬,有的考古工作者曾依据传统的概念,将它们划分为二个不同的地方类型。但这种划分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虽然这些墓葬在具体的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差别”,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组织结构,这些“差别”应该是表现了墓主人的阶级地位不同,而不是文化性质差异。由此可见,在这里,“文化”已经从单纯的物态性质转化为物态与非物态的统一体了,成了一定的时空范围中包含各种社会阶级关系在内的“文化”。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那些墓葬又被统一起来了。
1978年湖南资兴旧市镇发掘一处战国墓地,共80座墓葬。在那里,大多数墓葬随葬品中与“楚文化”完全类似的器物至少占50%或更多。据此,过去的研究全部将它们归属在“楚墓”的名下。显然,这种研究自有其根据,并不违背那时期考古学文化概念的精髓。但是,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地及邻近地区春秋时期土著墓葬及发现,在那些战国墓的器物组合中,存在一种“无形”的文化传统与“有形”的具体面貌相互背离的现象。即当地居民面对“楚文化”势力的强烈扩张和影响,部分或全部借用外来楚文化的器物表现自身源于春秋时期的文化传统。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墓葬中的楚文化面貌日益明显,甚至完全“融合”。类似“貌合神离”的现象,事实上,在许多历史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以往的研究过分拘泥它们的物态性质而未能发现。正因此,透过“楚文化”的外貌,着眼于它们的文化传统内涵,那种土著文化就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考古学文化“二元结构”的体现。
由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的考古学文化理论实际已经落后于实践活动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发展,并为了开辟考古学文化整体研究的理论道路,重新定义考古学文化概念已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长期的研究成果,考古学文化应该可以理解为:一定的时间与地域范围内,由其中的人类所创造并反映其各种社会活动及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有相应外貌特征的遗迹遗物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或许并不成熟完备,但它至少希望表达考古学文化的“二元结构”,并希望由此恢复人类活动与物质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恢复考古学文化的整体研究。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一方面是出于它自身“二元结构”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学科重点转移强化人类活动研究的需要。它主要有二个基本点,(1)在研究过程中,要实现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的相互联系与作用;(2)在研究内容中,要包括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此,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造传统的形态学研究模式,大力加强以聚落为纽带的综合研究。
第一,改造传统的形态学研究模式
(1)研究内容的拓展
长期以来,传统的研究模式一直坚持以文化的年代、性质与相互关系为其主要内容,并取得了不容否定的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学科重点的转移,那些内容已不再能满足更深层次研究的需要,如果说,以往更关心的只是那些能与其它“文化”或“类型”相区别的宏观地方特征。那么为了认识同一文化中各聚落与聚落,聚落内部各区域,以及各区域不同遗迹现象的功能、性质、互相联系的方式与结构,现在则必须强调对各种遗迹遗物形态与组合细微差异的区分,甚至对各种动、植物遗骸、陶器碎片、石料残片的形态、微痕也要予以充分注意。这也就是说,研究的范围与深度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予以扩展,以便获得更多的人类活动信息。
(2)研究方法的改造
只要学科仍以遗迹遗物为基本研究对象,类型学的方法论意义就将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不仅只是一些具体的分析技术,还包含了利用技术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过去,因考古学文化一元结构理论的局限,类型学在实际作业中,绝对排斥人类活动的因素在遗迹遗物分类与排序中的影响,也不考虑是否有必要使主观的研究与客观的实际过程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使原来可能分属不同阶级,具有不同意义,以及可能代表不同生活侧面而难以比较相互重要性的因素,全部统一在泛形态与组合的尺度下,从而导致结果只具有形式逻辑的真实性,降低了历史真实性的普遍水准。为了使研究的逻辑过程尽可能实现与历史过程的统一,并为人类活动的研究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在积极探索改造传统方法的途径。他们的主要思路是,变分析的角度由“物→物”为由“人→物”。其中,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
在那里,研究者首先并未把着眼点置于随葬品的形态分类与排比,而是把暗示了某种人类活动与制度的墓葬等级分类置于研究过程的首位。然后,再依不同墓类分别排比各自随葬品的形态演变序列。结果发现,同类器物出现在不同墓类的时间先后不同,且彼此间的数量、质地、纹饰、颜色、工艺等都有重要差别。显然,这种方法不只是墓葬分类与分期前后秩序的简单颠倒,而是指导思想不同,将那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它所同步揭示的器物在时间、空间、社会三维结构中的意义及运动过程,使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更多的历史真实。
关于楚文化渊源探索的最新思路同样也具有改变传统方法的意义。它首先致力于把遗迹遗物与社会的等级结构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关于楚文化多元系统的认识,并以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楚文化”的主要代表。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分别探讨不同阶级文化的特点及其来源。尽管统治阶级的文化在统一的“楚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尚需进一步深究。但是,这种思路的本身相信将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启迪。
第二,加强以聚落为纽带的综合研究
聚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考古学文化的组成部分。立足于聚落的综合研究既是考古学文化整体研究的具体体现,又是立足考古学文化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可以说,这是学科继以考古学文化表面形态特征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之后,又一个新的认识和研究阶段的起点。
所谓综合研究,就是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广泛收集信息资料,对聚落的经济社会、制度、宗教、观念、工艺、技术、文化传统、对外交流、环境与资源、艺术等,进行全面的多学科的研究。目前,根据国外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内已经发端的动向,环境考古学、文化行为、聚落形态等研究,将是综合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环境考古学是二次大战以后,环境科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形成的考古学的专门分支,与单纯环境科学有重要区别。(1)虽然具体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第四纪,尤其是全新世环境演变史的研究。但是,从其诞生至今,其主要目的都在于探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探讨考古学文化产生、发展、衰亡,以及各种人类文化行为、聚落分布规律的环境背景。(2)它的环境研究范围随人类活动而转移,具体内容主要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自然环境的特点与演变,以及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可供人类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3)从总体上看,环境科学更关心的是环境宏观的分析和研究,而环境考古学关心的则是局部的甚至是微观的。正因此,环境考古学不能被看作是环境史的资料工具,或与环境科学相提并论。
我国环境考古始于60年代初关于半坡遗址的植物孢粉分析,但后来的进展并不理想,这部分是由于学科研究重点的局限,部分则是自身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由孢粉分析所得到的气候演变信息,而未涉及诸如地质、地貌、土壤、动植物群落等其它环境要素,同时也未能将环境、生态、资源与文化、聚落、行为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推进我国的环境考古必须与变革考古学的具体目标保持一致,必须把所有有关的研究都结合在一起,并落实到具体的聚落。
关于文化行为的研究实际一直与我国考古学相伴为伍。然而,这种现象与其说它长期受到重视,不如说是考古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行为科学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种研究基本上还滞留在遗迹遗物一般行为意义揭示的水准上,极少深入探索行为的方式与特点,行为的文化与环境背景。如“狩猎”的研究,以往只是根据工具或动物骨骼粗略地推测有无此类活动,以及这种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至于狩猎的对象、性别、年龄、狩猎的活动范围、时间、季节变化等,则极少过问。事实上,这类研究一般并不需要特殊的科技手段。这就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方法,而是指导思想,即不能仅注意它在经济形态研究中的意义,而是要通过对那些行为的多方面研究去理解当时人类的具体生活、观念与文化。可以说,这正是今后将文化行为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
相对前述二种研究,聚落形态研究具有更高的综合性。它的核心是聚落的功能与性质。具体的工作则以环境考古、文化行为等研究为基础,探讨(1)聚落的规模、内部结构、居住与各种活动的区域和范围,(2)聚落与聚落的相互关系与分布,(3)聚落与聚落群的相互关系与分布。50年代中后期,关于仰韶文化村落布局的研究实际上标志我国也开始了这种工作。但是,由于从一开始就只注重对社会性质的研究,以致过早地丧失了自身研究深度与广度的拓展。80年代中期,以探讨“牛河梁”女神庙及其周围同期遗址间相互关系为契机,预示着这种研究又行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至今的这类研究还只存在于某些能直接有助于“文明起源”课题讨论的地区。不过,随着学科重点的转移,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及其意义日益为学科所认识,相信它一定会很快成为学科研究的主流之一。
以上三项工作虽然在这里只是从聚落综合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它们的意义绝非如此。对于当代的中国考古学,它们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研究目标与方法,而且为之提供了一种把各种遗迹遗物与环境和人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新视角新途径。
结束语
惟有变革,才有发展。今天,学科内外的形势都向学科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这是学科发展的机遇。
不过,问题是复杂的。学科在以往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们有理由乐此不疲,视一切变革为对过去的“否定”。然而,学科总要前进,不会在原地排徊留连忘返。在这里,以往的局限与不足就向变革提供了余地和依据。全盘否定固然错误,但没有否定的发展也不存在。因此,对以往“局限”和“不足”的认识,也就成了是否需要“变革”,如何“变革”的关键。
本文的写作,仅只是通过对学科研究重点的转移与考古学文化整体研究趋势的分析,表达了对那个问题的认识。因为不成熟,或可能偏颇,欢迎批评、指正。
来源:《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
- 0001
- 0000
- 0005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