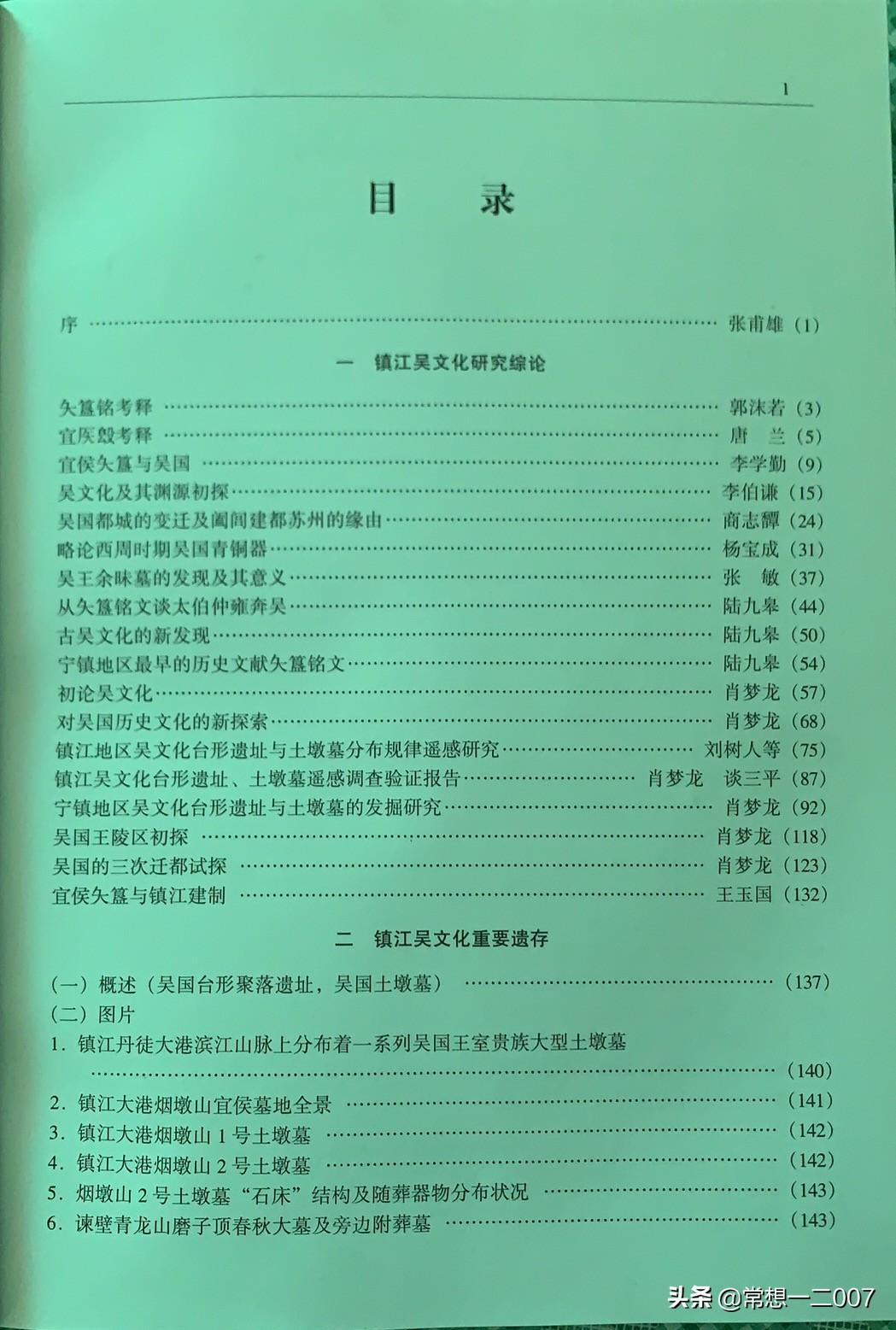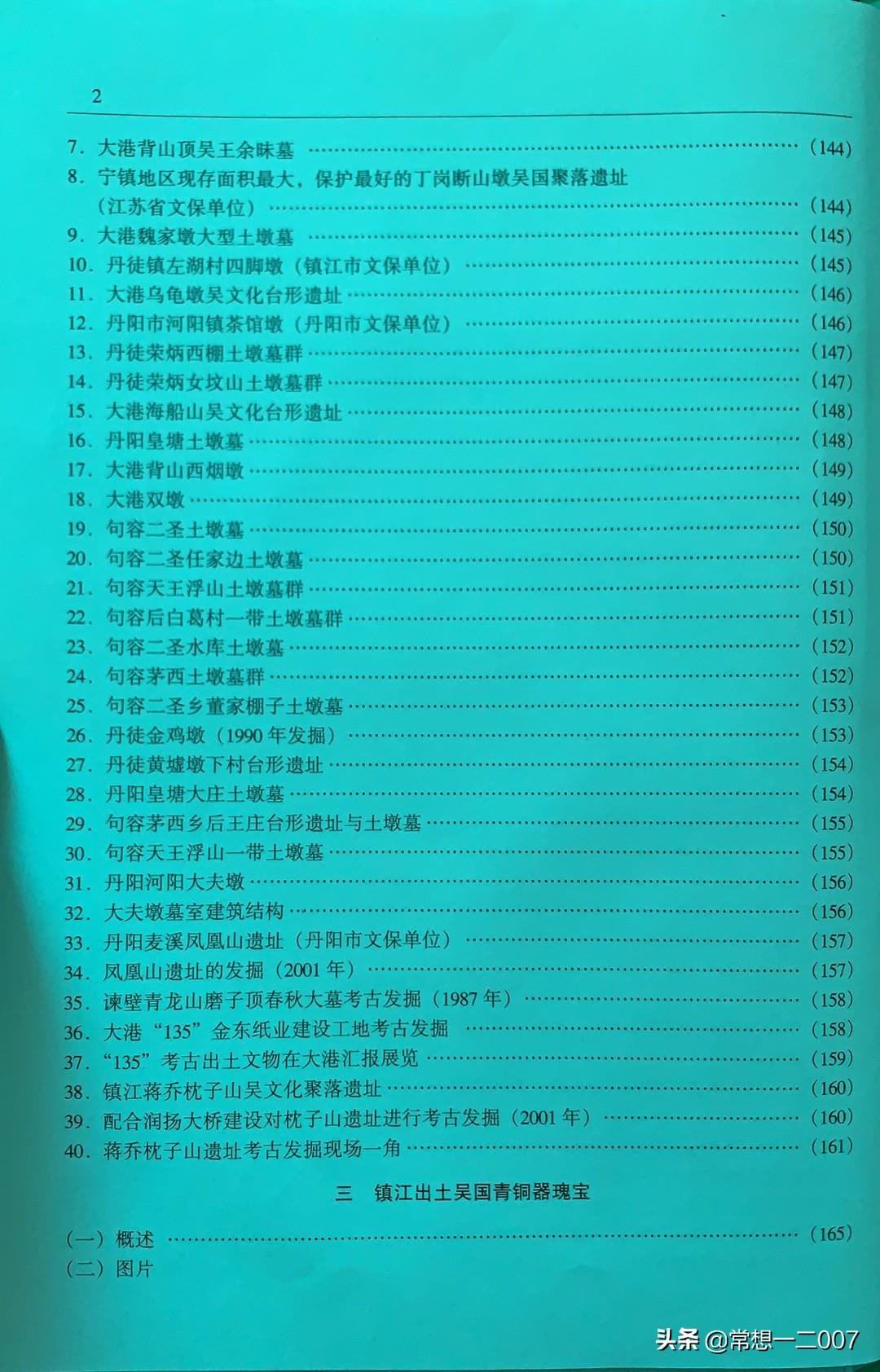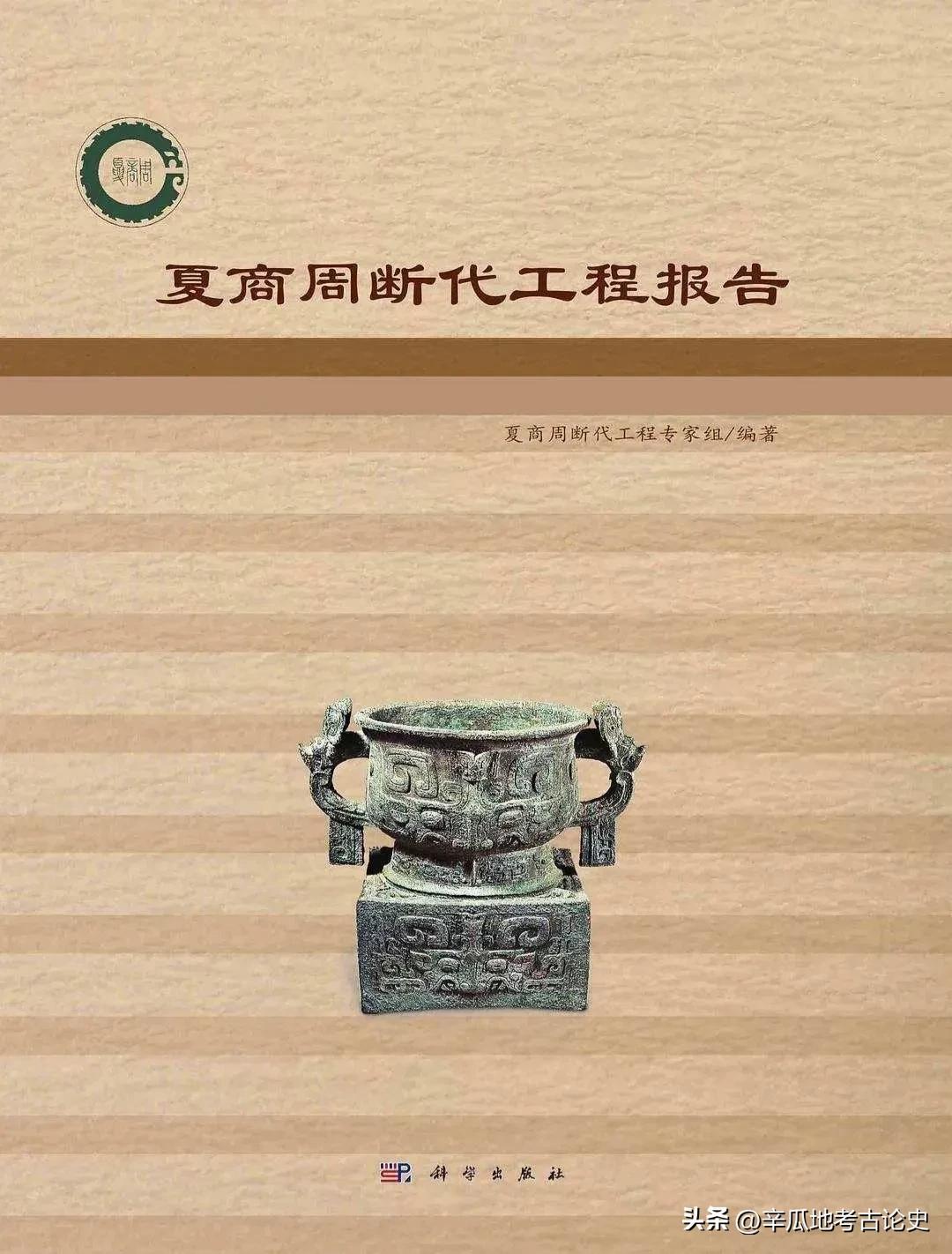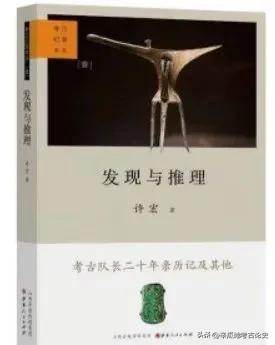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上)?
本文运用自然环境、考古与文献资料,并从文化记忆这一视角论述神农神话的发祥地。神农英雄之形象代表稻作文明关于其源头的认识。古籍指出长江中游为神农故事的发祥地,而考古资料表明,该地确实经历了从稻作萌生到文明起源的完整过程。创造稻作技术的彭头山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其有很多特殊点,与伏羲神农的传说相吻合:如彭头山文化确实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有“制作为历”。因此,神农为皇圣的传说,很有可能隐藏着长江中游上古文明关于彭头山文化的文化记忆。长江中游社会发展成为文明时,早已不能保持彭头山文化这一源头的“纯洁性”,但不妨碍其将对远古彭头山文化的记忆,升华为神农皇圣时代的理想。
【关键词】神农;稻作起源;彭头山文化;文化记忆;长江中游;
本文作者郭静云、郭立新,原文刊于《中国农史》2020年6期。

清代梁玉绳对三皇传说早已提出质疑。当然,“三皇五帝”这一结构并不代表真实的古史,而只是基于象数宇宙观建构的帝·国历史哲学。但这么说,却并不能否定三皇和五帝的个别故事,或许有源自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以及蕴含着远古人经验、理想和传说的成份。
笔者虽然不认同顾颉刚所提出的,三皇五帝可能是中国境内不同族群的祖先,但也认为所有的神话并非全都凭空而来,至少部分地奠基于某种族群、社会、区域的生活经验、理想目标以及文化记忆的根源。
如从伏羲、神农的神话来看,其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就是世界古代文明通见的原始“黄金时代”的理想。只是由于不同古文明人之生活经验各有所不同,其“黄金时代”的理想也因此各具独特性。就伏羲、神农的形象来说,他代表着远古的崇高智慧,在这方面与其他古文明相同,都会有被认为是智慧到极致的英雄,但至于何谓至高智慧,则各文明的认识却未必一致。比如,可能是不败的勇士,或是能听懂禽兽语言等,这都取决于该文明的主要生计方式。伏羲所寄托的理想是放弃危险的狩猎,致力于发展在水边定居地的生活;而神农形像背后所表达的则是人们终于达到了养育厚载的理想境界。由此我们不妨做出假设,伏羲和神农的故事表达了古代东亚某个区域文明“黄金时代”的理想。
其实,若深入思考则可以了解,在水边采集和捕捞,耕种土地以获取食物,这两者的确可以配套进行,表达同一种生活背景的理想:依靠这两种生活方式,人们才可以不再流浪,定居而从土地养育自己。因此,或许可以从这种文化内容出发,思考伏羲、神农这种历史英雄传说的滥觞,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记忆的背景。
对类似伏羲、神农之类的神话传说进行研究,不宜将焦点放在讨论具体英雄的存在与否,而应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入手,一切神话故事皆蕴含着传承而来的文化记忆,该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的经验和理想,皆有可能在故事中留下痕迹。由于早期时代的文字记录恐怕都没有保存,传到周秦汉时,远古传说只留下了极少数历史英雄的名号。这是在漫长流传过程中,各种文化或时代中形成的诸多历史碎片拼凑糅合的结果。这导致一位英雄之事可能跨越几百年的历程,而且时代越早,一位英雄所跨年代的时间越久。这是世界上古传说的共同之处,中国亦不例外。
西方汉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神话体系。这是由于中国神话包括历史神话呈现出特别碎片化的面貌,显得不完整。导致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很多,大体可分成两类:
首先,由于殷周之前书写文字的载体是竹木简牍,并不像西亚石碑或陶版书那样能被长久保存。因此,虽然迄今考古及古文字资料都足以证明,诸如竹木简之类“典册”在商之前就已存在,但未保存下来,故其内容不可知。到了殷周,虽然另外开始用甲骨和青铜等载体刻写文字,但是甲骨金文都不属于叙述性的文字,其内容仅限于占卜、祭祀和宗庙记录。是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故事性的记录,已经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版本。不但时代晚,且早已不是曾经创造这些神话的上古社会所留传的一手记录。虽然战国文献中的上古故事,大部分或可溯源至商以前的时代,但是经过后期历史的筛选,仅只留下了极少数最有名气、被众多人最常纪念的传说和英雄名号。
其次,由于历史久远,对古事的理解随时代而变,且在中国多元族群长期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多次发生过将原本属于某族群的传说,部分被忘记,部分由他者吸收,然后重新讲述和传承下去的例子;直到汉帝国乃至更晚时代,才成为今日所见的样子,形成最后的版本。通过这样的版本,已经很难看到真实的上古文明的神话体系以及相关主体的历史谱系和自我认识。
尽管如此,迄今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已足以证明,殷周之前存在着远不止一个上古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其技术和生活面貌,以及深刻而系统化的精神文化。我们不妨考虑,在有关商以前的时期的传说中,隐藏着某些上古文明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碎片。虽然碎片化程度非常高,文化记忆中还是会遗留其根源和传承的线索,有时候这甚至会是一把钥匙,帮助人们了解这些神话源自何种时空,表达何种环境及生活方式的记忆。但这些代表性的细节往往在经历了后期人重重理解和再诠释的扭曲和遮蔽后,被隐藏在表象深处,极难辨识。因此本文拟从远古留下的碎片记录思考,看能否从中抽出一些规律,帮助理解“黄金时代”英雄的形像可能源自何处的文化记忆。
本文拟重点讨论神农这一远古英雄。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常讨论神农和炎帝是否为同一个对象。虽然神农完全有可能是某一农耕族群传说中发明农耕的神祖,但是作为五帝之一的“炎帝”这种名号所代表的却是秦汉帝国的六方、十二辰、五方、八极等象数时空结构;在此结构中,将每一方位之地(四方与中位合并为“五”之数),与传说中的英雄及故事作连接与匹配。亦即诸如神农是否为炎帝的讨论,并不会帮助我们理解神农神话文化记忆的源头;同理,伏羲与青帝是否为同一个对象的讨论,同样如此。所以下文讨论神农神话时,并不准备将其置于五行、五帝的结构中。
《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班固《白虎通‧号》亦载:“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这两个文本比较,《白虎通》将伏羲放在前而强调他树立人间规律,在此基础之后,神农才来教民农作。这种顺序明显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农耕生活的发生早于五行和八卦之类概念的出现;但是这种顺序安排却很明显符合汉代人的意识形态,即将教导人们以伦常制度为体,而以实际生活为用,体为本而用是末,伏羲培本而被置于前,神农启用而被安排在后。其实,如果单纯从伏羲传说来着手,我们恐怕没办法讨论这一神话的来源。各地都会有类似的传说:掌握崇高智慧的巫师,了解禽兽鱼虫,建法立规等,并创造了影响天地人生之祈祷占卜的神秘系统。这种形象不带有特定地方的特色。但《易‧系辞下》在描述伏羲的贡献时,却呈现出另一种角度,强调他对自然界的知悉,并指出网鱼始自伏羲;而在伏羲之后,神农来教训农耕。
如果从伏羲教导人们网鱼的说法来思考,并将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结合起来分析,则可想到人类一万多年来的进化,确实有少数猎民在刚开始定居时,曾经依靠水边的生活,逐步转化为渔民;之后才有一些在水边生活的人群开始耕地,而逐步转化为农民这一远古的历史。如果这不是偶尔巧合,或许可以假设这两位历史英雄的形象,蕴含着一些较具体的含意,确实源自同一个文化记忆,而其背后或许隐藏着人类对新石器革命的记忆。换言之,这两个 “黄金时代”英雄的形象,或许真的隐藏了某种差不多一万年前的文化留下的记忆。
但是这种假设有一种必要条件:存在某个人群,经历了新石器革命之后,长期定居且一脉相承地发展,最后发展到文明化的程度;而且这些发展到愿意反思自己源头阶段的人们,在自己的文化记忆中,高度认同其从猎民转化为农民的始祖英雄,并将此转化视为自己族群诞生之初的记忆。
换言之,早期农民只有不再迁移,定居范围不变,在生活方式一脉相的条件下,人类对新石器化生活转变的经验和记忆,才会在经历长远的传承过程后,依然留传给后裔,才有可能让他们上百代的子孙后裔,仍然保留有自身文化的记忆且一直薪火相传。
在中国众多文化中,有没有符合这种条件者?若依上述思路,至少能让我们排除很多不符合这种生计发展的区域。那些因河流湖泊不足而不能依靠捕捞维生的地带,那些人类生活不稳定而并无几千年一脉相承的定居生活的地带,都不太可能是伏羲、神农故事的源头。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新石器革命”,是一万余年前人类在水边定居促发新生活的滥觞,故笔者称之为“蓝色革命”。然而,在一万多年前,“蓝色革命”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康庄大道,不是全部人类在一定的时代都必然会经历的发展阶段;“蓝色革命”仅是极少数独特区域内曾有幸完整经历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原创者的历史。所以,如果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的原创形象并非后人的想象,而有文化记忆的成份,那么,此般文化记忆的发祥之地就绝不会到处都能存在。
学界经常将某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做联接。虽然我们不宜完全否定其中的确存在某些关系的可能性,但在众多文化中如何做选择?总体而言,借用历史神话来解释考古文化,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方法,容易陷入于学术性较低、无据可从的现代人猜测的境地。只有经过多层面的考虑,才有可能将某些考古文化与某些神话故事做假设性的联接。在依传说诠释考古遗址之前,我们最好先更加细致地分析传说故事本身的独特意义,初步厘清故事细节所反映的情况。
在传世记录中,神农的黄金时代曾经源远流长,《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且除了上引《系辞传》和《白虎通》之外,其它文献也都强调,神农教民耕地。如《管子‧形势解》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种表达特别强调人类开始农耕生活对整个天下带来巨大变化,不宜将这里的“天下”理解为统一的国家,而是指广泛的地域,即人类生活方式相同的相对宽大之地。
西汉初《新语‧道基》云:“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此段描述了人们脱离原始猎民的生活,定居而学会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生产食物。这种描述恰好与人类所谓“蓝色革命”(或谓“新石器革命”)漫长过程的内涵一致。对汉人而言,农耕已经太普遍,他们自己很难想象远古人类只是狩猎、食肉饮血,衣皮毛,不知五谷,不知麻、丝,但是在汉代人所传的传说中,认识蔬食和农耕的发生仍被描述成伟大的转变。身为汉帝国的人,很难伪造这种故事;所以,我们不妨推想,其当源自某个更古老的社会对自身滥觞期的认识,源自其传承不断的文化记忆。
东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记载另一种发明农耕的神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这里的帝其实就是被称为炎帝的神农。神话中另有载,不仅是神农才善于耕地,其子都大力发展农作至丰盛,如《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烈山氏或连山氏亦指神农,详见下文)。
除了农耕之外,文献所表达的第二个主题是,编织手工也属于神农所教,如《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叙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文子‧上义》和《淮南子‧齐俗》也都载:“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同样强调农耕和编织两种生活的基础。这两种意思的相关性也非常明确:既然神农教人们放弃狩猎,那他们不仅没有肉食,也没有皮毛作衣,所以需要用编织、纺织取代兽皮衣。
第三,文献有表达,神农致力于发展对自然界的认识,了解百草、周年季节等,洞察自然界的规律,如《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淮南子‧主术》也曰:“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描述神农通识植物和气象,掌握四方、四季年岁规律,此乃历法之基础。而《周髀算经‧卷下》直接说:“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历,度元之始,见三光未如其则。”即历法是伏羲、神农共同之功。这一思路也很清楚,农耕生活必须建基于严谨的历法,依时而耕,不违农时。王充《论衡‧正说》讨论“三易”的问题(即《周礼‧大卜》所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易并不都是伏羲的贡献,也是神农所创造,并且夏商所用的易法源自神农,只有周的易法才跟着伏羲:“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换言之,四方、四时、易卦都属于相关的知识,确实基于发展农业的需求。
梳理上述文献后,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表达的三个层面互补相关。第一,身为从猎民转化成农民的人们,需要将自己的食谱从大肉转换到鱼类和植物,食谱变化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人不再跟着野兽奔跑,而是定居捕捞,同时因为定居生活,仅靠攫取大自然的食物往往不足以维生,所以开始自己生产食物,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由于伏羲、神农所表达的理想是放弃狩猎,因此不仅需要以捕捞、农耕取代获得食物的方式,也需要用编织、纺织植物材料取代兽皮做衣。第三,定居生活自然不但人们深入了解周围资源;而且促使人们详细观察天文运转,以了解周岁规律;依靠这些知识,耕作才能成功。若不懂四时、四季,不能靠粮食生活,这样只能回森林狩猎。因为天文、地理、本草知识都启发贯通,并发明纺织的衣服,所以定居生活稳定下来,人们可以生生不息。这一整套全新生活方式,在文献中都被描述为神农英雄的伟大功劳。
除了上述成套的记录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独特的记录,如《淮南子‧泰族》曰:“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三皇本纪》则总合一切说法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以上所引均表达同一个要点:神农是传说中教导民众农耕的圣人,这一点是所有的文献都表达,部分还特别强调他有了解水土的品质,认识所有的植物,据此唐代司马贞发挥说,神农始作医药。除了农耕之外,《淮南子》与《周髀算经》说伏羲、神农作定历法。此外,很多文献说,神农教人绩麻织布。由于这三种说法互相关联,可视为同一时代的一套体系,其都含有可以考证的余地,当然不必把神农当作具体的人,但故事本身的来源值得思考。
虽然《周易》另有记载,神农教人作交易和发展市场(司马贞亦从其说),但在人类历史中,创造农业和发展交易并无绝对关联,非农耕社会也会发展交易,况且交易行为存在于比早期农耕晚得多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笔者认为在溯源神农形象的源头时,不必将是否产生市场作为指标之一。至于《淮南子》云神农作琴的说法最不靠谱,应该免谈。
虽然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农神应该是很普遍的神话形象,但若细察之,却可发现,并非所有民族都有这种神话,只有在极少数文明的信仰中,才有类似于神农的崇高形象。如在苏美尔文明中,虽然在原始创世的恩利尔(Enlil)气神的神能中,提及创造农业的工具,但神话中所留下的恩利尔形象是一位老神的角色。虽然他是旧世界的缔造者,但他也引发灭世洪水毁了自己创造的世界,所以他的重要性已经过去。两河流域其他具有崇高地位的主神,如恩基(Enki)水神、伊南娜(Inanna)圣女,更不用说巴比伦马尔杜克(Merodak)神皇,都不是农神的身份。苏美尔文化的农神主要是恩奇杜(Enkimdu),但在神话中他的重要性远不如杜木兹(Dumuzi)牧神,在这两位竞争当伊南娜圣女的配偶时,农神输给了牧神。
比较世界古文明的神话只能使我们惊讶,在各地留下的资料中,农神当神皇的情况极少,古埃及对欧西里斯(Osiris)的崇拜是特例。在很多一般性的介绍和现代人的理解中,欧西里斯被误解为“死神”。准确地说,他不是死神,而应该被称为永恒造化、死生、死而再生的圣王。在古埃及的信仰中被认同为上古先王,有描述他曾经教导人们不吃肉,耕地种麦,修灌溉系统等,这是他最重要的神能,其它如教授医疗、制造文字法典、使用金属、祭祀神祇、善于建筑等,这应该都是后增加的伟大神的功能,但都不是重点,他被崇拜为“神农”才是核心所在。
在古埃及观念中,欧西里斯虽然被杀而尸体淹到尼罗河里,但被杀又被淹后还能生出自己的分身:荷鲁斯(Horus)。荷鲁斯既是他的儿子,也是他本身,两者也是同一位,是不可分的死生循环。埃及的肥沃农耕领土被视为是欧西里斯的身体,且被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埃及的土地在每一周年都要经过与欧西里斯的生死同样的过程:经过枯死后淹水而再生。这三段表达了古埃及的神秘历法观念,自然界的三个季节与欧西里斯的生命被视为是一致的:皇圣王经过死(四个月植物都枯死的干旱季节,古埃及文称为shemu),之后他被尼罗河的水淹没(四个月看不到土地的洪水季节,古埃及文称为akhet),而再生(在洪水留下的肥沃沉积土上,有四个月可以耕地与收获的季节,古埃及文称为peret)。在世界神话中,欧西里斯可能是最完整的神农圣王的形象,不仅是教民耕地,而且亲自化身成为埃及人的农耕地,他的死生过程同时也表达了古埃及的历法。
欧西里斯神话是由创造而笃信这一信仰的人记录且保存的,所以详细而丰富;而中国留下的有关神农的纪录,都载于时代非常晚的文献上,且不是由创造或笃信这一信仰的人所记录,所以神农传说远没有像欧西里斯那么丰富、详细和神奇。今日存留下来的提及神农的文献,是记录者在不清楚当时具体历史的情况下叙述几千年前的古史和信仰,且记录者的时空、国家、族群观念、认识创造该神话的人已经有相当大的变化,甚至编撰文献的人,不仅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已与神农时代相去遥远,而且其编撰的地带,与实际传下神农形象的地带也未必相同。
当然我们的论述奠基于无法证明的假设:认为神农神话并非全部出于后人的幻想,而至少部分基于早期农耕文明文化记忆的元素。然则此神话创造者的时空是上古农耕文明,而现有版本的记录者所处的时空则是涵盖了很多原来上古文明地域的秦汉帝国。我们很难了解文献叙述的故事原本来源自秦汉帝国的哪个区域,又涵盖哪一个或哪几个上古文明所留下来的记忆。
秦汉时期将神农记载为皇帝,把他的形象历史化了,其中大部分原来的神秘意义应该早已不被理解而遗失了。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神农故事非常简单,不象欧西里斯的信仰那么有意思而蕴含了上古文明深刻的天地死生观念。但这并不等于在上古文化中,对神农形象的认识也像在后期文献中那么简单。
当然,因为中国与古埃及自然与社会的环境都不相同,神农与欧西里斯两种信仰的内容和故事原本不可能相似,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农神皇”的信仰,都具有将农业创造者视为崇高的神皇以及视为圣王的身份。
汉帝国与原本创造神农信仰的古国的关系,就好像吞并埃及的希腊化帝国与古埃及本身的关系。我们想象,假如古埃及本身并未留下记录,商博良亦无机会摸索到解读古埃及文的钥匙,而希腊化帝国曾决定创造大一统的合并的历史;倘若如此,其关于欧西里斯记载的程度,恐怕只会与中国大一统朝代对神农的记载类似,后人就不会知道原来的信仰多么复杂、独特。
换言之,虽然中国神农信仰留下的说法过于简单,但是其故事原本的丰富程度并不亚于古埃及欧西里斯,且一定含有自己独特的形象和生命观念。但是因为没有留下信仰者本身的描述及说明,后人只知道有教人耕地的神农,但不知道与他相关的信仰中哪怕再稍微详细一点的内容,更不知道是否曾有过崇拜神农的礼仪。可惜,经过多次被新族群攫夺、毁灭,然后互相吞并、同化与融合,最后被大一统帝国消化,上古多样而独特的远古文明中的绝大部分知识都失传了。是故,神农形象的深入涵义已不可知。
神农皇圣是教导人们放弃狩猎转身为农的神话英雄。他的故事,是以历史英雄表达某一种文化的原型。
经过文献分析,可以从中抽出该神话的核心所在。神农在发明农作的同时,呼吁人们不再吃野兽的肉,因此也不再穿兽皮,用植物编织衣被。在神农之前,伏羲教人网鱼,所以人们可以从鱼取代野兽的肉。伏羲和神农的智慧在于了解大自然规律,知道以各种植物为药,并确定历法。这种神话结构很系统,可与考古所见相呼应,故应并非全部由后人凭空创造,而有着来自远古文化记忆的成份。
返观世界神话可知,虽然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以灌溉农业为基础,但在神话中却极少将农神视为文明之始祖者,只有古埃及欧西里斯和中国的神农如此。这使我们考虑,原本与神农有关的信仰观念可能并不像现在能看到的那么简单,且可能代表着某一个曾经繁华的上古文明,它跟古埃及一样早已灭绝、失传。后来,在几千年传承的过程中,经过多次转手,神话故事失去原来很多独特的内容,现在已没办法复原。
虽然神农神话的原貌已不可知,但从其基本神能,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判断其原创的地域及其所描述的文化属性。只是讨论此问题前,我们应该分析方法的严谨性,明确哪些原则和指标可以用来作为了解该传说渊源的依据。
神农这位历史英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本文用符号学中的“符号”概念),表达了该文化自我认知的关切所在,这种“文化符号”蕴含了该文化的人生活的自然及社会情况、生计活动、生活中所缺而追求的愿望、完美典型、观念及理想。因此,我们不宜讨论神农这位历史英雄是否代表具体的人物、宗族或部族,或者是否为多元文化总和的英雄形象,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重要,也没法获得答案。他的故事,是以历史英雄表达某一种文化的原型,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神农的形象与相关神话的产生地,即不是他本身或他的后裔生活在哪里,而是何时何地何种文化可能创造了神农这一皇圣的原型。
如果古史传说不是全部由后人凭空创造而来,而有来自远古的成份,则创造古史传说的文化应该全面符合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神农是教导农作的神皇,这种神话只有非常成熟的农耕文化才能创造。伏羲和神农的黄金时代,是人们放弃游猎,少食野兽肉血,少穿野兽皮毛,依靠网鱼及农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代。在这一文化的观念中,耕作能养活人,并不需要猎野兽。所以传下神农皇圣记忆的人们的生活环境,应该不缺水和水生动植物,土地肥沃足以使那些技术还处于初萌阶段的农业者也能养活人;并且,因为定居生活是发展农耕的必要条件,说明人们可以在相对固定的范围内获得足够的食物,而不需要同时奔跑狩猎;同时,这应该是气候温润的地区,至少农作物的种子在冬季不会冻坏,可以年年稳定地稼穑。换言之,神农神话无疑应是生活在自然条件良好的农耕文化的传记,并且从留下的记载来看,农耕生活被当作该文化的理想,因此农神被视为圣王或神皇。
其实在老子的语录里可以发现这种理想的影子。郭店楚墓出土的竹书乙本、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乙本以及传世的《老子》,都有同样的一句话:“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即是“穑”的本字,表达农事的意思,王弼理解为:“啬,农夫。”。换言之,在老子观念中,留下了统治者应当以农夫为榜样的崇高理想。虽然在汉代以后的理解中,更多是跟着《韩非子‧解老》:“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其后河上公对《老子》用“啬”字的理解就深受韩非子影响,而忽略了统治者以农夫为样板这一层意义。这是因为在汉帝国文化和思想中,这种古老的理想已失去其深入意义。尽管如此,老子语录还是表达了统治者身为农夫之理想,所以不能排除该观念映射了从远古传下来的以神农为皇圣理想的余晖。
第二,以渔、农为本的生活是定居生活。定居生活意味着人们依靠周边资源维生,定居也是稳定发展以农耕为本的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一原则还涉及到传承问题。现在还存在的文化,无论他是流动或定居,人们都会把自己的理想和故事传给后裔。但是我们不怀疑,崇拜神农为皇圣的文化,到汉代已基本上不存在,正因为如此,有关其故事的记录就会变得零碎。虽然如此,为何其文化记忆却没有完全消失?只能说明该文化的基础深厚,存在长久,对周围及后世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早已灭绝的文化的砂砾才有可能在后世文化中继续存在。
长期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定居,是实现此类传承的必要条件之一。流动生活面临不断变化,族群不稳,多次分散和重组,导致观念及神话模糊而不成型。当然在游猎族群存在时,他们也有自己的英雄故事,但是流动或重组后,传说故事也跟着变形。已消失的游民群体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留下来,基本上只有通过两种途径:被邻近的定居社会记录(如斯基泰、匈奴的故事,基本上是通过其与希腊、汉及其他定居文明的交往而存留,但其本身却并无传承脉络);或者游民放弃流动生活而定居,形成自己的传记,或包含定居之前的几代传记,但能够向前追溯的时间不会久,最多也只能到达两、三百年(以秦史为例,关于秦人在关中定居之前只剩下了一点关于从事马政的记忆),至于更为久远的游动生活,已很难留存在族群的主体性记忆中。
是故,组成这些有关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碎片,很难源自猎民或其他流动的族群,大部分还是要到原本在较固定范围里生活的族群或文化中进行溯源。更不用说,神农英雄形象的创造者肯定是长期定居文化的先民。
第三,这些长期定居的农耕族群很难是小部落,因为小部落哪怕是稳定生活,如果范围小而不扩展,并不会形成影响力,在他们消失后,有关他们的记忆也会消失。能把自己的神话传到后世的人,应该是那些曾经扩展到相对大的定居范围,拥有长期一脉相承而不断发展文化的族群,通过扩展区域以增加本身文化的权威性,对周围族群也形成影响,这样才可以在后世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种子。这说明,这些人的生活区域不会是小盆地,而应该是不封闭的大空间,是有足够水源和肥沃土地的宽阔之地,有着发展同一种建基于农耕生活的客观自然条件。
第四,这种长期稳定发展、扩展、产生影响的文化,显然只能是进步、发达、文明化程度高于周围地区的社会文化。只有达到文明化的社会,甚至在该文明消退后,其精神文化才仍会被后世文明传记。未达到文明化程度社会的传说,在该社会解散之后,很难留有英雄形象的记忆。比如说,迈锡尼到达文明的高级阶段,因此打败他们的多利安人才得以传记迈锡尼的神话及神史;而古埃及人虽然多次打败周围的文明化程度不高的非洲族群,却从未留意到他们自身的传说,因此这些文化不高的族群的传说和英雄没能留在人类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殖民地原住民的传说,也不会留下来。
换言之,诸如神农这般传承久远的传说形像,应该曾经是被上古大文明所崇敬的历史英雄。该文明从农耕定居生活起,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内逐渐扩展,其文明化程度超越周围地区,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累积自我认知及认同观念,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愿意思考、评价及传记自己的源头,将他们自己的长期文化记忆及传说升华为始祖英雄的神史。
因此,孕育神农神话的文明,在几百、几千年养土地种谷粮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身内在发展并长期保留自我认同,同时累积足够的影响力,在文化上保持主导地位,周围地区可能自愿加入到该文化范围,那些距离偏远的族群也愿意学习他。换言之,神农传说的根源,应该不是某个不明不白的“部落”或族群留下来的,而是完整成熟的农耕文明的文化记忆,所以后世的新族群才将其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并继续传播下去。这种情况犹如迈锡尼—爱琴文明对古希腊的主导作用。
第五,虽然其文明所在地域应该不小,但也不能以大中国的规模来思考古史传说的来源,它们只是某些具体文化的英雄和故事,后来被修编及合并为一套大一统的神史。而这些留下传说故事的文化,一定发生在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区域,是某种具体的文化体系。此文化经过长期一脉相承的自身发展,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力和自我传播的能力,所以他们的故事才有能力传到后世文明。
有了上述基础性的理解,才可以分析早期农耕文化的考古遗迹,以尝试厘清神农这一形象的原型可能源自何处。而且,可能需要汇集文献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化石植物学、古地理学、气候学、土壤学等客观资料,从而研判神农神话最有可能产生于何地。其实,神农神话发祥地的问题,在学界屡被讨论,是故,下文将从前人诸说入手。
有关神农活动区的问题,目前有两种传世文献记录的说法,以及数种现代人的看法,其范围南到两湖,北到陕西、山西、河北等。这些讨论的出发点皆是因为学界认为,神农神话并非全面由后人杜撰,包含有真正源自上古文化记忆的种子;并且依靠现有考古学成果,可初步划出神农神话形成的可能的地域范围,可考虑哪些考古文化最有可能代表衍生神农传说的文化记忆,以及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社会情况。学界这种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神农毕竟是远古历史英雄,不宜以“活动区”这种概念来考证,这种作法就好像把神农视为某个具体的个人或族长等身份的存在者。我们应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探索,分析在中国大地内,哪些区域、哪些考古发现的上古文明,最有可能传下这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下文拟先从已有的山西高平、渭河流域、湘鄂地带、湘西会同等说法出发,试图评估这些区域是否有可能留下有关神农皇圣的记忆。
将高平视为神农之地的讨论如下:“今高平市北的羊头山和郊区不少乡、村都保存有传说遗迹和有关建筑,如羊头山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毅畦、末耙洞、炎帝陵,中庙村的炎帝中庙,故关村的炎帝行宫等等。”不过由于太行山以西晋东南地区很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学者们将该地区关联到太行山以东的冀西武安磁山文化:“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此地有磁山文化遗存,说明农耕文化早在距今七千年左右就在这里形成和发展。……炎帝有八代的发展,其中有一代或几代就在此地生存和发展。”贺晚旦和杨红保提出,羊头山南麓现存几个神农炎帝育植五谷的主要遗址,并有炎帝采药中毒到殁葬的系列遗址等可证明炎帝神农源自高平。
高平地处晋东南山区,很难视为农作的发祥地。此说法依靠本地民间的现代传说以及提到炎帝的地名,这种资料很难用来做证据。两千多年以来,神农炎帝被称为汉人远古神祖,因此中国各地都可以听到关于他的民间说法,相关地名甚多,比如说鄂西有神农架山岭区,难道仅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认为教导农业的神祖传说源自并不符合农耕生活的山区?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平地的环境,同样也都不符合产生早期农业的条件:气候既偏冷又偏干,水网贫乏,人类文明早期很难有定居发生并在相对小的范围内难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平原腹地很小,缺乏可以扩展的空间;考古也并没发现此地在全新世早中期曾经有难以稳定的农耕生活持续发展的情况。此地考古遗迹出现得很晚,晚到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所以主张山西高平说的学者,也只能把神农教民耕地的传说看得很晚,比东亚农耕起源的实际时代晚很多。至于有些学者认为高平可能有河北磁山文化的遗存,迄今未曾发现有明确的考古证据。
如果磁山文化来讨论,在考古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确实曾被视为粟作(或黍作)起源地之一,此外,东北兴隆洼、黄河中上游大地湾、黄淮平原裴李岗等文化也曾被视为粟作起源地。
磁山遗址虽然发现有碳化的粟粒或黍粒,但是学界均不怀疑,这一在太行山东麓形成的社会及其生计模式是以狩猎、渔业、采集为主,小规模农耕为辅(图一:1)。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脉与河北平原交界之区,鼓山山麓,洛河边的台地上。这一自然区域已告诉我们,在这里活动的人依靠山麓狩猎,同时在河里捕捞和射水边的禽类,交界区域的生态颇为丰富,有利于采集食用植物,这种环境也允许发展粗放农业。
关于磁山人用谷物的目的,学界曾有争议。磁山遗址出土所谓“粮食窖穴”,一般被视为粟作的直接证据。磁山文化下层发现62处存有禾本科植物谷类的窖穴,堆积谷物的厚度现存0.3~2米。在谷物之上有较厚的一层黄色硬土,上部又有堆积为包含陶片的地层,有谷物的一层也有些陶片(以H346为例,图一:3);H5在谷物堆积的底部还有两具整体的猪骨;H107同样埋葬猪骨架一具;此外几处谷物窖穴还埋葬了猪头。磁山上层也有几处堆积腐烂谷物的坑,上部出土陶片较多、下部是谷物。当然不是所有的坑都埋有谷物,下层遗迹另有124个坑没有谷物,含谷物的坑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上层遗迹188个坑中,只有18个坑含谷物,只占十分之一的比例,谷物堆积层也不像下层那么厚,不过同时也发现两个坑含树籽堆积层。

很多人将这些出土谷物窖穴的遗迹视为具有粮食储存的功能,但是严文明、乐庆森等学者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粮仓”看不出有防雨措施。卜工坚决否定那些发现谷类的坑有储存粮食的功能:“磁山遗址的灰坑恰恰不能作为窖穴和垃圾坑来解释。这类坑中常出有猪、狗的骨架。其中,H12、H14、H265的猪骨架均出于粮食堆积的底部,HS粮食堆积底部有两具猪骨架。不论是把活猪还是死猪置于粮食底部,都显然没有考虑猪肉腐烂的因素。这种现象不能作为贮藏解释是显而易见的。既使坑底堆放的是零乱的猪骨,仍然不能作为贮藏理解,而只能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王仁湘最早把磁山遗址葬猪,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常见的葬猪祭礼,属于一种“陷祭”、“埋”活动的雏形;卜工亦循着这一思路说“磁山遗址葬猪的宗教意义,是很有道理的。如此,则同坑埋人的粮食也必然与宗教活动有关,两者都是祭祀的奉献,而不是被贮藏的食物。”笔者认为这种观察和理解颇有说服力。这种理解与新石器时代猎民崇拜野猪并祭埋猪的习俗有关,华南、华北都有这种传统,各地有自己的特点。磁山先民献祭猪的意思可能包含把猪视为人与神之间联络者的观念,用它祭祀而同时祭祀它,向它祈祷,请它把祈祷送达神,祈神保佑,这类似于后世献巫的活动。因此埋猪的祭祀坑里放谷类,实际上是用来作猪的随葬品,给猪世后吃。
可以进一步思考:倘若还是把磁山视为农业文化,初期农作技术不高,那么辛苦种出来的谷子,大量倒进祭祀坑里浪费,似是很奇怪的动作。耕粟是一种产量不甚高的苦工,粟粒很小,产量不高的谷类被大量倒进坑里之后,并不会剩下给自己吃。磁山下层祭祀坑里谷层很厚,给人的感觉是根本不考虑留给自己吃。因此,难以想象磁山下层的谷物是栽培种,很有可能是采集野生种,目的是为了作猎野猪的诱饵,以及专门为此种仪式所用。到磁山上层时,埋葬谷物的遗迹变少,并有以树籽取代谷物,这更加说明,这都不是储存粮食的窖穴。因为发展到上层时,磁山人已经不愿意将那么多谷物倒到坑里烂掉,或许间接表明这时这类谷物有了更好的用途;甚至不排除此时已有初步的小规模栽培行为。但总体而言,上层文化跟下层一样,以狩猎为主要生计模式。
综合考古遗迹的分析,磁山下、上两期都有很多骨镞和渔镖等狩猎、捕捞工具。据周本雄分析,磁山先民四季都有猎获。出土的兽骨中,鱼骨、禽骨都有,除了猎犬之外都是野兽,大型动物中鹿科最多,其次为野猪,此外还有兔、鼠等小型动物,以及水边的禽类,零碎的骨头在遗址中到处皆有,这种现象正好是猎获普遍被食用的痕迹。磁山先民用鹿、猪的骨头作猎器,所以我们也可以合理判断磁山先民曾用兽皮作铺垫和衣被。
在磁山文化中,狩猎所占比重大,显然其生计以狩猎为基础,也许同时开始养幼猪(但还没有到驯化出家猪的阶段),前面介绍的祭礼活动直接表达了其崇拜野猪这种属于猎民文化的信仰;由于捕捞工具以鱼镖为主,少见网坠,可知渔业的规模不会很大,比重明显低于狩猎;至于农业,可能有一些原始粗放的栽培行为。从考古遗迹整体分析,“磁山文化…….还不至于进入农业社会的阶段。虽然有人认为磁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的农业色彩比较浓重,但相关的佐证还是少有说服力的。”
可见,这种生活方式与神农神话相比较,差异性太大,很难想象对磁山文化的记忆会形成这种放弃狩猎、不吃血肉、不穿兽皮的“黄金时代”的理想。换言之,磁山文化不符合前文所提出的判断神农形像发祥地的第一种基本原则。
就磁山文化所在的空间而言,太行山东麓只有一条很窄的生态多样的环境区;再往东就是河北平原低地,这里原本是低洼的黄泛区,只有到很晚时期农业已经很发达的时候才被开拓。在新石器甚至青铜时代,河北冲积平原还是一大片沼泽地,且沿海低洼地带还存在海水倒灌造成土地盐咸化的风险。退一步说,既使在水位低时,河北平原曾经有一些稀薄的文化层,在海平面及水位上升时,恐怕只能被淹没,所以也很难被发现。磁山文化依靠小区域内相对丰富的生态环境而适宜定居,但是受到自然腹地小的空间限制,没办法扩展。同时,因位置偏北,亦容易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
依据年代范围可知,在磁山文化的晚期之后,距今约7400年,气候曾一度变为干冷,导致华北地区前期初步萌生的定居生活崩溃。由此可见,磁山文化无论腹地空间还是自然环境,均不符合定居农耕生活稳定发展及扩展的条件。因此,一方面,农神很难成为该社会的主要英雄;另一方面,该文化扩展自己影响力的时空范围皆相当有限。
就磁山文化制陶技术来看,根据发掘者检测,窑温在约三百年的较短时间内,从700℃发展到800—700℃。所以当时应该处于较快速发展的社会,循着气候快速暖化,磁山文化乘机利用几百年的温暖适宜期,而发展定居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可惜,因空间及气候限制,这种定居生活被迫中断且没有传下来。磁山文化在气候干冷化时,基本上散失了,所以我们看不到河北武安地区考古文化有一脉相承发展的情况。对此,学界已有讨论,“无论是磁山文化还是北福地一期文化,对于这些刚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向新石器时代晚期过渡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并未形成像裴李岗文化一样的一套统一的文化系统,当时在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只是零星的、局部的。这也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史前文化自始至终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连续发展的文化区的最初表像。”换言之,磁山文化中断了,并没有继承者。既然如此,无论它曾经是否有英雄故事,都很难传到几千年以后的世界。
前文对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太行山两边都没有以农耕为基础的早期社会,磁山文化也许有一些粗放的农耕活动,但规模小,比重低,磁山先民主要还是以狩猎采集维生。神农传说强调的重点是,神农教导人不吃肉,而磁山人反而一直以吃肉为主,并没有放弃狩猎。
(2)该文化空间范围也相当窄,土质也比较贫瘠。处于山麓与小平原交界之地,这样的环境便于食谱多样、生计混合,在河北冲积平原稳定之前,并没有扩展农地的条件。
(3)该文化时代范围相当于距今7900─7500年间的气候暖化期,之后经历了中断,基本上没有继承者,故不宜视为有着长期历史的农作起源地。
(4)至于磁山文化与山西高平地区的关系,更难有资料佐证。
是故,磁山或华北其他新石器早中期文化,虽可能有小规模的农耕活动,但却没有证据支持其为神农传说发源地的观点。
现代学界,可能最流行的说法,乃是将神农视为曾经活动于陕西的英雄。如郭沫若曾提出:“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徐旭生观点相似。白寿彝论述:“相传,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部落。一个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领是黄帝;一个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领是炎帝。这是两个近亲部落,它们结成了部落联盟。它们活动的地区,初是在渭河流域,后来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带。”
对于姜姓,范文澜提出另一说法:“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不过大部分学者还是遵从郭沫若渭河姜水流域的说法,并将之具体化为宝鸡,如邹衡提出:“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这样,上述文献记载就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炎帝的原生地……在陕西宝鸡一带。此出自《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与姜水今固不能确指,但其范围肯定是在宝鸡,在陕西周原和宝鸡一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考古研究看,今已在宝鸡、周原一带发现‘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在这一带发现很多,更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
何光岳提出一群炎帝的说法,以试图解决文献中提到随州以及宝鸡等不同地方的说法,不过他认为最初的发祥地还是在宝鸡。
秦地说唯一的根据是文献提到神农为姜姓或居于姜水。但是恐怕不能用非常晚的姓氏体系来讨论农作起源的时代。农作萌生时代难道已经有规整的父系氏族和姓氏名号?神农难道真的会有姓?或者会有以他为祖先的具体氏族?神农难道只是某一家的祖先?至于因姜姓而指认农作起源缘于游牧族群的贡献,则更不符合史实。同样,地名也是很不可靠的证据,中国境内有不只一条以姜水为名的小河流,包括主张湘西会同说者,也提出会同有姜水。
张文彬从考古资料的角度认为,渭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神农教民耕地于此:“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北首岭发现新石器时代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为探讨炎帝故里和炎帝氏族……奠定了科学基础……2002年又在宝鸡关桃园发现了早于北首岭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姜炎文化提供了新线索。”也就是说,他认为北首岭、半坡就是农作发展之地,并将其视为神农部族的活动区。渭河流域半坡文化的聚落和技术确实相当发达,粟作耕作的比例也较大。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半坡社会是否有可能产生神农先王英雄的理想。
新石器中晚期北首岭、半坡、大地湾等西北地区遗址均表现出狩猎、捕捞、采集及粟作等混合生计模式。虽然发展粟作,但却仍以肉食为主。北首岭、半坡等遗址的兽骨也显示,野猪和鹿科动物的数量最多,这是渭河流域猎民最主要的狩猎对象。同时,他们用鹿骨、猪骨制作箭头、渔镖、渔钩等狩猎、捕捞工具(图2)。石质工具也包括猎器。
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很明显是以性别来区分的社会,男女生活方式不同,故村落中安排女性公房和男性公房,大部分合葬墓都是同性合葬;在这一社会中,狩猎属于男人的活,采集和粟作栽培等应属于女人的活(与《商君书》文献所表达“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并不一致)。男女性别群体的分工情况在墓葬里有所反映:男性墓一般随葬猎器和野猪獠牙,这些獠牙有穿孔或被磨的痕迹,故应是穿绳挂在脖子上或者挂在衣服上的宝贵佩带,用来象征猎人的力量。这一点是在表达,在半坡精神文化中,男性的力量不在于耕地,而在于当猎获猛兽的英雄。因此很难想象,这种文化会把呼吁放弃狩猎的神农视为自己的皇祖圣王。
在黄渭流域,半坡、大地湾、马家窑、庙底沟等新石器文化彩陶图案反映出对鱼、鸟、蟾、蛙、蜥蜴等动物的神化,如在半坡丧葬文化中特别突显的神鱼形象;其它彩陶形象的信仰意义不甚清楚。不过同时各处可见崇拜野猪的痕迹,如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一座明显为献巫的高级墓葬(77M17号墓),墓主可能是聚落首领身份的巫师。该墓随葬品丰富,身上有席子覆盖的痕迹,在缺头的位置上有皮毛的灰痕,其上有带黑彩符号的尖底陶器;而在巫师腰旁有野猪獠牙,可能曾经握在手中。这直接表明野猪獠牙有崇高的象征意义,是神猎大巫的宝贵佩带。(图3)

总之,渭河流域之人,虽然有粟作,却饮血食肉、衣皮毛;这种文化的理想英雄也不会是农人。黄河上游大地湾文化之人也佩带野猪獠牙,一样有猎人崇拜野猪的遗迹。就此而言,很难相信神农神话源于此地。
就空间来说,虽然黄河地带这一类文化较多,所在范围也较广,但是各自生存在有限的空间内,如渭河谷地、兰州盆地的绿洲等,山脉和黄土高原等破碎地形限制其扩展。就时间来说,虽然这些总称为黄河地带彩陶文化体系者总共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早期的北首岭遗址始于距今约6800年,而属于半坡晚期类型的福临堡等遗址显示,同类文化及生活方式,一直存在到距今4500年左右,并且部分地被庙底沟二期所传承。虽然可以看到大约持续两千余年的文化谱系,但最终还是断绝,在距今4000年以后,气候干冷化对在这一带的粟作定居生活造成很大的危机,导致黄渭地带新石器晚期的定居生活基本上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两千余年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由独立分散的遗址所代表的小型社会。总体来说,该地很多遗址虽然曾经有过互相影响和传承的关系,其生活方式相近,器物相类,但同时却看不出有跨聚落的公共活动区,并没有出现超越聚落的更大的社会体系。这或许是因为地形与气候条件不利于发展社会网络,也许还有其他原因。重点是看不到主体社会一脉相承的文明成长过程,未见在自己的土地上经由自身发展并长期保留自我认同。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在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很难把渭河流域视为农耕大传统的发祥地。只有到了殷周及以后,因为文明与政权的大变动,马匹贸易兴起而使西北地区的贸易线变得关键和重要,使黄河中游联通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草原,或通过渭河上游联通宝鸡、天水、兰州等地的传统贸易线路兴隆起来,这种文化才一度使周原变成为庞大国家的核心之区。但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在不同时代有影响不同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不宜将殷周汉唐的情况与新石器时代混为一谈。
黄渭地带的新石器社会,虽然种粟,但主要食物依然是猎获的肉类;且这些猎民社会,虽然曾定居,却跟后期周秦文化少有传承关系。在周秦器物上极少可以发现源自本地新石器文化的造型母题,同理,源自本地新石器文化的传说应该极少有机会留传并进入本地青铜时代的故事之中,尤其是这种猎民社会很难创造出神农形象。
上述文化均为以狩猎为主、以粟作为辅。这不仅是因为农作发展不足,粟作产量较低,加上渭河流域气候不允许一年有超过一次的收获,低山地形和山谷的空间不宽,所以远不能用粮食生产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也曾遇到过的困难,所以秦国不仅用力加强技术,又采用严厉的特殊手段,努力发展本地农业。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既没有新技术,又没有秦国集中国家力量的能力,也没有这种需求,因为依靠低山林中的狩猎、溪河谷边捕捞和射鸟活动,即依靠森林维生已足以保持小规模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产生教导人们少食肉的神农形象?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另一种本质性问题。现在很多讨论似乎有这样的先验预设:即神农是教导粟作的神祖。石兴邦认为,“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他们的足迹超不出粟作农业分布的范围。虽然在黄淮流域交错地区粟稻种植有交错……但那是很有限一个小的区域,可以肯定炎帝部落迁移的足迹没有跨过长江,达到今天对炎黄崇拜炽热的两湖地区……所以,两湖地区的炎帝崇拜,是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所形成的。”所谓“粟稻交错带”的范围其实相当宽,曾经涵盖河南省的中南部。此外,稻作和粟作技术不同,粟作并不需要水田,依靠粟作的经验无法教人种稻。是故,我们难以理解,何故会认为因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而提出长江流域为炎帝故事的发祥地?周、秦、汉、唐政权中心都在北方粟作地区,若依这些后起政权的立场,绝不应该将重要的文明起源故事特意改讲到被视为“南蛮之地”的地方。
虽然有一条文献提及神农与粟的关系,即清代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但这是经过屡次转手引用的文献残句,原来版本的用字不详;既使春秋战国时代的版本也曾经用“粟”字,也并不能用来作证据。周王国所在之地是粟作农业范围,是以若用周人的背景讨论农业起源,当然会讲到粟。但这并不能证明,神农从一开始就是周人远古的英雄,尤其是考虑到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情况,我们很难将神农传说视为后世于此建国的周人的历史。
王震中认为,既然南、北各自发展不同的农作,所以神农并不代表某个具体族群的传说,而是大中国的文化符号。但是,传说不可能是互不知悉语言且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的不同族群共同创作出来的,英雄形象不可能从衍生伊始就已是跨地域、跨文化的共用“符号”,除非它真的只是在帝国时代伪造的。是故,如果相信神农传说确有源自上古的成分,其也只能代表某个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创作。
如果从神农传说的内容以及粟、黍农作物的性质来思考:粟黍的自然产量有限,很难当主食来用;同时,传统粟作地带主要是黄河水系的河流,湖潭不多,所以水生动物种类也有限;另一方面,该地区大型野兽反而不缺,狩猎条件良好,并可以尝试从纯狩猎发展到饲养业。在此地带教导人们不猎兽、不吃血肉者,就很难成为英雄。况且,气候相对寒冷,植物性食物不够多,需要多吃大肉、穿皮毛过冬,教导人们不穿兽皮,也是很不妥当的做法。所以,在此地带很难形成这种关于“黄金时代神农英雄”的记忆。
黍作、粟作地带新石器考古也表明,早期发展粟作、黍作社会的生计,均不以农耕为主,其狩猎成份都非常高。只有稻作是从新石器早期起,经过漫长的发展就成为平原农耕社会的主食来源以及社会组织之基础。只有稻作才促使人们脱离游猎生计,靠近水和低洼地稳定地定居,砍伐森林,开拓大平原,配合农作改造水土等。因此农耕的发明,惟有对食稻的族群才会带来革命性的生活变化。是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神农故事不应代表粟作,反而是从稻作文明传下来的神话。
此外,黍作、粟作地带的农业和聚落规模,在新石器时代相当长的历程中,都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一直都属于单个村落。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耕作方式不涉及合作治水和改造领土的必然性。因此,在促成组织和形成社会的潜力方面,粟作不如稻作。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才是古文明社会生活之基础。以稻作为基础的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而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神农恰也被描述为南方的英雄。这可能不是后人的想象,而是有着源自最古老文化记忆的颗粒。
文献普遍指出炎帝在南方。出土文献如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炎帝乃命祝融……”(祝融在南方,炎帝命之,故南方是他的管理范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黄帝南伐赤帝。”传世文献如《楚辞‧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墨子‧节葬下》:“楚之南,有炎人国。”《淮南子‧时则》:“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天文》:“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史记‧五帝本记》:“南至于江,登熊、湘。”裴骃《集解》引《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引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南十八里也。”(今岳阳洞庭湖边)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另曰:“厉山”、“厉山今随之厉乡也。”李泰《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山。”司马贞《三皇本记》:“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同时,曰:“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汉书‧魏相传》:“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宋罗泌《路史‧后纪三‧炎帝》云:“盖宇于沙,是为长沙,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有唐尝奉祠焉。”
传统经学有关神农生活地的讨论,最靠北的说法,是依靠汉唐文献所载神农源自“烈(列)山”或“厉山”,后人视之为鄂北随县厉山镇,现建有炎帝庙;最靠南的说法,则是炎帝葬于长沙茶乡,或说在今株洲炎陵县。大部分文献指出长江中游南楚地区,以洞庭平原为中心,南至湘中盆地,北达江汉至汉北平原。传统上关于长沙或厉山的考证,都是采用几千年后的文献中的地名,既不考虑文献中这些地名的来源,又不考虑同名的地区,尤其是文献中说法很多: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烈山氏、厉山氏,又说姜姓等等,这些说法的意思无法厘清,更加不能与现有的地名对照。可见,依靠地名讨论神话的产生地相当不妥。不过我们由此了解,传统所指出的地理范围,确实包含了稻作发祥地以及最早的稻作文明古国的范围。
大部分文献依据五行结构把炎帝定在南方。虽然在此结构里,被视为楚国始祖的颛顼定在北方,却没有人据此以为颛顼是华北的帝王,换句话说,虽然文献一惯地表达神农为稻作地域的神,但却很难用这些文献做直接证据。在不含有五行概念的文献中,子弹库帛书只是表达南方之相对方向而已;只有《列子‧汤问》和《淮南子‧时则》所表达南方的意思比较具体:前者指出炎人国在楚国之南,后者则说明赤帝所司在颛顼统治的国家以南,也许可以据此考虑,战国、西汉时期的观点认为,战国时期的南楚地为神农的发祥地,即今湖南平原地带。虽不能用这种晚期记录做证据,但却可将其视为线索,恰与考古发现之间存有呼应关系,如时代最早的稻作聚落以及最早且最原始的稻田遗存,都发现于湖南省北部的洞庭平原。
最近还陆续出现一些新的说法,其中有把湘西会同视为神农故里者,依据是认为《帝王世纪》所说的“列(烈)山”或“连山”,即是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连山,而连山盆地北部的火神坡就直接源自炎帝。
还有些学者将位于怀化的高庙新石器文化视为炎帝神农“部落”的遗址。此地确有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生活的遗迹,据此说法,高庙文化被解释为早期稻作文化,并认为有似照八方安排的八庙遗迹,而刻纹白陶为神农部落信仰与精神文化的表现,如双头鸟的刻纹被视为《拾遗记‧炎帝神农》所提“丹雀”图案等。
在召开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时,李学勤还提出,需要“克服湖南特别是湘西地区是古代荒蛮之地的偏见。”在上古时湖南地区绝对不是“荒凉之地”,此乃毋庸置疑。不过怀化一带是低山区(图四),这里的高庙文化是有代表性的游猎族群文化,并非稻作农耕文化,所以不可能产生神农神话。至于周围旧石器时代的遗迹,更不能用来说明该地有农耕生活的成分。因此湘西高庙文化的说法不能成立。
综上,基本上可以排除神农为某一华北地区的神祖。就考古所见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可知,在华北粟作聚落生活中,狩猎大型动物的比重仍很大,并且在信仰方面也可见有猎民英雄。这些人群的生活情况很难形成教导人们不吃野兽的肉、不穿皮毛的皇圣王英雄。由于粟黍产量不高,且粟作地带的自然环境冬季较冷,所以在新石器时代,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完全以农耕为主的纯粹粟作文化;只有在稻作的北界地带(豫中南部为主),形成了比重不同的以稻作、粟黍为主的农业社会,但这都是时代较晚的非原始农业文化。
长江流域稻作文化所产生的生计方式更加符合产生神农这类英雄。出土及传世文献中关于神农的描述,均表达他是南方的英雄;传统经学考证将与神农有关的地域划于两湖地带,包括湘江、长江、汉江流域的平原。文献所描述的空间范围,确实既是稻作萌生之地,也是早期稻作文明的发祥地。这种关系,陆续有人提出,但却不能因此而直接论定神农神话源于此,因相关文献时代都很晚,不能用作直接的证据。英雄传说与地方上古文化记忆的关系,需要经过前文所述几种不同的层面去评估。
第一,就长江中游自然环境来看,此地土肥水多,气候相对温润,所以陆生和水生动植物众多。有浅水和深水的鱼、虾、螺等,因此也有吃鱼的鸟类;水中有莲、菱角等,水边有野生稻丛,因此也有吃谷的鸟类。因此这是生态环境丰富之地,允许在较小的范围内满足一小群人对食物的需求,既而吸引人们定居;在野生稻丛附近定居的人们,认识水稻,进行采集、栽培。
第二,长江中游考古研究表明,洞庭平原西侧(主要是澧阳平原,图五),从旧、新石器之际已始见在水边岗地上的小聚落,这是半定居和全定居生计的萌生。这些人因为依赖水生食物资源,不得不邻水而居,并在这种环境中认识了稻谷而逐渐发展出稻作农业,处理水与居地的关系便成为此时择址营居的重要考量。
第三,洞庭平原新石器考古研究表明,十里岗文化(年代范围预估在距今13000─9500年间)时期岗地上的人类活动面上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在此基础上,彭头山文化(约距今10000─7800年间)成为最早的稻作文化;并且,长江中游的农耕发展,从彭头山文化以降,经过皂市下层文化(约距今8000-7000年间)、汤家岗文化(约距今7000-6000年),表现出了完整的一脉相承的进步过程。到了新石器晚期的汤家岗文化,已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技术和稻作农耕社会形态。
第四,按照前文所提出的寻找神农传说发祥地的指标:只有长久在同一个地区定居的文化,才能稳定地发展农业,并将远古祖先的故事一代接一代地传给子孙后裔。换言之,仅从稻作萌芽来关注,还不足以厘清神农故事可能的发祥地,还需要考虑长期一脉相承的发展。因为只有相当成熟及成功的稻作社会,才能有这种对其萌芽之初的文化记忆,并将其具象化于神农英雄这种形象。
神农神话的产生,应是以稻作起源到后续农耕社会生活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观念对自我的反思为背景的。故这一定是以耕作为主要生计的文化所创造的,是非常成熟的农耕文化对自己源头的反思,从几十代几百代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中,升华为黄金时代的英雄皇圣。汤家岗农耕文化,已不是早期那么依靠粗放农作,因其已发展出很高的技术,其时在灌溉、稻田等方面,都表明集约农作已有一定的发展,且其直接的源头正是本土族群转身为从事稻作的栽培。
换言之,在长江中游地区,从彭头山文化稻作起源至汤家岗文化稻作生产方式基本成熟,这是一个长达三、四千年的持续稳定地在本地发展的过程。长期在同一地域范围定居及发展的族群,因为不流动且不中断传承,才能形成“本地社会”以及人们自我认同为“本地社会”的主题。这种认同意味着大家对其源头均有共识,所以其自然观念、价值判断和英雄形象是共同的。如果本地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教导耕地的英雄就应该被认为是共同的皇祖。也就是说,长期定居于自身族群故乡地区定居的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累积起足够的自我认知及社会认同,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思考、评价及传记自己的源头,以继续传给后裔。
第五,上述这种因长期保持自我认同而创造与传记史诗与英雄的状态,其实进一步标志着该持续发展的古社会正在走向文明化的阶段。而长江中游从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所谓“新石器革命”起,发展到所谓“城市革命”,这是从本土社会内部原生创造出原本从来没有过的国家文明。长江中游的农耕文化体系,从水田技术发达的汤家岗文化起,社会规模开始变大。大溪文化时(约距今6300年-5500年),整个长江中游平原已被开拓,且与周围山地人有较多来往、交易,并对后者生活方式产生实际影响。稳定而长期定居,一脉相承地发展,逐渐扩展领土范围;最后,该区域也从新石器早期聚落社会起,经过自身内在发展,直至青铜时代及国家文明阶段。在油子岭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时(约距今5750-4750年),长江中游平原大区域范围内衍生了以灌溉稻作为组织和生计基础的东亚最早的古国家文明。接着在石家河文化(约距今5000-4300年)、后石家河文化(约距今4300-3700年),以及盘龙城文化(约距今3700-3250年间)时期,可以继续观察到连续发展、扩展及演化的文明及政权体系;其中,盘龙城文化即是商文明。
以澧阳平原为例,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从彭头山时代直至石家河时代的聚落,人们有几千年居住在此地及种稻,稻作、制陶、工具技术一脉相承地发展,生活的基础一以贯之。虽然很少有遗址叠压了从彭头山到石家河的全部地层,但是人们在这个区域定居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且遗址的规模和数量一贯地增加。
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地区,从稻作萌芽起,就表现出完整而一脉相承地进步及演化过程:从新石器早期到青铜时代;从定居的小聚落到大型国家。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澧阳、洞庭平原扩展到江汉之间,又越过汉水到达汉北地区;并从屈家岭时代起,自汉水北岸继续向北开拓而影响整个黄汉平原。所以这不仅是长久的历史文明进程,也是影响力广大的历史文明。这种文明,虽然最终还是被毁灭及消退,但它的精神文化仍会在后世文明中留下痕迹,后世的新族群也会把已消失的文明的故事吸收而视为己出,继续传播下去。
谨慎观察、思考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地图,恐怕只有长江中游平原地带,才有创造神农传说的条件。大约应该是从相当于汤家岗文化或大溪文化时候的社会以来,神农传说才成为重要的共同理想,但是神农神话所追思的时代,应该大致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笔者详细分析彭头山文化遗存后发现,该文化不但时代非常早,而且从内容来看,它也确实是一种独一无二、非常完善的新石器文化,与同时代甚至更晚时期的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相比,彭头山文化都堪称奇迹;并且彭头山文化有很多独有的特殊点,恰与神农传说相吻合,这种现象值得我们用心思考。
(未完待续
- 0000
- 0000
- 0000
- 0004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