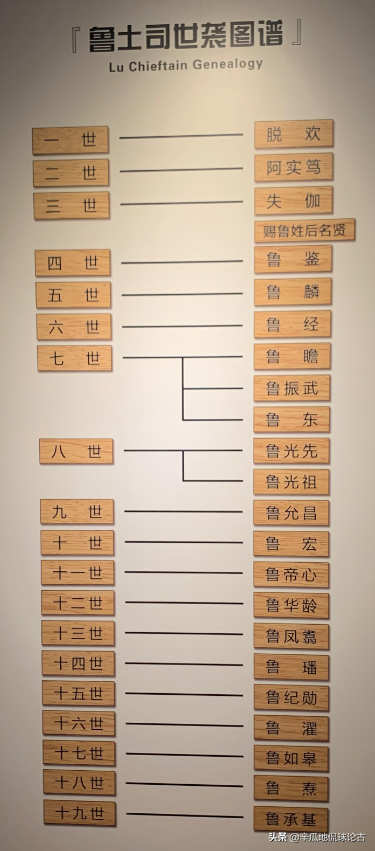霍巍: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
本文讨论的“古代青海”,主要指史前至唐代时期的青海。青海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北隅,周围被部分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积石山等山脉所环绕,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与同处这一地理单元内的西藏高原相比较,青海的自然环境更为优越,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均在2000米至4500米之间,湟水、黄河谷地和柴达木盆地的海拔则只有2000米至3000米,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各具特色的地理区域:其北半部为河西走廊南侧祁连山脉所隔阻而成的高原,其自然景观主要为沙漠和草原;其南半部为昆仑山脉以东的延伸地带,为长江和黄河两大河流的发源地带,其自然景观为起伏的地形、连绵的高原河谷与宽广的草原相接;其东半部则为河湟区域,其自然景观以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为温暖的地带。总体而言,青海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起伏和缓、地域辽阔,由各条山脉所分割形成宽谷与狭谷地带,根据不同的纬度高低形成若干条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的自然通道。日本学者曾经形象地将这些自然通道称之为“冰原之道”、“河谷之道”、“水草之道”和“绿州之道”①。活动在青海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群,通过长期适应这一自然环境,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顽强地生存繁衍,同时也利用这些高原通道积极向外开拓发展,书写了青海古代文明史。
但是,长期以来,在古代中原士人的心目中和他们的笔下,共处于青藏高原的青海、西藏等地都是人烟罕见的不毛之地,不仅荒凉穷困,而且与世隔绝,很难想象这些地区历史上也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的经往之地和区域性文明中心。事实上,无论是在古代文献典籍当中,还是近代以来青海地区的考古发现,都提供了大量证据,表盟青海并非是一座“文化孤岛”。水涛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方,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环境差异甚大。整体看,中国内地的地形呈西北高耸、东南低平的走势,自西而东形成三个落差很大的台阶。……作为中国一个局部的大西北地区,地理环境更为封闭,这里恰好处在黄河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中间位置,是不同文化接触、渗透的敏感地带,也是探索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关键地区”[1]。青海作为大西北地区的战略要地,自远古以来便有史前人类频繁的迁徙活动来往于此;而且著名的“青海道”在南北朝时期曾经一度还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干道之一;隋唐时代吐谷浑、吐蕃先后对青海的有效控制,使得南来北往的官方使节、各国使臣、求法僧侣、商队贩客们都曾经在青海这块土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本文仅选取历史长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三个重要片断,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试作探索。
一、史前至汉代青海的对外交流
从较为可靠的考古证据上看,至迟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开始,青海地区便已经出现了若干具有外来文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大多是通过游牧的草原民族传来。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的一种土著文化,常见的遗存主要为墓葬,既有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也有部分为偏洞室墓,葬式复杂[2]。在卡约文化的墓地中,出土有大量具有草原游牧文化色彩的青铜器,包括铜泡、铜铃、铜管等马具或装饰品,另外还出土具有北方青铜文化特点的铜镜、铜矛、铜刀、铜斧、牌饰等器物以及刻划有鹿纹的骨管等器物。日本学者三宅俊彦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器中的文化因素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卡约文化独自形成的文化因素,但与北方系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类是与中原和北方系青铜器共同的文化因素;第三类则完全是来自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3]。其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在湟源县发现的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中,曾经出土过一些造像特殊的青铜器,如采集到的青铜人面饰上,横杆的上方饰有四个人面,有的仅有头部,有的延伸到颈部,其造像都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第87号墓中出土有一对“青铜竿头饰”,青铜的横竿上铸出一对牛的形象,一大一小,相向而立,这种在青铜器上塑造动物形象的做法,无论是从造型还是风格上而言,都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铜装饰艺术具有相同的特点,所以可以肯定,其源流也应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带,只是在传入青海境内之后,被卡约文化的居民加以了改造[4]。
两汉至魏晋时期,青海主要是羌人的聚居区,也有一部分匈奴、月氏人杂居其间,汉武帝时期,汉的势力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东汉时随着平定羌人战争的扩大,终两汉之世,在青海形成多胡、汉多民族杂处的格局。同时,随着汉武帝对西域的开拓与征发,张骞通西域之后汉帝国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丝绸之路”成为东西交通的主要路线。青海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近便,很可能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之一。这个时期从考古文物上也可见到一些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遗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青海上孙家寨墓地连续发掘出土了180多座汉晋时期的墓地,其年代从西汉至魏晋初期,墓地中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包含有汉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相似的杀牲随葬、截体葬、二次葬等葬俗,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在该墓群乙区第3号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具有西方色彩的银壶,应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入青海境内的西方金银器[5]。此件器物形制为直口、长颈、鼓腹、平底,一侧带有单耳,在器物的口、腹、底部有三组错金纹带,口饰钩纹、底饰三角纹,腹部纹带由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杂组成。关于这件器物,发掘者初步认定其可能是3世纪的安息制品,腹部捶打出的一周花纹酷似西方流行的忍冬纹样。之所以在青海出现西方的错金银器,有可能与墓葬的主人族属为匈奴人有关,因为在同一墓地的第1号墓中,出土了一方带有印文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铜印,这应当是东汉政府颁发给当时青海境内匈奴部族首领的印信,既然此墓为匈奴人的墓葬,那么出土银壶的第3号墓的墓主也应当是同一族属。因此,这件安息制品出现在远距安息千里之外的匈奴人的墓葬中,与东汉时期青海境内已经随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断出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活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相关。
1982年,在青海平安县窑坊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当中,有一方画像砖的内容也曾引起过学术界的讨论。这方画像砖主体画面为一庑殿顶的房屋之内,有两个相对而坐的人物,他们的特点均头戴帽子,身上披有一件与佛教僧人的袈裟极为相似的衣物,左臂袒露,右臂下垂或置于膝上,两人的中间为一案,案上置有一钵,案下为一小人双手捧一罐跪伏于地,作奉侍状。关于这幅汉画像砖的内容,学术界有意见认为图像中所反映的系禅坐的“佛教僧人比丘形象”,有可能与“僧道送丧”的情景有关[6]。如果仅仅从这件“疑似”僧人的画像砖上推测此时青海已经就出现了“僧人比丘”和“僧道送丧”的习俗,显然还证据不足。但是,如果结合东汉时期国内各地已经普遍发现过一些受到佛教影响的所谓“早期佛像”画像这一点来看[7],东汉时期佛教经过西北丝绸之路也传人到青海这种可能性的确是不能排除的。与青海相邻近的四川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钱树上,都曾经发现大批“早期佛像”,但实际上均是接受了佛教文化影响之后,中国本土固有的神仙信仰体系中“西王母”之类图像的“佛装化”变型而已,并不真正具有佛教偶像崇拜的意义[8]。宿白先生认为,东汉时期出现在四川成都和长江中下游的这类“早期佛像”一个重要的来源,很可能是从西方通过西域的胡人部族传人中土,他称其为“胡人礼奉之像”[9],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如果将青海平安出土的这方汉画像砖也纳入到这类受到佛教影响的“早期佛像”图像中来看待,似乎也并无不妥。如此说不误,则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青海一地因自汉晋认来便是胡汉杂容之处,西域的“月支胡”、“湟中胡”、“羌胡”等大批胡人游牧族群都曾在此迁徙活动,汉晋时期的早期佛教信仰和带有佛教因素的图像通过青海再传输至益州成都、孙吴等地也是可能的。联系到下文中我们将要进一步讨论的南北朝时期“青海道”的开通这一问题来考虑,更增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海道”
所谓“青海道”,又称为“吐谷浑道”、“河南道”,是指传统“丝绸之路”支线的从青海至西域的一条线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北道多被塞堵不通,其重要性开始凸显。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一文中论述:“汉代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以入西域,是内地和西北边区间乃至中外间的交通要道。但这并非唯一的通路,根据史籍记载,我们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张骞在大夏见来自身毒的邛竹杖与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后虽然不那么显赫,但南北朝时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结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颇大的作用”[10]。据唐长孺先生考证,西晋末年以来,东晋、刘宋等南朝政权与北方的前凉、西凉和北凉这几个割据政权占领河西走廊期间,还一直保持着通使往来,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由于秦陇地区多被中原或地方政权所隔绝,自江南通往西域,多从长江溯江而上,先西行入益州,再由青海入吐谷浑境,然后借道前往西域[11]。
继唐长儒先生之后,学术界对于“青海道”的讨论已经十分深入②,所列举的文献材料中涉及这一时期不少通过益州(今成都)北上,沿“青海路”抵达丝绸之路西段进入西域,或由“青海道”先抵益州,再顺江而下抵达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求法僧侣、商队与商人、官方使节等不同身份人士的有关事迹,史料甚为丰富,兹不再一一列举。从考古实物材料上看,这一时期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资料可为佐证:
早在1956年,在青海西宁市内城隍庙街便发现盛储货币的陶罐一件,其内盛有银币约百枚以上,当中有76枚银币经鉴定属于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6-484)在位时所铸,夏鼐先生曾对此作过详细考证[12],认为这是当时中西交流频繁的实物证据。这批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可分为A、B两式,区别在于正面卑路斯王冠装饰不同,A式王冠象征“天”和袄神奥马兹德,B式冠以鹰鸟之翼代表太阳[13]。对于这项考古发现,徐苹芳先生指出:“西宁波斯银币的埋藏虽已晚至唐代以后,仍可说明4至6世纪河西走廊被地方政权割据之后,从兰州(金城)经乐都(鄯州)、西宁(鄯城)、大通、北至张掖,或西过青海湖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至敦煌或若羌的这条‘青海道’路线,它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线”[14]。
2000年,青海乌兰县城20公里以外考古发掘的大南湾遗址中,发现墓葬、祭祀遗址和房基遗址等[15]。墓葬的形制与吐蕃本土发现的石丘封土墓极为近似。从房基当中出土有金币1枚、银币6枚,其中金币两面均有图像和铭文,据考古发掘简报描述,“正面是王者正面半身像,头戴有珠饰王冠,两耳部各坠有一对小吊珠耳环,上衣系交领外衣,褶皱处用联珠纹式的小点来表示。左侧为一圆球,其上立十字架,右侧为NVSPPAVG字符。背面图案为带双翼天使立像,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着圆球,圆球上立十字架,图像右侧环绕有AAVGGGE字符”。银币6枚共分为四式,基本特点正面均为王者肖像,王者多戴冠,有的在冠上饰以新月、圆球图案,背面多为拜火教祭坛,坛上有火焰,火焰两侧有的饰以新月和五角星纹饰。据初步判断,这枚金币为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时期所铸,而银币则可能属于波斯萨珊王朝的不同时期[16]。
2002年,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发现的4座古墓中,又出土了1枚拜占廷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在位时期的金币[17]。上述这些外国古代货币的发现,是这一区域中外交流的一个有力证据,从时、空范围来看,可能与粟特人的商贸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均证明这一时期东西交通经过“青海道”的繁荣情形。
近年来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方面新获得的一件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人出人、出马条记文书》,经荣新江先生释读研究之后,又提供了关于“青海道”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18]。阚氏高昌政权建立的背景,是在439年北魏灭北凉之后,北凉王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北上占领高昌,建立高昌大凉政权,高昌太守阚爽投奔漠北的柔然汗国,柔然于460年杀沮渠安周,灭大凉,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成为吐鲁番历史上第一个以高昌为名的王国,阚氏高昌王国实际上成为柔然建立的傀儡政权,直到488年为高车王阿伏至罗所灭。这份文书主要记载了阚氏高昌王国迎送来往使节时向属下各城镇分派出人、出马匹的情况,文书中出现的各国、各地使节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带“使”字的婆罗干、若久、处罗干无根、郑阿卯等为高昌官府所熟悉的柔然使者;另一类则是带有“使”、“王”、“客”等字样的使者或者国王,如乌苌使、吴客、于合使、婆罗门使、鄢耆王等。荣新江尤其关注到文书中提到的“吴客”,应是来自南朝的使节,过去曾在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持世经》卷一尾题中出现过,只是一度将其解释为一般“来自江南的寓客”[19]。荣新江认为,新出的这件文书证明,“吴客是阚氏高昌官府派出大量人员所送使者称谓,则应为正式的南朝使者,他们和子合国的使者在永康十年(475)三月八日一起前往北山,应当是出使柔然的刘宋的正式使团。因此,在早期的高昌文书中,‘吴客’或者并非简单字面意义上来自南朝流寓高昌地区的普通人,而更可能是高昌官府对于南朝来的使者的特定称呼”[20]。这个重要的发现表明,既使是在南北朝时期混战的情态之下,南朝使节仍然可以与其他西域国家的使节一道,通过高昌出使当时的西域强国柔然,这些号称“吴客”的南朝使节所经行的路线,应当是循着“青海道”而行,具体而言是从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溯长江而上,再从益州(今成都)北上,经吐谷浑界抵达高昌。这条道路的前半段,也被称为“吐谷浑路”或者“河南道”,因为吐谷浑被南朝称为“河南国”之故[21],实际上也即本文所称的“青海道”。之所以有“吐谷浑路”或“河南道”的这一称呼,日本学者松田寿南曾经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
在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以青海地区为中心的吐谷浑国,曾经向关中(秦、雍),或河西(凉土),或通过后者向鄂尔多斯和蒙古,或者是向蜀,或是经过这些地方向南朝频繁地转送过队商,同时并与西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保持着很深的交往,作为西域贸易的中转者在东西交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北魏官吏宋云和僧侣惠生为首的人竺使一行,在进入西域时就要依靠吐谷浑的保护和向导,取道连接湟河、青海、柴达木、罗布泊南岸地区的所谓“青海路”。此外,在记载中也留下了经同一条道路东行或西行的若干僧侣。何况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西域的商胡频繁往来于此路。的确,青海路与“河西路”是平行存在的。[22]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青海道”的确立,不仅有大量文献史料可资佐证,还有不断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如银币、吐鲁番文书等)提供可贵的旁证。正是因为这条道路在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后来北魏对吐谷浑发起的攻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松田寿南认为“毫无疑问包含有把西域贸易中的竞争对手排除掉”的因素在内。因为吐谷浑对青海道的控制与利用,成为其日益登上国际贸易舞台的支撑点和进一步向西域扩张的出发点,通过“与蜀汉(四川盆地)、凉州(河西走廊)、赫连(鄂尔多斯沙漠地带)进行的盛大交易的背后,可以认为其中也隐藏着通过罗布地区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后来隋炀帝和唐太宗在西域经营中从远征吐谷浑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其中的原因也与“青海道”具有的重要战略、经济地位直接有关[23]。
三、唐代吐蕃对“青海道”的经营
唐代与西域的主要通道,主要是沿着汉以来凿通的“丝绸之路”从长安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到达沙州(敦煌),再由沙州进入到***,由***去往天竺、中亚等地。上述通道,也可称为丝绸之路的“东段河西路”,这是唐代与西方交通的主干道和大动脉。而青海则是这条主干道上重要的结点,至少有四条道路可由青海通往西域[24]。所以在唐代初年,由于吐谷浑仍然控制青海地区,并在唐太宗初期经常入寇骚扰这一地区,其目的和企图主要还在于干扰东西贸易通道[25]。实际上,中原王朝从隋炀帝时期开始,便已经注意到吐谷浑的这一意图,故派遣裴矩重开河西道,而有意识的冷落“河南道”,使河西道的地位有所回升。至隋末唐初,唐太宗即位之后,仍依隋旧制,采取再次开通河西道的策略,使控制青海道的吐谷浑再度失去东西贸易之利,不得不动用兵力采取阻绝骚扰河西道的策略,由此引发唐太宗在贞观八年(634)出兵大举讨伐吐谷浑,灭其国,使其余部依附于唐朝之事。
其后,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向外扩张,也将其用兵的主要方向指向了青海地区,与唐争锋。对于吐蕃的战略意图,台湾学者林冠群认为,此举不但具有突破封闭高原出口的功能,从军事上增加其防御纵深,而且可以取得较为优厚的农牧资源,对吐蕃的对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可使青海地区成为其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拓展之前进基地[26]。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一条,那就是从经济上首先掌控青海道,取得掌控东西贸易的一个立脚点,进而再向西域全境扩张,完全扼控唐代丝绸之路,从陆上卡断唐代中外交通的主动脉。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蕃的这一战略意图曾经一度达到。
近年来,青海地区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不少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线索。例如,在由青海省文物考古所发掘的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墓葬中,出土有各类丝绸的残片,据发掘主持者许新国先生的判断,这些丝绸品种中有18种可能为中亚、西亚所织造。许新国认定,出土的西方织锦中,有一件为中古时期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据他称这是“目前所发现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27]。都兰热水大墓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可能属于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对此许新国也有过论述[28]。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博士曾经考察过这些从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金银器,认为其中出土有一件奇特的器物,“一只银质珠宝箱被埋藏在那里,它看上去是准备用来装sarira(一种纪念品)的。虽然有一部已被压碎,就像是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再造的,但考古学家们相信这是来自粟特的工艺品。这只遗骨匣的形状和尺寸都使我们想到已经被挖掘出土的粟特银制遗骨匣盒及唐朝的金银遗骨匣”[29]。当然,这些金银器是否与粟特人的纳骨器性质相同还需要慎重考虑,不过,青海发现的吐蕃时期金银器当中带有明显的来自西方的装饰性图案和纹饰,倒是可以肯定的[30]。
在青海都兰墓葬中出土的丝织物当中,还发现一些装饰性图案具有西方神祇的因素。如赵丰先生便注意到在青海都兰发现的丝织物图案中,有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奥斯(Heíios)的原型。赫利奥斯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神许珀里翁及其妹兼妻子特伊亚的儿子,每日驾驶四马金车在空中奔驰,从东到西,晨出昏没,用阳光普照人间。他的形象早在欧洲青铜时代已有发现,盛行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典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这一形象也随之传到东方。赵丰认为,当赫利奥斯出现在北朝—隋之际的织锦上的时候,其所含的文化因素来源已经十分复杂,从***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织锦上,已经含有来自希腊、印度、波斯、中国等文化圈的多种文化因素[31]。但是,太阳神驾着四马所拉的马车奔驰这个最为基本的构图原素,却始终忠实地被保留在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织锦当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物证[32]。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地发掘出土的遗物当中,还有大量珠饰类的装饰品,现保存在都兰县博物馆中③。当中有玛瑙、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等不同的材质,在制作工艺上也采用了当时的许多先进技术,有些工艺是通过印度、伊朗甚至更为遥远的西亚各国传来的。例如,其中一类看上去通体呈墨黑色,但上面却有一道道虎皮斑纹似的白色线条,这类珠子考古学家们把它称为蚀花琉璃珠,主要产地在今天的印度和伊朗高原[33],后来通过远程贸易传入到中国,传入到青藏高原[34]。藏族人民至今仍然十分喜爱这种朴素但又显得高贵的珠子,把它们称为“天珠”。其实,它上面的花纹是采用一种特殊的饰花工艺制作而成。
从上述这些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唐代中原王朝和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对青海一地的争夺,虽然最终以吐蕃对青海的占领而告一段落,但这并没有隔绝中原与青海、西藏等地传统的交流往来,吐蕃出于其长远的谋略,在夺取青海之后,向东将其控制区域直接与唐代中原地区相接连,既可由青海东进河湟,也可由青海北出西域,通对西域丝绸之路,经印度河上游的大、小勃律(今雅辛及吉尔吉特地区)、护密(今阿姆河上游的瓦罕河谷地区)等地以及***地区南疆的于阗(今和田)、喀什一线,直接将其势力扩张到中亚地区。
吐蕃对青海的经营具有多方面的目的,既有其东向发展、与大唐王朝争夺河湟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不可低估其通过控制青海、从而控制西域丝绸之路的更为宏大的战略意图。从客观效果而言,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进一步扩大吐蕃与我国唐代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走出封闭的高原、面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习和吸收周边地区与国家先进的文化与技术、艺术与思想等因素,提升和改造自身的文化品质,最终融人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当中,都具有潜在的历史意义。
①[骈日]阿子岛功.《青海シルク口ードの自然环境——谷ぁいの道、水草の道、绿洲の道、冰原の道》,《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口ードの研究》,《シルク口ード学研究》Vol.14,2002,1:P37—77。
②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相关的论述较多,如: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J].史学杂志,1939年,第48编第12号;松畴男.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76—191;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学报,1958(1);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J].考古通讯,1958,(1);周伟洲.古青海路考[J].西北大学学报,1982(1);周伟洲.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一青海道[J].西北历史资料,1985(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也有关于“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等论及青海道与河南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八十三,1985年;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教[J].佛教艺术,1995年,第218号;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J].历史地理,1986年,第4辑;薄小莹.吐谷浑之路[J].北京大学学报,1988(4);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J].中国史研究,2001,(1);姚崇新.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来风格渊源再探[A].华林[C].北京:中华书局。2001:245—258,后收入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2—62页;陈良伟.丝绸之璐河南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J].四川大学学报,2005(2),等。
③这批资料因多系盗墓所出,没有明确的考古出土背景,材料也尚未正式公布,系笔者于2012年实地考察时观察注意到的。
参考文献:
[1]水涛.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A].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02.[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编.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A].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63—165.[3][日]三宅傻彦.卡约文化の青铜器叨.シルク口ード学研究,2002,(14).[4][17]许新国.青海省考古工作五十述要[A].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6-18.25.[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缩.上孙家寨汉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60.[6]许新国.青海平安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像考[A].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C].北京:燕山出版社:101—102.[7]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J].文物,1980,(5).[8]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2007.[9]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J].文物,2004,(10).[10][19]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A].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北京:中华书局,1983:189—190.[11]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向江南的道路[A].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北京:中华书局,1983:168-195.[12]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学报,1958,(1);王丕考.青海西宁波斯萨珊朝银币出土情况[J].考古,1962,(9).[13]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学报,1958,(1).[14]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J].燕京学报,1995.(1).[15][1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青海鸟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2,(12).[18][20]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J].历史研究,2007,(2);转引自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2—58.49.[21][23]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78.180-181.[22]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J].史学杂志,1939;转引自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80.[24]赵荣.青海古道探微[J].西北史地,1985,(4).[25]周伟洲.吐谷浑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76.[26]林冠群.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A].唐代吐蕃史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70.[27]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15—16).[28]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中国藏学,1994,(4).[29]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3).[30]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31]赵丰.魏唐织锦上的异域神祗[J].考古,1995,(2).[32]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55—257.[33]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J].考古,1964,(6).
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 0002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