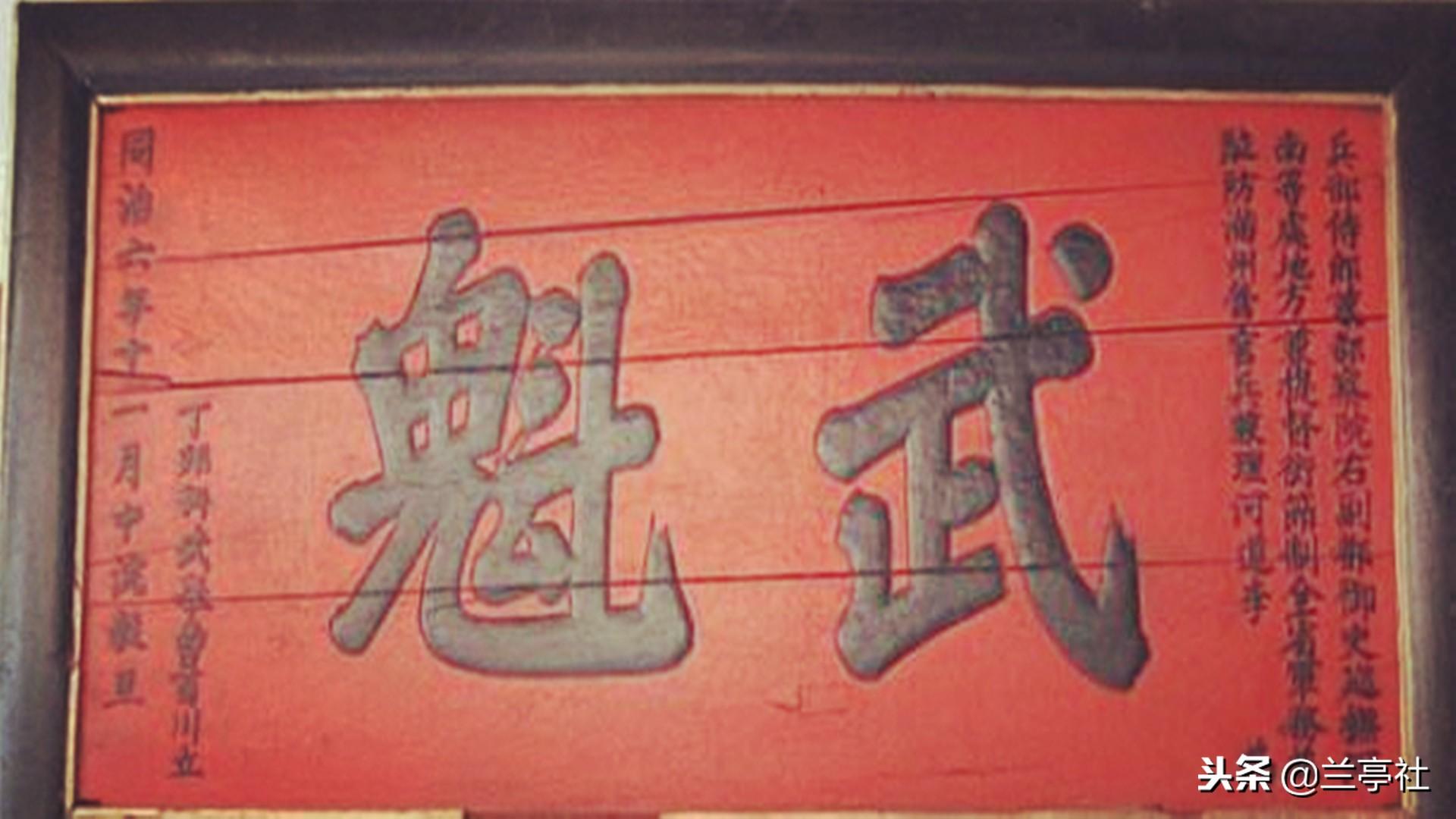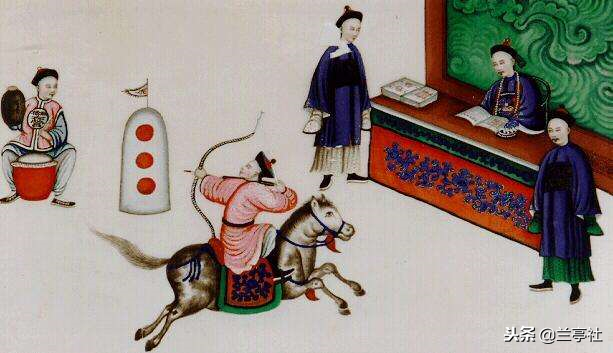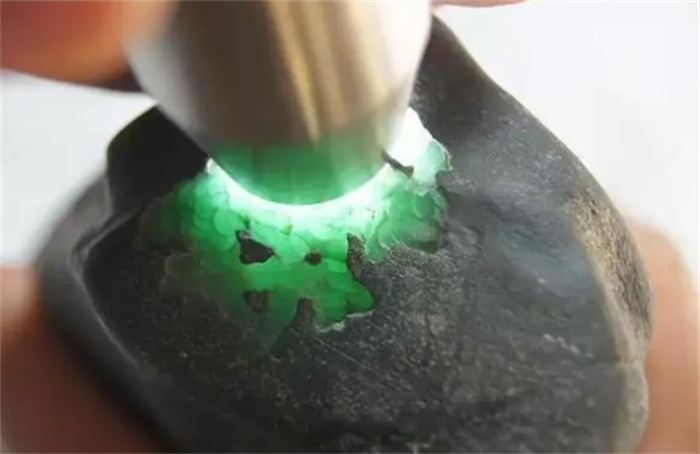滕铭予: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
史载西周中期孝王时,秦之先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始有“秦”之称。非子所居“犬丘”与邑“秦”之地望,研究者多认为在今天的甘肃省东部(注: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33注(16);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 《文博》1987年1期;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 1994年。)。但嬴秦之先祖中潏早在商时就已“在西戎,保西垂”(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西垂”的地望亦被认为在今陇东地区(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1982—1983年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发现了上限可至西周早期的秦文化遗存(注:甘肃省文化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 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嬴秦一族活动于陇东地区的历史,应早于“邑秦”之时。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15年后,秦王朝遭覆灭,西汉政府在其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使当时的中国又处于一种半分裂状态。诸种考古学资料表明,到西汉武帝以后,中国南北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才开始趋向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所创统一大业,至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完成。
由此,本文所论“秦文化”,其时间范围上限包括西周中期“邑秦”之前,下限至汉武帝时期,其内含是指嬴秦一族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在其生息、活动所至范围里,创造、使用、遗留至今并已被科学的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遗存,那些与嬴秦族有着紧密关系,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人群,在同样的时期、同样的地域里所使用的,与秦文化具有同样风格的古代遗存亦属于本文所论“秦文化”范畴之内。在秦文化研究中,长期被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极为关注的关于“秦人起源”的讨论,因尚缺乏能够说明问题的考古学资料,不在论述范围之内。
一
对于秦文化的科学田野考古工作,始于30年代中期北平研究院在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对“屈肢葬墓”的发掘,到今天已有6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发现与界定
当年发掘宝鸡斗鸡台的“屈肢葬墓”时,并未明确认定其为秦墓,苏秉琦先生只是指出:这种屈肢葬墓“与中原的古代传统习惯不合,……似当是一种新的外来文化,……”(注: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第五章·年代与文化》,《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半坡和沣西客省庄,分别清理了112座和71座东周时期墓葬(注: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9年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发掘者也只是讨论了这些墓葬的年代,均未涉及墓葬的国别及性质。
到了60年代中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有计划地对曾为秦都的咸阳故城遗址(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6期。)、雍城遗址(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查》,《考古》1963年8期。)、 栎阳故城遗址(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1期。)以及秦始皇陵园(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8期。)进行了勘查,开始了目的明确的、 针对秦文化的考古工作,同时对宝鸡附近的福临堡(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年10期。)、秦家沟(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村秦墓发掘记》,《考古》1965年7期。)二处春秋墓地进行了清理, 并因其所在地在春秋时期属秦国所辖而论及可能为秦国墓葬。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对秦文化的认识是从确认遗存所在地的国别开始的。
70年代到80年代,是秦文化考古资料发现和积累的时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点对雍城和咸阳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发现了与秦都城有关的宫殿、宗庙、陵园以及城郊的墓地等大量遗存(注:对雍城所做工作:凤翔文化馆等:《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省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 文物出版社,1980年;雍城考古队:《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9期;雍城考古队吴镇峰:《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雍城考古队尚志儒、 赵丛苍:《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补正》, 《文博》1986年1期;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3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一年凤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工作站:《凤翔邓家崖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1988年发掘)。
对咸阳所做工作:陕西省博物馆等:《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1期;王学理等:《秦都咸阳发掘报道若干补正意见》,《文物》1979年2期;咸阳市文管会等:《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陈国英:《咸阳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5 年3期;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由于兵马俑坑的发现, 对秦始皇陵园的勘查和发掘工作亦全面展开(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临潼县文化馆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12期;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园陪葬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7期;秦始皇陵考古队:《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简讯》,《文博》1987年1期;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宫”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6期。)。在宝鸡(注:宝鸡市博物馆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11期;王光永《宝鸡市渭城区姜城堡东周墓》,《考古》1979年6期;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9期;王红武等:《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9 期;何欣云:《宝鸡李家崖秦国墓葬清理简报》,《文博》1986年4期;高次若等:《宝鸡县甘峪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文博》1988年4 期。)、陇县(注:尹盛平、 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1期;肖琦:《陕西陇县边家庄出土春秋铜器》,《文博》1989年3期。)、 长武(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长武上孟村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 户县(注: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省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曹发展:《陕西户县南关春秋秦墓清理记》,《文博》1989 年2期。)、铜川(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枣庙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2 期。)、大荔(注:陕西省文管会、大荔县文化馆:《朝邑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1978 年。)和甘肃东部(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刘得桢等:《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1 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天水西坪秦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88年5 期。)也发现了较多的秦文化墓葬,对秦文化的各种考古学遗存的认定也因其均地处秦国统治范围而明确无疑。首次被研究者确认为秦国墓地的即是在雍城南郊发掘的八旗屯墓地(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年。),由于该墓地在墓葬形制、葬式、随葬器物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可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因此八旗屯墓地以及在雍城南郊发现的诸墓地,便成为此后研究者界定秦墓的重要标准。
这一时期,在湖北云梦(注: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6期;湖北孝感地区第二期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9期;云梦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1期。), 四川荥经和青川(注:荥经古墓发掘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四川省博物馆、 青川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1期。),湖南溆浦和汩罗(注: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溆浦马田坪战国西汉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湖南省博物馆:《汩罗县东周、秦、西汉、南朝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河南泌阳(注: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9期。)、三门峡(注:黄士斌、 宁景通:《上村岭秦墓和汉墓》,《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内蒙(注: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崔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5期。)等地,亦发现了大量带有秦文化特点的遗存。
2.分期与编年
到80年代初期,秦文化的考古发现已初具规模,积累了有关城址、建筑、陵园、墓葬的大批资料,必然会引起对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此基础上,始有学者对已发现的秦文化墓葬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的研究,标志着秦文化研究已经从对其面貌的确认上升到将其作为一个历史进程而对其进行进化式的研究。韩伟在《略论陕西春秋战国地区秦墓的年代与分期》中,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和组合,将关中地区的中小型秦墓,分为七期,并将各期秦墓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了秦文化墓葬的发展序列和编年(注: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叶小燕在《秦墓初探》中, 将秦墓分为五个阶段,虽然在分期问题上较韩文简约,但其所论不仅涉及到秦文化的分期,而且还将其与外部文化进行了比较,讨论了其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注: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陈平所作《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对秦墓青铜容器进行了形制的排比以及分期与年代的讨论(注: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3 期。)。其后亦有学者对秦文化墓葬进行过分期研究,但其结果大体没有超出上述范畴。
上述对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的研究,都是以已经界定的秦文化自身的特征为出发点,其目的是搞清秦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序列和年代序列,并兼及与外部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为秦文化、尤其是秦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期与年代学的标尺。此后每有新发现的秦墓资料,发掘者大多以上述研究结果为标准,将新资料与之进行比较后将其纳入其中的某一位置之中。
3.源流与结构
对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当已建立起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年代序列后,研究者的目光往往会指向这一序列的两端,即起源和流向。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也不例外,实际上叶小燕在《秦墓初探》中已论及进入西汉初年后,在全国各地所见到的大量带有秦文化因素的墓葬,亦可视为对秦文化流向的讨论。其后又有宋治民《略论四川的秦人墓》(注:宋治民:《略论四川的秦人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刘曙光《三门峡上村岭秦人墓的研究》(注:刘曙光:《三门峡上村岭秦人墓的研究》,《中原文物》1985年4期。)、 高至喜《论湖南秦墓》(注:高至喜:《论湖南秦墓》,《文博》1990年1期。)、 陈振裕《试论湖北地区秦墓的年代与分期》(注:陈振裕:《试论湖北地区秦墓的年代与分期》,《江汉考古》1991年2期。)等, 亦多涉及到秦文化征服六国后与当地文化的关系,以及秦文化在进入汉代以后的流向。
早在80年代初期,已有学者开始涉及对秦文化渊源的探索,主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秦墓中出现的屈肢葬、洞室墓和铲脚袋足鬲进行分析,俞伟超先生曾指出这些特点是秦文化的典型因素,都与西北地区的古代文化相近,进而认为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西戎文化(注: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期,1980年。);韩伟则认为这些特点出现在秦墓中是有条件的,并非是秦文化的传统因素,进而否认秦文化起源于西北地区的西戎文化(注: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4期。);刘庆柱则明确提出秦文化源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注:刘庆柱:《试论秦之渊源》,《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这几种观点都因缺乏没有年代更早的考古资料而显得说服力不足。80年代中期在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发掘了两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和墓葬,从而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线索(注:甘肃省文化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3期。)。赵化成在《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注: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和《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注: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1期。)中, 通过与丰镐地区的西周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的秦文化进行比较,对秦文化进行了界定,并在分析其文化因素构成的前提下,讨论秦文化的渊源。在后文中提出“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的构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墓葬的葬俗,……可能与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有关,二是陶器的基本组合与器形与周人有关。”亦表明作者试图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去追溯秦文化的渊源。
90年代初期,笔者作《关中秦墓研究》,在对随葬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其所存在的不同文化因素,以探求秦文化自身的内部结构,虽未直接讨论秦文化的源流问题,但已指出:对随葬器物所作的某些类型学分析,或“暗示出秦文化与周文化有着某种联系”,或“表明秦文化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注: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最近有牛世山作《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在分析了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各文化因素后,提出秦文化起源于先周文化,并为西周文化的一支地方类型(注: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3期。)。
上述讨论,已不再把秦文化作为一个封闭的单线进化结构来对待,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多元谱系结构,并且在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秦文化的渊源和结构问题,表明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划分阶段的目的是想籍此使研究者清楚秦文化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研究目的与研究层次间的关系,各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每一后起阶段都是以前一阶段的工作为基础,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学科的历史,如同不断的河流,存在着沉淀和扬弃,在它向前涌淌,提出新课题并著力研究的时候,是以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石,又要回头观察前段应解决而未曾研究的问题,甚至还得重新检讨以往看来似已解决的问题。”(注: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二
综上文所述,秦文化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在60余年的历程中,是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进行的,因此到目前为止的对秦文化的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多以城址和墓葬为中心而展开。下文将对秦文化城址和墓葬的研究现状进行论述(注:在秦简、货币、长城、金属工业等方面,亦有学者进行过较深入的整理和研究,由于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因而上述各研究都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1.城址与建筑
据文献记载,秦自“邑秦”之后,曾屡迁其都,有“襄公二年,徙都汧”(注:《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年下张守节《正义》注:“《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宁公(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卜居雍”、“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等。目前经过田野考古工作并已确认的秦都城遗址有雍城、栎阳和咸阳故城遗址。
(1)雍城遗址
雍城是秦国历史上为都时间最长者,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时始, 一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止,长达294年,秦迁都栎阳后,这里仍为秦国西方一个重要的城市(注:《史记·秦本纪》记,秦迁都栎阳后,尚有孝公、德公在雍建橐泉宫、蕲年宫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王行王冠之礼亦在雍进行。)。自70年代后期以来,雍城考古队围绕雍城遗址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目前已确认雍城遗址在今凤翔县城南,雍水北岸,总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在城内中部偏西南地区发掘的马家庄一号建筑群,被认定为秦都雍城时的宗庙遗址(注: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2期。);在姚家岗清理的建筑基址,被认定为德公元年初居雍时的大郑宫遗址(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或认为是春秋时期的雍高寝(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在其附近还发现了储冰用的“凌阴”遗址(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省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和青铜建筑构件的窖藏(注:凤翔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经过钻探的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 被认定为秦的朝寝建筑(注: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在中部偏北处的高王寺、凤尾村一带, 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窖藏,被认为是该地点为战国时期宫殿区的重要线索(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在城内北部勘探出一个近长方形的封闭式空间遗址,被认为是秦“市”(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在雍城的南郊还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可能为雍城的离宫别馆和祭祀场所(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另外在雍城的南郊还发现了大型陵园和中小型墓地(注:见①④中对雍城所做工作中的有关资料。)。
在认定上述诸遗存的性质和用途的基础上,可知雍城坐北朝南,平面略呈方形,其平面布局基本同于《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其宗庙建筑亦可与文献记载之“祖庙、昭庙、穆庙”的三庙制度相对应(注: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2期。)。
(2)栎阳遗址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 栎阳作为秦都的时间仅有30余年。此后栎阳一直作为都城咸阳通向东方的主要门户,是当时军事、经济、交通的中心之一。秦末项羽三分关中之地,栎阳曾为塞王司马欣之都城(注:《史记·项羽本纪》记:“故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汉初刘邦曾以栎阳为临时政治中心(注:《汉书·高帝纪》记:汉王二年,冬十一月“汉王还归,都栎阳”。),东汉初年,栎阳城废弃。因此现将栎阳称为秦汉栎阳故城。
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秦汉栎阳故城做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工作,现已确知栎阳故城遗址在今临潼县武屯乡关庄和王宝屯一带,石川河流经故城北部和中部。已做的工作涉及到城墙、城门、道路、城内的多处遗迹及城西北、东南和东北的墓地等。大多数遗存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只是在城址内出土的少量遗物及城东南墓地的部分墓葬,年代可以早到战国中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因此目前所了解的栎阳故城的形制、平面布局等, 都很难说就是秦都栎阳时的原貌。
(3)咸阳遗址
据文献记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 筑冀阙,秦徙都之”,秦统一后,仍以咸阳为都,并在渭水南岸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一直到二世亡秦(公元前206年),项羽“屠咸阳, 烧其宫室”(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在长达140多年的时间里, 咸阳作为秦战国中晚期和秦代的都城所在地,在诸秦都中以至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对咸阳城的考古工作始于50年代末,后经70年代到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陆续对渭水北岸和南岸做过较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现知咸阳故城遗址在今咸阳市东北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因渭水不断北移,使城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渭水北岸窑店乡牛羊村北塬上发掘了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宫殿遗址(注: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1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咸阳市文管会等:《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首次发现了秦的壁画。据推测这几座宫殿可能是当时“咸阳宫”的一部分,但尚不能说明其具体用途和性质(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三章·都邑》,三秦出版社,1994年。)。在咸阳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文,以及在部分地区调查所发现的遗迹现象,为探索城内手工业作坊区提供了线索(注:陈国英:《咸阳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5年3期。);在咸阳故城附近发现以及发掘的一些建筑遗址, 为研究城郊的离宫别馆提供了资料(注:尹盛平:《泾阳县秦都咸阳望夷宫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张海云:《芷阳遗址调查简报》,《文博》1985年3期;左忠诚等:《渭南发现秦大型宫殿遗址》,《陕西日报》1990年12月2日1版。)。不过由于咸阳故城被破坏严重,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工作,还不能为讨论咸阳城的范围、形制、平面布局、整体面貌等提供足够的资料。
(4)其他
除了对上述三个都城遗址所做的考古工作外,在其他一些地点发现的遗存为探索其他秦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陇县边家庄及其附近多次发现随葬有成套青铜礼器的春秋早期墓葬和春秋时期的城址(注: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5期。), 为秦都“汧”邑提供了线索,在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了秦武公时铸造的秦公镈、秦公钟(注:宝鸡市博物馆卢连成、宝鸡县文化馆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11期。),在其附近一公里左右的西高泉村发现了出有青铜礼器的春秋早期墓葬(注: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县图博馆:《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年9期。),此处很可能与秦都平阳有关。只是目前两处都还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资料,尚难以对其做出更明确的认定。
2.中小型墓葬与大型陵园
(1)中小型墓葬
对秦文化中小型墓葬所做的工作,一直是秦文化考古中的重要部分,对秦文化的界定、分期与编年等研究多是在对中小型墓葬中的随葬器物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目前普遍认为中小型墓葬为秦普通国人的墓葬。从30年代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鸡台“屈肢葬墓”开始,到现在已发掘的秦文化普通墓地有近50处,清理的中小型墓葬近千座,已经具备了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条件。
对秦文化中小型墓葬进行分期与年代的推定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工作。目前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组合与形制进行排比而确认的秦墓的逻辑发展序列,基本已达到共识。只是对于春秋早、中期的部分墓葬、秦统一后的部分墓葬的绝对年代,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注: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2期。)。
据目前对秦墓的研究,已知蜷屈厉害的屈肢葬、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洞室墓以及独具特点的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等,是秦墓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墓葬的典型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葬式,或认为“跽式葬应是秦国奴隶们的一种固定葬式”(注:韩伟:《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或认为“仿象‘鬼之所恶’的‘窋卧’,”以“防止鬼物侵扰”(注:王子今:《秦人屈肢葬仿象“窋卧”说》,《考古》1987年12期。);或认为“当出于某种灵魂托转的宗教信仰”(注: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考古》1992年8期。)。而笔者最近提出正是由于大多数秦墓的葬式为屈肢葬,所以其出现的直肢葬更应具有特殊的意义(注:滕铭予:《论秦墓中的直肢葬及相关问题》,《文物季刊》1997年1期。)。
秦墓中的洞室墓亦是秦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在50年代首次大批量发掘的半坡战国墓地90%以上为洞室墓,所以往往把洞室墓看成是秦墓中特有的墓葬形制,并多认为战国中晚期在关东诸国出现、以及汉代以后流行的洞室墓,均发端于秦(注: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笔者曾作《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一文,指出秦墓中的洞室墓是在战国中期后段出现的,其在关中地区的流向是由东向西的(注: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2期。)。
对关中秦墓中随葬器物的研究,有陈平作《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将秦墓中的青铜容器分春秋型秦铜容器群和战国型秦铜容器群,前者又分为三期七组,后者又分二期三组,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各群、期、组的总体面貌与文化特征,以及二群内各期组间的承继关系,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与年代提供了可比较的标准(注: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笔者所作《关中秦墓研究》,是从秦墓中出现的独具特点的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出发,通过对其形制所做的类型学分析,揭示出秦文化所具有的多元结构,以及秦文化在与外部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与之所发生的不同层次的关系(注: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
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和笔者《关中秦墓研究》二文中,都提出了依随葬器物种类的有无对秦墓进行分类的思想,并指出墓地中所存在的不同类别的墓,反映出使用墓的人群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后者还提出根据墓地所含墓葬类别的不同,将墓地分为不同的等级,并进而分析与墓地相关的居址的等级,而不同等级的墓地和居址,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亦不相同。
(2)大型陵园
大型陵园是秦国君的聚葬之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自襄公“始国”至二世亡秦,享国国君共三十二代,死后葬地有西垂、雍城、毕陌、芷阳和骊山等几大陵园(注: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目前经过考古工作可确认的有雍城、芷阳和秦始皇骊山陵园。
A.秦始皇陵园
秦大型陵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秦始皇陵园。据史籍记载,秦始皇陵园在嬴政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建,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入葬止,前后历时37年之久(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8期。)。50 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其进行过调查,70年代以兵马俑坑的发现为契机,开始了对其全面的、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临潼县文化馆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12期;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园陪葬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3 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7期;秦始皇陵考古队:《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简讯》,《文博》1987年1 期;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骊山飤宫”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6期。)。
秦始皇陵园位于临潼县东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北临渭河南岸, 包括了陵墓、地面礼制建筑、陵城和庞大的从葬区、陪葬区等,占地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陵城位于陵园西部,为南北长、东西窄、平面呈“回”字形的双重陵城。其中南部为秦始皇陵墓所在地,现地面尚存有高大的封土堆,陵城北部为礼制建筑和园寝建筑。另外在封土周围、内外城墙之间,还分布有马厩坑、铜车马坑和珍禽异兽坑等。在陵城外东部主要是从葬区和陪葬区,分别有兵马俑坑、马厩坑和陪葬墓区等。在有关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中,以兵马俑坑的发现与研究最为世人瞩目。目前的认识为兵马俑坑象征着秦始皇的御用军队,各俑坑为排列有序的、具有不同功用的队阵。由于兵马俑坑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包含了从葬制度、手工业技术、艺术、服饰、甚至人种学等方面,现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专注于兵马俑的研究,秦俑学亦已成为秦文化考古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B.雍城陵区
雍城秦公陵区位于雍城南郊雍岭一带,为秦都雍城时期的国君陵园,年代与雍城为都相始终,大体上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雍城秦公陵区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注: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焦南峰、田亚岐、 王保平:《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 对其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已探明其中包括13座分陵园,每座分陵园内由不同数目的大型墓葬和车马坑组成。大型墓葬的平面有中字形、甲字形、刀形三种,车马坑为凸字形和目字形两种。其中部分墓葬有墓上建筑。在整个陵区外部,每座分陵园和部分墓葬的周围,分别有用以区划的“兆沟”(注:陈伟:《凤翔、临潼秦陵濠沟作用试探》, 《考古》1995年1期。)。
陕西省考古所还对一号分陵园内的一号大墓进行了全面清理,该墓为有东西向墓道的中字形墓,椁室外积炭并填白膏泥,填土经夯打。墓室内有主、侧两个椁室,主椁室又分成前后二室。墓室上部有宽阔的生土二层台,埋殉人166个。地面有墓上建筑。该墓经后世近百次的盗掘,随葬器物已被破坏殆尽,由劫余的石磬所刻文字中有“天子匽喜龚

是嗣……”(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分析,该墓的墓主人应是秦共公、秦桓公的嗣君秦景公。由于被盗掘严重,仅据劫余资料,已不能了解该墓的详细情况。
C.芷阳陵区
芷阳陵区于80年代中后期发现,位于临潼县韩峪乡西南、骊山西麓的霸水右岸,是秦都咸阳后期的秦国君陵区,目前认为即文献中所记秦“东陵”(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勘查和钻探,已发现4座分陵园, 各分陵园周围都有人工或利用天然沟豁围起的“兆沟”。各分陵园内有数目不等的亚字形、中字形或甲字形大墓,以及陪葬坑、陪葬墓和地面建筑等(注:陕西省考古研究等:《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等:《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据推测这座陵区可能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包括昭襄王和唐太后、孝文王与华阳太后、庄襄王与帝太后以及悼太子的陵园(注:王学理等著:《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
秦都雍之前的秦公陵园,尚无明确地望,近年在甘肃礼县大堡子村发掘了三个车马坑和一座大墓(注: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后记》,《文物》1995年6期。),资料尚未发表, 但由最近流散海外的传出于这里的金饰片分析,此处很可能为秦立国之前、“邑秦”之时的秦仲或秦庄公的陵园(注: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后记》,《文物》1995年6期。)。
三
纵观秦文化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及现状,虽已取得很大成果,但若要使研究深入,则不仅需要考古学资料的进一步积累,更重要的还有赖于研究方法和解释理论的变革。笔者认为下述问题应是秦文化研究者引起注意并积极进行思考的课题。
1.关于秦文化的界定
目前对于东周时期秦文化的界定均以在雍城附近发现的中小型墓地为出发点。正如对殷墟的确认认定了殷墟文化一样,这种方法无疑是科学的,也是有效的,但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现已知一个遗址的等级越高,与其他外部文化发生交往的机会就越多,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就越复杂。殷墟是这样,西周的沣镐遗址是这样,雍城亦不能例外。因此通过雍城近郊墓地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并不一定是单纯的秦文化,亦不能笼统地将其全部视为秦文化的典型因素。因此对于秦文化的界定,还有必要对已知的东西做进一步的文化因素分析,以清楚哪些是秦文化传统的、典型的因素,哪些是在与外部文化发生交往时以某种方式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哪些是前者与后者融合后产生的新因素等。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具备进一步分析秦文化的谱系结构、文化源流等更高层次的问题。
2.关于秦文化的时空框架
秦文化的活动地域。自西周时期起,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大体是实现了一个自西向东的过程。在这个文化不断东移的表象之后,是秦文化在其所到之处,因当地文化传统、地理环境以及自身需要的不同,与原有文化间所发生的不同层面与层次的关系,或排斥、或吸收、或融合。因此秦文化的发展,会因其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面貌。所以建立秦文化的时空框架,就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单线、静态、封闭的系统,排列出单一的序列,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多元、动态、开放的系统,建立一个多空间、多线索的时空框架,以便研究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上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差别与关系。
3.关于秦文化与外部文化的关系
这种研究的实质不是去说明在秦文化发展过程中与哪些外部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而是要说明和解释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与外部文化发生不同层面与层次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往往只是指出秦文化曾与很多外部文化发生过关系,并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但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若能接受外部文化的影响,必定会有其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秦文化也不例外,其外部的原因是外部文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秦文化加以影响。这可以是文化载体的迁徙,或进入秦文化的活动区域,或因军事、经济、社会等原因与秦文化形成某种关系,如占领与被占领、贸易、联姻等。而作为秦文化内部的原因更应引起注意,即秦文化自身是以什么样的前提接受这些外部文化的影响,或是由于其自身的平衡机制失调,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或是由于二者在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生产技术等方面有相近之处等。而基于不同的内部原因所接受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对秦文化自身及其发展所起的作用亦不相同。
4.关于秦文化的层次结构
所谓层次结构,是指在考古学文化中由存在于不同层次上的遗存所形成的结构,如高台建筑和小型居址、大型陵园和中小型墓葬、青铜礼器和日用陶器等就可视为处于不同层次上的遗存。在秦文化的诸种考古学遗存中,以墓葬最能体现其层次结构,将墓葬划分为不同类别的实质,就在于划分秦文化的层次结构。不同类型的墓葬反映墓主人生前不同的社会身份或地位,因而文化的层次结构反映了该文化的人群处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之中。所以探讨秦文化的层次结构,是探索秦文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若能把对秦文化的层次结构的分析与文化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则可进一步考察秦文化中处于不同层次的人群,在秦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5.如何从考古学研究走向史学研究
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秦文化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所关注的重大课题,而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仍可归入广义史学研究的范畴之内。所以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最终仍需上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无疑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中,必然会有部分与史学研究的成果相吻合,或可对其做出部分的修正,但是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也必然会包含有史学研究以及文献记载中所无法解释或阙如的部分,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部分的存在,考古学才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必须也必然上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说明解释史学研究以及文献记载中难以解决、或未能解决、或不曾解决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走向更高的层次。
附记:本文是笔者在学习“先秦考古学”博士课程中所写学期论文,其间得到导师徐苹芳先生、张忠培先生的指导,志此以表谢意。
来源:《华夏考古》1998年第04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