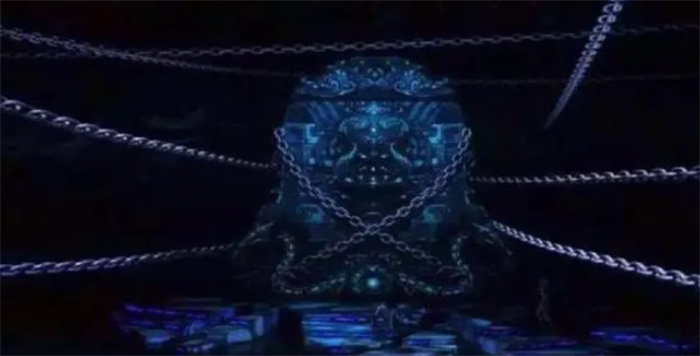王兴: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资料”是考古学①与历史学发生直接关系的连接点。关于考古学、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值得一提。“二重证据法”成为后世很多学者研究古史、古文献,或者探讨考古学、历史学之间关系的一种“典范”,甚至有学者指出它“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②。如果就实践层面而言,“二重证据法”如何运用?如何具体地用地下材料补充印证纸上材料,进而证明古书当中哪部分为实录,哪部分仅是一面之事实?一般认为,考古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是历史视角,但是历史视角如何具体应用到考古发掘的全部过程中,历史学的因素又如何影响其中?这也许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与文化情境泛泛而谈,而必须从特定时代及思想语境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夏鼐的早期学术经历,探讨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特别是二者在具体研究的实施层面的关系。从《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日记》)中涉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材料入手,并参以其他相关材料,可以考察夏鼐对考古学认识态度的转变,进而分析考古学在当时学界的地位、历史学者对考古学的认知与期待、这种认知与期待是否恰当等问题。近代学科分化日益明显,若将考古学的发展置于历史学乃至民国学术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互动关系,以及考古学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一、夏鼐自身的学术经历及其对考古学在学界地位之认识
(一)从考取留美生到安阳实习期间:“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
1930年夏鼐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1年下半年他转学至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4年5月,夏鼐阅报得知“清华今年留美生有历史2名,即美国史及考古学,详章未公布”③。在他的初步认识中,留美考试中“考古学”是“历史”的一个专业方向。然而他的这种认识与后来公布的招考信息有所“出入”,第二届留美考试“名额仍定二十五名,共二十一学门,计历史(注重美国史)一名、考古学一名……”④也就是说“历史”与“考古学”同为留美考试中的“学门”。
1934年10月,夏鼐考取留美生后,曾写信给好友刘古谛,信中提及他由燕大社会学系转入清华历史学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但是他“对于十字街头”仍然“有些恋恋不舍”。当他转入历史学系不久,曾阅读《史记·六国年表》,并参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加以校注,由此产生自我反省,“替自己恐慌,恐怕因此跌入故纸堆中翻不得身,成了一个落伍者。不过念历史的人又不能绝古书而不读,此种矛盾不知该怎样解决才好。”⑤也许后来夏鼐攻读中国近代史,正是解决这种矛盾的一种途径,由此“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夏鼐选择清华历史学系,“固出于追求学问的欲望,却也未失掉求解社会问题的初衷”。⑥如果就“剖析当前的社会”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夏鼐也曾认为自己要“以史学为终身事业”⑦。但是突然改学考古学,简直就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这样“离十字街头更远了”,也就难以达到他“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的目标。
本来预备学的是中国近世史,但是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他“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他并“没有预料到”。他曾和吴晗谈及此事。吴晗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了,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⑧当留美考试结束但录取结果未公布时,夏鼐曾假设自己如果考中,以后他的“生命史将翻过一页,眼前展开的是一条完全未曾践过的新路”⑨。
夏鼐最初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专业方向。而从他考取留美生后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和友人的交谈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他们都在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区别,这种区别“实在太大了”。在他们看来,学习历史学,还是学习考古学,日后的人生事业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与当时及后来很多学人强调历史学与考古学之间存在着的紧密关系又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随着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逐渐深入,他仍在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区别,但也会就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按照规定,夏鼐出国前需在国内预备并实习一年。1935年春,他到安阳参加殷墟发掘。在此之前,他向傅斯年、李济等人多次请教。李济曾对他说“田野工作,非有强健之体格不可”⑩。实习期间,李济到殷墟发掘现场视察时,问他“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他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苦笑而已”,认为“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因此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11)。此处“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很大程度上提示出夏鼐当时的心态。至少从考取留美生到安阳实习期间,他都认为考古学在当时只是“第二三流事业”,凭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在其中做“第二三流人物”。夏鼐当时认为自己“不适宜于田野工作”就主要源于此种心态,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中的“第一流”学问是什么,是历史学还是其他学科?从《日记》的相关记载来看,夏鼐心中的“第一流”学问或许是那些对现实社会有更大和更直接影响的学科,这也能解释为何他最初选择社会学这一专业。
实习快结束之时,夏鼐“觉得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如能得一新证据,有时可以与旧材料一对证,发现新见解,将整个的旧材料由死的变成活的”。(12)1929年,负责殷墟首次发掘的董作宾曾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以“科学方法发掘之”(13)为特色。董作宾未受过近代考古学的系统训练,他的看法只是在安阳发掘初期他个人表现出的局限,并不代表后来主持安阳发掘的考古学者李济、梁思永的看法。李济后来就不同意董作宾的此种观点,他认为“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14)。考古新人夏鼐仅在几个月的实习之后便有同感,说明他的眼光还是非常敏锐的。当然,夏鼐所说的“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并非专指安阳的发掘,因为当时除史语所的安阳发掘外,尚有北大等一些单位也在从事小规模发掘,而其主持多非经考古专业训练者,故夏鼐有此看法。他对“科学式发掘方法”的强调,也是对“科学的考古学”的强调,他的这些看法显然与董作宾等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夏鼐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可以看出,专业方向从社会学转入历史学、再从历史学转入考古学,都并非完全符合夏鼐本人的意愿。然而转入新的专业后,夏鼐都会主动思考新专业的学科特点、不同专业之间的区别以及他自己如何适应新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尽管在并未完全弄清留美考试中历史学和考古学关系的情况下,便考取了留美考试的考古学专业,他还是认定考古学是“二三流事业”。夏鼐虽然对投身考古学的选择仍持犹豫态度,但是在经历了安阳考古实习之后,他开始初步认识到“科学的考古学”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学所不具备的、考古学自身的独到价值。
(二)留学期间:“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
1935年8月7日夏鼐离开上海,乘邮船赴英国留学。(15)9月,夏鼐初抵伦敦后,首先困扰他的是入学问题。10月,夏鼐在伦敦大学考陶尔德研究所注册,师从叶慈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但是没过多久,夏鼐觉得在英国学习该专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1936年4月,他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详细陈述自己准备改学埃及考古学以及申请延长留学年限的缘由。比之于“史前考古学”,“有史以后之考古学”对掌握文献的能力要求更高,困难也就更多,夏鼐因而准备“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考古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并且“由古物以证古史”,这些是“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的方法。若参以“具体之实物及实例”,才能领悟这些方法。想要达到这些目的,又“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表明掌握历史、宗教、文字等知识对于从事考古事业的重要性。(16)
上文提到,夏鼐于安阳实习快结束之时,惋惜当时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这恰与他留学期间希望“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想法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考古活动之后,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进行,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十分提倡及重视在考古发掘中运用科学方法,并且在夏鼐之前,李济和梁思永已经完成了中国考古学从金石学转为近代考古学的基本建设过程。(17)然而,不同学者心中所谓的“科学的考古学”的标准会有所不同。(18)在夏鼐看来,当时兴起及被时人所实践的考古学,是否符合“科学的考古学”的标准尚需考虑。当然,夏鼐眼中的“科学的考古学”的标准,也会随着他认识的深入而变化。
改学埃及考古学后,夏鼐除了学习埃及象形文字以及修读相关课程外,也非常重视田野考古实习。与此同时,他也常从阅读中获得感悟和认知。1936年7月,他读了博厄斯《原始人的心理》和戈登威泽《早期文明》后,在7月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读这两本书的感受,涉及人类学知识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考古学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考古学的前途等问题。夏鼐此处提及的“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其中的“实证”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在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因创立史语所而开创一种史学科学化的“新史学之路”,“实证史学”在当时形成“思潮”,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及考证进而对历史加以解释是“实证史学”的基本特征。(19)而考古学给学者提供的材料,也可以通过“实证”达到解释历史的目的。关于“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这一点,可以与夏鼐曾认为考古学只是“第二三流事业”的看法相对照,不过此时他似乎并不悲观,不再觉得自己将成为“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而是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旧的中国上古史体系被“打破”,很多学者期待考古学能为重建中国可信上古史提供有力的材料。1924年李玄伯(宗侗)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中言道,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20)支持顾颉刚疑古一派的傅斯年后来转向古史重建时也受李玄伯观点的影响,认为“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21)。夏鼐在清华读书时,读过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比较二书之后,认为“地下材料未能充分发现以前,新派史学对于殷周以前之史迹,亦只得搁笔”(22)。虽然在夏鼐看来新的传说不能令人满足,但是假如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形稍为安定,那么考古学的工作大有可为。此条日记是夏鼐“书此以自勉”(23),也可看出他想在考古学领域有所作为的自我期待。
1936年暑期,夏鼐随惠勒于多切斯特附近的梅登堡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实习结束回到伦敦后,9月14日,他和吴金鼎讨论目前国内考古现状,指出“中研院考古组开始时,即有计划,惟非考古计划,不过欲掘有字甲骨而已”。事实上,从1928年10月到1932年12月的七次安阳发掘中,小屯被选为工作中心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曾出土过有字甲骨。(24)对于亲历殷墟发掘且已接受一些近代考古学专门训练的夏鼐而言,他切身体会到国内考古观念及技术、方法的落后,也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中国考古学需要在科学方法上加以提高的重要性。
1941年1月,夏鼐返回祖国。2月3日抵达昆明。2月21日,夏鼐应罗常培之邀,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讲演“考古学方法论”。此次讲演是夏鼐回国后的第一次学术“亮相”,他对此极为重视。讲演内容涉及田野考古学方法、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关系、国内考古学现状及发展方向等诸多重要问题。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关系,夏鼐认为:
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史学家有专写有新得之论文或专著者,亦有喜写广博之通史者。普通考古学家,认为撰述田野工作报告及专门论文,已为尽责。但亦有进一步而作综合工作者。根据现所已知关于某一时代之遗迹古物,重造当时文化之概况……今日吾国考古学之材料,仍极贫乏,作此项综合工作者,更须谨慎。将来材料累积至相当程度后,则此项工作,亦不可少,以考古学及历史学之最终目的,即在重行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瞭人类之过去生活也。(25)
夏鼐已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的表现;他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相同,“即在重行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人明白人类过去生活状况。此外,在夏鼐眼里,皮特里发掘塔尼斯遗址时,对考古发掘方法大加改进,“谨慎周密,堪称为科学的发掘方法”。(26)
很显然,出国留学后,夏鼐逐渐改变了先前考古学是“二三流”学问的看法,转而认定“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此种看法又与当时一些学人致力于古史重建的努力有关。到改学埃及考古学之后,夏鼐已确定了以考古学为人生事业的目标,并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工作大有可为。与此同时,夏鼐对国内考古学界情形、学人史料观念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整体表现出一种“不满”态度。这种不满,又主要基于他对“科学的考古学”的强调。夏鼐在“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中,给予皮特里考古发掘方法很高的评价,而他在讲演中关于田野考古学方法、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认识,又为他日后的考古实践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史前考古学与中国史前史研究
1950年以前,夏鼐在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成就。
(一)年代的考订
1944年春,夏鼐在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历时两年。1945年4—5月,他在甘肃洮河流域考察,发现并发掘了两座齐家文化墓葬,后撰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为修订齐家文化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证据。
1924年,安特生发现了齐家文化居住遗址,但并没有找到齐家文化期的墓葬。1943年,安特生发表了关于齐家文化居住遗址发掘的详细报告,但是因为没有墓葬方面的材料,并未深入阐明齐家文化的性质。关于齐家文化年代的问题,安特生认为齐家文化较早于甘肃仰韶文化。梁思永曾认可安特生关于甘肃史前分期的观点,但夏鼐对此“表示不满”(27)。
1945年4月,夏鼐初步考察辛店遗址时,发现辛店B遗址有灰层,并“检得半山及辛店期彩陶片,以前者为多”;而“辛店C为齐家文化,无彩陶”(28)。等到挖掘辛店C遗址时,夏鼐进一步判断是“一齐家文化遗址”;而对比辛店B仰韶遗址,在“地面发现一带柳条纹之灰陶,似属齐家文化(齐家文化虽多红陶,亦间有灰陶)”,这种现象“暗示齐家晚于仰韶(半山)”(29)。随后,夏鼐在发掘齐家文化期墓葬过程中记下了“初步分析之结果”,认为“甘肃仰韶与马厂,似属一期,今名之为半山马厂期”,甘肃仰韶“似较齐家为早”,并列举出地层、陶器形式等方面的证据。(30)夏鼐又在“1号墓内填土发现彩陶二片,齐家期之较后,更得一证明矣”(31)。考察结束后,夏鼐回到南京,关于西北史前文化的问题,也引起梁思永、李济等人的关注。梁思永曾问夏鼐“西北史前文化除安氏所已发见者外,是否另有他种文化”,夏鼐虽然“对此亦颇注意,但当时并未曾发现新的古代文化”(32)。李济也和夏鼐讨论过“安特生氏之中国史前修正年代问题”(33)。1948年5月,夏鼐发表了此次发掘的正式报告,“新发现的结果,不仅对于齐家文化时代的埋葬风俗及人种特征方面,供给新材料;并且意外的又供给地层上的证据,使我们能确定这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二者年代先后的关系”。(34)
在齐家文化期的墓葬中,除了殉葬品外,有两片带黑色花纹的彩陶碎片,夏鼐判断“就陶质及花纹而论,皆与标准型的仰韶文化彩陶无异”,而墓葬中发现的殉葬陶罐“皆属于标准型的齐家文化陶器”。对于安特生判断的齐家文化较早于甘肃仰韶文化,尹达等人提出过疑问,但因为没有可靠的地层上的证据而无法纠正安特生的判断。夏鼐认为这次“发掘所得的地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根据这个新证据,“安特生也许可以同样地承受齐家文化相对年代的修改”。但是关于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夏鼐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仍无法确定,他以为如果“将齐家和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加以修改,互相倒转”,之前安特生等人关于齐家文化绝对年代的估计等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35)。
刘燿认为,安特生对于仰韶村和齐家坪两遗址的认识,实为当时的材料所局限,他如果能将这两遗址重新作一次相当的发掘,这许多问题才会获得最真实最可靠的解决,“新事实的发现往往可以补充或纠正过去的人们对于一种事物的认识”,这是“科学进步的常识,考古学亦自不能例外”(36)。夏鼐在洮河流域的发掘可以说是幸运的,他发现的齐家文化墓葬,为解决安特生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夏鼐对齐家文化年代的修订,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37)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后来考古发现的支持与验证。
除了判定齐家文化的年代之外,夏鼐通过对寺洼山遗址发掘、研究,也分析了寺洼文化的年代。他后来发表了《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关于寺洼文化的年代,“只能大略的断定它是晚于马家窑期彩陶文化,早于历史上的汉朝”。和分析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一样,夏鼐判定寺洼文化的绝对年代时,也“因为证据不够,更难断定”(38)。
夏鼐曾说,“排定古物之先后,仅能知其相对年代,而不能知其绝对年代”。(39)由以上论述可知,就当时的考古技术水平而言,考古发现的地层证据以及出土物等材料仅能判断史前文化的相对年代,我们由此知道史前各文化的时代先后,甚至了解人类演进的情形。不过,要想解决绝对年代的问题,有时考古学家也会束手无策,大部分情况下仅能估计史前各文化的绝对年代。绝对年代问题的解决,要等到后来碳-14测定年代法的发明及使用。
(二)考古学与原始民俗
夏鼐发掘寺洼山遗址时,认为当地“火葬之举,似足证其非汉人之风俗”(40),寺洼文化与辛店文化“二者之民族,似皆非汉族,以其葬俗之特殊也”(41)。他在考察寺洼期的葬俗问题时,就安特生、裴文中之前的研究以及当地人的描述,提出了两个问题:“(1)是否没有殉葬品的平放仰卧的尸体是属于另一文化的墓葬?(2)有殉葬品的墓葬,是否原来都乱骨一堆?”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夏鼐觉得“先要对于原始民族处置尸体的风俗说明一下”,因为此次发掘的范围过小,他“不敢十分肯定的说这些是由于‘二次埋葬制’的缘故”,但大体上分析,寺洼文化有三种葬俗同时存在,即“二次埋葬制”、全尸仰卧平放葬、火葬。夏鼐引用美国人类学家克劳伯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克劳伯认为“在一部落中某一种处置尸体的葬俗常限于某一社会阶级,但一个部落中可以有好几个同时存在的葬俗”。夏鼐以为“火葬制在寺洼出现,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氐羌中有些部落确曾行过火葬制的。这次火葬制遗迹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他通过考察寺洼期的葬俗,不仅分析了洮河流域的一些原始民俗,更指出了寺洼文化与后来氐羌民族可能存在的关系。至于寺洼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关系,“只能在陶鼎陶鬲上推知他可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42)
李济、高去寻在研究葬式问题时,都将葬俗与民族关系联系起来。(43)夏鼐对寺洼期葬俗的研究也是如此,由葬式本身的研究扩展到原始民俗的研究,进而考察这种风俗与氐羌民族的关系。
大体而言,民国时期学术界所理解的史前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在具体研究层面上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首先,在对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社会的研究中,考古学材料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对很多重要问题的解决,考古学材料都有发言权。其次,时间的变化构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要因素,在考订史前文化的相对年代方面,史前考古学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史前考古学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变化的基本问题(如史前文化的相对年代),也关注民族关系、社会风俗等更为宏大的问题,进而探索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
三、历史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研究
进入“历史时期”,因文字的存在,考古研究便需要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以及运用文献的考据功夫。通过夏鼐的学术实践,我们还可以考察“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发生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
(一)文献阅读与考古发掘
1941年7—11月,夏鼐与吴金鼎等人在四川彭县等地调查古迹,并发掘了王家沱、豆牙房沟等处的汉代崖墓。从是年4月开始,夏鼐便开始阅读《华阳国志》、《四川郡县志》等书,根据所阅书籍作“汉代益州郡县图”、描摹宜宾至李庄地图。他还阅读了一些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南地区的考察报告或研究论文,如托马斯·托兰斯《中国四川的埋葬习俗》、谭锡畴《四川地质发展史》等,为后续发掘崖墓作了充分的文献准备工作。在发掘期间,夏鼐还阅读了两汉书。
1944-1945年,夏鼐在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及发掘。出发之前他就开始阅读《肃州志》、《甘肃通志》等书,并描摹敦煌一带地图;同时他还阅读了比林·阿尔提《齐家坪》、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等研究性文章以及徐旭生《西行日记》、向达《西征小记》等考古日记。在考古调查期间,夏鼐还翻阅《史记·大宛传》等并作札记,也阅读了《汉书》的相关列传。1945年10月16日,夏鼐与阎文儒在武威南山发掘出金城县主及慕容曦光二志,10月20日夏鼐便到当地文献委员会借阅《新唐书·吐谷浑传》,后来又“参考‘两唐书’及《通鉴》,预备为墓志作跋也”(44)。夏鼐之后回南京撰写文章时,又“阅《册府元龟·外臣部》,为吐谷浑慕容氏墓志搜集材料也”(45)。
从夏鼐这两次的考古经历来看,在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以及考古发掘阶段,他所读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地方志;相关研究著作或考古日记。前两种书籍主要为考古发掘者提供基本史料,使他们了解发掘地的相关背景性知识,甚至可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地方性经验”;第三种主要使考古学者掌握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而在后续的发掘、研究中发现并解决相关问题。在历史时期,阅读文献可以促进考古学工作的有效展开,这样的研究方法至少在客观上又进一步拉近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二)古代遗址的考证
1944年冬,夏鼐与阎文儒考察两关遗址并掘得汉简数十片,其中一简有“酒泉玉门都尉护众”等字,涉及玉门关初设置时的地点问题。1945年初夏鼐致信傅斯年、李济时,提到他“根据未发表之史料,亦颇有新意见,有暇当作一‘两关问题的新史料’以求正于当世之贤者”(46)。在夏鼐看来,掘得的汉简是解决两关遗址问题的“新史料”,夏鼐于1947年撰成《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47)一文,论证了玉门关初设置时的地点。
自从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发现玉门都尉诸版籍后,其地即为汉代的玉门关,已成定论。但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以前的玉门关是否也在小方盘,尚成问题。沙畹根据《史记·大宛传》的内容,认为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敦煌西北的玉门关是后来迁移过去的。王国维《流沙坠简·序》、劳榦《两关遗址考》中也基本赞同这种说法。(48)然而夏鼐觉得如果用常识来推测,汉代既将敦煌收入版图,纵使暂时附属于酒泉郡,不另设郡,但是汉朝如果想设置边境极西的重要关隘,自然不必在敦煌以东,而应在敦煌以西,否则无法稽查出入。有“酒泉玉门都尉护众”等字的汉简一出,为验证夏鼐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夏鼐又参以《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等文献材料,认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便是太初以后的玉门关,也就是敦煌以西的小方盘。
大约十年后,郑振铎对夏鼐能找到玉门关旧址仍感到“奇怪”。其实这并不奇怪,夏鼐在发掘前就对玉门关作了详细的考证,再加上他有考察古文化遗址的田野工作经验,所以玉门关旧址幸运地被他发现了。(49)换句话说,如果夏鼐在发掘前未对玉门关做相关功课,可能找到旧址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小。
(三)考古学补“正史”之阙失
1944年,夏鼐在西北进行考古调查,“虽以发掘工作为主,而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50),他于武威文庙获观近年出土的吐谷浑慕容氏志石四方;次年秋天,他与阎文儒赴武威南山发掘,得金城县主及慕容曦光二志。
夏鼐根据看到的墓志材料,认为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阙失。具体表现为:第一,“史传仅谓县主为唐宗室女,据《志》知其裔出懿祖光皇帝,为唐太宗之再从堂妹,可以备史之阙”;第二,“《志》中详叙世系,可补《新唐书·宗族世系表》”;第三,“《志》中之交州大都会稽郡王道恩,《宗族世系表》失载,此可补其脱漏”;第四,“慕容明墓志中神龙二年授左屯卫翊府左郎将,景云二年三月授左屯卫将军,亦皆作屯卫,足以补正《旧唐书·职官志》等之阙误”;第五,“慕容曦光躬预其役,曾立战功。惟以位在偏裨,史书失载,其名字遂湮没无闻。今此《志》出土,足以补史之阙”等。墓志材料在补充史书记载之阙失的同时,文献材料有时候也可以证明墓志材料中的错误,如:虽然《志》可补《新唐书·宗族世系表》,但是“《志》亦有误;考史须参稽各种史料,加以抉择,不能专以碑志为正也”;由《志》可知,永徽三年(652年)四月,乃许嫁制昭之颁发年月,当时金城县主仅10岁,慕容忠仅5岁,到了出嫁时金城县主已22岁,当在麟德元年(664年),而“《志》误合为一事,谓永徽三年出嫁,春秋二十有二,以致前后自相牴牾”等。(51)历史考古学须尊重相关文献的记载以及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不能用考古学上的“孤证”轻易否定文献记载的史实,也不能仅靠考古学的“发现”做出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在将墓志材料与史籍综合考证的基础上,夏鼐还编写了贞观十三年(638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吐谷浑失国前后的史事年表,这为后人了解吐谷浑的相关史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上文提到,夏鼐留学期间多次强调“文籍与古物互证”、“由古物以证古史”的研究方法。将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与相关史籍对照,补充史书记载之阙失,正是他对留学期间所认识的考古学方法的具体实践。
(四)考古学与历史文化
1944年夏鼐在敦煌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时,对敦煌的历史、地理也尤为重视,并希望通过考古发掘最大限度地还原敦煌的历史。
夏鼐在敦煌发掘的墓葬,可以分成两群:早期的一群,约在东汉晚年到晋朝,有些晚到南北朝;另一群是唐朝的墓葬。夏鼐认为“敦煌有它的特殊情形,例如墓葬所在的地层的土质,当地可以利用的各种原料,以及当时边区的风俗习惯”,如果将敦煌的墓葬和别处一时代的墓葬相比较,会发现很多方面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可以说“东汉至唐末时代的敦煌文化,已经完全成为中原文化的一支了”(52)。
夏鼐通过对敦煌墓葬的发掘、研究,用“地下的材料”充实敦煌的历史,由此了解当时敦煌文化的发展程度,并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得出东汉至唐末时代的敦煌文化已是中原文化的一支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材料的互证,而是体现出更为宏观的相互作用。通过考古发掘,由墓葬了解历史,由历史了解文化,考古发掘的意义便上升到文化、精神等比较抽象的层面上。
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筹备展览,夏鼐观后写了《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一文。(53)他从考古学的观点谈到了敦煌千佛洞的历史,基于之前在敦煌的考古发掘,夏鼐此处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了考古学与敦煌千佛洞历史及其背后文化的关系。
在历史时期,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在具体研究的实施层面上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文献的阅读是历史考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由于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有着对方所不具备的各自的优势,即使有新的考古学材料发现,文献材料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如果将历史考古学研究工作分为前期文献阅读、现场的调查及发掘、材料的整理、调查报告及研究性文章的撰写四个阶段,那么一旦考古现场的发掘工作结束,考古学性质的主要工作在实际操作层面便已结束,剩余需要处理的工作恐怕必须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所共同面对才可能更好地得以解决。第三,历史学与考古学都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只是这些资料的表现形式不同,将两方面资料相互印证,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双方材料的价值。
综上所述,夏鼐在考取留美生初期、安阳实习期间、留学期间,对考古学在学界地位、考古学发展前途及自身价值等问题有不同认识。这跟他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不无关系,也跟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以及其他学者的影响有关。从夏鼐的思想发展与学术经历中,我们可以将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在具体研究的实施层面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对于“史前”和“历史”时期的研究,考古学材料的使用比重不同。在史前史研究方面,考古学材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历史时期研究方面,虽然考古学材料有时很有说服力,但是文献材料还是占主要地位的,因为如果脱离了历史文献材料,很多考古材料的价值便无从谈起。
第二,在历史考古学方面,“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的研究方法起着重要的作用。“史前”与“历史”的界限在于文字的产生,因此“文字”之于“历史”就有重要的意义,而文字和历史的内容本身又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夏鼐留学期间,曾劝曾昭燏“专从事于‘文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54)。“文籍”与“古物”相互印证,可应用于古代遗址的考证、补充“正史”之阙失等方面。
第三,史学方法、治史精神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不管是史前考古学方面,还是历史考古学方面。比如考订史前年代时,虽无文献材料可征引,但是历史学考证的方法却无处不在。即使是应用相关的科学技术解决史前考古学的年代等问题时,严谨、客观的作法仍不可缺少。
第四,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还原、认知古代社会。剖析古代社会,也许是夏鼐的考古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1941年,他在“考古学方法论”讲演中就明确指出“以考古学及历史学之最终目的,即在重行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瞭人类之过去生活也”。夏鼐曾说:“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情况。”(55)甚至认为除了文籍上的考据以外,只有用考古学的方法,才能恢复敦煌地区“已经丧掉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6)复原历史是考古学的最终目的,但历史不仅仅是一批遗物,还包括人类生存的环境。马克思曾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7)诚然,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古代遗迹、遗物,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乃至思想文化都有重要的作用。比起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更加直观、更加具有原始面貌,不仅可以补正文献之阙失,还可以增加人们对古史甚至古代社会的认识。此处所指的古代社会,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文化思想的。考古学非常重视考古材料背后的“人文”信息,通过考古学考察史前年代、古代遗址等,都算是一种基础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上升到对古代社会文化的了解。夏鼐先对寺洼山墓葬的葬俗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思考当地的丧葬仪式、宗教信仰等抽象问题;他通过对敦煌地区墓葬的发掘,由此了解当地的历史及文化。考古学与历史学同属于人文学科,二者探究古代社会面貌的共同目标,也可以算是人文学科学者的共同“情怀”。
夏鼐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同1950-1985年间中国的考古事业紧紧连在一起”,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丰碑”(58)。所以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有益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界的整体状况。同时有助于促进对于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思考。
①本文涉及的考古学,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安特生的考古工作为起点并逐渐兴起的重视田野发掘、运用地层学及类型学等方法的“近代中国考古学”。
②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③《夏鼐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卷一,1934年5月15日,第239页。
④《第二届留美公费生考试消息》,《清华暑期周刊》第5期,1934年8月13日。
⑤《日记》卷一,1931年12月25日,第86页。
⑥戴海斌:《清华园里的夏鼐与吴晗》,《读书》2015年第3期。
⑦《日记》卷一,1932年12月27日,第141页。
⑧《日记》卷一,1934年10月2日,第264页。
⑨《日记》卷一,1934年9月26日,第263页。
⑩《日记》卷一,1935年1月4日,第285页。
(11)《日记》卷一,1935年5月8日,第320页。
(12)《日记》卷一,1935年5月31日,第328页。
(13)董作宾提到“甲骨既尚有遗留,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并列举“计划发掘之法”有分区、平起、遞填,见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1929年12月。
(14)李济:《安阳》,《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
(15)按:夏鼐考取“留美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到美国留学。在选择国外学校、导师方面,李济、梁思永都给予夏鼐切实指导,并且在李济的帮助下,夏鼐将赴美留学改为赴英。
(16)此信写于1936年4月11日,并全文附于次日日记之后。在《日记》正式出版之前,王世民将此信整理并注解,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7)实际上,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胡适等人对夏鼐的早期学术成长也产生了影响,此点拟另文探讨。
(18)比如1926年李济主持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梁思永就认为它从“科学观点上”确可以说使中国考古学“至少有一次精密的发掘了”(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而夏鼐后来的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的看法便与此不同。
(19)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第7期。
(20)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
(21)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上海)第1期,1930年12月。
(22)《日记》卷一,1934年7月25日,第250页。
(23)《日记》卷二,1936年7月5日,第53页。
(24)李济在总结安阳前七次发掘时提到“安阳发掘虽不以殷墟为限,然而这些次的活动却专重殷墟,事实上并以出甲骨文字之小屯为工作的中心”,见李济《编后语》,《安阳发掘报告》第4册,1933年6月。
(25)《考古学方法论》,《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26)《考古学方法论》,《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27)《日记》卷二,1937年1月30日,第91页。
(28)《日记》卷三,1945年4月6日,第304页。
(29)《日记》卷三,1945年4月11日,第306—307页。
(30)《日记》卷三,1945年4月30日,第321—322页。
(31)《日记》卷三,1945年5月13日,第329页。
(32)《日记》卷四,1946年3月2日,第28页。
(33)《日记》卷四,1946年4月21日,第118页。按:李济也曾就安特生关于甘肃仰韶文化的标年提出过疑问,参见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1930年12月。
(34)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1948年5月。
(35)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
(36)刘燿(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3月。
(37)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38)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4期,1949年12月。
(39)《考古学方法论》,《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
(40)《日记》卷三,1945年4月26日,第319页。
(41)《日记》卷三,1945年4月30日,第321页。
(4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4期,1949年12月。
(43)参见李济《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3册,1931年6月)、高去寻《黄河下游的屈肢葬问题》(《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3月)。
(44)《日记》卷三,1945年10月23日,第410页。
(45)《日记》卷四,1947年12月3日,第159页。
(46)《夏鼐致傅斯年、李济函》(1935年1月23日),《史语所档案》:李38—5—7。
(47)载1947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南京)。
(4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7年7月。
(49)参见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50)夏鼐:《陇右金石录补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51)参见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6月。
(52)参见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3)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
(54)《曾昭燏致傅斯年函》(1936年6月19日),《傅斯年档案》Ⅱ:460。
(55)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58)高炜:《继承夏鼐先生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 0002
- 0000
- 0000
- 0000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