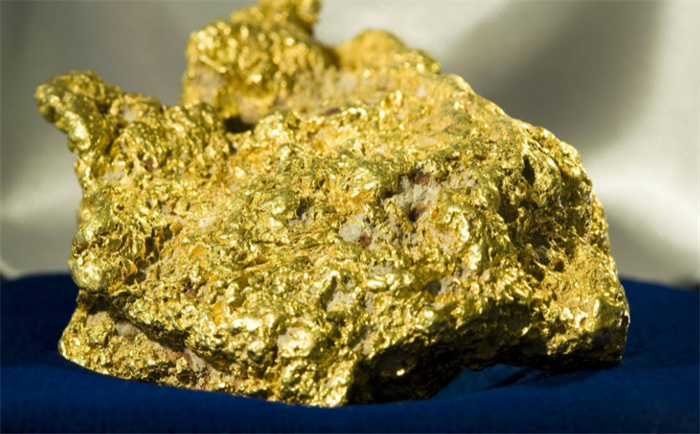周大鸣: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
“民族考古学”,自80年代开始在我国的讨论多起来。众多学者对民族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定义、内容、方法、理论、范围及发展史都已做过论证(注:容观琼:《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中南民族学院》1984年第3期;容观琼:《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张寿祺:《论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兼及对西方哲学“整体论”的分析和批判》,《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民族学和考古学两门学科历史的回顾,叙述早期的民族考古活动,论证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由此可见西方学科进入中国后本土化的过程,亦可见人类学对考古学影响的过程。
一.中国近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形成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在西方它们成为独立的学科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我国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形成,都是在本世纪“五四”运动前后。
所谓近代考古学,是指考古工作者通过地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去发现文化遗迹,加以整理,并据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在西方(欧洲、北非、西亚)是1840~1870年,19世纪末30年代是成熟期(注: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美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则稍晚些。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是与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是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而来的(注: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人类的考古活动很早就开始了。在古代中国,古物在统治者手中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政治意义,私人也竞相收藏古物,作为古玩。宋代形成的“金石学”到清乾嘉时期大大发展,其重在器物收集、文字考据,目的欲在鉴赏。也有不少著述,如梁代顾煊的《钱谱》,唐代徐浩的《古迹记》,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欧阳修的《集古录》等等。中国古代的学者,为了著述的需要也研究古物,访寻古迹。如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除引用丰富的史传、碑志之外,还亲自考明了许多古城、古迹的沿革。司马迁著《史记》也访问了许多史迹(注: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这些可以说是考古学的萌芽。
到晚清初期有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字”,他们利用甲骨、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等,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中国近代考古学批判地继承他们的成果。
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的考古学已经开始渗透到中国,但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来的。英、德、俄、法、日等国纷纷派遣探险队到***和甘肃西部、东北、内蒙古进行探险工作,这些探险队常常以考古为名,掠夺古物,也做了些考古调查和发掘,如敦煌、楼兰、居延等地的考古发现(注:荆三林:《考古学通论》,第二篇《考古学史的发展》,郑州大学讲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以后国内学者把历史、民族、考古相结合的边政研究。
历史学也是考古学的重要来源。如五四运动后兴起的古史辩派,吸取了西洋史籍考订法和史事考据法。顾颉刚先生意识到要建立新的史学,必须依靠民俗学(包括民族学)和地下考古的发现(注:顾颉刚:《古史辩》,朴社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先秦诸子(包括儒学)和两汉经师所制造出来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因为经受不住史证,而被怀疑、抛弃。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1922年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研究室,1923年成立古迹古物调查会,并开始了对仰韶遗址(1921年)、甘肃洮河流域史前遗址(1923~1924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1921年)、殷墟(1929年)等考古学文化的调查和发掘。
民族学知识的萌芽,同样可以上溯到很远的时代。我国《史记》不仅记载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各民族状况,还包括东亚许多民族的资料。另外还有《诗经》、《楚辞》、《山海经》、《蛮书》、《百夷传》等以及大量的杂史、地方志。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民族共同体间的差别。史书上记载的民族已多达“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但古人不能合理地解释这种差异。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于民族起源的,如纳西族的长篇叙事诗《创世纪》就描述同一个母亲生下了藏族、纳西族、白族三个民族的祖先。
我国近代民族学的兴起时间与考古学大致相同,是本世纪初开始的,也就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兴起的。但直到1926年,蔡元培先生发表《论民族学》一文提出“民族学”的名称(注:蔡元培:《论民族学》,《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1927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主要活动是广西凌云瑶族调查(1928年)、台湾高山族调查及研究(1929年)、东北赫哲族调查(1930年)、湖南西部苗族调查(1933年)(注: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1集,民族出版社1981年。)、云南彝族调查(1928年,中山大学)(注:周大鸣:《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早期民族学的形成,一方面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丰富的材料。蔡元培先生指出,民族学不但要继承古籍中丰富的材料,同时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早期民族学研究调查中已注意到民族学的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的关联。
二.中国早期民族考古活动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但它们成为独立的学科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而我国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形成,是本世纪“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两门学科形成后,在平行发展中出现了交叉,在接触点上产生相互作用。而这两门学科中的相互作用,我们称之为“民族考古”。早期民族学活动可以分为两类:
1.考古学印证民族学的问题
在我国追溯早期人文科学的学术史,往往会提到王国维先生。王国维(1877~1927年)是我国近代大学者,开创了许多学科的学术潮流。王国维先生是最早开考古证民族史之先河。如他在《匈奴相邦印跋》一文中,从匈奴相邦玉印考证“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玺,当是战国讫秦汉之物”,又谓“此印年代较古,又为匈奴自造,文字并同先秦”,这些结论为后来考古发掘所证明(注:林斡:《王国维对匈奴史的研究》,余大钧:《论王国维对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这种以“考古证民族史”的方法多为后来历史考据学家仿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古代民族的形成来源上。如对北方民族史的考证(注:孟世杰:《戎狄蛮夷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胡君泊:《匈奴源流考》,《西北研究》1933年第8期;董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1942年第2期;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期。),东南沿海民族的探索(注:卫聚贤等人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并主编《吴越文化论丛》(商务印书馆),关于东南吴越民族的研究文章多裁于此丛书,如卫聚贤的《吴越释名》、《吴越民族》、《太伯之封在西关》、《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陆树栅的《吴越民族文身谈》等。),楚民族的来源(注: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1册,北京大学潜社出版1933年;蒙文通:《古代民族移徙考》,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1937年;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第2期。)等等。其代表人物有孟世杰、方壮猷、胡厚宣、徐炳旭、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罗香林等等。其文字多见于《古史辩》论集、《禹贡》半月刊等刊物中。
2.民族学印证考古学问题
最早提出这种方法和研究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在《美术的起源》(1920年)一文指出:“考求人类最早的美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古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学的材料。二是现代未开化民族所造的,是人类学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古物学”,即指考古学,“人类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族学”。在文章中,他鉴于古代文物是“静的,且往往有脱节处”,因此不得不借助于民族学材料来加以说明。认为“考求美术”的原始,要用现代未开化民族作主要研究材料。
蔡元培先生还开创了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人种、民族和文化,说要利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民族的体质特征,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民族文化的差异(注:蔡元培:《美术的起源》,《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胡起望:《蔡元培和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一集。)。
林惠祥先生是一位人类学家,是我国最早注意到运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遗物的学者之一。在1929年调查台湾少数民族时,除了收集高山族各类民族学资料外,还注意收集考古学材料,并调查了园山贝丘遗址。运用民族学材料对“雷公斧”作出正确解释。同时据台湾普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的石器、陶器、骨器、贝器,证明台湾番族与大陆之联系(注: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0年。)。
早期民族考古学活动主要表现在几个专题上,试举几例。
一是西南地区发现的悬棺葬(或称“岩葬”)的研究。本世纪20~40年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一种与中原不同的葬俗——悬棺葬。对于这种时代延续长而发现与中原以外的考古学遗物,研究者确认这是古代某民族的葬俗。但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葬俗呢?于是一些学者从古代文献中寻找有关民族活动的记载,调查这种葬俗分布区域的现代民族的风俗(主要是葬俗)与悬棺葬的联系。用以证实其族属。葛维汉、郑德昆等认为是白人(注:葛维汉:《四川古代的白人坟》(1932年)秦学圣译等三篇文章。)。向达认为是苗族的葬制(注:向觉明(向达):《中国崖葬制》,《星期评论》第二十七期,重庆,1940年。),而方欣安认为最早起于埃及和波斯,后传入中国西南(注:方欣安:《所谓蛮洞》,《星期评论》第15期,重庆,民国三十年。)。
把考古学文化与地方民族史结合研究,首推卫聚贤及同人。1936年,卫聚贤与同人组成“吴越史地研究会”,结合当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如良渚文化,探索吴越民族的族源(注:孟世杰:《戎狄蛮夷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期;胡君泊:《匈奴源流考》,《西北研究》1933年第8期;董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学艺》1942年第2期;郑师许:《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期。)。
此外还有些学者把一些普遍发现的考古学遗物,与古代民族相联系,作为某一古代民族的文化特质,如罗香林先生考证铜鼓是越族的文化特质之一(注:罗香林:《古代越族考》,《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第2期。)。
周口店,北京猿人发现地,是早期最重要的考古基地之一。在对北京猿人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当地民族学材料。如在北京人遗址发现的头骨化石,许多头骨上都有人为砸击而成的裂纹,有人根据当地一些原始民族中存在的食人之风,认为北京猿人时代已经存在食人(注:吴汝康先生对北京人遗址进行分析后得出食人的结论。)。在发现山顶洞人的洞里,发现一批穿孔兽牙、穿孔的海蚶壳、穿孔的小石珠、穿孔小砾石、穿孔鱼骨和有刻沟的骨管等。以穿孔兽牙最多,大多制作精美,在上面还发现染成红色。在一些“落后部落”中,喜戴装饰品的风尚比“先进民族”要盛行得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永久性的如文身,安置耳、鼻、唇的穿塞饰物;再有一类是不固定的,如发饰、颈饰、腰饰和四肢饰等。因此山顶洞人的穿孔器类应该是装饰品(注: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出版社1984年。)。
本世纪4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如夏鼐、曾昭燏、冯汉骥等人都提倡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学遗物。如夏鼐先生对寺洼文化的墓葬研究,“据此分析了寺洼文化的内涵,并提出将出土遗物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以研究少数民族早期历史的方法”(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用于历史研究。对民族考古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蔡元培、郭沫若、翦伯赞、尹达等先生。
郭沫若先生1929年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其自序中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古代”(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张寿祺文:认为恩格斯的《起源论》是当时所得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对古代社会的发展加以论证,包含了“民族考古”的成果。)。郭老在此书中综合了古籍、史经、传说以及当时能找到的考古学材料、少量民族学材料编写成中国古代史。这种治史之书在我国是第一部。
尹达先生于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延安完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也提倡科学地综合研究,注意把民族资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开展原始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注: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翦伯赞、范文澜先生在编史中也运用民族志材料结合出土实物论证南方系统的民族,补历史记载之不足。
以上简述了我国早期的民族考古活动。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在这两门学科的形成之始就已开始了交叉——民族考古活动。这一点也构成中国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一重要特色。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
1、历代史籍为我们留下来丰富的民族志遗产。但这笔遗产是杂乱无序的,需要我们整理。所以考证民族史从很早就开始了,利用新发现的考古实物考证民族史是自然的。
2、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研究人文科学都离不开“民族”,民族在研究历史和考古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3、近代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有着共同的渊源——大都受过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很多都是民族学、考古学双修。正是由于这一共同渊源,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门学科结合比较研究,因而成为民族考古的先驱者,许多后来成为民族考古学家(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三.从民族考古到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不等同于民族考古学似无疑问。笔者认为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民族考古仅是民族学与考古学的交叉,而民族考古学则是两门学科的整合,从考古学中分裂出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有自己的理论、方法、研究领域,或者说要有构成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正如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所说的“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实物结合起来,就会创造一个结合的整体,从而形成了称之为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注:容观琼:《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中南民族学报》,1984年第3期。)。
所谓民族考古学究其实质是把人类文化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加以相互结合。其理论基础是要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当代社会的观察与近代这种观察积累的材料中,寻求有助于我们解释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系统性知识,从而更好地复原没有文字记录或只有语言不详记录的以往人类历史的全貌(注:Patty Jo Watson:"The Idea of Ethnoarchaeology:Notes andComments".Ethnoarchaeology Edited By Carol Kramer.P277,ColumbiaUniversity Press,N.Y.1979.)。这种理论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全世界各民族从古到今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进化阶段。根据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那些“社会活化石”(即现代民族志材料)可以与考古学实物类比复原古代历史。但要进行类比分析必须有研究基础:一是大量民族学调查和完整的记录,同时民族学家要注意记录和收集对于考古学家解释文化遗迹与遗物意义有价值的资料。二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以及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文化序列和分布。这样在正确的分析和解释了物质遗存背后表现出来的文化意义后,考古学家才可能致力于进一步研究史前时代人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组织、家庭形态、整体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结构)(注:Michael B.Schiffer"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Ethnoarchaeology",Explorations in Ethnoarchaeology Edited By R.A.Gould.University of NewMexico Press Albuquerque,1978,P299。)。有别于传统的考古学家、民族考古学家在探究古代文化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观察与分析当代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居民的物质文化,并在类比分析的基础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力求全面地解释一个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与特定文化遗物的背景和意义。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是具有联系的物质文化体系,通过把考古遗存与现代民族志(特别是考古学家亲自获取的民族志材料)、历史文献有机结合一起进行研究(注:Carol Karmer:Village Ethnoarchaeology:Rural Iran in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P4.Academic Press N.Y 1982。)。
但要看到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是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民族考古可以说是民族考古学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萌芽阶段。在民族考古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总结,相关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的壮大,势必发展成为民族考古学。
条件成熟的时期终于到了。1949年解放后,迎来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学:史前遗址和青铜遗址在全国各地的发现、古代文化分区工作的开始、多学科合作对许多考古遗物、遗迹的解释。民族学:通过以民族识别为目的调查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排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文化序列。中国民族考古的特色得以继承和发展。考古学、民族学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开展民族学材料与考古学实物资料的对比研究。新的基础、新的理论、新的研究者终于导致了民族考古学的产生。
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有一个积累的过程。50年代以林惠祥先生为代表,他就我国东南地区和南洋及太平洋诸岛发现的有段石锛,运用现代台湾和太平洋诸岛的民族志资料,论证其发明、发展及用途,研究南洋民族与我国华南古民族的历史关系,也是他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资料的成果(注: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梁钊韬先生也运用考古学文化结合民族学和历史文献资料阐述有关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与古代吴越民族以至现代少数民族关系(注:梁钊韬:《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年代探讨》,《考古》1959年第9期。)。
到60年代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多了。如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研究,首先运用考古学方法,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性文化。但对这一文化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和族属等问题的讨论,正是运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才使之深入,获得今日之成果。冯汉骥先生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中,利用铜器上的人物图像来探索他们的族属关系,辨认出当时滇东北的民族聚落情况,“滇族”是这一文化的主人和创造者(注: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59年第9期。)。汪宁生先生则从另一文化特征(主要是发饰)作出类比分析,得出四类人与今天云南各族之间的因袭关系(注: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二是对半坡仰韶文化的研究,利用民族志材料对其葬俗、社会性质进行类比研究(注: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文物》1964年第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第8期;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的远古人类的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第7期;张忠培:《元君庙基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此稿写于1964年。)。
民族考古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断一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得到了迅速扩展。有关论文和专著出版增多。明确意识到民族考古学对复原古代社会的重要作用。尹达先生为《史前研究》创刊号撰文谈到,30年来民族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石兴邦同志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具体,明确民族志资料是“社会活化石”、是古代社会的记实。它对现在氏族部落状况的研究,可以解开古代社会之谜,成为复原人类早期历史的依据(注:石兴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关古代社会的考古研究工作》,陕西《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对推动民族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对综合类比研究,起着一定的作用。其具体研究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典型,运用民族材料对比研究河姆渡的古代实物资料,解释和复原当时的经济生活。如对干栏的复原、纺织技术的复原、生产工具的复原和功用的解释等等。其专著可以宋兆麟等人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为代表。
梁钊韬、张寿祺著文《论民族考古学》在国内首次使用了这一学科之名,并对这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形成进行了论述。接着客观琼先生发表《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一文,对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历史进一步论述,特别是对国内的民族考古学活动进行了总结。随着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民族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并开设“民族考古学”的课程,民族考古学也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点研究方向。这些,标志着民族考古学的真正形成。1992年,容观琼和乔晓勤先生整理出版了《民族考古学初论》的专著,书中对这一分支学科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列出研究个案(注:容观琼、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成熟。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也多次呼吁进行民族考古学或“人类学的考古学”的研究。他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题讲座中说:“考古学方法的设计和使用离不开民族学。一则是人与物之间有机联系关系的蓝图在民族学的情况中是可以详细画出来的,可以给只有‘物’或只有一部分物可用的考古学以参考。二则是民族学可以提供多种变异的很多蓝图,作为研究现在或与后世现象有所不同的古代现象的参考”(注: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他还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和“修重部头的民族学课”。
俞伟超先生在介绍国外新的考古学思潮的同时,对中国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的《考古学新理论论纲》用“十论”概括了对考古学发展的反思,不仅概括了聚落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计量考古学和新考古学,同时还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将文化观、全息观、价值观融入考古研究。他强调考古学不仅要研究“物”还要研究“文”,“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是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它进入一个学科,常常变成一种认识工具,使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客体有更好的把握。文化这一概念进入考古学,扩大了考古学文化的畛域,使研究者对考古文化作出整体性的思考,这正是科学进步的一种表现”(注: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四.结论
中国民族考古活动比西方晚得多,但其发生却与我国民族学、考古学同步,这构成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一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其一是离不开中国肥沃的“土壤”,即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其二是世界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的相继传入给中国土壤施加了肥料。中国历史上播下的“考古学”(金石学)、“民族学”的种子与西方近代考古学、民族学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催化下,发芽、生长,而两门学科本身的发展,研究对象的部分重合,研究者多受过两门学科双重训练,使两门学科的相交是必然的发展。但是,早期两门学科各自还发展不充分,两门学科的相互印证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因而称之为“民族考古”而非民族考古学。
1949年解放后,考古学与民族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考古学的发展,必然会从单纯研究遗迹、器物中跳出来,研究实物所反映的意义、文化创造者。而我国丰富的民族学材料又提供了最好的类比材料。这样,一大批学者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终于迈向了民族考古学的轨道。
中国从民族考古到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出来的。与此同时兴起的西方民族考古学,可以说是与我国的民族考古学“殊途同归”。(一)兴起的时间大致相同,西方民族考古学是二次大战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二)指导理论的相似性,西方这门学科是受“新进化论”影响,主要以“文化唯物论”作为指导,而“新进化论”的产生是受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核心思想,即“承认全人类文化发展具有共同规律性”的影响;(三)都是以复原古代社会为目的,西方把这门学科研究限于史前,而中国扩大到文字记载不详的青铜时代。
中国的民族考古学已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仍可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一)区域性民族考古学研究。中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和文化多元的国家,考古学上的分区分系研究已相当深入,而这种研究离不开民族考古学。如在吴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研究显示出这种趋势。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可以说是区域性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典范(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区域性考古学研究的意义在于:1)为各地区传说时代或史载不详的民族提供大量考古学物质文化背景,丰富了对文化渊源、族源的认识,如对百越、百濮、氐羌的研究。2)揭示华夏汉民族族源主体的若干民族的文化渊源,如对先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等文化的研究表明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和形成过程的复杂性。3)揭示古代民族的活动范围、迁移路线和文化变迁等。如宿白先生从考古发现论证了拓跋鲜卑从东北兴安岭一带迁往平城、洛阳的路线和过程(注:宿白:《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材。)。
(二)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边疆地区今天以少数民族分布为主,在古代这些地区的人群不断与中原民族交往,考古发现将寻找到民族关系与文化渊源。如***、东北、内蒙古、西南、东南的民族考古(注:李遇春:《建国以来***地区民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李逸友:《内蒙古北方民族考古工作的进展》,《民族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申戈:《云南民族考古发掘与研究概述》,《民族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干志耿:《黑龙江考古与民族历史》,《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谢端琚:《青海民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蒋廷瑜:《广西民族考古研究综述》,《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王明珂先生所著《华夏边缘》,利用族群理论阐释考古学和民族史的资料,论证了华夏生态边界和族群边界形成的过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论证了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西辽河流域地区从旧石器文化向农业社会发展,又从农业社会向游牧社会发展,以及这些地区的民族逐步成为华夏边缘的过程(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三)以某种或某类特定的物质文化为核心,形成富有特色的民族考古学专题。这些专题研究将考古学发现,结合民族民俗文物与民族民俗志记述综合研究,揭示若干民族共同的文化创造,族际的文化借用、文化传播。如细石器的分布、流传与狩猎技术、游牧民族的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与北狄、匈奴、鲜卑等游牧马上民族的关联,几何印纹陶与古代百越的关系,等等。如吴春明先生根据印纹陶文化的谱系和序列分析了东南地区古代土著民族与地域的关系和土著民族发展史;此外他还把东南地区一些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东南土著人文特征加以讨论(注: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四)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研究。一些学者利用侗族、壮族等民族志材料和考古材料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注: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李富强:《“蛮荒”稻香——壮族农耕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更多的学者利用民族志的资料探讨考古发现的工具的功能、性质。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引进酋邦的概念,打破了我国早期国家不是由部落社会直接转化而来的观念,而是古代酋邦在政治上演变的产物(注:容观琼:《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当然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复原文明的过程、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发展、聚落的形成等。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考古学成长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民族考古学将有更为美好的背景。首先,随着国际间学术的交流,可以向西方新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学习理论和方法不断充实自己的学科;同时有着比西方民族考古学更好的研究条件,这就是56个民族的民族志材料和祖国大地上遍布的考古文化和发掘资料,为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也就是我们深信民族考古学能在历史文化研究中肩负重任的理由。
来源:《东南文化》2001年第03期
- 0003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