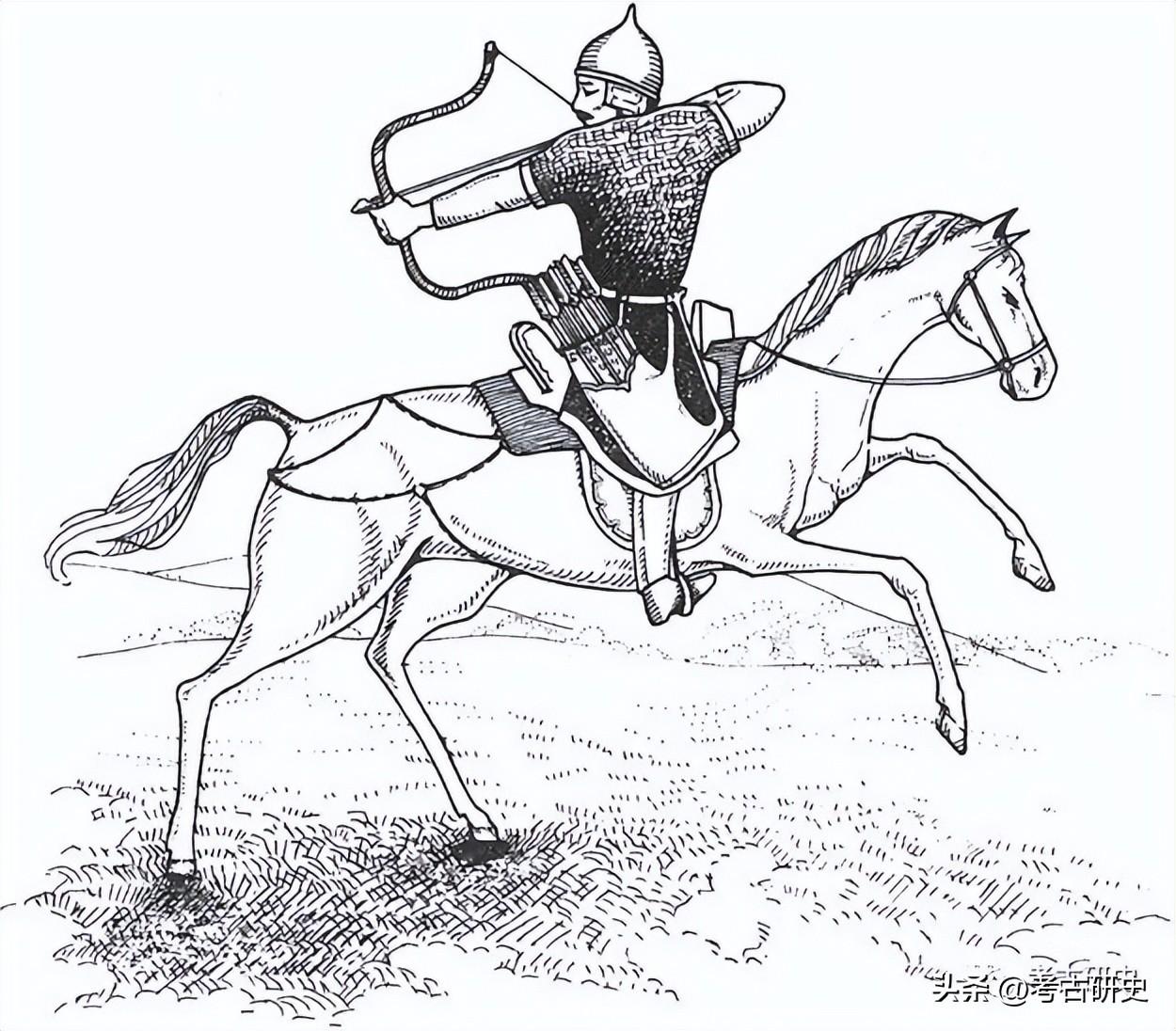论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笔谈)
谈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李学勤
说起经学,今天在社会公众甚至学术界中,每每引起一种神秘感。常听见有人慨叹:经学太深太难了,似乎是一种高不可及,只好敬而远之的学问。
其实,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近看钱穆先生《新亚遗铎》里的演讲,他强调“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我们还要说经学是儒学的核心。这样说,并不是想渲染经学有什么好。不管现在对经学怎样评价,经学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既深远又普遍的影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研究传统文化,阐扬其间的优秀因素,无论如何不能对经学弃置不顾。
什么是经学?《辞源》讲是“研究经书,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之学”。这个意义的“经学”一词出现很晚,具体时间有待考证,其流行要到晚清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以及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等以后,“经学”所指的那种学问的起源却非常早。大家知道,经书的“经”字本义是“常”,被认为常道可以作为典范的书便称为“经”。经书的地位得到确定,必然得到传习和注释解说,也就是有人作训诂、讲义理。因此,不妨认为有了经,便有了经学,至少是经学萌芽的存在。
先秦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代以下只有五经。这一点有些学者不相信,他们主张《乐》本无经。近几年,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里见到六经之后,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古书里提到《诗》、《书》、《礼》、《乐》等,这些经书都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取得经的地位也互有先后。《诗》、《书》、《礼》、《乐》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古文字材料看,商代晚期甲骨文已有“太学”,西周金文涉及学校的更多,教学内容当即包括《诗》、《书》、《礼》、《乐》之类。到了春秋时期,记史的《春秋》(不一定是鲁史)也列入教材。例如《国语·楚语》载,楚庄王任命士璺做太子箴(后来的楚共王)的师傅,士璺向申公叔时请教,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令(命)》、《故志》、《训典》属于《书》类,《春秋》、《世》、《语》属于《春秋》类,加上《诗》、《礼》和《乐》,六经已有其五。
六经系统的确立,自然是经过孔子的工作。孔子以六经(或称六艺)授弟子,他对经书的删述,用现代的话说,是编订基本教材。特别是孔子老而喜《易》,据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要篇》,子贡曾对孔子质疑,孔子明确表示,他自己对《易》的看法和做卜筮的“史巫”不同,所注重的不是占筮,而是古之遗言,“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我观其德义耳”。这样,就把原来只是占筮书的《易》转化成了哲理的著作,使《易》正式进入经书的行列,《易传》十翼也由此撰成。
孔子及其门弟子对六经的传习论述,不像《左传》、《国语》中春秋时期人物那样只用片断的引用和解释,而是系统的研究。有些人看《论语》,以为孔子关于《诗》、《书》等只限于零星的评论。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诗论》,足以改变这种印象。由《诗论》不难证明,那时已经有了和今传本基本一样的《诗经》,而且孔子本人有丰富深入的论说,这显然已经是经学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时代”,过去多以为到汉代才开始,现在看还是肇端于孔子及其弟子。
从诸子百家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经学的影响在逐步扩大。比如墨家非儒,但《墨子》书里引用《诗》、《书》的地方很多,道家的《庄子》也是一样。《庄子》对孔子嬉笑怒骂,但透过其寓言、重言,正能看到孔子和六经具有的权威。
传统经学的特点,就在于经书的权威性,而其权威又集中在孔子身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足见经学与经书和孔子的神圣权威是分不开的。历代的经学,尽管各有其历史背景与具体主张,在这一特点上却是一致的。
这样的传统经学居统治地位的“经学时代”,到了现代,已经在社会的变革中结束了。于是有学者提出以经学史来取代经学。在这方面最富先见的是周予同先生,他在《“经”、“经学”、经学史》一文中讲“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亟待开展”,代表了他的见解。周先生提出经学史有三项特有的研究任务:第一,“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各个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如何在经学范围内展开思想斗争”;第二,“历代的经学思想又如何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服务”;第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由此可知他所提倡的经学史是走思想史的路子。与之类似的,在最近有姜广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经学思想史》。还有不少分论不同时代经学史的著作,所采用的方法也差不多。
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经学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果。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今天我们来探讨历史上形成的经和经学,还必须采用另一个角度,这就是文献学。
经对于当前的社会来说,早已不是什么常道,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经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其神圣权威性的被剥夺,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把传统的经书作为历史文化的核心文献来考察,应该是文献学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历代汗牛充栋的经的注疏论说,都是对经的诠释。今天我们由现代的学术知识出发,可以对经书作出新的研究,新的诠释。这些研究和诠释,只要不以经具有神圣权威为前提,便不会落入传统经学的窠臼。相反的,现代的文献学的研究诠释,会为评价历史上的经学诠释的得失,提供比较客观的尺度。这样,用文献学的方法,不仅能有新的“经学”,也能建立与思想史角度不同的经学史。
上个世纪,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这种文献学的工作。在近二三十年,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文献材料,为扩大和深入这方面研究提供出前所未有的条件,也使大家关于经与经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的认识大有改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编著出以文献学为基础,同时结合思想史研究的经与经学史,这一定会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探讨和阐扬有所贡献。
作者简介:李学勤,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经学研究应以文献学为基础
徐有富
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经学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经学在古代书目的分类中一直处于首位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古代经学的首要任务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难免会对儒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种种曲解。我们今天从哲学、史学、文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经学重新进行审视,势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学为基础方能奏效。今试以《关雎》为例,略作说明。
首先说一说主题,我们认为《关雎》不过是首情歌,但是为了进行封建说教,《毛诗序》却解释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正是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人们对《关雎》的思想内容作了种种歪曲。有认为其为美诗者,如毛《传》云:“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有以为其为刺诗者,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周道缺,诗本之衽席,《关雎》作。”晋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亦云:“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机而作。”
无论美诗,还是刺诗,都是从《关雎》一诗的教化作用出发形成的观点。其实人们早就觉得这种说法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如欧阳修《诗本义》卷一怀疑道:“《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於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元代的马端临对教化说也深表怀疑,他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明确指出这是一首表达情欲的诗:
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
清人崔述《读风偶识》卷一也指出:“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
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还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了雎鸠不过是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根本不是什么“挚鸟而有别者”,他指出:
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雎之声乎?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其喙锐者,则其声骘骘,此天籁也。关雎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
用捕鱼来比喻追求异性是非常普遍的。闻一多《说鱼》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指出:“正如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此在先秦也不乏其例,如《管子·小问》篇说过一个故事:“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此诗通篇写的都是找对象没有找到的感受,以“关关雎鸠”起兴也是为了比喻找对象,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深刻的寓意了。
其次谈一谈这首诗的作者,我们认为《关雎》起初是民歌,后来被乐师们收集并加工过。但是,古往今来不少人都认为这首诗并非采自民间,朱东润还特地写过一篇《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特别提到:“即以《关雎》、《葛覃》论之,谓《关雎》为言男女之事者是矣,然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在今日文化日进,器用日备之时代,此种情态,且不可期之于胼手胝足之民间,何况在三千年前生事方绌之时代?”这一观点似乎为一些学者所普遍接受,如魏炯若《读风知新记》说:“《关雎》诗里有琴瑟中鼓,诗为贵族而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必须注意《关雎》一诗是经过乐师们加工过的民歌,他们加工的目的当然是为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服务的。因此乐师们在对歌词进行加工时不能不反映贵族们所熟悉的生活,运用贵族们所熟悉的语言。应当说这首诗的基本素材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如诗的前十二句,写水鸟在河中的小岛上叫着,写一位姑娘在采荇菜,写一位小伙子见了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以致朝思暮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反映的基本上是老百姓的生活与情感,使用的也基本是群众语言。后八句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恰恰是乐师们为了迎合贵族的需要,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加上去的,考虑到演唱的场合与观众的身份,于是将采荇菜的姑娘称作“淑女”,将害单相思病的小伙子称作“君子”,从而使这首诗歌打上了贵族阶级的烙印。
古有采诗制度,如《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显然,文中的“比其音律”,说明大师对收集上来的民歌进行了加工,再配上音乐,以供演唱用。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曾对乐师们加工民间歌谣的情况作过分析,指出:
我以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唯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
乐师们对《关雎》的加工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认为前十二句基本保留了《关雎》一诗的原始面貌,它真实、生动、鲜明地表现了民间一位男子追求一位女子尚未获得成功的情感,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因此广为流传。为了更好地发挥歌曲的娱乐功能,所演唱的歌曲一般都要重复唱上好几遍。重复唱的歌词与曲调同前十二句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了使所唱的歌词,每一遍之间有所区分,便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改了几个字,这也正是国风中绝大多数诗篇各章之间结构基本相同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专门谈一谈《关雎》的分章问题,《关雎》共二十句,如何分章,《毛诗注疏》卷一指出:“《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解释道:“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显然,郑玄将《关雎》分成了五章,而早于他的毛公,则将《关雎》分成三章。应当说将《关雎》分成三章更原始,也更可靠一些。问题是三章如何分,正因为毛公的分法不够科学,所以郑玄才将三章改成了五章。我们认为分三章是正确的,其正确的分法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关雎》中有三段诗的结构基本相同,这三段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它们理应并列地分在三章。国风中绝大多数诗篇都是这么分章的,如果毛公、郑玄等不这么分,后人就会提出疑问。比如《小雅》中的《伐木》一诗郑玄分为六章,章六句,未加说明,可见毛公也是这么分的,朱熹在《诗集传》中改作“三章,章十二句。”并说明道:“刘氏曰:‘此诗每章首辄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当为三章。旧作六章,误矣。’今从其说正之。”刘氏指刘敞,其《七经小传》持此观点。毛公虽然将《关雎》一诗分为三章,但并未将上述结构相同的三段诗,并立地分在三章,而郑玄将之分为五章,也未反映出这三段诗的并立关系,故也不是正确的分章方法。我们的分章方法,准确地反映了三者的并立关系,因而是正确的分法。
章是音乐单位名称,《说文三上·音部》指出:“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当然,章同时也是抒情表意的单位,《文心雕龙·章句》篇已说明了这一点。
刘勰所论不局限于诗歌,诗歌当然也包含在其中。章既是音乐单位,同时也是抒情表意的单位。我们在分析《关雎》的分章问题时,不能不考虑这一重要因素。
《诗经》中的歌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乐谱的支配,乐谱奏两遍,则歌词就分两章;乐谱奏三遍,则歌词就分三章。歌词的每一章,从音乐与抒情表意的角度看,都应当是相对完整的自足单位。就拿160首国风来说,即以郑玄所分章句为例,其中分为三章的有91首,分为两章的有40首,分为四章的有21首,而分为五章的只有5首,分为六章的只有2首,分为八章的只有1首。显然一首乐谱,连奏三遍、两遍、四遍比较受欢迎。而连奏五遍、六遍、八遍就会使人感到厌倦。就内容而言,分为三、二、四章的都是一些篇幅短小的抒情诗;而分为五、六、八章的都是一些叙事成分较多的篇幅较长的抒情诗,如《谷风》、《氓》、《七月》等。就《关雎》所在的《周南》而言,共有11首诗,其中有9首为三章,1首为四章,所以将短篇抒情诗《关雎》分为三章是正确的,而郑玄将其分为五章是错误的。
歌词是合乐的,因此各章之间的歌词应当是大致整齐的。就160首国风而言,其篇章结构大致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各章之间章句基本相同,约有103首;第二种情况是各章之间部分章句基本相同,约有26首;第三种情况是各章之间,章句基本不同,约有31首。无论哪一种情况,每一章从音乐与抒情表意的角度看都应当是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而且,为了便于演唱,一篇之中,每章之间的句数应当基本上是一致的。以郑玄所分章句为例,各章之间句数相同者有149首,而不同者只有11首。就周南11首诗而言,毛公将《关雎》分为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且从音乐与抒情表意两个角度来看都不伦不类,毫无规律可循,无法演唱,特别是他所说的第三章八句诗同义反复,意思显得很不完整,其他诗篇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而按照我们的分法,不仅三章结构完全一致,而且从音乐与抒情表意的角度看,每一章都很完整。
既然《关雎》分为三章,每章十二句,那么为什么除第一章十二句外,第二章、第三章的首四句与末四句缺而不载以至导致后人产生误会呢?这是因为第二章、第三章的首四句与末四句与第一章完全相同,因此在抄写时就省略掉了。现代歌曲也有这种情况,如果一首歌有好几段歌词,每段歌词完全相同的部分,除第一段照录外,其余各段也是省略不载的。应当说起初这样做对《关雎》的演唱毫无影响,而当《关雎》不再演唱以后,人们忽略传抄时被省略的部分,对如何分章理解不同,如何分章便产生了歧异。
此外,以重文符号代表重文也不乏其例,如《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所录魏武帝《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等六首诗,即以“=”代表重文,王仲荦校曰:“古人凡重字,下一字可作=画。石鼓文凡重字皆作=画,盖其滥觞。此篇每一字之下作=画者,其读法犹若音乐中之复奏。如本段读法,自‘晨上散关山’至‘长恨相牵攀’前后八句,通段复一遍,又非每句或每字一复也。”在王先生看来,重文符号=画,不仅代表重字重句,而且可以表示重段,音乐上的复奏。
《关雎》分章有误,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人们常从脱简、错简的角度加以解释。我们认为既然章是乐曲的组成单位,从演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诗经》中一些诗的分章问题加以研究,应当会有新的收获。我们以《诗经》首篇《关雎》为例,指出它的主题、作者,甚至如何分章都有从新探讨的必要,只要我们以文献学为基础,经学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
作者简介:徐有富,南京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谈谈经学与古文献研究的关系
赵生群
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经学研究在古文献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所谓学问,主要是指经学。自从孔子论述六艺,其后学者传承不绝。至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奠定儒学在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儒学。三礼、三传、《易》、《书》、《诗》以及与儒学经典相关的《论语》、《孟子》、《孝经》、《尔雅》都被尊之为“经”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整个封建时代,所有文人学士,无不熟读儒家经典并从中汲取营养。可以说,儒家经典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犹如水之有源泉,木之有本根。与此相应,经学研究也备受历代学人关注,翻开《四库全书》,经学研究的著作真正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洋洋大观。
以往的繁荣和辉煌,在今天很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当我们在研究某些经学课题时,常常有人会问: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否还有必要?或者是:前人是否已经将这些问题研究到家了?
其实,几乎每一部经典都有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孔子与六经到底有没有关系?《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春秋》是经还是史?《春秋》有无“微言大义”?《左传》与《春秋》有无关联?《左传》的作者是谁?《左传》是《春秋》之传,还是独立的史书?《周礼》、《仪礼》、《礼记》作于何时?《尚书》今文与古文,到底是什么关系?《公羊传》、《榖梁传》成书孰先孰后?“孔子删诗”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
每一个有关经学研究基本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疑案,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只要我们仍然在继续阅读和研究这些典籍,我们就无法绕开这些问题。而且,当我们对某个问题作出选择的时候,往往牵涉到其他许多相关的问题。例如,关于《左传》的性质,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而与《春秋》无关。如果认为《左传》与《春秋》无关,那么,就必然要否定《左传》中解释《春秋》的文字,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言”、“不言”、“称”、“不称”之类,甚至认为这是出于后人伪造。这一问题,还势必要牵涉到《左传》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左传》的作者、《左传》的体例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左传》隐公元年共有13条传文,而其中解释《春秋》书法凡例的,达11条之多,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内容是后人增窜甚至是有意伪造。如果认为《左传》是为解释《春秋》而作,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完全不同。
就总体而言,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存在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关系到这些著作基本价值的判断,这些问题,事实上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感和印象。
唐、宋以后,人们对有关经典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辨伪之学逐渐为人们所重视,特别是清代以后,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颇多,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少佚籍重见天日,新的文献也大量出现,这为经典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契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使得原来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差异,甚至存在根本的分歧。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难以改变。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否则,与此相关的许多研究,都将受到制约和影响。
经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的关系极其密切,而每一部经典,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都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形态,在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及文字、音韵、训释等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新的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是古文献研究中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作者简介: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