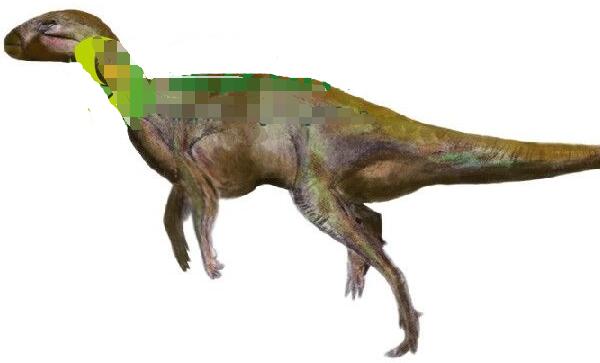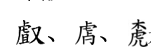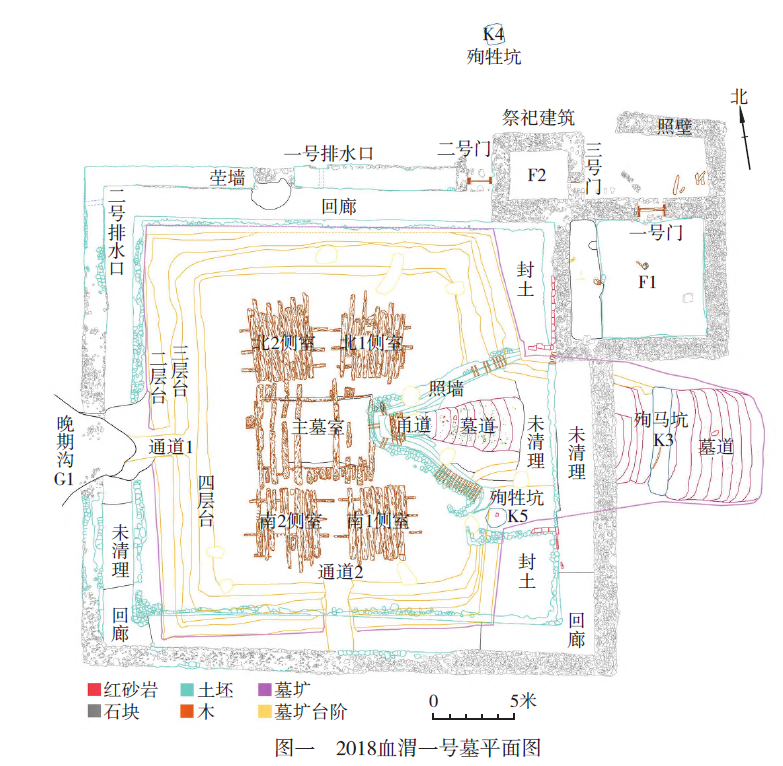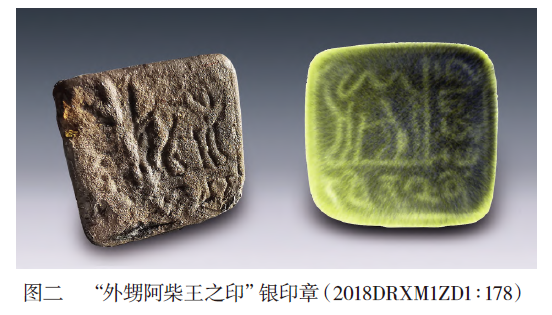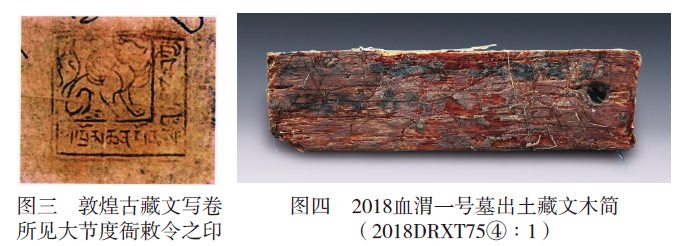李学勤: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我非常荣幸有这次机会和宝鸡文理学院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见面。其实我和宝鸡文理学院的关系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因为几年以前,我受邀担任《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学术顾问,可能有些老师曾经看过我的文章。宝鸡市邀我来参加昨天的炎帝大典,中国先秦史学会从昨天开始也在这里开会。那么,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见面,有老师问我讲些什么,我讲一个题目《理论与历史学创新》。我想将这次演讲,作为我送给宝鸡文理学院各位老师和在座的同学的一个小小的礼物。
为什么今天选这个题目《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这个内容不局限于历史学,因为和我个人专业的关系,我想举和历史学有关的例子。其实,我想借这个机会送给各位老师和同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或者说我们在科学上要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要求,因为科学发展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科学怎么发展呢?可是创新,我个人的体会是它最根本的在一个理论观点的创新。归结起来就是一点:这个观点就是一句话,但这一句话会引起整个学科甚至几个学科的巨大的创新。这个观点我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贡献给各位老师同学。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想在座的都知道,不管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都有很多例子。去年刚刚纪念了爱因斯坦提出他的“相对论”一百周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其实也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观点,但“相对论”就引起整个物理学的革命。很多科学的发展,包括历史学,听起来和物理学距离很大。实际上,它作出创新也同样就是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提的是正确的,就会引起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革命。
我在考古学、历史学方面举例来说明这个想法。这些完全是我个人亲身所见而得。下面,我准备讲三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人都是我亲自见过的,都和我个人经历有关。为了讲这三个故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我在大学念书时并不是念文史的,而是念哲学的。而我去哲学系念书并不是想学一般的哲学。因为我在中学念书时数学学的可以,那时我就想我上大学念什么。我最后选择和数学相关的学科——数理逻辑。当时学数理逻辑。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找金岳霖先生。金岳霖先生是长沙人,字龙荪,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现代的数理逻辑系统地加以介绍的学者,也是中国现代逻辑学最早的一位学者。当时,金岳霖先生时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于是我就考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跟金先生学数理逻辑。当时的情况可能在座的各位年长的老师都知道,学苏联的“钢”字化,在苏联不光数理逻辑,就是一般形式的逻辑都受到批判,所以我就不能学数理逻辑了。但由于我自己在业余时间学甲骨文,因此在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我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两年,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二所成立,我又到历史研究所工作,直到2003年我被调回母校——清华大学。下面我讲的故事里的人物都是历史研究所的老前辈。
我先讲第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他也是国务院副总理,又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后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还是郭沫若,这是历史研究所成立的第一位所长。郭先生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今天看起来是不朽的,起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他怎么起着这个影响?我就从这方面介绍他的经历。郭先生是一位革命者,在革命事业方面起着重大作用。1927年北伐过程中,发生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发动的“4·12事变”。事变后,国共分裂,蒋介石政权制造了迫害共产党的白色恐怖。郭沫若当时作为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逃到日本。在日本,他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很快掌握了甲骨文金文这门大家看起来很艰深的学科的材料和研究。他在1929年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出版。这本书一出版就掀起轩然大波,在当时中国学术界起来极大作用,引起一个大论战。这个论战就是“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今天讲郭沫若在历史学界为什么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最主要的就是这本书,而这本书为什么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郭先生当时写这本书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写这本书,怎么写这本书都是与当时历史背景,甚至国际历史背景有关。刚才给大家讲过,郭先生在1927年国共分裂逃到日本的。北伐1925年在广州开始,当时孙中山先生已逝世。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派专家马迦尔到广州作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本人在广州周围地区进行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这本书提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叫做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开头提到的,大意说“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经历了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等等阶段”,这里面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词从第二国际时期到列宁时期经过种种解释。而马迦尔到中国之后,当时主要问题是中国革命怎么走。中国革命应该怎么进行,这就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就要取决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而这个认识的基本一点就是马迦尔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有几个特点,它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是一个停止不发展的社会。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个社会。”这个观点引起很大影响。这个问题在苏联后来引起争论,特别是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大革命已经失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革命应该如何进行”?这就取决于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和矛盾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就是中国当时是不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或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解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苏联第三国际引起很大讨论,这一讨论在苏联到1931年结束。1931年,由斯大林领导政府组织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之后,苏联出现官方论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变种的封建主义。”这个讨论在苏联正式结束。可是在日本、中国这个讨论才真正开始。这个讨论的导火线就是郭沫若先生这本著作。郭先生写这本书就是针对当时在国际上,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而写的,可是这本书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情况,所以他一开始讲写这本书是继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为马恩著作提到希腊、罗马、日耳曼,没有提到中国。那么中国古代是什么样子呢?因此,郭沫若写此书是为了补充他们没有说的空白,来讲中国的古代,而中国的古代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相联系的。郭先生在这本书中所采取的论点是五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有争议的论点。这一点,今天我们听起来不稀奇,可是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是一种尝试。当时郭先生首先用五种生产方式而且用大量甲骨金文材料来论证,他说“中国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就要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他这本书用大量甲骨金文、诗经、书经等材料论证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的普遍规律。郭先生所作的创新不但和当时流行的非马克思主义论点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论点不同,而且和接近于或者隶属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潮流内部的观点也不同。这个创新就是用了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而且把这一论点与中国古代和考古学相结合。可是,这一观点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当时在中国学术界就是一个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论战时期。他的书一出版,使大家开阔眼界,就是我们解释中国今天的社会性质和今天农村经济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革命和社会进步。可是中国今天的社会和历史是和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商代、周代历史是分不开的。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所以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问题论战。这一问题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总之,郭先生写这本书首先用中国考古的、古文献材料结合了当时不为大家所使用的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造成了极大影响。
讲的第二个故事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历史研究所第二任所长,西北大学建立后第一任校长侯外庐先生。侯先生是我国和郭沫若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年龄比郭老低,因此很尊敬郭先生。实际上他在史学界影响也很大,所以历史研究所成立后,他担任副所长,后继任第二任所长,到逝世为止。侯校长于1949年与郭沫若一起坐船从香港回国。解放后,他担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不久,被任命为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当时最知名的一级校长之一。他担任校长到1957年,但实际上他于1953年已调到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我就在那一年见到侯先生,他将我从考古研究所调到历史研究所,我于1953年到历史研究所报到。侯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国思想史方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奠基人、创始者,是著名的马克思史学家之一。他本来学法律的,经李大钊介绍到法国留学。到法国后,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资本论》,所以侯校长是我国最早翻译《资本论》人物之一,他的全部手稿现在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目中保存。为什么讲这些?这些和侯先生所作的创新有关。侯先生在历史学方面最早的正式著作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是史学界传世名作,而且也有日本的翻译本。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在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和周总理关系密切,负责当时中苏友协工作。在这期间,他得到了当时在苏联最早发表的一个马克思的手稿。这是马克思在他准备《资本论》期间的手稿的一部分。这些手稿原文最早在德国出版,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侯先生看到这些手稿提出了他的新观点,就是针对中国社会史论战和苏联“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所以侯先生说他在历史研究方面是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他根据手稿,写了一本书《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独特的解释,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论点,也是一个极大的创新。这本书于1943年出版,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他把中国古代看成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一观点很奇怪,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可是大家想像不到在美国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到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夏、商、周)历史发展和希腊、罗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叫做破裂,一个叫做绵延。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希腊、罗马把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完全瓦解建立新的社会。而中国是在原有原始社会氏族制度基础之上建立文明社会。这一点正好和侯校长观点一致。我们不能确信张光直直接看过侯校长的书,但为什么他能够提出这一论点?后来,张先生死后,他的好友许倬云写他的回忆录时我们才知道他在台湾上大学时常看马克思著作。
下面讲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北大考古系创始人第一任系主任苏秉琦先生的。苏先生和宝鸡的关系很密切。在解放前,苏先生最主要的工作是对宝鸡斗鸡台东区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因此他和宝鸡田野考古关系最大。苏先生的重大贡献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上,他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很多区域,从每个区域来考察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文明起源为“满天星斗”。苏秉琦先生换句话说,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一观点正好和历史学革新相结合,在历史学上,这个时期也出现新的观点,即“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不同民族、地区共同创造、推进和发展了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个观点影响非常巨大,打破了过去长时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单线的,而且主要是黄河中游地区,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观点。美国著名学者何炳棣教授写的《东方文明的摇篮》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在黄河中游。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是以王朝为中心,而中国古代王朝基本上确实是在黄河中下游,包括黄河支流,渭河三秦地区,即使不在黄河地区也是和黄河挨着的,历代王朝绝大多数这一地区建都。所以考古学一开始出现时,眼光就看这一点,也就认为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情况真正改变是在文革以后,在全国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使考古面貌改观,就在这种条件下,苏先生提到这一观点,并推而广之。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以上谈到的三个例子是我比较熟悉的。总结刚才所谈,有这几点:
第一,学术科学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有创新。创新不是容易的事,不是躺在床上想到的一个点子。刚才三位前辈所作的创新,都是与他们长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与他们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密切关系。郭先生既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是科学事业的组织者、推广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革命活动者。因此,他才能把握住当时学术界和革命的历史发展实际的密切关系。侯外庐校长也是这样。他把马克思主义原著介绍给中国,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翻译者,开启了我们建国后古史分期的讨论。他认为从思想史可以研究社会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了中国思想史重要学派。所以说创新是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第二,创新看起来是个理论观点,但提出这个理论观点要有非常大的勇气。大家知道,真正的科学创新,都是和成见甚至常识相反的,都是否旧的。新就是否旧。所以任何新的观点都有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是所有人反对的,所以一直到50年代英国伦敦还有维护“地平说”的学会,但人们最终接受了“地圆说”的观点。因此,“地圆说”是对“地平说”的一个最大的革命。所以说,提出一个学术理论要经过三步曲:第一步,人人都反对;第二步,折中这种观点;第三步,赞成这一理论观点。所以理论创新,一个学术的新发展是和常识是对立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最后一点,创新是实际的。创新是实践里抽象、结晶而来,经过多年的研究才可能有理论创新;经过极其繁杂的工作才有创新的线索和机会。理论本身从实际中产生,脱离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不存在的。
谢谢!
(李春艳整理)
附记:
李学勤先生于2006年9月来宝鸡参加“炎帝·姜炎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受宝鸡文理学院邀请,于9日上午为学院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本文是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李学勤先生审定。在此,我们向李学勤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
- 0000
- 0001
- 0002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