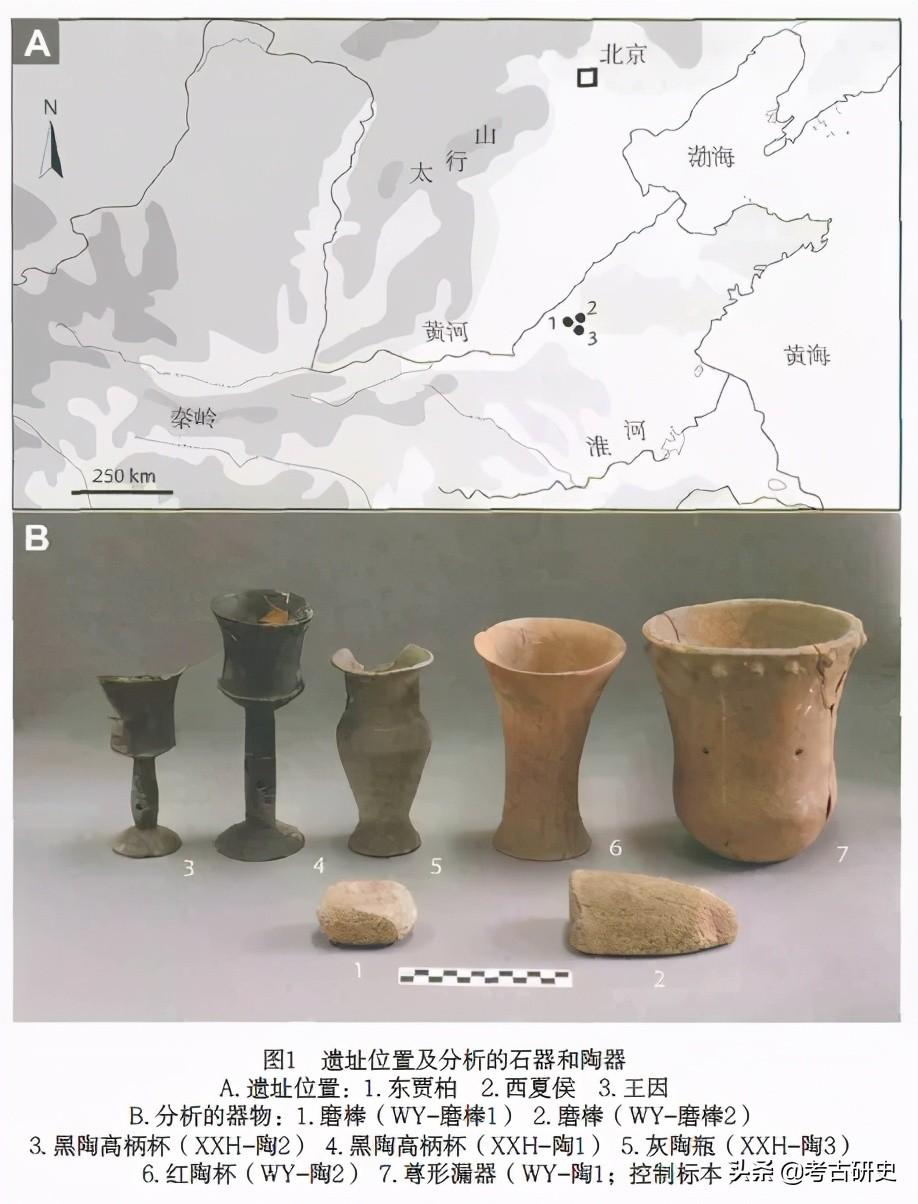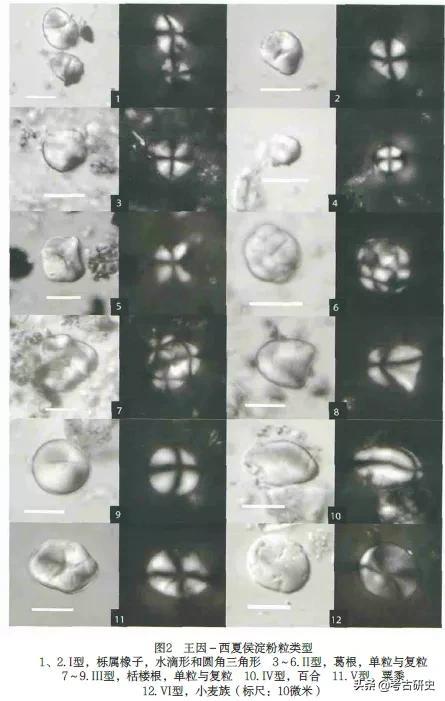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
当面临世纪交替之际,近期我们看到不少学者在论作中引述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注:《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65~69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这篇文章,是王国维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教,暑假应学生会邀请作的讲演,原发表于《清华周刊》上(注: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他指出,中国“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四项“最大发现”,就是“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这四项发现,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为海内外学术界共同研究,各有其重大影响。无怪乎现在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大家都要谈到王国维的远见卓识了。
王文说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随后又屡有出土,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有许多简牍以及帛书发现,其性质、内容和年代等方面,范围均比王国维所见扩大了许多。对各种简帛的研究,日臻兴盛,所形成的学问便是简帛学。
古人说“书于竹帛”(注:《墨子·兼爱下》、《天志中》。),竹木质的简与丝质的帛,是古代中国人书写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时期,才逐渐为纸所代替。因此,“简帛”长期被作为书的同义语,源出自简帛的若干词语,如“编”、“册”、“篇”、“卷”等,甚至沿用至今。可以想像,古代的简帛,数量应该是非常多的,不过其质料容易损毁,埋藏地下更难保存。尽管是这样,简帛仍是出土文物的一大门类。
迄今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它们的内容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类。
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汉志》未收的,如法律,遵照后来的目录传统,也可以列入。
文书,包括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边远地区所出与屯戍、津关、驿传等关联的材料,尤有特色。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
在这两类以外,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书札、历谱,有关丧葬的祭祷记录、遗嘱、遣策等等,虽然零碎,仍各有特殊价值。
占简帛主要部分的书籍和文书,两者性质不同,研究的方法途径有其明显区别,经过好多学者努力,看来已经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本文想专就简帛书籍发现和研究,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前面讲到的殷墟甲骨、敦煌卷子,都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首次发现的,简帛书籍的发现则并不自近代始,其历史实际可以上溯到西汉早年。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焚书事件。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所制定的律文,即《挟书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参看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汉因秦律,在一段期间内,《挟书律》仍然施行。看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书籍,范围均限于法令、医药、卜筮之类,可知《挟书律》的威压是相当有效的。
《挟书律》的解除,是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 该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注:《汉书·惠帝纪》。),人们才重新获得收藏阅读书籍的自由。《挟书律》的执行,虽然仅有二十多年,但给学术文化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为了继续和发展先秦已经辉煌繁盛的学术传统,汉人在收集、整理前代遗留的书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简帛书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重见于世,并且得到重视的。
那时出现的曾遭禁绝的书籍,大都是学者在法令威迫下隐藏起来的。例如《史记·儒林传》载:“伏生(胜)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他所传的是《尚书》。类似的例子如《经典释文·序录》云,《孝经》在秦火时“亦遭焚烬,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芝子贞出之。”
伏胜的《尚书》,颜芝父子的《孝经》,皆为焚书以前的旧籍,肯定是以六国古文书写的。这些书重新出现之后,当时像伏胜这样辈分的人仍能读六国古文,在其教学之中传抄,便改用秦统一文字后的字体,于是他们的本子被称为今文,原来的古文不再传流于世。
《左传》的情形有所不同。张苍从荀子处传得《左传》,汉兴,献其书于朝廷,所以《左传》的古文本在中秘保存下来(注:参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22页,中华书局,1984年。), 《左传》也就称为古文经了。
焚书时壁藏的书籍,有的很长时间没有被取出。最著名的事例,是汉景帝末年发现的孔壁中经(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82页,中华书局,1987年。)。据《史记》、《汉书》记载,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子后裔孔安国将书上献武帝,适遭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安国,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景帝时,还有河间献王好书,所得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如《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70页,中华书局,1987年。)。
此后,古文书籍有不少零星发现,史不绝书。最重要的,是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 年)发现的汲冢竹书(注:年代依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这是从汲县一座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经束晳、荀勗、傅瓒等整理,有书七十五篇,另“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他们整理的成果,《穆天子传》(包括《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传世至今,《纪年》、《师春》、《琐语》有部分佚文留传。
从现在我们整理研究先秦简帛书籍的经验感受来看,汉晋学者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孔安国的时代,距秦统一文字已久,六国古文早被罢弃,能直接读古文的人也已没有了。孔安国研究孔壁《尚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这种按古文形体结构,转写成隶书的方法,后来通称隶定,是每个研究古文字的人必须使用的。荀勗等整理《穆天子传》,先缮写古文,继列释文,缺字用方框(□)表示,也为古文字研究者共同遵循。
古文书籍的发现,为当时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孔壁中经及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多有不合,酿成今古文之争,结果是古文胜了今文。对古文本身的研究也成为传统,王莽时规定文字有“六书”,第一是“古文”,即“孔子壁中书”;第二是“奇字”,为“古文而异者”。东汉初许慎《说文解字》,也收有“古文”、“奇字”。曹魏正始年间,刻了三体石经《尚书》、《左传》(传文仅刻出一部分),三体为古文和篆、隶。古文书籍影响的巨大,于此可见。
文字方面的古文之学,一直下传到宋代。北宋初,郭忠恕著《汗简》,系按《说文》部首编的古文字典。他用“汗简”作为标题,正因为古文源于历次发现的先秦简书。不久,夏竦对《汗简》补充扩大,又依韵部编出了《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如今已成为大家研究六国文字的重要依据。
二
王国维所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的发现,是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出土百余支晋代木简开始的(注: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文物》1978年第1期。)。在这一类简中,也有少数零星的书籍,但都属于小学字书或者方技小术,学术价值不大,因而没有获得学者们的重视。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帛书。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出版后,讯息迅速遍传于学术界。这可以说是近年简帛书籍出土的真正开端。建国以来,随着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简帛书籍的发现越来越多,在内涵与数量上,均足与历史上的孔壁、汲冢相比美。我们不妨按照新发现简帛书籍的时代,将之分为下列四组:
(一)战国时期的简帛书籍
已见这一时期的简帛书籍,皆出自楚墓。发现最早的,便是上面说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帛书的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子弹库这次发现的帛书,过去多以为只有完整的一件,有900 余字,近来才了解至少还有三四件有残片留存(注: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又收入《李零自选集》,第227~2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批帛书都是阴阳数术的作品,墓主可能是这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最早发现的楚国简书,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 号墓前室所出的一篇。可惜这批简出土时已残断了,虽经整理缀合,只能读释出若干语句。书的性质,多年来被认为是儒家著作,近期始确定系《墨子》佚篇,记有“周公”(西周君)和申徒狄的对话(注: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值得注意的是,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
1987年发掘的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年代与长台关1号墓相近, 所出竹简字体风格也很类似。简数近千支,初步观察约有书五六种,有的很像《吴越春秋》,有的或系兵书。
更重要的发现,自然是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约800支竹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墓主可能曾任“东宫之师”,即楚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的老师。竹简主要是道家、儒家著作,道家有《老子》(包括《太一生水》);儒家有八篇,其中《缁衣》、《五行》等可能即《子思子》。此外,还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20辑。)。
上海博物馆四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据传也出于荆门一带(注:张立行《1200支竹简回“家”》,《大连日报》1999年7 月19日。)。简的内容有书八十几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另外如耈老与彭祖问答,则是论养生的方技书。
(二)秦代的简帛书籍
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1000余支,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秦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其中书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和数术性质的《日书》,而最重要的是秦律、《律说》和《封诊式》,均属法律范畴。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遗留极罕,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睡虎地11号墓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或稍晚一些, 在兼并六国之后,但律文可能在统一之前。1989年冬,云梦龙岗6 号墓又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注: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文字词语的特点看,应在统一之后。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 号秦墓也发现有《日书》(注: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甲种简73支,乙种简380支, 内容同睡虎地的两种《日书》相似。
最近发现的秦简,是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的(注: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这批《易》占性质的残简,经几位学者研究,证明是当时的《归藏》(注: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三)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
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发现较早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 号墓出土的大量竹简,墓的年代为汉武帝初年(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吴九龙《银雀山汉墓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简多残碎,统计有7500余号。经整理,知其内容包含《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等,以兵书居大多数。墓主姓司马,或许同齐地兵家传统有关。
紧接着,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3 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与竹木简(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此墓有明确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 《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竹木简则系房中书。总的说来,以道家及数术、方技占其多数,也应反映墓主的思想倾向。
与马王堆3号墓年代接近的,是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墓主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墓中所出竹简(注: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最重要的是《诗经》和《仓颉篇》(注: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1983年末,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竹简1000 多支(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墓的年代在吕后时期,所以所见汉律多沿秦律之旧。1988年,同地336号墓也出有汉律简,一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的相同,墓的时代则是文帝初年(注:李学勤《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 《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这座墓还出有《庄子》的《盗跖篇》。
(四)西汉中晚期至东汉简帛书籍
这段时期的书籍,较早发现的有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 号墓的东汉竹木简490支,以《仪礼》九篇为主, 余为《日书》之类数术书(注: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3年。)。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木质简牍,内容是医方(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1973年,发掘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晚期中山怀王墓,获得大批炭化竹简(注: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有《论语》(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家语》、《文子》、《太公》等书籍,兼有儒道两家的内涵。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良墓1978年所出木简(注: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陈公柔等《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5 集。),亦为西汉晚期,性质系兵书。
最近的发现,是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6 号墓出土的竹简木牍(注: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其中属于书籍的,有竹简《神乌赋》及《博局占》等。
以上所述,概括了近年出现的简帛书籍的主要内容。有关论著,可参看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注:见《考古学集刊》第2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简牍论著目录》(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日本门田明《中国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注:见大庭脩编《汉简的基础的研究》,思文阁,1999年。),在此不能缕述。
三
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历史上简帛书籍的大发现,像孔壁中经与汲冢竹书,曾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不难想见,近年古代简帛书籍的大量出现,也将对有关学科起明显的影响作用。
这些年新发现的简帛书籍,性质范围非常广泛,对中国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探讨,无疑都会有所促进。我认为,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直接涉及的,是古文字学、文献学、学术史这样一些学科。
发现对古文字学的影响,最为显著易见。
先谈战国文字研究。战国文字,尤其是六国古文的研究,5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热点,成果异常突出。不过,战国文字材料十分繁碎,例如玺印、兵器之类,字数甚少,不易由文例推求。简帛文字成章,有的书籍还能与今传本对照,为考释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由于地下保存情况较佳,现在大家看到的战国简帛书籍皆出于楚墓,这就使我们对当时的楚文字得有更多的认识。然而六国虽说“文字异形”,彼此究竟有不少共通之处,楚文字研究可认为六国古文研究的突破口。同时,古文内又蕴含着许多商周以来传袭的写法,为解读更早的文字充当了钥匙。藉助郭店简《缁衣》释出西周金文“祭公”(注: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文物》1998年第7期。), 通过同批简《唐虞之道》推定柞伯簋“贤”字(注: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都是例子。
秦至汉初简帛的文字,为汉字发展由篆变隶,即所谓隶变的过程的实物证据(注: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过去有关这一文字演变关键阶段的材料太少,致使学者无法详究,现在的情况便全然不同。
在文献学方面,简帛书籍的出现,使我们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例如自战国至汉初,经子诸书简帛,并不因内容性质而有质地尺寸的等级差异。再如好多书籍,因为抄写不易,材料难得,每每只是摘抄,或以篇章单行,出土的只能是整部书的一部分。若干单篇作品,常被编入不同书籍。诸如此类,对认识古书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
了解了当时书籍的这些特点,即可避免以后世著作情况套用于古书的一些成见。30年代余嘉锡先生著《古书通例》,所论种种多可于简帛证实,可惜余先生没有亲见实物的机会。
已发现的简帛书籍,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尤为重大。说古代学术史因之必须重写,是一点没有夸张的。
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的历史许多地方需重新考虑。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的《诗论》,包含若干佚诗,更为值得注意。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郭店简《老子》、八角廊简《文子》等,也深深影响了道家的研究。
银雀山简吴、齐二《孙子》与《尉缭子》、《六韬》等等,为兵家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与此有关的,又有张家山简《盖庐》等。简帛中兵阴阳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未见。
《汉志》数术家书众多,但久已无存,简帛书籍里这一类书填补了这项缺憾。方技类书对中医药史的探索,极有价值,已引起医学界的普遍重视。
秦律及其他法律性质书籍,在法律史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张家山简汉律的公布,估计会引起同样的作用。秦汉律的比较研究,是以前想不到能够进行的课题。
当前,由于郭店简在1998年出版,上海博物馆藏简传即发表,竹简中儒学佚籍的研究,正在形成焦点。揭示和探讨这些书籍代表的孔孟之间儒家的传流演变,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吸引着海内外很多学者共同努力。
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各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简帛书籍发现。我们更希望,对预计可能埋藏有此种书籍的墓葬,组织主动的有充分技术准备的发掘。已获得的简帛,应予以完善的保护,尽快整理公布,提交学术界研究。这对于下一世纪有关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阐扬,将有很大的裨益。
来源:《文物》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