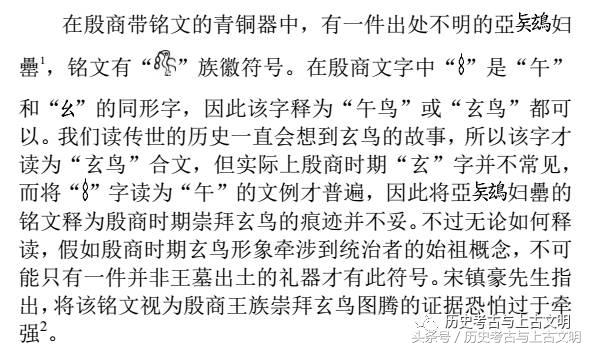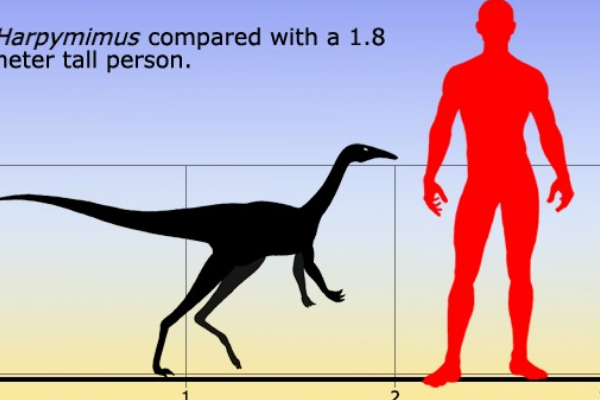宋兆麟:我的民族考古之路
我是在东北农村长大的,受过日伪的气,经历过解放战争。在战乱岁月,农村小学是关门的,学校是停办的。我仅念过一、二年级初小,后来就辍学在家,放牛、砍柴、种地,无论刮风下雨都不能例外。当时我们家参加革命的人不少,是有名的“八路窝子”,家里只有我是年轻的男人,是个“小男子汉”,这时我才懂得“革命家庭孩子早当家”的含义。记得家里养着一头骡子,种地运货全靠它,但后来它得了“肠梗阻”,死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痛。
1949年,解放了,家里被评为下中农,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去辽阳市读了小学和中学。我是穿乌拉上学的,文化上一无所知,土得掉渣,自然让人看不起。但我心里有一股劲:我一定要努力跟上!大概念了三四年书,我就能随“大流”了。1955年,我面临考大学,学什么呢?我思考当时的农村有两大问题:一是怎样解决温饱?根子在农业;二是疾病是农民的最大威胁,无病无灾是农民的最大希望。因此我很想学农业或医药。在大考前1个月,进行体质检查时发现我是赤绿色盲,没有学农或学医的资格,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不得不放弃最初想法。但让我学数学,我又没兴趣,只能改学文科,却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令人兴奋不已。
一、从考古学出发
北京大学有一个未名湖,环境很美,学校又有很浓郁的学术氛围,自己深感处于幸福之中,必须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当时,我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读了很多书,大口大口地汲取文化营养。翦伯赞先生的《汉代史讲演》、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夏鼐先生的《考古学通论》、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苏白先生的《佛教艺术等课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读了一年基础课后,开始分专业。我曾问前来指导专业分类的尹达先生:“我是赤绿色盲,能学考古吗?”他说:“问题不大,你不要学艺术考古,但史前考古还是可以的,又能与民族志结合。”最后我被分配到考古专业。北大考虑到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密切关系,又让我们去民族学院学习,包括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志》、吴汝康先生的《体质人类学》。其实外国的人类学就包括考古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我们的选课,开阔了我们的学术眼界,也为我从事多学科比较研究提供了机会。当时学校很重视社会实践,我们班就先后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史调查和王湾考古发掘,为时一年之久,使我们能把课堂学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很大,需要研究的领域很多,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来说,大有用武之地。
我是学考古学的,又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业务基本对口,但不能专门进行考古,而是侧重利用文物探索中国历史。
在学术研究实践中遇到一个问题,怎么研究历史?尤其是文物或物质文化史。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对我说:“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仅仅一小部分可以解读,还有多数不得其解。”社会上的研究方法,一般是以古代文献复原历史,这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王国维先生提出“二维法”,即利用文献考证文物,再研究历史,这基本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呢?当然有,还有不少呢。有些老一代学者指出,利用民族学资料也可探讨历史文化,这种见解是高明的,但他们没有具体实践的机会,只能留给后来者践行。我虽然踏入学术界较晚,但比较年轻,又具有不少考古学、民族学的知识,使我有机会多做一些民族考古的比较研究,这是探索工作,缺乏前人留下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心里没底,期间也犹豫过:“我能行吗?”还是苏秉琦先生开导了我,说:“你怕自己成了半瓶水,我理解,但你有考古学、民族学两个半瓶水,倒在一个瓶里就满了,单搞考古学或民族学未必能混个一瓶水。”他又说:“目前学术界有‘南汪北宋’之说,这就说明,学术界对汪宁生和你在民族考古研究上是很肯定的,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苏老师一席话,增加了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信心。
我的研究方法基本在考古学研究范围内,考古学色彩浓厚,主要是凭着考古学提出的问题,到民族地区寻找有关民族学答案,去解读考古学的问题,即利用民族地区所发现的“社会活化石”去解读和印证考古学的“死化石”,如石球用法、钻木取火、耒耜之制、织机演变、制陶方法、二牛三夫犁、漆器工艺等。这说明我是从考古学出发的,又落实到考古学上,中间研究也没有离开考古学。但是,有位老师说我离开了考古学,甚至说我是“考古学的叛逆”。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也与事实相左。说事者无非是让我“考古,考古,挖墓掘土”。我没有偏离考古,而是结合民族学来研究考古。
二、做好民族田野调查
要进行民族考古研究,也有相当难度,前提是应该具有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理论训练和田野调查实践,这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我在考古学上接受过专业训练,读过基本著作,参加过洛阳王湾考古发掘,考察过敦煌佛教艺术,但民族学调查仅参加过广西少数民族调查,这方面还有较大欠缺。要想做好学问,一要勤奋,刻苦努力,这一点我是不敢懈怠的,二要有好的机会,否则也难以成功。后来我遇上了一次好机会:1960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翁独健等多位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伯赞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反响较大。专家们提出:“民族地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文物将会迅速消失,建议文物局搜集一套不同时代的典型民族文物,供今天陈列、研究之用。”文物局接受这一点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领导考虑到我年富力强,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又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就让我做上述民族文物搜集工作,从而使我有较好的机会参加民族文物调查和征集工作。
第一次调查地点是内蒙古阿里河,地处大兴安岭西麓,当时正值严冬,不少人都说零下50度,泼水成冰,林海雪原,我爱人又临产,但我没想那么多,一切以事业为重,勇敢奔向大兴安岭。回家时已是春天了,小孩早出生了,爱人挡在门口说:“你说咱们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猜错了不让你进屋。”经过一番曲折,才看见早已出生的女儿。
我的民族调查,分为三种情况:(一)重点调查地区,如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林区、云南西双版纳、滇西北泸沽湖地区、大小凉山和海南省黎族地区。主要工作是征集一套民族文物、拍摄大量民族照片,不仅驻扎时间久——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之久,有的地区去过多次,补充、复查——如泸沽湖、凉山和海南岛。这些是我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地。(二)专题调查地区,如广西左江崖画、岭东南三族风俗、水族石墓、延边朝鲜族等,驻扎时间短,一般调查若干专题,写有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三)走马观花式调查,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江浙等地。主要是跑“面”,扩大视野,增加感性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为了扩大调查泸沽湖摩梭人走婚的来龙去脉,我曾沿他们迁移来的路线,从云南经四川,直到青海,我发现氐羌族南下路上,留下许多共性文化,尤其是象形文字。过去总认为纳西族东巴文字是世上唯一的象形文字,其实在我国西南各民族中都有象形文字,表明我国西南有一条象形文字链,它是我国西部半月形文化的特征之一。
当时田野调查很艰苦。北京到昆明还没有直达火车,中间要改乘汽车。从丽江到泸沽湖要步行11天。从泸沽湖到俄亚村又要步行4天之久。野外露营是经常的事,枕着大地,望着星空,野外生活极为浪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路过彝村,主人给我们烧洋芋吃,我以为这是吃零食,后来才发现这就是正餐,主人天天如此,我们也吃得心安理得了。田野调查最大的威胁是安全,路上遇上棒棒蛇、泥石流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骑马在金沙江边行走,突然一只豹子把马吓惊了,我马上跳下来,马却摔到崖下。在我们路过金沙江边、过雪山时,调查组四个人而伤其三,有一位战友还发生骨折,弄得我们狼狈不堪,这是田野调查难免的代价。
调查地点的选择,讲究人口要多、村落古老、历史文化丰富,又远离交通主干道,所以我们要走很多路,付出各种代价。严格地说,田野调查既是一种科学研究,又是一种危险的探险之旅。
我的民族调查有以下特点:第一,选择典型地区,搜集一套民族文物,如在鄂伦春族地区搜集了上千件民族文物;在西双版纳搜集了上万件民族文物,经过越南才运回北京;在泸沽湖地区搜集3600件民族文物,用40头骡子才运出来;在青海和新疆也搜集了数以千计的民族文物。当时搜集民族文物相当容易,有时伸手可拾。一次在泸沽湖乡政府发现一座仓库,历史文物数百件,全归我们所有。现在,这些珍贵文物都为国家历史博物馆所收藏。前几年,鄂伦春族、傣族和摩梭人要建博物馆,就地找不到文物,于是到国家博物馆复制,扩印照片,使我更意识到当时搜集民族文物具有抢救性,功不可没。第二,有详实的记录,天天做调查笔记,拍摄有关照片,这也是调查的真实记录。第三,调查工作本身是一种研究,事后也要坚持研究,但要结合其他学科资料,并产出专著,如《最后的捕猎者》《女儿国亲历记》《走婚与火婚》《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寻根之路等》。
上述民族地区调查,加深了我对有关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也为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佐证。历史表明,凡是有实践特色的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仅靠文献记载是不够的,前人留给我们的古籍太少了,其作者也未必去过有关民族地区,事实多半是传闻,所以我们不能当书斋式的学者,要身临其境,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搜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我们所调查的民族社会是动态的,尤其在当今转型时代更加如此。当我再访几十年前调查的村落时,发现的当地风俗大改,不少文化现象已经变化,更使我意识到自己收藏的笔记本、老照片的珍贵,于是奋力写成了多卷本《边疆民族考察记》。
三、向民俗学延伸
在学术研究中,深知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有机联系。其实它是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反映,有些少数民族的昨天,就是汉族的前天或大前天,两者之间有不少共性,自然可以利用民族学资料去印证汉族的历史,这就是民族考古研究可行性的依据。在学术研究中还发现,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与汉族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使我回过头来熟悉汉族历史,也关注民间大量存在的民俗文化,这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我退休以后,已失去了民族调查的条件,如经费不足,年事已高,再去新疆“折腾”就不适宜了,但是路途较近有待了解的民俗文化我仍然在坚持研究,也梳理身边的民俗文化,因此,我就把调查的中心从边疆转向内地,从民族学向民俗学延伸。在这方面,我做了三点:一是向老一代学者学习,其中钟敬文先生学问渊博,平易近人,给我指导最多,他表扬我说:“你们的《南宁纳西族母系社会》写得很好。”我们又谈了民俗博物馆筹建的问题。一次,有人建议中国民俗学会设一个文物鉴定委员会,解决来源问题。钟先生问我可行否?我说:“文物鉴定水很深,我们又没有出色的鉴定专家,以此挣钱,还不是骗人?恐怕不行。”钟先生也认为不可,便作罢了。二是认真阅读有关民俗书籍,其中把北京民俗古书列为重点。三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民俗调查,如北京妙峰山、河北龙牌会、蔚县蚩尤传说、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民俗等项目。
在民俗调查中,由于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定的民俗知识,对异地民俗容易了解,很快能进入角色,如生产民俗,多半是自己参加;人生礼俗也是自己多次体验过的;衣食住行与家乡的也大同小异;华北的民间信仰有一定特色,与东北萨满教有一定差别。从中能看到我国各地汉族民俗,有共性,也有地方性。
在民俗研究中,我除了配合多学科研究外,发现民俗学中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节日,它是民俗文化的龙头、中心,几乎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为此我写了《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二十四节气》,前者翻译成多种文字,作为国家礼品送外国外,后者也由台湾地区出版社出版成繁体字版。民俗文化中的民间信仰也很重要,如汉族的巫觋、北方民族的萨满、藏族的本教、彝族的毕摩教,它不仅让我破译了远古时代的巫觋信仰,也促成我从事有关研究,写成了《巫觋》《巫与祭司》《民间神像》《会说话的巫图》等书。我所用的资料,不限于民俗学资料,也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这是沿用多学科比较研究的延续。
还有一点应该提到,我比较重视民俗文物,但我并不收藏民俗文物,主要原因是数量收不起,但在旧货市场又发现不少珍贵的民俗文物。起初看见一位山西人卖六必居老字号文物,我建议他送给六必居,但六必居老板不感兴趣,不要六必居文物,但奖励卖主十瓶酱菜,还给一千元奖金。事后山西卖主找我,说:“人家六必居不要文物,却给了我1000元奖金和10瓶酱菜,本钱回来了,六必居东西就送给你吧!”我留下了,过半年又让学生给六必居送去,人家照例不要,还把我学生撵出来了,让我很心寒。于是写了《无奈收藏》,把上述过程写了出来,表明自己只能无奈收藏北京老字号文物。接着我又收集不少北京老字号文物,有数百件,其中以同仁堂文物最多。收藏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希望日后总有被重视的时候。
四、研究性收藏
一个搞学问的人,晚年是怎样度过的呢?我首先把调查报告、研究成果编辑了一下,总计写了各种著作达500多种,其中专著不下50种。我把上述目录交给商务书局了,听说他们将要出版我的文集。
我的研究范围较宽,总的说是用民族学研究考古学,偏重于文物或物质文化史,但是我的重点是史前文化或原始社会史,为此还写了有关专著,最早为《原始社会》,后来是《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远古文化》和《原始风俗》(中国风俗通史丛书之一)。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工艺技术、人生礼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文献著作。
自己搞了一辈子文物博物馆工作,由于在职时有《文博工作者守则》,自己对文物收藏是不沾边的,但是退休以后就不受束缚了。但是自己有收藏约束:一不介入文物买卖,更不能卖给外国人。记得我收藏一部金箔制的《天地八阳神咒经》,其中有高句丽记载,通过我学生的关系,传到首尔有关博物馆耳朵里,他们来人出高价购买,被我婉然拒绝。特点二是所收藏的范围不是毫无边际,而是专题性收藏,讲究系列,其目的是在研究,最后写出专著来。我最初收藏唐卡,数量多,古品不少,因此编辑成《古代唐卡遗珍》。又收藏一部《金刚经》,由8张纸写成,每张长300厘米,高40厘米,每幅都以楷书写成,极为工整,但每张纸上有3幅佛画,皆为藏式唐卡,因此写一部《辽代插图本楷书金刚经》。有时发现别人有好的收藏,自己也设法写成书。如有一位朋友收藏70多件辽代绣画,经朋友同意,我写成了《辽代绣画》一书。第三个特点是捐献文物,当我把书写完,收藏的使命就完成了,于是把有关藏品捐给国家性质的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已向吉林萨满文化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字博物馆、同仁堂中医药博物馆、六必居博物馆、北京商业干部学院、北京老字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泸沽湖摩梭人文化博物馆捐献了不少文物。
所谓研究性收藏,写书并不是唯一目的,它涉及民间收藏的意义。
我国近几十年的文物形势有很大变化。“文革”前我们文物管理较好,能控制住盗墓之风,当时最好的出土文物基本在考古所、博物馆,我们参观考古新发现到这些单位就行了。改革开放后形势有不少变化,有些公开提出:“要想富,先挖墓。”盗墓者队伍人多势众,比国家考古队多千万倍,而且利用各种现代设备,如汽车、推土机、探测器,更为严重的是,盗墓者与贪腐官员勾结,后者或明或暗介入盗墓,家家屋里都摆许多文物。现在到各地方看考古新发现,只到博物馆、考古所是不够的,但贪腐官员家却能实现“金屋藏娇”。这些又把文物推向市场,流向贪腐之家,有的走私到海外。有一次我在河北邢台,问河北省文物局长:“你们省能刹住盗墓之风吗?”他说:“刹不住,这是全国性问题。”这席话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的当前形势特点。
在这种形势下,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睁着眼睛加以否定,放任盗墓之风不管。市场上自由买卖文物,甚至走私文物到国外,不能任这种情况发展,必须给予制止、法办;另一种,承认其存在,提出积极措施,如对盗墓、贩卖文物、贪官伸向文物界等,给予坚决打击,以法律制裁。应该加强文物鉴定管理,设法规,发鉴定证书,防止冒充专家为非作歹。国家应该加大投资,把市场上的珍贵文物收购起来,对收藏家和私人博物馆进行指导,做好登记,决不能允许有些人以办民间博物馆之行,行贩卖文物之实的行为。对于爱国的收藏家应给予支持、表扬。做好上述工作,是需要大批文物专家的,既然如此,我们把这些专家“藏”起来好呢,还是请他们出来,为鉴定文物、抢救文物作出贡献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国的文物市场是很庞大的,基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某大拍卖公司,以收购鉴定文物为旗号,定期进行鉴定会,来者众多,带来文物也不少,有些是国家应管控的,但主人不以为然,国家文物局又不管,这似乎是隐形文物市场;另一种是诸如北京潘家园、报国寺之类的公开市场。对这类市场,我不轻易否定,而是认真对待,每周都定期去看一下,市场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新动态,这是我学习的大课堂,因为市场上有很多民族文物、民俗文物,有的熟悉,有的是书本上没说过的,如族谱、老文书、旧信札、七巧板、消寒图、年画等等。偶尔也能看见古代文物,如封泥、侯马盟书、陶俑、画像石等。至于旧书摊上的古籍更多。自己虽然搞了一辈子历史、文物,但还感到自己有不少盲区,有不少难以识别的文物,想到这里,就越发感到自己应该再学习,进行补课。潘家园之类的市场是进行再学习的课堂,它能使自己获得不少文化知识,包括学校老师没有传授的文物知识。
关于旧货市场应该说几句话。全国的旧货市场很多,有人说:“这是假货市场,全是假货买卖!”事实是这样吗?不能这么说,要具体市场具体分析。以潘家园旧货市场为例,其中的陶瓷摊、书画摊、玉石摊,公开声称是工艺品,说它们是文物中的假货是可以的,但是其中有两个书摊,除个别有盗版书外,基本都是货真价实的旧书,说它们是假货就太不应该了;在西门内的地摊上,既有真文物,又有赝品,几乎一半对一半,说它们全是假货也是不对的。由此看来,对潘家园的旧货市场,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然否定。由此看来,像潘家园之类的旧货市场,还是可以走动一下的,没准能捡漏呢!事实上,这种真假参半的市场,对于培养文物鉴定家至关重要。有人说“文物鉴定水很深”,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鉴定文物需要较广泛的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物实践经验,既要懂真文物,又要懂假文物,否则是不行的。记得国家文物局在筹建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时,曾去考古研究所找过夏鼎先生,请该所出几名鉴定委员,但夏鼎说:“鉴定文物需要有文物专长,又要懂假物,我们只搞真的,不搞假的,当不了鉴定委员。”因此历届文物鉴定委员都没有考古研究所参加。考古工地培养不出文物鉴定专家,但有真有假的旧货市场,却为文物鉴定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舞台。还有一种现象,那些卖真货、好货的人,一般并不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而是在附近进行交易,这部分往往是真货色。对旧货市场的评价,也应该包括这部分。
我从年轻时代起,就从事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工作,在长期博物馆工作期间,又常常与文物打交道,如鉴定、陈列、研究等,晚年又从事收藏,自然有不少经验、体会和方法,也发生过各种有趣的故事。对此我进行一定的总结,写了有关书籍。一种是理论性的著作——《民族文物通论》;一种是工具书——《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三是古代文物鉴赏、研究性书籍《古代器物溯源》。这些著作说明我对民族民俗文物了解较深,也有些古代文物知识的常识,可以是一个文物专家吧。但我不是文物鉴定家,因为这种工作水很深,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要有文物工作实践,又要懂得赝品的来龙去脉。鉴定起来也各有专攻,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万能文物鉴定专家,水分就太大了,恐怕是假的,或者是名副其实的忽悠家。
来源:《文化学刊》
- 0000
- 0001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