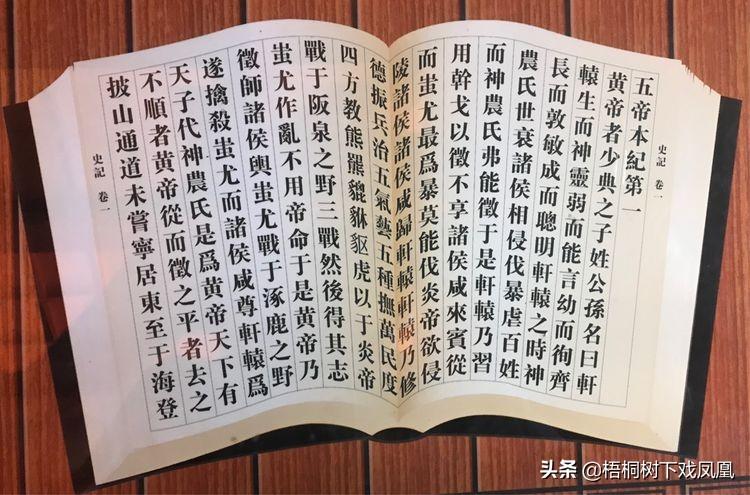李飞:土司,考古与公众——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与思考
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无疑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端地发生,而且随学科专业化的逐步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大众,转而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
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对播州羁縻·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展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依托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本文即拟以之为例,试对公众考古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剖析。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遗址三面环溪,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地势十分险要,《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共传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统领。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平播之役。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1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2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基本廓清了海龙囤的整体格局。经过多年的调查与试掘,现已探明海龙囤有约6公里长的环囤城墙,其所围合的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囤东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五凤楼)六关;囤西有后关、西关、万安三关,彼此围合的空间形成两个瓮城。囤顶平阔,“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其中最大的两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另有军营(俗称“金银库”)、敌楼(如“四角亭”与“绣花楼”等)、校场坝等遗迹。
第二,发现环绕“新王宫”的城墙,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基本厘清了其格局、性质和年代。环“宫”城墙长504米,其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探明其内建筑20余组,并对其中的F1、F2、F7、F8、F9、F10、F11等数组进行了重点清理,出土青花、青瓷、勾头、滴水、石构件、礌石、弹丸、铁铠甲片、石砚台、钱币等遗物上万件。发掘揭示,“新王宫”具有中轴线、大堂居中、前朝后寝等特点,与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献中亦明确称其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新王宫”实质上是一处土司衙署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它是一组明代建筑群,嘉靖、万历时期是其鼎盛时期,最后毁弃于万历年间的大火。
第三,基本确认了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来源。为了解砖、瓦和石料的来源,对海龙囤及其周边展开了针对窑址和采石场的调查和清理,发现民间传说的“采石场”确系一处采石遗迹,清理出采石所遗的各类楔眼上百个,与“新王宫”建筑石材上所见楔眼完全一致。另在“老王宫”东北角发现窑址数座,对其中一座进行清理(Y1),系一座明代砖窑。由此可知,建囤过程中石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均就近取用。
第四,通过调查与发掘,对海龙囤的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特殊时期,坚不可摧的海龙囤是土司的重要军事防御据点;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海龙囤则可能成为土司的别馆离宫。从南宋中期开始,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直便是杨氏统领播州的政治中枢,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龙囤与之并行不悖,前者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为山城,偏重于军事,它们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完备的城邑体系。
发掘的意义表现于:
第一,海龙囤特别是“新王宫”的整体格局与明故宫契合(同时也保存了本地建筑的一些特点),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二,海龙囤是我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换言之,其对推行羁縻之治以来,中央如何开发、经营与管理西南疆,边地又是如何逐步汉化而与华夏渐趋一体等问题的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这处设有衙署的军事屯堡,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羁縻·土司城堡,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点,对中国西南同期以及后来的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海龙囤的发掘可能引发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即将视线从中原的、早期的遗存更多的投向边地的、民族的、晚期的遗存中来,从而拓展考古研究的领域,并可能有益于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发展。
该发掘荣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俗称“六大发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何在这样一个遗址上开展公众考古活动?首先牵扯到我们对“公众考古学”的理解。
多数人将“公众考古学”理解为考古科普。中国考古学的科普工作起步较早,曾以“考古学的大众化”示人,但现在流行的“公众考古学”却是一个舶来品,内涵也较前者丰富。换言之,考古科普只是公众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底何为“公众考古学”?
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所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它将焦点聚集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合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
问题在于,谁是“公众”?他们又如何能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公民集合体,译作汉文,有“公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彼此间有争论并消费文化产品的大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b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译。虽然强调的对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众、考古学家和行政部门这三个主体。公众考古的实践,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围绕着考古资源的最优配置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活动。考古学家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达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通过与民众的合作,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到体现,从而实现其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1]
关系错综复杂,但对考古者而言,公众“这一名词只是方便用来指代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在我们的语境中,‘公众’只是因非专业考古学者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个概念”[2]。具体到某一个遗址中,我们认为除了在此开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外来的考古学家均可称之为“公众”。进而言之,在具体考古活动中,凡发掘团队与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众”的互动,均属公众考古的范畴。此时,开展考古活动的遗产地就变成了“交流”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场域,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适当满足。被视作公众考古学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3]均在此场域中得以呈现。相对于博物馆、陈列室等传统展示渠道,考古现场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的考古现场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域。借配合“申遗”而对海龙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机,经过周密的筹划,我们在海龙囤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为遵义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龙囤,因为与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关系,对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都充满诱惑,这是相关活动能顺利开展、各方利益得以体现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遗”背景下开展的,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到考古活动中来。汇川区人民政府通过专题会议、现场办公、文件等方式,极力推进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行政部门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体现。而针对专业化和公众直接参与的不和谐,我们则通过讲座、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得到部分满足。
首先,在中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策划了“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的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于6月10日文化遗产日当天,邀请著名学者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聆听海龙囤”的大型学术讲座,并从听众中产生70余名幸运者,于次日与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现场“触摸海龙囤”。此后又组织了黔籍知名画家进海龙囤,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摹400年前的土司生活的“画中海龙囤”活动;组织遗址所在地的高坪镇中小学生将课堂搬至考古现场的“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以及与遵义市政协共同组织了政协委员参观考察与文艺演出相结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遗”的活动。当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了全国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学家亲赴海龙囤,并召开现场座谈会,请他们为海龙囤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出谋划策,此举在“交流”中实现了海龙囤价值于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说“聆听”只是一个引子,其后开展的“触摸”则是活动的重点。包括外来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通过现场的观摩与体验,对海龙囤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相关感受又通过他们传达给更广的“公众”。
但能到现场“亲历考古”者毕竟少数,如何进一步调适专业化发掘与公众参与的不和谐?无疑,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互动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在“亲历考古”活动之外,我们与媒体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使海龙囤的最新发现得以及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尽可能满足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从“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利用和专业研究者的提高性利用”两个方面展开:前者是报纸、网络、电台及电视台的记者在田野一线采写稿件,在相应的媒体持续刊播;后者则是发掘者亲自撰写“考古手记”,对相关发现作出权威解读,在当地媒体连续刊登。其广度、深度及长度,贵州此前所未有;所取得的社会影响也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发掘期间及获奖前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媒体共推出关于海龙囤的各类报道140余篇(则),曾三上央视、三上“贵州新闻联播”、数次登省内媒体头版,并有多篇深度解读海龙囤考古的大版块文章,使海龙囤的最新考古成果得以迅速呈现在公众面前,甚至出现读者收集“考古手记”登囤请教的插曲。
国内外近百家媒体通过报刊对海龙屯的考古发掘进行了报道;海龙屯声名鹊起,成为国内外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而基于考古发现的专题学术讲座,实现了另一个渠道的传播与互动。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及发掘结束以后,我们在海龙囤、遵义、北京和贵阳举行了多场面对不同听者的学术演讲,广受好评。如9月22日,应遵义“名城大讲坛”之邀,在遵义市图书馆举行《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的专题学术讲演,数百名听众出席。10月16日,在“中国海龙囤·娄山关国际户外挑战赛”举行期间,在海龙囤巅向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北京等地的约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讲述海龙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上发表《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发掘》的学术讲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与社区居民和大中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受到普遍欢迎。
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现?相当部分当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事实上的“亲密接触”。部分村民则长期在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都是考古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此外,发掘期间,针对当地村民的贫困状况,我们联合媒体通过微博发起“考古探秘 公益慈善”活动,使城市中人在进行海龙囤考古探秘的精神之旅的同时,也能对当地贫困村民予以捐助。这一活动被新华社等媒体誉为“走出文化扶贫新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当地村民写诗传扬此举,称“杨雀记得千年树,乞丐记得贤惠人”。我们相信,当地政府会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诉求,未来海龙囤“申遗”一旦成功,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贵州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考古实践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为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该书在传统考古报告里开设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相关章节的内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话”的环节,使其晓畅易读[4]。这一尝试引发了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先后有约10篇书评公开发表。贵州省文物局从2011年开始策划的“贵州文化遗产丛书·考古贵州系列”,计划推出解普及性读物8本,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丛书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预计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这两项实践,应属“考古科普”的范畴,无疑也是公众考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以考古现场为依托,开展深度的、广泛的公众考古活动,海龙囤开贵州先河。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对慕名而来的大批游客未能有效疏导,使其有“亲历考古”的现场体验。再如对公众考古活动开启“民智”后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考虑和安排不多。对于后者,我们曾有过惨痛的教训。通过广泛的互动,不法者一旦认识到遗产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便可能受利益的驱使而对其采取恶意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在“打开天窗”前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公众考古遗产地,因此也需作充分的考虑和慎重的选择。否则,所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盗墓指南”。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公众考古亦不例外。好在海龙囤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活动才刚刚开启,我们的公共考古实践也才刚刚起步,尚有时间对不足之处予以改进。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贵阳)2014年第1期,第103-107页。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