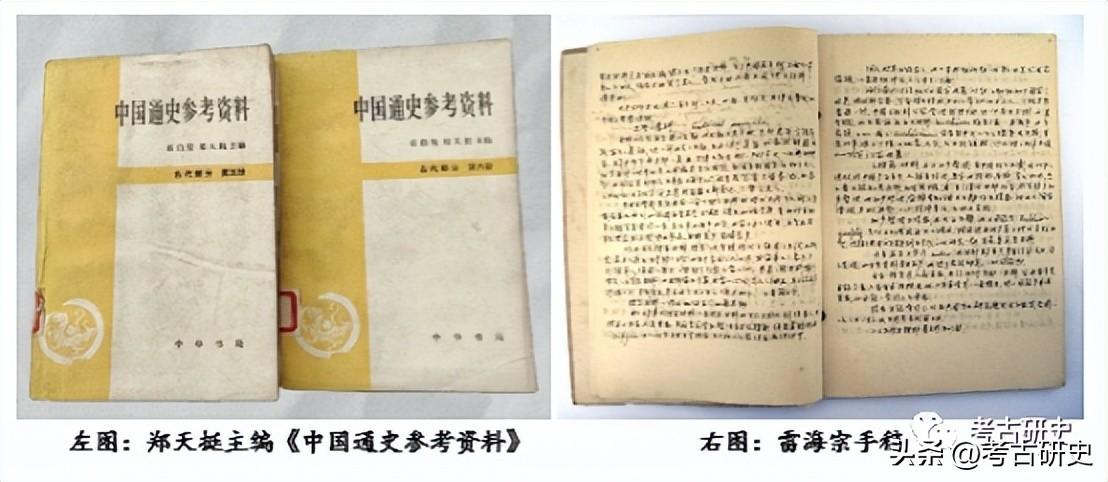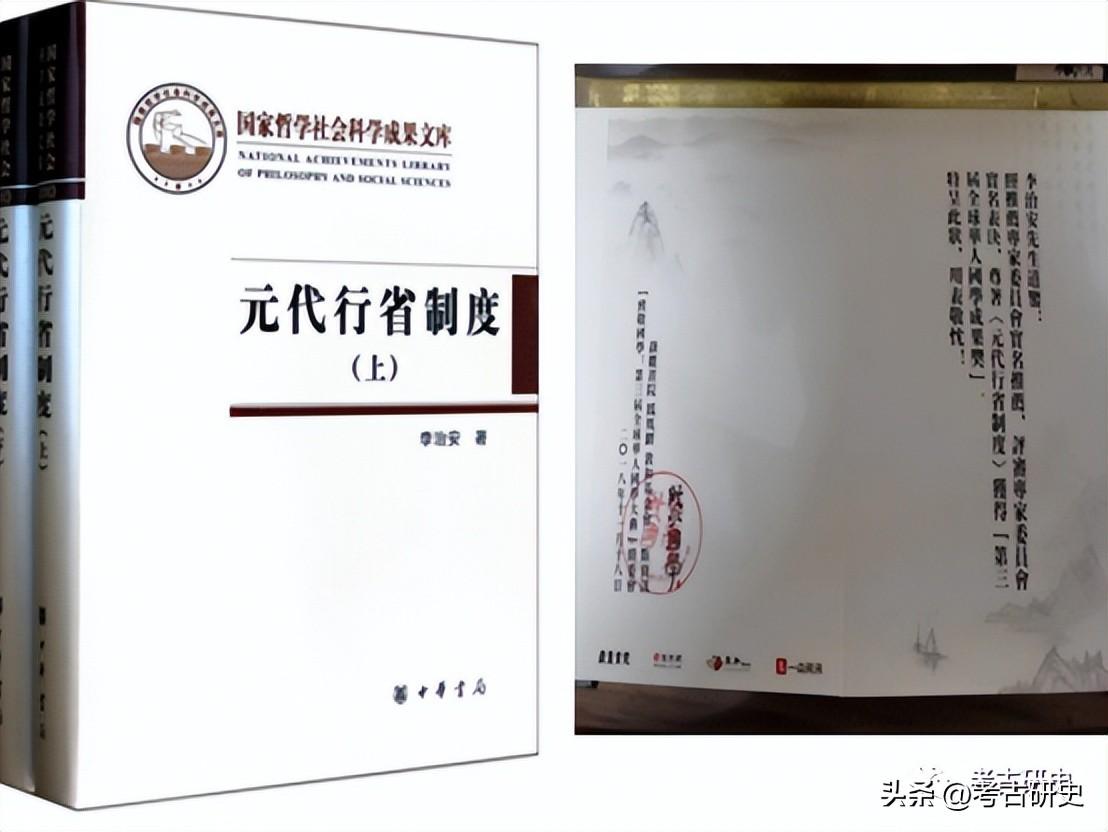李梅田:从考古志到考古学
一 考古志与考古学
1988年,美国历史考古学创始人狄兹(James Deetz,1930-2000)在纪念泰勒(Walter Taylor)的学术成就时,讨论了编年史、民族志与考古学的关系,第一次提出“Archaeography”一词,意指对古代实物遗存的客观记录与文化描述,类似于历史学家所做的编年史(historiography)、民族学家所作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它们分别是根据文本、民族志材料和古代实物材料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是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而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则有赖于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如历史学(history)和以“logy”(有“理性思辨”的涵义)结尾的ethnology(民族学)、archaeology(考古学)等①。
次年,狄兹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第一次美国考古学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针对当时各种考古学理论杂陈纷争的现象,重申了“Archaeography”一词的涵义:“至于Archaeography,我指的是基于地下或地上实物资料的文化描述,类似于民族志的描述。它与研究文化整体的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正如民族志与民族学一样。”他进一步解释,虽然实物资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进程是历时的(diachronic),但实物本身都是共时的(synchronic),在研究文化进程之前必须考虑实物的共时状态,因此,考古学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以获取共时的田野资料,如果是历史考古学家,还需要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与文献,这些工作的成果是未来进行人文或科学阐释的基础②。
“graphy”意指记录,根据狄兹的解释,不妨将archaeography译作“考古志”,它与考古学(archaeology)之间的差异类似于民族志(ethnography)与民族学(ethnology)、图像志(iconography)与图像学(iconology)。在这几个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里,民族志是通过田野方法,对特定民族(人群)的观察、参与、记录与文化描述,从生活方式、经济关系、家族制度、宗教仪式等方面理解该民族的整体概貌,而民族学是对若干民族的全面比较和综合考察,研究民族的发展进程及文化的运作方式。图像志着重对图像的描述和分类,以揭示某种母题在特定时空中的呈现方式、题材和意义,而图像学则是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对图像内涵的综合阐释,以揭示图像的发展演变进程及原因。
显然,以“graphy”结尾的考古志、民族志、图像志和以“logy”结尾的考古学、民族学、图像学的差别是:前者着重于个案的文化描述,从共时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社会;后者则强调文化的比较和综合的阐释,从历时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狄兹提出考古志与考古学之别,主要针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重理论方法而轻个案研究的现象,当时以新考古学为代表的各种考古学理论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因提出新的理论而“著名15分钟”,但“每个人的可信度只能持续30分钟”③。他认为考古志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理论方法都必须始于共时的文化描述,然后才是历时的文化阐释。
中国考古学的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丰富的考古遗存和深厚的金石学和史学传统孕育了重实证的中国考古学,但也缺乏综合阐释和理论建树。正因如此,中国考古学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作为历史学的附庸而存在,主要为史学研究提供辅证,在进行综合的文化阐释时往往力不从心,这个特征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尤其明显。目前中国考古学已经有了丰富的资料积累,也依靠实物资料建立了粗线条的编年体系,重提考古志与考古学概念,或有助于明确考古研究的途径与方向,让考古学有意识地迈向综合的文化阐释阶段。
考古志与考古学可以视为考古研究的两个层次:考古志是第一层次,是考古研究的基础,是整理和分析材料的手段,包括资料的获取与整理、定性与定量分析、年代和文化属性判断、时空谱系的构建等,是一种较为机械而客观的材料处理过程,带有自然科学的性质;考古学是第二层次,是考古研究的目标,是将实物资料与人类行为模式、思想观念的联接,是对文化进程的综合阐释。只有当考古志成果积累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借助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史等学科的方法,才可能从历时的角度思考人类行为和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这是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的最终目标。
其实关于考古学的层次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的定义里早有明确表述。1984年夏鼐给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不应限于古代遗物和遗迹的描述和系统化的分类,不应限于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确定它们的用途(即功能),历史科学应该是阐明历史过程的规律。”④夏鼐明确提出考古研究不应止步于考古志的研究,而应“阐明历史过程的规律”,即历时的文化阐释;对这种规律的揭示也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而是“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Societal或Social archaeology),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⑤。夏鼐将考古学的目标明确为历时的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同时强调考古学应揭示观念、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
在中国考古学著作里,极少以“考古志”自称,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做的考古工作曾被编写为《台湾考古志》⑥,主要是对台湾史前遗迹发现与发掘情况的记录与描述,类似于当今的考古报告。虽然也有对文化的分期研究,但仅限于对个别文化现象的讨论,基本上属于共时的研究,并没有综合的分析与归纳,没有对整个台湾史前文化的进程进行阐释。这样的考古志有些类似于正史里的蛮夷志、天文志、地理志等,侧重于记录,而不涉及文化进程的阐释,尤其不涉及思想观念等精神文化领域的探究,因此,它只是考古志,而不是考古学的研究。
在中国考古学近九十年的发展历程里,大部分工作属于考古志的范畴,从考古调查、发掘到类型学分析、对特定考古学文化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对图像的描述与阐释等,都是以共时的视角观察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所揭示的只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点或一个片段。只有当考古资料积累到相当丰富的程度,或当考古志的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时,才可以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归纳、综合和文化进程的阐释,才进入到考古学的研究。
在中国史前考古里,经过了考古志范畴的资料积累、文化属性研究、区系类型研究,建立起了基本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开始了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来阐释文化进程的研究,如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的苏秉琦文明起源研究⑦、当今如火如荼的早期国家形态研究⑧等,即是超越了考古志范畴的具有历时意义的考古学研究。
二 历史时期的考古志与考古学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起止年代一般指从商代至清末,即有文字以来的古代历史,这个时期的考古研究比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要复杂得多。强大的政治因素、曲折的历史进程、复杂的社会现象决定了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杂性⑨,使得历史时期的考古志和考古学研究之路更加复杂。
(一)从考古志到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考古研究有着明确的重建古史的目的,如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所作的“夏墟”探索工作、1928年在傅斯年倡导下开始的殷墟发掘等,都是为了重建夏、商的历史。由于中国考古学孕育于深厚的金石学和史学传统,也由于顾颉刚“古史辨派”疑古思潮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证史、补史重任,即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正如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⑩,考古学家扮演了史料建设者的角色。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初期,确实取得了很多令历史学家兴奋不已的成果,如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西北汉晋简牍等,但在当时学者看来,这些出土文献与内阁大库之元明档案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证史和补史的新材料,如王国维所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11)。考古新发现不过是增加了向所未见的新史料,或加深了对历史某一点或某个片面的认识,还无法以实物资料建立独立的编年体系,远不足以进行历时的文化阐释,因此只能是考古志的研究。
带有证史倾向的考古志研究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中国考古的主流,无论在实际考古发掘中,还是室内的研究中,都以获取新材料为目的,如最初的殷墟发掘就是以寻找甲骨为目的,青铜器的发现已令学者们喜出望外,他们对其他遗迹或遗物无暇给予更多关注,以致出现了重文字而轻实物、重贵重品而轻普通品、重遗物而轻遗迹、重物质文化而轻精神文化的现象。证史倾向使得中国考古研究长期无法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而停留在考古志阶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陶鬲进行研究,根据陶器的造型和纹饰进行分类,分析了殷商、先周、先秦文化的渊源问题,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王国维等所持的殷、周、秦不同源而自成体系的推想。尽管苏秉琦的工作仍有证史的倾向,但已摆脱了对文字材料的依赖,仅从器物本身的形态演变规律推定文化的发展轨迹,1948年发表的《瓦鬲的研究》标志着类型学的成熟,是以考古所获实物研究历史进程的重大突破,可以称得上是考古志向考古学的升华(12)。
1949年以后,全国范围的考古发掘逐渐展开,考古材料迅速积累,对不同类别实物材料的考古志研究也在深入,考古学方法论也在缓慢地进步,取得了很多历史考古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陈公柔、徐苹芳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他们将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500多枚简牍进行了考古学分析,结合《汉书》提供的居延屯田线索,全面论述了汉代在居延屯田的史实,超越了传统史学对于汉代边塞制度的考证(13)。此外,俞伟超和高明关于周代用鼎制度(14)的研究、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历程的总结(15)、宿白关于隋唐两京布局的讨论(16)、鲜卑遗迹的考察(17)、云冈石窟发展的进程(18)等,都是基于考古发现对文化进程的阐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历史时期各类别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
(二)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结合
苏秉琦以类型学为主要内容的陶鬲研究虽然摆脱了对文字材料的依赖,但仍以历史文献记载的殷、周、秦族源为线索,研究结论也需考虑与历史学的结论相符。陈公柔、徐苹芳、俞伟超、宿白等对汉代屯戍历史、周代用鼎制度和楚文化、鲜卑遗迹、城市发展史、石窟艺术的研究,也都是在历史学提供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对文化进程的阐释也要大量借助历史文献的记载。
考古实物资料是通过一套特殊的科学方法获得的,各类实物遗存之间是彼此联系,又有规律可循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比,不但更真实,也更具体;但是考古资料的获得带有很强的偶然性,资料又是残缺和片面的,并不能直接解释文化发展的进程,但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制度变革等史实能为我们提供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大量的史学研究成果也能防止我们对考古材料的阐释误入歧途。
此外,考古学一直不断地在为史学研究提供营养和拓宽视野,殷墟的发掘、陶鬲的研究将地下新材料从文字扩展到非文字;居延汉简的考古学研究不但充实了历史学所重的屯戍制度史研究,而且从埋藏环境和各类遗存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更全面的汉代西北屯戍史信息;对用鼎制度的考察廓清了《周礼》所记制度的模糊不清,通过用鼎随葬的实际情况阐明了周代礼崩乐坏的具体进程;通过隋唐两京城市布局的研究总结了城市形态演变的规律,将对都城史的关注扩展到普通城市;石窟寺的考古学研究扩展了历史学和美术史的佛教美术研究视野。
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推进了历史学的研究,不但重建了古代史的时空框架,也扩宽了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开启了古代史研究的无穷天地,“将来杰出的古代史研究,恐怕非要建筑在考古学之上不可”(19)。
对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来说,考古与历史的结合是基本的方法论,无论是个案的考古志研究,还是综合的考古学研究,需要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考古材料与文献的互证,考古研究和与史学研究的互补。
(三)历史考古的分区与分期
编年史学(historiography)主要解决历史发生的时间性问题,历史地理主要解决历史发生的空间性问题,二者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历史时期的改朝换代和行政区划虽然能够提供基本的时空框架,但它只是粗线条的,更何况传统史学向以华夏为本位、以中原为中心,所描绘的古代社会时空框架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古代社会。当考古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考古志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就可以依靠实物资料来构建基本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如史前考古研究中,苏秉琦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区系(20)、严文明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旱作、稻作、狩猎采集三大经济文化区(21),构建时空框架是进一步的文化阐释的基础,“是考古家送给古史学者的大礼物……借由各种文化类型的内涵,史家不但可以重建古代各地区的文化史,也可以认识各族群的文化交流”(22)。
依靠实物资料构建时空框架,不但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综合研究的必由之路,否则历史考古研究只能局限于正史所记的改朝换代和行政区划的时空框架内。
构建考古遗存的时空框架即分区与分期研究,它是由考古志转向考古学的重要阶段,主要是对实物遗存的共时性归纳。我们虽然无法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墓葬、器物、图像、石窟寺、古代建筑等进行分区研究,但它们都是某个时期特定的政治因素、地域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可以参考正史相关志书的记载、历史学研究成果,来构建较为可靠的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分区体系。例如,在做西汉墓葬分区时,可以参考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地理志》根据经济、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所作的文化分区,墓葬分区的结果与古人文化分区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23)。
今人的史学成果同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志研究不可忽视的学术基础,如周振鹤复原了西汉二百年间郡国一级置废离合的全过程,认为西汉初期东部十王国与西部十五汉郡之间判然有别,武帝之后在西南、西北、岭南、东北新扩的疆域又自成独立的体系(24),这些成果不仅是做西汉诸侯王墓考古志研究的参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汉区域文化的动态变迁过程。
分区研究是考古志研究的高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文化的分期研究,以阐明文化的发展进程,迄今历史时期考古资料较为丰富的时代(如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已经基本完成了考古的分区与分期工作,主要年代和地区的时空框架依靠实物资料得以构建完成(25)。但是目前大多数的分区与分期研究都是侧重于物质文化方面,很少涉及精神文化领域,还无法对实物遗存反映的人类行为和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做出系统的阐释,离考古研究的第二层次——考古学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
要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人文学科,仅仅探讨物质文化是不够的,而应充分吸收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研究途径上不仅仅是实物与文献的互证,也应该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互补。
三 以“晋制”为代表的墓葬考古学
墓葬是历史时期最丰富的一类考古材料,墓葬研究也经历了由考古志向考古学的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情况。
迄今大多数墓葬研究都属考古志研究,如对墓葬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判断、对随葬品和图像的考释等,墓葬文化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虽然是历时的研究,但主要是研究墓葬所代表的物质文化,大多不涉及丧葬礼俗、丧葬观念等精神文化的层面,因此也是考古志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分区与分期研究为代表的考古志研究逐渐完成了一些主要时期和地区的墓葬物质文化时空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的考古学阐释也逐渐展开,研究的重心经历了由丧葬礼制向丧葬观念的转变。
关于墓葬的考古学研究,较长时期里偏重于丧葬礼制,这是受传统史学的制度史倾向影响所致。杨宽对陵寝制度史的研究(26)、杨树达(27)对汉代丧葬礼俗的研究多以正史的礼仪志为主,考古材料为辅。传统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了丧葬礼制演变的脉络,但对于丰富的考古成果并没有充分吸纳,尤其对“礼制”所不及的中小规模墓葬缺乏关注,未能完整地反映“礼”外之“俗”。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学者试图从制度的角度来阐释墓葬的变迁,俞伟超1979年提出的“周制”、“汉制”、“晋制”三段论成为近四十年墓葬考古研究的圭臬(28),出现了大量关于墓制研究的成果,其中对“晋制”的讨论尤为热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墓葬考古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俞伟超对墓葬形制的阶段性演变进行了极好的概括,符合墓葬营建的基本规律,迄今发现的大量周代至魏晋墓葬基本上可以涵盖在这几个“制”里,新出土的材料也没有改变俞伟超的结论,只是让它更加丰满和充实。但俞伟超对墓葬形制变化原因的解释过于单一,如以墓葬形制比附宫室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了墓制形成和演变的原因等,这种对“事死如生”观念、历史唯物观的简单套用,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韩国河认为晋之新礼是对汉代礼仪的传承与创新,晋制的创新性具体表现在“不树不封”等薄葬制度、凶门柏历之制、新的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墓葬形制的单室化、明器组合的变化等。他认为晋制较之汉制,在等级性、礼法性上更为突出,并认为这种差异与汉、晋社会等级观的变化有关(29):“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降,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30)他对晋制的总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魏晋墓不如汉墓那样等级森严,是由于当时的门第观念盛行而士庶有别,但高门士族内的等级差别并不明显。韩国河还从实物上追溯了晋制的来源,认为墓葬形制和葬俗源自中原地区的曹魏墓,但东吴墓中的很多随葬品也被中原接受,如多子槅、牛形镇墓兽、牛车等,都成为晋制下的典型器物组合(31)。
杨泓在总结了汉晋厚葬与薄葬的具体表现后,认为葬俗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信仰的转变,汉代黄老学说和魏晋佛教的传入对汉、晋埋葬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32);吴桂兵认为晋制的产生与晋制新礼有关,东晋以后在各地发生了不同的流变(33);刘斌将考古学上的晋制归纳为五个方面:不树不封、墓室由多室向单室转化、土洞墓在高等级墓中使用、以牛车为中心的明器制度、墓志的出现,认为晋制产生的原因有经济因素、礼制变迁和玄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34)。
霍巍从墓葬装饰中的瑞兽题材嬗变讨论了汉制向晋制的转换,认为晋制的表现之一是以狮子为代表的瑞兽题材取代汉代以四神为代表的瑞兽系统,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丝绸之路开通后西方因素的传入、佛教思想的渗透、汉晋玄学的影响等,这种变化渊源于东汉,定型在南朝刘宋之后,最先在南朝帝陵和高级贵族墓葬中开始流行(35)。
学界对“晋制”的讨论可说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里少有的集中主题,除了对其实物体现进行了或详或简的归纳外,还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与文献记载的简单比附,并没有在考古实物与具体的丧葬行为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不过,从俞伟超提出三段论至今,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丧葬观念对具体丧葬行为的影响,这将墓葬研究从物质文化推进到了精神文化层面,从考古志向考古学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齐东方注意到唐代政治社会变迁与唐代墓葬变化之间的不尽合拍现象,主张要打破王朝更替对考古研究的桎梏,墓葬研究未必要拘泥于政治上的断代王朝,而应深入到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的层面来解释墓葬的变化。只有结合观念习俗和礼仪制度的分析,才可能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36)。他同样将丧葬观念视为讨论“晋制”的根本,提出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和丧葬制度四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是由丧葬观念产生了丧葬习俗,丧葬观念和丧葬习俗的结合提升为一种系统的阐释,成为礼仪,再进一步发展为强制性约束的制度(37)。齐东方对丧葬观念的重视已经大不同于俞伟超对经济基础的强调,代表了墓葬考古研究倾向的转变。
《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38),“如死如生”(或“事死如生”)常被用来概括中国古代的丧葬观念,但它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生死观与千差万别的丧葬行为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宏观的思想史背景来讨论生死观的演变及对丧葬行为的影响。
在墓葬研究从考古志向考古学转型的过程中,美术史的参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美术史家将墓葬视为美术史的一个亚学科,不仅关注墓葬图像,也同样重视与图像相关的墓葬建筑、随葬品及彼此之间的关系(39)。这与传统考古学者对于墓葬的看法基本相同,但美术史将墓葬视为一个整体的礼仪空间的做法,可能比传统考古学更易于解释墓葬设施与丧葬行为的关系。在这方面,黄晓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她从祭祀礼仪的角度来解释汉代墓葬结构的转变,认为祭祀方式在墓葬空间配置上起了决定性作用(40)。
墓葬里的图像在传统考古里是被作为与墓葬形制、随葬品一样的材料来看待的,常被冠以“墓葬装饰”,即墓葬建筑的一部分来看待,研究方法也主要是题材、布局的类型学研究,目的也是为了分区、分期服务,还是属于物质文化史的范畴,最多涉及一些丧葬礼制的问题,如墓葬规模与墓主身份等级的问题。但以巫鸿为代表的美术史家从空间、礼仪、观者等概念来解释墓内设施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将墓葬看作一定礼仪行为的结果,是生死观的再现(41)。
郑岩在墓葬研究中也非常重视空间、仪式等因素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他从生死观的角度来理解墓葬的功能,认为墓葬“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之下,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结合着相关仪式所构建的诗化的‘死后世界’(至少是其一部分)”(42)。
与考古学家重物质文化不同的是,美术史家似乎更希望通过墓葬构建一部观念史,即从丧葬、祭祀等礼仪方面探索古人生死观的进程,这其实也是墓葬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它是超越了考古志范畴的考古学研究。
巫鸿将汉画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低层分析是对单独图像的考释,高层分析是宏观汉画的发展及与社会、宗教、意识形态的一般性关系,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对特定图像程序的研究,即中层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揭示一个墓葬或享堂所饰画像的象征结构、叙事模式、设计者的意图,及“主顾”的文化背景和动机(43)。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所谓汉画的低层分析和中层的图像程序研究都属于考古志,高层研究属于考古学。
墓葬是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于一体的古代社会缩影,墓葬研究既不应满足于年代、墓主、等级、图像内容的考证,也不应止步于物质文化的探讨。在当前墓葬资料已经相当丰富、学科之间彼此渗透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已有可能将墓葬研究推进到丧葬模式的总结和生死观的讨论。
四 结语
考古学是以出土实物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古代社会面貌和人类行为模式的学科。将考古研究分为考古志和考古学两个层次,目的在于明确考古研究的任务,即揭示人类行为模式的规律和思想观念的进程,这是作为人文学科分支的考古学的最终目标。
虽然历史时期考古比史前考古更加复杂,但通过与历史文献的互证和多学科的互补,它在考古志的研究阶段更具优势;文化的分区与分期研究是考古志研究的高级阶段,也是进行综合性考古学阐释的基础。墓葬是历史时期最丰富的材料,考古学者通过对“晋制”的讨论,逐渐重视丧葬观念对丧葬行为与丧葬制度的影响,将墓葬研究从物质文化推进到了精神文化层面,从考古志向考古学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术史家从祭祀、观者等角度探讨礼仪空间的做法也为墓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①James Deetz,“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Theory:Walter Taylor Revisited”,American Antiquity,Vol.53,pp.13-22,1988.
②James Deetz,“Archaeography,Archaeology,or Arche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93,pp.429-435,1989.
③James Deetz,“Archaeography,Archaeology,or Arche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93,pp.431-432,1989.
④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页931-934。
⑤前揭《什么是考古学》,页932-934。
⑥[日]金关丈夫、国分直一(谭继山译):《台湾考古志》,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
⑦俞伟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页1-1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⑧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⑨徐苹芳对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区复杂性的讨论,实际上也阐明了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复杂性:一是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是历史发展更加曲折、社会现象更加复杂。参见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页82。
⑩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1分,1928年。
(11)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页3,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的研究》页1-18,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
(13)陈公柔、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60年第1期,页45-53。
(14)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页84-98;1978年第2期,页84-97;1979年第1期,页83-98。
(15)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17-30。
(16)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页409-425、401。
(17)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页42-54;《盛乐、平城一带的拓拔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页38-46;《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页42-52、100。
(18)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页25-38。
(19)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论的探讨》,《考古》1992年第4期,页343。
(20)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页10-17。
(2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页38-50。
(22)前揭《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论的探讨》,页337。
(23)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页86。
(2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页20,人民出版社,1987年。
(25)这方面的研究如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页19-44;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页147-184;黄佩贤:《汉代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页74-80、98;李梅田:《魏晋北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6)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7)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页117-124,文物出版社,1980年;《魏晋墓制非日本古坟之源》,俞伟超在此文中根据新发现的魏晋墓葬,进一步完善了“晋制”的论述,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页359-369,文物出版社,2002年。
(29)韩国河:《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文史哲》1999年第1期,页31-36。
(3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幸传》,页2302,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31)韩国河、朱津:《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页53-62。
(32)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1999年第10期,页60-68。
(33)吴桂兵:《晋代墓葬制度与两晋变迁》,《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页58-63。
(34)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页70-83。
(35)霍巍:《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015年第2期,页103-113。
(36)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页71、78。
(37)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页346。
(38)(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礼论篇》页366,中华书局,1988年。
(39)巫鸿:《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读书》2007年第1期,页59-67。
(40)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页92,岳麓书社,2003年。
(41)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的再思》,载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页101-122,三联书店,2005年。巫鸿其他关于墓葬的论述,参见《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之中篇为“观念的再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2)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代前言)》,载《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页1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3)巫鸿:《汉画读法》,载《文化的馈赠·考古学卷》页18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