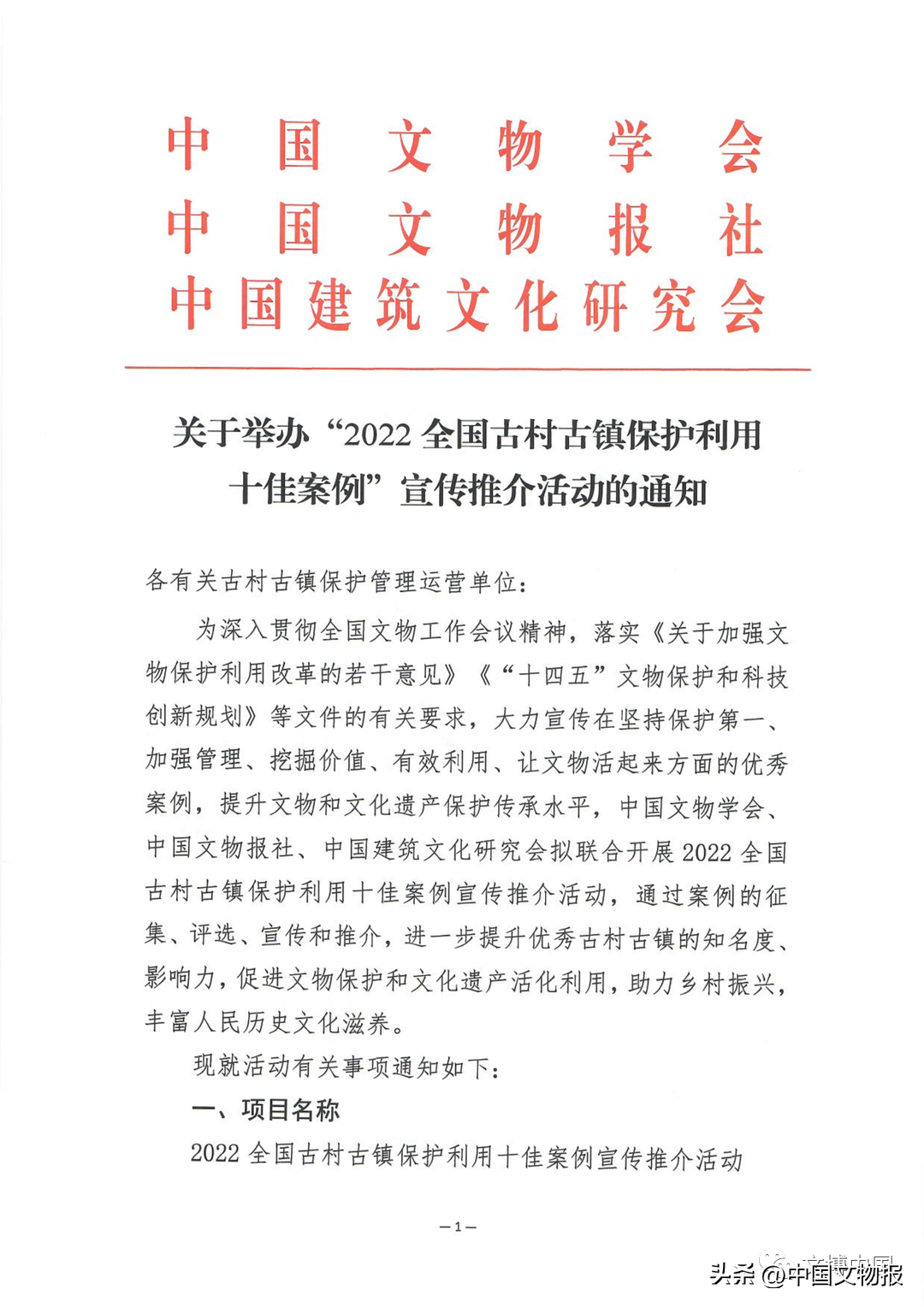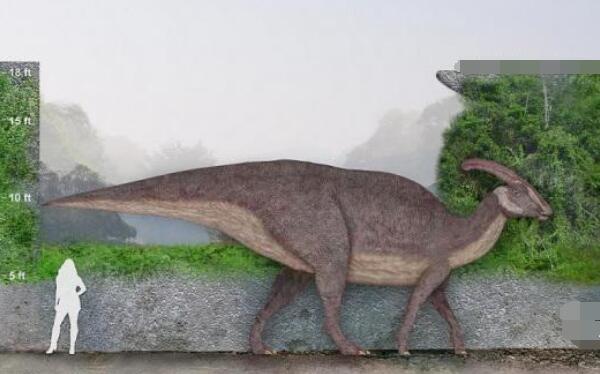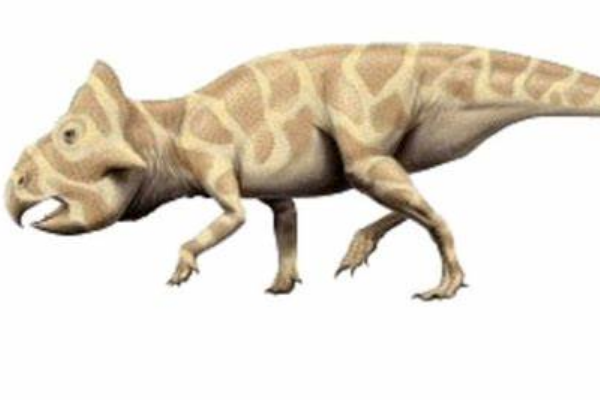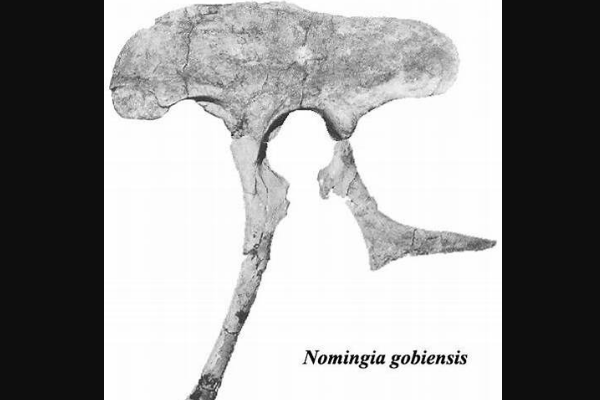朱乃诚: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对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座大型“祭祀坑”及一大批精美而奇特文物的高度赞誉。这一发现,展示了商王朝区域以外的一处最为辉煌夺目的方国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探索古蜀文明最为重要的资料,也是探索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最近,通过对三星堆遗址两座“祭祀坑”附近的再次发掘,又发现了六座“祭祀坑”,已经清理出土的大型金面具、大型青铜尊、玉琮与玉戈、象牙以及象牙雕刻作品等珍贵文物,再次放射出惊醒世人的光彩。
三星堆遗址的这一系列重大发现,显示三星堆遗址曾承载着一个经充分发展的文明社会,即“三星堆文明”。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性质、文化特征、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学科共同探索的系列重大课题,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以2019年及以前的学术刊物公布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资料为基础,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以期对三星堆文明的认识有所裨益。
一、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的高档次文化遗存及其年代分析
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自然不能简单地以已经发掘的两座“祭祀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座“祭祀坑”的年代作为探索的主要依据,因为这些坑是三星堆文明后期的遗存,而是应以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或最早一批能够反映三星堆文明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作为探索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能够反映其文明已经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主要有:发现于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类遗迹、三星堆遗址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一座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座坑、月亮湾仓包包一座坑类遗迹、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地、三星堆城址城墙、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存等。这些遗迹及其遗物是否为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或最早的一批遗存,需要仔细分析甄别,下面就对这些遗存进行逐一分析。
(一)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
1929年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发现的玉石器坑类遗迹,出土玉石器数量达三四百件之多。后来大多散失。华西大学博物馆于1934年3月在燕家院子门前太平场水沟处进行首次考古发掘,从发现者燕道诚及收藏人处受赠收集玉石器数件。1951年、1957年、1961年四川省博物馆先后三次征集了部分玉石器。后冯汉骥对1929年的发现进行了多次查访,并对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3件玉斧(锛)、3件牙璋、3件玉琮、3件有领玉璧,以及数十件石璧进行了专题研究。1994年陈德安公布1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可能是1929年出自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的牙璋。2017年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十多家单位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中,汇集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展出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出土的玉器19件,其中牙璋6件、玉斧(锛)3件、玉琮5件、玉璧2件、有领玉璧3件,并公布了彩色图片[1]54-150。这批玉石器的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制作年代也有区别。经对这19件玉器的初步辨识,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龙山文化时期的作品。如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226玉琮[1]124,外径7.4厘米、内径6.6厘米、高5.5厘米,玉琮的四壁中部施刻两道竖线,四壁角面上施刻上、中、下三道平行线纹,在上下两道平行线纹之间刻一圆圈眼纹,圆圈眼纹叠压中间一道平行线纹。这些特征表明其是良渚文化之后制作的仿良渚文化玉琮的作品。风格相同的玉琮在山东五莲丹土发现1件[2]山东卷28,[3]109。这类玉琮可能是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时期制作的,大致属龙山文化时期的作品。
第二类,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作品。如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260牙璋[1]72,长39.2厘米、刃部宽10.3厘米、柄部宽6.3厘米、厚0.4厘米。四川博物院藏品A313牙璋[1]80,长60厘米、最宽8.4厘米、厚0.8厘米。这几件牙璋制作精致,尤其是阑部的平行弦纹和扉棱扉牙,十分精细,扉棱扉牙的形制,已发展到顶峰。
与这几件牙璋的阑部纹饰和扉棱扉牙形制相同的牙璋,见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四期。如二里头75YLⅦKM7:5牙璋[2]河南卷12,双阑形成了复杂的扉棱与齿牙,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牙璋,是牙璋制作最为精美的阶段。
第三类,齐家文化的作品。如四川博物院A41玉琮[1]126,外径5.3厘米、高7.5厘米,四川博物院藏品A110485玉琮[1]127,外径9厘米、高11厘米。光素无纹,为齐家文化特征的玉琮。又如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441玉琮[1]123,外径5.9厘米、内径4.6至4.2厘米、高3.1厘米。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113玉琮[1]124,外径5.1厘米、内径4.1厘米、高5.1厘米。这4件玉琮,都是光素无纹,射口的外缘中部与玉琮四面外壁面一体,射口的制作是在两端的四角剔刻而形成,通常不规整,为齐家文化特征的玉琮。还有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439玉璧[1]138,外径18.5厘米、内径4.9厘米、厚0.6厘米;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131玉璧[1]139,外径10.5厘米、内径4.2厘米、厚0.4厘米。这2件玉璧也是齐家文化作品。
第四类,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作品。如四川博物院藏品A12有领玉璧[1]149,外径11厘米、高3.3厘米。这件有领玉璧,器形较小,领部略高,领部的两端口唇外侈,在领部两端外表接近口沿处施刻两道凹弦纹。这种风格的有领玉璧目前尚未见于商代晚期,也不见于二里头文化或更早的文化遗存中,推测可能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作品,大致属商代中期。
第五类,商代晚期作品。如四川博物院藏品A113915有领玉璧[1]150,残缺一小部分,外径12厘米、高1.7至1.2厘米、璧面厚0.2厘米。四川博物院藏品A110483有领玉璧[1]150,残缺一小部分,外径11厘米、高1.7至1.2厘米、璧面厚0.2厘米。这两件有领玉璧,器形较小,在璧面上施刻有十多道同心圆弦纹,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同心圆弦纹有领玉璧。其中四川博物院藏品A110483有领玉璧两面的同心圆弦纹被磨损十分严重,显示其制作之后可能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与这两件同心圆弦纹有领玉璧形制相同的器形,在殷墟妇好墓中有较多的出土。在有领玉璧的璧面上施刻复杂的同心圆弦纹,是商代晚期有领玉璧的特征[4]1-60。
以上分析表明,1929年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的玉石器坑类遗迹中的玉器,至少分属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四期、齐家文化、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代晚期五个阶段。而这座玉石器坑类遗迹的年代即这批玉石器的埋藏年代,只能依据这批器物的最晚年代来确定,应是在商代晚期时期埋入的。如果考虑四川博物院藏品A110483有领玉璧制作之后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而使其磨损,那么其埋藏年代可能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二)三星堆遗址附近高骈乡机制砖瓦厂一座坑类遗迹
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附近的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5],后藏入四川博物院。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5]图二.4,平面大致呈长方形,上端略宽、顶边向下微凹弧,下端略窄、底边向下微凸弧,平面横向弯弧呈瓦状,外侧近四角饰半环状小钮。铜牌饰面上有10个镶嵌绿松石块图案,左右对称,两侧各一排,每排4个图案,两端各1个图案。长12.3厘米、最宽5厘米。这是一件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但形体已经演变为瘦长,镶嵌绿松石块的图案已不见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常见的兽面图案的踪影,如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6]图二.1,图版壹,年代应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还晚于仓包包坑类遗迹中出土的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见后述),但早于铜牌饰外侧四角没有半环状小钮的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见后述)。这种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但形制变异并缺乏兽面特征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不是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作品,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一带制作的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推测其制作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三期。
四川博物院藏品A140328玉戚(见封三图7)[1]54,长17.9厘米、宽8.3厘米、厚1厘米。这件玉戚两侧偏下饰5个扉牙,5个扉牙的分布形式,以中间1个扉牙为中轴,上下各两个扉牙分别上下斜侈,扉牙呈尖状。这种玉戚扉牙的形式,目前尚不见于商代晚期以前的作品,即是在商代晚期前段玉戚上也鲜见,推测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的作品。
四川博物院藏品A140329玉刀的形制为玉铲(见封三图8)[1]76,长26厘米、刃宽11.2厘米、厚1.2厘米。这是一件由牙璋改制的作品,在下部穿三孔以便于安装铲柄。相同的作品见于金沙遗址[1]77,类似的作品曾见于湖北黄陂钟分卫湾M1墓中出土的玉铲[7]图三,6,可能也是由牙璋改制的作品。钟分卫湾M1墓曾被定为商墓,墓中出土有带胡的青铜戈,李学勤据此推定该墓年代为商末[8]。由此可推测高骈出土的这件玉铲可能是商代晚期后段改制的作品。
四川博物院藏品A140330玉矛[1]98,已残。类似的玉矛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商时期遗存中,无法进行比对分析,对其年代暂时不能明确。
通过以上分析,高骈这座坑类遗迹中出土的1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3件玉器,除1件年代不明外,其余的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和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据此推测高骈这座坑类遗迹的年代及其绿松石铜牌饰和玉器的埋藏年代在商代晚期后段。
(三)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坑内堆满了大批珍贵文物,大部分是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作品。但也有少量的早期作品。如一号“祭祀坑”K1:11-2玉琮[1]125,外径(边长)6.8厘米、内径5.2厘米、高7.3厘米,制作粗略,是齐家文化作品。又如二号“祭祀坑”k2③:201-4玉璋,器表两面施刻祭祀场景的图[9]572,图90,是由牙璋改制的作品,改制前的原件牙璋,可能是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的作品[10]。
关于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的年代,发掘主持者与发掘报告编写主持者陈德安将两座“祭祀坑”的埋葬年代,分别推定为殷墟一、二期之间与殷墟二期晚段至三、四期[9]4274-432。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陶尖底盏和陶器座[9]146,图七六.1-7,图版五三.1-4,这两件陶器可能是配套使用,应是有意埋入的。这类陶尖底盏见于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11]79-80,图五五、五六和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12]171-210。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陶尖底盏的形制特征,最早的可能属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早段。据此可确定一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四期早段,可能相当于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二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可能与一号“祭祀坑”的接近。
(四)月亮湾仓包包一座坑类遗迹
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以东约400米处的仓包包发现一座坑类遗存,出土铜牌饰3件、玉环(原称玉援)8件、玉箍形器1件、玉凿1件、石璧11件、石纺轮形器10件(原将11件石璧、10件石纺轮形器都称为石璧)、石斧3件、石琮1件[13]78-90。这批文物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是3件铜牌饰。3件铜牌饰平面大致呈长方形,上端略宽、下端略窄,细节形制有区别。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3]78-90,图三.2,平面横向弯弧呈瓦状,下端呈弧形,外侧近四角饰半环状小钮。铜牌饰面上形成铜牌饰框架图案结构、内镶嵌绿松石块。铜牌饰框架图案以中部上下一条主干架为中轴,与左右对称的斜支干、圆圈、小弯勾组成上下四组图案。正面铜锈上有细线织物的印痕,背面铜锈上有竹编印纹痕迹。铜牌饰长13.8厘米、上宽5.6厘米、下宽5.2厘米、厚0.1厘米。仓包包87GSZJ:16镂空铜牌饰[13]78-90,图三.1,平面横向弯弧呈瓦状,外侧近四角饰半环状小钮,铜牌饰框架图案以中部上下一条主干架为中轴,与左右对称的各种细斜支干、短弧支干组成,形成上下对称的以“S”形单元为主体、相间小三角形镂孔的五组卷草形镂空图案。器表铜锈上有少量朱砂与灰烬。铜牌饰长14厘米、上宽5.3厘米、下宽4.9厘米、厚0.2厘米。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13]78-90,图三.3,体薄,背面平整,正面中部凸出一竖向短脊,脊长4.5厘米、宽0.8厘米,脊两端分别连接一凸出器表、直径2.5厘米的圆饼状。铜牌饰长13.8厘米、上宽5.8厘米、下宽5.2厘米。
这3件铜牌饰的形制不同,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早晚关系。其中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形制与制作工艺与二里头四期的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接近[6]图二.1,图版壹,还保留了象征兽面眼纹的图案,其使用方式可能也相同,可能是捆绑在手腕部的一种兼具装饰的工具或防护用具①,年代相对较早。而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器体较平整,没有镶嵌绿松石块,也没有镂空,四角没有半环状小钮,整个风格不仅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迥异,而且其使用方式与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明显不同,显示其年代较晚。仓包包87GSZJ:16镂空铜牌饰的形制则介于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之间,年代应居于两者之间。这3件铜牌饰的相对年代从早到晚依次为: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仓包包87GSZJ:16镂空铜牌饰、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由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绿松石龙形器演化而来[14],在镂空铜牌饰上镶嵌绿松石以表现兽面。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接近,而器形演化为瘦长、兽面纹消失,但还保留了象征兽面的眼纹,制作年代应略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87VIM57:4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故推测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末段的作品。依次类推,仓包包87GSZJ:16镂孔铜牌饰应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的作品,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应是更晚的作品。仓包包87GSZJ:17铜牌饰的风格与二里头文化四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风格迥异,使用方式也不同,应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孑遗。其可能是在成都平原地区制作的,推测其制作年代大致在三星堆遗址三期或三期之后。
第二类,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是11件石璧、10件由石璧芯制作的石纺轮形器。
11件石璧,器形由大而小依次递减,相近两件之间大小差1厘米左右,被称为“列璧”。大都不成正圆,中部厚,边缘薄,周缘不规整,单面穿孔,有的穿孔偏于中心一侧。最大的一件87GSZJ:13石璧,一面经火烧烤,直径20.3厘米、孔径9至8.6厘米、厚1.3至1.1厘米,并且可与最大的一件石纺轮形器套合[13]78-90,图七.4。最小的一件87GSZJ:22石璧,穿孔偏于中心一侧,直径7.1厘米、孔径2.9至2.5厘米、厚0.7至0.6厘米[13]78-80,图八.5。这11件石璧,出土时按大小顺序依次垒叠在一起。
10件由石璧芯制作的石纺轮形器,形体较小,也是由大到小排列,有的可与一起出土的石璧套合,证明是利用这些石璧的芯片进一步加工而成。由于其本身是从石璧上经单面穿孔取下的石璧芯,所以这些石纺轮形器的两面直径不相等,在外缘壁上有螺旋纹钻痕。最大的一件87GSZJ:21石纺轮形器,是利用87GSZJ:13石璧芯制作,质地、色泽与87GSZJ:13石璧相同,也是一面经烧烤,并且两件可以套合,直径8.4至7.7厘米、孔径1.3至0.9厘米、厚1.2厘米[13]78-90页,图九.1。最小的一件87GSZJ:9石纺轮形器,直径3.5至3.1厘米、孔径1.4至0.9厘米、厚0.8厘米[13]78-90页,图九.10。
这种形制的石璧以及利用石璧芯制作的石纺轮形器,在齐家文化中有较多的发现,是齐家文化玉石器的一种主要特征[15]204-275。
经比对分析,可以明确仓包包这座坑类遗迹中出土的石璧、石纺轮形器的形制特征、制作工艺特征,都具有齐家文化的特征。但这些石璧与石纺轮形器有的可以套合,反映了它们的制作年代与埋藏年代相距不远,其不可能是在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制作后长距离辗转而来,而应是在三星堆遗址上制作的。这些石璧与石纺轮形器应是三星堆遗址上制作的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石列璧”与石纺轮形器,制作年代应在齐家文化之后,即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
第三类,具有商代晚期因素的遗存。主要是8件玉环。8件玉环大小相若,形制基本相同。直径在8.8至10厘米,孔径在6.1至6.6厘米,玉环面宽1.3至1.8厘米,厚0.3至0.5厘米。在环面上穿一小长方形孔,最大长方形穿孔,长0.8厘米、宽0.4厘米,最小长方形穿孔,长0.6厘米、宽0.2厘米。其中,4件玉环,素面无纹;4件玉环的两面施刻同心圆弦纹或较宽的同心圆凹弦纹。大都磨损严重。器体最大的1件,仓包包87GSZJ:30玉环[13]79-80,图五.2,经火烧成鸡骨白色,在玉环两面上施刻6道同心圆弦纹,直径10厘米、孔径6.4厘米、环面宽1.8厘米、厚0.5厘米,长方形穿孔长0.7厘米、宽0.3厘米。前已述及这类施刻同心圆弦纹的玉璧(玉环)为典型的商代晚期的风格。但在环面上穿小长方形孔的玉环,在商代其他遗址中尚未见到,这种小长方形孔是在同心圆弦纹之后施刻的。依此对照分析,可将这8件玉环的年代推定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以上分析表明月亮湾仓包包这座坑类遗迹中出土的文物,可分为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齐家文化因素、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的三类。据此推测月亮湾仓包包这座坑类遗迹的埋藏年代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五)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侧,1997年11月发现墓葬,经1998年1月至6月的发掘,清理墓葬29座。其中,17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有随葬品;4座为狭长形土坑墓,仅1座见有人骨和一段象牙。这些墓葬填土中有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末的陶片。共出土随葬品66件,其中陶豆1件、豆形器2件、尊形器1件、器盖1件,共陶器5件;玉石蜗旋状器6件、玉石泡形器4件、石纺轮形器(璧形器)2件、玉锥形器3件、玉凿1件、玉矛2件、石斧2件、石斧形器2件、黑曜石珠37颗、石弹丸2枚共玉石器61件。对于仁胜村墓地发掘的这29座墓葬的文化面貌与年代,发掘主持者陈德安曾有过初步的分析,认为6件蜗旋状玉器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斗笠状白陶器、成都南郊十街坊宝墩文化晚期遗址M6出土的圆形骨器近似,而5件陶器的陶质陶色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早的陶器风格一致,年代上限应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后段,下限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年代范围[16]。
笔者认为,如果依据这批墓葬填土中有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之末的陶片,而随葬陶器的陶质陶色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早的陶器风格一致,由此可以确定这批墓葬的年代要晚于三星堆遗址一期之末,属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另依据年代较早的M21号墓随葬有蜗旋状玉器5件[16]图一二.16、图版叁.1,[2]四川重庆卷8、蜗旋状象牙器2件、玉矛1件,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一带的文化遗存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文化遗存。那么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据此推测,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公元前1610年前后,可能是仁胜村墓地年代的上限。
(六)三星堆城址城墙
三星堆城址城墙自1989年发现以来,至2017年对三星堆遗址城墙的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可知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建筑城墙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至三星堆遗址三期在三星堆城址内的东北部形成了仓包包小城,在三星堆遗址四期还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17]221,[18]380-382,[19]293,[20]377-378,[21]380-381。这些现象显示,三星堆城址的城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
(七)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存
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存位于三星堆城址内西北角青关山高台上。土台呈二级台地状,最高一级高出周围地面4至5米,这里也是整个三星堆城址的最高处。2005年勘探发现青关山高台系人工夯筑而成,并在第二级台地南部局部揭露出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至2017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已经揭露出三星堆遗址三期的3座大型建筑基址,如F1、F3,以及略早的F2。其中F1为长逾65米、宽近16米、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由多间“正室”以及相对应的“楼梯间”组成,“正室”分为两排,沿中间廊道对称分布,廊道宽2.5米左右[18]380-382。在F1、F2、F3三座建筑基址下叠压有属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夯土台[20]377-378,其规模、结构有待探索。据此推测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可能存在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存。
二、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
通过以上对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及附近遗迹中发现的高档次文化遗存的分析,就比较容易明确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问题。
(一)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及附近遗迹中发现的最早一批高档次文化遗存,主要有仁胜村墓地、三星堆大城城墙,以及可能存在的青关山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其年代属三星堆遗址二期。其余的如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迹,埋藏年代都比较晚,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如果说三星堆大城城墙、可能存在的青关山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仁胜村墓地及其玉石器等高档次文化遗存,可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那么可以确定三星堆文明的最初形成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
(二)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具体年代
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形成,具体的年代是多少呢?这涉及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问题。分析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主要依据三星堆遗址二期的文化遗存及测定的年代数据进行②。此外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进行分析。
如果说前述分析的仁胜村墓地墓葬中出土的5件陶器,代表了三星堆遗址二期前段,那么可依据仁胜村墓地以及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迹中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物来推定三星堆二期开始的年代。因为这些遗物的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年代明确,而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又有较多的测年数据和研究认识可供参照。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最早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大概是前已述及的仁胜村墓地出土的蜗旋状玉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被改制为玉璋的原件牙璋。蜗旋状玉器的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10年之间。被改制为玉璋的原件牙璋的制作年代可能属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的作品,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80年前后。
月亮湾燕家院子坑类遗迹出土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255牙璋、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3.1)260牙璋、四川博物院藏品A35牙璋、四川博物院藏品A313牙璋,以及故宫收藏的那件燕家院子的牙璋、仓包包87GSZJ:36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大都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作品,具体年代可能在公元前1560年至公元前1530年之间。
由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制作使用的作品,辗转来到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其到达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必定晚于在二里头遗址制作与使用的年代。所以,依据这些二里头文化的作品,可以推定他们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遗存,主要是玉琮与玉璧。依据齐家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现象推测,这些齐家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也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如果这些齐家文化遗存是与二里头文化遗存一起由陇西南通过岷江上游地区这一文化通道到达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一带的,那么他们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年代基本相同,也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以仁胜村墓地为代表的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这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二期开始的年代,也大致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具体年代。
三、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这些高档次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文物主要分为六类: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遗存、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齐家文化遗存、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遗存、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属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的遗存,主要是建筑遗迹。属二里头文化遗存及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牙璋、蜗旋状器等玉器。属齐家文化遗存及具有齐家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是玉琮、玉璧、石列璧、石纺轮形器等。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存主要是玉琮。这六种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地区出现的背景与机制是不同的。分属以下四种现象。
第一,三星堆大城城墙、可能存在的青关山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是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遗存,它们的前身应与宝墩文化的城址城墙、大型建筑基址有关。
第二,二里头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存,都是从成都平原地区以外区域进入成都平原地区的。
第三,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而年代晚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以及具有齐家文化因素而年代晚于齐家文化的遗存,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一带制作的。
第四,属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琮可能是与二里头文化遗存、齐家文化遗存一起进入到成都平原地区的,因为在三星堆遗址一期遗迹或宝墩文化遗迹中没有发现中原地区或海岱地区、太湖地区等龙山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琮,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遗存,可能是作为遗玉由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进入成都平原地区时携带进入的。
这些现象显示,三星堆文明是在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下,并与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相结合后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这可能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
至于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的,推测可能是通过岷江上游这一文化通道实现的,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岷江上游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形成了甘南文化南下川北的文化通道,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的遗存,陇西南地区分布有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在陇西地区发现了许多二里头文化高档次的文化遗存[22]。如甘肃天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已经被改制成玉钺的牙璋,甘肃庄浪县出土的利用二里头文化大玉刀改制的玉钺,还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的陶盉、大石磬等文化遗存。这些器物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器,是二里头文化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重器出现在齐家文化中,不仅仅表现了二里头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精华向齐家文化的转移。这些现象显示,二里头文化进入陇西地区之后融入齐家文化中,然后经陇西南地区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一道通过岷江上游这一文化通道进入到成都平原。
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代表性遗存,是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可能存在的青关山高台上的早期建筑遗存、仁胜村墓地,以及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迹等考古学单位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牙璋、玉琮、玉璧等玉石器所代表的高档次文化遗存。
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所以,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主要文化内涵,包含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三种文化因素。成都平原地区宝墩文化的继续发展,可能会产生文明,但不会产生具有三星堆文化特色与文明特质的三星堆文明,因为三星堆文明中不仅仅是宝墩文化后继者一种文化因素。据此推测,如果成都平原地区在三星堆遗址二期时没有受到来自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及陇西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可能就不会产生三星堆文明。
二里头文化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可能是夏文明的代表。这种夏文明遗存以及齐家文化遗存来到成都平原地区,不应仅仅是文化遗存本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支系部族人群向成都平原地区的转移与迁徙。这两支系部族及其文化来到成都平原地区,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以及齐家文化因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那些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注释:
①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可能是捆绑在手腕处的认识,是由黄翠梅于2014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二里头遗址发掘5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明确的。见黄翠梅:《功能与源流:二里头文化镶绿松石铜牌饰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015年第33卷第1期。
②目前测定的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数据,早晚年代悬殊较大。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考古》1983年第7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六)》,《文物》198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一)》,《考古》1984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四)》,《考古》1987年第7期。
[1]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2]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朱乃诚.蛰伏升华推陈出新:殷墟妇好墓玉器概论[M]//妇好墓玉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5]敖天照,王友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J].文物,1980(9):7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2(4):294-303 385-386.[7]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古文化调查[J].考古,1988(4):300-306 313.[8]李学勤.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J].南方文物,1992(1):25-29 18.[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0]朱乃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祭祀图”牙璋考[J].四川文物,2017(6):51-59.[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十二桥[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2]四川大学博物馆等.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M]//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M]//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4]朱乃诚.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J].中原文物,2006(4):15-21 38.[15]朱乃诚.素雅精致陇西生辉:齐家文化玉器概论[M]//玉泽陇西:齐家文化玉器.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5.[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J].考古,2004(10):14-22 97 100-101 2.[17]袁金泉.广汉三星堆遗址[M]//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8]雷雨.成都市三星堆商代遗址[M]//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9]雷雨.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M]//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0]雷雨.成都市三星堆商代遗址[M]//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1]雷雨,冉宏林.广汉市三星堆遗址[M]//中国考古学年鉴: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9期。
- 0000
- 0000
- 0002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