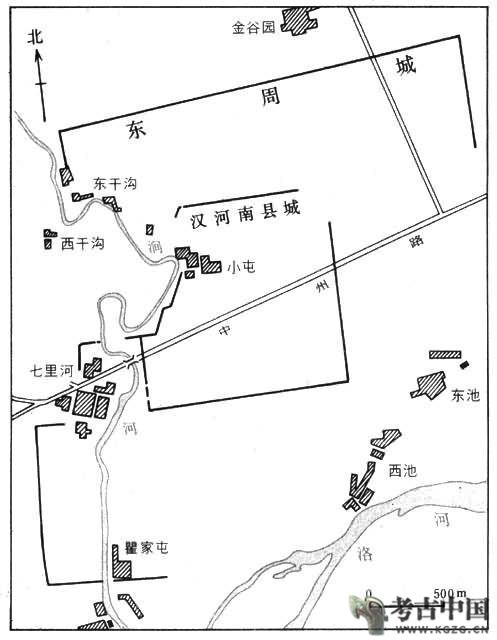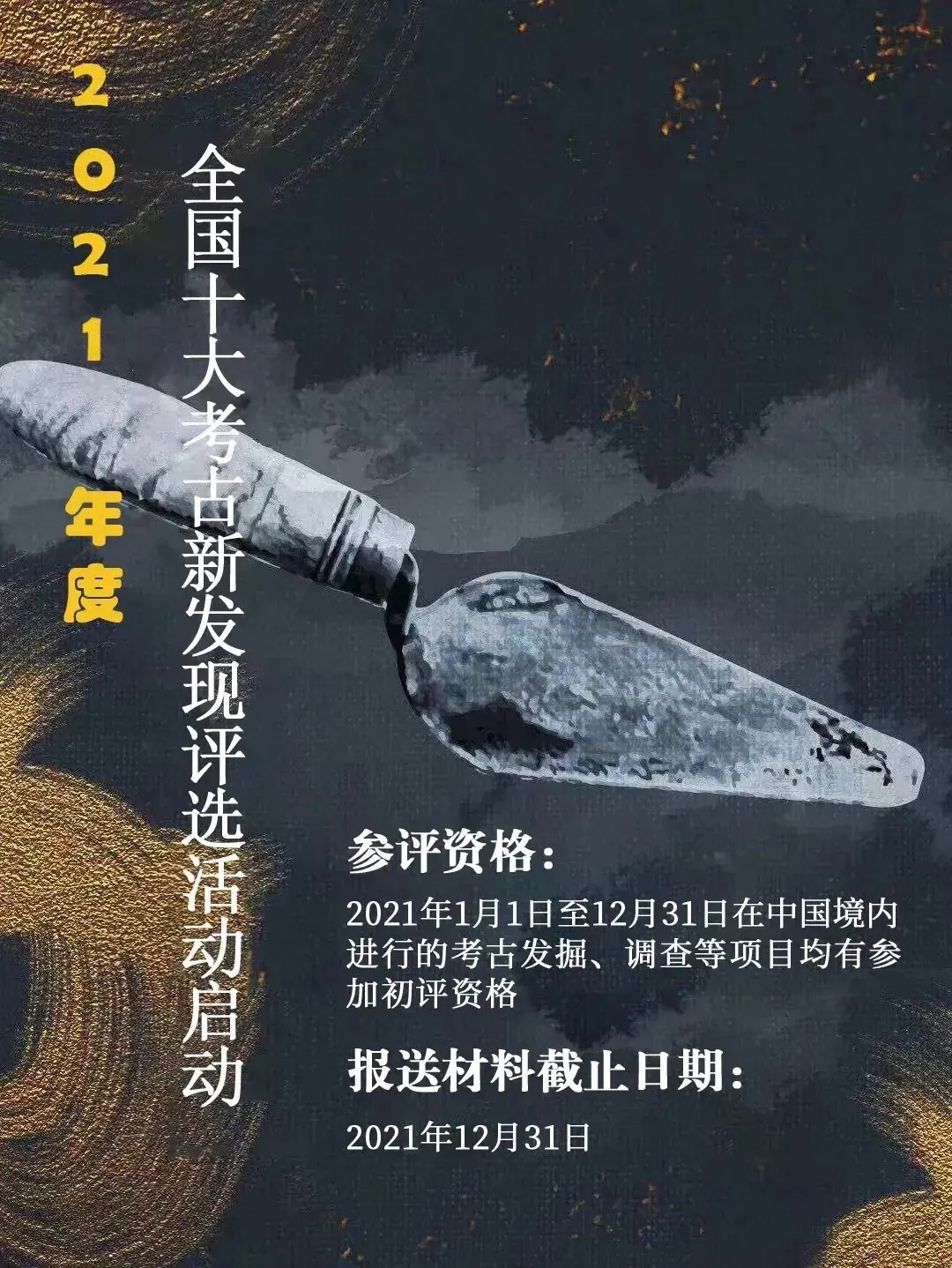叶朗谈北大的人文传统
关于北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文修养
学生:您认为北大是怎样一所学校?它之所以能成为无数青年向往的高等学府,凭借的是什么?
叶朗:北大是我们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有人说现在北大不行了,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北大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文化担当。
我经常跟北大的同学们引用冯先生的一段话:“人类的文明,就像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在燃烧。它之所以不灭就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他们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火不灭。”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冯先生说:“他是欲罢不能。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这话说得非常好。“欲罢不能”就是人生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一种对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有限意义的超越。我们知道每个人个体生命的存在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这种“欲罢不能”就是对有限存在与有限意义的超越。这是一种生命力、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体现。我觉得“欲罢不能”这四个字就可以用来概括我们北京大学的一种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这是对中华文化、人类文明的献身精神,对个体生命有限存在、有限价值的一种超越,对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我们人类社会有物质的追求,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子、要生活得富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北京大学的传统里就有这种精神的追求。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大家会说这个人很庸俗;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追求也会很危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就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坚守一种文化的使命,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要靠我们来这些大学来传承。
为什么全国多少青年向往北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具有一种深远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这也是决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特殊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我们要来维护这一种传统,要来发扬这种传统,不能让它中断。
学生:在您看来,我们北大的精神追求体现在哪里呢?
叶朗:在我看来,我们北大这种精神追求就体现在我们北京大学一批大学者的身上。我们这期茶座举办的这个地方是燕南园56号,它原来是燕京大学教授住的地方。当初,这个房子是由一个美国建筑师按照当初最好的美国住宅标准设计的,燕南园里大概二十几栋房子,每一栋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房子在当时可是很高档的,每一栋房子都有独立的供暖系统,还有壁炉,据说门窗也是从美国买来的。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以前就住在这里。解放以后,北大就搬到燕园来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我们北大教授住的地方。除了燕南园,北大也有一些教授住在燕东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栋是56号院,是我们当年的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住的地方。前面56号院的对门是冯友兰冯先生住的地方,那里有三棵松树,所以叫做三松堂。隔壁55号院是哲学家汤用彤先生住的地方。在这边是冯定先生住的地方,他也是个哲学家。那边是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住的地方。在这里生活过的还有地理学家侯仁之,他对北京市的地理是最熟悉的,写了好多书。还有我们的马寅初马校长住的地方。还有翦伯赞先生、朱光潜先生、林庚先生——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是诗人,等等。一些理科的教授,我不太熟,也住在这个地方。这些教授住在燕南园,正是这些教授,这些大师,构成了北大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朱光潜朱先生的例子。朱先生是美学家,朱先生的身上就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朱先生对中国美学有一个不朽的贡献,就是他翻译了很多经典的西方美学著作,比如说黑格尔的《美学》。黑格尔的《美学》一共三大卷,四大本,朱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翻译了一卷出版;还有两卷他翻译了一部分。当初周恩来总理就说,像黑格尔的《美学》这样的著作,只有朱光潜朱先生来翻译,才能使人愉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很难翻译,这个“很难翻译”不光是语言的问题,因为黑格尔的《美学》涉及面很广: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如果不懂这些东西,翻译起来就很难。翻译这件事,一是要对西方的语言很熟悉;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条件(一般我们不注意)就是你要对本国的文字把握得好。朱光潜是安徽人,受到桐城派文学传统的熏陶,所以中文修养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流畅。我们看很多翻译的作品,读起来不流畅,除了翻译者对西文掌握得不是很好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文也不太好。
德国有一个教授叫顾斌,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是我的朋友。他翻译《鲁迅文集》,也编《中国文学史》,他对中国文学史有深入的研究。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谈到对于中国一些书籍的德文译本,他说东德的学者要比西德的学者翻译得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德的学者对德国的历史批判较多,因而他们对德国的文化、语言不太看重;而东德的学者依然比较看重德国的历史文化,德文也一直很好,所以东德的学者德语方面的修养要比西德好,翻译自然也做得好。这个例子就说明,翻译对于译者而言不仅外文要好,还有具备本国文化的修养。
关于如何写文章
学生:我知道您曾编写过《文章选读》这本书,我想请教您一下,您编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要写好文章,该从何入手?
叶朗: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同学对于写文章重视不重视。我认为,不管学什么专业,文科还是理科,都应该重视写文章。这点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后要多动手写文章。前两年我编了一本书叫《文章选读》,之所以编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同学不会写文章,所以想把好的文章挑选来介绍给同学们去读。现在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往往在文字上有问题:第一是啰嗦。同样一句话,要反复地说,一个内容用一段话就能说清楚,但却写了四五页纸。第二就是不通畅,晦涩难懂。当然,这也与学界的一些风气有关,现在学界有一些人引导了一种风气,喜欢写一种大家都看不懂的文章,以为“你们看不懂就说明我的水平高啊”,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一篇好的文章要有思想、有学识、有情趣。首先,文章一定要有思想,光堆一些华丽的辞藻不行;其次,要有学问;最后还要有情趣。
“五四”以来的一批大学者,比如说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郭沫若、闻一多、范文澜,还有历史系的翦伯赞,他们写的文章都能做到以上几点。我希望同学们以后写的文章也要这样:要简洁,要通畅,千万不要写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古人用“艰深文其浅陋”来批评这种艰深晦涩的文章,“文”就是文饰,用艰深来掩盖自己的浅陋,让别人乍一看以为他很了不起,其实没有内涵。黑格尔讲过,深邃就像一个井、一个洞,深邃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东西,一种是里面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个井很深,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艰深文其浅陋”,讲的就是文风的问题。希望我们北大的同学一定要培养一种好的文风,明白、简洁、通畅。
学生:您说文风很重要,那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哪些作家的文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叶朗:朱光潜先生的文风就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他的翻译也是一样。他翻译文章,通常会在读者可能看不懂的地方,在原文下面加一个注,告诉你这段什么意思,尽量让人看懂,而不是尽量让人看不懂。有人说哲学家是要把大家不太懂的、艰深的内容,用大家都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现在有的人相反,是把大家都懂的道理用大家都不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当然是很不好的。
朱光潜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当时翻译的稿子也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幸好后来又找到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朱光潜先生就把黑格尔的《美学》另外两卷翻译出版了,此外还有《歌德谈话录》和莱辛的《拉奥孔》。这几本书加在一起120万字,当时朱光潜朱先生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人生追求。后来朱先生去世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来悼念他,我在文章里引用丰子恺先生在一幅画作上所题的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出条,气象何蓬勃。”我觉得用这首诗来作为朱先生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作为他人生境界的象征是很恰当的。
我在《文章选读》中选了闻一多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庄子的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讨论庄子最好的文章。闻先生说庄子的文章是一种客中思家的哀呼,哲学就是对精神家园的一种呼唤。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冯友兰。冯先生直到他八九十岁的时候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写的东西也非常简明流畅,我在《文章选读》里也选了他的文章。当年朱自清先生就说,大学生、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想要写好文章要多读冯友兰先生的书。朱自清先生不是从哲学的角度,而是从写文章的角度推荐大家多读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因为冯先生文章对问题一层一层分析,细腻而不烦琐。他到八十多岁时,文章依然写得很有味道。冯先生当时眼睛和耳朵都不太好了,自己不能写东西,他就通过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但即便这样,他的文章依然那么有味道。有一次我碰到我们哲学系的张岱年老教授,我问他:“张先生,冯先生口述的文章读起来依旧很有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张先生说:“是这样的,冯先生口述后,还要念给他听,他还要修改,一直改到口气、味道跟他的完全一样,所以你看起来就跟他自己写的是一样的,依然有味道。”
当时我们北大有位教授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去世时,冯友兰先生就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对熊先生一生的治学经历做了一个概括。他说熊先生的治学是先从六经、儒家再到佛学,最后又回到儒家的一个过程。冯先生说熊先生回到儒家之后又对佛学做了一些清理。在唐朝的时候,关于佛学有一些争论,这个争论在现在看来就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争论,当时佛教内部思想有些混乱。玄奘大师当时去印度就是为了一观究竟,回来之后他就写了《唯识论》,专门来澄清这个问题,他是主张主观唯心论的。熊十力先生就写了一本《新唯识论》,反对玄奘,他认为玄奘主张的“识”也是虚的,认为宇宙的“心”才是最高的,这个“心”不是个人的“心”。《新唯识论》的“新”就新在这里。我看了那篇短的文章以后当时非常吃惊,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就把熊先生一生的治学做了一个总结,冯先生都八十多岁了,思想依然那么锋利,非常了不起。所以文章写得好跟理论思维有关系,文章当然与文字修养有关,但主要还是思想,要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
关于理论思维与哲学经典
学生:您刚才提到理论思维。那么您认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叶朗:对于做文科的人来说,理论思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理论思维,研究哲学、文学理论或者美学都很难做好。20世纪80年代我们请了一个美学家叫王朝闻,80年代第一本《美学概论》就是他主编的。王先生原来是搞雕塑的,“刘胡兰”就是他的作品。那个年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的研究生座谈,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学问,写了许多文章,但他写的文章始终不精彩,始终平平淡淡,你们想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比较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没有理论思维,就好像那里有一堆材料,却不能从中提炼出新思想和新观点。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在写论文时要有论点,要有论,论文没有“论”就不能称之为论文,提炼不出论点,写不出新东西,这就是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体现。
学生:那我们该如何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
叶朗:恩格斯讲过,一个人要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读历史上那些哲学经典。因为历史上那些哲学经典就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我们读他们的书就是用人类的最高智慧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人不是生来就是天才,都需要不断地学习。要打下做人和做学问的根底,一定要读几本书。这里所说的“读几本书”,就是经典,历史上的经典。
但读经典不能要求快,反而要放慢速度,就是要做到精读、细读。熊十力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称赞某人‘一目十行’,其实这样根本成不了大的学问,至多是个名士而已。”所以我们读经典一定要放慢速度,把它读懂、读通、读透。“读懂”就是要弄清楚每句话说的意思;“读通”就是要领会每句话背后的精神要旨,把它融会贯通;“读透”则是要把它吸收到自己的头脑中,成为你自己的东西。用朱熹的话来讲就是“熟读玩味”,要放慢速度。
我希望同学们除了读专业书籍之外,可以订个计划,读一些中外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每年能够坚持读一两本就可以了。如果一年读两本,十年就是二十本,那你整个人就脱胎换骨了,你说出来的话自然就不一样了,写文章也不一样了。
关于人生境界与审美情趣
学生:叶老师刚提到写文章和读经典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很有好处,但有的时候我会感到读书很枯燥,我想知道您是如何从读书中找到乐趣的呢?
叶朗:我在这里还要举冯友兰先生的例子。冯先生九十岁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有同学到他家里去访问,就和他说:“冯先生你现在眼睛也看不见了,耳朵也不行了,你还要写书,你应该好好休息。”冯先生说:“我虽然眼睛不好了,不能再读新的书,但是我可以把我过去读过的书重新来思考,产生新的理解。”他这句话很重要,对于过去读过的经典,你可以不断地重新思考,产生新的理解。冯先生说:“我好像一条老牛躺在那里,把过去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细嚼慢咽,不但其味无穷,而且其乐无穷。我想,古人所谓乐道,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乐道”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学生:关于您提到的人生境界的问题,您认为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体现在哪里?它对我们的人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叶朗:冯友兰先生认为,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是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学说。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境界高境界低指的就是人生境界、精神境界。人生境界,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人精神的追求,包括你的思想、理想等。这种人生境界有一种导向的作用,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境界,就意味着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冯先生说,从表面上看,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但实际上世界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比如说,两个人都到山里去游览,一个地质学家看到的是地质构造,一个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历史遗迹。同样一个山,对这两个人的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冯先生说,没有两个人的世界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相同的。这点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学生: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学习哲学和美学的意义是什么?
叶朗:张世英先生,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一位老先生,他现在已经93岁高龄了,还在继续写书写文章。他也同意冯先生的说法,他说:“哲学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人生境界”,所以同学们,提到美学和哲学对人生的意义,我只能说它不可能解决我们人生的一切问题,专业问题还必须要专业知识来解决。美学解决不了你治病救人的问题,医学学生还是要去学医,物理学学生学物理,化学学生学化学,但是哲学最根本的是提升你的人生境界,使你有高远的人生追求。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哲学和美学都会引导你,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每天早上起来你要对自己说:“你看,又是一个新的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来到了,又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天,非常珍贵啊!”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一个人在这无限的宇宙出现在地球上也是很偶然的。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但我觉得每个生命的出现都是很偶然、很短暂的。正因为很偶然、很短暂,所以才非常宝贵。你要从短暂的、偶然的人生中悟到人生的真谛,使你这个短暂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没意思。
我也很赞同冯友兰先生、张世英先生的观点,哲学、美学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像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他们的人生就是创造的人生、五彩缤纷的人生,他们一辈子做的事比普通人做的要多得多。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他们这些是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他们人生极限的人,这就叫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和“创造性”是一个概念,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通过学哲学、学美学,把你的人生提升为创造的人生、五彩缤纷的人生,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王夫之说过,有的人“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就是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就想着实际的功利,想着升官发财,而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人的一生做一番事业,但同时也不能没有审美。审美这个东西没有直接的功利性,你背几首唐诗,人家问:“你读唐诗有什么用?”或者“你读《红楼梦》有什么用呢?”你学的外语你可以用,你学的计算机马上能用得上,这是工具性的东西。唐诗不是工具性的东西,但是你从小念唐诗和你从小不念唐诗还是不一样的。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俄罗斯有一位电影大师叫科夫斯基。他的母亲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母亲就让他读《战争与和平》,并告诉他哪一段怎么写得好。他讲:“从此《战争与和平》对我来讲就成了趣味与艺术的标准,那些垃圾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后来成为电影大师跟他从小的这种修养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过去一些大的文学家、大的思想家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游历的一个作用当然是增加知识、增加阅历,但最重要的是拓宽胸襟。把你的胸襟拓宽,这个对你成就大的学问、大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讲,游山玩水本来不是功利性的,但从根本上对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个审美活动对人来讲当然还是有用的。
学生:您认为怎样才能将生活过得更有情趣呢?
叶朗:情趣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工作,要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之外,生活还要过得有点情趣。
香港有个富豪得了癌症,在家里养病。有一天他的太太陪他到公园散步,一阵凉风吹来,他感到非常爽快,他说:“多好啊,为什么过去我没有这种享受呢?”他自己领悟到他过去的人生是有问题的,本来清风明月是不用花钱的,但对他这个很有钱的人来讲,过去这个清风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同样的世界对不同人来说是不同的。在过去我曾听到对话,“颐和园的玉兰花开了,是不是去看一下?”(有人回答)“我哪有这个时间,哪有这个闲工夫啊!”不是说他没有钱买门票,问题在于颐和园的玉兰花对他的人生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过得是没有情趣的,一旦没有情趣,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小。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淮南子》。《淮南子》里面有段话说,对于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是“衣与食也”,穿衣和吃饭,这当然是对的了,不穿衣吃饭你就活不了。但是今天如果把你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让你吃得很好,穿得也很好,你还是不会感到快乐的,因为在黑屋子里你看不见也听不见,你的人就被紧紧地束缚在我刚刚讲的个体生命的有限范围。我们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能够看出去,能够看得很远,这样就可以超越我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耳朵和眼睛不仅是我们主要的认识器官,也是主要的审美器官。这个时候如果在墙上给你打一个洞,听到外面下雨,你就喘了一口气,因为你的空间稍微大了一点了。如果把门一打开,你看到外面人来人往,你就感到空间更大了。再进一步,让你登上泰山之顶,你看到日月星辰,无限的宇宙,“其乐岂不大哉!”你感到一种极大的快乐。从打一个洞开始,就开始超越你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越往上,到登上泰山之顶,你就越接近一种无限和永恒,所以感到一种快乐。要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人不能仅仅被束缚在一个功利性的有限的地方,要拓宽自己的空间,胸襟要宽,眼界要宽,有一种精神追求。
张世英先生在讲美学的时候提倡一种美感的神圣性。他说我们要相信人生有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这种美感的神圣性最早是中世纪基督教美学提倡的,它们是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不指向上帝,我们指向人生,我们认为人生中有一种神圣的绝对价值。确实,很多大的艺术家、大的科学家都在现实人生中追求这种绝对的、神圣的价值。他们坚信人生有种神圣的价值,而且去追求这种价值,并在灵魂深处分享这种价值。这种信念和追求,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世界万物的无限的爱,使他的人生具有意义。我认为张世英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比如贝多芬的《欢乐颂》,有人就这么评论:“它是超越了生命本体,超越了此岸与彼岸世界的一种欢乐。它启示我们在经历人生的苦难后,抬起眼睛,仰视天空,歌颂生命,放下心灵的负担,了解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所有大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康德讲,有两样东西,我一想到它,我就感到敬畏。一个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认为,有一种人生的境界与灿烂星空的神圣的光照有一样的价值。我们北大校园一直是在康德讲的这种神圣星空的照耀之下,我们要去追求人生这种神圣的价值,信仰和追求。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人生注入一种严肃性与神圣性,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
关于中西文化传统
学生:您之前说过,现在的社会比较注重现实和利益,技术方面的东西比较多。西方的文化比较实际,比较注重人的自由,东方比较重视人的社会性,您觉得怎样把握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
叶朗:对这个问题我自己并没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只能谈一些我的感想。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期出现比较文学热,出现了很多关于比较美学、比较文学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都是一些表面的了解,对东西方文化都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文化研究不能根据个别的事例去做普遍性的结论。比如当时有人说西方的文化是外向的,面向大自然的,中国的文化则是面向内心的。一般来说我们觉得这样讲也许是对的,但也不能笼统地这么说,像汉代的张衡,他就既是文学家又是大科学家。
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中西比较美学的一些结论我感到不符合实际情况。朱光潜先生在的时候,我也对他说过这个问题。朱光潜先生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中西比较美学、中西比较文化不具备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东西没有做系统的研究,对中国的东西也没有做系统的研究。读了两本书就开始作比较,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我并没有做研究,但是一般来讲,中西文化肯定是各有特色。
学生:那您认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色都有哪些呢?我们该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
叶朗:近代以来,西方重视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但并不是说西方一直如此,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而中国过去,一般比较重视家族的、社会的价值,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吸收西方重视个性、自由的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因为人总是社会的动物,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重视社会的特点抛弃掉。
关于“人与万物为一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生态美学在世界上也是独特的。中国画和西方画是不一样的,西方画画的厨房,会画一条死鱼挂在那里;中国从来不会画一条死鱼放在那里,中国鱼都是活的,鱼活在水里,这是生命的表现啊,怎么能画一条死鱼挂在那里?西方是主客二分的,中国是天人合一的。人和宇宙是一体的,与万物为一体的,所以朱熹、程颢,看到河里的小鱼都喜欢观,观鱼的一种自然生意,人与万物为一体。
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是讲主客二分的,而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是讲天人合一的。这两者不一样,但各有各的好处。有同学问,什么叫诗意的人生,我的理解诗意的人生就是天人合一的。张先生认为,和“与万物为一体”不一样,“主客二分”这种思维模式也有好处。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和“主客二分”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吸收它好的一面。
中西方的文化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说中国高于西方,或者西方高于中国,而是要研究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把好的东西吸收来。我们中华民族从历史上看是一个开放的民族,特别是唐太宗那时候,非常开放。对于外面的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过来,但也不因此妄自菲薄,这样我们才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我们讲的盛唐气象,什么是盛唐气象?就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青春的气象。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吸收外面的好的东西十分重要。
关于文化传承与自我坚守
学生:您说我们要过一种创造的、有情趣的人生,过去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经历,现在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走着,将来也会有一些新的成果。但各种选择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我们有时会实现真正的创造,有时却会被所谓的充满新意的幻觉欺骗了,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区分真实的创造和自我的幻觉?
叶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下面从两点来说:一是从历史上学习。为什么要强调文化的传承呢?因为历史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是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好的经验吸收过来。但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有时很难,我在书上看到以后只是淡淡地看过了,只有我自己有过实际经历和经验之后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东西,我才能真正有所感悟。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学习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经验,必须要在自己痛苦的经历过后才能学到,不经受痛苦的经历是学习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刚要发展汽车的时候,国外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我们那时已经知道发展汽车的弊端,然而我们仍旧要大量地发展私人汽车。很多人写文章说这个不能发展、有问题,但这些意见都没有被听取,因为我们要发展、要拉动经济,我们要就业,我们要眼前利益。现在好了,汽车都来了,所以现在的污染这么厉害。这次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为了这几天的蓝色天空又费了多少力气?过去国外早就有这种教训,可我们为什么不吸取呢?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自己的痛苦经历,所以很难做到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因此,我们要结合自身的经历来学习历史的经验。我们在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难有人能告诉应该怎样做,你自己要善于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面发掘,总结这种经历跟历史的关系。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是善于从历史上来学习前人的经验、学习历史的经验,同时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学习和自己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如果你脱离自己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空,要善于将这两者相结合,反复地磨炼。同学们一定要非常重视自己的经历,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脱离亲身经历即便读再多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学生:我想问您一个关于浮躁的问题。如今,不同专业的学生都有目的性地想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一些研究,十分功利。我想请叶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下陶冶情操,坚守自我?
叶朗:对于陶冶情操、坚守自我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记得当年宗白华先生跟我们讲,学美学要爱美、爱艺术,要去欣赏。他自己就很喜欢去看画展,看各种演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宗先生也没有私人汽车,所以他每次都是背着一个书包挤公共汽车进城去看的。我是浙江人,浙江有一个婺剧,还有一个越剧,越剧是绍兴戏,婺剧是金华戏。有一次婺剧的一个剧团到北京来演出,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我当时去看了,到散场的时候发现宗先生也在那儿看。由此可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审美的追求。
以前,我们一些老教授经常进城去看一些演出,我提倡我们的同学也能够在完成专业学习的情况下,抽出时间来多参加一些艺术活动,培养自己的艺术爱好。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同学都有艺术爱好,比如说有些人会弹钢琴、拉小提琴、会弹古琴,或者喜欢去看看昆曲、看看芭蕾舞,去听听音乐会,当然太贵的学生可能负担不起,但便宜的还是可以去看的,电影也可以去看,这个很重要。当年白先勇先生的昆曲到北大来演出,我也在旁边帮助他来做,后来这个昆曲在全国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第200场纪念演出我也去看了。我们同学看了《牡丹亭》以后觉得非常好,过去大家不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美的东西。有人说青年人不喜欢这些东西,其实不对的,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看过当然就不喜欢。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牡丹亭》《红楼梦》这些经典。现在有红楼梦协会想要在我们北大普及《红楼梦》,比如有人提议在北大开一门《红楼梦》的全校通选课,我是很赞成的。因为《红楼梦》太重要了,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蕴含着许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此我自己有体会,我过去读《红楼梦》很随意,后来大学的时候又花时间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以后感到自己的文化有了大大提升。所以我们要提倡大家都来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或是艺术修养、文化素养。
学生:除了个人之外,如今的城市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就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APEC这件事情。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而言,北京是一个比较具有文化传统、文化精髓的城市,但由于企业的转型、经济的推动,如今北京也不得不面临一些在环境破坏和历史保护之间的权衡问题,这也是一种浮躁的现象。那您认为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叶朗:我觉得提高个体的文化修养是提高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文明水平的基础。
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从事各行各业,成为骨干或是成为官员,而官员对城市的建设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官员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那城市建设必然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举个二十几年前的例子,中央工艺美院,就是现在的清华美院。那里有一个老师请我去看他一个毕业生的展览,我看他们设计的那些东西非常好,比如热水瓶设计得非常美。我当时就是想去买一个雅致一点儿的热水瓶,但就是找不到。当我看到他们那个设计的时候就想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拿去生产呢?那个老师告诉我,这些学生毕业后去工厂做设计,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要厂长认可才能生产,厂长看不中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由此可见,厂长的修养很重要,厂长修养不够,再好的设计也被扼杀了。
整个民族的修养太重要了,但我们只能一步步来做。具体到个人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作为一名北大的教师,我可以通过讲课和写书来对社会产生一点影响。我们要加强大中小学的美育和艺术教育,使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小就拥有一种美的心灵,这个话讲起来好像很空,其实并不然。向孩子灌输这样一种艺术的心灵、美的心灵,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整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审美气质也都慢慢变化了,这样子城市的面貌就会改变,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
你们作为学生则要努力学习,培养自己的专业素质和文化修养,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所,就业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强调就业。一个人要学好技术、学好知识,更要拥有完满的人格和高尚的精神追求。这样不管他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人生里碰到什么坎坷,都能够继续往前走。我在这里想把冯友兰先生讲的一段话送给诸位。冯先生说:“看《西游记》的人都有一个问题,唐僧的弟子孙悟空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为什么不让孙悟空背上他,一个筋斗翻上西天,而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经历九九八十一个磨难呢?冯先生说,回答很简单,唐僧的路必须由他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否则就不能成佛。”
我们在座的同学,你们前面的路也必须你们自己一步一步地走,想一个跟头翻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中你们必然会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但是你要坚持,跌倒了爬起来,朝着一个远大的、光明的、灿烂的目标继续往前走。这样,你们终究能达到目的地,能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最后能够成佛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圣西门的家里很有钱,在他小时候他的仆人每天早上在门口喊他:“少爷,起床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我非常欣赏这句话: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你要早点起床,迎接每天的太阳,做你每天的工作。我也借此来鼓励同学们,希望你们都能经受住挫折的考验,始终盯着灿烂的人生目标,将来有所成就。
2014年11月20日下午燕南园56号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 0001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