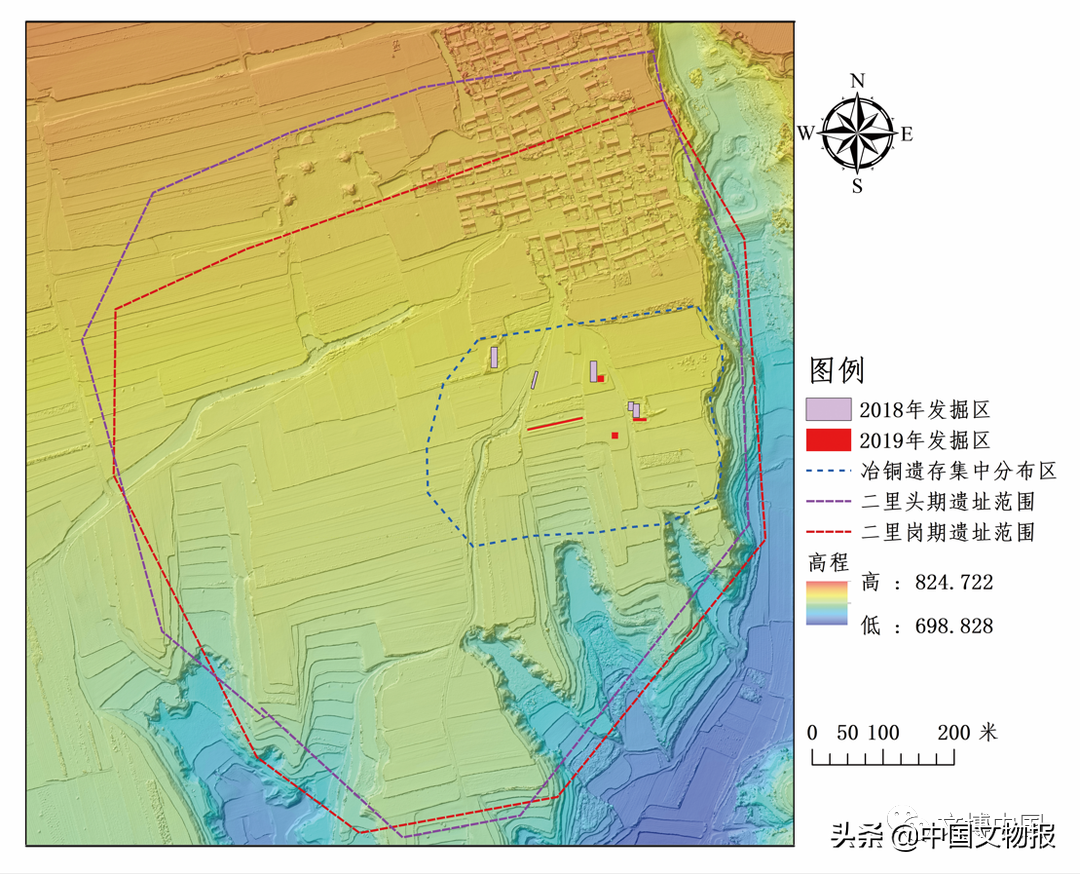甘怀真: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
一、前言
“天下”与“中国”概念是探究东亚王权的两个关键词。其中关于“天下”概念与制度,长期以来就是史学研究的课题,近年来更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① 天下研究的原因多端,而我个人作为研究者之一,目的在于探讨传统中国的政体为何。今人惯用“国家”、“帝国”一类的概念以定义或称呼传统中国的政体。但古人却自称为“天下”。故我才说“天下作为一种政体”。因此,我相信,“天下”研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是学者开始用中国史自身的语言与概念去研究中国历史。这并非是一个与西方对抗的民族主义立场与策略。而是我们相信,从中国史自身的核心概念出发,是探究真实的中国历史的重要策略。至于我们是否可以将天下概念提升为世界史的一个用语,如国家、帝国一般,目前研究仍不成熟,前路漫漫,但也值得去实验。
天下研究的现阶段须解明天下概念如何作为王权的世界像,即探讨天下如何作为一种世界观。理解古代天下观念的最大障碍是现代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的所谓启蒙与科学革命之后,我们以所谓客观实证的科学作为思考外在世界存在实态的凭借。故我们无法理解古人为何可以自称自己是居“中国”而治“天下”。我们应假设古人从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有不同的世界观。故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是来自宗教性思维方式与外在世界所产生的主观与客观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这个观点探讨天下概念的成立过程。
以下,我略谈一下方法论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概念起源研究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必须正视汉字的限制。探索概念的起源,几乎除了利用汉字史料以外,别无他法,尤其是远古阶段的概念。但古代的概念是起源于口语,借口语传播。待书写制度出现后,口语中的概念才转译为文字。近年来,海峡两岸兴起经典诠释研究。② 整体而言,经典诠释的观点主要受到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影响,它是一个哲学运动。在这个层面上,诠释学的哲学关怀无法直接适用于历史学。若我们不执着于所谓建构“中国诠释学”的意图,则诠释的研究方法仍有助于拓展史学新视野。至少启发了我们对于语言与历史关系的再思索。
就语言与历史学的关系而言,再分作两个课题:一是史料批判,二是汉字问题。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在疑古与信古之间对抗前进。无论疑古或信古,几乎所有史学家的基本信念都是要将历史建构在史料所呈现的事实上。此原理至今仍是圭臬。而诠释学告诉我们概念、语言(文字)与历史脉络之间的复杂关系。史料成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要将史料,尤其是记载史料的著作当成是一个论述。史料既包含了事实,也经常是著述者有意的连结与操弄,故史料经常没有说真话。学者应检视史料成立的过程与作者的企图,经过批判才能筛出事实。如果史料没有说真话,则史料的搜集与排比,只是复制了古人所欲建构的观点。
以本文的论题为例。我们要探讨远古以来的天下概念,必定要运用战国以后成书的诸子百家著作。这类著作记载了战国之前的史实无疑。但它们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特定历史脉络中出现的。这些著作为了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立场与观点拼凑与诠释过去的事实,更不排除伪造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在信古与疑古之间,对史料中的记录做出史料批判。③
诠释学的语言观点也引导我们重视汉字史料的问题。中国历史研究得以展开,是拜汉字史料之赐。但是汉字也会误导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不得不谨慎。从我们目前对汉字发展的新认识而言,汉字源自上古的政治系统,从政治符号转换而来。虽然我们可以推测汉字与统治者口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我们仍应视汉字所构成的汉文为一套独立的语言系统。尤其我们不能认为汉字是中国人口语的直接表现。真正能“我手写我口”要等到近代的白话文运动。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历史上的中国人而言,汉字都是外来的,其运用是要经过学习的过程。我们会认为汉字与古代日语之间存有某种翻译关系,其实汉字与中国的地方口语之间又何尝不是?因此,汉字与地方口语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如果思想是要借语言表达,而这类口语又要转换为汉字,则我们如何从汉字史料再推论当事人的思想,就不只是“让史料说话”的问题而已了。
因此,我们从诠释观点与史料批判的立场,重新探索天下概念的起源,容或有新的收获。
二、周文王神话中的天下
天下的意思当是“天之下”。过去我们在思考天下观念时,多认为天下是在表述一个地理上的平面空间,但这可能是后起的观念。在起源的阶段,如西周,此天下观当是一个立体的宇宙图像,且主要是表现在上天与下土。一般所论的“中国”相对“四方”的天下观,当成立于战国以后。
天下观的成立必须先有“上天”与“下土”的相对概念。天或上天的观念成立于何时,在中国史研究中聚讼纷纭,无法克服的原因之一,是天的概念最早是表现在口语中,而这个部分无迹可寻。当这个概念开始由语言形式转换为文字时,我们也不容易判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天”、“帝”都可能表现了口语中的“上天”的概念。且当天与帝的汉字定型化后,不同地区的使用者使用此字来表达其地方知识中与天相关的概念。但使用者使用这些文字究竟表达了何种事实,也无法得知。只想靠古文字学的钻研无法获得进一步的答案。此即历史研究中的汉字的局限性。
以目前的研究业绩为凭借,我想上天的概念至迟成立于殷周之际,至少以“天”字的成立作为判断的根据。此“天”究竟何指,虽也众说纷纭,但指宗教的天则无疑,或可笼统的说是天神。④ 与之同时成立的观念是至上神(天、帝、上帝)居于此“上天”,支配其下的人间。故天下是指此天神管辖或笼罩的区域的“下土”或“下国”,包括“下民”。推而论之,天下“概念”源于远古以来,各(大)国的统治集团认为自身统治的区域即其国或部落的天神所支配的区域。若至上神是某种之天,则各政权都可自称支配天下。即使在这个阶段没有“天下”的语汇。
我们可以推想西周以前的各个区域性王权,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都可能出现了天下概念。区域性王权首长所统治的区域亦即该首长主祭的天神所支配的区域,虽然我们可以推测不同的文化圈有不同的天神观与不同的祭祀制度。
而天下的“文字”(汉字)形成于中原王朝,最早为周王集团所使用,也一定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汉字本来就是中原王朝所独占与使用的技术。
若从文字面去追论天下观的起源,则可上溯到“周文王神话”。此神话主要表现在《诗经》中,在时间上或可追溯至西周前期。《皇矣》是《诗经》中唯一出现“天下”一词之诗篇。为讨论之便,我节录此诗如下,再加以说明: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文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这首诗叙述上帝弃绝商纣王而选择周文王。这位上帝居高高在上之“天”而“临下”。此上帝“临下”所监督的区域当即“天下”,而王者(如周文王)所对者即此“天下”。此“天下”是由“万邦”所组成,其人民即“下民”。而由于周文王受天命,故周文王为“下民之王”。
此诗表现出天下观念的初期形态,即天子与上帝(天)联结,而得以受天命治天下。在初期阶段,这种天下观相较其后儒教的理论化,具有浓厚的巫教、魔法色彩。上天与下土的联结是借由王者的上天、下地的宗教能力,并作为天与地二界的媒介。文王就是这样的宗教领袖。⑤ 如《诗经·文王》曰: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可以升天,下地,而伴随着上帝。初期天下概念中的空间,是居于上天的王者由上而下所看到的范畴。王之所以居于上天,当然是基于当时的宗教信仰。而周文王就是一类具有宗教能力的圣者(宗教领袖)。
这首诗也作为周统治者的政治论述,在说明周人之所以成为中原集团诸国的领导者的原因在于文王“在帝左右”,而得以支配下土的“天下”。《文王》之诗又说“仪刑文王”。即周人只要效法文王,即可以永保“天下”。
类似的诗句与概念也出现在《诗经》中。如《诗经·殷武》:“天命临监,下民有严。……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里出现“天”相对于“下民”、“下国”的世界像。周王所统治者即此“下民”与“下国”。另一诗《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也是“上天”相对于“下土”。
我们可以推论这种王者伴随上帝在“上天”,并受天命以统治“下土”、“下国”、“下民”的观念,即天下观的初级阶段,当完成于西周。而文王是最重要的典范,故整个政治论述以“周文王神话”为根据。
那么周王的“天下”的具体范围为何?我想只包括与周王有朝贡、册封关系诸国所构成的领域,亦即本文所谓的中原集团的诸国。这个领域是以周王为主祭者的祭祀圈。从上述“天下”理论重新理解《诗经》中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北山》),其意不是指“全世界”皆(应)是王者的统治领域,而是指同一位上帝所监临的区域内,皆是“王土”。因此,不是这位上帝(天)所监临的区域,即“天下”以外的区域内的人民,以今天的说法,是异教徒,则不生活于“王土之内”,也不是“王臣”。
三、禹传说与天下
即使我们可以从《诗经》中推论天下观念起源于周文王神话,可能流行于西周,却缺乏直接证据以证明天下一词成立于西周。近年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界宣称发现西周中期的燹公盨(遂公盨),其铭文中有“天下”一词⑥,引发学界振奋。若其说属实,则天下一词的出现可上溯至西周中期。但该器物仍存诸多疑点,信凭度亦待商榷。⑦ 在这些前提上,燹公盨铭文仍是不能直接利用的史料,至少不能当成主要证据。
燹公盨铭文的主要内容是禹治水神话。它给了我们探讨天下观念起源的另一条线索,即天下观念源起除了周文王神话之外,另外一个脉络是与禹神话间的关系。“天下”概念,尤其是“天子治天下”概念的形成,当与该铭文所载“禹敷土”的理论有关。禹敷土的理论亦见于《禹贡》。我们先分析这份文献。
《禹贡》收入今本《尚书》,属其中“夏书”的一篇。目前学者多承袭宋儒朱子以来的意见,认为《尚书》是汉人所编成的作品。但其中《禹贡》一篇当是战国时的著作。我亦持此看法。传统学者说本篇是夏代作品,从今天汉字文书演变的历史来看,自属无稽之谈。说是春秋的作品,或说是孔子所作,虽然孔子审定《诗》、《书》之说,但通观《禹贡》的知识内容,尤其是地理学的知识,当属战国时的著作无误。⑧
成文化或成书化的时间本身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成文化并不意味着该文件或文书的内容是在这个时间点才成立。《禹贡》一文成立于战国中期或其后,并不意味其内容是成立于此时且只是反映这个时期的事实。在成文化之前,人类更常运用的是口语传播。我们相信许多事实是通过口语被表达与传播,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断地被转述,故可能会转述错误,或被加上说话者的当代诠释。若燹公盨的铭文确实是西周中期,则可推知当时禹神的样态,而其中“禹敷土”的传说的成立可上溯到西周中期。但如《禹贡》所载的禹神话的内容,却待战国中期始得成立。
《禹贡》全篇的主旨是叙述禹平定山川,而规定各区域(州)的贡赋内容。它反映重要的支配原理即“为什么天子治天下之民”。《禹贡》利用禹神话的信仰,论证土地是禹所创造的,且农民耕作禹(王、天子)所造的土地,故与禹发生赋役关系,通过赋役而成立天子与民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农业化”是《禹贡》全篇的关键概念。众所周知的“大禹神话”主要事实是所谓“大禹治水”。禹治水的传说也非完全无稽,可能有其历史背景。目前的研究显示,距今五千年纪的后半,从距今约八千年前农业革命以来的农业进展,尤其是距今六千年前以来的快速发展,遇到瓶颈,甚至大幅衰退。其原因有可能是自然环境变化,在公元前三千年纪的后半到二千年间,东亚地区出现干冷化的现象,进入寒冷期。⑨ 激烈的气候变化造成中国许多地域的政治组织没落,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出现一时的衰落。其中黄河下游的平原出现洪水泛滥的现象。这可能是尧舜时期出现大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所对应的真实历史。而禹可能是约距今四千年始,某个推动且恢复农业的王权集团的部落神一类的神祇。⑩
《禹贡》一文之开头曰:“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11) 这应该是长期传说的新版。若遂公盨铭文真的是西周中期,则禹神话的早期形态的内容可由此看出一斑。该铭文曰:“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12) 所谓敷土,既有大禹治水传说通说认为是填土以塞洪水。但我们不需过度从塞洪水的角度去思考,其重点在于新生土地。即在洪水中重新生出土地。目前所见的禹治水的早期史料,都呈现这个意象。如《诗经·长发》曰: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经》的主要批注者郑玄太执着于《禹贡》的“九州岛”说,故将“敷下土方”注为“正四方”。在《诗经》的阶段,重点不在九州岛的领域,而是由天而下,建立了地上的“土方”。用另一种说法,即是建立了人间。至于“四方”、“九州岛”的概念当是后起的。《山海经·海内经》曰: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13)
今天学者多相信《山海经》虽成书较晚,却保存了不少先秦的神话传说。故我们可以推论所谓“息壤”说,可能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原始版。息壤是会不断生长的活土。《淮南子》中也有“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之说。(14) 息土与息壤为一物,指会不断生长的活土。(15) 故这个神话是说,鲧偷了这种神土,以创造洪水上的人间。但鲧的这种擅断行为,惹恼了上帝,致使鲧被处死。但是上帝还是派遣了禹在洪水上“布土”,创造了新的人间。至于禹所定的是“九州岛”,恐是战国时的说法。(16) 而这个神话被改造后,收入战国以后的所谓儒家经典,如《禹贡》。在成文化过程中,也经理性化处理,去掉了该神话中的魔法内涵。
“敷土”就是在洪水上布置土地,其后这块土地生长为“九州岛”。从这个神话的传统来看,这块土地是天(上帝)交付禹所创造的。民赖此土地为生,也因此与禹及其后传承禹的天子位的王者间建立了关系。这应是东亚王权的正当性理论的原型,也是天下理论的原型。概言之,为什么人间存在王权的支配形式,尤其是天子(王)与民的关系,是因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乃原始阶段的王者所创造的。且王权带来了农业。民居这块土地上,使用天子所传播的农业为生,故与天子之间发生政治关系。
关于王权与农业的关系,以下举《禹贡》中的冀州为例,其文曰: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17)其文先述禹治理冀州洪水的情形,举出主要的地名,包括山名、水名,如壶口、太原、岳阳、覃怀等。再叙述此地土壤的情形,如冀州是“白壤”。以及该区域的赋役的等级,如冀州是“上上错”,即主要是上上等,即九等中的第一等,但也有部分地方属第二等以下。而该地的“田”则属中中,是九等中的第五等。学者也争辩为什么田是第五等,根据何标准。我们先置之不理,至少可以知道不同区域因为土田的等第,而农民所纳之赋有所不同。其后则说因恒水与卫水得以治理,故新的土地,所谓“大陆”,得以产生。再其下有“岛夷皮服”之语。岛夷或为“鸟夷”。“皮服”则是记其为异类,表示这类“夷”是有不同的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推论,禹创造了新土壤,带来了农业,一般的民都成为农民,但其境内(不是域外)也存在着非农民,即所谓“夷”。最后则叙述该田赋的运输途径,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河”。
其他八州的叙述也是同样的形式。再举数例,以加强论证。如徐州之例:
厥土赤植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18)在徐州条中,《禹贡》同样描述了土壤与田地的状态,并制定赋的等级。并规定了冀州所没列举的“贡”,如五色土、夏翟种类的鸟、孤桐的植物与磬等。而丝织品如玄、纤、缟等也是另类贡品。此外也看到对于“淮夷”的描述,所谓“珠暨鱼”,可见这类夷是非农民的渔民。
学者或许有兴趣去考证《禹贡》中的地理名词是现今的何处,甚至去考证其所谓之“夷”是现今之何民族。此类研究的确可以有所发现,但也有可商榷处。《禹贡》成书于战国,作者的知识资源来自当时已发达的地理学。故其对于九州岛的相关地理描述,自有其信凭之处。但整体而言,《禹贡》的目的是作为王权论述,用来证明“天子治天下”,而非地理论述。
《禹贡》揉合了两种王权的理论。一种初期的理论,是至上神(天、上帝)派禹在洪水中创造了土地,使民得安居于土上。同时禹也保证了农业的实行,创造了农民。第二种当是春秋、战国的新观念,即中原王权所治的领域及于“九州岛”,此“九州岛”包括西周以来周王治下之诸侯所形成的中原国家,或称华夏,也包括此外的吴、越、楚等南方诸国,亦可包括四川盆地的巴、蜀。此区域亦即当时的“天下”。
第一种理论具东亚王权的共通性。禹治水的传说可联想日本“记纪神话”中的“苇原中国王权”的诞生。我们可以推论这是一套同样在铺陈农业王权的政治论述。相较于禹治水的神话,记纪神话更为复杂。我们可以推想保留在口语传说中的禹治水的神话原型是复杂的故事与不同的说法。而禹治水神话是被书写于公元前数百年的战国时期,限于当时的书写制度,故只留下简单的记载。另一个原因当是战国时期儒家与墨家的理性化观点的结果。相对之下,记纪神话长期存在于口语传统中,在第八世纪被成文化时,日本书写的相关制度已更加成熟,故复杂的神话得以被记载下来。就史学研究而言,自然不可以用日本记纪神话去论证中国禹治水的传说的内容,但可以去推究二者所反映的东亚王权的共通性。
记纪神话是指记载于第八世纪前期成书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神话。这些神话都有其复杂的地域性的传统,但被整合与成文化于上述二本书时,是作为天皇制的政治论述。其内容可大分为二类。
第一类是诸神的诞生,与诸神间的复杂关系。世界的形态也由诸神的活动与关系所决定。
我们可以推测,大禹治水不是孤立的神话传统,它是庞大、复杂的神话系统中的一部分,也是目前我们能知道的一部分。这个神话系统当包含诸神的历史,如其间的恩怨情仇。但这类神话传说在战国以后所成文的经典中都被理性化而多抹去,或仅留下尧、舜、鲧等传说。此外,如汉代的纬书,与《山海经》一类的典籍中,仍保留比较原始的神话传说的内容。
第二类是环绕国土诞生的诸世界的形成。此国土是“苇原中国”。此处是“天孙降临”之地,也是其后天皇统治之处。记纪神话世界的整体结构为何,众说纷纭。其中一说如下。
我们可以将神话世界的空间大分为天与地。天为“高天原”。在高天原诞生诸神,其中有天照大御神。“高天原”之诸天神,创造了一块人间之地,其中一块最丰饶之地,即“苇原中国”。而天皇之始祖是源自初始之时,天照大御神之孙神由高天原降临在“苇原中国”。故天皇拥有“苇原中国”之统治权。(19) 在记纪神话中,地尚包括海原、根之坚国、黄泉国、常世国。它们与“苇原中国”之间有诸种关系,如根之坚国赐给苇原中国以生命力,海原赐与水等。(20)
《古事记》中,在“高天原”的天神命伊耶那岐命、伊耶那美命等二位神,“修理固成”“国”。此即“地”的创造。此地是漂浮之国,是水上的诸岛,最后生成的是所谓“大八岛国”。苇原中国也被解释为大八岛国,亦即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列岛。这个传说与大禹治水的相似点是国土生于水上。虽然《古事记》没有治洪水的说法,却记载了所谓“修理固成”,即修理水上之土地。这也是“上天创造下土”的模式。在记纪神话中,此天可以是《古事记》中的“高天原”。其所创造的下土,部分是居海中的土地,其中的中央即王者(或天皇)所治的苇原中国。
苇原中国的成立与农耕社会的成立有关。苇原的意象是一片农业的土壤。或许在早期信仰中,苇与召唤谷灵的仪式有关。故有学者称之为“始源之田圃”。这里的农业尤其是指稻作,所谓“水穗”。(21) 此苇原中国是其后“天孙降临”之所。借由这些神话的串联,日本的天皇制取得作为农业王权的正当性。
《古事记》所载神话与禹神话也有很多类似之处。这不是偶然,因为二者都表现同样的王权论述,包括“上天创造下土”与“农业王权”。且二者都基于类似的宗教信念。所谓“九州岛”说类似于“大八岛国”,都是水上的土地。《说文》解“州”为“水中可居曰州”。(22)《禹贡》的九州岛意象即是水中可居之地。
远古神话传说的考证非我所长,本文也就不追究。禹传说的起源自是一学术课题,论者多矣。或有学者以为禹的出现是作为西南夷之古羌人的信仰之神话。(23) 即使有此可能,从禹神话起源之后,禹的信仰当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广泛地被接受,包括中原地区。至战国时期,中原国家的官方祭祀中所表现的禹神话中,禹都是农业的创造者。《孟子》的记载当是这个神话传统的反映,且极为生动,如《滕文公上》曰:
当尧之时,天下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24)这段话出现了本文所探究的两个关键词,即天下与中国。孟子之时的战国中期,古代圣王所治之范畴为天下的信念或知识已成立。其中“禹治九河”以至“中国可得而食也”之语,若与《禹贡》合观,则可知禹在洪水上敷土,为“天下”带来了农业。其中“中国”也因恢复农业,而人民得经营生业。
然而,大禹治水神话的原始形态已不可考。我们一方面推想其原初的形态应包含更多的诸神魔法等宗教内涵。另一方面,若以现在儒墨经典所见的大禹治水传说与记纪神话比较,可以发现二个重大的差别。
一是诸神的历史消失了。二,在宇宙创造的过程中,性的重要性完全看不到。就第一点来说,我也曾指出,中国儒教的祭祀理论没有日本神话中的诸神的历史。儒教的天神皆为非历史的存在,即这些神没有宇宙间活动的记录,没有神话传说。这种形态的天神观影响了中国王权(皇帝制度)的性质。(25)
就“性”的内容而言,在记纪神话中,诸神之间的性交与生产过程,是宇宙形成的动因。但这个因素在儒教的祭祀理论与宇宙观中完全不见。相对于性,儒家的祭祀理论是由“食”所构成,强调人与诸神间的共食关系。
最后,关于禹“敷土”的说法,表现在《禹贡》中,并未明言是谁派禹从事这些水土工作。历来的注释家因受到古史系统论的影响,不假思索的认为派禹治水者一定是帝尧与帝舜。但就《禹贡》而言,所谓古史系统不是不言自明。《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被编入《尚书》是战国以至汉人之作。我们不能以《尚书》中的其他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的帝王系统学说去推论《禹贡》。如《禹贡》最后一句:“禹锡玄圭,告厥功成”目前有三解。一是有批注家认为是“禹献玄圭于天子。”(26) 这是因为相信舜派禹治水而尧、舜、禹三帝王相承的古史系统论。第二说则更古,至少上溯自《史记》,认为是天子(尧、舜)赐给重臣(禹)以玄圭。此考证或有离题之嫌,故不细加论辩。《史记》要建立其古史的系统,而决定以黄帝为信史之首,其后接尧、舜与三代。在这样的历史图像中,“禹锡玄珪”被解为尧帝赐禹以玄珪,故《夏本纪》曰:“(尧)帝锡禹玄圭。”于是其后的批注家多从司马迁之说。晋孔安国的所谓“伪传”以来,也多持此说。(27)
然而,此处的“禹锡玄圭”,当是天赐禹以玄圭,以奖励禹治水土之功。这是古代的“物”的信仰。天对天子赐下“物”,如玄圭一类。这类物是王权的证据,而它们来自至上天神。汉代的纬书《尚书璇玑钤》屯有这么一段记载:“禹开龙门,导积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28) 此纬书成立于汉代,当记载了上古以来的神话,在成文化的过程中,作了若干修饰或改造,其内容是说禹在治水土的过程中,在龙门之地得到玄圭。至于其所说上面刻有禹受天命之说,当是汉代之人根据当时的受命之说而有所添加的。
另一证据是燹公盨。其铭文明言:“天命禹敷土。”(29) 我们可以相信这是禹治水土的原始版说法。战国时的《禹贡》在成书时,亦持此说法。
我们可以推想,自西周初年以来,中原王权的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及黄河下游、淮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等。周王权为了加强自身支配的正当性,运用了当时广为存在的禹神话,将天下定义为“禹迹”。这使得周王所统治的“天下”都源于一位创造者:禹。此即《禹贡》所载禹神话的原型。而其重点为燹公盨所载的“天命禹敷土”。此禹神话是陈述禹受上天之帝之命,在人间浩瀚的水上,铺设土地,并带来农业。于是古来的“天下”概念就更具体为禹所经营之土地,即所谓“禹迹”。(30)
禹带来了农业之说,在古史研究中,已是非常清楚。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还原到神话信仰中。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禹是后土之神,而后稷是谷神。周人巧妙将其祖先神后稷与造大地的信仰结合,故有“后稷封殖天下”(31) 之说。周王之所以治天下,是因为其始祖神后稷推行农业于天下。这也是农业王权的论证。我们可以推论,中原王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农业。亦如上述《禹贡》所论,凡服从于此王权者为“民”,即农民。而不愿从事农业者即“夷”一类的非我族类。
四、霸王政治与天下理论
前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天下观念如何从周文王神话与禹传说中发展而成。故我们可以说天下观念的源起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然而,这个宗教性的主观世界像(即天下概念)不会无媒介与无过程的成为中国王权(指皇帝制度)的政治原理。因此,以下接着讨论了此天下观如何在春秋、战国期间的霸王政治脉络中确立下来,而为其后的皇帝制度所继承。
所谓霸王政治,指春秋中期以后,以大国君主为首的国际联盟形成,于是出现新形态的政治结构与秩序。这其中相关史实,夙为学者所知。但历来学者多将春秋战国时期的霸者,如齐桓公、晋文公一类君主的出现,视为周王权的变态。然而,这种观点是受到战国学者的历史论述的导引,而突出表现在司马迁《史记》中,其结论是证明周—秦—汉的相承与正统性。就王权研究的立场而言,我们应视霸王政治是中国王权的一个阶段。但这个课题另当别论,本文只说明霸王政体的出现如何确立了其后的天下观念。
让我们重新检视春秋战国的历史。过去我们对于春秋战国历史的理解多依从战国后期至汉代学者的历史论述。(32) 这个论述,简单而言,即“周王权衰弱”说。原本强大的西周王权因故在春秋之后衰微,于是原服属周王的诸大国从周王的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进而无视甚至僭越周王权,而各自发展其势力。这套学说中的诸事实并非全然假造,但整体的历史像却是虚构的。战国的统治集团为创造继承周王的新王的王权理论,故假托历史上曾出现强大且统一的周王权。这个历史的(西)周王,曾支配战国人所认为的“天下”。此学说又为汉代学者所继承,用以宣告秦朝与汉朝是继承周王权及其支配领域,此领域即“天下”。
目前我们对于西周王权的形态,无法究明之处甚多。且诸学说中的异同,我也没有能力断定是非。(33) 容我从我的观点简略描述周王权。周王自西周始,在一个广域内拥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与统治权,以汉字表现即“王”者,亦有称“天子”。但其权力的展现,从比较王权的角度,主要是“祭祀王”。周王只是广域的祭祀圈内主祭者。参与祭祀者主要是华北的诸国君主。我们不能将西周王权想象是专制君主在上,而君臣关系严密的政治形态。周王与服属之国之间有册封、朝贡与共同祭祀的关系。周王与诸国君主间的关系主要是礼物交换与汉字的赠与,此即所谓朝贡与册封体系的初期形态。
大国崛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这些大国的出现是古来文化地域的诸政权整合的结果。如燕辽区出现燕国、海岱区出现齐国、江浙区出现吴国、中原区出现晋国、甘青区出现秦国、两湖区出现楚国等。这些大国,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一方面对内加强支配力,提升国君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对外联结诸大国,并试图在国际间建立自己的霸权。
春秋时期,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秩序,即霸者成立,于是有我所说的霸王政治。我们应视这种政治形态为新的王权,在时间上介乎周封建与皇帝制度之间。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可以预设皇帝制度的理念是继承自霸王政治,而非周封建。天下理论成为中国王权的主要政治论述是成立在霸王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目前我们对于春秋以至战国时期的“霸王”的王权不甚理解,其研究尚待开展。先简单析论如下。这类的霸王是一种新形态的王权,其性质可借司马迁对于项羽作为“霸王”的说法表明,即“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34) 司马迁的说法诚良史之见识。霸者的王权即“以力经营天下”。或许我们可以用“战争王”定义之。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春秋以来的霸者欲“以力经营天下”,却无法建构独立的王权。故这些霸者,如齐桓公、晋文公,在建构其国际间的霸权时,都采用了借助周王权威的策略,主要是周王的祭祀权。
春秋以来的“尊王”之议,其目的之一是要借助周王的祭祀权,以辅助霸者自身不成熟的战争王形态的王权,并用以团结北方诸国。其他诸大国君主之所以呼应霸者而加入尊王的政治运动,是意图借由这项政治主张以加强其在国内的支配权,如伸张对于国内其他都市(被称为“大夫”阶层所支配的都市)的支配权。但这是复杂的政治过程,也离题稍远,容此处略去不论。(35)
再回顾历史,春秋以来,北方诸国与南方的吴、越、楚等国发生战争。借由这些交流,新的国际秩序逐步建立,而主要的结果是南北诸集团的整合。霸者的“以力经营天下”的秩序原理表现在诸国会盟时,各自展示军事实力,而推出诸集团联盟的霸主,即战争王。(36) 于是我们看到如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脱颖而出。
借由霸主性质的战争王的体制,诸国间的联盟体制也逐步成型。这是“天下”的原型,也是其后“天下”的空间范畴的基础。历史上的重要概念的诞生不会只是观念的游戏,一定也是历史脉络下的产物。先秦“天下”概念成型的历史脉络之一,是春秋以来的霸者所主导的会盟政治。参与会盟的诸集团、诸国家所建构的政治空间即当时人所认识的“天下”。《论语·宪问》记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句话。自齐桓公的霸业始,北方集团与南方集团开始联盟,一个新的“天下”诞生。这句话是否真的是孔子如实之言的记录,亦须谨慎。至少将之视为战国人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意味南方楚国等在内的领域也是周王支配的固有“天下”。但这是当时中原国家的政治论述所塑造的历史像,故意将楚、吴、越等国君视为历史上周王的“诸侯”。
而到战国中期,周王的权威崩溃,中原诸国竞相称王,诸国君宣告自己是最有资格继承周王的地位的新王。如公元前351年魏国国君称惠成王,前339年齐国国君称威宣王,前326年赵武灵王即位,后一年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23年燕易王称王,前322年韩宣惠王称王。新的王者的理论是宣告自己是包括北方诸国、南方诸国在内的“天下”的最高政治领袖。于是王者所治是“天下”的想法确立下来。
战国中期,周王职位已名实俱亡,政治社会在期待新王。(37) 于是各国不同的政治、学术集团书写各自的典籍以创造新王的理论。这些典籍构成所谓诸子百家著作的大部分。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礼》等。这位被期待的新王,被认为是周王的继承者,也是“天下”的统治者。历史上周王也被形塑为理想上的王者,尤其是西周之文、武、成王与周公。而当时所认为的天下,是当时北方的霸王政治体制所认识的天下。这个天下也为其后的秦始皇所继承。
这种天下观念是一套战国的政治论述。虽然其内容包含若干事实,但将北方集团与南方集团诸国视为是历史上(西周)的周王支配领域,却是虚构。在这个天下论述中,周王被想象成曾统治包含楚、吴、越、巴、蜀等地,是“天下”的统治者,而非北方诸国的共主而已。春秋、战国以后,楚、吴、越诸国与北方诸国(如齐、晋等)发生外交、战争与文化交流等诸种关系,此类史实非常明显。但这类事实却被中原国家改造,说成是楚、吴、越诸国是在竞争一个原本由周王所支配的“天下”的主导权。“战国七雄”之说就是这种论述的产物。“七雄”之说当源自秦始皇灭“六国”。此六国加上秦国自身,即所谓“七雄”。(38) 此七国中,包括南方的楚国。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此七国都曾是周王的诸侯。如东汉班固所言:
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39)这是典型的汉代学者的历史像。在他们所建构的周代历史中,战国诸国,如“战国七雄”所代表,都曾是周王的“侯伯”。因为周王权力在春秋以后下坠,故周王领域内的诸强国,彼此竞争,于是分裂诸夏。
上述《禹贡》的“禹敷土”的论述就是形成于这个脉络下。春秋战国时期扩大的天下领域概念也表现在战国的“禹贡”思想中。换言之,《禹贡》是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霸王政治的历史脉络中。具体而言即“九州岛”概念的诞生。(40)《禹贡》将大地分为九州岛,其区域包括上述的北方诸国与南方的吴、越、楚等。禹治理的“天下”即其后天子当统治的区域。这个说法也将原属不同政治版图的各集团整合为一个天下之内。《禹贡》说:“九州岛攸同。”(41) 这个“九州岛”的范畴即战国时期南北诸国通过霸者主持会盟整合而成的领域,而不是周王所支配的领域。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上述空间范畴的天下观已在战国中期成立,并成为其后“新王”的支配理论。我想已不用再详细说明,这个天下观不是西周的天下观。西周的天下是与上天相对之空间。战国中的诸论述都清楚指出此天下是北方诸国与吴、越、楚的整合。举一例如《周礼》中的“职方氏”,其文曰: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乃辨九州岛之国,使同贯利。(42)此“天下之图”、“天下之地”包含蛮夷戎狄之民。此范围亦即九州岛。所谓九州岛,在战国时期当是固定的概念,即《禹贡》所载。此段《周礼·职方氏》的下文是如《禹贡》的九州岛论述,说明九州岛的人民状态与农业的情形。(43)此九州岛是: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此九州岛的范围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集团诸国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
这样的天下领域观当在战国中期起已成为共识。即华北黄河流域,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并扩及华西的甘肃;以及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这个区域即“天下”,亦即继周王的新王应支配的领域。《吕氏春秋·有始览》理解并诠释当时的九州岛说,有下面的发挥:
何谓九州岛?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44)此九州岛说的特色在于说明九州岛是相应于春秋、战国的大国。也如我反复说明,这是一个战国的历史论述,将春秋战国之大国视为历史上周王之治之天下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所说的“诸子百家”的著作,多成立于战国中期以后,亦即在此“天下”观念成立的历史脉络上。综观这些著作,多借由编造“三代”的史实,以论证王者或天子曾支配当时所认为的“天下”,也同时提出学者所认为的理想政体。这类著作是根据周封建的历史经验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崛起、国君权力上升的现况,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政体。这种政体是以某大国国君为天下之共主,称为王与天子。其他大国国君为诸侯,其下还有卿、大夫等封建等级。代表者如《礼记》中的《王制》与《周礼》。
我们可以推论秦始皇的天下观,就领域范围的认识这一点而言,是同于战国中期以来的思潮。当秦始皇在战国的最后阶段异军突起,自认为是继周王的新王,故其统治的领域即包含战国七大国在内的“天下”。也因此当秦始皇征服了六国后,基于当时的天下观而宣告自己“并天下”。(45) 虽然另一面,秦始皇推行的是军事征服体制的郡县制,而非上述战国学者所设计的封建制。
五、结语
本文立足于诠释方法中的史料批判立场,重新探索中国的天下概念的成立过程。尤其是该概念在春秋战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而如何成为其后皇帝制度的主要支配理念。
天下概念发生于远古的早期王权(或称邦酋、首长制)的历史脉络中。当时地域统治者主张其所统治的区域是其所祭祀的主神所支配的领域。至迟在西周时期,当这位统治者所祭祀的主神为天(上帝)时,王者便宣告其所统治的是“天下”。我们能考察的最明显事证是周文王神话。而禹神话则是另一个阶段。从王权理论来看,禹神话所反映的天下观的重点,在于王者(天子)创造了大地,而“民”在此下土得以进行以农业为主的各种生业。于是天子(王、君)与民的关系是以土地及生产物为媒介。这些生产物以赋役的形式缴纳给天子,作为天子赐给他们土地与生产物的回报。此即赋役制度成立的理论。《禹贡》曰:“成赋中邦。”(46) 九州岛内之赋,皆运往“中邦”。此“中邦”即“中国”。(47)《禹贡》的理论是九州岛生产物所征调之赋要交给居“中国”之天子。于是《禹贡》也奠定了其后皇帝制度的核心概念:“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本文也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霸王政治”与天下概念形成的关系。这是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值得史家重建。本文说明了霸王政治促成了原属于周王集团的北方诸国与不属于周王集团的南方诸国的整合。霸者的特质是战争王,但其王权理论仍需借助周王所拥有的祭祀权威,即天下理论。战国的学者运用既有的天下理论,加以改造以说明当时涵盖南北诸国的新的政治领域。此领域被认为是周王曾支配的“天下”。这个天下概念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所运用与发挥,以作为即将登场的新王的王权理论。秦始皇的“六王毕,四海一”或许是战国历史发展的意外,但秦始皇仍继承了战国的天下观念,故宣称自己“并天下”而为皇帝。
注释:
① 我目前所见,最完整的学说史回顾见游逸飞《四方、天下、郡国——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变革与发展》,第一章《研究回顾与反思》,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版。中国史部分,我个人如《“天下”观念的再检讨》,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秦汉的“天下”政体:以郊祀礼改革为中心》,《新史学》16:4,2005年12月版。
② 我个人参与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也作过介绍,参见甘怀真《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
③ 可参考拙著《从历史论述中解放出来:读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有感》,《文化研究》5,2007年版。
④ 此应是共识,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08页。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台北:允晨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6页。
⑤ 文王的宗教性的讨论,进一步可参考白川静《中国古代の文化》,东京:讲谈社1979年版,第31—40页。
⑥ 见保利艺术博物馆编《燹公盨:大禹治水为政以德》,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一书诸作者的考证,有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亦参考周凤五《遂公盨铭初探》,《华学》6,2003年6月版。
⑦ 其讨论参考竹内康浩《燹公盨の资料的问题について》,《史学杂志》115:1,2006年版;平势隆郎《战国时代的天下与其下的中国、夏等特别领域》,《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第82页。
⑧ 屈万里认为是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其说值得参考,见《论禹贡著成的时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1964年版。
⑨ 近十年来,无论从自然科学或历史学、考古学出发的相关的研究甚多,如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5:6,2005年版;王绍武《全新世中期的旱涝变化与中华古文明的进程》,《自然科学进展》16:10,2006年版。通论性研究可参考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市:允晨文化1997年版,第45页;安田喜宪《気候と之文明の盛衰》,朝仓书店2005年版。
⑩ 大禹的性格问题,从《古史辨》以来就是疑古与信古之间的最大争辩,争议之文,汗牛充栋。我想顾颉刚最初的论断仍然是最正确的,即禹是天所派来之神。见顾颉刚《鲧禹的传说》,《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 《尚书·禹贡》,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影印阮元校十三经本,第5页。
(12) 根据裘锡圭《燹公盨铭文考释》,保利艺术博物馆编《燹公盨:大禹治水为政以德》,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36页。以现行文字释之。
(13)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72页。
(14)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页。
(15) 根据《山海经》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16) 我也不排除九州岛一说在春秋晚期已出现。现存“叔尸钟铭文”有:“咸有九州岛,处禹之堵”之文。有研究者认为该器物是春秋晚期齐灵公时所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0页。《左传》中亦有数例,但皆存在于对话中,其信凭度应存疑。
(17) 屈万里《尚书集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8页。
(18) 屈万里《尚书集释》,第53页。
(19) 如水林彪研究《古事记》中的天皇像的创造,如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现御神”等理论的创造。相关的理论使得日本的王权成为一种人间主宰的王权,参考氏著《律令天皇制の神话的コスモロジ一:初期宣命おょび‘古事记’の天皇像》,收入《王権のコスモロジ一》,东京:弘文堂1998年版。
(20) 参考水林彪《记纪神话と王権の祭り》,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123—126页。
(21) 引自神野志隆光《古事记の世界覌》,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152页。
(22) 《说文解字注》,台北:汉京1983年版,第574页。
(23) 工藤元男《禹の伝承なぬぐゐ中华世界と周缘》,《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の形成と东方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版。
(24) 另一位有贡献者是益,他带来了火。
(25) 甘怀真《大唐开元礼中的天神观》,收入《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 屈力里《尚书集释》,第72页。
(27) 为孔传的错误早在顾颉刚的“古史辨”期间已被明白指出,见氏著《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第95、96页。
(28)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重修纬书集成》第二册,东京:明德1971年版,第59页。
(29) 见前引裘锡圭《燹公盨铭文考释》,第36页。
(30) 此天下为禹迹之说,参考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文史》,1992年版,第34页。
(31) 《左传》,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影印阮元校十三经本,第779页。
(32) 对春秋战国历史论述的研究,参考平势隆郎的一些著作,代表者如平势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华へ:殷周 春秋戦国》,东京:讲谈社2005年版。
(33) 较近期的学说史回顾,可参考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第一章《序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4) 《史记》卷七,第338页。
(35) 参考平势隆郎《第四章 霸者》,松丸道雄等编《中国史1—先史—后汉》,东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版。
(36) 会盟也有其宗教性,自不迨言。参考吕静《春秋时期盟哲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7) 参考拙作《秦汉的“天下”政体:以郊祀礼改革为中心》,《新史学》16:4,2005年12月版。
(38) 参考杨宽《七国考》,《战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9) 《汉书》卷一百上,第4227页。
(40) 《禹贡》中的“九州岛”概念的研究,可推到20世纪前期的“古史辩”运动,历来受到重视,相关学说史的整理参考陈穗铮《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版,第164—167页。我也参考诸家之说,如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胡阿祥《“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岛”论述》,唐晓峰等编《九州岛》3,2003年版;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平势隆郎《战国时代的天下与其下的中国、夏等特别领域》,收入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
(41) 屈万里《尚书集释》,第70页。
(42)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59—61页。
(43)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五册,第62—87页。
(44)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2—663页。
(45) “并天下”的说明,参考拙作《“天下”观念的再检讨》,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
(46) “并天下”的说明,参考拙作《“天下”观念的再检讨》。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
(47) 平势隆郎《都市国家から中华へ:殷周 春秋戦国》,东京:讲谈社2005年版,第169页。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010年第9辑
- 0000
- 0001
- 0004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