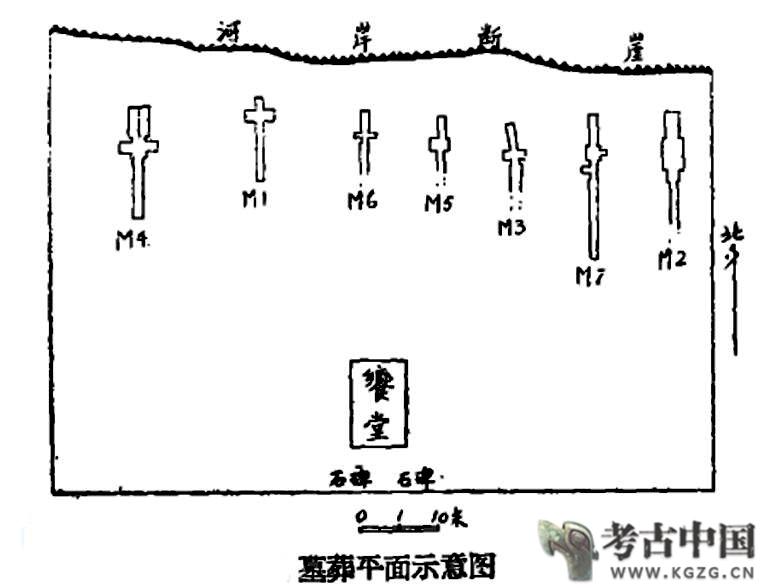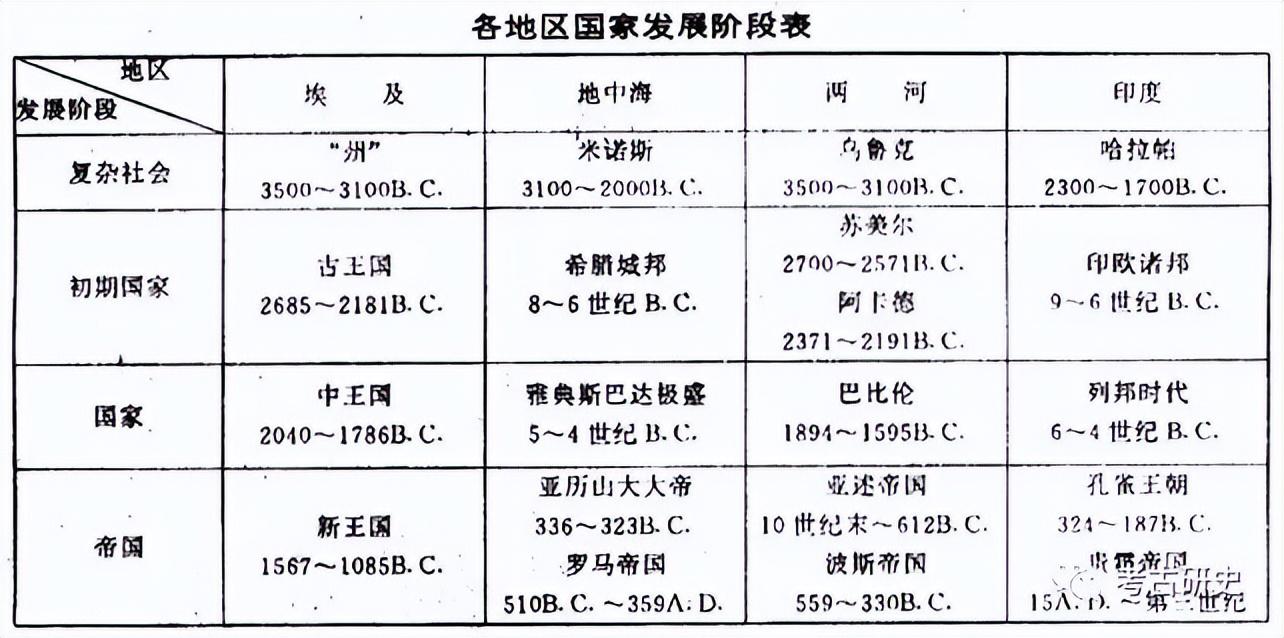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摘要:商周之际天命观念的变革,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人文精神的跃动和觉醒,并非周人天命观念的全部内容。在翦商及建国过程中,周人基于现实需要而宣传天命。周人与殷人的天命论并非迥然有别。西周以降,周人的天命论绝非沿理性的轨道做直线式发展。理性中夹杂非理性,觉醒与非觉醒相交织的状态,仍然是“精神觉醒”后周之上层思想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关键词:殷周变革 德 天命观
对于商周之际天命观念的变革以及周人天命观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学者曾以“人道主义之黎明”,[1]“人文精神的跃动”[2]等加以描述、概括。众多学者指出,周人“天命靡常”、“敬天保民”观念的提出,意味着周人抛弃殷人徒恃天命以为生的观念,转向寻求明德以为永命之基。此一关键性转捩造成殷商命定之天向周人道德之天的转变,理性精神亦随之出现,继而得以发扬光大,从此成为传统文化的正统,声威远被。
周人天命观念的变革,在文化史上的确具划时代意义。可是,如若考察周人天命观的完整意义,而不只注重于其中的理性因素,则可见周人的天命观显现出不为平常所注重的多样性来。应当说,学者称之为周人天命观所表现的人文精神的跃动、人类精神的觉醒,是周人天命观中至为重要的内容,但是理性因素并不是周人天命观的全部。并且,周人的天命观念并不是沿着理性的轨迹直线发展,相反周代历史发展中反复出现非理性因素。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相纠缠、觉醒之后仍有非觉醒的状态引人深思,“人类精神觉醒”之后的思想状况也值得进一步探究。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多瞩目于周人天命观中的理性因素,而对天命蕴涵的其他意义以及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关注不够。本文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考察殷周天命观的异同,揭示周人天命观的意义,缕析周人天命观念的变化,意在由此窥见周人天命观念的总体轮廓。
一、周初的天命论及其意义
周初天命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分析该时期天命观包含的因素,有益于了解周人天命论的完整意义以及此后周人天命观发展变化的线索。
青铜铭文中的“天命”一词,最早见于成王时期的《何尊》。是器记载周成王诰教宗小子,谓“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大兹令”,[3]其诰辞明确提到文王受大令(天命)。周初人所说的文王受天命,其旨意何在?由《何尊》铭上下文意看,它无疑有君权天授的意蕴。《何尊》记载成王在诰宗小子辞中,特别提到“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4]武王克商后,特意向天做出汇报,此举正如《尚书·多士》所说“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日:割殷,告敕于帝”,克殷之后,将此消息祭告于天。在告天之辞中,武王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意谓我将在中心区域行建制,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武王诰天及其诰辞透露出,武王对于天十分仰赖与敬畏。惟其诰天,获得天命的认可,才拥有合理的统治中国之权。由《何尊》分析,当周人的天命观成熟之时,其主要内容是宣扬文王受天命、武王攻克殷纣,意在强调周人取得政权合于天意,具有绝对的正当性。这层意思在传世文献中所记甚多,[5]如《尚书·多士》录周公之语,谓“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意谓上天终止殷之命,而眷顾于周,周人由此获得统治权。很显然,“文王受天命”是周人对自己获得政权的认识与解释。这应当是周初人们宣传文王受命的根本意义所在。
周人宣扬文、武受命,主要从文德和武功两方面入手,[6]至汉代《史记·周本纪》、《尚书大传》讲周之受命仍无外于这一思路。此外,纬书中“洛出书”、“赤雀衔丹书入于丰”,[7]等以祥瑞来宣扬周人受命的说法,皆被指不可信。但新近刊布的清华简《程寤》篇也记载有文武受命的内容,与传统之论有所不同,值得注意:
隹王元祀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械柞。寤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俾灵名凶,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幣告宗枋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蚕,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8]
简文之意谓周人受皇上帝之命,天命由商转移至周。而显示受命的事件,则是太姒之梦。梦中,商人之廷生棘,太子发将周廷中的梓植于商廷,长出松柏棫柞。太姒梦醒后,文王举行了消除灾害的“祓”,并祈祷于宗庙社稷山川,责骂商人之神,举行郊祭、冬日之祭,占卜于明堂,遂受命于皇上帝。显而易见,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以文德、武功来宣传周人受命的说法不同,这里用以显现受命的竟是太姒之梦。从其他文献看,周人对此梦十分在意。《逸周书·文做》记载:“维文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日:汝敬之哉!”前人指出,这里的告梦,“即告《程寤》之梦”,在文、武王并拜吉梦后,“作此篇以儆太子发”,“此因拜受吉梦于明堂之后,恐后嗣以吉祥废人事也”,[9]是说文王对于太姒之梦格外重视,竞担心武王依恃“吉梦”而不知奋发,所以特别告诫武王当借助吉梦而更加黾勉从事。[10]此外,《吕氏春秋·诚廉》篇记载,殷周之际,伯夷、叔齐批评周人“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毕沅指出“扬梦以说众”,就是《程寤》篇所记之梦。[11]按照伯夷、叔齐所说,殷周变革之际,在“杀伐”之外,“扬梦”是周人所运用的“翦商”的重要方法。如是,则太姒之梦的意义非同凡响。《程寤》篇所记,包含战国时人对文王受命的理解,但揆诸《吕氏春秋》所载伯夷、叔齐之说,似乎周人“扬梦”有可能源自比较早期的说法,尚有部分史影为之素地。若果,则可说在文德、武功之外,周人又以征象来宣扬受命。宣传征象或祥瑞,无非就是使笼罩在天命之下的民众能够从心理上、观念上,较为容易地接受周人将受天命这一事实。因此,宣扬文王之德、鼓吹太姒之梦,都是为适应当时的情势,为殷周天命的转换制造舆论影响。
周人建国后,文王或文武王受“天命”(大令)的说法不断被加深、巩固,但凡忆及周人代殷,或祖述先王之德,“丕显文武膺受大令”都是周人有言必称的内容,[12]这一观念在周人的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成为周王朝立国的根据。除此之外,天命又是周王朝用以号召民众,巩固周邦的重要手段。青铜铭文中常常可见,周王告诫同姓或异族领袖,他们的祖先辅弼文武王,顺应天命。言外之意,作为后代的他们应当继续顺服周天子,唯有如此才能顺遂大命,获得护佑。如穆王时期《彔伯<冬戈>簋》记载:“王若曰……自乃祖考有恪于周邦,右(佑)辟四方,惠圅天命。”(《集成》04302)录(彔)伯为录国首领,非姬周族。[13]是器记载穆王追溯录伯的祖先敬于周邦,协助开拓疆土,天命仁惠宽大,至录伯则当“女肇不墜”,不废弃先祖的功业,继续辅弼周王。恭王时期《乖伯簋》记录:“王若日:乖伯……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有革(当)于大命。”(《集成》04331)铭文辞记载乖伯之祖从自己的国中来到周邦辅佐周先王,符合天命,而乖伯则协助益公奉周王之命“征眉敖”,光大先祖之业。显然,对于非姬周族来说,天命是周人极具号召力的法宝。在周族内部,天命同样具有感召力。共王时期《询簋》记载:“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令,则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集成》04321)周王说在文武受命之时,询之先祖即辅翊周王,如今王再次任命询,以克弼周王,顺从天命。西周晚期《单伯昊生钟》记载“单伯吴生日:丕显皇祖烈考,徕匹之王,恪谨大令(命)。余小子肇帅井朕皇祖考懿德,用保奠”(《集成》00082)。单伯吴生白谓其先祖辅佐周先王恪守天命,而他则将秉持先祖之德,捍卫周王。对于同族或异族,周王或周之上层皆以天命为号召,如此之类,青铜铭文中不一而足。这些铭文显示“天命”不仅是周王朝“革殷”立国的根本依据,而且对于周人维持统治亦具重大现实意义。
概括而言,周初之时,周人宣扬文武受天命,此时的天命包含“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这样统御四境、具有绝对权威的意蕴。周初乃至有周一代,周人极力以不同的方式宣扬文武受命。考诸当时的情境,可说周人宣传天命,并非急迫地想要进行思想上的变革,而是适应现实之形势,为王朝的建立寻找依托,并以此晓喻天下周革殷之正当与合理。换言之,立国之际,周人的当务之急不是思想革命,而是政权过渡。即便是在建国之后,周人不断加深受命之观念,亦是出自巩固周邦的需要。因此,前辈学者所称的“理性的觉醒”的出现,实有赖于现实情境的需要。若只强调周人天命论中的理性因素,而忽视天命之于周人的现实意义,则无从理解周人为何总是藉天命讲王朝代易,为何始终高悬天命之帜以相号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此后天命观的发展与嬗变。
二、“德”与周人的天命观
周人天命观大异于商人之处,在于提出天命不于常的观念,并将道德因素注入天命之中,天命依人事而变易,从而否定了天之于人的绝对意志。[14]毫无疑问,周人注意到天命不专佑一家,不可常赖,这是周人的高明之处。然而需要深究的是,周人注入天命中的“德”,其所指内容是否如学者所说为道德之德,是主观方面的修养以及正心修身的功夫?[15]
应当说,周人之“德”确实包含道德方面的含义。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周初时期,“德”并不是道德,而是指具体的统治方法或周人具体所得。典型者如《尚书·康诰》中“明德慎罚”与“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德”与“罚”并列。对此,学者指出,“‘德’是施以恩惠使人柔服。‘刑’与‘罚’就是暴力惩罚。所以这里的德是指具体地给以恩赏,与具体地给以刑罚相并提的”。[16]据此,“明德慎罚”之“德”尚不能理解为道德之德。而“肆王惟德用”以及“肆惟王其疾敬德”之“德”,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得”而非道德。《梓材》中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是说上天已将中国之民以及大片土地交付先王,王则敬用其得(即上天之所交付)。而《召诰》中所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其所敬之“德”,亦可理解为“敬所得”,就是敬天所命之哲、吉凶、历年。因此,传世文献中,周人之德虽然已有伦理道德的含义,但在许多情况下,德是指周人具体所得(特别是得自于天)、指具体的统治术(怀柔民众),尚不能说周人之德皆为道德之德。
青铜铭文中亦有不少“德”的记载,且与天命相联,分析上下文意,有益于了解“德”的具体内容,以及德与天命的关系。青铜铭文显示,早在周初,周人已将天命与德联系起来。周初器《何尊》在讲到文王受天命、武王诏告于天后,继续说到成王对宗小子行告诫、,云“尔有虽小子无识,睨于公氏,有爵于天,徹令敬享哉”。《何尊》并谓“惟王恭德谷(裕)天,顺我不敏”。“睨”即“视”,引申为效法;“爵”,学者释为劳、恪等,表示恭敬。是说成王告诫宗小子要看到并效法父考公氏,其具体内容就是谨敬上天,通达命令、敬事奉上。可见,行为准则中,排列在最先的是对天的恭敬、顺从,其次是对在上者的敬奉。“惟王恭德谷(裕)天,顺我不敏”,是赞颂时王的语汇。“裕天”学者释为顺应天,[17]而“恭德”,具体含义无法确指,但从其与“裕天”相联看,“德”显然不是抽象的道德。由《何尊》所记可说,周初之“德”确乎包含着人事方面的内容,但“德”同时与天紧密相联。
西周中期以来,“德”更常见于彝铭当中。著名的《大盂鼎》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今我隹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命二三正”。由铭辞看,所谓“文王正德”就是文王任命适合的官正,“德”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修养。[18]铭辞又称,王告诫盂,“敬雝德经”,学者倾向于将“德”与“经”解释为道德与准则。那么,道德与准则具体何指?分析上下文意,应当就是后文所说的“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即勤敬王事,畏服天命。总之,这里的“德”指治国、执行政事时的具体原则。再如,西周穆王时期的《班簋》铭文亦谈到“德”,此铭记载毛公班告事成功于王,说:“隹民亡<彳{止口}>哉,彝昧天令,故亡;允才(哉)显,隹敬德,亡攸违。”(《集成》04341)意谓民不明天命,故亡;显明的是敬德,则无所违。“敬德”与“彝昧天令”相对,显而易见,敬德当与恭敬天命有关。
西周中晚期以后,周人对于文王受命之事仍然津津乐道,他们将文王之德与天命相联,如《墙盘》谓“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途受万邦”(《集成》10175),《<疒興>钟》谓“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粤,匍有四方,匌受万邦”(《集成》00251),意谓文王开始做到了政事和谐,集大命于厥身,上帝降懿德大粤,得到四方,众多方国完全臣服。铭文中的懿德,学者们多根据传世文献,从古注释家之说,将其理解为文王美德。[19]然而,此观点有可商之处:其一,铭文谓“懿德”由上帝所降,显然,这个“德”不是由个人内在所生发出的观念、情感,它外在于人,与“内得于己”之德还有差距,因此很难说“懿德”就是文王之美德;[20]其二,所谓“懿德大粤”,“粤”,学者据孙诒让说,释为“号”,[21]《说文》“{血丂}定息也”,指安定,是说上帝降懿德与安定于文王。铭文中“懿德”既与“大甹”并列,则“德”与“甹”之含义应当相关,不是指文王德行。窃以为此处之“德”与“甹”皆有具体所指,就是其后所言的“匍有上下,<辶合>受万邦”,为上帝所赐予文王的四方与天下,这就是文王之德(得)与所定。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德”最多者,当属《豳公盨》,其铭谓:
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奏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饗,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美唯德。民好明德,□才天下,用厥昭好,益求懿德,康无不懋。孝友讦明,经齐好祀无□心,好德婚媾亦惟协。天厘用孝,神复用祓禄。用御于宁。豳公曰:民惟克用兹德无悔。[22]
铭文指出天命降临于禹,且特别强调“德”的重要性,以“德”贯串始终。不难看出,“德”为天所降,为天所授予,经由禹民众才“贵德”、“好明德”、“求懿德”。联系上下文,则知“德”与“孝友”、“经齐好祀”有关,即孝于兄弟、祭祀不坠、婚姻和谐。这里的“德”,经过禹而落实为民众之品行,开始与个人道德发生联系。然而它来源于天,可说是由天贯注下达的品行,还不是个人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功夫。西周铜器铭文中,亦多见“帅型祖考秉明德”之语,学者业已指出,“德”多指政治品行与作为,且以此宣称的贵族往往世代担任王官,其目的在于彰显家族势力以及自我勉力,因此所谓的祖考之“德”亦非道德。[23]
所以,西周时期人们所说的德,常有“得”之意,即上天所赐,周人特别是文王所得。此外,德亦指“驭民之德”,指怀柔民众的治术。虽然不能说周初之德不包括道德的因素,但显然上所引德之内容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德行、道德,它是介于抽象的道德与具体的事物之间的一种状态,尚未完全变为纯粹的道德观念。[24]“德”非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且有关德的内涵及时代意义,学者已做过很好的分析。[25]本文仅从探讨天命的角度,说明周人虽将德注入天命之中,但就整体情况来说,周人之德还不能脱离天命来理解,尚未发展至个人的德行、修养之境地。因此,可说周人常以人事论天命,但尚不可说其天命论已发展至完全以道德为转移根据的境地。
三、殷周天命论的关联
周人注重以人事论天命,这是周人贡献巨大之处。然而,周人与殷人天命论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迥然有异?本文认为,殷周天命论存在关联,周人天命论中理性精神的出现,实是由商人铺垫而来。
说到殷人的天命观,学者多以《尚书·西伯戡黎》所记“西伯戡黎,祖尹恐。奔告于王……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上天’”为据,证明殷人以为天命不可更改,而周人则发展出“天命靡常”的思想,故殷周天命观存在根本差异。但细审文献,则可见殷人对天命的认识并非皆如殷纣一般,殷人的天命论特别是殷商晚期的天命思想,实是周人天命观念发展的基础。
殷商时期天的思想,学者据卜辞指出,天虽尚未成为商王室崇拜对象,但商人有尊敬、景仰天的意识。[26]且商人崇敬上帝,作为天神的上帝,与天或有相通之处。[27]由卜辞看,商王尊帝,[28]亦努力探求帝之旨意,[29]因此,天与上帝之类的天神,在商人的信仰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商人天命观念,与其上帝观念相联。
周人在总结殷之统治经验与教训时,曾追溯殷人对天的态度以及对德的运用,从侧面反映出殷人的天命观。《尚书·康诰》记载,康叔往封于殷之旧地,周公告诫康叔“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是说康叔至封国卫地之后,要遍求殷先哲王安治人民之道。周公还说“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这里的“求”,可读为仇,匹之意,[30]意谓周公思虑殷先哲王安治殷民之德,希望能够像殷先王那样安治民众。周公又说“我闻惟日: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尚书·酒诰》),这里强调指出殷先哲王上畏天之显道,下畏小民,行德而执敬。可见殷人注重治理民众的方法,协恭上下,将敬天与民事的治理结合起来。周人在总结历史经验,追溯殷人历史时,甚至明确指出殷先王重视人事,以人事来保证天命之不坠。其辞谓: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义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尚书·多士》)[31]
周公所强调的是殷先王黾勉于德、谨慎于祀,殷先王不敢失去天意,他们无不配合天的恩泽。由周人所述,殷先王所以负荷天命,畏天、慎祀,以致之也。这里的“明德恤祀”,与《豳公盈》所说“经齐好祀”,其意相当,可见殷人之观念对于周人的影响。所以,在殷人的观念中。也存在有天命时依人事而变易的意识,这一意识虽不如后来周人所论那样明确清晰,但确实存在于殷人的思想中。
《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诫群臣之语,其中涉及天命,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日其克从先王之烈?……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盘庚在这里强调殷先王对于天命皆恭敬谨慎,告诫群臣当继承先王恪谨天命的做法,降心迁徙,施德于人,否则,天命会终止(天之断命)。盘庚所说,隐含着天命变动不居、天命的变化与统治者之治术相关的意蕴。然而,《盘庚》篇所论天命究竟出于商人自身,抑或周人的想象,迄今并无定谳,尚需深入研究。[32]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殷末,部分殷人已经意识到天命不可常赖。彼时商纣确曾说过“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33]言有命在天,天命不改,依恃天命而对于周人大军压境之举无所恐惧。然而,向商纣汇报西伯戡黎的商臣祖尹的说法却为人们所忽略。祖尹说:
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34]
祖尹向纣陈言:殷之天命即将终止。由善人之意或由大龟占卜来看,皆没有吉兆。并非先王不护佑子孙,实在是王过度恣心肆意,不度知天性,不率循常典。所以民众无不希望天降威以警示。王之罪孽深重,累达于天,如何能够求取天命(延续)?显而易见,祖尹所论与商纣“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观念截然不同。他已然意识到天命变易,而且这个变易与统治者的所为,特别是王是否极意声色、率心长夜,是否审慎度知天命、循行常法有关。并且,天命的变更与民众的心意也息息相关,民众希冀天大降丧,则天不会听任王暴虐肆意。这样说来,以为天命不变的,仅仅是商纣等一些商之统治者,而这个集团中的另一些人如祖尹,已然知晓天命不可能专注一家,天命有其变化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统治者的作为及其民心所在。因此,天命的“予我”与“弃我”,或以人事为转移,这一思想并非周人的发明,而是渊源有自。
关于殷人的天命观,学者指出殷人笃信天、帝,多依赖占卜而少倚重人事。事实上,在笃信天命,尽力探求天意方面,周人与殷人是一致的。《尚书·大诰》记载周公决定平定三监之乱,他劝诫邦君庶士从征之辞曰:
猷!大诰而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
此段为周公劝诫邦君庶士往征平叛。他说天降凶害于周邦,周人当度知天命。大龟曾经辅助先王接受天命,于今不能忘其大功。周公以文王遗留的大宝龟卜问天命而获吉卜,表明天将助周平叛。可是有人却反对出征,甚至说何不违卜。周公告诫他们,吉卜为天所示,不可替废周命。周公此番话,有几点尤可注意:(一)天命不可违。由此可知周人仰赖天命,天命至高无上;(二)努力探知天意、天命。从周公之语看,周文王时期即用大龟占卜的形式来探求天命,而在平叛之前,周公再次以龟占卜,测知天意。以龟探知天命,事实上与以人事为天命的转移存在不同。以人事为转移,表明人的主动性,而以占卜来显示天命,事实上是对人事的否定。周公以占卜为号召,说明在周之贵族当中,此种方法十分有效,周人对天命乃至对占卜笃信甚深。
这样,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第一,殷人的天命观问题。过去学者在考察殷人的天命论时,鉴于周人天命观中的理性因素,常常将殷人的天命观视为周人的对立面。特别是殷末纣王在周人兵临城下时仍宣称“我不有命在上天”,造成人们认为殷人以天命为不变的印象。但通过上述分析,知殷人已经认识到天命与人事是有关联的,纣所言不能代替殷人对天命的认识。昔时,傅斯年在论述殷周之际的天命观念时,曾指出“知民监而上天难恃之说,既闻于当时,更传自先世,其渊源长矣,周公特在实际政治上发挥之耳。至于此古人为何时之人,谓‘天不可信’者为何人,今固不可考,要以所谓商代老成人者为近是”,[35]他指出周人观念受商之“老成人”影响,诚为公允之论;第二,若说殷人笃信天命、上帝,则可见周初之人亦不例外。由周人宣扬天命,用天命以相号召,以及周公运用大龟占卜而测知天命等等事例看,周人对于天命亦深信不疑。
这样,可说周人天命观并不是对殷人天命观的全盘否定,殷周天命观有相承之处。前贤多注重阐发周人天命论中的理性因素,以及所显示的人类精神的觉醒。但由上述殷周天命观的对比可知,精神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周人是在借鉴殷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之上完成了觉醒,理性因素的出现实是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同时需要看到,周人固然在人与天的关系方面有了理性认识,展示出理性精神的觉醒。然而,综合分析周人对天命的认识,却又发现这一觉醒还是那样有限。即便上层统治者已然揭示出“敬天保民”的观念,但他们笃信天命,宣扬天命、利用天命,又以占卜而探测天命的做法,与殷人并无二致。因此,就思想观念而言,在某一关键点上的觉醒或突破,诚然十分可贵,但并不意味从此即可振聋发聩、牵一动百而导致观念的完全觉醒。具体到天命观而言,周人的觉醒还只是局限于若干人群当中,局限于某一点之上,距离完全的觉醒尚有遥远的距离。觉醒与未觉醒相交织,理性与不完全理性相纠缠,应当是周初天命观的大致状况。
四、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念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其大端来说,天命的内涵与西周时期不同,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春秋时人常言天命,但天命不再是统一的、神圣的、专属周天子所有,它已经下移至诸侯、卿大夫阶层。此种现象在青铜铭文中并不少见,春秋早期秦武公《秦公镈》铭谓: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令,商宅受国……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秦公其唆令在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敷有四方,其康宝。(《集成》00267)[36]
秦公宣称秦人先祖受天命,而非周人习称的文武王受命。秦人先祖受天命的说法亦见于传世器《秦公簋》,其铭日“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绩”(《集成》04315)。“商宅受国”即秦先公赏都邑受疆土而立国。秦公不但称颂先祖受命,甚至说自己也“膺受大令”。关于秦武公称秦人受天命之事,学者曾经指出在礼制浓厚的地区,诸侯力量即使再强大,也不敢作非分之想,但僻在西陲的秦国则称受天命,边远的诸侯敢僭越天命,正表示天不再属于周天子独有。学者所言极是,但是,僻在西方的秦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先祖和自己受天命,其意图在于超越王权,抑或其所使用的天命内涵已有变化?需要辨析。
秦因国力强盛,自称有天命,而褊小的蔡国亦称有大命,则很难理解为是对王权的僭越。蔡侯敬共大命的说法见于《蔡侯尊》与《蔡侯钟》。《蔡侯尊》日:“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共大命,上下陟<礻否>,<扌篦>敬不惕,肇佐天子。”(《集成》06010)《蔡侯钟》记载:“蔡侯申曰:余虽末少子,余非敢宁忘,有虔不易,佐佑楚王。雀寉豫政,天命是,定均庶邦,休有成庆。既聪于心,诞中厥德。均(君)子大夫,建我邦国。”(《集成》00210)这两则彝铭的大意是说蔡侯虔敬地接受天命,上天降懿德于蔡,蔡侯尊奉天命,持之以敬慎而不更易,常备裎祀,永远得到上天的保佑。《蔡侯尊》为媵器,是大孟姬嫁于吴国时所作,其铭辞中称蔡侯“共大命”,“肇佐天子”,都不免有自我赞扬、吹嘘之嫌,但绝对不是僭越王权。事实上,学者认为此两器中之蔡侯申为蔡平侯。[37]平侯时期,正为蔡国经历覆灭之灾后为楚王所复立之时。[38]彼时蔡正受制于楚,国弱君轻,如同附庸,怎敢妄称天命而僭王权?因此,他所说的天命,是说得之天佑助,而非普天之下国祚之转换,其意与周初周人所称的文武受命,革除殷命,已完全不同。
其实,不但是僻处西陲的秦人敢于称天命,其他诸侯也未必不敢为,《晋公盆》就记载晋人先祖受命之事: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公曰:余惟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固燮万邦,徐莫不曰<卑页>。余咸畜俊士,乍□左右,保嶭王国。(《集成》10342)
是器学者定为晋定公时器,为春秋晚期。这里晋定公说晋人先祖叔虞接受天命,辅助武王,晋定公表示他将以先祖为榜样。《晋公盆》为晋公女嫁与楚公子时所作器,[39]晋定公追溯祖先功业,是为当然。晋定公之时值春秋晚期,中原霸主皆已中衰,吴人乘势北上,晋吴会于黄池,晋国不复为春秋盟主。而晋国国内,范氏、中行氏等几家卿大夫势力日益坐大,在这种情势下,晋侯自身势力难保,并无僭越之可能。因此,其宣称祖先“膺受大命”,仅仅在于显示其先祖功烈而已。[40]春秋时期称天命的还有《佣戈》,其铭曰:“新命楚王,膺受天命。倗用燮不廷……”[41]此器所出之墓墓主与楚康王同时,因此学者认为铭文中的楚王即楚康王。[42]据文献所载,康王继位经历颇不寻常:楚共王去世后,难以选定嗣位之子,于是“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左传》昭公十三年),按其理,应当压中玉璧的平王继位,但最终“康王以长立”。[43]或许是由于楚康王继位时的情形比较特殊,铭文中言“膺受大命”,是对他继承楚王位的肯定,而不是对周天子王权的挑战。[44]
战国时期,仍有铭辞称天降大命。《中山王厝鼎》记载厝自述:“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姆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贾,克顺克卑,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佐佑寡人。”(《集成》02840)中山王厝时当战国中晚期,中山国曾为魏、赵两国所并,复国之后仍然处于强国夹迫之中,是以其所言“天降休命于朕邦’’绝非篡夺王权之谓,仅仅表示得天之助,将有复兴。这样的一种状况与燕王哙所宣传的“受命于天”的说法非常接近。燕王哙之时,燕国正处于衰颓之际,说士苏代到燕国游说。在听毕苏代之建议后,燕王哙意气振作,说“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战国策·燕策一》),认为获得苏代的协助,则有望复兴。当时的燕国迫于大国压力,岌岌可危,燕王听从苏代之谏后,即有复兴之志,说将“受命于天”,不言而喻,他所讲的天命就是获天之惠助之意,而非僭越王权。
由上所引看,春秋战国时期天命的使用者、含义都发生了变化。原来高高在上、唯有天子才能独享的专指国祚之天逐渐和天子以下的阶层发生关联,天命失去了威严。不过,春秋战国诸侯所谓的受命,并非意在觊觎王权、取代周天子,更多的时候,它指获得天命的护佑以延续国运,这与西周时期天命特指受天之命而改朝换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亦有不少有关天命的论述,其中不单可见统治者(如诸侯阶层)的天命论,亦可见卿大夫阶层的、智者的以及诸子的天命观念。[45]此外,有关天的表述也有不少,除天命外,还有天、天道、天意等。就整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命论与西周时期区别显著。
东周时期有关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们常常论及天,但天命出现的频率却不高,这与西周彝铭以及《尚书》八诰中天命频繁出现的情形大不相同。春秋时,人们常常论及天对诸侯大国的眷顾,如《左传》记载楚国实力蒸蒸日上,随国大夫季梁就曾说“天方授楚”(《左传》桓公六年);宣公十五年,楚欲与宋人平,宋人告急晋国,晋侯欲救宋,大夫伯宗却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左传》宣公十五年)劝阻晋侯不与楚争胜。齐、晋、楚三国势均力敌,互与争锋,时人就有晋、楚、齐尽为天所授的观念。如齐晋鞌之战,齐军失利,晋提出“尽东其亩”的条件,齐宾客予以周旋,郑、卫之国也倾力调解,日“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左传》成公二年)又如晋、楚鄢陵之战,楚压晋军而陈,形势于晋不利,范匄鼓舞晋人士气,曰“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左传》成公十六年)春秋后期继晋、楚而起的吴、越,不可一世,在当时人看来,亦“唯天所授”(《国语·吴语》)。上述春秋霸主,得天假之时,“唯天所授”,其状况与殷末周初文王“昭事上帝……以受方国”(《诗经·大雅·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诗经·大雅·皇矣》)获得上天眷顾、授予方国的情况一致,但是,霸主们只是“天所授”,而非“天所命”。又,春秋时人往往议论某人得天之庇护,如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时人评价“天未绝晋,必将有主……天实置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重耳途中过郑,郑文公不礼焉,大夫叔詹评价重耳“天之所启,人弗及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劝说郑公以礼对待。又如晋六卿之一魏氏,其祖毕万在春秋时即有“天启之也”(《左传》闵公元年)的说法,谓得天之佑,子孙必蕃。“天实置之”、“天之所启”一类的说法,事实上就是天降大任的意思,与受命于天表达的意义相去并不远。然而,就在几乎相同的情况下,时人偏偏不用“天所命”、“天命之”这一类的表述方法,这似乎暗示出,在那个时期仍有人严守西周传统:天命专指天所授予的统治四方的权力,特别是天子统御四境,而不单单是天对某人、某个团体、某一国家的眷顾、庇佑。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命仍然具有庄严、崇高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命与德之间关系的认识也有变化,天命与德、人事之间的关联有所模糊。这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在承认德之于天命有重要影响力的同时,也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这与西周传统有所差异;(二)意识到人事并不能决定天命,尽人事未必成天命,这是人们对人事、世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之后,对于天命的新认识。《左传》宣公三年记载: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一面坚持周人的传统说法,谓“在德不在鼎”,以德之盛衰解释三代之更替,将天命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面他又对自负的楚人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强调天命的绝对意义。王孙满为广闻多识之士,但在与楚人周旋时,却也肯定了命定之天的作用。《国语·晋语》六记载“鄢之役,荆压晋军,军吏患之,将谋。范匄自公族趋过之,曰:‘夷灶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奸也,必为戮。”在楚军兵临城下之际,范匀越级而献策,引起其父范文子的不满,认为天命在上,哪里有小子置喙的余地。上述两个记载中,天命与德、与人事的关联并不具有必然性,其与西周时期周公所强调的以人事为天命转移根据的观念有所区别。
天命不仅与人事、德行关联模糊,崇高意义赫然减退,并且时又成为若干贵族粉饰自己为所欲为的武器,工具化的色彩十分突出。此例甚多,兹举一二。鲁国季氏专权,驱逐昭公,宋、卫两国请复昭公,盟会之时,晋范献子取货于季孙,固辞宋卫之卿,曰:“季氏之复,天救之也……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由于收受季氏贿赂,范献子极力美化季氏。鲁昭公固然寡德,专权的季氏未必就德厚,却赢得“天赞之”的美誉,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背离了西周以来赋予天崇高意义的传统。又如,郑人侵伐许国,郑庄公谓“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人欺凌小国,却假托天之意志行事。“天”为人所“挟持”,任人摆布,毫无德性可言,这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念判然有异。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人也否认天命与德之间的关联,这是由于他们切实地意识到天命未必以人事为根据,在人事之外尚有其他力量左右,这或许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观念之滥觞。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曹沫之阵》篇记载鲁庄公时,国力衰微,庄公却“将为大钟”,曹沫劝谏,以“修政而善民”、恭敬勤俭之道告之,陈说国家兴衰之道,庄公遂与曹沫就天命有所辩论:
庄公曰:“昔池舶(伯)语寡人曰:‘君子得之、失之,天命。’今异于而言。”曹沫曰:“[□]不同矣。臣是故不敢以古答。然而古亦有大道焉,必恭俭以得之,而骄泰以失之。君言亡以异于臣之言。君弗尽,臣闻之曰:‘君子以贤称而失之,天命;以亡道称而没身就死,亦天命。不然,君子以贤称,曷有弗得?以无道称,曷有弗失?’”[46]
池舶(伯),竹简整理者指出或为《国语·齐语》中施伯。如是,则施伯为鲁君谋臣,以洞见与智慧著称。[47]以施伯之睿智,他传递给鲁庄公的观念是“君子得之、失之,天命”,意谓君子或得或失,实在不由人之意愿或主观努力所能决定,而是天命主宰一切。施伯的看法过于消极,但他毕竟看出了在人事之外,存在人无力把握的因素。曹沫较之施伯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一方面看到尽人事却不一定成天命、天命与人事无关,但另一方面,他从反面看到,不尽人事则一定不能成天命,天命与人事有关。由施伯与曹沫之例看,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天命固然与人事有若干关联,但其中却包含有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个人力量所无法企及的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了肯定命定之天的有关论点,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延续着西周传统,将德与天、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所谓“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即是典型的表述。[48]天或天命与人事相联这一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极端发展,就是将天命与灾异联系起来,企图以严厉的天谴来约束人事。上博简《三德》篇谓:
敬者得之,怠者失之,是谓天常,天神之〔□。毋为□□〕,皇天将举之;毋为伪诈,上帝将憎之。祺而不祺,天乃降灾;已而不已,天乃降异。其身不没,至于孙子。阳而幽,是谓大感;幽而阳,是谓不祥。齐齐节节,外内有辨,男女有节,是谓天礼。敬之敬之,天命孔明。如反之,必遏凶殃。
这里天命与人事紧密相连,人事倘若有悖天命,则秧咎大降。《三德》[49]篇所透露出的观念与战国时期诸子主张的灾异观相吻合,如《吕氏春秋·应同》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蟥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於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在这个记载中,天命与人事的关联被推到极致,两者的关系绝对化,开了后世灾异论的先河。
综括上述,春秋战国时期天的观念或天命观念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首先,天命或天已从西周时期高悬于社会之上的、只与普天之下的国祚相关联的绝对权威地位下落,它降贵纡尊而开始与个人的命运发生关联,其含义也转化为获天之佑助,而不再强调政权的转换;其次,人事、德行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至东周时期也发生了变化。周人的传统~强调人事与天命之间的关联,在东周时期时有人提倡,甚至进一步发展出以天之灾异警示人事的学说。但是,将德与天命分离的说法却更引人瞩目,这一时期,有人重新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另有人则根据世事的变化,体察到人事、德行并不是左右天命或天的唯一因素,人事之外尚有无法确定的因素作祟,后者当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以及天命的思考,是社会中出现的新的更为深刻的思想。
五、小 结
周人的天命观,是周人在克商之际发展起来的重要思想,周之上层统治者在总结殷所以亡的教训中,强调“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观念,将人事与天命的关系在殷人所论基础上扣得更紧,使得人不再盲目地听天由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束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这一精神不独为此后的天命论确定了一个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重要智慧。前贤在探讨周人的天命思想时,深刻揭示了周人天命论中的理性精神。但是,倘若只关注周人天命论中的理性因素,则显然对于周人天命观的完整意义乃至周人思想世界的总体轮廓理解不够。如前所述,在周初的政治环境中,周人倡导天命,其天命论包含有现实意义。周人以宣扬天命来说明代殷的合理性,以为其政权廓清思想意识方面的障碍,又利用天命来巩固周之同盟,因此,天命对于周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周人在建国的历程中,否定了天命恒长的说法,奠定了理性精神的基础。但无可置疑的是,周人并没有完全突破天命,而是仍然诉诸超自然的天,以之作为思想或推理的基础,作为人事之旨归。因而,天仍然是最高神灵,是周人信仰所系。可以说,周人之于天命的突破,是在某一重要点上获得成就,但不代表完全的突破。
在西周以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天命论也并非沿着理性的轨道直线发展。东周时期,诸侯仍自称受天命,以天命为号召,足见天命仍是周人广泛的信仰依据,具有现实意义。春秋战国时期,周人传统的天命观继续发展,但值得关注的是天命论中出现的新线索:1.不仅将人事与天命之间的关联紧密扣合,并且将天命与人事的关联绝对化,出现了将天命与灾异相联的论调。这固然不失为以天命对现实政治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法,但它并不是理性精神的新进展,反而是转向了另一蒙昧的路途,与理性背道而驰;2.出现了肯定命定之天作用的论点,显示人在天之下的无可作为,这显然与周人所开创出的以人事论天命的理性精神相异;3.淡化人事与天命之间的关联。经历了世事的变迁之后,人们意识到在人事、德行之外,还存在着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强调人事、美德对于天命的主导作用,相反,尽人事、成天命的思想逐渐成为一些人的共喻。这一观念是在洞察世变之后的反思,其较之周人所发挥的以人事、以德行论天命的观念,无疑更进一步。此后,这一思想也成为传统文化天人关系论中影响至为深远的观念。
由缕析周人之天命论,可以窥见其思想观念发展的复杂状态。周人之天命论,主要是周人统治集团上层思想意识的体现。这一集团中的精英在周初明确提出“惟命不于常……天畏棐忱”(《尚书·康诰》)的观念,导致理性精神的出现。然而,同是这一集团,在意识到“天不可信”的同时,却又时时将天命视为人事之圭臬,对于天命虔敬而笃信。因此,就精英阶层来说,其观念世界同样体现出多层面的状态: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交织互错,没有绝对的界线。同时,精英阶层确曾在某一关键的思想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观念领域中,非理性因素消失殆尽。换言之,精英阶层的观念亦可区别出层次来,其间理性与非理性并存。此外,就西周以降的天命思想发展轨迹而言,周人的天命观念也不是在理性的路径中做直线式的发展,反而是有停滞、步入他途甚或倒退。由此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精神觉醒”之后的思想世界,其面貌如何?[50]仅就周人天命观的发展来看,可以窥见到的是,精神、意识的觉醒没有导致完全觉醒的思想局面,觉醒还仅仅局限于若干人群,局限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理性因素仍然只在局部的范围内做进一步的发展,而不可能促成对全部思想观念的改变。因此,理性中夹杂非理性,觉醒后仍有非觉醒的状态,或许应当是“精神觉醒”之后周人思想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附识:承蒙两位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1]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2、2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06014。下文简称《集成》。
[4]彝铭之“廷”,专家或读为“莛”,即《离骚》之“以莛篿”。(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页)莛,本指小折竹。莛篿,指结草折竹以卜;或谓通“侹”,敬也。(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5]如《尚书·召诰》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按,《诗经·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其所表达的观念与《召诰》“改命”之说如出一辙。又如《尚书·康诰》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6]如《尚书》的《康诰》《无逸》等篇称颂文王之德,《诗经·大雅》的《皇矣》《文王有声》等篇则文 德、武功并颂。
[7] 《诗经·大雅·文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531页。
[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第136页。
[9]陈逢衡说,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
[10]关于太姒之梦和《逸周书·文儆》所记内容的关联,参见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转引自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1页。王利器指出《庄子·让王》作“扬行以说众”。(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184页)
[12]如周康王时期《大盂鼎》(《集成》02837)“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恭王时期《乖伯簋》(《集成》04331)“朕丕显文武膺受大命”,懿王时期《师询簋》(《集成》04342)“丕显文武,膺受天令”,懿王或孝王时期《<疒興>钟》(《集成》00251)“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西周晚期《五祀<害夫>锺》(《集成》00358)“明<喜畐>文乃膺受大命,匍右四方,余小子肇嗣先王,配上下,乍氒王大宝,用喜侃前文人,墉厚多福,用<□貈>先王,受皇天大鲁令”(按,此铭开篇突兀,缺少主语。学者认为应上接另一钟铭,前面的语句,当是赞美文王或文、武受天命。参见穆海亭、朱捷元:《新发现的西周王室重器五祀<害夫>钟考》,《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西周晚期《徕鼎》“丕显文武,膺受大令,匍有四方,则繇隹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爵谨大令(命),奠周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等。
[13]《通志·氏族略》三“禄氏,子姓。《风俗通》云:纣子武庚字禄父,其后以字为氏。泾阳有此禄姓,亦出扶风。”(《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4页)按照《氏族略》所说,录非姬周族。
[14]学者常引《尚书》所记以说明,如《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惟命不于常”,《酒诰》“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召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15]郭沫若曾说周初的“德”字,“不仅包含着主观方面的修养……(还)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2页)
[16]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03页。
[17]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74页。又有学者将“恭德裕天”解释为“王之恭德裕容于天”,但细绎其意,“恭”、“裕”当为丽动词并列,其意应相当。
[18]“正德”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句或与《左传》文公七年卻缺所语“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有关,卻缺所说“正德”并非纯正之德的含义,“正”用如动词,意为端正德,所以“德”乃中性词。“正德”亦见于春秋晚期《羊编镈》铭文。(参见刘雨、严志斌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47,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4页)
[19]“懿德”见于传世文献,但分析其意,未必尽指个人之美好德行。例如,《诗经·周颂·时迈》一般认为是周初乐歌,《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之语,认为此篇为周武王所作。是篇谓:“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注释家多将懿德解释为美好德行,但诗篇既曰“我求懿德”,则懿德非为个人美好德行之谓。《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富辰谏周王之语,曰:“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扦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富辰之意为,周得天下,但巩固政权则莫如以亲亲行分封。十分明显,这里的懿德不是个人美好的品德,而是指周白上天获美好所得。因此,即便是春秋时期,懿德的这个含义仍然有所保留。但自西周晚期以来,则可见懿德用如美好德行之例逐渐增多,如《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篇为周宣王时诗,诗中言“物”言“则”,言“民之秉彝”,则“懿德”为美好德行。义《左传》昭公十年晏子语“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懿德为美好德行。由上述分析可知,懿德最初未必用如个人美好德行之意。
[20]与《墙盘》《<疒興>钟》相似,西周晚期《毛公鼎》谓:“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集成》02841)“皇天引厌厥德”,“引”,《尔雅·释诂》“长也”;厌,饱也。意指上天赐予长久之“德”。德为天所赐予,同《墙盘》、《<疒興>钟》所说帝降懿德同。
[21]孙诒让:《籀庼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7页。
[22]释文参考李学勤:《论豳公盈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裘锡圭:《豳公盈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朱凤瀚:《豳公盈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李零:《论豳公盈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23]刘源:《试论西周金文“帅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内涵》,《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24]从青铜铭文中看,至西周中后期以降,德所包含的道德因素逐渐增强。
[25]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6]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27]如《尚书·多士》记载“殷命终于帝”,而《召诰》则说“天既终大邦殷之命”,显然,周人所说的“帝”就是“天”,“帝”“天”具有共通性。周人于此未特别区分商人之天与帝,说明周人有时将两者混同使用。《诗经·大雅·文王》亦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意谓殷人没有丧失民众,所以能够配上帝。这里所说的上帝,与天含义相同。进一步而言,周人在追忆商人天的观念时,很有可能将其上帝与天混而视之。卜辞中亦有帝“令雨”、“令风”的记载,学者指出,令风、令雨的帝,实质上是自然之天。参见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8]陈梦家曾经指出,帝之于商王,意义重大,“王之作邑与出征,都要得到帝的允诺”,“王伐方国,卜帝之授佑与否”,帝对于时王有善义的保护等等,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67—569页。胡厚宣也指出,殷人以为帝在天上,能够下降人间,在许多情况下,殷王需要占卜,求知是否能够得到帝的保佑,帝掌握着殷工的祸福。参见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
[29]如《小屯南地甲骨》7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记“来戌帝其降永。在祖乙宗,十月卜”,意谓在祖乙宗庙中占卜,以此探知上帝之旨意。
[30]王国维指出“作求”为周人成语。他说:“《诗·大雅》‘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者,仇之假借字。‘仇’,匹也。‘作求’犹《书》言作匹、作配,《诗》言作对也。《康诰》言与殷先王之德能安治民者为仇匹,《大雅》言与先世之有德者为仇匹,故同用此语。”(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观堂集林》第1册,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8 79页)刘起釪指出此句之意同于伪《孔传》中所说“乃欲求等殷先智王”,参见氏著:《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349页。
[31]经文的“泽”,顾颉刚认为泽、怿、嗣并通,其意为绪,继续之意。参见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516页。
[32]值得注意的是,《盘庚》篇中记载武庚也提到“帝”,谓:“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意谓上帝将兴复高祖的德运,上帝此项权能,与甲骨文所记相契,或可说明《盘庚》篇确包含商人的因素。
[33] 《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8页。
[34]此段主要文字释意:既,将也。俞樾指出“是时殷犹未亡,乃云‘既讫我命’,义不可通。古书‘既’与‘其’每通用。《禹贡》‘潍淄其道’,《史记·夏本纪》作‘既道’;《诗·常武》篇‘徐方既来’。《荀子·议兵》篇引作‘徐方其来’,并其证也。‘天既讫我殷命’,当作天其讫我殷命”。格人,大人。俞樾谓:“元,大也;格,亦大也……《史记》‘格’作‘假’,《尔雅·释诂》‘假,大也’……凡有大义者,皆有美善之义。”(俞樾:《群经平议》,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046页)责,《说文》“求也”。
[35]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第327页。
[36]又,秦公大墓石磬残铭中亦提到天命,参见王辉、焦南锋、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
[37]有学者亦认为蔡侯是平侯之子蔡昭侯。无论平侯或昭侯,无改于蔡国依附楚国,受制于楚的局面。
[38]蔡景侯之时,蔡国发生内乱,太子般弑其父景侯而自立为侯,是为蔡灵侯。楚灵王趁机以蔡灵侯杀父之名,处死蔡灵侯,蔡亡。楚灵王封太子弃疾镇守蔡地。后楚国亦有内乱,公子弃疾在蔡人朝吴的帮助下,夺取政权,是为楚平王。为答谢朝吴,楚平王兴灭继绝,复立蔡国。这就是《史记·管蔡世家》所说“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
[39]器铭称“<午隹>今小子,整嶭尔容,宗妇楚邦,无咎万年,晋邦维翰”,可证。
[40]春秋时期另有称天命的为齐之《叔夷钟》。《叔夷钟》(《集成》00276)为齐灵公时器,春秋中期偏晚。器铭记载齐灵公任命叔夷治理三军、职掌国事等。叔夷则祖述其先,曰:“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削伐夏司,<{田貝}攵>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4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
[42]参见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
[43] 《史记》卷40《楚世家》,第1709页。
[44]春秋后期之《羊编镈》亦记载有天命,谓:“曰古朕皇祖悼公,严恭天命,哀命鳏寡,用克肇谨先王明祀。”(刘雨、严志斌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47,第64页)铭中悼公为滕悼公,他亦称自己“严恭天命”,但滕为姬姓小国,根本不具备挑战姬周之天命的实力。(详见董珊:《试说山东滕州庄里西村所出编镈铭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http://www.gwz.fudan.edu.cn/Default.asp)。2008年4目24日)
[45]春秋战同时期有关诸子的天命论需专文探讨,非本文所能概括。
[4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7—249页。
[47]关于施伯的智慧,《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射齐桓公而为鲁所俘,桓公听鲍叔牙之谏欲释前嫌而重用管仲,请鲁国将其放回。齐桓公知施伯为能,十分忧虑,说“施伯,鲁君之谋臣也,夫知吾将用之,必不予我矣”,担心施伯看透自己的心计而不放人。鲍叔牙教桓公欲以戮管仲于群臣以为说,但即便如此.施伯仍然看穿了齐人的计谋。
[48]春秋时期仍然常常可见人们将天或天命与人事相联,如晋楚城濮之战时,楚成王告诫令尹子玉不要与晋军交战,因为晋文公是天所立之君,“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从表面看,似乎是晋文公获得天赐之机,实际上,晋文公“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依靠自身作为而终获天所赐,这里的“天”实际不离人事。又如,郑庄公出兵许国,谓“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左传》隐公十一年)许君昏庸,郑庄公说是“天祸许国”,但他又说郑不宜久留于许,因为姬周日益削弱,“天厌周德”,天命不再,所强调的仍然是德与天的关联。
[4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9—290页。
[50]关于“精神觉醒”之后的思想状况的阐述,参见晁福林:《人类精神觉醒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5月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