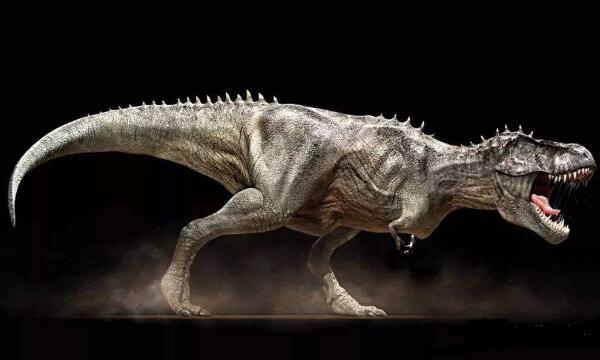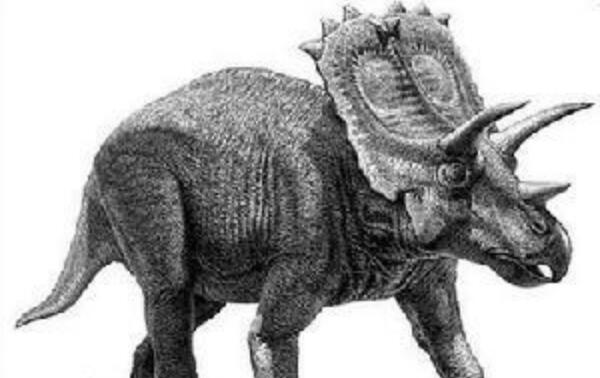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刮起了一股追求新史料之风,这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是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文献的重视,即新的研究旨趣或新的研究取向导致了对以往利用较少的史料文类的关注。
这股风潮还有另一个源头,即与考古学有关。因考古发现而造就某种新史料,进而造就某种“学”,已有百余年历史,如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近数十年来一直方兴未艾的秦汉到三国简牍也属此类。此类发现往往大解史学界的燃眉之急,因为上古甚至中古历史的资料库似乎已囊中羞涩。但这毕竟类似于靠天吃饭,如果考古学工作者没有挖出大量有文字的东西,我们也只有守株待兔,徒呼奈何。历史学假若真正到了这个地步,多少是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不少机构斥巨资通过不同来源购得新史料、出版机构又斥巨资将其整理的同时,不仅有可能(或已经)造就一个新的巨大的产业链,而且可能造成对地方历史生态的破坏,中国的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可能因此而走向没落。当然这已溢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兹不赘论。
一、史料的新旧与史观的新旧
所谓新史料,主要是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以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这是在比较狭义上说的,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含义。在具体的研究题目上,这样的史料可能比较重要,但对整个学术的导向意义比较有限。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档案,也利用档案做出了出色的研究,但从20世纪初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得到重视以来,这已经不算新史料了。
档案材料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一是因为20多年前学者们还较少使用它,那时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的国内学者寥若晨星,来此踏访的海外学者也曾对此表示惊讶;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使国内学者可以使用国外的档案,比如藏在美国、英国、俄国的与中国近代史关系密切的档案,而这些材料以前也很少用于我们的研究;三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地方档案,从巴县、获鹿等地档案到现在的南部、龙泉档案等等,虽已有一些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版,但还远远未达到“常见史料”的程度。
不过,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档案,特别是政府档案,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19世纪在欧洲史学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兰克史学,就是以使用档案著称的,而且,他们坚信通过秉笔直书就能够求得历史真实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利用档案基础上的。而这种科学的迷思,80年前就已受到过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讥评。所以,作为新史料的档案只是对某个以往研究中没有用过档案的问题而言的,即由于用了档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被推进了一步。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史料都可以是新史料。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通过田野工作,发现了许多民间文献,多数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某部族谱、某个碑刻),但借此研究的问题和结论,除了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和事以外,并没有说出新的道理。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让我们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人和事,在史学上难道没有意义?当然不能这样绝对。比如对于上古时代那些我们几乎全然陌生的社会,能窥知一二就已经令人兴奋了;但对于史料已然十分丰富的近世社会,我们就无法满足于仅仅描述一个我们以往没有描述过的事实,而这个描述并未引发读者新的历史反思,只是在重复前人通过描述另一件事实所引发的历史反思。
同样,法制史研究的同行近年来也利用地方司法档案,甚至契约文书进行研究,对传统法史学进行改造,我们看到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冕宁县档案、徽州文书、贵州清水江流域文书等等得到利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作为法学框架内的部分法史研究关心的始终是传统法学的问题,即往往通过对史料中司法程序的梳理回答一些与基层司法实践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巴县、南部、冕宁、徽州、锦屏等等地方的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关系,研究者也不关心那些打官司的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如何生活。于是,这些文本产生的情境就大多被抽离了。这不仅存在一个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些文本的意义的问题,而且导致了我称之为有“法”而无“史”的困境。
更有甚者,由于史料浩如烟海,研究者受条件限制,没有发现某些史料已经被使用过,还以为有了重大发现。比如有的研究者偶然发现《临榆县志》中记载了清初士绅佘一元的资料,认为是重新认识甲申“关门之变”的新史料,殊不知30年前就被学者使用过了,并得出了类似的判断。
回首20世纪初的新史料发现,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是以西学传入后的新史观为前提的。它们的对立面,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而梁任公对后者的批判是大家耳熟能详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汉简的逐渐出土和利用、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新史料。而这些新史料与作为当时的“新史学”之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一部族谱,既可以被用成旧史料,也可以被用成新史料。一则传说,一幅图像,亦复如是。
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者,搜集和利用各种民间文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但是,对于缺乏史观的人来说,它们完全可能成为一堆垃圾。否则,它就不会留在那里长期无人问津,或者干脆被毁弃。
二、旧史料的新价值
同样,在我们熟知的史料文类中,仍有许多宝贵资料“养在深闺人未识”。以下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例一,沈榜《宛署杂记·元代公移》:
元都大兴府,则今宛、大,乃其赤县,相去仅二百余年,而公移故牒,已无多存者。谚云:十年沧桑,讵足长息!尝过宛平西山栖隐寺,得一断碑,刻有宛平旧牒,令、丞、簿、尉俱称行,想元时或以他官行县事,抑胡人迁徙不常,夏则北徙,故各官多称行。如我朝前此北都未定,尚称行在,各衙门皆有行字,及今行仆寺、行都司,疑此例也。
碑云:
今月二十六日,奉大兴府指挥,奉尚书工部符文,今月初八日,承都省批,大理寺断,上工部呈,大兴府申,宛平县李仁莹等每仰山寺僧法诠争山林事来断。李仁莹等告仰山寺法诠占固山林,依制,其僧法诠不合占固,外据李仁莹等到官虚供不实之罪,合下本处契勘,照依制法决遣施行。然如此,缘本僧有天会年间书示施状,及正隆二年告到山林为主榜文显验为系已久为例之事,兼是省批,寺驳,补勘事理,诚恐所拟未当,乞都省详酌施行外,检法董伯璋等所见,除相同外,据委官打量到四至内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问从初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不得争告条理,其山林合分付仰山寺僧法诠依旧为主,占固施行。然如此,缘鞔寺已拟,本寺不合占固,乞一就都省详酌施行,本部看详,若准检法董伯璋等所见,是为允当,乞明都省详酌事,因蒙批送寺、鞔寺参详。据李仁莹等告僧法诠争山林事,若为僧法诠供称,所争山林,有天会年间已后节次为主文,凭此上便断与本寺僧为主施行。又缘照到制内明:该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今来本僧见争山林,虽见收天会年施状碑文书示,正隆年间榜文,及在后立到私约文字等为主凭验,然是未抚定已前占固为主,既在制有立定不许占固刑名,便是冲改。兼本寺根脚,别无制前官中许行占固堪信,显验难议,便准此时僧尼私不转施等文凭,断与僧法诠为主,以此看详李仁莹等告仰山寺僧法诠占固山林,合依上制文,其僧法诠不合占固施行外,司直王浩然、张藻、评事尹仲连、孙溥权,披断高十、方奴,知法孟源、张仲仁、萧胤里、胡赌、萧长奴等所见,除相同外,若准鞔寺便断将李仁莹等所争山林,本寺不合占固施行。又缘照得僧法诠供称,所争山林,有天会年间皇伯宋国王书示,并天会十五年二月为恐人户侵斫山林,此时僧存帅告本管玉河县申覆留守司文解,及天会九年有住持普大师将未抚定已前元为主、旧仰山寺道院等四至山林,施每故青州长老和尚为主,其山林系是本寺山坡,见有施状碑文,正隆二年官中拘刷僧尼地土园林内不堪佃山冈石衬地诸杂树木不在支拨之数,仍勒本主依旧为主,有此时僧人行显告到,本县榜文,禁约军人不得采斫文凭,委官辩得别无诈冒,及村人前后做官户抽到四至内安斫打柴文约,并丁从整等偷斫至内柴薪陪钱文字,及照到贞元二季分承省劄,奉炀王旨:山林陂湖之利,非私家所宜专有,除合存留外,并许诸人采斫。在后,却奉炀王旨:休令采斫,依旧为主占固施行。然在制:该古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今来本寺,自皇统二年未降制已前为主,到今五十余年,即非制,后行擅便将山林占固,以此看详僧法诠既有上项逐节为主凭验,委官辩验得别无诈冒,兼见告人李仁莹等别无供掯,见得是官山显迹,亦无官中许令百姓采斫文凭,又已招讫虚告,四至地里本罪。据委官打量到四至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问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无不得争告理。其见争山林,合行仰山僧法诠依旧为主施行,是为相应,伏乞尚书省照详酌施行。蒙批:呈讫,奉台旨,准司直王浩然等所见,送部行下帖,仰照验前项所承都省批降处分事意施行,仰照验依准所奉符文内处分事意施行,年月下该司吏李道等施行,何行榜者,右具知。前准奉旨挥照会到在案。本寺僧法诠元告争山林,东至芋头口,南至逗平口,西至铁岭道,北至搭地鞍,其四至分明断本依旧为主。今据元告人僧法诠告乞依奉府衙旨挥已前断事理,合出给执照,仍出榜禁约施行。除已行下本村首领并两争人省会所断,并旨挥本人依断为主外,合出榜省会依准所断事理,不得于本寺山林四至内乱行非理采斫,如有违犯,许令本寺收拿赴官,以凭申覆上衙断罪施行,不得违犯,各令省会知委。大定十八年十月初一日榜:行县令张押,行县丞苏押,行当簿郦押,行县尉王押。
右元时僧人告争山林,该管官司为之听理,僧因刻石以志不朽者。然观此,见元人虽夷,其于民间小事,亦必委曲会勘,略不轻率,其以胡人而得有人心百余年,以此。
这样一部“常见史书”中的一篇重要资料,居然没有任何人做过研究(此残碑仍在栖隐寺山门内),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肯定与金元史及北京史研究者的史观有关。对它的解读,自然要放在金代华北的历史脉络中去,其间涉及女真制度、佛教势力与汉人社会,当为另文申论。
例二,民国《宜章县志》卷一七《氏族志》:
县中大姓,约略言之,黄岑水流域著姓什数,以李、吴、彭、曾为大;章水流域著姓什数,以杨、萧、欧阳、邓、邝、刘、蒋为大;武水流域著姓什数,以黄、李、欧、邓为大。黄沙则黄、李、彭、刘、程、蔡、杜、萧为之魁,笆篱则刘、谭、周、张、陈、曹、范、邓为之雄,栗源则陈、李、胡、姚、王、周为之杰。……城厢著姓,明时盛称卢、廖二氏,有“卢半学,廖半都”之谚。
全县氏族约分三类:曰官籍,则系其祖曾官于此,或流寓于此,而子孙留住成族者;曰商籍,则多系明初来自江西、福建两省;曰军籍,则以明初峒傜不靖,调茶陵卫官兵戍守三堡,遂成土著。
我与诸友刚去过地处骑田岭下的湖南宜章,并经宁远、蓝山至都庞岭与萌渚岭相夹的江永,自龙虎关出湘入桂。上面这样的描述,在民国方志中,亦不算罕见。但就是这段话,描述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结构(三条水的流域为宜章的北部,县城在焉;三堡为中部,聚落最为密集,即地方文献中的“九溪四十八峒”;没有描述的是北部的莽山,即“过山瑶”所在)。需要做的,便是厘清这个“历史结构”的过程。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纲领,无非如此。
例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
乙酉,知溧阳县李思模以苍头潘茂为城守。……有彭氏仆潘茂者,素鸮恶市井,狗屠辈悉聚食于其家,而彭氏主人又纵之为爪牙,前县尹金和欲置之死地,赂邑宦陈献策得释。闻南中陷,遂与其党史老柱、史德升……聚众连结,思欲为乱。思模乃集乡绅陈献策、宋劼、周鼎昌等图之,竟以茂为城守甲长。献策置酒,要结群聚,劼以白布百匹、银杯一对慰赠之。城中于是浸浸哄矣!
珍,茂弟也。茂与珍欲谋叛其主,遂倡为削鼻党。盖江南人每呼家僮为鼻故也。茂自为旧甲长,珍为新甲长,凡邑中仆隶悉招入甲内。
庚戌,潘茂以溧阳户口册籍降于清。
以上是关于清初江南削鼻班的记载。以往的研究是将其置于江南“奴变”的背景中去讨论的,特别是将其定性为农民起义。谢国桢在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一文中指出,《濑江纪事本末》“歪曲了这项事实,不甚可靠”,但未提出任何证据。需要指出,他所利用的《金沙细唾》是乾隆时的材料,而《濑江纪事本末》就是顺治时的文献。
其实,关于这一时期所谓江南“民变”的记录非常丰富,而且为大家耳熟能详,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被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拿出来重新审视。今天看来,情形要比以往学界解释的复杂得多,《研堂见闻杂记》说:
乌龙会之剧也,二三无赖,腰斧出入,无不丧魄狂走,鸡犬一空。乡人患之,各为约:遇一悍者至,则以呼为号,振衣袒;一声,则彼此四应。顷刻千百叫号,数十里毕达。各执白梃出,攒扑其人至死。于是会中不敢过雷池一步,而乡民势盛。
说的是城里的“无赖”组成的乌龙会与乡村农民发生的对立,牵扯到自明代以来非常复杂的城乡关系及绅民关系。清军南下后,不仅为此关系格局的变动提供了契机,也成为这一关系格局中一股新的力量。
三、余论
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已远远不同于20年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人们也对地方文献给予了更大的热情。现在的问题是,对所谓“旧史料”究竟应该怎么看?我显然不是搜集、整理和解读“新史料”的反对者,所倡导的只是“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并重。
若干年前,由于大量考古新发现,论者针对顾颉刚先生的学术遗产提出“走出疑古”。因时代的进步、新史料的发现而超越前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顾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层累地制造古史”理论是在对旧史料的重新认识基础上得出来的,这就不那么寻常了。他的错误可能在于某些具体的结论,但他的功绩却在于一般的方法。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更可怕的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用到下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
来源:《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 0000
- 0000
- 0002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