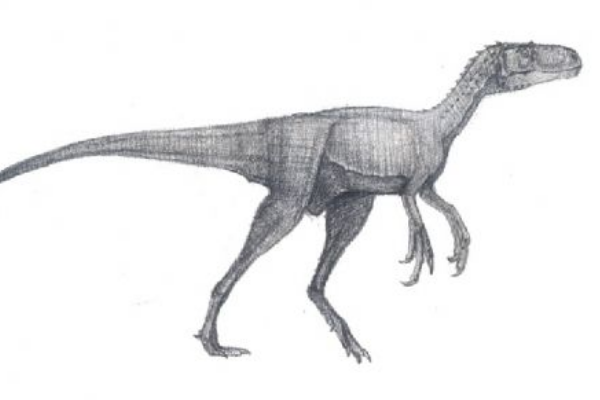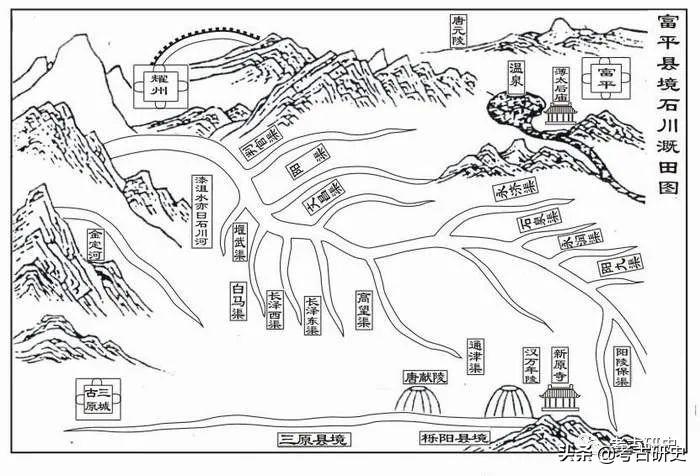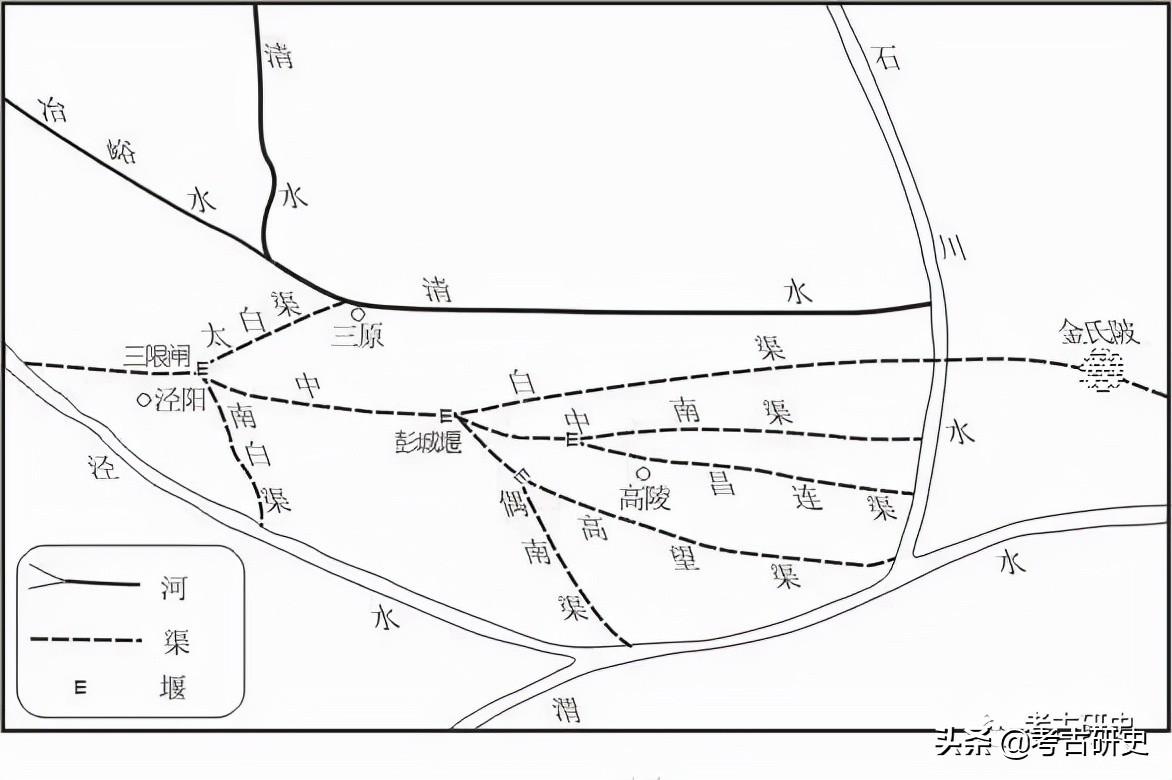李孝聪:北京城内的四合院民居与会馆建筑
一座城市是否有魅力,当然要看她的历史是否悠久,文物古迹是不是比较多,周围的风光是不是秀丽等等。但是,如果从总体来看,看一座城市是否具有超过其他城市的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应该看看这座城市的整体结构和形态,是否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独特的风貌。表现一座城市所具备的内在气质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街道和民居建筑。古都北京,作为历史上封建王朝最后规划建设的统治中心,不仅整体布局严整,宫阙建筑宏伟,就是那以四合院为主的民居,也有如城市结构的细胞,遍及全城,更给人留下不同寻常的深刻印象。
传统的中国城市一般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有着独特的文化风貌,区别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新兴的工商业都市。中国城市的风格是城市社会在许多世纪以来,适应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需要,在形态上长期演变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形态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每个阶段既继承前代的传统,又融以新的特色,反映后一历史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每座城市平面布局展示的意象特征:可识别性与可印象性,都是城市成长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脉络和特征,历史学者传统的研究方法通常是从文献入手,描述城市的经济生活和各色行业、城市的政治生活与阶级斗争、城市的文化生活及风俗习尚;进而试图分析一座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特点。可是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总是着重于政治,着眼于大的历史事件,因此其研究视野总是平面的、线性的,即使照顾到城市的经济和文化,给读者的感觉仍然是相互割裂的,一些条条块块的拼凑,就像是中药铺的药方或饭桌上的拼盘,其结论也很难令人信服,很难使人对所研究的城市的特征得出清晰的印象,至于城市社会和市民生活是如何运作,城市文明的历史基础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如何发展演化,就更无从说起。
一、北京城内的四合院民居
元代坊巷胡同制布局,最有利于沿着各条胡同的南北两侧安排兴建民宅。这是元朝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与传统的五行、形胜等文化观念在国都建筑布局上最集中的体现,也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元大都建城之初,规定居民自金中都旧城迁入新城,按统一规定的“以地八亩为一分”宅基分配建房,而且必须是有财力充分利用这一分宅基进行建房的住户,才准予迁居新城。当时是否规定了统一的住宅标准和建筑式样,史无明文。但是以后的考古发掘表明元大都城的民居基本上都采用了坐北朝南、相互垂直,布置主要房屋的设计。这一特点是和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和北温带季风区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受到元大都城街道框架的制约。1969年拆城墙修地铁时,在北城墙基址下发现了元代住宅遗址。后英房胡同一所大型住宅主院的正房建筑在坐北朝南的台基之上,前出轩廊,后有抱厦;正房前有东西厢房,东跨院是平面为工字型的建筑,用柱廊把南北两屋连接在一起,显然继承了宋代以来最流行的建筑形式。另一种一般的居住形式是在一个院落内建两明一暗的长方形房屋,并列成排,暗室环三面墙筑土炕作为卧室,两家共用一堵山墙,据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统一修建的专为出租的廊房。元大都的民宅建筑型式介于唐宋与明清之间,虽然有别于后世明、清两代标准的四合院落,但四合院的框架雏形和功能已经出现,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应当看作北京四合院建筑的前奏。
(一)明清北京城四合院建筑的形成
北京的四合院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原地区城市住宅最典型的代表,它的形成肇基于明清两代颁布的住宅等级制度。
明朝规定:一、二品官员宅第的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不许在宅院前后左右多占地,或构筑亭馆开挖池塘;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明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宗法观念已经比较鲜明,讲求家族内的长幼有序,既声气相闻,又要尽量保持自家的隐私不外漏,只有把房子建得面面相对并筑起高大的院墙将其封闭起来才可能实现。可是,同时又必须照顾到元大都留下的胡同之间的宽度,大约70米,不能过深,以及适应北京地区气候条件的坐北朝南形制。那么只有两进、三进的四合院制式最为适宜了,一些贫民的小院则散落在穿插于大胡同之间的小胡同两侧,或深宅大院之间的空地中。尽管有些达官显贵、富商大贾们并不严格遵守建房规定,但总体来讲,明北京城内的住宅在严格的禁奢制度和现实条件制约下,在继承了元大都住宅传统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整齐化一的四合院格局。
清朝,顺治五年(1648)下移城令,驱汉人迁出内城,到外城居住。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同时规定,汉人可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而旗人领俸,不事生产,皆分配内城原明代遗留下来的宅院居住。这种民族隔离政策直到清朝道光以后才逐渐松驰。为了避免旗人迁入时的混乱,顺治年间规定了住宅配给的标准,按官职高低分配前明留下的宅院,大量低级官吏和八旗士兵只分给一至三间。由于这项制度的规定,既保持了明代业以出现的四合院不被拆除,也使明代留下来的贫民小院派上了用场。某些已经废弃不用的,明代遗留下来的仓场,则改建成王府,例如:太平仓,清初改作庄亲王府;西城坊草场,被慎郡王府占用;台基厂,建造了裕亲王府。而且一并按照明代王公邸第的四合院落加花园跨院的形式而建。康熙年间,随着北京城市人口的增加,开始增建新的官兵住宅,同时颁布了新房屋的配置标准、尺寸和装修用料的规定。
康熙十四年(1675)谕令,按官位品级分配住房或建造宅院的标准:一品14间、二品12间、三品10间、四品8间、五品6间、六至七品4间、八至九品3间,其式全仿效明代勋戚之旧。清代再次颁布建房的等级标准,使旧北京内城民宅建筑的四合院风格更趋于设计上的规范化。
清朝,满、蒙、汉八旗官兵都是携家属而居,在北京内城的分布规律具有圈层结构。皇城以内,仅由满洲八旗人分配居住,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皆无资格,在最接近紫禁城的皇城内形成内圈;第二圈是由蒙古八旗人,分配在皇城根四围;外圈即最外围居住的是汉军八旗人。皇帝亲统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人口最多,被分配在皇城的北面,这种现象反映出明显的族群差别和地位亲疏。满、蒙、汉八旗各有衙门官厅,原设置于本旗辖域内,以后全部由皇帝选定位置,分处于城内几处,称都统署。例如:西单北大街英子胡同东口南侧路西是镶蓝旗满洲都统署官厅之所在,门面虽已改建,院落结构尚能辩识。八旗官兵在北京内城的分布和组织形式是按照都统——参领——佐领,由高到低,层层负责。佐领是最基层的军官,共1128名,掌握手下的三百名士兵及其家属,散布在全城各地,俨然为一个个城市社区。在这些佐领管区内,既有王公贵族的府第,也有下层军官的小院和士兵们携眷居住的营房,还有衙门、官所和寺庙。另外,八旗还设立了各旗的宗学、官学、义学等各级学校,训导八旗子弟以备将来选拔为官。这些八旗子弟学校都设有小校场,供平时操练之用,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八旗的官衙和学校都被改作北京的中小学校。譬如:西城区祖家街的北京三中校园就是原正黄旗官学校址;西单北大街石虎胡同原民族学院附中曾是右翼宗学旧址,民元以后一度改作蒙藏学校;西四北四条(原受壁胡同)小学,即原北师一附小则利用了原正红旗官学的旧址。无论这些建筑物的职能有多么大的不同,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有多么大的悬殊,有一点却是出乎意料的一致,那就是都采用了统一的四合院的组合形式,这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二)四合院的组合结构与传统文化
一般说来,四合院总是一个被高墙封闭的院子,按照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标准的住宅大门面南,并开在东南角,它产生于传统的中国相宅说中的方位法则,离、巽卦位易于成名,有利财运,所谓大吉也,故多被遵循。门或三间或一间,巍峨华焕,大门内迎面建影壁,使外人不能窥到宅内的活动。由此左转西进二门,至前院。南侧的一排房倒座,就是门窗向北开,冬天冷夏天热,称作“下房”,通常用作客房、书塾,堆放杂物或听事(男仆)的住所。前院正北设第三道门,常常修成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内侧迎面仍然矗立一座影壁或木制屏风,挡住来人的视线,使外人感到深邃莫测,而主人则从容不迫。穿过垂花门,始入正院,院北的正房最适宜居住,是长辈的居室,也是家庭成员们集中活动的地方,俗称上房。前廊开间很大,后墙不开门窗,冬暖夏凉。上房的东西必有套房,或曰耳房,一般配置厨房或厕所。院子的东西各建三间厢房,亦有耳房,名曰蠡顶。厢房是晚辈的住处,前廊出檐,后身也不开门窗,既安全又可以免去上下午日光的东晒或西晒。整个院子用抄手回廊联系,不畏风雨,颇便往来,构成全部宅院的核心部分。在正房耳房的一侧开有过道或穿堂门以达后院,后院的北边建筑一排后罩房,安置女眷、女佣或用作储藏室。也有的将上房设计为主人的书房或会客的地方,而把卧室移到后院的北房里,左右再建东西厢房,这样就组成了两进或三进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官僚大户,家室财产多,房子不够用,则在主四合院落的侧面修建跨院、别院,依然按照标准的四合院式样,在南北纵轴线上对称地配置房屋;更有在住宅院落左右营建花园者,以满足家族情趣的需要。采取跨院的形式,完全受制于两条胡同之间的宽度只有50步(77米)。这些主院、跨院、别院或花园之间,通常都有随时能够启闭的门来限隔,以区别中国传统家族中的子女分房,所有院落在一起则组成一个复杂而有序的四合院群体。
北京四合院的房屋建筑采用传统的抬梁式木构架,外围砌青灰色砖墙,硬山式屋顶,墙壁和屋顶都比较厚重,为的是抵御冬季凛冽的寒风和夏日炎热的酷暑。屋内和院子的地面皆铺以方砖,雨水通过暗道排出院落。室内根据生活需要,利用隔扇、屏风或博古架划分空间,较少筑砖隔墙。元代室内设火炕取暖,明朝以后逐渐被木床取代,床的位置和家具的摆设也很有讲头,既要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也要遵循风水观念里的气。
北京四合院的设计反映了强烈的封建家族宗法礼教的思想,长幼有序,主次有别,不得造次。也反映了中国人传统心态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价值观念,即身处世外桃源,与世隔绝。对于外部世界,只能从自家的房子里看到邻居的树梢,不能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不肯也不愿意洞悉邻人的惊变。而对于内部来说,家庭成员每天都可以在庭院里相见,亲亲热热,那个四方院子顶上的天空,永远只属于这个家族的自我。另外,四合院的建筑设计充分照顾到环境与气候的影响,高大的院墙挡住了街道上的喧嚣,庭院内栽种的花木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构成一个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它那背北面南的房屋设计原则,垂直轴线上对称配置的传统,大门方位选择上的精心思考,无一不是黄河流域早期原始聚落居住结构的世代传承,更处处闪烁着植根于黄土高原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者——伏羲学说的精华。北京的四合院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清晰地显现出以家庭为单位,凝聚一体,既能声气相通,又保持着相对的隐私性的意向。
二、老北京城的会馆
在北京城里还有一批与内城四合院形成强烈对比的外城众多的会馆建筑。
(一)会馆的类别与管理
截止到清朝末年,北京南城曾经分布着460余座会馆,它与内城的四合院私宅在建筑布局结构上有些接近,职能上却有相当大的不同,建筑风格上也有着一些差别,构成老北京城市的又一种传统文化风貌。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会馆分作两类:一类是各省府州县的官吏士绅按照乡籍在京城设立的憩息燕乐之所,称为同乡会馆。那时的每个省、较大的府都在北京设立不止一座会馆,例如:山西的省馆有三座,江西会馆有二座,属于南昌府的南昌会馆也有三座。至于县馆就更多了。另一类是由商人、手工业者在京城依乡籍或行业差别而修建的共同居住的场所,称作行业会馆。譬如:颜料会馆、银号会馆等等。修建会馆的主要目的是照应、保护同乡同行的利益,以避免受到外界势力的欺凌。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每隔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考试——会试,待贡院出榜之后,凡榜上有名者再参加殿试,分出等次名次,也有一次未中,懒得返回乡里而留京城准备再考者。所以每到考期,各省举人多赴京赶考,一时多达万人。这样便出现了以接待赶考贡生,类似当代的地方招待所性质的会馆。至于外省在京城经商的商人,为了议事、联络乡情,或临时寄居,也需要按行业、按地区建立一些公房。当然,也有两种性质兼顾的,因为商人一般都有钱财,能够购置房产为乡里做些公益事业。
一般来说,会馆的房产来自以下几个途径:其一,在京城为官的显宦出资捐建,如:芜湖会馆是明朝永乐年间工部主事俞谟出资买私人房产捐建,福州会馆系林则徐所捐;其二,在京的官宦将自己的私宅捐献改建,如:全楚会馆系由大学士张居正的旧宅改建;其三,官僚发起,商人出资,大多数会馆属于此类;其四,商人独资购置,主要是行业会馆。也有某些家势衰微的名人欲出卖自己的房产,则为会馆购置产业创造了机会,因此,有些会馆曾经和名人的旧居联系在一起,而带有几分文化色彩。例如:韩家潭广东会馆,原是清初著名学者李渔(笠翁)在京旧居,曾在此编写《芥子园画传》;广安门内的扬州会馆则是名士徐乾学的故第“碧山堂”。
会馆的管理,一般是由同乡人中在京城居官地位高、富于声望者主其事,也有类似董事会之类的管理团体。平时住在馆里的工作人员叫“长班”,也有几代都在会馆中做“长班”的。北京的会馆以江西省最多,明代已有14所,清光绪年间达到65所,占了全部会馆的七分之一;其次是浙江41所,安徽、山西、广东、湖北、江苏都超过30所;就连新疆也有一所哈密馆。
(二)会馆的分布
会馆在北京分布的地区是有规律的。最初,会馆总是选择城市中交通便利的城门内外,并且多与商业街区为邻。这与会馆拥有较多的流动人口,以及行商坐贾、手工业者有关。另外,明清两朝的贡院一直位于东单牌楼东边未动,殿试在紫禁城内的保和殿,它们的位置也决定了外城的会馆总是分布在趋向于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的道路两侧。会馆很少能在内城中心或官署衙门附近落脚,这大概是一条规律。明朝改造元大都城以后,内城的南城墙向南移,通惠河北段被包入皇城,江南来的船只再不可能进入北京城中。人们在趋近正阳门的道路两旁贷屋赁居,搭盖棚房,存储买卖货物商品,形成前门外的商业街和正阳门内棋盘街的“朝前市”。从而吸引会馆首先在前门外这一地区发展起来。清朝初期的满汉分治和移城令,更迫使会馆只能在南城择地,但又避免距离前三门和商业闹市过遥,所以,几百座会馆主要集中在天坛、先农坛以北,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大街两侧的地段内,形成清朝末年北京城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富裕的地区。
(三)会馆的建筑结构与文化特色
北京的会馆一般都屋宇轩昂,房屋众多,只有那些僻远的小县馆庭隘而屋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集资而建,财力雄厚,更主要的是会馆里往来人多,官绅、客商、赶考的贡生,没有大量的客房不行,所以会馆往往需要盖许多单间房屋。在会馆里投宿,不收房租,还供应开水,但是不许携眷,禁止住女人。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述锡金会馆曾为一求宿者饰婢为童,引起阖馆大哗。鲁迅先生当年住在绍兴会馆时也遇到过类似的争吵。
按照地方民间风俗传统,全国各地都有本乡本土尊奉的神癨。譬如:江西人普遍尊奉先贤许真人,福建各地尊奉天妃,山陕商人尊奉关圣大帝(关羽)或三圣公:刘备、关羽、张飞,湖广崇奉大禹,两广尊奉关圣……各省的各府、各县也往往各有所尊。为了求得所奉神癨的保护,凡同乡人一起筹建会馆,必先建立乡祠,使同乡人得以聚会,通过共同的祀神活动,达到联络乡谊的目的。因此,会馆总少不了供奉乡神、乡贤的殿堂,而且以这座乡神(贤)殿为中心构成会馆的主体建筑。更有一些会馆干脆就以祀神的祠堂作为会馆的名称。诸如:前门外西河沿正乙祠,系浙江银号会馆;宣武门外土帝庙斜街三忠祠,系山西省馆;达智桥岳忠武王祠,系河南会馆;前门外打磨厂萧公堂,系江西南昌乡祠会馆;鲜鱼口二忠祠,系江西吉安会馆。
某些规模较大的省、府会馆,在供奉乡神(贤)的主体殿堂对面常常盖一座戏楼,例如:虎坊桥湖广会馆、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前门外小江胡同平阳会馆的戏楼都是很出名的。戏楼与主殿堂及它们之间的院子构成了一个“共享空间”,是会馆内的各色人等会聚的场所。每逢节日,在这里祭祀乡神,聚餐演戏,联络、聚合同乡、同行业人们的情谊。清朝末年,西珠市口的浙绍乡祠(又称:越中先贤祠)几乎天天都有堂会戏。这也正是造成自徽班进京以来,京剧能在北京植根,发展到脍炙人口、历久不衰的一个物质条件吧。
会馆的外观常常也是一个用墙围成的四合院,乍看并不容易与私宅相区分。但是,由于会馆的功能既为敦睦乡谊,招待来往的官绅学子,又是维护行业共同利益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不是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生聚的私人宅院,所以,无论在平面布局或建筑结构上,还是环境氛围方面,都与传统的四合院私宅有所区别。四合院的每一进院落都用墙和门来隔断或封闭,喜欢用影壁或屏风来挡住人们的视线,保持自家的隐私。会馆的大多数院落都是打通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往来,也不必使用影壁或屏风阻挡外人窥视的目光。四合院南北主轴线上的正房作为主人的居室,北墙壁不开门。会馆主院落轴线上的正房不住人,或是乡祠,或作为公议堂,有的北墙也被打通,参仿南方民居的过厅形式,正中布置乡贤牌位,牌位屏风背后的北墙正中开一门;更有把主轴线上的所有房屋前后墙皆打通开门,所谓“九门相照”者。会馆院落群组的配置并不完全遵循背北面南设计主轴线的原则,因为北京南城的街道大多没有经过规划,而是明朝中叶增建外城以前,随着人们趋向南城墙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这三座城门踏出的道路自然形成的,因此有许多斜街,从而限制了会馆兴建时房屋院落轴线方位的选择。另外,会馆大门的方向也不似四合院那么固定而较为随意,这自然受制于所在的街道走向,不过从风水观念讲,有几个方向还是注意采用的。如:向北开门能使业务兴隆,东南开门有利财运,西北开门有利向外发展等等。更多的大门在设计时着眼于气派宏阔,或适于进货进车,修成坡道直贯而入,而不拘泥于方位。四合院是封闭的、家庭式的,讲究宗法礼教;会馆则是开放的、乡里乡亲的,注重情义交往。四合院的气氛是含蓄、幽雅的,会馆则是热烈、甚至是喧闹的。四合院的家族色彩浓重,而会馆的地域特征极强。当然不应否认,从整体上看,南城的会馆,无论来自江南,还是西北诸省,其建筑形式大部分仍然采用了北京最流行的四合院数进院落与正房、厢房配置的结构,而没有把当地的民居形式照搬过来,应该说是人们为适应北京的气候条件和京城文化传统的一种选择。
会馆也许更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在首都北京生存,保持其风格和传统创造了有利条件。会馆集中的南城前三门地区汇集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各种文化、各种习俗相互交融,在会馆集中的街区往往还保存着不少代表过去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建筑。诸如:各种老字号商店、老北京的戏院、饭馆、酒楼、茶馆、书肆、当铺、妓院大多集中在这块地区,正是适应这里聚居着的大批异乡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不同需要。会馆甚至也为近代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从康有为兄弟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七树堂筹划变法,发起公车上书,到设于粤东会馆的保国会鼓起更大规模的维新声势;从武昌首义后湖广会馆传出的句句革命口号,直到毛泽东去烂漫胡同湖南会馆发动驱张运动,都是利用会馆的开放性,把思想变成行动,进而推向广大的社会。所以,老北京的会馆是留住历史的记忆,值得注意的传统风貌。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每年再无众多的考生来京居住,会馆的房产又非个人一家私有,无法经营护理,逐渐出售给个人,遂演变成大杂院。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通常人们从文艺作品或影视传媒材料中看到的那种邻里之间声气相合的印象,不过是在帝制解体、民元以后的大杂院里才逐渐出现,既不可能在私宅四合院里出现,也不会是会馆内产生的社会现象。
老北京城市建筑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鲜明的,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四合院式的平房难以适应人口压力对住宅的需求。政府不断地拆除一些四合院,改建高楼住宅。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改建从未停止过,但是截止到80年代中期,北京城市的传统文化特征还没有被破坏。这是因为过去四十年迁入北京城市的人口,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社会威望和文化水平方面基本上是协调的、均质的,与旧的城市文化特征基本上是和谐的。近十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外游客、涉外单位、常住北京的公司、企业代表剧增,高薪阶层人口比例上涨,打破了城市文化的均质性。这种变化不仅导致对住房和购物有高标准的追求,而且追逐与市中心接近的良好区位,造成现代风格的高层宾馆饭店、写字楼在老城区内争相建造。这些象征金钱与欲望的全金属玻璃外壳式的建筑,同北京传统的城市特征是极不和谐的,它们不仅蚕食着北京城的传统文化风貌,也夺走了北京人追求静谧淡雅的情怀。
当今天的城市迈进发达的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走向自身现代化时,随着成片的、居住了几代人的传统房屋建筑的拆毁,的确给市民送来了乔迁的喜悦,但是也带走了祖辈传下的文明。面对越来越失掉民族风格的“家”,将不只是情怀的失落,也产生着困惑:是否旧的建筑都应该或迟或早地被拆掉吗?什么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国城市的特征,应该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而被保留呢?如果希望回答上述问题,其切入的视角应关注城市社会的空间结构与运作机制,城市文明的兴衰及其特点。只有明确这些,才能在社会转型期,当城市面临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时,有意识地保护那些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特征的建筑与结构,使中国城市不会失去民族特点和文化魅力。
来源:《黄河文化》,华艺出版社,1994年
- 0001
- 0000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