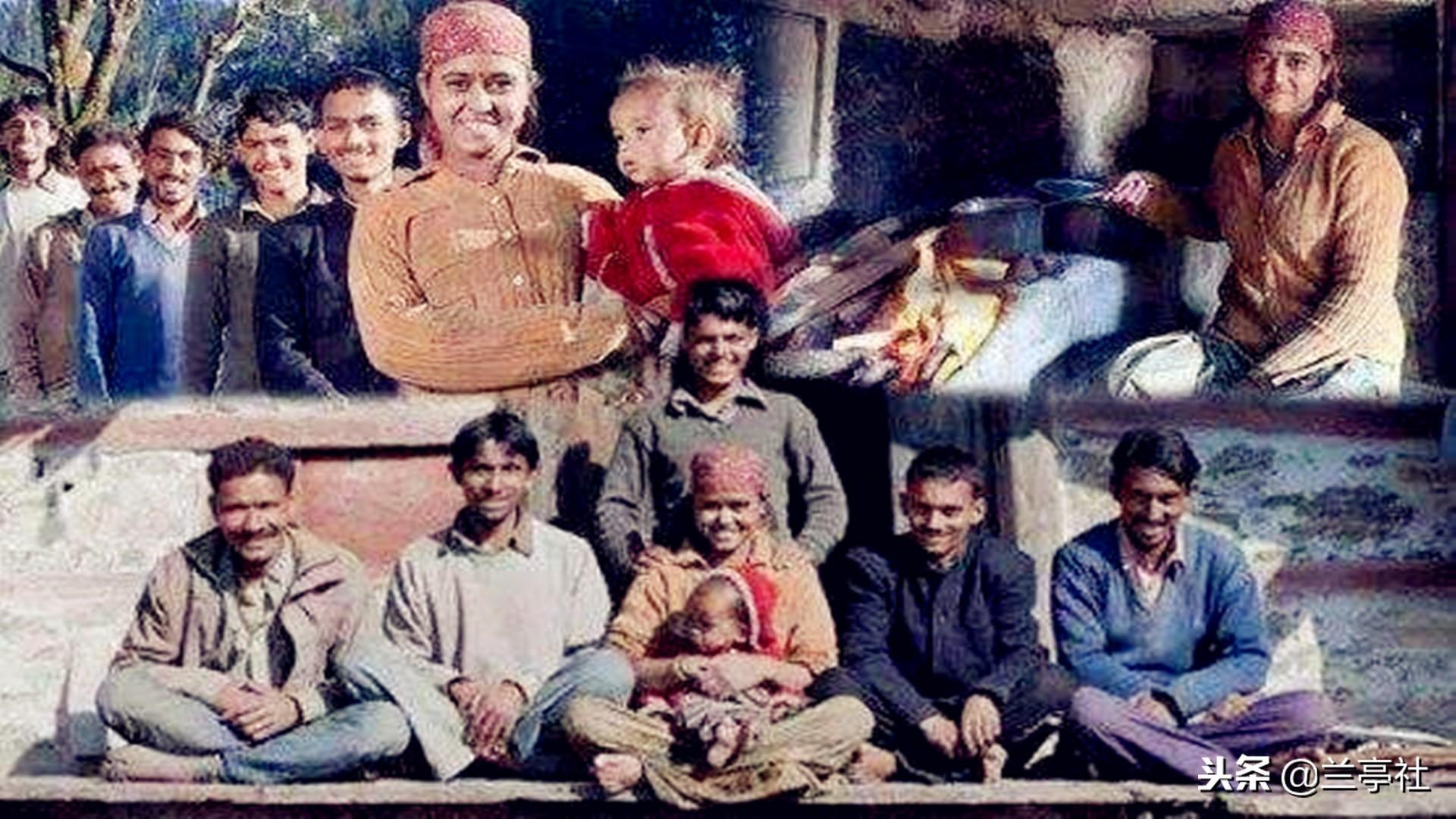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问 你说吕思勉先生也是一大家,可否提出一些评述的意见?
答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1884—1957),江苏常州(武进)人。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诚之先生平生著述极为丰富,为人所习知的,以出版年份序之,有《白话本国史》(1922)、《经子解题》(1926)、《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先秦学术概论》(1933)、《史通评》(1934)、《中国民族史》(1934)、《燕石札记》(1936)、《中国通史》(1940、1945)、《先秦史》(1941)、《历史研究法》(1945)、《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燕石续札》(1958)、《隋唐五代史》(1959)诸书。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未发表的札记与已发表的两部札记合并,分时代编为《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1982),还有《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未能完成,不知将来是否有人能整理出来,作为未定稿出版。
综观先生一生著作程序,可知他的国学基础极深厚,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属于国学范围的居多,所以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这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在1920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顾颉刚师在《当代中国史学》下编《通史的撰述》一目中列举诸家通史,就以此书为首,认为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谓当之无愧。我想这部书大约是当时极有销路的一部通史,193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也是我读的第一部通史,相信这部书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必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先生在1945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称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他说唯物史观“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吾人应当注意,此时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好几年。再看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册,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次年出版的《先秦史》,其编排次序,在先秦各代政治事迹之后,分类述文化现象,也是这个顺序。这一程序,正是他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更可见他这种意识发萌很早,与中共得政后一般趋附者大不相同。就因为早有此种意识,所以他治史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在通史及各断代史中,这方面的篇幅相当多,《读史札记》中这方面的条目也不少,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
就著作量言,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通贯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我想这可能有几项原因。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诚之先生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有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前文谈到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而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记得高中读书时,看到张贴在阅报栏中的一张报,有一篇短文描写诚之先生与另一位文学家的生活习性。近年又看到黄永年所写《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一文与钱宾四师的《师友杂忆》(第二篇《常州府中学堂》第二节)写诚之先生一段,再参以他的著述风格,与半生株守光华一事,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的阅读过三遍,是可以相信的。
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当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有好处,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只是厚古薄今耳!至于材料取给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参用,须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几部断代史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正是一项难能的基本功夫,后人尽可在此基础上,详搜其他史料,为之扩充、发挥与深入、弥缝,但不害诚之先生四部书之有基本价值也。
1983年6月20日初稿,8月10日增订
来源:《治史三书》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