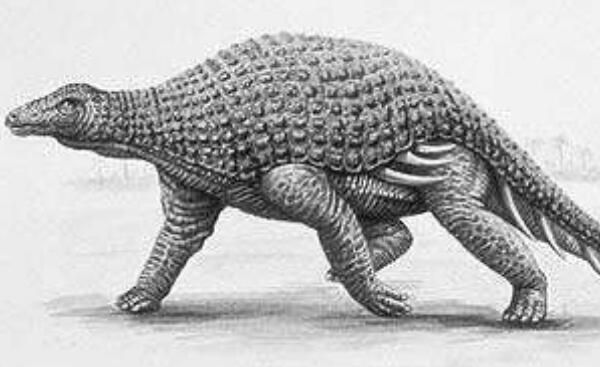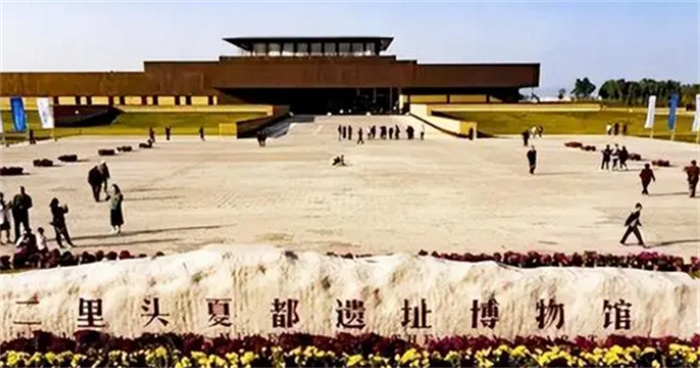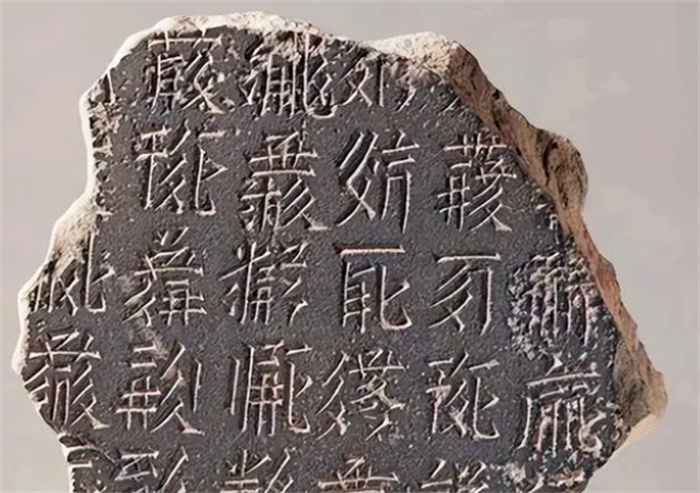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建筑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组织的田野工作所搜集的材料上。要了解新基础的性质,我们应该先检査一次旧基础的结构。由北宋到清末,中国的古器物学家有过不少的辉煌成绩;但是很显然,假如我们墨守传统的方法做下去,这门学业的前途,就显得没有多少路可走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原因。让我把八百年来古器物学在中国进展的情形,先做一番概括的说明。
留传到现在,最早的,比较最完整的金石著作,自然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这是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完成的。就很多方面说,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1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象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的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约三十年后,规模更大的《宣和博古图》问世。有了皇家的支持,金石学——古器物学的前身,渐渐地在那时的学术上就占了一个地位。但《博古图》的组织及编辑,纪录的方法,考订的题目,叙事的体裁,差不多全以《考古图》为准则;只在若干小的方面有些改进。从此以后,经南宋、元、明,直到清代,在这门学问上致力成专家的,有不少著名的学者。但是,很奇怪,这些名人的贡献,差不多完全在文字的解释及器物名称的考订上。吕大临为古器物学所悬的三大目标: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似乎只有最后一条吸引了南宋及清两代的金石学家全部的精神,得了若干结论。在材料本身的处理上,这几百年内,不但没有进步,并且显露了退化的迹象。前清二百六十余年内,出有不少的大收藏家,有好多是看不起宋人的工作的。但是,假如我们拿光绪三十四年出版的《陶斋吉金录》——清代最后的一部具规模的金石著作,比《考古图》晚了八百一十六年——与《考古图》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端方及他的门客所编纂的这部书,连抄北宋人都没抄会。吕大临很小心地注意到古器物的出土地;陶斋的记录,包括这一项目的却很少;单就这一点说,我们已经可以辨别他们不同的治学精神了。民国年间,王国维纂辑《两宋金文著录》时,曾说:
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其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谬诚若有可讥者,要亦国朝诸老所不能免也。……
这可以说是一段非常公允的批评。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在11世纪已有的一门光芒四射的金石学,经过了八百年以上的时间,两朝皇家的提倡,仍停滞在不进步的状态中?是否因为成了一种宫廷学术,就构成了它不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设也许说对了一部分,但并不能成为全部答案。这问题的范围牵涉到中国全部的思想史,及治学的态度。我们可以说,自然科学在中国落后的原因,也就是古器物学在这一悠长的时间,没有进步的原因。这个原因,概括地说,可以推溯到两宋以来半艺术的治学态度上。自然科学是纯理智的产物;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在这一演进中,吕大临为古器物学所悬的目标,也就像秦、汉方士所求的三神山一样,愈求愈远,成了永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因为与这一学业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没有被这半艺术的态度照顾到,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
上面所说的注意地基工作,在现代学术工作程序上,等于原始材料的审订。中国古器物学的创始人吕大临,原认识这一点的重要,故在他的《考古图》所录的二百一十九器中,注明了九十七件的出土地。很可惜地,他的继承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方面充分地发挥那内在的重要性。
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安阳发掘报告》的第一册的时候,蔡故院长孑民先生曾替这刊物作了一篇序,勉励我们这些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人们。说:“……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自宋朝以来,中国考古学这段光荣的历史。”“但是”,他继续地告诫我们,“近几百年,世界为自然科学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尽适合现代的要求。……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异我们的立点和方法,哪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时代进步呢?……”
蔡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自然科学开始动荡中国的时候。在中央研究院前总干事丁文江先生及现任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先生领导下的地质调査工作扩大的范围内,已将那沉没在神话传说中的远古人类历史的东亚的一面,给我们一种新的认识。同时,科学的考古发掘,也就在这一风气中开始了。顺着这一方向努力所获的成绩,给研究古器物学的人们至少有两种启示: (1)古器物学的范围,决不能以三代为限度,更不应封锁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内;人类的活动,表现在器物上的,有很多不同的资料;在时间上,也超过我们过去所知道的百倍以上。(2)古器物学的原始材料,也同其他自然科学的原始材料一样,必须经过有计划地搜求、采集及发掘,最详细地纪录及可能地校勘,广泛地比较,方能显出它们的真正的学术价值;经过古玩商手中转来的古器物,既缺乏这种手续及有关的记录,自然没有头等的科学价值,更不能用着建筑一种科学的古器物学。
田野工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训练,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及若干生物学的部门,都是不可少的;地质学的重要推论,差不多全靠着田野工作得到的观察。古器物学依靠这一门训练的程度,至少与地质学相等;所需要的精密的程度,有时也许还要超过地质学的要求。我们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一训练的必要性。诸位中有很多是听过安特生博士的大名的,他是瑞典的一位有名的地质学家,约三十年前,被聘到中国来作地质调査所的顾问。安特生博士确实替地质调査所作过不少的事,包括若干具有永恒价值的贡献。他的丰富的兴趣,并不限在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范围以内;在他的田野工作期间,他做过几件动人的考古工作,第一次发现了华北史前文化,领导了好几次科学的发掘。他的考古报告久已成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必读的书。但是,最近已有不少的专门学者感觉到:他的田野观察,虽甚精确,似乎尚可做得更精确一点;他的推断,大部虽极可靠,但那可靠的程度,显然尚可提高。他在甘肃工作时,只亲手发掘了几个遗址,却大量地收买了盗掘的古董。根据有限的发掘经验,评定大量的盗掘器物,结果就陷入若干短时期难以纠正的错误。他的有名的甘肃史前六期的推断,照最近在田野的复察,已需要基本的修正;他的更有名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所作的推论,是否完全符合地下的实在情形,已招致了不少的疑问,到现在已成为史前考古在中国的一件亟需要解决的公案了。
以安特生博士在地质学的成就及他的广大的田野经验,来做几回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尚不能满意地配合现代科学的要求;我们可以由此认明,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所需要的这一项训练,应该是如何的严肃、坚实、透彻了。这决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能办理的。这更不是故意地要把田野考古工作的方法说得特别的艰难深奥。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一个作化学、物理学或生理实验的科学家,虽也靠不少的助手推动他的工作计划,但到了紧要的阶段,总是自己主持,亲自动手工作,并作记录的;他决不会想到躲在家中或图书馆内遥遥指挥,托另一个人代替执行的办法;对于同行的实验,在接受以前,大半都要在自己的实验室复做一次,或若干次,看它准确到什么程度。重复实验,可以说是帮助同行朋友最虔诚的友谊表现,到现在,已成为实验科学的一种固定习惯了。靠田野工作得原始材料的科学家,却享受不了这种实验室的互助。田野考古的情形尤为特别。冰川的遗迹、火山的构造、断层的暴露,均可供给无数的地质学家继续的踏査、复査及再复査。但人类的历史却永不重演。一个重要的遗址,一座古墓,一尊纪念石刻,若是被摧毁了,没有第二个同样的遗址、古墓或石刻可以代替的。同样,若经手发掘古代遗址、古墓的工作者有了错误的观察,或不小心的记录渗入他的报告内,这种错误很难用直接的方法在短时期内校勘出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像这样的情形,除了古生物学外,没有其他的科学可以比拟的。因此,我们更感觉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人们所负的科学使命之重大,这种责任感应该使实际工作者加倍小心。无论如何,他应该用自己的耳目,作自己的观察。这自然不是唯一的条件,但是不可少的条件。如此得来的材料,至少可以给采集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这种材料的可靠性,由此亦可以得到研究人的信心。这是一门科学能够成立的起码条件,宗教家所说的“起信”的作用。这种信心的培养,必须完全由纯理智的观点出发,不能杂任何情感的成分;若在任何方面,情感与理智发生些微的冲突,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应该有勇气放弃他的情感,遵从他的理智。只有如此地做下去,方能把这门学问建筑在牢固不拔的基础上。
中国古器物学,经过了八百多年的惨淡经营,始终是因仍旧习,没有展开一个新的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原始材料审订的工作及取得手续,这八百年来的古器物学家没有充分地注意。他们很显然地都晓得,古器物是一种珍贵的史料;但他们很少感觉到,这些材料的本身另有一段历史,为说明它们所以成为历史性材料的不可少的知识。若干对于古器物的来历有直接兴趣的人们,却没有把这兴趣正常地发展出来,只在古器物的本身上抚摩,想由这一方法断定它的真伪。真伪的断定,在他们的下意识中,似乎不必在“出土”问题这个方向寻求;向这一方向寻求所引起的可能困难,不但是远在断定真伪之上,同时也是不值得读书人尝试的。
十余年前,罗振玉的儿子罗福颐,校补王国维的《国朝金文著录表》,改名为《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表内列了他认为可靠的古器物,共五千四百二十三器。表中有出土地一栏,但大半都是空的;填有出土地的器物,共为一百三十三件,占所录全数的百分之二点四五。就是说,在这表中所列的器物,每一百件内,平均只有将近二点五件的器物有出土地的记录。但所记的地名,大半是关中、秦中、洛阳这类地理上的共名,虽说是比没有好,但它们的科学价值甚为有限。这一表足以证明清代的古器物学家对于古器物出土地的极端的忽视。
要是我们再进一步,追求古器物流传的真相,更可以进一步地了解,宋代及清代的收藏家所重视的古器物,只能代表极狭小范围内的选择标本。根据这些标本发展出来的古器物学,也随着流行的选择标准,完全变成了文字学的附庸。有田野工作经验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到,清代学者著录的五千四百二十三器,照那时的搜集及流传的情形看来,至少代表十倍以上的损失;换句话说,录存的五千余器,每一件都是由很多数目中挑选出来的一件。古董商挑选的器物,除了“有款识”为他们的最高标准外,还有若干不可少的附带条件:这些器物必须是完整的,花纹好的;只有如此,才能入收藏家的眼,才可以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代价。在整理安阳出土的器物时,我常感觉到,小屯发掘出来的青铜礼器,要是用古董商的尺度来衡量,八十二件中可以拿出来与收藏家见面的,最多也到不了八件,其余的也许经手搜集的人根本就不会用正眼一看。这一实情,是每一个有常识的古玩商人都要承认的。我们姑且不必凭吊这种惨重的损失,但我们必须认清:根据这些无情淘汰幸存的标本所建置的古器物学的发展,是畸形的、片面的、不健全的;这一发展决不能解决古器物学的基本问题;好像研究上海或北平社会问题的专家们只根据他们在上海的四大公司或北平的三海内里绕圈子所找的资料,他们显然不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近三十余年,田野工作所搜集的与古器物学有关的材料,可分两组解说:一组是由地质的调査及古生物的寻求所涉及的人类遗物与遗迹,主持这一工作的机关为地质调査所,及与地质调査所合作的机关;又一组为完全寻找早期历史材料而发现的人类居住遗址及墓葬所得的成绩,主持这一工作的机关,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领首。这两组工作虽说是由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但在短期间,他们却携了手;在方法及工作技术上,他们有绝对的相同的地方,只在题目上,各有各的范围。由地质调査及古生物探寻入手的工作者,最紧要的课题之一是想把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打成一片。专门历史学的人,眼前的问题为急于把纯历史性的若干主要迹象,由田野考古的途径,向远古追溯它们的根源。这两种出发点是可以同时进行不悖的,在若干方面是可以互相辅佐,充分合作的。近二十年来,这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共同努力,是我们学术界最可喜的现象;他们的收获值得我们在此作一简单的报告。
德日进神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时,曾把近二十年在华北一带搜寻远古人类遗迹所得的成绩作了一次简单的综合的叙述。据他的意见,周口店的北京人时代应该放在早冲积期,约等于三门系的红土期;周口店的第十三、第一、第十五各洞穴的文化遗存虽代表一长时间的发展,有先后的秩序,大致均属于一期。继红土期而起的黄土期文化,曾在甘肃、陕西、山西一带陆续出现,以宁夏附近靠长城边的水洞沟的遗址为最晚,所包含的内容也最进步。到了晚冲积时期的终结,就到了德日进神甫所称的黑土期,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快到了先史学家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最足代表这一期文化的遗址及遗物,为散见于蒙古沙漠的石片工业及最近在哈尔滨附近札赉诺尔所发现的先史时代的遗存。红土文化期,照德日进的推断,大致与西欧的赛吕(Chellean)文化同时;黄土文化在模斯(Mousterian)及奥吕(Aurignacian)两期的前后。
这几条重要的结论所依据的材料,可信的程度确实合于科学的最严格的标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可以说象征了人类最向上的精神活动;就纯科学的立场说,周口店的工作成绩,在质与量的方面,世界上尚没有可以比得上的。以周口店的工作为模范,在华北一带,从事广泛搜集远古人类遗迹的工作者努力所得,在方法与成绩上,很多可以与周口店的发掘比美。到现在,我们根据这些原始材料,所能推想的东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进展,虽远赶不上西欧或北非的丰富,但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能证实这一类文化在远东区域同样地存在,已足使以三代为上古的中国古器物学家有所省悟了。
到新石器时代,就快接近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期间。这一类的遗址,在华北一带,就已发现的论,远较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为多。第一次从事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是已经提到的安特生博士;据他的《奉天沙锅屯洞穴层发掘报告》记载,他在中国领土内寻找早期人类遗迹的工作开始于1919年,发现仰韶及沙锅屯遗址,在1921年。有名的仰韶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阶段似紧接着关外的黑土时代文化,虽仍属于先史时代,但是,若把史前的人类遗存从周口店算起,仰韶已是尾声。不过,若是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向前推溯,仰韶遗存,自然又可视为中国远古之文化了。仰韶式及比仰韶较晚的彩陶遗址,经过二十余年田野工作人员的不断搜寻,已经证明,满布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一带,由西而东,将近山东境界,转向北及东北,直达热河及南满洲。由甘肃向西北踏査,中国的彩陶,似乎与中亚、小亚细亚及多瑙河流域一带的遗址所出的类似陶器有些不可忽视的关系;这虽是些未定的推测,彩陶文化的国际性是很显然的。专从这一角度看这一批材料的历史意义,仰韶文化的重要,可以与水洞沟的相比,它们都超过了国际的界线了。安特生博士在最早的期间,更注意到彩陶文化与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关系,把仰韶遗物与三代器物作比较研究,得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结论。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蔡院长的领导下成立,所选择的第一个发掘遗址,就是出甲骨文字的安阳小屯村。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联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那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阳发掘时,由于在有文字的甲骨层中一块仰韶式彩陶的发现,大加增高。现在事隔二十年了,回想这一片彩陶的发现,真可以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安阳发掘团前后所记录的小屯出土的陶片,差不多快近二十五万块,但始终没得到第二片彩陶发现的报道。那时注意这问题的,在发掘团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要不是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块陶片的出现,很可能就被忽视了。有了这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同时,这观察也增加了我们搜求类似遗址的信心,参加殷墟发掘工作的几位青年考古家,对于陶器的研究,也就大感兴趣了。
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的同志,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渐渐地得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这一信念,若是用语言加以说明,就是:要解决一个遗址所引起的问题,我们必须参考好些其他遗址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须是科学的发掘事实,具有同等的可靠程度。因此,在这一个小圈子内的青年考古家,短期内就养成了一种跑外的习惯。在抗战开始的前二三年中,这种外勤工作的兴致差不多成了一种狂热。每一季节中,除了经常的发掘工作外,总有几次调査的团体出发。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觉到腰酸背疼。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仁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这种辛苦确实可以得到极丰富的报酬。1930年,考古组田野工作的第三年,我们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发掘了一个小的遗址,却得了极重要的收获,开始了黑陶文化研究的一幕。黑陶文化的发现,解释了一大批在殷墟遗址发现的实物中难加说明的现象;继续的研究,证明这一文化,在中国东部的文化圈内,是由史前到历史期间最扼要的一道桥梁;它的存在,不但把若干专门的考古问题顺利地、明朗地解决了,也把我们对于黎明期中国文化较简单的、单调的印象所具的内容充实了,并增添了丰润的色彩。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一时成了田野考古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中心对象,占了他们的不少的时间。
城子崖发掘一年以后,我们在安阳境内,小屯附近的一个新遗址——后岗,发现了三种文化重叠堆积的现象。领导这一工作的梁思永先生,是第一个断定彩陶文化、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继承秩序的人。从这时起直到抗战的一年,每年考古组的外勤人员都有新黑陶遗址发现的报道;风气所及,别的学术机关,也感到同样兴奋;西湖博物馆在杭州良渚发掘黑陶遗址的工作,确实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成绩。1939年,梁思永先生曾为太平洋国际科学会议把黑陶文化的分布作过一次综合的报道,统计起来,在那时已有七十几个遗址可数;大多数均集中在洛阳以东,黄河流域下游,河南、山东、皖北一带,南到杭州湾了。抗战期间,日本的考古学家在辽东半岛也发现了黑陶遗址。虽说德日进神甫仍不相信这一文化单位尚滞留在石器时代阶段,但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没得到在黑陶文化层中金属器存在的任何证据。
同时,我们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仍是我们田野工作的中心。“七七事变”一年的春天,是我们在安阳的第十五工作季。这不是一个以猎取甲骨文字为唯一目的的工作团体;假如我们把历年发掘的实物分类列举,所得的重要项目为:陶器、骨器、石器、蚌器、青铜器、玉器,腐朽了的木器痕迹,附于铜器上的编织品,在原料状态中的锡、水银及其他矿质,作装饰用的象牙、牛骨、鹿角,占卜用的龟版、兽骨,铸铜器用的铜范,镶嵌用的襄阳甸子,当货币用的贝,残留的或作牺牲用的各种兽类骸骨,保存完全的人骨,等等。这还只是比较显著的节目。每一类的数目均甚为可观,譬如陶器,可以看见全形的,有一千七百余件,若单论出土的碎片,经统计的将近二十五万片。兽骨的种类,曾经杨钟健博士及德日进神甫分别鉴定,除通常的家畜外,包括东海的鲸鱼,太白山的扭角羚,南方的水牛、象及其他若干在现在安阳气候不适生存的种类。有文字的甲骨,青铜制的用器、武器与礼器,均积到一个可观的数目。这些都是头等的、最可靠的古器物学的原始资料。
处理这批材料的方法,自然有不少可以斟酌的地方。科学考古报告的写作,已有一种国际的标准,今天我不打算在这儿讨论;所拟讨论的是在写这报告以前,对于这些发掘出土的器物了解的程度,应该推到什么限度。不加任何解释,赤裸裸地把原始材料公布出来——如气象局、人口局经常所作的——虽是一种有效率的处理办法,却不是古器物学家应该效法的;若说是,必须等到对于每一实物、每一现象的各方面都有一个说法,然后才发表他的报告,争取这样理想标准的科学家能否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却是不能预定的。假如我们把研究与发表分开来讲,我们讨论的范围,就可划分得清楚些。
所谓“对于一种事物的了解”大半是由研究的趋向发展出来的。吕大临八百多年前为古器物学所悬的三个目标——探制作的原始,补经传的阙亡,正诸儒的谬误——每一项均代表对于古器物了解的一面,均是现代的古器物学家应该继续追求的。
但是,“探制作的原始”,单就这一目标说,真是谈何容易!对于一件器物或一种制度,能把它的原始说出来,照现代的观念发挥,就是对于这一器物或制度有了全面的了解。这工作最迫切的先决问题,应该是所谈的对象在地面的分布与时间上的秩序。现代考古学及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对于所搜集的实物及所观察的现象,发生区域的测定,已到了比较可靠的程度;但对于它们发生时间的推断,却离那精确的标准尚远。
断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可以说是自北宋以来,古器物学家用力最久,最没上轨道的一件工作。一件可以完全证明不是伪造的古器物,若也不是由科学发掘得来的原始材料,大约除了这器物本身有文字,文字中带有时代的启示,没有其他更可靠的方法可以用来准确地标定它的年月的。自然,根据已经知道的事实,作若干原则上的规定,用作校定游离物品的时代,一般地说来,不失为合于逻辑规律的办法;但是这些原则,无论是如何精密地归纳出来的,若运用得不小心,很容易领入严重的错误。这是处理古器物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我们细心地检讨一次。
我们可以举两个实例说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方面。譬如,以赵希鹄这样精于赏鉴的人,他所举出的第一条辨别钟鼎彝器时代的标准是这样的:
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素质无文,周器雕篆细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论,而夏器独不然。余尝见夏琱戈,于铜上相嵌以金,其细如发。夏器大抵皆然,岁久金脱,则成阴款,以其刻画处成凹也。相嵌今俗讹为商嵌(《洞天清录集》第五页)
他这一段理论,几条原则,被近代考古发掘的事实差不多完全推翻了。由发掘所得的商器,虽也有“素质无文”的,但并不是“一定不易”的现象。殷墟所出的商代礼器,文饰繁缛的居大半;至于周器,有八百年的历史,更是变化多端,不但有时代的差异,还有地域的区别。最无稽的,为所说的“夏器”,夏代中国有了铜器没有,尚是考古学的一大问题。
赵希鹄所定的断代标准,完全是由“夏尚忠……”这几句话演绎出来的,再把自己的收藏经验杂乱地附会上,算是为“天统说”加了一种新的注释。现在看来,他的理论力量的浅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假若我们记得清楚,这是远在自然科学动荡中国以前的著作,阴阳五行说所笼罩的学术空气下的产品,这又何尝不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套理论。他所推演出来的标准,经不起现代科学的考验,算不得很奇怪的事。
近三十年来,在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下,关于古器物学的工作,中国的学人已有不少的劳绩。科学的源头在西方,故鞭策我们最紧的也就是西方的汉学家。瑞典的高本汉教授,是现代欧洲汉学家中最特出的一位,对于中国古代语音学有过很大的贡献;抗战前,在伦敦举行中国艺术展览的前后,他对于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也产生了热烈的兴趣,陆续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内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论文。最初,他根据了四十六种有关中国青铜器的图录及铭文的著作,作了一番甚详尽的分析、比较,由此找出来了殷铜器与周铜器的基本分别,并把周铜器分成殷周、中周、淮三式。他所选的类别标准,以铭文为出发点,包括全器的形制,各部的形态,文饰的结构,图案的内容;他所作的比较工作,不但将器与器比,并且把每一器的个别部位,及构成每一图案的文饰细目,都作了极详尽的分析,极仔细的较量,故他归纳出来用作分辨各期的标准,要算是极实质,极缜密的了。这是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器物一个最有贡献的成绩,值得我们重视。
至于他所提供的若干辨别时代的具体的标准,是否完全符合由考古发掘所得的事实,自然是我们应该有的追问。据我所知道的答案,他并没做到十全的程度;这一点,高本汉教授却并不愿放在他所愿讨论的范围以内。他的目的,据他的申明,只是要把见于有图象著录的,或有照片的中国古青铜礼器,整理一个秩序出来。他很巧妙地用了统计学的论证法,有若干数目字作他立论的根据;在这一方面,他所下的功夫最足令人钦佩。
假如我们用小屯出土的青铜礼器校订一下他的结论,有两事值得大家注意。(1)“举”、“亚形”、“析子孙”,高本汉教授认为标定殷代器物的三种基本符号,在小屯出土的八十二件礼器上一次也没出现过。(2)他所认的有殷代铭文的器物,所表现的形制与文饰,统计地说来:有些在小屯器物上完全没见过;有若干虽见于小屯器,却不甚寻常。小屯器物的形制与文饰,在高本汉的标准单上漏列的亦不少。
这两件可以注意的事实,自然可以有若干不同的解释;但是,无论我们加以何种解释,高本汉教授的结论可以运用的范围却是大大地被限制了。所受的限制,就纯理论的一方面说,也颇有它的必然性;因为,他的研究所根据的原始材料,虽是极精致的拣提标本,同时,却是经过了有偏见的选择的一群,已经失去了一般的代表性。根据这一群材料所得的推论也就必然地为材料的特性所限制,只能在适当的条件下,方能采用。
在器物本身上寻找它的时间性,如高本汉教授所作的,在欧洲史前史研究的程序上,原是一件经常的工作。这一方法,如用在考古发掘的资料上,往往可以收更宏大的效果。大体说来,一种器物的形态表现,也同一种生物一样,有它的“生命史”;形态的演变是随各器物存在的年岁依次显露出来的;把时代展进的秩序与形态演变的阶段——两者相依的关联,有系统地说明出来,实在是现代古器物学家的中心课题。
由形态的演变说起以探制作的原始,可以说是最稳当的第一步。再向前进的路程,当然也不是一条平坦的直线。过去的古器物学家,最不容易避免的一种错误,是把器物的形制、文饰与功能,不加分辨地混在一起谈。于是文饰的差异,可以认作是形制的差异;形制不同的器物,常被它们的类似功能,在观念上同化了。完全免除这一类的错误自然是绝对的需要;没有这种混淆,形制的真相方能认明。
用作这种比较研究的器物,自然是以来历分明的、时代清楚的为最上;在田野考古极度发展的时期,这一目标是可能达得到的。虽说不是每一个古器物学家都可以有这样的幸运,但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也有它的限度;这一限度,以清除赝品为绝对的、不可少的条件。故在所选的原始材料中:来历不十分分明的,还可用;时代不十分清楚的,还可用;但是,有仿造嫌疑的,必须全部剔除。辨别真伪所需的功力,有时远在科学发掘所需的训练以上;这一困难的克服,是每一位古器物学家必须要完成的。
有了大量的、可靠的资料,方能谈到“类别”工作。“类别”绝不是单单的一种秩序的排列。按器物形态的差别,排出一种行列,固是分类工作的必要节目;但在开始这一节目以前,一个分类学家,对于器物形态发展的秩序应有充足的认识:有些几微的差异,可能象征重要演变的开始;若干显著的、离奇的、庞大的形变,或只代表一种暂时的病态。若把分类工作完全限在外形测量上,那就真是皮相之谈了。郑重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对于器物的形态——无论是集团的、个别的或部分的——发生的起点,可能的演进方向,消灭的原因,都是他们所要细心追求的。有了这种经验,才能选出—种合理的健全的类别标准;经了这种标准的类别,器物演变的原委,也就可以看出一个头绪了。
但是,要对古器物求全面的了解,专在形态的演变方面下功夫,无论作得如何彻底,也是不够的。器物都是人类制造的,它们的存在,既靠着人,故它们与人的关系——器物的功能——也必须要研究清楚,然后它们存在的意义,以及形态演变的意义,方能得到明白的解释。要充分地解释古器物的功能,民族学的训练显然是最大的帮助;这在多方面已经证明了。看红印度人打制石器及用石器的方法,就增进了史前学家对于石器时代生活无限的了解;看他们围猎野牛的方式,万年以前洞穴艺术发展的背景好像就重演出来了。邻近冰川过日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住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所对付的自然环境是极相像的;他们适应环境的方式,大概有若干仍旧沿袭那些古老的办法,所以他们的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若干用具,还保守着冰川时代的样子。云南的麼些人习用的象形文字,有不少的字可以使我们领悟到若干金文及甲骨文字的起源。这一类的例子,现代民族学家,如索那斯教授在他的名著《远古的猎人》所作的搜集至为丰富,这些都是古器物学家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这种参考资料,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古器物的个别了解,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古器物所代表的全部社会的远景,得一明确的、有比例的认识。有了这一认识,古器物学的研究就可以推进到一种全新的、更稳固的基础上了。
[ 1948年1月11日上午,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礼堂,中央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同学会联合组织的纪念蔡孑民先生学术讲演会上宣读。原讲演后段,有幻灯片说明,本文未能插入,只将讲辞改写数段,以求连贯;但大半仍是宣读原文。付印前,曾请沈刚伯、董作宾两先生校正字句,特此志谢。]
1950年4月2日夜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