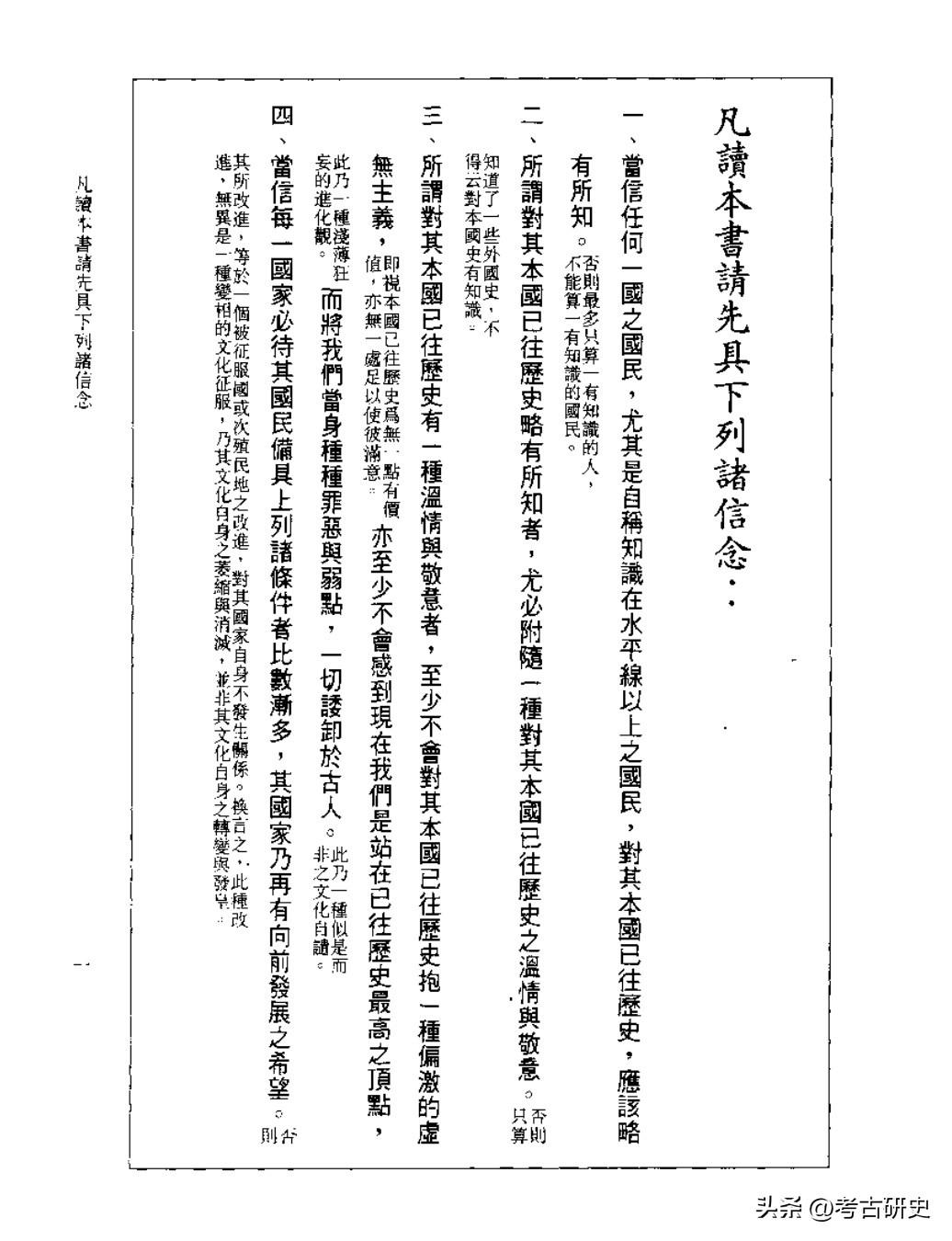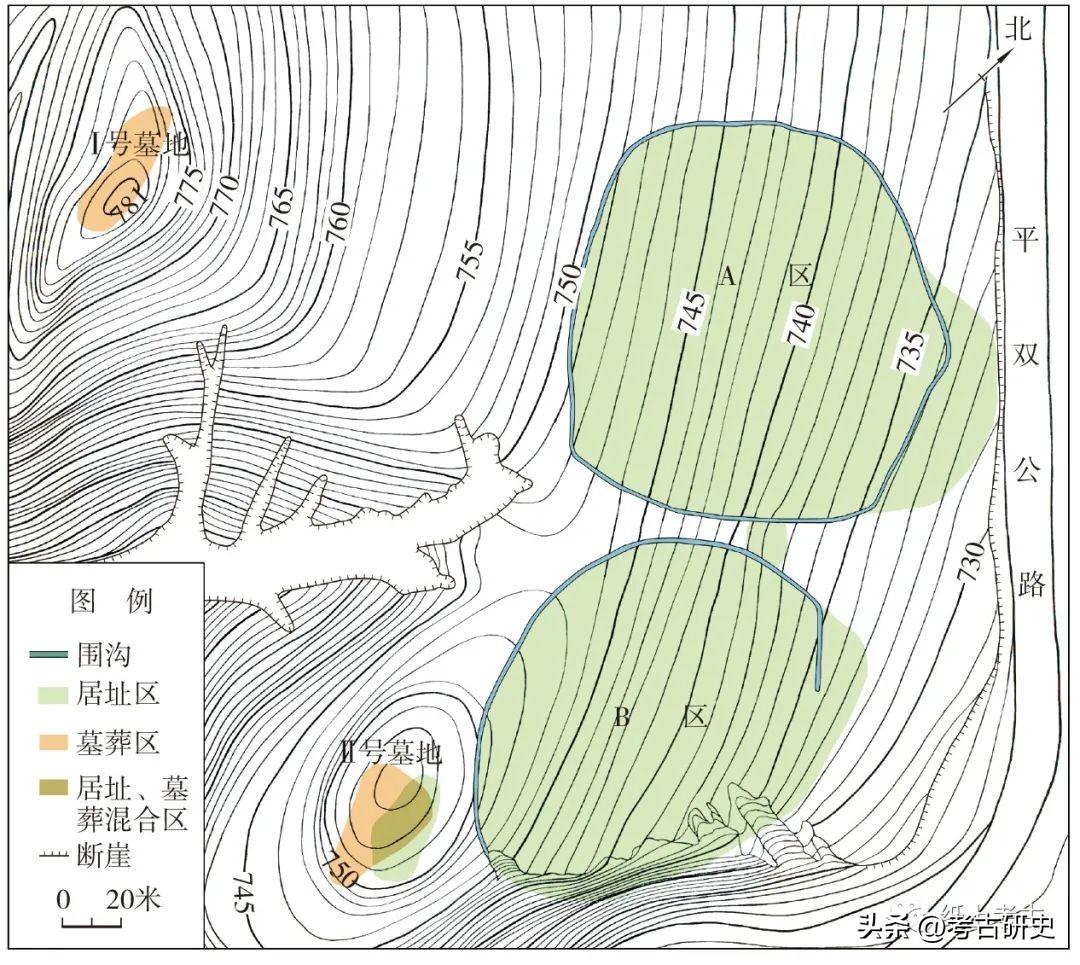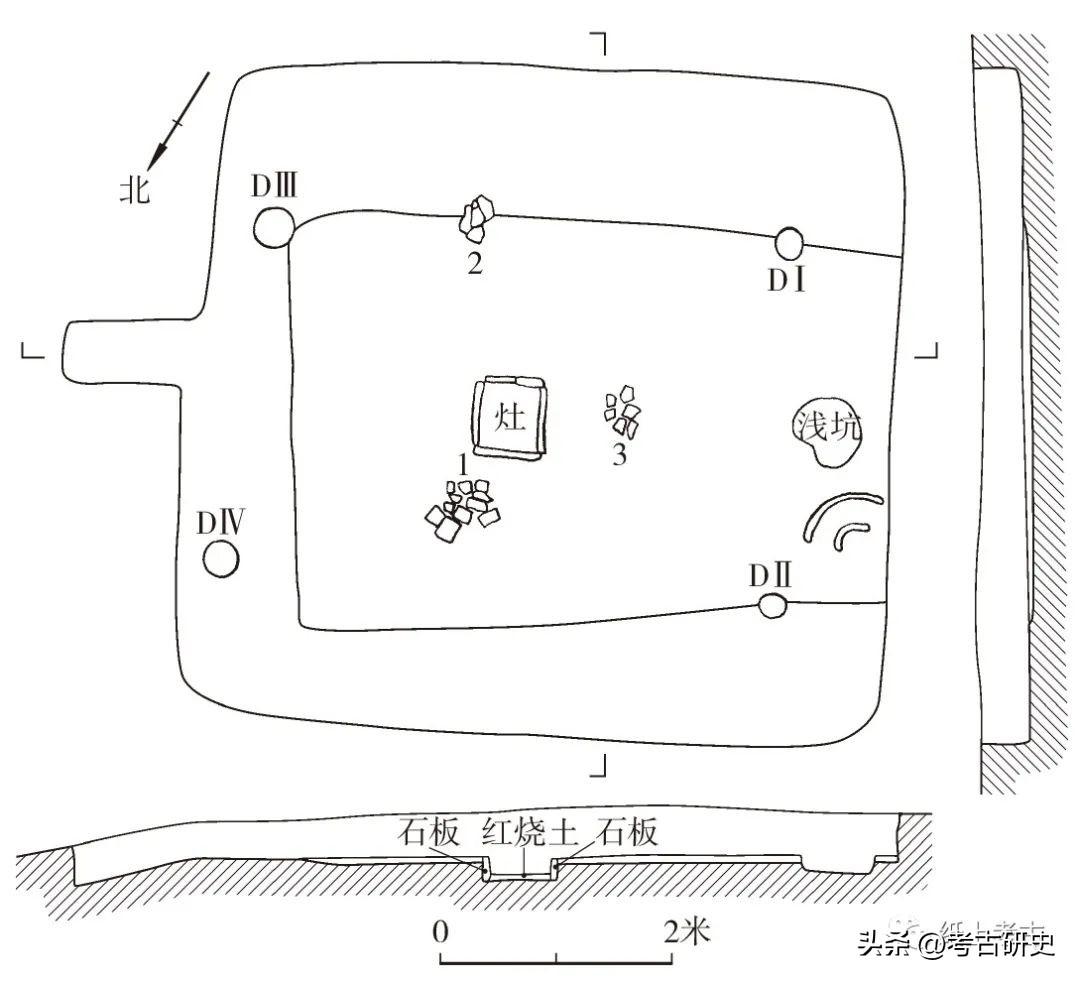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
一部能说明中国民族文化之原始的上古史,是现在一般人渴望好久的了。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却有若干不同的看法。现在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相当多;各有不同的见解、立场以及成绩。今天我要讲的,是把本人参加过或是自己熟悉的工作,加一点分析,向诸位先生求教。
这题目的意义是不难懂的;名词也没有不易解的地方。但我个人的看法,所谓“中国”,所谓“上古”,似乎都可以另加界说。前些时,我讨论一批考古资料的时候,深深地感觉到,中国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从某一立场来看,以长城为中国文化北方的界限,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都是汉朝以后的事。汉朝以前,我们中国人列祖列宗活动的范围,是否以长城为界限,是很有问题的。故“中国”这两个字,根据新的材料来说,应该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上古”呢?过去的史家,譬如司马迁,最早只讲到黄帝,但司马迁本人已经感觉黄帝这个人的存在不是没有疑问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上古的人物,大多都成了问题。从新的材料上看,他们也是有问题的,但那问题却在另一方面!到现在,“黄帝”事实上已经不能作为上古的界限;上古史可以推到黄帝(假如真有这个人的话!)以前。我们有一门新兴的科学:史前史。史前史的资料,广义的说,全是上古史的资料。究竟是上古史包括在史前史里,还是史前史包括在上古史里?这是另一个问题。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远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是比传统的历史长到几倍,或十几倍,甚至于几十倍。
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新的问题是中国民族的原始和中国文化的原始。因为是我们本身的问题,便觉得亲切,格外重要。西洋人看这问题,一般地说,与看其他的问题一样;但是当价值问题发生的时候,就有了偏见。譬如讲到年代,西洋人在选择两个可能的年代时,总要偏向较晚的一个。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照我个人的意见,是还没有解决的。董作宾先生把这年代定为公元前1111年,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事实上西洋人和董先生所根据的资料是一样的;两方的资料,由科学的标准而言,都缺乏决定性的性质。但是西洋人便一笔抹杀了较早的公元前1111年,采取了较晚的公元前1027年。再例如周口店的北京人,中国人和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把他的年代放在更新统中较早的时代,西洋人则把他放在更新统中较晚的时代,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的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安排。因为这种缘故,中国人对于此种资料应当加强研究,这不但是为了明了中国的古史,而且我们对于史学和科学本身负着责任。
我今天想说的是:第一,现在所有的新资料,对于中国民族的原始问题,已有不少的启示。第二,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
我先从一个客观的事实说起,再来讨论这两个问题。这一事实大家都知道,但还没经过综合的说明;就是:由考古学的立场看来,乌拉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东,和印度洋以东;平均地说,亦即东经九十度以东的亚洲大陆,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的区域之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说,最早的中心点在中国。安阳的甲骨文,在时代上,是这个区域里的任何地方所不能比的。西方的考古家常常忘记了这点,而我们今天讲中国上古史,必须记住这点!如此则若干不相干的学说便可以不必讨论。由这点出发,我们便得到了两个据点: (1)中国最早的文化,即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殷商文化,它的背景是一个广大的区域,包括东经九十度以东的一个大区域。如果进一步寻求殷商文化的来源,则所找到的范围不是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可以满足的,而必须向四面射到,包括了太平洋群岛,南北美洲,从北极到南极。这区域里一切考古学、民族学的资料,都是中国上古史的参考资料。如果把我们的眼光限制在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则我们所了解的程度,也就比例地限制下去了。(2)但这不是说,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孤立的世界。以此为中心,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也是同等的重要;这个关系,可以从黑海,经过中亚草原,新疆的准噶尔,蒙古的戈壁,一直找到满洲。
以上所说的是一个看法;对于资料的寻找,是不是可以这样做?绝对可以。近几十年出现的资料说明了,向这一方面之研究,一定会有所得。
现在讲到本题,先谈中国民族的原始。
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些平易而并不是困难的方法;只要有人肯做,去做,材料是不难得的。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人在做了,虽然被战争所耽误,但仍然有进步;与三四十年前的情形比,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看得清楚些。
中国早期的人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历史上并没有说明。西洋科学家来到中国以后,对这问题也有很大的兴趣,但至今外国人仍不敢太肯定地说。不过,他们找的和我们找的一切资料,都可以帮助这个问题的了解、认识。那是哪一类的资料呢?就是人体本身的资料。近几十年来,北方的史前考古有若干重要的发现;与文化的遗存一起,同时有若干早期人类的骨骸。最早的如周口店的北京人,有人说是五十万年以前;周口店的上洞里也找到了现代人的骨骸。周口店以外,旧石器也有发现,人骨却很少见,只在河套地方找到了一枚牙齿。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接近铜器时代的时候,人骨发现的较多,有北平地质调查所收集的数十副出土于甘肃、河南和奉天等地史前遗址里的华北人。更晚期的有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搜集到的一批极宝贵的资料,商人头骨一千多副,抗战的时候,很不幸地,散失了不少,但现在最完整的一些还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有的已经完全整理了,有的还没有完全整理。但是目前所得到的大致的结论,已经可以看出有关中国民族的若干问题出来。这是关于启发中国上古文明的民族的基本资料。先将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择其重要的,报告一下:第一,这些资料表现一件事实,即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代的人骨,都是绝对百分之百的蒙古种(Mongoloid)。从体质人类学上说,这点是不成问题的。第二,这一批人在蒙古种的范围内,并不完全一样。固然照现在生物学和一般情形而言,没有一种生物可说是完全一样的。凡生物都有个别的差异,因此方有进化。我在这儿所说的意义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代,华北一带的中国民族的体质也有变动。这个变动在骨骼的品质方面看得很清楚,现在从这些品质中举头形为例,加以说明。头形是讨论欧洲人种变迁最常用的研究资料,欧洲的人类越早头越长,越晚头越圆;在整个欧洲的每一区域的民族演变,常有这个趋势。也有一部分人类学家提出圆头民族是由长头民族演变而来的这种学说。我有一次根据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代的资料,比较若干不同的测量,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事实就是,至少在这一期间内,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比较,似乎也有时代越晚头形越圆的趋势。请看下面这几个不同时期的头形指数:
1.金石并用时代(Aeneolithic)二十五个头骨头形指数平均:七十四点九六(步达生所报告安特生氏在甘肃、河南、奉天等地金石并用时代遗址中采集的人骨) ,这是显然的长头。
2.混合的史前时期的(Pooled Prehistoric)四十个头骨头形指数平均:七十六点零零(步达生氏所报告;将上举材料与青铜时代早期材料混和而得,大致言之仍为史前)。
3.殷商时代侯家庄出土的一百三十五个头骨头形指数平均:七十六点九六。
4.现代华北人八十六个头骨头形指数平均:七十七点五六(现代华北人的材料,有四个不同的测量,这里用步达生的)。
以上数字的趋势是,指数一直向上升,头逐渐短下去。这种资料所表现的这一变动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某种的意义。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殷商时代,头形的变动较大;从殷商时代到现在,变动较小。这种事实也许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国的历史期间,在华北区域,人种上大体没有变迁,都是蒙古人种居住。但大范围里面的小范围有变动;这变动的意义,完全从体质人类学立场上说,现在言之尚早。如果资料加多,将来也许可以说明不少的历史事实。
如把平均数化为若干成分,只有殷商时代的材料可说,这批材料得自侯家庄的殉葬习惯。殷代殉葬规模之大,世界少见;侯家庄的大墓,除了所葬的主人之外,在墓道和墓四周的小坑中,还有排列整齐的殉葬人骨。侯家庄出土一百三十五个测量过的头骨,大多数来自殉葬坑。殉葬的人是中国人?是奴才?是俘虏?还是亲信?都有可能。因此指数所表现的,不能说代表仅仅商代的本身;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更详细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构成殷代皇室的若干人群。从他们头形指数的分配曲线看,与新石器时代的比,已有若干变动。这不是很大的基本变动,如白人消灭了红印度人或澳大利亚土人那样,而代表着小人群之间的混合、接触。
除了头形外,还有头高(basion-bregmaheight)可说。以上所举的资料一致表现,在华北的头骨,头高特别显著;不但高于东亚邻近地域的民族,且高于大多数欧洲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因此,步达生氏称这项特征为“东方的特征”(Oriental peculiarity)。这本是步氏研究新石器时代头骨的结论,侯家庄的资料更增加有力的证实;他所得的这项测量,与世界其他民族比较,更形显著。哈佛大学的孔恩(Coon)教授所著的《欧洲人种》(Races of Europe)—书里,列举了五十三族的人体测量资料;拿他们的头高这一项与侯家庄的比,只有十三组可以比得上;但构成这十三组的个别测量都很少。日本人类学家岛五郎氏也注意到步达生的结论,他说日本人同虾夷人也有这项特征。岛五郎认为日本人可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高头民族移往日本的。侯家庄的发现,不但证实了步达生所发现的东方特证;同时,也是殷商民族的体质与新石器时代的华北人比,没有基本差异的证据。不过这项特征的历史意义何如,此时还不能加以论断。关于这一点,我们尚需再进一步地收集资料。
在上述资料之外,我们还应该说到周口店上洞的资料。据魏敦瑞博士的意见,在上洞里没有现代中国人的老祖宗;保存完整的三副头骨,一个是爱斯基摩形的,一个是美拉尼西亚形的,还有一个是原始蒙古形( Hooton以为更像虾夷人)。这些都不是华北的现代土著,而出现于周口店。魏氏以为他们是过路的民族,被真正的中国人所消灭。但近二十年来,却并没有能发现与上洞头骨同时的真正中国人的祖先;不过我们也可将这问题从另一方面去看。
周口店上洞里的民族,有类似白人的,有类似黑人的,有类似北方的黄种人的,这表示远在新石器时代以前,旧石器时代最终之际,在华北平原活动的民族,完全与现代中国民族不相干。当然我们的老祖宗在这时不见得不存在。到了历史期间,铜器上有时雕刻的人像,看得出来的固然大部分是黄种人,但尚保留有若干其他民族的面孔。
综合而言,大概中国近代民族(我说的是自新石器时代的民族开始,就全部的人类历史说,这是近代的开始)的形成,曾经过长期的奋斗。大约二万年以前的前后,黄河流域一带,人种问题已是相当的复杂。那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大概只是若干成分中的一个;以后经过一番剧烈的战争,才能安住下来。阪泉涿鹿之役,如“特洛伊”( Troy)城的战争一样,是奠定中国文化与民族在华北立足的战争。他们的来处呢?我相信,中国的历史不能以长城为界限。内蒙古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的发现,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除了梁思永先生在昂昂溪和热河林西一带作了一点调査以外,这些发现大多数是外国人的工作。瑞典与中国合作的调査团,有一队曾从绥远沿北纬四十二度一直到新疆,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及出土物,一般地说,甚为简单;但有一发现是长城内所没有的:长城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为晚期的,而内蒙古一带的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其次,在关外一带,比新石器时代早一期的,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且分布得相当地广;所产的细石器(Microliths)亦为关内所不多见。最要紧的观察,据瑞典人在内蒙古工作的报告,原来新石器时代遗址集中的若干部分,现在都已经干旱;而沿沙漠的边缘,常见鸵鸟蛋壳与中石器时代人类用它所作的饰物,这是中石器时代最确凿的指标。由此所得的一种要紧的历史推论,为:在内蒙古一带,有一种气候演变的清楚迹象;由有水草、多人迹的沃野变成今日的沙漠。很可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中心就发展于内蒙古一带。在长城内外,河套附近亦有旧石器的发现。将来,在这一地带,也许可以找到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老祖宗。德日进在河套发现的一枚人牙,经过步达生鉴定,无疑是属于蒙古种的;这供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
现在再讲到中国文化的这方面。
数十年来,地下出土的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相当多,事实也相当复杂,若作一简单的介绍,不很容易。1933年前后,伦敦的《古物》杂志( Antiquity)登载了毕士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之新石器时代》;1940年,这杂志又登了他的一篇《远东文化之原始》。前面一篇文章主要的大意是说,如果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中国的显得非常贫乏,它的成分大多是外国已有的。譬如家禽家兽一方面,在欧洲有牛、山羊、绵羊、猪、狗,在中国只有猪和狗;家禽之中,鸡来自缅甸,麦、黍也都不是中国的东西。在后面一篇文章里说,如果把北极附近地带画出一个圆圈,可以看出里面有几种共同的文化,如穴居、复弓;中国的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青铜时代的车战、版筑,在西方早于中国一千多年便有了。他说他不愿作任何的解释;只把事实列举出来,便可以证明中国早期的文化,不是来自西方,就是来自北方,没有任何成分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发展的。他的文章本来是在美国Smithsonian Institution写印的,英国的杂志转载了。所以他的意见,不但代表美国人的说法,而且为欧洲人所同意。
我们有没有一个答案?这不是争辩,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中国文化之常常接受外国文化,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能接受才能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文化的内容全是外来的,则它在世界的文化史上,却也不能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我想作一个非正式的回答。他用家畜为例,是一个很不幸的例。我为什么说不幸呢?因为, (1)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兽骨,并没有经过详细的分析,作为现代科学标准;搜集一切兽骨加以鉴别的,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部分工作外,尚没有别人。毕士博立论的根据,是1933年以前安特生所作一般性的说明;这种根据甚为薄弱。(2)山东城子崖发掘出来的兽骨,都经过专门的鉴定,其中不但有牛、羊,而且有马。最足以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有牛的,是城子崖下层出土的占卜所用的牛肩胛骨。城子崖的黑陶文化时期,尚没有龟版占卜;所用的以牛、羊与鹿的肩胛骨为普通。安阳的兽骨,在毕士博文章发表的前后,送请德日进和杨钟健两位先生鉴定。鉴定的结果,证明不但有牛有羊,在安阳附近还有很多的水牛和新种的殷羊;这种水牛和殷羊,已有古生物标本证明,完全是在华北完成其豢伏的;它们在华北,都有未经豢伏的更新统时代的老祖宗发现。
关于麦子,可能他是对的。甲骨文里,“麦”字就是“来”字,证明麦子是外来的;但当时中国人是吃稻子还是吃小米的,是不容易解决的,仰韶时期已有稻子发现。中国的小米历史还不能说定。
现在我把他第二篇文章里的问题讨论一下。
在安阳出土物里,青铜占重要的地位。青铜文化的原始问题,由于缺乏新的资料,至今未能解决;就现有的资料推测,若干器物的确与西方有关,如矛、如空头斧;此外就难说了。中国大部分礼器在国外很少发现。最近讨论得很激烈的,是青铜刀子;它的作法,尤其兽头形的装饰,似乎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一带以及西方的相似,所以使得一些美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青铜刀子与北方的有关系,而在时代上,中国的比西伯利亚的晚。我相信这是他们把武王伐纣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很大的道理;把中国拉下来几十年,再把西伯利亚提早几十年,于是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了。
这一点是的确很难说的。安阳出土的东西里面有与西伯利亚相似的,是个事实;但何以不能说西伯利亚的是从中国去的呢?除了刀子以外,安阳还有文字,这是西伯利亚所绝对没有的;在中国的境内,有不少青铜原料的产地,这是我们早想从事研究而新近被日本人发表了的问题。放射性碳素标定时代方法(radiocarbon dating)发表了以后,欧洲古代遗物的年代被向下拖,美洲的和日本的反被提早;造成先史学的革命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年代早晚问题,也不是像西方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安阳除了青铜以外,还有车,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曾想把中国古代的车从汉代向上一步步复原出来,还没有完全作成。商代的车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车有若干部分是和西方相似的。安阳又有版筑;中国用版筑营造,不但发现在殷代,可能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山东黑陶文化。
以上所说资料的解释都是可以争辩的。我现在想举出若干不可争辩的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东西;从现代考古学的标准上说,为任何有偏见的科学家也不能不承认是中国所有的东西。第一件,我想举出的是骨卜。骨卜的习惯,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但在历史期间,即遍传于小亚细亚、欧洲与北非。
第二件是丝蚕。中国的丝蚕业,清清楚楚,传入西方的时间最早在汉初的先后。据考古学的发现,中国本土,公元前1000年的商代,不但在文字里看得见它的存在,而且还发现过丝制包裹的遗迹。在山西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査过,证明这是家蚕( (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第三件是殷代的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殷代的装饰艺术,铜器上的,以及骨器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作一个整个的观察,完全代表一个太平洋沿岸的背景。在艺术的观念、装饰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风上,代表很早的太平洋一个传统。它向东北经过阿拉斯加传入北美西北海岸,向南传入现代太平洋的诸群岛,这些都没有西方影响在内。
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骨卜代表当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蚕丝代表物质生活的一部分,而装饰艺术代表他们的艺术生活。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体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
由安阳发掘所看到的中国早期文化与民族的事实是很丰富的,大致可以以上所举各例为主体。有的成分可以肯定地说明它的性质,有些还是问题,只有等将来的发掘才能解决。它们无论是我们的老祖宗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是接受外国的,都能表现一种很大的活力。由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上古史,似乎和传统所说的,记录上所有的上古史不一样;但从这种眼光去找材料,也许更有把握。尤其,根据这些材料来建立中国上古史,不但对它的本身可以说明,更紧要地,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史的位置也可以说明得很清楚。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说得更妥当些。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没有这个联系,一切材料都只是时间和空间不能确定的材料。有了安阳出土的这一部分材料,我们对于以前华北出土的许多无从捉摸的材料,好像有了一条绳子可以把它们连串起来了。
[本文为1954年1月11日上午,在台北市徐州路台湾大学法学院大礼堂,“中研院”与北京大学同学会联合举办的蔡孑民先生八十七诞辰纪念会上的学术讲演词。]
- 0000
- 0001
- 0004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