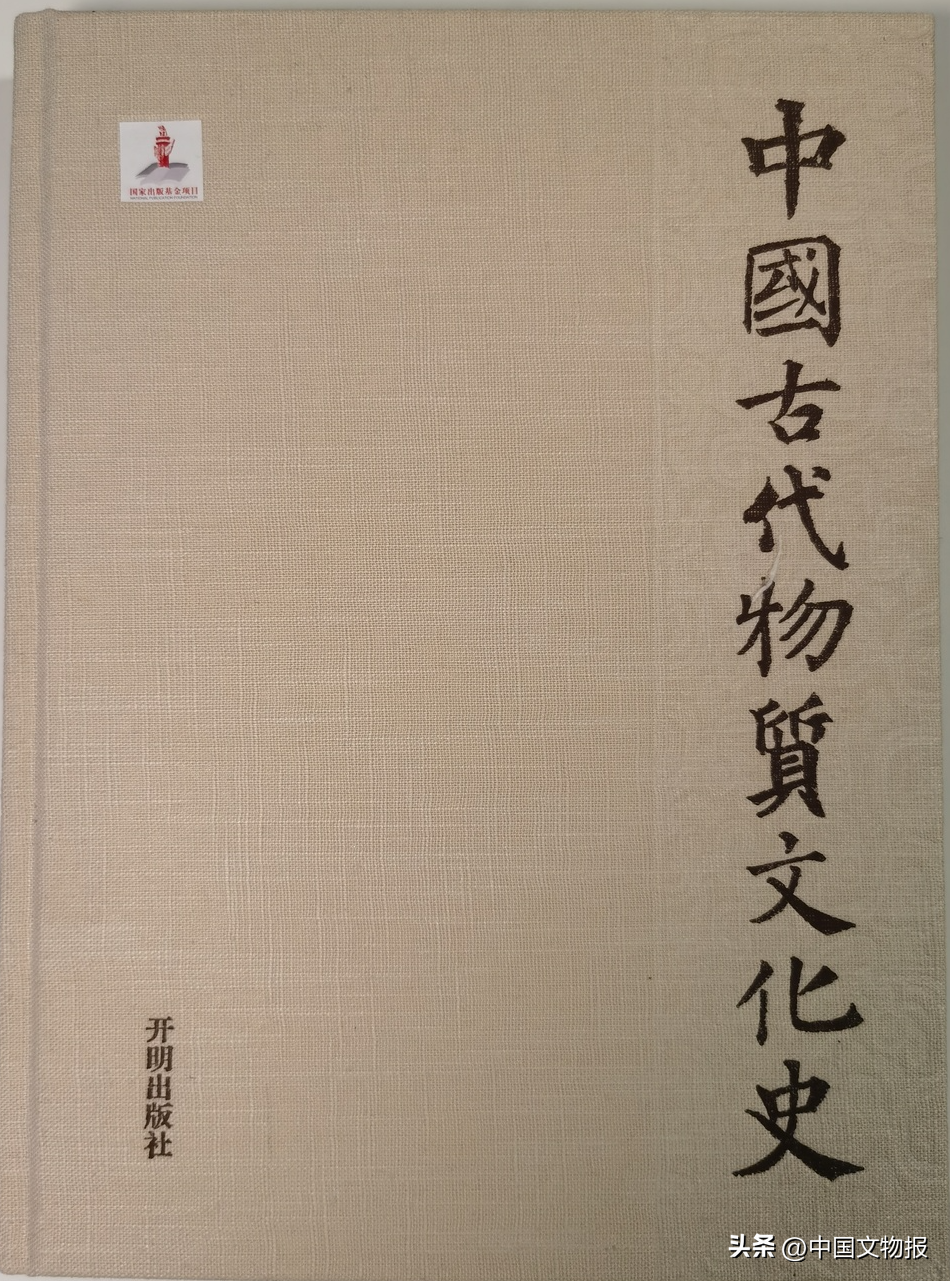陈志华: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的诞生
一幢古老建筑可以有多方面的价值。它可以有实用价值,能住人;可以有经济价值,卖得出一笔钱;可以有情感寄托价值,引起一些人的怀念之心。这些价值都不稳定。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它们都会渐渐降低甚至消失。但它有一种价值是不会降低和消失的,那就是历史认识价值。它们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主要是在艺术史和科学史的框架里体现。就是说,古老建筑都携带着历史信息,而这信息的价值只会随时代的变迁而越来越强。一幢古老建筑,当它携带的历史信息比较丰富、独特,在所有历史信息的系统中占有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地位时,它就可以被审定为文物建筑。
这就是说,决定一幢古建筑能不能成为文物建筑并确定它在文物建筑大系中地位的不是它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而主要是它的历史认识价值,也就是它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的价值。
作为史书,一座北京故宫,让你读懂封建大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座江南村落,让你读懂宗法制度下的农耕文明。它们的生动、具体、形象、细致,超过任何一本别的史书。这就是文物建筑的基本价值。可以说,文物建筑的性质,首先是文物,其次才是建筑。当代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原则和方法,都从这个认识演化引申出来。
这种对文物建筑保护来说根本性的认识首先成熟于欧洲。要这样来认识文物建筑的价值并不容易,它要求整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要求文物工作者有很高的眼光和丰富的知识,还要求有足够的时间来克服种种片面的或者文不对题的认识。可以肯定,早在石器时代,人类一学会造房子,同时就学会了修缮房子,而且不断地又造又修。由于宗教或政治原因,人们也很早就保护过若干有神圣意义或象征意义的建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曾委任拉斐尔管理古罗马的建筑遗产,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大画家,而是因为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拉斐尔忠于职守,给教皇写过长长的报告,激烈地大骂那些破坏古罗马建筑的行为,骂那些人是野蛮人。早在1630年,瑞典国王就敕令成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国有古物,1666年,又敕令保护所有的文物建筑。但欧洲的文物建筑界,并不认为那些事件和任务开启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历史,因为那些保护并没有致力于建立保护的学理,也没有探讨保护的科学方法。欧洲的文物建筑保护学界,可以说一致认为,文物建筑保护的学理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探讨,经过一百多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告成熟。这以前,不过是文物建筑保护的史前史。这个成熟的标志,就是提出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系统性学理并终于得到欧洲多数从业者和学术界的赞同。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系统性学理,是由《威尼斯宪章》总结了一百几十年的探讨而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的,时间在1964年。通过这个宪章的是一个国际组织ICOM,是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前身。宪章的第一小节开宗明义地写道:“世世代代人民的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饱含着过去年月的信息而遗存至今,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人们正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各种价值的一致性,并且把古代的重要建筑物当作共同的遗产。人们承认,为了子孙后代而保护它们是我们大家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完完全全地把它们的原真性传递给后代。”宪章的其余部分就是把这段话具体化。它的这个第一小节可认为是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界的共同纲领。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一个“欧洲文物建筑年”,进一步把这个纲领传布到全球。从此,《威尼斯宪章》基本上奠定了它的主导地位。
欧洲学者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探讨保护文物建筑的学理,是因为19世纪欧洲的文化全面发展。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着手建立,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中亚的考古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和非洲的居民社会的考察蓬勃展开,文学、艺术、哲学达到了灿烂的高峰,自然科学这时候也飞快进步。因此,欧洲学术界的眼光扩大了,对事物的认识深刻多了。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开始了正经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建立了机构,制定了法规,着手探讨文物建筑保护的学理。从此渐渐脱离“修缮古老房屋”的旧式工匠道路。
在这一探索中,欧洲曾产生过三个主要流派:英国派、法国派和意大利派。英国派裹在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中,过于偏爱中世纪的宗教建筑,而且迷恋“富有诗意的死亡”,陶醉在废墟前的伤感情怀中,甚至不赞成修缮古建筑。英国派有它的贡献,它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建筑遗产的关注,但它过于片面,影响不大。
法国派的实质就是建筑师派,代表人物是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授维奥莱·勒·杜克。他关注的是建筑学眼光中雄伟壮观的“杰出”的珍品,如主教堂、宫殿、贵族寨堡等等,它的保护方法也是建筑师式的,把古建筑维修得完完整整,“像它应该的那样”,甚至“比原来的更好”,风格更统一,功能更合理。当时巴黎的行政长官跟他心心相印,对巴黎城大拆大改,把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大量普通建筑拆光,让“有价值”的大型建筑物“亮出来”,形成城市的艺术焦点,或者给它们拆出“视线走廊”来。建筑师也好,行政长官也好,只在城市的“风貌”上下功夫,并不懂得从古老城区和古老建筑的历史意义着眼。这种建筑师的方法在欧洲流行了足足有一百年左右,抢救了大量濒临毁灭的古建筑物,可是由于思路和方法不对,也造成了严重破坏。后来专业学界带点偏激地说,他们对古城和文物建筑的破坏甚至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意大利派则重视古城和古建筑的历史文化意义。他们既不赞成英国派那种任凭古建筑走向“有永恒之美的自然死亡”的态度,主张要千方百计制止它们的“死亡”,同时也不赞成法国派那种主观地“改造”、“提高”古城区和古建筑,导致它们携带的历史信息混乱甚至消失的思路,他们主张尽可能多地保护住古城区和古建筑的原真性。意大利学派的奠基人是波依多,他提出,文物建筑是文明史和民俗史的重要因素,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既不能任它败坏,也不能随意修改,而要保护住它的“现状”,包括它存在过程中所有的改变,不可以“恢复原状”。1883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性工程师和建筑师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保护和修缮文物的指导思想》的决议,它在波依多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原则:第一,除非绝对必要,对文物建筑宁可只加固而不修缮,宁可只修缮而不修复;第二,为了加固或其他必要的原因,添加于文物建筑的东西必须使用与原用材料不同的材料,并使它明显区别于原有的。
意大利派和法国派的争斗十分激烈尖锐,起初法国派占绝对统治的地位,意大利派通过自己的实践,渐渐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并提出了完整的工作原则和方法,终于以《威尼斯宪章》对法国派赢得了胜利。文物建筑保护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不再等于“古建筑修缮”,它把保护文物建筑所携带的历史信息放到第一位。不过,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世界上便没有了法国派的影响,尤其在没有建立文物建筑保护专业而由一般建筑师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国家里。建筑师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素质自然地使他们倾向于法国派,他们和他们的行政长官还在坚持着早被欧洲人克服了的法国派老路。《威尼斯宪章》在1964年通过,那时人类已经到月球上逛了一趟回来了,所以说,它属于很“现代”、很“先进”的文化。一百几十年的探索过程说明,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的建立和推广,需要社会有很高的文明程度,需要国际的交流和合作。《威尼斯宪章》还有很重要的缺点,主要是它关注的“文物建筑”的面还很狭窄,使用了“monument”这个词,也就是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其次是它只提到对文物建筑环境的保护,还没有足够重视对历史地段的保护。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十九次全体大会制定了《内罗毕建议》,建议保护“历史的或传统的建筑群”,当然包括城市街区。街区里有“普通的”房屋,但当它们形成群体后,就成了一个有更大意义的系统的因素,也就不“普通”了。1987年,ICOMOS在华盛顿开会,通过了《华盛顿宪章》,建议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城市,不过,在这宪章诞生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已有了整个受保护的城市。1999年,ICOMOS又通过了关于保护乡土建筑的《佛罗伦萨宪章》,不但主张保护乡土建筑,而且指出乡土建筑的保护要以聚落的整体为单位。
于是,国际上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思路就越来越完善了。
来源:《北窗杂记三集》
- 0001
- 0000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