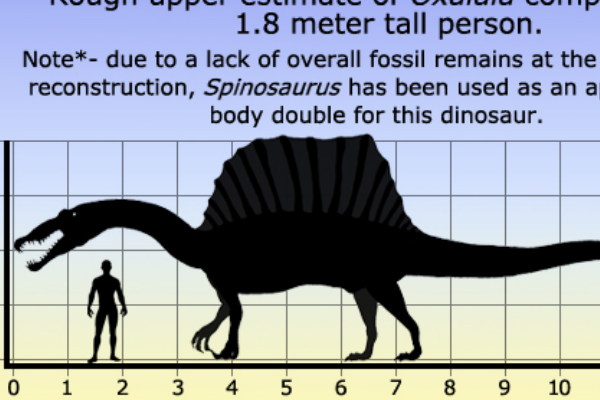李振宏:关于中国史学科的发展问题
最近的学科调整中,中国史学科被列为一级学科,一时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不少地方都在以各种形式讨论该学科的发展问题。其实,不管它是否列为一级学科,中国史研究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始终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大课题。学科的性质,学科的发展方向,学科的研究规范,学科的学术风气,学科的理论体系等等,都大有讨论的必要。而这些问题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学科的理论体系问题。
中国史所以为中国史,是有它的特殊规定性的,它之命名本身就说明了它有自身的学科体系,而它的学科体系,则是由它自身历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从理论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建构体系;历史的建构,是由历史本身的内容来决定的。而当我们认为中国史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独立学科的时候,也就是以承认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为前提的,而这个特殊性自然要求在学科建构从而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上得到体现。
确认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本身,表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史学取得了重大进步,表示人们已经冲破了带有明显斯大林印记的教条主义束缚;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讨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而只有充分肯定并认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才可能建设具有内在理论体系的中国史学科。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涉及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文明起源模式问题、上古三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古社会形态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特点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矛盾问题等等,都属于本问题的范围。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确立中国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不是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仅是以其中的某些问题为例,来谈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建设中国史学科的重要性,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一)中国文明起源模式问题
中国早期文明是如何展开的,我们的远古先民如何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这段看似遥远的历史,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铺垫丁后世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文明起源模式是研究中国历史特殊性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根据摩尔根与恩格斯的观点,认定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发展出来的最高组织形态,文明起源的模式定格为部落联盟一军事民主制一国家起源。欧洲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写道:“尧舜之时,我国正处于氏族制下的部落联盟时代。”“在部落联盟中,实行着一种民主制度。有酋长会议,管理民政;军事首长管理军事、司法和宗教等事。这便是所谓‘军事的民主制度’。”“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都是由酋长议事会经过全体酋长一致选举出来的。”“我国古代尧舜禅让的传说,实际就是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1]这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史学界的普遍认识。1980年代以后,史学界又引入了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认为部落联盟并不是人类走人文明时代的普遍形态,更具普遍性的文明演进模式是“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其核心是用“酋邦”代替“部落联盟”。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杜,1995年)一书详细介绍了酋邦理论,并以此解读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与这些引入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明起源的做法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出发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如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模式,[2]王震中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三阶段说”,即从农耕聚落发展至中心聚落再发展到都邑国家[3]等。中国学者关于文明起源模式的说法很多,朱乃诚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中有详细介绍。[4]本文无意也无力探讨这个问题,但想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学者的诸多中国文明起源说,多重视现象的描述,而缺乏像恩格斯部落联盟说或塞维斯酋邦说那样的理论抽象,难以将之上升到“模式”的高度,而理论化的模式研究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解读后世中国历史道路更具意义。比如,用部落联盟说还是用酋邦说解读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就直接影响对后世中国历史特殊性的认识。
酋邦对应于部落联盟阶段,是一个部落联合体,但却与部落联盟的面貌截然不同。王和的《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一书中,对酋邦与部落联盟之不同有过明确的总结。他说,就产生的过程而言,部落联盟具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部落联盟的产生完全是和平和自愿的,联盟形成的具体方式是举行一次会议而非通过征服;第二,联盟的产生起因于有关部落间的长期相互保护的关系;第三,参加联盟的部落是有亲属关系的部落,相互间有共同的血缘渊源。从人类政治权力形成的角度看,部落联盟在权力机制上也有三个特点:第一,部落联盟没有最高首脑,其最高权力属于集体的,而非属于任何个人的权力;第二,部落联盟会议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通过,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有权力是不可想象的;第三,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保持各自的独立,相互间地位平等。在部落联盟的发生和结构上的特征中,贯彻了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部落间的平等和个人性质的权力的微弱。与部落联盟不同,酋邦产生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征服,组成这种部落联合体的部落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其次,由于征服在酋邦自身的形成中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而征服的结果往往导致部落间的臣属关系,所以,各部落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第三,正因为酋邦是通过征服形成的,所以,与部落联盟相比,酋邦是具有明确的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在有些个案中,酋长的权力甚至已发展到接近绝对的程度,对于一般的部落成员乃至下属首领们都有生杀予夺之权。这与部落联盟模式对于个人权力的高度制约显然大相径庭。部落间的不平等与个人权力的强大,是酋邦模式的两条最基本的特征。[5]
酋邦模式与部落联盟模式截然不同。如果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真的类同于酋邦的话,那么,酋邦模式的研究,对于如何认识中国早期国家,以及如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文化个性,就具有理论上的重大意义。由于酋邦是具有明确的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所以当它们向国家转化后,在政治上便继承了个人统治这一遗产,并从中发展出集权主义的政治形式,形成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这样,中国所以较早形成君主专制政治模式的原因就得到了历史的说明。
中国文明起源是酋邦模式吗?弄清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对于中国历史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实在是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重大问题。
(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特点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点,是相对于我们习惯所讲的经济决定论而言的。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体系中,经济因素被看做是历史运动中最具根本性的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或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7]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景究竟如何,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是否能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症结?用这样的眼光去观察中国古代社会是否有益或可行?抑或说,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表达?这也是建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理论体系所需要考虑的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史学科独特的理论体系也是难以确立起来的。事实上,最近一些年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刘泽华较早关注此问题,并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特征归结为“王权主义”。他说:“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传统社会更为具体,更为恰当。”[8]
从10世纪90年代以来,像刘泽华这样从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支配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王家范就认为,中国历史中的一切内容,都是以政治为转移的,整个社会是一个“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类型。他说,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却总被遮蔽,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9]
在2010年5月《文史哲》编辑部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研讨会上,这种观点已相当普遍。有关会议报道中说:“与会专家对秦至清末的社会形态基本形成了如下重要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并着重把‘国家权力’和‘文化’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形态的研究和命名中,认为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10]
在《史学月刊》近期发表的一组笔谈中,不少学者在谈秦至清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时,都强调从政治权力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李若晖说:“我们一直认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马克思有鉴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大工业生产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社会而得出的结论。实则近代欧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冲决了传统社会的旧有外壳,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被经济大潮裹挟而前。但是在古代,在古代中国,当经济力量相对弱小时,能否基于近代欧洲的经验,给予经济这样高的地位?”[11]张金光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根本特点是“国家权力塑造社会”。他说:“传统的方法略去了国家权力这个维度一一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维度。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这一维度是维中之维,纲中之纲,国家权力决定一切,支配一切。在中国不是民间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权力塑造社会,国家权力、意志、体制支配、决定社会面貌。”[12]黄敏兰说,“国家权力决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这一认识,突破了以往的单纯经济决定论,抓住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13]李若晖指出,马克思重视经济的决定作用是从欧洲近代的历史特点出发的。如果这个看法有道理,那么,中国古代历史和欧洲的近代历史断然不同,在看待中国古代社会时套用经济决定论也就行不通。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特征,是不是政治权力决定一切,政治是不是看待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决定性维度,的确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虽然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肯定性看法,但远没有形成共识。如果这个观点得到确认,那么我们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角度、方法论思想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的确是建立中国史研究理论体系,进而建立独立的中国史学科体系所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三)中国古代社会矛盾的判断问题
按照传统的阶级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秦至清)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这是否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需要研究。就笔者所及,黄敏兰1995年的文章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她说:“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14]所谓“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官民矛盾的表述。
1996年迟汗青发文指出:“官民关系是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对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根本的规定和影响作用。”作者从政权性质、经济结构、政治运行、官僚资本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结论说:“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官民之间利益关系的对立性,而私有性质的政权又维护并强化了这种对立性。”[15]
1998年,又有两篇论证“官民对立”的文章发表。一篇是孟祥才接续黄敏兰文章对“官民对立”问题作深入的阐发和补充,他说:“中国古代留下的大量史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这个征课对象的主体应是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其中当然也包括不享有免赋免役特权的一般地主……这说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与农民阶级同封建国家的矛盾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居次要地位。”[16]孟祥才认为,即使存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它也是次要的矛盾,而“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篇文章,是顾震发表在《东方文化》上的论文《审视“定论”与等级分析——以关于封建时代农民、地主的理论为例》,明确提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税民”与国家的矛盾。税民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庶民地主。文章认为,“地主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之说,忽略了地主构成里包含庶民地主。[17]
到目前为止,将“官民对立”视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还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响应,要在一个基本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取得普遍的共识,就中国的情况说,需要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显然现在还很难做到。尽管如此,关于“官民对立”的认识,也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张金光的论文可为代表。他说:“官民二元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官民之间,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经济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以土地国有制、国家权力、政治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或叫权力型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比之民间社会的任何经济关系都具有无可与之伦比的稳定性、凝固性、恶劣性、暴力性。这一对生产关系,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比之民间的任何生产关系都具有无可伦比的广泛性和普遍意义,此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基因。三千年间,这一生产关系总是以不同形式重塑着中国社会历史,万变而不离其宗。舍此便不得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之本。”[18]
从学术史的角度说,王亚楠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提出“官民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阶级分野的观点,认为“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19]。但是,王亚楠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学理性分析;1990年代人们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向王亚楠问题的简单回归,而是在经历了阶级斗争理论形而上学猖獗之后,对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问题的新思考。坦率地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可以作为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视角(尽管这个地主阶级的概念极其含混)的,但却无法说明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无法对秦汉以后两千多年间以专制主义官僚制为其基本政治特色的社会进行政治解读,无法面对历史上几乎每日每时都在重演的“官逼民反”、“官民对立”的基本事实。因此,废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根本对立的基本矛盾说,从官民对立的角度去理解古代社会是有其本体论依据并因而有其合理性的。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理解古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建设中国史学科的理论体系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官民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说法,还需要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还有不少学理性问题需要探讨。譬如:官民对立是不是阶级对立?如果是,官僚阶级、庶民阶级的说法如何成立?界定官僚阶级或庶民阶级,在阶级概念研究上自然会突破马克思列宁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角度定义阶级的思想理路,而判定阶级的出发点或基本依据又是什么?如果不是,应该如何看待官民对立的矛盾性质?官民矛盾在社会属性上如何定性?在认定官民对立为基本社会矛盾的前提下,还存在不存在阶级矛盾?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通过艰难的研究去解决,而只有解决了这些理论难题,官民对立的基本矛盾说才能真正确立。看来,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又是建立中国史学科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以上举例性地提出了几个中国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史学科的建设或发展,首先要关注的就应该是这些宏观性的大问题,这是认识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无所依傍。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从而中国史学科在国际史学中的独特地位,自然也就确立起来了。
注释: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
[2]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3]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参见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8-275页。
[5]王和:《从邦国到帝国的先秦政治》,济南:泰山出版社,2003年,第10-l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7页。
[8]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9]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2页。
[10] 《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
[11]李若晖:《关于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方法论省思》,《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12]张金光:《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方法沦问题》,《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13]黄敏兰:《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14]黄敏兰:《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15]迟汗青:《传统社会官民对立及其调整》,《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
[16]孟祥才:《如何认识中国农战史研究中的“失实”问题》,《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17]转引自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
[18]张金光:《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19]王亚楠:《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载《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 0002
- 0000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