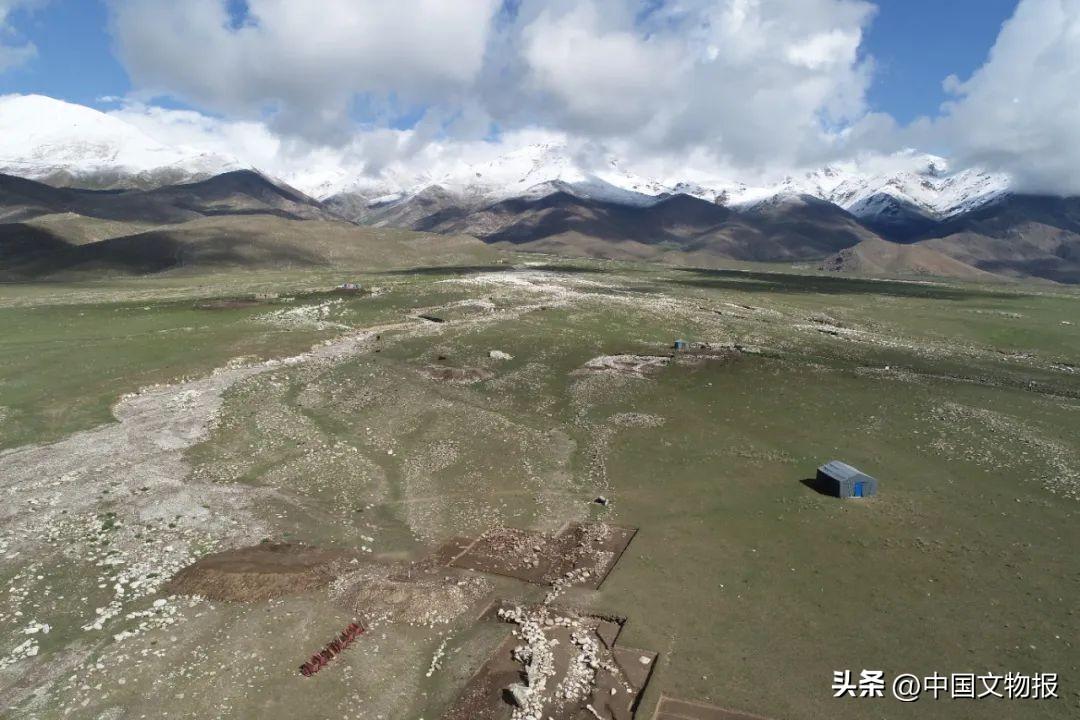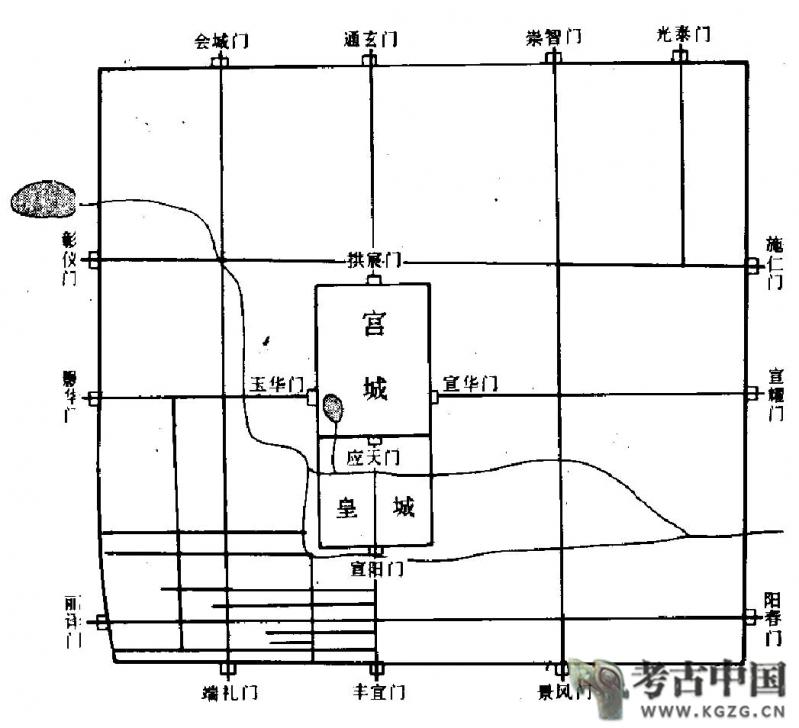严耕望: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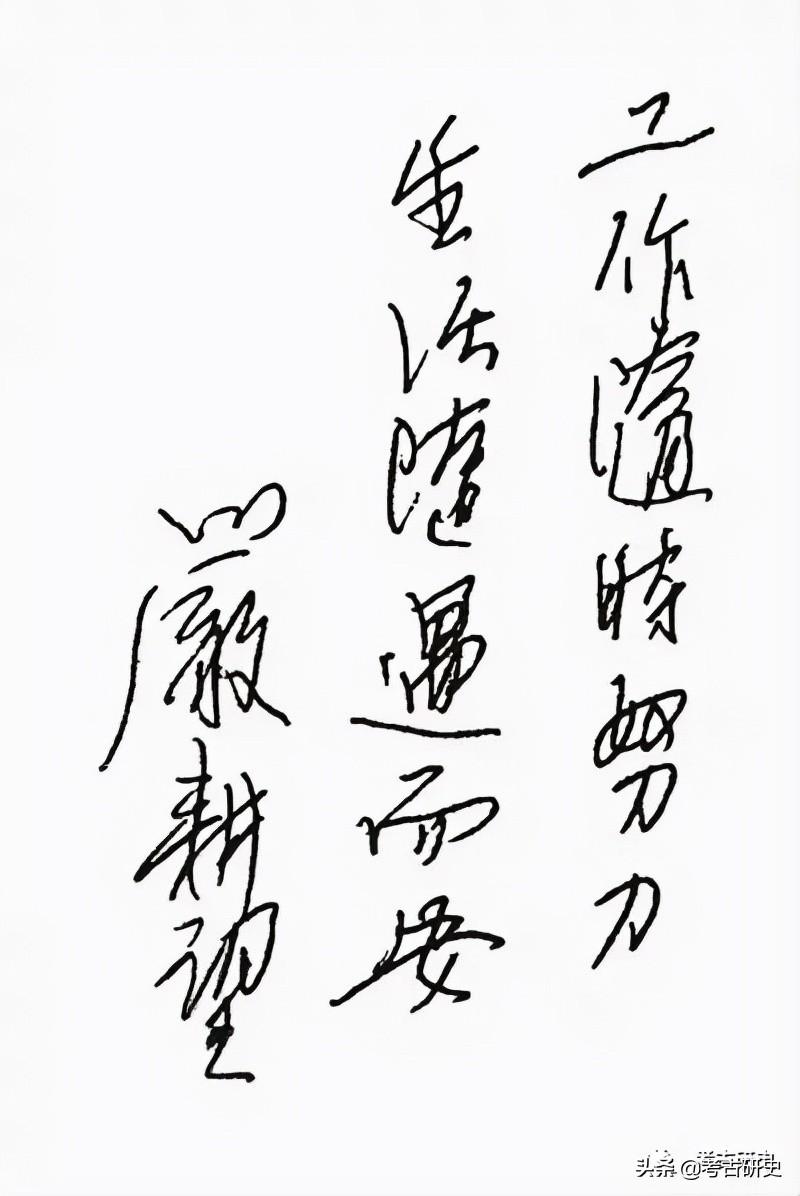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通常总是要有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两者相配合。客观环境所涉甚广,可说整个国家社会无不息息相关,而最直接影响个人成就的当是早期的教育与成年后的工作环境。主观条件,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天分、性情与身体健康等等。教育与工作环境多少有些要碰机会,天分更是先天生成,不可强求。但不懈的努力对于这些多少都可作若干主动的创造与控制。
就教育言,现代教育几乎是绝对开放的,自己的努力,虽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的取得如意的机会,但能获得的可能性总很大。谋取适合的工作环境,虽然比求学难得多,但我相信,只要自己具备应有的条件,至少可以自己操纵一半。好多人频遭顿折,总以为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诅咒社会;其实大半还是自己没有具备各种适当的条件(不只是自己的能力)!我相信这个社会虽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还是有相当公平的,真正能先充实自己,做人正常,大都不会被埋没!我个人今日有这一点成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的培养,无疑的是项重要因素,这当归功于当年傅孟真先生大公无私的录用一个毛遂自荐的陌生青年。这就是社会仍有公平的一个显例。不过如果不是自己善于利用这一优良环境,而懈怠自己的工作(史语所工作是无人督促的),或分心外务(外骛名利的机会仍相当多),相信像我这样才具平庸的人,恐怕很难有相当成就。李济之先生曾慨乎言之的说,“你是充分利用了史语所的环境!”我自信这话非常正确。中研院诚然是中国唯一的最好的治学环境,但就我来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十余年的体验,大学教职,若自己能摒除外务,淡薄名位,而集中心力,控制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台湾一般大学教职更较清闲(兼课太多自当别论),大可埋头做自己工作。何况教书也有好处,在讲授中往往发现新问题,涌现新见解,也可扩大注意范围,而且多少有点心理上的压力,这都是中研院环境中所不及的。因此可说正常的大学教职仍与中研院的环境相差不远。所以主要的关键仍在自己的人生修养与工作精神!没有这些主观条件,环境再好,也没有用!至于像钱宾四师在小学中学教书,每周授课时间,有时多到三十几小时,仍能做出超人的成就,那是特例,自不能希望人人都能做得到!
再说人的天分虽然是先天生成,但“勤能补拙”这句话多少还有些真实性,并非只是鼓励人的格言。就我的经验而言,假若人的天分以理解悟性与记忆力为重要的两方面,我认为记忆力很难凭努力而得到增进。努力虽不能真正增长记忆力,但不断努力的结果,仍可吸收到丰富知识。我实在鲁钝之至,尤其记忆力之坏,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在大学读书时代,碰到两位记忆力特强的同学,他们几乎真能过目不忘。其中一位,《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等能整部背诵,自己真很惭愧,深感人类记忆力何以相差如此之远!但我并不气馁,随时与书本接触,也就记得不少,只是不能整篇大段背诵耳。而那两位同学并不因为记忆力特强而有优良成绩,后来一个英年夭折,一个迄无所闻。所以归根究柢,仍是努力最为重要!但努力不是一时的,是要长久不懈的,有方向有计划的,这就牵涉方面很广;而且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治学的成就尤有绝大关系!
此下两篇,我想就做学问努力的途径、工作要诀与日常生活、人生修养等问题,提出一点意见。其中虽多属老生常谈,但默察今日社会情形,仍觉有提醒一般青年的必要。惟是涉及范围比较庞杂,亦只拉杂言之,分节标题不定恰当。
兹先谈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立志与计划
做学问要想有较高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这是努力途径的起点。
第一有抱负。也就是要有大志,这种志趣抱负,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谈起立志,记得我在小学初中读书时,老师常常灌输同学此种意识,自己也跟着看些讲立志的文章,憧憬着某些古人的丰功伟业,也想着自己将来要如何如何。现在青少年,似乎很少能接受到这类熏陶。当我的儿子晓田在高中读书时,我曾经向他提到要立志,他竟然毫无此种观念,似乎学校教育,从来未向他灌输此种意识,这也是我的疏忽。默察其他青年,恐怕也大多如此,只知读书谋生,争取社会地位,上焉者有些为社会服务的意念,但问他有什么远大抱负,恐怕很少人能具体作答。这样一个没有长远目标的青年,离开学校,投身社会,自然完全为社会环境所控制,没有一点自立的余地,机会好的,可在社会上做出一份事业,颇有成绩,在学校可充当一位教师,甚至颇有名的教授,但要在学术上有真正较高的成就,就不太可能;至少史学方面是如此。因为有些学术园地,尚可半凭天才,史学则十之八九要靠努力,所以国际上,历史上,有极有名的年轻科学家、文学家,但不见有一位很年轻的大史学家,因为史学必须要经过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始可能做得到,没有远大志气,如何能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
或者曰悬立个远大志向,但不一定能达得到,岂非徒然妄想,不切实际。其实不然。有了远大志向,始能有个目标,比如大海航船也要有个固定的目的地,才能有一定方向,中途纵然遇到种种海流的阻挠,终能曲曲折折,突破种种困难达到目的地。若无固定的目的地,那只有随波逐流,不知漂航到何处!至于说立志不一定能达得到,那诚然也是事实,但有有志而不成,无无志而有成,立志可能失败,亦可能成功,若无一定的志向则绝少成功的可能,这中间自然有很大差别。何妨有个远大抱负,一步步的去做,纵然落于空想,有如作梦;但能好好的作一番梦,也很不错,是幻是真,姑且不论!
第二能自信。这是跟着立志而来的必要的信念。一个人没有自信心,纵然立志,也等于未立志。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不能自信有天才,想凭借天才以达到立志的目标,那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第三有计划。有大志有信心还不够,因为只有大志有信心,仍是空洞的,必需采取实行的步骤。实行的步骤第一要有较长远可行的计划。古人为学,也许有些并无一定长远的计划而能成为大家,哲学家、文学家可能较多,史学方面也可能有,但相信比较少,一般大史学家仍是以有目标有计划的工作者为多。例如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写《通鉴》,马端临写《通考》。这些都是大规模的艰巨的工作,要说是事先没有计划,可谓绝不可能。温公作《通鉴》的过程最为人所知,那是绝对事前有周详计划的工作,决非随意工作的成果。近代史学更趋繁难,若只求小小成就,固无所谓,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例如陈寅恪先生,是近代一位伟大史学家,据俞大维先生说,陈先生有意写一部《中国通史》,但未成功(见《怀念陈寅恪先生》,刊史语所出版陈先生论文集),原因可能很多,但陈先生似乎始终没有个计划,当为最大原因之一。
就我个人而言,为学志趣经过几次变迁或修正,但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个目标与计划。自1946年以后,我为学重心转到中国历代人文地理方面,要想从地理观点讲中国历史,也妄想为中国历史建立一个立体的历史观。在这个大前提下,遂有三步计划。第一《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唐代人文地理》,最后《国史人文地理》。这三步计划,由小而大,由专而通,有其一贯性。中间尽管曾经自觉才力有限,时间不足,有放弃最后一项计划的想法,但后来仍是想尽力而为,不轻易放弃最后目标!有了这样三步骤的计划,三十余年来一直以此为中心,不懈的工作,也成为我生活中乃至生命中最主要的支柱,乐此不疲。今日看来,第一部书《唐代交通图考》已接近完成阶段,应无问题。第二部书《唐代人文地理》,虽然按照既定计划搜录材料已逾八九万条,略近完备,但仍撰述需时。第三部书《国史人文地理》只杂集史料为讲义,逾百万言,抄录复印资料、购置参考书刊亦不少,但撰布论文才三四篇,去完成阶段更为遥远,而年事已长,惟当知其不可而为之耳!我这些工作,虽不一定都能完成,但可完成逾半,殆无问题。然若事先无一定的目标,无坚强的信心,无长远的计划,相信一部都不能完成。即以《唐代交通图考》一书而论,单讲规模之大,或工作之仔细,都不足异;但兼而有之,恐怕并非易事,决不是随意工作者所能幸致!
(二)工作要诀
在学术工作进行中,有几点须要切实做到。胡适之先生曾提出“勤”“谨”“和”“缓”四字诀,似乎宋人也已说过。我想这是基本的工作要诀,还有“恒”“定”“毅”“勇”四字,也同样重要,当切实做到。就中“定”字诀留在下一篇再谈,兹先就其余七事略加说明。
(1)勤。这是学术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不能勤,根本谈不上做学问,做其他的事,恐怕也不会有多大成就。就治学言,要勤于阅读,勤于思考,勤于抄录,勤于写作,也相当勤于听受与讲授。下文就此各点稍加说明。
阅读要精读、粗读、检读、泛览兼具并行。精读是指基本的书、基本史料言,随读随作笔记,最好同时进行圈点,至少作选择性的圈点,将紧要处圈识出来,以便再检时易于发现。粗读是指一般非基本书籍史料而言。检读大抵就写作时临时检查而言。论著写作,基本功夫在平时阅读思考与抄录。而临时勤于检查也极重要,有时复查已录材料再次精读,有时因已录材料而联想其他材料,有时为问题的联系而临时翻查,总之有种种必要,须不惜时间,不怕麻烦的检查,纵只一两个字,也不能马虎,轻易混过!泛览则博识群书,略识大义,尤指自己论题专门工作以外的知识而言,这样可以扩大眼界,有时对于专门论题也有帮助。
思考与阅读事实上是同时进行的,阅读而有所识别,就已经用了思考,若不用思考识别,则阅读何用?此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然而有些聪明的作者,喜欢凭空思考,懒于阅读,这在史学绝对要不得,此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不过有时却不妨丢开书本,脱离材料,到山颠海滨去玩一玩,凌空的想一想,对于材料的联系,条理的抽绎,系统的建立,也许有很大帮助。不过基本的功夫还是在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上。
抄录。在古人治学,抄录或许不太重要,因为须要阅读的书籍少,特别着重记忆,四书五经四史之类多能上口成诵,所以不重抄录材料。但书籍不易得,动辄全本抄录,也能增加了解与记忆。现在书籍太多了,工作也更精细了,无论记忆力强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专凭记忆来做学问,必须在阅读的同时,选择与自己论题目标有关的内容动手抄录,记忆反居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内容简短或极重要,就须节录原文;内容太长或次要,就当摘录要点。在摘录的同时,就要考虑到此条的作用,以一两字识之,或在原文重要字句旁作一记号,以便将来应用时触目即知其用处。一俟材料书阅读完毕,即可运用这些抄录的材料分类排列,逐章逐节完成。在写作进行中只能临时翻查材料作为辅助联系之用,或就已录材料加以核对;若专靠临时翻查,或大部分材料靠临时翻查,则必挂一漏万,其文必不能精。这样抄录材料,近人谓之做卡片;但一般卡片,太讲究形式整齐,或又太厚,供大家公用,固极称便,但就个人而言,写录慢,运用时又欠灵活,倒不如我只用薄纸片,小纸条,来得省事方便,有时一片中不只一条材料,有时一片中只极简单提示几个字,更见省事,增加工作速度!此外应准备小纸簿,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想到什么,立即写录,以免悠忽即忘,可惜我于此点并未养成习惯!
再谈写作。一般而言,写作只为发表。有了学问要向外发表,让他人认识,就必须写作,所以写作似乎只为对外而言。然则假若有人非常恬静,有学问并不想发表为人知,那么他就可以只研究问题不必写作了!我想此大不然。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不写作为文,根本就未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未成熟。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搜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的写作出来,始能成为真知识真学问。因为平时找材料用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要到写作时,各种矛盾,各种缺隙,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一一解决,理出一条线索,把论断显豁出来,这条论断才站得住;否则只能算是个人看法而已,不足称为成熟的学问。所以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作成文,不能视为研究终结。至于发表不发表,就治学本身言,反不是写作的最大作用!
写作是学问成熟的最后阶段,然则写作就一定是成熟的吗?此又大不然,要看各人的学力与训练。不过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不能等到学问接近成熟时才写,而要在青年时代就训练写作。据我所了解,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所以我常常劝告青年同学,要及早训练写作技术,但不要抢着发表!不但要即青年时代开始训练写作,中间还得常常写作,搁笔太久,再从事写作,有时也会感到下笔凝滞。我是1964年来香港任教的,过去不曾正式教过书,而且一向不大说话,口才显得太差,突然要讲授几个课,就得先作充分准备;因此不得不暂时搁置论文写作,准备讲稿。到1966年夏天,才得暇再事论文写作。来港之前,我每年至少写一两篇论文,总出版量大约已近三百万字,写作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不意停了两年,就显得颇为生疏。第一篇论文是《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刊《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册),就写得非常吃力,浪费了很多稿纸。固然可说这次写的是关于历史地理问题,性质与以前偏重制度或人事者不同,但两年未写,技术稍疏,也不无关系。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写论文正也如此,不能中断!
最后谈听受与讲授。听受在青年学习时代固不待言,优良教师的课应该仔细的听,一则他们讲授的内容可能很多是他一家之言,别处听不到看不到。二则听来的印象较阅读得来的印象要深刻些。在离开学校以后,听受的机会少了,但有好的机会,也要能听受他人意见,不能以为自己学问成熟,而固拒自蔽!讲授当是学问相当成熟以后的事。职业性的讲授太多,固然浪费时间与精神,有害于治学,但不太多的讲授仍极需要,因为兴致淋漓的讲授中,思考常很敏锐,所以往往在讲坛徘徊讲说中发现新问题,涌出新看法,此即有利于研究。若能有好的学生,提出有意义的询问,那就更加有助于问题的研究了!所谓教学相长,并非虚言。
(2)恒。对于治学而言,“勤”是基本要诀,但若无“恒”以济之,虽勤亦不能有成。而且在我看来,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我常向青年朋友说,“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因为一时或短时期的勤,几乎人人可以做到,但一时短期的勤实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长时间永恒的勤,这就不易做到;若能做到,学问必有成就。就我个人言,朋友们都说能勤奋用功;其实我不算顶勤奋。我在学校读书时代,诚然相当用功,但我总按时就寝,绝少为考试温习功课而延迟上床时间,出校门以后更不会有。只有二十年前在哈佛访问时,看到他们中日文图书馆所藏日文图书丰富,且对我极有用,故临时再参加学生行列,去学日文,赶看日文书,因为时间有限,往往读到深夜两三点钟,这是我平生的唯一例外时期。现已老年,晚上更少读书。就是白天,工作也不紧张,大约每天真正工作平均不会超过五小时,当然不能算是极用功。不过我除了幼年时代有一段顽童生活之外,自十二三岁开始迄今五十年岁月,几乎没有一天离开书本,而且一心一意的做我的学术工作,不参与任何活动——包括学术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的参加,因为我觉得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不如自己多多的泛览各方面的书刊;至于行政性的工作,当然更不愿沾惹,就是教书也是最近十几年到香港以后的事。记得新亚书院接受雅礼协会补助的初期,宾四师来到台北,约牟润孙兄到港任教,并嘱其到杨梅乡间来约我。当时我的生活虽极困难,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但自觉学业基础尚未巩固,所以坚持不兼差,也绝不考虑到香港谋求生活的改善;畹兰不曾敦促我多赚些钱,补贴家用,也很难能!
这是我对学术工作之能永恒坚持处。所以要说我对于学术工作有一点小成就,主要是靠一个“恒”字诀;“勤”还在其次,因为只是相当勤,并不顶勤。所以我常向青年朋友说,出了校门置身社会,任职谋生,不可能人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做学问。但无论职业怎样忙,年轻人,精力旺盛,每天抽出两小时读书,绝不困难,只要减少无谓的交际应酬与消遣,便可做到。每天两小时虽不多,但十年累积就很可观。若能永恒的坚持十年以上,一定会有相当成就。若不能持恒努力,纵然得到好机会,出国留学,得博士,在大学谋得悠闲的教职,在名位上可能得意,但学术成就仍不可必,因为未必能每日认真读两小时的书!
(3)毅。上文说的“恒”,就已包括“毅”,没有坚强的毅力,如何能永恒的工作下去?再者,毅力在另一方面表现是耐性。学术工作,耐性极重要。因为工作有时不免繁重,或遭遇困难,非用无比的耐性加以克服不可。而有了坚强的毅力,无比的耐性,问题也一定会获得解决,很少白费功夫!我的经验,有时写论文,刚把材料摊开来时,往往显得头绪纷繁,甚至矛盾重重,不知从何下手,尝试着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但我不灰心,坚持着慢慢的想办法,最后总能理出一点头绪,找到一条线索,把那些纷繁矛盾的材料穿贯起来,写成一篇相当满意的论文。当然我有时也想到,这是我作茧自缚。有些人写论文,只搜录重要的材料,那些琐细似乎不关紧要的材料就不管,那末写起文章就较简单轻快。我搜录材料太细太详,有如收荒货一般,细大不捐,因此不免繁杂,要把这些繁杂的材料都组织起来,自然比较困难,这不是作茧自缚吗?不过经过整理穿插仔细的组织所写出来的论文,总要比较踏实坚强些!
(4)勇。勇敢也是治学的一个要诀。前文所说“立志”,就要有勇气;要大规模的做大问题,也要有勇气。要永恒的坚持下去,也是一种勇气。此外对于问题要勇于怀疑,勇于设想,勇于立论。胡先生说“大胆假设”,也就是此意。若是没有勇气,就不会能提出新意见,得出新结论,大规模的著作更谈不上!
(5)谨。谨慎是勇敢的反面,但相反而相成。只是勇于怀疑,勇于立论,若不能慎于判断,就很容易出错误,甚至闹笑话。胡先生一方面说“大胆假设”,同时又说“小心求证”,正是此意。他又屡次提到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也就是谨慎之意。
(6)和。在谨慎中已寓有温和。研究问题要从容客观,尤其与别人讨论问题,要态度温和,绝不可采取敌对立场,不但不要嫉视反对意见,无宁要尽量听取反对意见,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为自己的主观所蔽。有了反对意见,正好借此反省一下。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免有主观成分在内。也许自己由此一条线索去设想,而忽略了别的线索,所以想得偏了,有人从另一角度另一线索去设想,岂不很好,比勘一下,也许别人的反对意见正确,也许更显得自己的意见正确,也许相互磨砺,引出另一个更好的看法,也未可知。学术是天下公器,真理愈辩而愈明,没有面子问题在内。若是意气用事,文过饰非,纵可争狠于一时,终当暴白于异日,强辩饰非,只见其识见之隘陋,度量之不恢宏耳!
(7)缓。缓慢在学术工作中可有两层意思。其一,工作缓缓的做,不要抢快。其二,著作完成后,最好暂缓发表。
先谈第一点。学术工作,尤其文史学术工作是期永久价值,不是商业广告,不是政治宣传,不须要争取一时之效。既要做文史学术工作,就要认定能坐冷板凳,慢慢去做。因为任何问题,甚至很小问题,要搜集充分资料,都不是短时间中所能奏功,动辄要屡经寒暑,所以千万不能急功。慢工诚然不一定能出细货,但细货则必定出于慢工,草率抢工完成的东西,决不会好。现在研究院硕士班学生大多没有写过正式论文,要在两年修课期间写成论文,殊为不易。所以我常告诉他们,只是作为训练,不要期望为成熟之作。就是我要在两年之内做个陌生题目,也未必能做得好。事实上,我写论文,除了应酬之作,凡是正式论文,自起意到写成,大约至少要在四五年以上,目前陆续发表的论文更是在三十年前已开始准备了,可谓缓慢之至!就是这样,还有些写得不满意,甚至讲错了!所以决不能抢快。然则这样慢,岂非一生中做不了几篇东西?此又大不然。就以我而论,每篇论文准备的时间虽长,但作品总不算少,原因是第一篇所说作广面的全面的研究,同时注意很多问题。准备时间虽长,一旦准备充分,就有很多论题可写。例如我目前所写历史地理方面问题,三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准备,中间二十年毫无声气,几乎无人知道我在做这种工作。但一旦开始写作,就每年可出若干篇,至今至少还有二三十篇交通与其他有关人文地理的文章,可随时抽出来就写,如此总算起来,岂不很快!所以工作虽慢,成绩却不一定就少。换言之,从长远来看,工作缓慢,并不碍于进度之速!此之谓以慢为快。
次论第二点,论著最好暂缓发表。人人都有发表欲,论著完成,就想发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最好能克制一下,搁置一个时期再发表为佳。因为论著初成,必尚多问题未考虑周全,致有小漏洞,至少在撰写方面尚不够精炼,有可改进处。当然在初稿写撰时已仔细改了,但文章工整,绝无止境,搁置一个时期,必定发现有当改进处;若已发表,便懒得再改了。这在我已有不少经验。如《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因为屡次拖延未能出版,结果屡经改订,臻于满意。《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初稿撰成即为印刷费所迫立即付印,未能再加删改,至今为憾。又如《北魏尚书制度考》,即以长编付印,久欲改作而未果。若当时未迅即发表,相信必已改订,较合理想。复如《唐仆尚丞郎表》,发表以后发现部分金石材料已录而未用到,《文苑英华》亦因当时环境所限未加利用,若非当时政局不佳,不得不即早印行,则至少必已就此两点详加增订,更趋完美。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验,前文(第七篇)亦已分别提到过,不再详谈。近十余年来,写唐代交通问题,也不免为文债所迫,文成即印,出版后却发现不少当增补或当改订处。好在已发表者为散篇论文,等待全书出版时,仍可做一番改进功夫,期能弥补,达于较完美境界。即如这本小册,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著,但我也准备在初稿写成后搁置几个月才付印,以期能随时有所改进!
来源:《治史三书》
- 0001
- 0003
- 0000
- 0005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