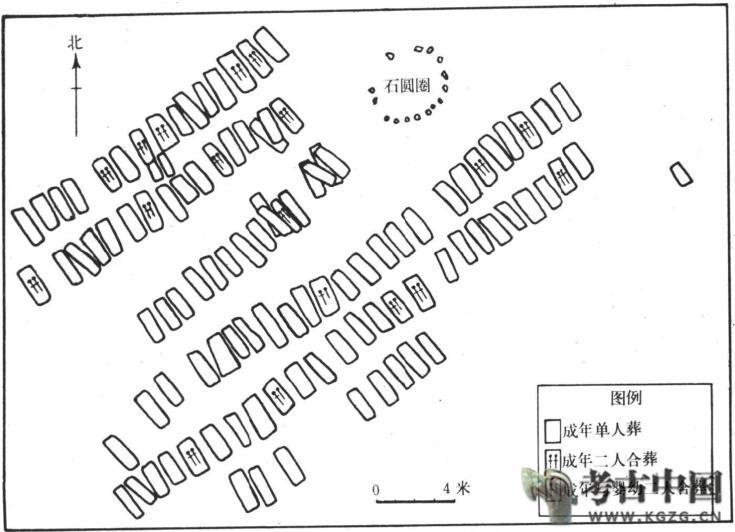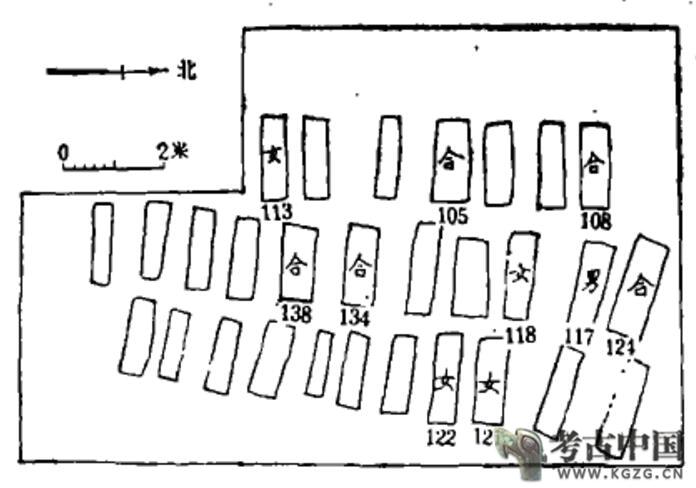李根蟠: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践
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相继衰落了。曾经登上古代文明巅峰的古希腊、古罗马,在公元5世纪蛮族入侵后,也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起源早、成就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造成世界文明史上这一奇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中华文明有一个发达的、稳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农业为它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在中华民族的农业开发史上有着众多的发明创造,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东亚和西欧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要以为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天灾人祸交织导致的剧烈社会动乱多次造成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使中国社会陷入困境。但这些困境没有一次是由于农业技术指导的失误引起的。相反,正是精耕细作的传统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正如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所指出的,具有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柢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1]
近代,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对象,中国传统农业也在近代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被西方远远拉开了差距,但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而地力经久不衰的事实,仍然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惊奇和关注。美国的农学家金氏(King)是最早试图探索其中奥秘的西方学者之一。1909年,他拖着老迈之躯花了五个月时间到中国和日本、朝鲜考察农业,其中在中国呆了四个多月。回国后撰写了《四千年的农民》[2]一书,高度评价东亚的传统农业。该书的副题是“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 Permanent Agriculture”可以翻译为“永久农业”,也可以译成持续农业。金氏堪称近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驱,而他所属意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正是中日韩的传统农业。[3]
的确,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它在近世虽然落伍了,但它包含着足资现代人借鉴的丰富历史经验,包含着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合理内核,是决不应忽视的。那么,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中,包含了哪些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实践呢?
一、“三才”观
我们现在提倡可持续发展。但可持续发展的根据是什么?何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按照现代的生态理念,地球生物圈是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人类是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并由人和自然协同完成的。因此,如果人类的经济活动能够遵循生态规律,保持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那么,它就有可能像大自然的再生产那样生生不息。我认为,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实可能性的客观根据。
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在于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了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摆正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关系。
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一词最初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易传》中,指作为宇宙构成三大要素的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三才”理论是在农业生产中孕育出来的,并形成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去[4]。农业上的“三才”理论的经典表述见于《吕氏春秋·审时》: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这是农业生产的对象。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天”和“地”在这里并非有意志的人格神,“天”指自然界气候,“地”指土壤、地形等,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因此,上述引文是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它反映了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生产的本质,与现代生态理念完全吻合。
在“三才”理论中,自然(“天”“地”)是能动的有机体。由于它是能动的,所以能够作为农业生物的生养者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由于它是可变的,所以能够提供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与“天”“地”并列的“人”,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自然过程的参与者和调控者。这就是所谓“天人相参”。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因任自然、无所作为的;“精耕细作”本身就要求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但这是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客观规律“这个词,但传统农业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正是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说:
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5]
在这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知”被置于首要的地位,人在农业生产中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之上的。这正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精髓所在。
总之,“三才”理论是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和灵魂,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
二、农时观
中国传统农业的农时观念非常强烈。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有观日测天图象文字的陶尊。《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先秦诸子政见多有不同,但异口同声主张“勿失农时”、“不违农时”。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交配和孕育,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为“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捕猎,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也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6]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对象是经过人工驯化的或野生的动植物,它们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首先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荣枯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种生产秩序正是适应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而形成的。
“顺时”“趋时”是中国传统农业农时观的核心。其深刻的意义在于保证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按照自然的节律正常进行,在此基础上加以利用。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7])“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俎代庖”,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8]。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9]。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地力观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如果地力不能获得补充能恢复,就会出现衰竭,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中国在战国时代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这基础上逐步发展了间套轮作和多熟种植。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有的西方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的办法是用地和养地相结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改土。
中国传统农业这种成功的实践升华为有关的农学理论,而这种理论又反过来引导农业实践走向新的成功。
中国传统土壤科学包含了两种很有特色而相互联系的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各有适宜生长的植物和动物。土脉论则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能变动的、与气候的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尤其是后者,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传统农业改土培肥的道路。
“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
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
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土脉论的深刻意义在于从理论上揭示了作为农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壤的能动性、可变性以及人工培肥土壤的可能性。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形成了南方以水田为中心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施肥改土的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宋陈旉在其《农书》中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它和“土脉论”是一脉相承的。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从而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物性观
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措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后者也包括两个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两者都是以日益深化的对各种农业生物的特性的正确认识和巧妙利用为基础的。农业生物各有不同的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_人们把这概括为“物宜”。“物宜”这一概念,战国时《韩非子》中已经出现,明清时,人们把“物宜”和“时宜”‘地宜’合称“三宜”。清杨屾《知本提纲》说:“物宜者,物性不齐,各随其情。”
中国传统农学的物性观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有两点:一是物性可变的观点,二是物性相关的观点。
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生物的性状不但可以代代相传(遗传性),也会发生变化(变异性)。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指出,在粟的诸多品种中,“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即是生物变异的表现。贾思勰还观察了作物引种到新环境后发生的各种变异,看出作物具有逐步适应新环境并形成新的特性的能力。如四川的花椒引种到山东,“此物性不耐寒,阳中之树,冬需草裹,不裹即死;其生小阴中者,少禀寒气,则不用裹,所谓习以性成”(《齐民要术·种椒第四十三》)。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即其可变性,不但是人类能够选育新品种的客观依据,而且是人类能够引进新物种的客观依据。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认识到在一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有相应的一定的植被和生物群落;而每种农业生物都有它所适宜的环境。“橘逾淮而北为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风土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若把这种关系固定化和绝对化,正确就会转化为错误。元代,政府在中原推广棉花和苎麻,有人以风土不宜为由加以反对。《农桑辑要》的作者专文予以驳斥。文中举出我国历史上引种成功的事例,说明在人的干预下,能够改变农业生物的习性,使之适应新的环境,从而突破原有的风土限制。这种有风土论而不唯风土论的意义,在于指出农业生物的特性是可变的,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可变的。
正是在这种物性可变论的指引下,中国古代人民不断培育新的品种和引进新的物种,从而不断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因素和提供新的前景。
不是孤立地、而是从相关性中去认识和把握物性,并采取相应的栽培管理措施,是中国传统农学和农业的一大特点。
这种“相关性”又分两种。一种是同一农业生物内部的相关性,即农业生物的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各个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之间的相互关联。人们可以抑此促彼,为我所用。《氾胜之书》记载用耙耧壅根的办法抑制小麦的冬前生长,以保证明春小麦返青后的正常生长(农谚“子欲富,黄金覆”,“麦无两旺”);《齐民要术》记载的“嫁枣法”[10]、“枣树振狂花法”[11];瓜类的摘心掐蔓;桑果的修剪整形;畜禽的阉割、强制换羽等——均其例。
另一种是不同农业生物之间的相关性,即农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自然界的不同生物,有“相生”(共生互养)的,有“相克”(互抑)的,人们也可以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从总体上提高农业生物的生产能力。生物“相生”关系的利用,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又指出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动物生产中共生互养,则有草鱼和鲢鱼等鱼类的混养[12],等等。生物“相克”关系的利用,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稻田养鸭吃蝗蝻、蟛蜞;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桔害虫;等等。
在利用农业生物的相关性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农业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和合理的农业生产秩序。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南宋陈旉对此有所总结,他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农书·六种之宜篇》)
这里讲的就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所谓“相资以利用”,则是上面所说的把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巧妙利用到农业生产中来。这种认识和实践完全符合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是建立在生态规律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成为农业生产“绵绵相继”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证。
“相资以利用”之妙不但可分别应用于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畜养中,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张履祥《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五、循环观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
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
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
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
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六、节用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13],而“强本节用”成为当时一个响亮的口号。《荀子·天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管子》也谈到“强本节用”。《墨子》一方面强调农夫“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另一方面又提倡“节用”,书中有专论“节用”的上中下三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此评论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14]“强本”就是努力生产,“节用”就是节制消费,两者密切相连,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经济腾飞的双翼。
中国古代农学家也十分重视节用,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节用”最直接的目的之一是积储备荒[15]。也有些思想家从自然对农业的制约、生产难以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需求这样一个视角进行分析。例如: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16]
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17]。
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18]
这里已经接触到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之一——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由于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人类所利用的资源的供给是有限度的,因而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满足人们消费的无限需求。缓解这一矛盾的正确途径之一是节制消费。当然,上引这些思想家主要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19]
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荀子把道理说得很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20]。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
将近一百年前的金氏(King)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持续农业”,是很有眼光的。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深受金氏《四千年的农民》的影响,他指出:
他(指金氏)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份。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将继续养育许多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21]
是的,中国传统农业之是一种“持续农业”,它之所以成为“持续农业”正是由于它符合生态规律,而中国人也因此成为大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一环。作为社会人类学家的费孝通,他的认识与农史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中国传统农学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农学,它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 这是2006年秋我在韩国举行的东亚农史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未在报刊上刊载,但网上已经流传。
注释:
[1]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农业出版社,1980年。
[2] F.H.King,D.SC.,Madison,wis.,Mrs.F.H.King,Farmers F0n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3] 参阅陈仁端《关于太湖流域的水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若干思考》,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4] 参阅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5] 马一龙《农说》
[6] 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7] 《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8] 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9] “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10] “嫁枣法”是用斧背疏疏落落地敲击树干,使树干的韧皮部局部受伤,阻止部分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向下输送,使更多的有机物留在上部供应枝条结果,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林擒、李树也用类似方法。现代果树生产中的环剥法,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11] 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果树的大小年现象,并且采取人工的措施予以调节,“振狂花法”即其一种,相当于后世的疏花疏果。
[12] 据明王士性说,这些鱼类混养的好处是:“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13] 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等等。
[14] 《史记·太史公自序》
[15] 例如《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元年二月甲戌“给流民公田诏”曰:“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 贾思勰说:“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凡人之性,好懒惰矣,率之又不笃;加以政令失所,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赀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齐民要术·序》)把“用之无节”视为酿成灾荒和经济危机的首要原因。
[16] 《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17]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18] 明韩文《裁冗食节冗费奏》。
[19] 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生之有道,用之有节”。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0] 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21]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1985),载《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第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版。
- 0001
- 0000
- 0002
- 0000
- 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