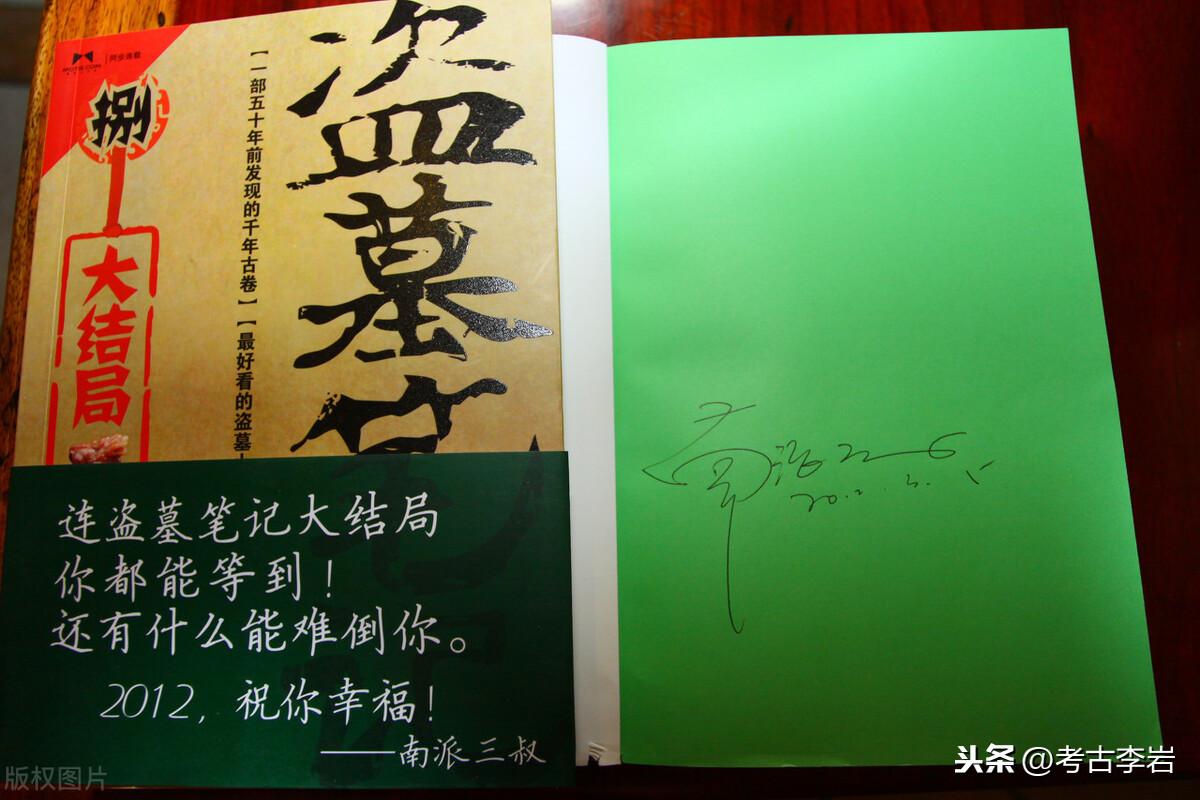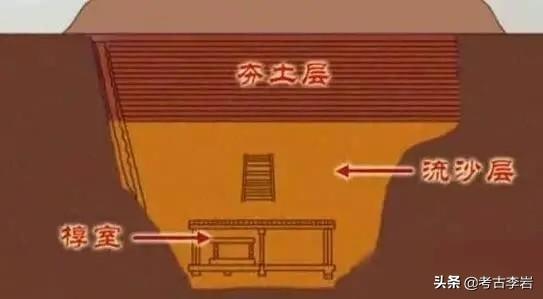郭静云:中国上古文明的历史脉络

笔者经过多年搜集、对照考古、文献以及其它学科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商文明”的历史得出新的理解。此研究成果较详细见于拙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因为对精神文化的理解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在着重于讨论古人信仰之前,下面拟简略描述笔者对于上古史基本框架的认识。
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到早期青铜技术的差异。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上、中、下游均成为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孕育,相当于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最丰富的文明。相比较而言,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按照考古所得,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的发祥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从未断绝:从彭头山文化(大约距今10400─7800年,含早期的宋家岗、杉龙岗、华垱和晚期的八十垱等遗址)到皂市下层文化(大约距今8200─7000年)、汤家岗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大溪文化(大约距今6300─5300 年)、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55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4800─3800年,含后石家河文化)[1],最后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3900─3300年)。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相似,年代亦相同。
先楚文明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这一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黃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考古揭示,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脉,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文明化的发祥地。并且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的颛顼、尧舜、三苗以及禹夏统治的历史阶段,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国──楚──的历史中的颛顼、尧舜时代和夏王朝。顾颉刚先生曾经透过对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地通读和考证,证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传说中的历史英雄[2];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时代位于汉水北岸偏西边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势力大,或许恰好是尧舜、三苗及夏王室统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经作过夏王国的都城。
文献留下的记载表达,三苗应该是尧舜时代之后、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补正此传说。依笔者的考证,所谓三苗,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3],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愈来愈多地见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鄂西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石家河文化晚期(约距今4300—4000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谭家岭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以笔者浅见这就是代表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长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属性在上编第七章进一步讨论)。《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4]

仔细阅读文献所载,从其神话性的叙述可以钩沉一些讯息。第一,三苗之治可能不稳定,出现异常气候,各种势力互斗频繁。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结束,这一“天命”之事经过口传而入文献,《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5],描述大约两千年才能发生一次的超级紧密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的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阳历2月24日[6];这很难是偶然而巧合,这一天文指标确实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时代。第三,文献在神祕的描绘之间或许暗示一些当时气候与社会的激烈波动:“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气变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见一层薄冰(“夏冰”的意思应该不是夏天有冰,而是指在名为夏水的汉江下游河面有冰冻的现象);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老百姓也因此动乱。第四,据此传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阳加持而保祐,说明这都属于楚大文明的历史;夏禹显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没有面对大洪水经验的北方人,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人显然没有能力组织适当的治水工程而阻滞洪水。
也就是说,在约公元前2300年开始的洪水时代中,曾经有来自湘鄂西部山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脉)的三苗族团掌握了江汉平原地区的政权,而在约公元前1950—1800年间,汉水下游继而为夏王国都城所在之地。可是文献另也记载,大禹之后夏王国并不稳定,考古也显明,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文明体系中,曾经发生过国家结构的屡次演变,古代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天门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最终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其可能就是以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为代表。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资料,或许正是夏朝兄弟乱及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进一步对照资料及循着历史思考,使笔者了解:考古与文献中商史资料存在众多矛盾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资料隐藏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与王朝合并的情况,是后世都城在安阳殷墟的统治者的王朝(屈原将之称为“殷宗”),打败前世中央靠近汉口的“汤商”之后,有意地强调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传承的正统性。
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汤商另可谓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录的楚这个大文明中的“汤商”朝代阶段。盘龙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占领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这是一个源自长江中游自身文化发展而来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殷商文化的脉络里。[7]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盖整个江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二里岗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于南方农作区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强攻的前线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洛地区),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
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
直至距今3400年以来,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从地理关系来说,汤商文明的范围以江河中原为核心,是庞大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文明。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东北角落上,但经过多次战争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汤商文化为基础的。尤其是汤商文明(包括郑州、偃师一带被鉴定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礼器所表达的信仰,明显被殷商传承,成为殷周系统的宗教观念之基础。
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此乃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殷商上层贵族的精神文化颇为系统,所以应该定义为上古帝国宗教体系。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而形成庞大体系;周代继续传承,西周后半叶才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不过总体而言,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观察与分析,本书将着重于透过礼器造型、甲骨金文以及后期神话的纪录,通过现有出土文物资料与后期神话的交叉比对,重新解读两商信仰的要点。
[1]笔者参考及基本采用郭伟民先生的断代,不过同时照自己的分析略有修正,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页16—37。另参陈铁梅、R.E.M.Hedges,《彭头山等遗址陶片和我国最早水稻遗存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文物》,1994年第3期,页88—94。不同遗址的年代比较,显示文化之间经常有较长的过渡时段,部分遗址已有很多新文化的因素,但另一部份遗址的遗物继续保留早期文化的面貌,因此早晚的文化间,自然有两种文化互相重叠的时段。此外笔者认为,油子岭文化特征及其在大溪与屈家岭年代框架之间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所以临时不划出。
[2]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册•中编•四二《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三)《禹的来源在何处》,页118—127。
[3]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108。
[4]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68-69;战国宋‧墨翟著、清‧孙诒让闲诂、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146。
[5]宋‧李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一册,第一部,卷七,页34。
[6]郭静云,《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台北:万卷楼图书,2010年,页287-291。
[7]在此地除盘龙城之外,周围亦有甚多遗址,包括城址,但发掘不足,所以目前还不能更准确地理解楚商政权中央的位置,所以暂定已有发掘基础的盘龙城遗址。
说明: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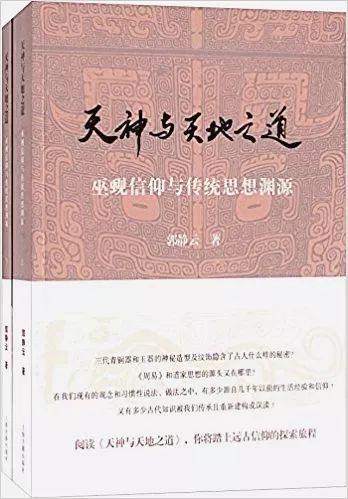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