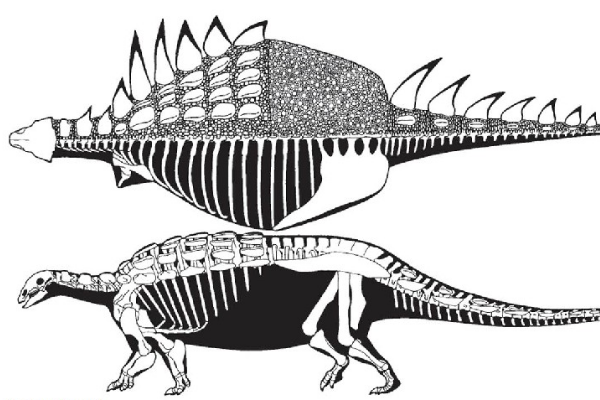葛剑雄:中国传统智慧与生态观
公元初的西汉人口不超过7000万,到1851年在清朝统治的范围内人口总数已突破4.3亿,增长了6倍。虽然清朝疆域的范围远远大于汉朝的疆域,但如以可耕地面积比较,增加量有限,因此如以农业产量为指标,两者还是有可比性的。在农业生产依然停留在人力作业的条件下,这4.3亿中国人完全是依靠本国生产的粮食和物资养活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自西汉到清,中国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西汉时建立郡县的范围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西域都护府管辖的范围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东起朝鲜半岛中部,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至阴山山脉,南抵今越南中南部。清朝的极盛疆域面积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东起库页岛,西达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北至外兴安岭,南抵南海诸岛。人类历史上尽管还有过幅员更广的政权,但都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也没有实行像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度。直到19世纪中叶,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疆域辽阔的国家完全是依靠人力、畜力和非机械交通工具维持着行政管理、人员和物资的流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迹。
这些奇迹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体现了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农历与二十四节气
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农业区集中在国土的东部(不包括东北)和中部,受东亚季风控制,气候多变。根据历史记录,水旱灾害几乎每年发生,或者同时发生。异常气候和自然灾害也经常出现,如虫灾特别是蝗灾、风灾、霜冻、雪灾、严寒、酷暑、沙尘暴、地震、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传染病(瘟疫)等。在传世的正史、地方志、地方史、家谱、档案、个人史料中有大量记载,覆盖每一年。
历代中原王朝疆域辽阔,其农业区内部的地形、地貌和景观多样,不同地区间的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即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难以用统一的模式管理和控制农业生产。
所幸中国传统农历的发明、完善和普及使农时的掌握变得简单易行,即使在边远偏僻地区的单独农户也能通过二十四节气做到“不失农时”。
中国的农历可以追溯到存在于公元前21—公元前16世纪的夏朝,因而又称为夏历。很多人误以为农历属阴历,实际是一种阴阳混合历。即以月球环绕地球一圈为一月(朔望月),而一年(回归年)的长度取决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位置。由于根据月球环绕地球一圈确定的一个月是29天或30天,以12个月为一年的平均长度是354天或355天,比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要短。为了使阴历年与阳历年取得平衡,农历采用了加闰月的办法,即“十九年七闰”——每19年间有7年每年插入一个闰月。但由此带来了新的矛盾,闰年有13个月,一年长达383天或384天。
即使是一个住在偏远地区的普通农民,要观察和了解月份的变化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月中总有见得到月亮的机会,可以做大致的判断。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了解阳历年的变化就很不容易,因为要观测和计算出置闰月、闰年的规则就非天文学家和专家学者莫属。
农时一般是与地球在绕太阳轨道上所处的位置有关,但即使每个农户都能拥有一本历本,也很难让他们根据日历来掌握农时或确定农业生产中的特殊时令。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历朝历代无不致力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包括如何使农民不误农时,于是节气应运而生。所谓节气,就是在一年中确定的二十四个特定的日期,以此划分阳历年。
节气是以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形成了仲(中)春、仲(中)夏、仲(中)秋和仲(中)冬四个日子的名称,日历中有了固定位置。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到秦朝(前221年—前207年)和西汉(前206年—8年)前期,形成了二十四个节气的名称,确定了它们在天文历法中的位置。公元前103年(西汉太初元年)邓平、落下闳等制定的《太初历》中已采用二十四节气,此后的历法一直沿用。
由于节气的日期都取决于它在地球太阳轨道上的位置,所以在公历(格里高利历)上的日期也是基本固定的,在上半年一般是每月的6日或21日,在下半年一般在每月的8日或23日,相差不超过一两天。
二十四个节气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从这些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显示了某种气候、景观、概念、特征,能够方便地被用作农业生产的节点、日程、指导、警示,都与特定的农事相联系,如耕耘、播种、除草、间苗、整枝、施肥、除虫、收获等。甚至直接与某种作物的各种作业相联系,如稻、麦、豆、小米、高粱、蚕、油菜、茶、蔬菜、水果、花卉等。尽管节气的确定主要是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与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但只要根据本地的实践和经验在时间上略做调整,就能适应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实际上,节气在中国古代获得极其广泛的重视和运用。与节气相关或从节气产生的民谣、谚语、民歌、口诀、诗歌、绘画等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诀窍和日常生活的经验。
节气制度的确立为这个农业大国的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指导提供了便利,产生了很大的效益。在新年来到前,朝廷会在全国范围内颁发标明下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历书。从君主至基层官员,“劝农”的主要手段就是提醒或督促农民不误农时——按节气安排好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直到20世纪初,根据节气安排农活还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基本准则。在绝大多数基层政府没有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和农业专家、农民基本都是文盲、个体小农家庭与外界的来往极少的条件下,节气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日常生活所做的贡献是无可取代的。
犹太人创造希伯来历法的时间与中国的夏历大致相同,也是一种阴阳合历,平衡朔望月与回归年的办法居然也是“十九年七闰”,在两千多年前形成了类似节气的特殊日期的名称。所不同的是犹太人没有能像中国人那样拥有一片数百万至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延续两千年的时间内使用他们的历法和“节气”,结果自然无法同日而语。
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中国的城市历史正在不断改写和上溯,发现古代城市遗址的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早期历史文献中一些有关城市的记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由于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国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有“万国”之说。直到春秋初(公元前8世纪后期),有记载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一般来说,一座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主宰该城的诸侯或贵族的宫室,同时也是该城的行政和祭祀场所。城的四周一般围有城墙,有的还有相应的防卫工事。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富余,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还可能有农田。相比之下,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用今天的眼光看,城市内部这样的结构和功能并不合理,却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也体现了当时人的智慧。对每座城的居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安全。这些都离不开君主和城墙的庇护,二者在城中占主要地位是顺理成章的。
自秦朝以降,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以西汉为例,全国1500多座城被分为首都,郡、国(诸侯国),县、侯国(列侯的封地)、道(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邑(皇后、公主等的封邑)这三个等级,逐级管辖。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都筑有城墙,宫殿(或衙署)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
西汉的长安城是在秦朝废墟上新建的城市,事先就有严格的规划。长安城的面积约36平方公里,但城内的主要部分是宫殿,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合计约12.6平方公里,加上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设施,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供百姓居住。由于城内容不下众多的官员、贵族,他们大多居住在长安附近新建或扩建的“陵县”(因皇帝的陵墓而设置的县)内,以至形成了一个人口比长安还多的城市带。
东汉首都洛阳城的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内的南宫、北宫等宫殿占地约4平方公里,再除去衙署等建筑,留给居民的地方大概也不过三分之一。
首都以下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的宫殿,但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
在一个农业社会,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除了本来就住在城里,或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商人、工匠等,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因为城市对他们并无多少吸引力,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
东汉末年开始的分裂割据,以及其间反复出现的饥馑、战乱使原有城市受到很大破坏,但一些新因素也导致了城市的进步。例如,各个政权为了增强实力,在城市建设中更讲究实效,避免形式化。原有宫殿毁坏,或者没有能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民居在城市中所占比例相应增加。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首都与大城市中往往形成特殊的景观。
以北魏洛阳为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原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种新气象,恰恰是以往的首都城市所未见过的。
唐朝的都城长安已经兼顾了城市的不同功能。
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面积达80多平方公里。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于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整座城市规划整齐,布局严密,规模宏大,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36.7公里。皇城也呈长方形,周长9.2公里。城内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两侧都设有排水沟。其中5条干道宽百米以上,特别是朱雀街宽达150米,两侧沟宽3.3米。这些街道将城内分为110坊,各坊建有坊墙、坊门,坊内为居民住宅、宫衙、佛寺、道观等。寺观遍布各坊,建筑豪华壮丽,有的占有全坊之地。著名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就建在慈恩寺和荐福寺内。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面积大致相同,两市都筑有围墙,市内店铺、作坊密布,商业繁荣。三条渠道将河水引入城内,以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并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人口最多、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也限制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局限要到宋代才得到突破。结合《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和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城市在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
发达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使经济发展迅速,民众获得实利,生活水准提高,并且突破了城墙的限制,扩大到近郊。当时不少城市都在城外形成新的市场,南宋时,杭州的商店和市场不断向城外扩展,以至城外部分超过了城内部分。道路、河流、桥梁、津渡形成便利的水陆路线,将各地的人员和物资引入城市。农村与城市间的交流频繁而密切,每天形成熙熙攘攘的人流。
流动人口迅速转化为移民,城市人口增加,人口的素质提高,多种文化相互竞争,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娱乐方式和设施名目繁多,餐饮等服务业应有尽有,佛寺、道观众多,城市居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得到享受。
中外史学家都认为,宋代的经济文化水准达到了新的高度,民众的生活富裕而舒适,社会繁荣而稳定。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市镇人口及以城市、市镇为生的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和服务业扩大,城市生活水准提高。
因此,尽管在宋代以后,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了封闭性的政治中心的传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如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
水运和首都
在完全没有机械化交通工具的时代,水运无疑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中国历来的政治重心都在北方,以西安、洛阳、北京为首都的时间最长,形势最稳定。但经济重心一直在东部,以后又转移到了南方。北方河流较少,水量季节性变化大,不利通航。西北更缺乏通航河道。北方的河流基本都是由西向东流,没有南北向的天然水道。为了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充分利用水运,必要时开掘运河成为历朝建都的前提。
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标志着首都咸阳正式成为这个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中心。作为皇室和中央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咸阳及其周围地区必定需要迁入和保持数量庞大的官员、将士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人员和平民。由于关中盆地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还需要大量粮食供应西北边境的驻军,粮食的运输从一开始就成为秦朝面临的难题,由此产生的沉重负担最终成为激发民愤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将太行山以东地区所产粮食运至咸阳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有黄河及其支流、渭河的水道可以利用。只是整个运输过程都是溯流而上,三门峡天险更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西汉的首都长安就是在咸阳的废墟上重建的,其形势与咸阳无异,长安的粮食保障也与秦朝采取的办法相同。但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大批移民的迁入,加上西北开疆拓土和安置移民的需求,每年由关东输入关中的粮食从西汉初的几十万石增加到了常年的四百万石,最高达到六百万石。尽管关中一直在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还在西北推广屯垦,但与激增的人口相比无异杯水车薪。东汉建都洛阳,此后经常有人建议应该迁回长安,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原因之一就是洛阳更接近粮食产地,不仅水运距离缩短,而且可避免三门峡的天险。
当然,首都的确定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隋、唐的首都又回到长安,但仍以洛阳为东都。粮食供应又回到了西汉的态势,而且由于长安人口的增加和西北疆域的扩展而更加紧张。一旦关中粮食歉收,原来的供需平衡就会被打破。为避免增加运输量的困难,皇帝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和关中百姓到洛阳“就食”,“东都”实际成为临时首都。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上百万人力开凿由洛阳往东南的通济渠,又拓宽加深了山阳渎,形成了连接洛水、黄河、汴水、泗水和淮河直达江都(今扬州)的运河。608年(大业四年),又在洛阳附近开挖永济渠,沟通卫河后向东北至涿郡(今北京市境)。同时又疏浚整治江南运河,使东南终点延伸到杭州。隋炀帝开凿运河固然有其个人巡游和用兵的目的,显然也有扩大和改善水运条件以利粮食运输的考虑。新运河的开通也增加了洛阳的粮食储备,巩固了长安和洛阳政治中心的地位。
唐朝后期,北方和关中战乱不绝,天灾频仍,经济衰落,长安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越来越依赖于南方。一旦江淮漕运受阻,就连皇帝都会陷于恐慌甚至绝望。唐末朱温逼朝廷东迁洛阳,固然是出于严密控制并最终篡位的目的,但从朱温称帝后定都于开封可以证明,水运的便利肯定是决定因素之一。果然,此后各朝的首都再未返回长安或洛阳。北宋仍以开封为首都,并且由于更接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地,水运更加便利,开封的繁荣程度超过以往的长安和洛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不解决粮食供应,首都的功能和地位就无法维持。于是自1281年(至元十八年)起,先后开通济州河、会通河、坝河、通惠河,将原来隋朝绕道洛阳的运河改造成由北京经山东直达杭州的大运河,距离缩短了900多公里。明、清时期又多次进行局部改造,保证了首都和北部边境的粮食供应。元时漕运最高达334万石,明朝增至400万石。如果没有这条运河保证漕运,北京就不可能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时尚未完全占据北方,但他深知南京偏离中国中心,不宜作为全国统一后的首都,因此一直在北方物色合适的地点。他曾以西安为首选,见其残破不堪,难以恢复。一度准备迁都开封,但实地考察后发现汴渠故道已经淤塞,其他河流也水浅量少,无法通航,不得不放弃。其实在元朝已开通京杭运河的情况下,舍北京已别无选择。
历代首都由长安—洛阳—开封—北京,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符合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要求,水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古代生态观的贡献与局限
尽管以上只是三个例子,不足以全面显示我们先民的生存智慧。但从中已能看出,他们拥有理性的、相对先进的生态观念。他们敬畏自然,将生活中、生产中遇到的特殊自然现象归结为天行、天意、天命,变恐惧为敬畏,约束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以遵天命,即遵循他们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他们相信世间万物的存在皆出于天意,因而尽可能不改变它们荣枯兴衰的程序,不破坏它们优胜劣汰的规则,客观上保护了自然和生态环境。在人口压力逐渐增加,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养成了节俭的美德,并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以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获得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在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时,他们一般会采取趋避的办法,如迁都、移民、改变交通路线、休耕弃耕等,而不是强调“人定胜天”。他们尊重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产业界线,早在西汉时就认为长城一线是“天之所以限胡汉”的农牧业分界线,反对不顾实际条件轻易扩大农业生产范围。
但是应该承认,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足以使国人能认识基本的自然规律,更无法自觉地、有效地运用这些规律。即使通过长期积累已经有了一些正确的、自觉的观念,也还不能将这些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现在往往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只是出于今人的解释,却并非古人的本意。天人合一的提出无疑是为了强化君权神授,强调皇帝是天的化身,他的言行体现了天意天命。因此,自然灾害被称为天灾,是天对人的警告或惩罚,是不可抗拒的。
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曾提出“天行有常”的观念,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掌握、利用自然规律而加以运用,并非今人所曲解的“人定胜天”),但这一正确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正因为人还不具备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对自然的敬畏不可能没有消极的一面。在异常气候和自然灾害面前,往往以不变应万变,消极地等待它们自生自灭。例如蝗灾暴发时,一些人认为对蝗虫不能消灭,只能等它们迁移或消失。在洪水面前只能祈求天神息怒,尽职的官员甚至跳入洪水,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天的怜悯。西汉时就有人认为水旱灾害的增加与盲目砍树与开矿有关,但只能解释为矿洞泄了地中的阴气。这自然不具有说服力,也不能制止这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迷信风水使一些山川森林得到严格保护,但为了截断他人的“龙脉”、败坏别家的风水也导致毁林、截流、烧山、断岗。隋朝灭陈后,将陈朝的宫殿和整个建康城彻底破坏,就是为了消除它残留的“王气”。
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使先知先觉的人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也找不到消除这些不利因素的途径。特别是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生产更多的粮食成了头等大事,因此而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只能听之任之。例如,林则徐、魏源、汪士铎等人当时已认识到大规模无节制地开垦山区是造成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频仍的原因,但他们无法找到其他增加粮食生产以养活新增人口的办法,汪士铎将这归咎于“人多之害”,主张采取激烈措施减少人口,被后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他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绝无实行的可能。
原载《文汇报》2013年10月21日第2版
- 0001
- 0000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