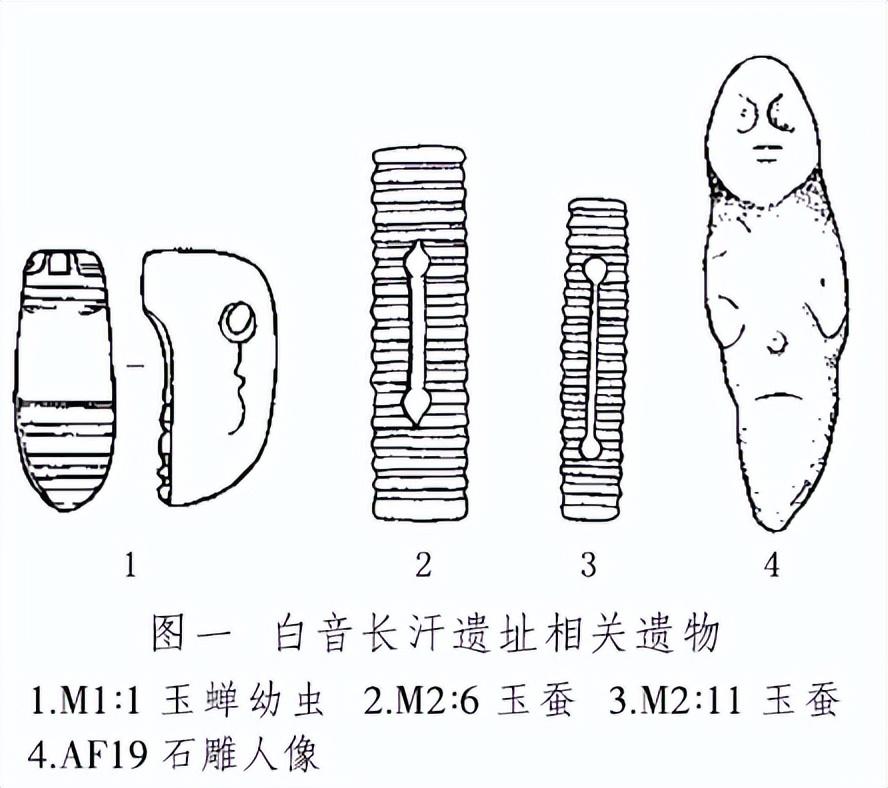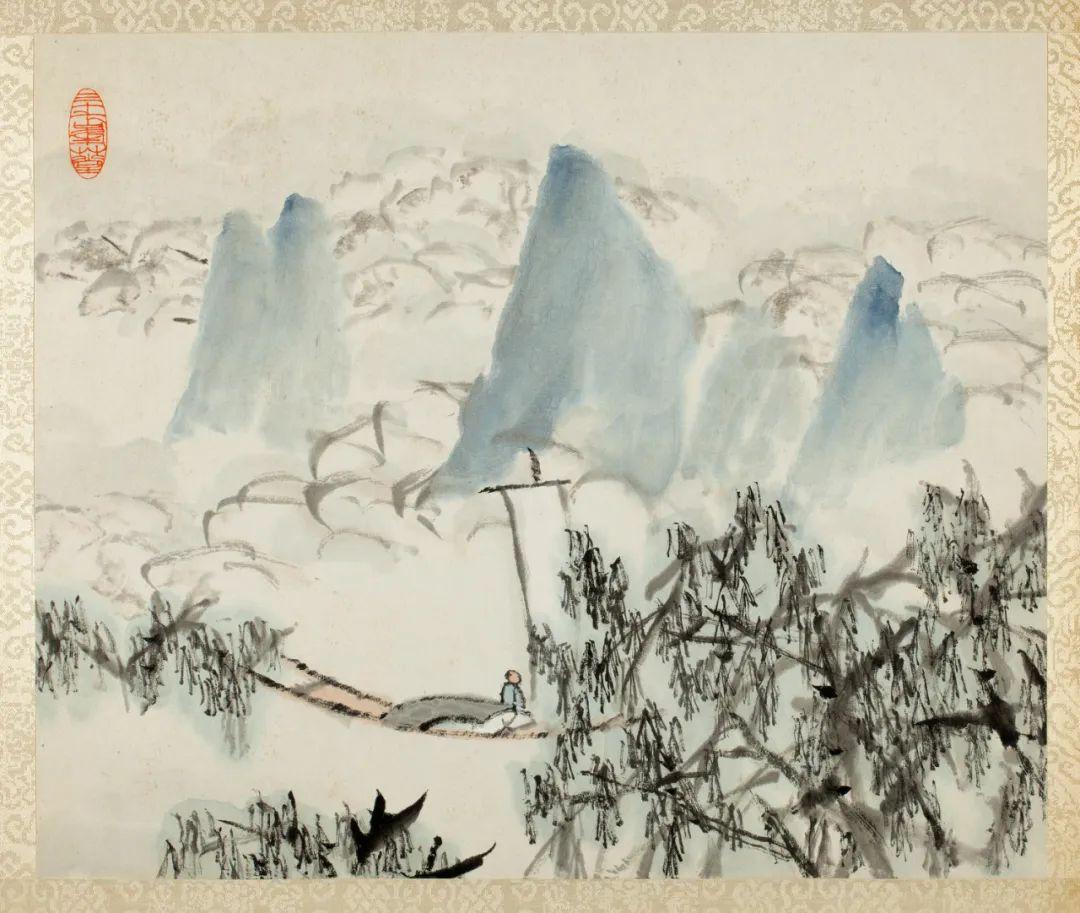葛剑雄: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主编和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三十多年间,一直无法回避一个重大问题——这套地图集需要显示的从原始社会到清末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以什么为标准,在地图上如何表示?在当时,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学术难题,更面临着政治上的风险,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和“心有余悸”的年代。
到《图集》终于开始分册修订,即将公开出版时,他在《总编例》中正式确定了这一原则: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映射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这套图集力求把这个范围内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政权的疆域全部画清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之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为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在此前的1981年5月,谭先生在北京出席“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报告,比较详细地谈了他确定这一原则的根据和想法。但据他的报告整理出来的文章却迟迟未能问世,直到10年后才发表,后收入《长水集续编》,在先生去世后的1994年出版。
众所周知,《图集》在正式出版时尽管由谭先生作为主编署名,但一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由一个专门设立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以下简称“杨图委员会”)指导,由中央主管部门审定的。《图集》所依据的原则、观念和处理办法必须与官方立场一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先生所能做的是如何在官方所划定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事实,使这些政策化的原则找到恰当的史料根据,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实际上,谭先生连自己确定的(也是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原则也无法完全遵守。例如唐安南都护府的南界、隋唐的北界等,只能放弃自己根据史料做出的判断,根据领导的裁决定稿。直到1982年,他坚持增加一幅公元820年吐蕃(藏族的前身)分幅图以显示其最大疆域的主张,有幸“上达天听”,由胡耀邦批示“同意”,才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谭先生的认识与观念也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图集》编绘、修订的阶段,即1955—1988年的中国——经历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苏论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等政治运动,都曾直接或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图集》,甚至具体而微的某一条线、某一个点的确定、移动、增加或删除。当时对“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的理解,是尽可能找到“政治上”有利的史料,或者对史料尽可能做对我方有利的解释。而对重大的“政治原则”,是无法越雷池一步的。如对台湾的画法,尽管谭先生的主张最终被接受,但《图集》的出版因此而推迟了五六年,经过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努力并获得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部长)圈阅方能实现,而作为主编的他也不得不同意做某些变通。否则,就像他曾经悲观地预测,在他的有生之年会看不到《图集》的出版。
谭先生在晚年,曾不只一次与我谈及编绘《图集》的往事,也提到他提出“历史时期的中国”与“中国疆域”处理原则的艰难与无奈。我曾告诉他,质疑或反对他的意见的人两方面都有,有人认为《图集》所画的“历史时期的中国”超出了实际因而太大了,也有人指责这个“中国”的范围太小了,例如6世纪后的高句丽、高丽应该包括在内。他叹息道:“我是没有办法了,今后看谁能解决吧!”
地图上的“中国”
有关地图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夏代,相传直到东周还珍藏在周天子宫中的象征九州的九鼎,就已将各州的主要地理要素铸在鼎上,具有原始地图的功能。现在最早的地图实物,是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一号墓中出土的七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约绘制于战国秦惠王后期(公元前4世纪初)。显示范围更大的地图则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一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主区已包括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附近地区。这些区域性的地图,无论是传世的还是仅见于记载的,都比较精确具体,因为它们都有具体的功能和直接的用途,甚至事关国计民生。如刘邦抢先占据秦朝的首都咸阳后,萧何深谋远虑,立即接管了秦朝的地图与档案,使刘邦了解“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其中大部分信息显然来自地图及其附录。这一传统为后世的同类地图所继承,所以在采用现代制图技术之前,无论是以“计里画方”绘成的地图,还是山水画式的写意地图,制图者的主观意图总是希望显示实际的地形地貌、人文景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对其中某些要素做些夸大或缩小。
但如果是画一张全国地图或“天下”地图,就必须服从“天下”的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居于“天下之中”。本朝或前朝的疆域政区都要画出,但“天下”的边是画不到的,本朝或“中国”以外的属国、蛮夷、化外之地、蛮荒之地就可以随意处理了。既然非声教所及,不画无所谓。但如果画了也无不妥,总不出天下的范围,而且能说明王朝的影响无远弗届。
例如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汇报,得知黄河发源于于阗(误以为今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游),即“案古图书”(查考古代地图及附录文字),将源头的山脉命名为昆仑。而当时今塔里木河流域还不在汉朝的管辖之下。
又如唐贾耽绘《海内华夷图》,“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汉书》)发源”,包括“左衽”(非华夏诸族)地区。按其比例尺计算,该图的范围东西有三万里,南北则在三万里以上,都已超出了当时唐朝的疆域。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藏日本龙谷大学)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以李泽民《声教广被图》(1330年前后)和元末明初僧清睿的《混一疆理图》为底本绘制,《大明混一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属同一系统。《大明混一图》不仅几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也画出了非洲。“混一疆理”不过是“天下”的同义词。此图绘制在郑和航海之前,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显然来自元朝与蒙古汗国时代,也包括阿拉伯人的地理发现,但画入“大明混一”之图显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直到清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画成的《乾隆内府舆图》还是如此,该图西面画到了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面画到了俄罗斯北海,尽管在清朝疆域以外没有标出多少地名,却依然体现了乾隆皇帝与臣民的天下观念。
正因为如此,这类地图历来被当作政治符号,即皇帝受命于天,奄有四海的象征。官方绘制的地图被当成国之重宝、皇家珍秘藏于金匮石室,其内容也被蒙上神秘色彩。如果说春秋笔法是历代正史的传统,那么在全国性的或天下的地图的绘制过程中,“春秋绘法”就更不胜枚举了。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这类官方地图完全可以自娱自乐,秘而不宣,以致外界既没有看到的机会,更不可能也不敢加以评论的话,《图集》却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难以承受的政治使命。由于这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中共和国家主席毛泽东询问时建议实施,并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一项任务,《图集》无疑必须在政治上绝对符合中共的路线和国家政策,在学术上必须能体现国家水平和主流的共识,而在名义上却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华地图学社”、虽存在而不能署名的“编绘组”以及署名为“主编”而并无全权的谭其骧的成果。
吴晗一开始的建议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为此而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专门成立的委员会也以此为名。但很快就发现政治上的巨大障碍——杨《图》只画历代中原王朝,甚至连一些中原王朝的疆域也没有画全,要按这样的地图改绘出来,岂不显示中国的疆域要到清朝乾隆后期才形成?如何证明辽阔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呢?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会受到质疑和挑战。
于是“重编改绘”的名称虽还沿用,实际却成了新编一部中国历史上全部少数民族政权和分布区域在内的中国历史疆域政区的地图集。但由此而产生的困难是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此前虽有包括“华夷”的地图,对“夷”至多写上一个名称,根本不必顾虑其准确性,更不会置于与“华”同等的地位,而现在必须体现民族平等和共同缔造中国疆域。也就是说,对中原王朝以外的政权,特别是非汉族(华夏)的政权必须以同中原王朝同样的规模画出它们的疆域政区图,但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却相差悬殊,或者根本找不到直接记载的材料。例如有关古代西藏的汉文史料相当有限,有的朝代只是重复抄录往年的记载。近代的英文资料倒不少,却因政治原因而无法全部运用。由于藏文中也难觅确切可靠的记录,精通藏文的藏学专家也束手无策。谭先生曾专门向阿沛·阿旺晋美请教,也没有获得什么线索。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年代,中原王朝的边界爱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甚至可以根本不画界线,以表示天朝大国的疆域“无远弗届”。到20世纪50年代就没有那样自由了。尽管中国与大多数邻国的边界形成于近代,尽管不少边界都标为“未定”,却都可以追根溯源,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小心谨慎。这不仅是因为邻国都成了主权国家,不像当初有的还是藩属国,有的尚未建立政权,有的还是未开发或不宜开发的无人区。更麻烦的是,这些邻国已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或为友,或为敌,或亦友亦敌,或由友而敌而头号敌,抑或由敌而友而好友。学术障碍固然不易克服,但还有路可退,实在画不了可以保持空白,或只画出少量地名,或不画界结,政治上的障碍却只能服从政治,稍不谨慎就会招致批判,在“文革”甚至会因此而被打成“牛鬼蛇神”,成为反革命。
例如,《图集》中外蒙古与其北地区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绘的,两汉图幅将坚昆、丁令(零)的北界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北界,有一段画在苏联(今俄罗斯)境内的安加拉河以南,即所谓南线;隋唐图幅以契骨、黠戛斯的北界为中国北界,有一段画在安加拉河一线,即所谓北线;都已获得外交部审查通过。谭先生在汇总时,觉得前后不统一,画在北线并无可靠的根据,所以将隋唐图也改成画南线,而从元图开始仍画北线。《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时期)出版后,一部分已经发行,地图出版社发现这一册与元明图的画法不同,认为是严重问题,就于1977年4月8日上午通知新华书店发行所,第五册暂停发行,听候处理。5月5日又通知已发行的全部收回,未发行的待修改后重新印刷。并于16日报告外交部,要求对北界的处理做出决定。谭先生反复查阅史料,更确定对这些部族的北界画在今安加拉河并无确凿证据,因为这些部族都是游牧民族,其占有地区或活动范围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界线,所以不能因为元朝吉利吉斯的北界画在这一线,就一定要将隋唐的北界也定在那里。他与同仁去南京大学协商,讨论了一整天,双方依然无法一致,只能提交外交部审定。自8月2日起,外交部召集双方与地图出版社、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相关人员,先后开了多次不同范围的会议,于20日做出最终决定,隋唐图也采用北线。到了今天,我完全可以肯定,外交部之所以采纳北线,并非因为持此主张的人多,或者余湛副部长能做出学术判断,而是因为这条界线是画在当时苏联境内,而“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比“美帝”(美国帝国主义)更危险的头号敌人。将历史时期中国的疆界尽量北推,自然是政治正确,并符合“国家利益”。
另一个例子是朝鲜。由于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素的纠缠,这无疑是《图集》最难处理的关系之一。对此,谭先生专门做过说明:“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当时确定这一原则,是经过反复讨论的,最终也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高句丽的主体由今中国境内扩展到朝鲜半岛全境,而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拥有今中国境内辽河以东的一大片土地,高句丽及其后的高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这些过程都相当复杂。但地图上必须描绘为清晰的点、线和颜色(如中国与外国的不同基色),高句丽由中国的基色变为外国的基色必须有明确的界线。即使能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之间还是要有明确的界线及不同的性质。因此这一原则尽管不是无懈可击,却是权衡利弊后不得不采取的适当办法。
不过,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朝鲜不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朝鲜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部会批准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吗?果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认为《图集》从5世纪起将高句丽画成外国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损害了国家利益,随之而实施的一项耗费巨资的“工程”据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图集》中高句丽的处理办法本来就有不同意见,重新进行研究或做出结论完全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就是观点偏激些也无可厚非。但一定要与政治联系起来并等同于国家利益就属耸人听闻,因为即使在5世纪后的地图上继续将高句丽画成中国境内的政权,将隋朝与唐初对高丽的征服解释为国内镇压叛乱,也改变不了此后朝鲜半岛最终脱离中国的历史,更不会对今天的中朝、中韩关系产生任何积极影响。反之,保持《图集》的画法绝不会引起或加剧中朝、中韩间的冲突,更不会对中国的实际利益带来丝毫影响。
可是,直到今天,总还有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纯粹是无知,会千方百计夸大历史地图的作用,《图集》一再被曲解或不恰当地利用,即使谭先生还在世,肯定也只能徒唤奈何。
《图集》虽然是一套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不计不占篇幅的插图)、约7万个地名构成的巨型地图集,但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纸本印刷的普通地图集。加上《图集》采用“标准年代”的编绘原则,即在同一幅图中的地理要素都以存在于同一年代或大致相同的年代为取舍标准,所以每一幅地图所显示的“历史中国”只能是某一年或某几年至多十多年这样一个阶段内的“中国”的范围。例如唐朝画了三幅总图,也只能分别显示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和元和十五年(820年)的疆域和形势。如果再多画几幅,当然能提供更多的史实,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唐朝疆域的变化。可惜在纸本印刷地图的年代,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即使到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年代,也还受到原始史料的制约,不可能将古代疆域的变化过程完全复原重建。
采用标准年代的编绘原则后,《图集》的科学性得到提高,基本保证了历史地图的本质,即在同一图幅所显示的是同一时间存在的地理要素及其分布,却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未必能显示某一朝代理想的“极盛疆域”,而这不仅是传统史学家所追求的,也是当代的政治需要。而实际上,即使是一个强盛的朝代,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年代,正好在其四至八到都达到最大的范围。还是以唐朝为例,它控制咸海以东的马浒河(今阿姆河)和药杀水(今锡尔河)流域是在龙朔元年(661年),但到麟德二年(665年)就撤到葱岭,实际仅维持了三年,而那时尚未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灭朝鲜后在当地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已退至辽西。天宝十载(751年)唐将高仙芝的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城)被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击败,唐朝的疆域又退至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灭薛延陀,置燕然都护府,辖有今内蒙古河套以北、蒙古国、叶尼塞河上游及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但到仪凤四年(679年)突厥再起就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了32年。如果一定要画出一幅东西南北都达到极点的唐朝地图,除了将不同的年代混杂一起,别无良策,“文革”期间定稿出版的“内部本”上的总图正是这样画出来的。以往的正史和传统的史书也是这样写的,并且长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在教科书中沿用。
但一些重大的疆域变化的确因不在标准年代而无法显示,而由于《图集》的巨大影响,客观上也使这类史料越来越鲜为人知。例如明朝初年在平息了安南(今越南)的内乱后,于永乐五年(1407年)在其全境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下辖17府、47州、157县;同时设置都指挥司,下辖11卫、3所。至宣德二年(1427年)全部撤销,恢复安南的属国地位。《图集》第7册明时期的两幅《明时期全图》分别选了宣德八年(1433年)和万历十年(1582年),第一幅图选用宣德八年,自然不可能出现六年前已撤销的交趾布政使司和都指挥司。至于为什么不选用宣德二年之前若干年,为什么不能另附一幅交趾布政使司辖地的插图,我没有问过谭先生,他也未主动谈及,但我可以肯定,正是因为那时中越之间存在着“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既然对方讳言这段历史,或者是作为本民族抵抗“北方侵略”的光荣历史加以宣扬,中国方面还是不提为宜,以免引起双方的尴尬。
历史学界与民间对这样的处理并不完全认同。谭先生的老友张秀民先生虽以研究中国印刷史著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却情有独钟,对于永乐四年统兵平定安南的张辅极其崇拜,称之为民族英雄。张先生对《图集》不画明交趾布政使司及其他有关越南的画法深为不满,多次与谭先生争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交恶,张先生再次提出改图,谭先生却表示:既然当初这样定了,这样的画法也不违反历史事实,就不能因为现在两国关系变了就再改变,否则还要历史地图干什么。
历史上的中国
对于在《图集》中为什么要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谭先生有过具体说明: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时期的“中国”为中国。举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推翻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就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推翻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谭先生的意见说得很明白,他确定的“历史上的中国”是今人的概念,并非历史时期各个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的人都一致,都认同的。既然要用这样一个概念来确定《图集》必须显示的范围,就一定要有一个前后一致、基本稳定的空间,因此才有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这样明确的规定。现在有些人不了解谭先生这样做的目的和原因,从不同角度批评“历史上的中国”这样的规定,基本上都是文不对题。例如有的人说,历史上“中国”的概念是不确定的。不错!但如果《图集》的主编和编绘者也“不确定”,那这些地图怎么画呢?
其实,中国的概念在其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本来就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的。
就客观性而言,也存在着四个不同的概念:
政治性的中国,指政权和国家。最初的中国是指众多的国中处于中心、中央、中间区域的国,即国君所居之国,商朝和周朝的首都、国君直接统治的地方。但东周时天子权威丧失,形同虚设,诸侯相互兼并,强者称霸,主要的诸侯国渐渐以中国自居,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和相邻区域。到秦始皇灭六国建秦朝,秦朝的首都和中心区域固然是中国,那时候秦朝的疆域也可以称为中国了。此后,从西汉直到清末,各个朝代的疆域都可称为中国,只是随着该政权统一和开发范围的扩大而扩大。但是中国还不是各朝代的正式国名国号,如清朝的正式名称是大清、大清国。正因为如此,“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被一致接受的政治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清朝人使用“中国”时,既可以包括满洲、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在内的全部疆域,也可以只指内地十八省,甚至连云南、贵州等边疆省份也可以不在其内。另一方面,明清时的朝鲜、越南等藩属国也以中国自居,以属于中国一部分而自豪。鸦片战争后国门渐开,在与外国的交往中,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逐渐巩固,到清末基本形成。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最终正式成为我国的名称。
民族性的中国,指汉族及其前身诸夏、华夏诸族,以及受汉族影响深而基本被同化的其他民族。按照这个概念,非汉族的聚居区属夷狄、蛮夷、四裔或外国,不属于中国。随着汉族由聚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大到南方和边疆,包括在此过程中大量非汉族被融合,作为民族概念的中国也随之扩展。由于古代区别华夏和夷狄的标准一向是文化,是礼,而不是血统,夷狄一旦接受了华夏文化,就能“由夷变夏”。虽然就局部区域和局部时间而言,也存在“由夏变夷”的过程,即原来的“中国”成了非“中国”,但总的趋势是民族概念的中国范围越来越大,覆盖的人口越来越多。
文化性的中国,指汉族或华夏文化区,特别是汉字文化圈。文化概念的中国与政治概念的中国并不一致,例如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汉字是朝鲜、越南、琉球的官方文字,或者是当地唯一通行的文字,但在中国疆域内部,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通行文字却不是汉字。文化概念的中国也不一定与疆域的扩展同步,例如西南的大部分虽从秦汉以来就纳入版图,但大多要到改土归流,置府县,设学校,开科举后,才获得文化上的认同。
地域性的中国,等同于中原。早期二者完全通用,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用的“中国人民”即“中原人”的同义词。中原,自然是以一个朝代的疆域和首都为坐标的,一般是指首都或政治中心一带。但由于成为并于行政区划的代名词,所以往往没有明确的范围。今河南固然是最老牌的、无可争议的中原,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也未尝不能称中原。在分裂时期,主要的政权都将自己首都一带称为中原。不过,由于主要朝代的首都不出黄河中下游的范围,中原的概念一般也就在其中。
但是就主观意识而言,中国的概念不仅存在时间、空间的差异,就是在同一时空范围中,不同的群体或个体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正因为如此,论者尽可以不认同谭先生所确定的“历史上的中国”的概念,但如要运用或讨论《图集》,就必须以这个“历史上的中国”为范围,为标准。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对《图集》中所画出的中国疆域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史料的记载,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也需要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其中不少图幅编绘、定稿于“文革”期间,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造反派、红卫兵当家做主,谭先生被剥夺了主编的职权,是“一批二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协作单位的教授、专家也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形成了一些荒唐离奇的错误,或者为了突出政治、“反帝反修”、“国家利益”的需要,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故意制造了一些“新发现”、“新突破”。在“文革”结束后的修订中,大多数错误已经纠正。但由于工作量太大,修订的时间有限,遗漏了一些错处。加上当时多数作者还心有余悸,思想还不够解放,有些处理原则和办法还囿于陈规旧说,并未完全做到实事求是。“‘文革’中被无理删除的唐大中时期图组、首都城市图和一些首都近城郊插图,被简化为只画州郡不画县治的东晋十六国、南朝宋梁陈、北朝东西魏北齐周、五代十国等图,以及各图幅中被删除的民族注记和一些县级以下地名,若要一一恢复,制图工作量太大,只得暂不改动。”年过七旬的谭先生和一支经历十年浩劫青黄不接的团队,对此也只能徒唤无奈。
但在重大原则上,谭先生对中国疆域的处理是经过深思熟虑,始终坚持的。
长期以来,出于政治目的,史学界对今天中国境内的疆域一直强调“自古以来”,似乎中国从夏、商、周以来一直是这么大,似乎不找到一点“自古以来”的证据,一个地方归属于中国就失去了合法性。其中最敏感的地方就是台湾,由于谭先生坚持实事求是,以史料史实为根据,“文革”期间成为重大的反革命罪状,受到严厉批判斗争。在修订过程中,他对台湾的处理方案多次被主管部门否决,《图集》的出版也因此而推迟了好几年。直到中央领导过问并签阅,才涉险过关。但谭先生坚持认为:
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臣,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儿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要把台湾纳入中国从三国时算起,理由是三国时候孙权曾经派军队到过台湾,但历史事实是“军士万人征夷州(即台湾),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只俘虏了几千人回来,“得不偿失”。我们根据这条史料,就说台湾从三国时候起就是大陆王朝的领土,不是笑话吗?派了一支军队去,俘虏了几千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孙吴的了?孙吴之后两晋隋唐五代两宋都继承了所有权?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南宋时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县辖境之内,元朝在岛上设立了巡检司,这是大陆王朝在澎湖岛上设立政权之始,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张“台澎一体”论,说是既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可见元朝已管到了台湾,这怎么说得通?在那么小的澎湖列岛上设了巡检司,就会管到那么大的台湾?宋元明清时,一个县可以设立几个巡检司,这等于现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设在澎湖岛上的巡检司,它就能管辖整个台湾了?有什么证据呢?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
(台湾)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
但这种机械的、教条的观念根深蒂固,无处不在,以至在解释任何一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总是采取实用甚至歪曲的态度,只讲一部分被认为是有利的事实,却完全不提相反的事实,使绝大多数人误以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例如新疆,只说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却不提王莽时已经撤销,东汉时“三通三绝”,以后多数年代名存实亡,或者仅部分恢复。只说唐朝打败突厥,控制整个西域,却不提安史之乱后唐朝再未重返西域。只提蒙古征服西辽,却不提元朝从未统治整个西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要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才重新实现。对于清朝来说,西域的确是新的疆域,因此才会有“新疆”的命名。谭先生还以云南为例,虽然汉晋时代是中原王朝统治所及,但是在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朝。南诏以后成为大理。总之,从6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700年,到13世纪才由元朝征服大理,云南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所及。
不过,谭先生特别强调:“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
虽然作为学生和助手,我完全理解谭先生无法突破政治底线的苦衷,但我不得不指出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并且实际上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性。从秦朝最多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到清朝极盛时期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不能一概称之为“自然形成”。不能因为最终形成了疆域如此辽阔的国家,就将以往一切侵略和扩张视为统一、进步,秦始皇征服岭南,汉武帝用兵西域,唐朝灭高丽、突厥,蒙古人建元朝,清朝灭明、准噶尔,尽管客观上促成统一,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准备了有利条件,但无不属于侵略扩张,未必有正义可言。但另一方面,在尚未形成国家和民族平等的观念,尚未形成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之前,全世界能够存在和发展下来的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无一不是侵略扩张的产物,中国岂能例外?1840年前的中国疆域之所以比较稳定,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是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致在工业化以前的外界缺乏打破地理障碍的能力。尽管如此,唐朝的军队也在中亚受挫于阿拉伯军队,以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取代佛教,葡萄牙人实际占据了澳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占据过台湾和澎湖。沙俄依靠侵略手段掠夺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这也不能不说是“自然”的结果。在中俄雅克萨之战并导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应该了解俄国人的真实意图,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移民实边,却继续实施对东北的封禁,以致俄国人进入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如入无人之境,至今一些俄国史学家还声称俄国人是这片“新土地的开发者”,而非中国领土的掠夺者。但在清朝对东北开禁,鼓励移民,设置府州县,建东三省后,俄国与日本尽管仍然处心积虑要占据东北,却未能得逞。这岂不也是自然的结果吗?至于一定要强调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些事例不仅显得牵强,并且与前面对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论述自相矛盾。
从谭先生一生的经历和他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他是始终与时俱进的,也总是在超越前人,并希望我们这些学生能超越他。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相信他早已突破这些局限,所以我的放胆狂言一定会得到他的宽容、理解和鼓励。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8页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