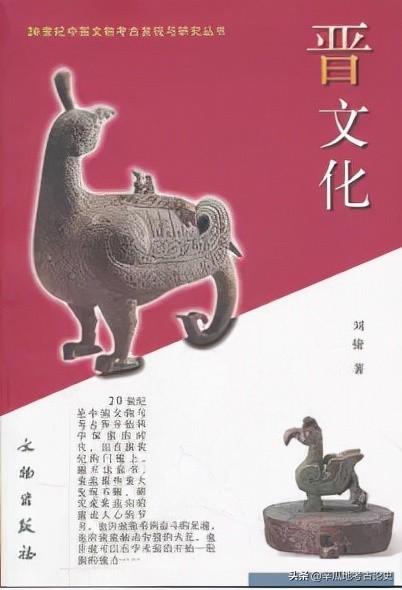李零说《孙子》
《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属于人文学术,大体相当现在的“文史哲”;后三类属于科学技术,大体相当现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还有相关的技术,当然还有现代人称为“迷信”的非科学成分。
中国传统:人文,经为首;科技,兵为首。
中国古代,兵学很发达,说别的可能脸红,这事一点儿不吹牛。历史上,中国的兵学最发达,搁到全世界去讲,也一点儿不吹牛。
研究人类社会,现代科学叫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学问,一门是政治学,一门是经济学。经济学,发达比较晚,不如政治学。
《礼记·哀公问》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1]
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西方传统,研究人,主要有两门学问,一门是伦理学,一门是政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原来是搅在一块儿,老是分不清。古人都讲“以德治国”,我国这么讲,外国也这么讲。大家都盼望“好人政治”,相信“好人”搞出来的政治一定是“好政治”。
柏拉图作《理想国》,喜欢讲正义。他老把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混为一谈,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
这类想法,和我国差不多。比如孔孟一派的思想家就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小,焉有大。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细胞,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
这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亚里士多德作《政治学》,才把伦理和政治分开来。他知道,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的“城里人”,离开城邦,什么也不是,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2]
马基雅维利作《君主国》,第一次把政治当作一个“坏世界”来讲。他把政治从伦理剥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政治学。他很像中国的法家,讲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跟道德掺乎,非常诚实,非常坦白,非常严肃,因而也非常冷酷。
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都强调大道理管小道理。
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科学。
中国的政治学,告别道德后的政治学,叫“刑名法术之学”。这门学问,毫无疑问,是由法家奠定。但法家成于秦也败于秦,在中国的道德世界始终抬不起头。只有它的兄弟学科一脉单传,留于后世。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兵法。
中国的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兵法”。[3]战国晚期,天下流行的是“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韩非子·五蠹》),治国和用兵分不开。特别是讲“大战略”,两者分不开。[4]现代军事学,头一条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兵法,早就这么讲。
《孙子》开篇讲“五事七计”,“五事七计”的头一条就是“道”。“道”是政治。
我国古代,“道”是终极性的原理,管着一切小道理的大道理。
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大道理。数术讲天地,方技讲身体,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真正讲人,主要集中在兵书。
兵书是讲“人道”。
《鹖冠子·近迭》有一段话,和《礼记·哀公问》形成对照: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
作者生活于杀人盈野的战国晚期,当时的战争太残酷。其惨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相比。这对人的世界观是很大的刺激。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历史。
战争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兵法是解读历史的金钥匙。
中国人是把兵法当作研究人的大道理。[5]
兵法是一种斗争哲学
兵法研究的是人。
有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冲突,小则妇姑勃谿,大则你死我活。
人比动物更能“窝里斗”。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借西方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中国的子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两部开山之作。他们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
兵书,按传统分类法,是附属于子学。中国的技术书都归子学。过去,儒经占据统治地位,子学低于经学,技术又低于子学,《孙子》没有地位。除了军人,除了喜欢议论军事的文人,没有多少人关注《孙子》,更不用说其他兵书。子学也好,兵学也好,都是赖西学而复兴。
胡适、冯友兰,他们讲先秦哲学,是以儒、墨、道为主,虽涉名法,旁及阴阳,但于兵书、数术、方技,全都不着一字。冯友兰讲他的“取材标准”,特别提到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讥讽该书太高抬《孙子》,竟把兵书列入哲学史的范围。
兵书是技术书,最讲实用,这样的书,难道也有“思想”,也有“哲学”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他们会问。
我说,当然有——不但有,而且很有。战争,人命关天,千变万化,奥妙无穷,不动脑筋,不长心眼,那不是找死?
哲学是爱智之学,兵法最讲智慧,里面当然有哲学,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我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的思维,和兵法有很大关系,不懂兵法就不懂中国哲学。
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这么看,武装斗争出身的毛泽东不这么看。
毛泽东研究兵法,主要在1936—1938年,兵法和哲学是一块儿读。1936年,他写信给叶剑英,让他派人到白区买《孙子兵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他引用过《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937年,他读过苏联出版的哲学书。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身,1937年7—8月)中,他引用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也引用过《孙子·谋攻》(同前)。1938年,他在延安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读《战争论》,读恩格斯的军事著作,请何思敬从德文翻译,边译边讲。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郭化若将军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他写过《军事辩证法》(1999年),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1940年),写过《白话译解孙子兵法》(1944年)。他们都把《孙子》当作很有哲理的著作。1949年后,中国各大专院校的中哲史教材普遍讲《孙子》,讲《孙子》中的辩证法,应该说是延安的遗风。
1958年和1980年,冯友兰两次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收入了《孙子兵法》。今天大家都承认,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没有《孙子兵法》不行。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辩证法就是起源于《孙子兵法》。[6]
《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兵法,都很有哲学味儿。这种哲学是什么哲学?其实就是生存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是以斗争求生存的哲学。
人与人斗,很残酷,但无法回避。这是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人的所有行为,不管哪一种,都是对生存环境的反应。
英国战史家富勒说,19世纪,有三个“卡尔”是讲这种哲学的先知,一个是普鲁士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一个是英国的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的“查尔斯”,就是德国的“卡尔”),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这种哲学。[7]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最早。1911年的《大战学理》是最早的中译本(从日文版节译)。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很有哲学味道,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由于列宁和前苏联军事界的重视,由于毛泽东和延安军事界的重视,在我国影响很大。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比前者晚16年。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的译本。由于十月革命,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中国也影响很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比《战争论》和《共产党宣言》都晚,但中国人知道进化论,却比《战争论》和《共产党宣言》要早。《物种起源》在中国出版是在1920年,但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已经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亡国灭种”的“盛世危言”下,对中国人的震撼,简直如山呼海啸。其社会学的意义(救亡图存)要远远大于生物学的意义。
革命和战争有不解之缘,有目共睹。两者都是暴力,互为因果。现代的两次革命高潮就是和两次世界大战相伴随,不必多说。
今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值得纪念。他的《物种起源》,在美国常被人骂,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骂,甚至有人把他当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骂,骂他,甚至超过了马克思。其实,《共产党宣言》比《物种起源》早11年。
古人讲战争,喜欢从含牙戴角、前爪后距,擅长使用毒药的动物说起。[8]战争确实很动物,兵法的很多想法都来源于打猎。
动物战争,一直是人类战争的参照。它们为了争夺食物,争夺水源,争夺领地,争夺交配权,打得不可开交。动物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类的丑陋。动物是人类的老师,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在种内攻击这一点上,人类比动物更突出。
动物,上天、入地、下海,无所不能。它们,浑身上下,全是高科技,雷达、声呐、远红外、GPS、电磁波、生化武器和各种伪装术,应有尽有。即使讲武器,论技术,动物也是人类灵感的源泉。我看电视,经常看跟动物有关的节目,就是从动物学军事。
人类非常好斗,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斗争。这是个冷酷的事实。研究这个冷酷事实的哲学叫斗争哲学。
虽然,“斗争”二字,现在已经不时髦,但斗争依然存在。
兵书四门,贵谋尚诈
西汉晚期,刘向、刘歆把天下的兵书分成四门: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汉书·艺文志》)。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
(一)权谋
班固的定义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权”是权变,“谋”是谋略。“权谋”是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的大计。古代兵书,《司马法》、《六韬》和《孙子兵法》,是权谋的代表作。战争全局,是“用兵”和“治国”的关系。比如《六韬》,既讲治国,又讲用兵,就是属于“大战略”研究。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是《老子》的话(出第57章)。治国是靠“正”,御臣下也好,管老百姓也好,要守规矩,讲道德。但用兵不一样,它是对付敌人,想方设法,跟敌人拧着来。它靠的是反规则,这叫“奇”。比如《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忠)人(信)”就是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讲“兵以诈立”,就是讲“以奇用兵”。
“先计而后战”,是《孙子》的特点。它以《计》篇为头一篇,先庙算,次野战,次攻城。计必先定于庙堂,然后才兵出于境,这就是“先计而后战”。
“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是说它有综合性,下面三类,它都讲,就像医书中的医经,不光有理论性,还有综合性。《孙子》,不但《汉志》著录的82篇本可能是四门都讲,今本十三篇也是如此。
(二)形势
班固的定义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形势”,是战术对策,好像医书中的经方,对症下药。它强调的是快速反应,灵活机动。兵书讲形势,对话体,最方便。但《孙子》不这么讲。它是把“形”、“势”二字当一对矛盾,先作理论分析(《形》、《势》、《虚实》),再作过程描述(《军争》以下五篇),从“合军聚众”到“交和而舍”,从走到打,一环一环扣着讲。
“雷动风举”,就是“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后发而先至”,就是“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就是“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这些话,都出自《孙子·军争》。
(三)阴阳
班固的定义是“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阴阳”,是数术之学(古代讲天文地理的学问)和阴阳五行说(数术之学的理论)在军事上的应用,主要和天地有关。俗话说,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指这类学问。这类学问,早期文献多已失传,读者要想了解,只能看出土材料。这里简单说几句。
“顺时而发”,是讲选择时日(术家叫“选择”),用兵要合于时令。古代的选择书经常讲用兵,兵书也经常讲选择。出土发现,子弹库帛书、睡虎地《日书》,很多数术书,都有这类内容。
“推刑德”,“刑德”是一种选择术,它和用兵关系很密切。马王堆帛书《刑德》就是这种书。孔家坡汉简《日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随斗击”,古代占卜,有一种工具叫式盘,当中是北斗,周围是二十八宿,北斗犹如表盘的指针,二十八宿犹如表盘的刻度。古人相信,斗柄指谁谁败,相反的方向才是吉。孔家坡汉简《日书》有《击》和《斗击》,就是讲这种数术,张家山汉简《盖庐》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因五胜”,是讲五行相胜的数术。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就是讲这类数术,孔家坡汉简《日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类学问,充满迷信,但在古代,却是“高科技”。古代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地理学,就是集中在这一类。
《孙子》也讲兵阴阳,主要集中在后半部。一是《军争》到《九地》,《孙子》处处讲地形,涉及阴阳、顺逆、向背;二是《火攻》,《孙子》讲“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讲“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这类学问,古代叫风角。诸葛亮借东风,就是这种学问,古代属于兵阴阳。
(四)技巧
班固的定义是“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技巧”,和人有关,既和武器的使用有关,也和军事技能的训练有关。
“习手足”,“习”是习练,“手足”是人的手脚。古代的军事训练,包括单兵格斗和阵法操练。单兵格斗,也叫“技击”或“武术”,有徒手和器械两种。它包括手搏(拳术)、剑道(剑术)、射法等。古代的军事体育,角牴(摔跤)、蹴鞠(古代的足球)、博弈(六博和围棋),也属这一类。[9]阵法操练,主要是队列训练。现代的制式动作(如分列式)就是这种训练的遗产。
“便器械”,“便”是便利,这里指熟悉和掌握;“器械”指戈、矛、剑、戟、弓矢等武器。
“积机关”,“积”是储积,“机关”是机械性能复杂,用钩牙、齿轮、滑轮、皮带和绞车操作,带有自动或半自动特点的武器。[10]“机”是器之巧者,“关”是有控制装置。比如攻城守城的各种器械(如弩、炮和楼橹、辒之类),就是这类武器。
“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指用于实战,特别是攻城和守城。大家读一下《墨子》中的城守各篇和宋代的《武经总要》,就会明白,中国古代最先进的武器,主要是用于攻城和守城。
谋略在先,技术居后,这是中国的传统。[11]
谋略的本质是什么?是“诈”。
再说“兵以诈立”
“兵以诈立”是《孙子》原书的说法(《军争》),后人叫“兵不厌诈”。我在北大讲《孙子》,就是用这四个字作我的书名。
什么叫“兵以诈立”?我们要弄清两个概念,什么叫“兵”,什么叫“诈”。这两个字的含义并不简单,对研究《孙子》很重要。
(一)什么是“兵”?
《孙子》全书,第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第一个字就是“兵”。
这个字,现在的出版物,白话翻译本也好,英文翻译本也好,除我,几乎毫无例外,全都翻成“战争”,我必须指出,这样理解并不准确。正确翻法,“兵”是“军事”,不是“战争”。军事的概念比战争大,打仗有军事,不打仗也有军事。
我们要知道,现代汉语的“军事”一词,是从日语借用的外来语,相当英语的military affairs。[12]卫灵公问陈,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军事”就是“军旅之事”,和军队有关的事,中国古书原本就有这个词,也叫“兵事”。[13]
“兵者,国之大事”,正确的翻译是“军事,是国家的大事”。
“军”和“兵”是军人,是军队,既包括人,也包括他们的武器。“兵法”研究的“兵”是武装起来的人,而不是战争。古代训诂,没有以战训兵的例子。
什么是“兵”?古书用法有三个含义:
(1)“兵”是武器,相当英文的arms。“兵”字的本义是兵器,但我们要注意,《孙子》中的“兵”字,没有一处是指兵器。[14]
(2)“兵”是军队,相当英文的army。《孙子》中的“兵”,主要指人,不是军队,就是与军队有关的事。即使不打仗,照样有军事,古人叫“武备”,“武备”也属于军事。
(3)更确切地说,“兵”是用武器武装起来的人,即所谓武装力量(armed forces)。
这种词义辨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战争史,武器的发展太快,令人眼花缭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军事史就是武器史。马克思曾经说,商品世界是个头足倒置的世界。[15]武器的世界也是个类似的世界。
现代兵家几乎等于兵器家。
这里,我们要辨明的是,军事的主体是人,而不是武器。
(二)什么是“诈”?
韩非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这是“兵不厌诈”的出典。
“诈伪”的本义是什么?“诈”跟“作”有关,“伪”和“为”有关,都暗示着某种人为制造的成分。人为制造造什么?一是造形造势,造各种假象,二是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形势重要,心理效果也重要。
在《兵以诈立》中,我曾提到,克劳塞维茨说,弱者比强者更偏爱“诡诈”。[16]这话很重要。但这里我想补充,“诈”分两种,“暗箭”固然是“诈”,“明枪”也可以是“诈”。而且一般地说,两种“诈”总是相互制衡,充分体现出什么叫“不平衡的平衡”。
人们往往容易记住的是弱者的“诈”,而容易忽略的是强者的“诈”,以为强者完全是依赖实力,根本不用“诈”。其实,依靠实力的“诈”同样是“诈”。有一位研究武器史的美国专家说得很清楚,“美国冷战军事思想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其外表太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对手不得不认真对待”。[17]
当代有两种“诈”互相斗法:
(1)核讹诈(国家恐怖主义),苏美两强对抗,主要比武器,比国力(政治、经济、外交的总体实力),古巴导弹危机是典型案例。
(2)恐怖战术,弱对强,实力太不对称。弱方几乎一无所有,只有AK47和“人肉炸弹”,“9.11”是典型案例。
这两种“诈”,都利用对方的恐惧,有强烈的心理震慑作用。前者是靠绝对优势,绝其交援,围死对方,困死对方,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吓倒对方,用武器的优势抵消伤亡,用最小伤亡换取最大胜利。后者是靠不怕死的精神,你怕死,我不怕死,抓住强国和富人的最大弱点,朝死里整。
怕死有怕死的主意,不怕死有不怕死的主意。
《孙子·九地》有两段话,值得玩味:
一段话,是“夫(霸王)〔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一段话,是“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
“王霸之兵”靠的是实力,“诸、刿之勇”靠的是勇气。
唐且使秦,秦王以势压人,霸气十足。他说,你听说过“天子之怒”吗?那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就是“王霸之兵”。唐且只有一个人,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说,那你听说过“布衣之怒”吗?那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这就是“诸、刿之勇”。
这不是血肉之躯和坚甲利兵的悬殊较量,而是人与人的拼死搏斗。
“兵以诈立”还是“兵以器立(或兵以技立)”
战略源于诡诈。中国,兵法挑战军法,兵法脱离军法,“兵不厌诈”是标志。从此才有战略研究。
中国的战略文化最发达。贵谋尚诈,是中国军事学的传统,这反映在兵书分类上。
上面讲兵书四门,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它把谋略摆在技术之上,这就是贵谋的表现。
中国讲谋略,权谋是大计,形势是小计,它是把权谋摆在形势前。
中国讲技术,阴阳和天地有关,技巧和人有关,它是把阴阳摆在技巧前。
这四门,无论谋略,还是技术,都是强调人。武器往哪儿摆?是放在技巧下面讲,跟人搁在一块儿讲,没有独立的地位。
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不能拆开来,片面强调,像相声说的,眼睛和鼻子哪个更重要。“兵法”的“兵”是什么?“兵书”的“兵”是什么?它既是武器,也是军队,两者是结合在一起,要说重要都重要。
大家说武器比人重要,从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武器的进步,武器的革命,突飞猛进,太明显,人有什么进步?几千年都过去了,要从身体看,还是一鼻子两眼儿,没什么进步,不但没有进步,还有退步。武器越发达,人类越怕死。文明人,都是娇气得不得了。
武器发展快,武器真厉害,没错,但大家不要忘了,武器是人造出来的,人不是武器造出来的。武器可以杀人,人也可以消灭武器。消灭武器,才是人类的理想。[18]
可惜,现在的兵学,已经变成兵器学。很多人都相信,由于技术的发达,武器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人,变成废物点心。
人和武器,哪个更重要?这是老问题,不是新问题。
中国古代有个传说,是讲这个问题。据说,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天官叫蚩尤,他是武器的发明者,历代祭祀,号称“兵主”,是个邪恶的战神。蚩尤反叛,黄帝伐之,九战九不胜,非常苦恼。最后,还是靠了两个人的帮助,才打败蚩尤,让他死得很难看。这两个人叫风后和玄女,一男一女,他们有高招。蚩尤有好武器,他们有好阵法(九宫八阵);蚩尤会兴云作雾、飞沙走石,风后有指南车,可以辨方正位。指南车是什么?就是古代的GPS。这是高科技打败低科技。科技可以提高武器的性能,但科技的源头是人。
现在的武器,最厉害最厉害,莫过于核武器。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当时都以为,武器发展到这一步,到头了。这是“终极武器”或“绝对武器”,[19]跟施瓦辛格演的那个电影(《终结者》)一样,它是“终结者”。美国有了这玩意儿,很得意,开始设计他们的“世界议会”,把联合国当自己家开的商店。大家都说,原子弹一出,谁都不用打了,打也没戏。它是“和平之神”![20]但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纸老虎。[21]美国有了原子弹,也害怕,一怕自己下不了手,二怕别人有。而事实上,很快,苏联就有了核武器。武器是传染病,从来如此,现在怎么样?早就把世界传染了。大国都有这个“富贵病”,后边不让排队,但总有排队的。[22]
我说过,Discovery Channel有个节目,就是讲“终极武器”。它说,这种武器,一点不新鲜,人类一直追求这玩意儿,已经不知发明过多少次。
什么是“终极武器”?“终极武器”是人。武器当然可以消灭人,但全称的武器消灭全称的人,这是人类的自杀。
最近,美国打过四场战争。他们觉得,一口恶气,总算喘过来。大家说,美国的武器太厉害,不能不服,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谋”还有什么用?“诈”还有什么用?人还有什么用?现在已经不是“兵以诈立”,而是“兵以器立”、“兵以技立”。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我说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
有人说,打仗如打架。打架,己所不欲,强加于人,看谁拳头硬,看谁拳头大,和打仗一样;除了动拳头,还要抄家伙。没有家伙,怎么行?武器确实重要。
战争,除了短兵相接面对面的肉搏,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躲在武器后面打,谁都想找个称手的家伙,隔老远,就能打到对方,而对方却够不着自己。弓箭,已经包含了这种设计。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武器发明者的共同追求。力量大、速度快、距离长,加精确打击,一样不能少,现在的火箭、导弹,后面还是这一套。
但打架和打仗,毕竟不一样。项羽说,“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就学“万人敌”(《史记·项羽世家》)。“万人敌”才是打仗。打仗是集团性的搏斗,千头万绪,千变万化,没有头脑行吗?人,四肢退化,大脑发达,要开运动会,什么都比不了动物,连参赛资格都未必有。进化半天,就剩这么件东西,你还说没用,这不是开玩笑?
很多人讲人,都是只讲身体,不讲脑袋。
高科技不是科技产品,不是武器,而是人的聪明才智,人的创造发明。科技和谋略的对立是人自身的对立,不是武器和人的对立。它们的关系,只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谋”的意思是战略,战略的意思是对战争全局的通盘考虑。既曰全局,便既有军队,也有武器。科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人说,在核武器面前,道德、勇气毫无用处。什么“二百米内硬功夫”,什么“人的因素第一”,全是笑话。
人,血肉之躯,不用说杀人无数的核武器,就连最原始的武器都抵挡不住,哪怕一根棍子、一块石头都可致人死命,这还用说吗!
武器从媒介和手段变成主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战争,不是人和人打,而是武器和人打,武器和武器打。大家都揣着宝贝,你往天上扔个宝贝,我往天上扔个宝贝,看宝贝和宝贝在天上打。
这类说法,不是笑话,而是神话。我叫“当代封神榜”。
现在,由于武器的发达,有人开始幻想无人战争,不仅天上飞的是无人飞机,而且地上跑的是纳米战士。人还有什么用?这种神话,不但把我们的脑子搞傻,还导致了对战争的美化。从保存自己讲,是“零伤亡”,对国内民众好交代;从杀伤敌人讲,是“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杀死的全是恐怖分子,没一个老百姓,多仁慈。
军队变成医院,杀人的都是大夫。
当代战争给我们描画的前景,不是“没有武器的世界”,而是“没有人的世界”。
然而,再好的武器,也不是神创,而是人的发明。即使现在,最先进的武器,也还离不开人的操作。即使最发达的军事强国,比如美国,也还养着陆海空三军。没有人的战争,目前还没发明。
没有人,武器和武器还打什么劲?那不是闹鬼了吗?
没有人的世界,武器只是废铜烂铁。
兵法,对人类道德的挑战
兵法是杀人艺术,军人是职业杀手,用不着美化。
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离不开用兵,但谁都没法美化它,战争总是受到道德谴责。还有用间,那是“诈中之诈”。刺探情报搞暗杀,总不能光明正大。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谁都离不开间谍,谁都骂间谍,就跟人骂狗一样。
当然,他们都是只骂别人的间谍,不骂自己的间谍。自己的间谍自己疼,自己爱,隐蔽战线、地下工作,对谁都不可少。
《孙子·用间》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在他看来,不是圣人,还不配当间谍。
兵法和道德有冲突,可谓由来已久。“兵以仁立”,还是“兵以诈立”,一直有争论。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和临武君就吵这个问题,一吵就是两千多年。宋以来,很多人说,《司马法》是正,《孙子兵法》是奇。《孙子兵法》不如《司马法》。
荀子的学生,韩非,既学儒术,又学道家,他想区别这两个方面,折衷这两个方面。
韩非讲过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问舅犯(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我军将与楚人交战,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诈之”。同样的问题,文公又问雍季(公子雍,晋文公的儿子)。雍季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意思是“诈”只能收一时之利,却非长久之计。文公表扬雍季,说很好,但采纳的却是“舅犯之谋”。晋国取胜后,论功行赏,照理说,舅犯功劳最大,但文公却把雍季排在舅犯之前。群臣不解,都说“城濮之事,舅犯谋也”,您怎么反而把他排在雍季的后面。文公说,这你们就不懂了,舅犯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才是“万世之利”。孔子听说,大发感慨,说“文公之霸”是理所当然,他是“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呀(《韩非子·难一》)。[23]
中国古代,虽有正奇之辨,道权之辨,儒家总是强调“仁义”高于“诡诈”,军法高于兵法。但在用兵的问题上,没人可以靠道德吃饭。泓之役,宋襄公的死就是教训。从此谁都知道,战争是靠“兵不厌诈”。
这是“兵不厌诈”的出典。
兵法对道德是最大挑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诈坑降卒,一个是血腥屠城。
现代战争,有《日内瓦公约》,有红十字会组织,好像体育比赛,有一套规则。打仗是军人和军人打,不可袭击平民,不可屠杀和虐待放下武器的军人,叫“人道主义”。但打仗是杀人,杀人怎么还讲“人道主义”,一边杀一边救,本身就是讽刺。[24]
况且,就连这么一点儿“人道”,都来得如此不易。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二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那些死者,可并不都是军人呀,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古代战争,诈坑降卒、血腥屠城,全世界很普遍。白起坑长平,英布坑新安,成吉思汗屠城,丰臣秀吉筑耳冢,这并不是多么遥远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就是现代版。
古人为什么会这么野蛮?原因很多。久攻不下,兽性大发,疯狂报复,是一个原因。折首执讯有功,也是常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嫌俘虏太麻烦,太危险。你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几十万人,管吃管喝,疗病疗伤,那是谈何容易?这且不说,光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不容回避。古代,即使赤手空拳,几十万人暴动,怎么防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都杀掉,杀不过来就坑。你只有理解人性的脆弱和人性的残忍,你才能理解,孙子讲“卒善而养之”(《作战》),这在古代有多不容易。
《孙子》这本书,是以说理为主,不是以讲故事为主,人物当然少。他的书,只有四个人:两个是恐怖分子(专诸、曹刿),两个是大特务(伊挚、吕牙)。“诸、刿”是勇敢的象征,“伊、吕”是智慧的化身,都是光辉形象。这对道德,本身就是挑战。
专诸、曹刿,是古代的刺客。《孙子》对他们,一点儿不嫌弃,还很推崇。
这是古风。
古代兵书,讲这种勇敢,不光《孙子》: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吴子·励士》)。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相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尉缭子·制谈》)
《吴子》、《尉缭子》推崇的“死贼”也是恐怖分子。它们都推崇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勇气,甚至说,以五万之众(或三军之众)“为一死贼”,本身就是“王霸之兵”。
伊挚、吕牙是商周的开国功臣,也是古人崇拜的对象。《孙子》以他们为例,要说明什么?他要说明的是,间谍不但很道德,还是道德的化身。不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还不配当间谍,只有圣人才配当间谍。
战争总要杀人,间谍总要不择手段,这种暴力,这种诡诈,谁都骂,先秦诸子都骂,现代的知识分子也骂。但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都不可须臾离之。人类对暴力是又恨又爱,爱恨交织,爱恨之间还夹杂着恐惧。
“兵以诈立”,对军人来说,必须如此。除暴安良,不能不如此。
军人很坦白,仍有古风。
现在,承平之世,《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商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很多人都以为,不流血的政治就是生意,就是买卖。
商人心里想,商场如战场,有竞争就有对手,有对手就有这一套。“商以诈立”、“商以利动”,“商以分合为变”,推广于商,还有问题吗?好像没问题。
但商人也敢这么讲吗?不敢。相反,他们总是说,做买卖全靠诚信二字。
天下有贼,有大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钱包是小贼偷的,金融海啸是大贼闹的。
我是研究兵法和方术的。领袖班、总裁班,他们请我讲课,我发现,他们最爱听两样东西,一是阴谋诡计,二是装神弄鬼。我想,三十六计那一套,他们肯定比我懂。所以,我就不讲了。
我是把《孙子》当兵书读,商战,我不讲。
兵法,对人类智慧的挑战
兵法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有三大特点:
(一)它是在高度对抗中思维。打仗是两军对抗,不是一厢情愿。我方的行动要取决于敌方,敌方的行动要取决于我方。在激烈的对抗中,我变敌变,敌变我变,瞬息万变。任何环节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全局的改变,不可测的东西太多。特别是“人心难测”。“人心”是最大的变量。
(二)任何军事计划,都要落实到行动,在行动中修正,在行动中改变。不管事先有多充分的准备,多全面的调查,多周密的部署,都要跟着形势变。战斗需要的是马上接招,快速反应,而不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思考,只是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判断力胜于理解力。
(三)在战场上,已知总是包裹在未知之中,未知常常大于已知,尽管指挥者都想多知道一点,敌情我情,尽量了解,也做不到算无遗策,“料敌制胜”的“料”只是一种模糊判断,难免带有猜测和赌胜的成分。科学判断只是认识的一部分,整个认识,整个行动,都带有蒙的成分。
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类智慧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人类,在对抗中思维,在行动中思维,而不是像在实验室环境下,像看一只死老鼠那样思维,其实是认知的常态,大部分情况都如此。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道理是对的。人类的思维总有这两部分,但王倪的问题问得好,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庄子·齐物论》)。特别是“不知”,既然是“不知”,你怎么“知”。战场上,百密犹有一疏,再充分的侦察,再周密的预案,仍有很多漏洞。战场很残酷,一个判断做出,错就是错,不允许重复,不允许后悔,死者不可复生,亡国不可复存。这对科学是巨大挑战。
我们这个时代,据说是科学的时代,科学万能,已经覆盖一切。但即使今天,我们也得承认,科学只是思想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大家习惯说,那叫迷信。
兵法是科学还是迷信,这对科学史是个挑战,对思想史也是挑战。
我们都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绝对开不起任何玩笑,不讲科学怎么行?但科学之所以叫科学,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它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屡试不爽可以重复的东西。《孙子》说,“兵无恒势,水无常形”(《虚实》),怕的就是重复,上一次管用,下一次照搬,是兵家的大忌。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是屡试不爽。
军队是最讲规则的地方,“军令如山”,必须服从,绝对服从。而兵法又是个挑战规则的东西,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最像赌博”,[25]我也讨论过“卜赌同源”。[26]占卜当然是迷信。
兵法是研究测不准的东西,研究测不准的东西,在古代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占卜也是研究测不准的东西。
古人的思维,科学和迷信总是搅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只是迷信的一部分。你别以为,这是讲古人的脑瓜。今人的脑瓜也是如此。比如赌马、摸彩票、预测足球,科学是要大打折扣的。
有未知,就有对未知的猜测;有对未知的猜测,就有迷信。
研究战史,总结成败,把流血的经验写成兵书,这是“沙里淘金”。
沙里淘金。金子被淘出来,才叫金子,没有淘出,只是沙子。金子是沙子中的精华,没错,但不是沙子的总体。沙子才是总体。
思想史是“沙子”史,“沙里淘金”史,不是“金子”史。
科学只是思想的一部分。
兵法,西人叫Art of War,Art是艺术。军事学是艺术还是科学,一直有争论。
其实,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里面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也有可以称为艺术的谋略。
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涉及各种军事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第一层次)。
军队的战争筹款、军事预算,还有管理和训练,属于社会科学(第二层次)。
指挥艺术是小战略,政治艺术是大战略,属于战争艺术(第三层次)。
艺术才是处于最高层次的东西。
怎样读《孙子》
兵书作者,大多是“冷眼旁观者”、“事后诸葛亮”,他们可能是政治家,可能是参谋人员,可能是随军记者(类似体育教练和体育记者)。真正的军人,特别是战斗在一线的指战员,一般都不写兵书。
读兵书的,就更是旁观者。
我是旁观者。
我读兵书,主要是两个角度,一个是军事史,一个是思想史。商战、管理类的推广,不属于我的讨论范围。这种学问,是日本人搞出来的,很像“文革”的“活学活用”(他们还有《兵论语》一类傻书)。凡是研究这类学问的,大都无师自通,不必用《孙子兵法》装门面。
阅读《孙子》,我有七点建议:
(一)《孙子》的精髓是谋略。研究谋略,最好读战史。西方兵法,最重战史。古典时代是以战史为兵书,现代兵书也喜欢凭战例讲话。谋略是求生术,死里逃生术。兵法是无数流血经验的总结。不知死,焉知生。血的教训,写进战史,谁敢不重视?我国也重视。我国军人读兵书,也要结合战例。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战史,中外兵书,最好对着读。比如西方传统,重兵器,重实力,重勇气,重财力,重技术支持,重海外扩张,有一股凶蛮之气。他们喜欢强调的东西,往往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东西。我们贵谋尚诈,没有这些过硬的东西,谋、诈就被架空了,两者可以互补。
(三)兵法有主客之分、攻守之异,《孙子》尚攻,《墨子》尚守,不一样。孙子和克劳塞维兹也不同,克氏尚力,强调先兵后礼,孙氏尚谋,强调先礼后兵。这些都是正规战。毛泽东兵法强调非正规战。游击战和持久战,都是弱势兵法。弱势兵法更强调诡诈。我们要注意,《孙子》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兵法。
(四)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军、民的界线被打乱(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就已出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是轮着用。《战争论》注意及此,才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说。战略变成大战略。《孙子》论兵,牵涉多广,有君、将关系,有军、民关系,有军赋和出兵的关系,有伐谋、伐交、伐兵的关系。我们要注意,他的谋略也是大战略。
(五)读《孙子》,大家最陌生,可能莫过于其中的兵阴阳说。比如它讲地形,比如它讲火攻,都牵涉到这方面的知识。碰到方术知识,碰到方术术语,怎么办?大家可以学一点方术。方术是古人的自然知识,天文、气象、地形、地貌,都属于这种知识。我写过两本讲早期方术的书,[27]大家可以参看。
(六)《孙子》讲武器,讲装备,主要集中在《作战》、《谋攻》两篇。讲野战,重装备有马车、牛车,驰车、革车,各种战车;轻装备有甲、胄、戟、盾、矛、橹(蔽橹)、弓矢和弩。讲攻城,有楼橹、辒、距堙。《火攻》篇讲的“火”,也属于广义的武器。研究《孙子》,还要有兵器史的知识。武器属于兵技巧。
(七)兵技巧,还有个方面是技击和体育。技击(武术),包括手搏(拳击)、角牴(摔跤)、剑道和射法。体育源于军事训练,比如奥运会,田赛径赛、五项全能,追根溯源,全是军事训练。我国也如此。中国体育,射箭、投壶、蹴鞠(足球)、博弈(六博和围棋),也和军事有关。战争充满狂热,体育也充满狂热,和平时期,体会战争,最好的代用品就是体育比赛。
但我们不要忘记,战争可不是“公平竞赛”。
[1]参看: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作者说,“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5页)。他是把政治哲学定位于“坏世界研究”。他说,“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1页)。该书即以《哀公问》的这段话作为题词。
[2]原话有两种翻译,一种是“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一种是“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7页。案:“政治”(politics)一词是源于“城邦”(polis)。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动物”其实是“城邦动物”。
[3]赵汀阳说,“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兵法’;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法理’”(《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页)。
[4]中国古代的法家,往往也是兵家。有趣的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写了《君主论》,还写了《兵法》。
[5]自古以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严密的组织手段,最聪明的思想方法,都是首先用于战争。
[6]参看: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收入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7—105页;何炳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收入所著《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35页。
[7]参看: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卷三,6页。
[8]李零《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03—104页。
[9]大家都说,奥林匹克精神是和平的精神。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奥林匹克的所有运动项目,几乎都与军事有关。
[10]我国古书中的“机关”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器官,如《鬼谷子·权》“故口者,机关也”;还有一个意思是自动或半自动的机械,如《论衡·儒增》说的“木鸢”,就是用“机关”操作。日语是用“机关”(kikan)翻译英语的organ,用“机关炮”(kikanko)翻译英语的machine gun (汉语作“机关枪”),用“机械”(kikai)翻译英语的machine。现代汉语的“机关”和“机械”是借自日语。
[11]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几乎不谈武器。有人说,这是“哲学家的失误”。参看:罗伯特· L·奥康奈尔《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卿劼、金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226页。其实,任何以谋略为主要对象的书,都不会把武器放在第一位。
[12]现代汉语,“兵制”改叫“军制”,“兵法”改叫“军事学”,“兵书”改叫“军事著作”,很多“兵”字都换成了“军”字。许保林先生提到过这一现象,他以为,这是因为现代汉语的“兵”字含义缩小,无法概括所有军事问题,见他的《中国兵书通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5页。其实,中国的现代科学术语多借自日文。这是由翻译引起,而不是其他原因。
[13]这两个词频见于《左传》、《周礼》和《史记》、《汉书》,含义很清楚,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指军旅之事,只有“兵事起”(如《史记·田叔列传》)或“兵连祸结”(如《汉书·匈奴传》)这样的话,可以把“兵”字解释为战争。
[14]上世纪70年代,我到齐思和教授家请教。他问我,顾炎武说,先秦古书的“兵”字都是当武器讲,秦汉以来才当士兵和军队讲(《日知录》卷七),对不对?现在我的回答是不对。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四节《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87—101页。
[16]参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一卷,216页。
[17]罗伯特· L ·奥康奈尔《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403页。
[18]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的武器都是内置,上天所赐,与生俱来,无法解除武装;人类的武器都是外置,完全可以销毁。
[19]弗雷德里克·邓恩等《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20]这种“和平”,当时的意思,是美国少死很多人,后来大家才悟过劲儿,给它加了定语,叫“恐怖的和平”。
[21]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1189—1194页。
[22]冷兵器时代,弓弩一度是“终极武器”,但一经传染,也就不成其为“终极武器”。后来,火药发明,火器也是如此。核武器是不是“终极武器”?也不是,除非它把人类杀光。
[2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晋文公问“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的回答是“诈”。克劳塞维茨也说,弱者比强者更偏爱诡诈。
[24]这类“人道”,后面有中世纪的武士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2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一卷,41页。
[26]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5—20页。
[27]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0001
- 0001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