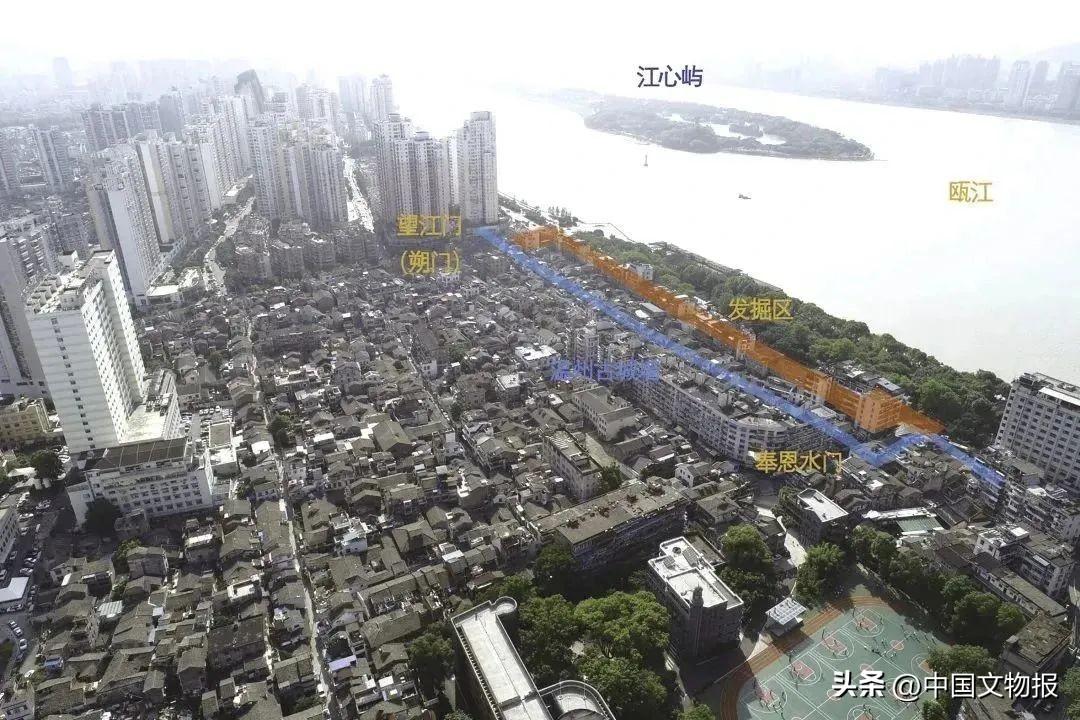何炳棣|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二)
二、氏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构成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6],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两面,二者间存在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关系。事实上,人类学理论也认为只有将二者一起研究才能收相得益彰之效[7]。
我国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分布最广、延续最久、文化堆积最厚、已发现遗址最多。内中保存最好的是西安附近的半坡和临潼姜寨等聚落遗址。对这类型聚落布局的中心意义,资深考古学家苏秉琦有代表性的看法[8]:半坡、姜寨那种环壕大型居址,其中以大房子为中心,小房子在其周围所体现的氏族团结向心的精神,以及居址之外有排列较整齐的氏族墓地……说明氏族制度发展到了顶点。
仰韶聚落布局中最能反映宗教信仰的是墓葬方式。诚如著名《西安半坡》专刊撰者石兴邦所综述,在已经系统发掘的仰韶遗址中,一般成人尸体有条不紊的排列方式反映每个家族或个人在氏族中最后都有应占的归宿和位置。尸体大都头向西方或西北方。墓葬方向可以认为是“祖先崇拜和灵魂信仰的表现之一”,因为“墓葬方向的选择和决定,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相当严肃而慎重的”[9]。数量上次于仰身葬的二次葬似乎也反映当时的信仰:要等到血肉腐朽尸骨正式埋葬之后,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小孩死后一般都举行所谓的“瓮棺葬”,这类陶瓮通常都放在居住区,不葬在墓地:瓮顶留一小圆孔以供灵魂出入,继续承受母亲关爱之用。
近年仰韶精神文化研究有多方面突破性的诠释。首先,半坡彩陶中最重要的鱼纹饰已不能再像1960年代那样释为图腾了。因为半坡和姜寨文化上确有血肉的联系,两处彩陶中共有鱼、蛙、鸟、鹿多种动物纹饰;此外,两处遗址都发现大量多样的捕鱼工具,说明鱼是当时人们经常的美食。这些都与图腾理论冲突。比较合理的新解释是:鱼,特别是抽象的双鱼,是女阴崇拜的表现;而姜寨那种体内充满卵子的蛙的图案,也是象征生殖能力的崇拜[10]。早在1946年,闻一多先生在遇难前数月撰就的《说鱼》一文里已经阐发鱼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一向是“匹偶”、“情侣”的隐语,因为“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11]。
生殖能力的崇拜完成了祖先崇拜必具的三个时式:过去、现在、未来。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早期45号墓发现三组以蚌壳摆塑的图案。古文字和天文史家冯时具有说服力地说明第一组墓主人两旁的龙虎图案是后来发展完成的二十八宿“四陆”中的“二陆”——苍龙和白虎;墓主尸体下边移入的两根胫骨代表“北斗”。墓形反映当时已有天圆地方的说法。总之,第一组蚌壳图案可以认为是二十八宿宇宙观的滥觞[12]。张光直先生提出第三组图案中的龙虎鹿正符合《道藏》中保存下来的原始道士的“三蹻”——巫师骑乘上天下地与鬼神交通的媒介;并认为这样早的巫觋宗教(或称萨满教Shamanism)证据,“对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上有无匹的重要性”[13]。
西水坡45号墓中惊人的天文知识和具有高度魔术幻想力巫觋宗教的结合,强有力地说明该墓的主人已不是平常的氏族长,甚至也不仅是张先生认为的巫师,而是一部落酋长般的人物了。夏代的建立者大禹不就是以“巫步”闻名于后世、三代权位最高的“王”还不一直兼有大巫或大司祭的职能吗?西水坡的“三蹻”也正说明半坡、姜寨同期文化里亦有巫觋的存在。那种由圆形黑白(阴阳)人面向头顶、两耳、两颊外射的五条或三条三角形鱼饰的神秘图案,还不是巫师的有力证据吗?半坡、姜寨相隔50公里,而半坡陶器上的字符却出现于150公里外合阳莘野村的同期仰韶文化遗址。这样长的宗教、文化交流半径似乎在说明这已不仅是氏族间,而是部落间的交流了。
仰韶人民虽然崇拜多种自然神祇,但由于聚落布局中居住区和墓地同是组成部分,生者累世相信不时可获逝者灵魂的佑护,而逝者又需要生者不时祭荐,祖先崇拜很可能在整个宗教信仰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
上承仰韶、下启三代的龙山时代(大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出现了一系列多姿多采的区域性文化。它们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发展虽各有各自的特色和步伐,而且华夏中原地区的文化在此时期并非处处领先,但各文化间千年之久的双向吸收和反馈却使它们大致朝向同一方向演进:祖先的神灵随着部落的扩展渐渐变成部族至高的保护神:政治权威和等级社会的出现加速了氏族制度的蜕变。
最能显示龙山时代多方面演变的是玉器群和礼器群。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的大本营远在浙西太湖以南,其玉器群最有代表性。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即已有象征军事统辖权的玉钺和宗教重器玉琮的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玉制神兽、神鸟、兽面或兽身的“神人”和“神徽”。这些“神人兽面纹的普及和规范化,说明在其通行的地域内,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原始信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对至高无上的神人的崇拜,实际上是从信仰意识方面,统治者起到了维护独尊地位的作用”[14]。稍后辽西红山文化中也具有地域特色的玉器群,再稍迟山东海岱区系的玉业也开始形成独特色格,“并给予三代玉器以深远的具体的影响”[15]。
陶制礼器群以山西襄汾陶寺类型最富代表性。礼器中除为设奠用的桌子是木制的,其余陶制的各种炊器、食器、酒器、乐器等类不但式样功用各各不同,而且严格地反映这些随葬品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不同。“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陶寺早期已初具规模。……墓中的礼器和牲体已成为墓主身前权力和地位的标志。……在形成三代礼制的过程中,中原处于核心地位。”[16]
山东龙山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有重大的突破。寿光边线王城发现边长240米,面积57,000平方米的外城和配套较小的内城,并发现祭奠所用的猪牲、犬牲与人牲。而城子崖的城东西约430米,南北最长530米,面积大约200,000平方米(即1/5平方公里、50英亩、相当公元13世纪英国首都伦敦城的1/6)。高广仁教授认为这已不是单纯军事防御性的小城堡,而已是“具有永久性统治权力中心的都邑性质”。这样规模的城和10米宽夯筑墙体,“除非靠大量的强制劳役,否则是难以完成的”。此外,泗水尹家城和临朐朱封大墓内的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上财富分配不均,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17]。
综结以上,龙山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说明当时氏族内部已有社会分化,造成了贫富分配不均和等级化的身份制度萌芽;宗教方面,祖先崇拜已提升到以部族至高祖宗神为对象。这些现象与传说中炎、黄大部族同盟,英雄魅力式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大体吻合的。
有关夏代的考古资料仍在多方慎重鉴定中。从君主世袭的观点看,夏不愧被称为朝代。但“所谓的夏朝,实际上是以夏后氏为盟主,由众多族邦组成的族邦联盟”[18]。《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古籍中所谓的诸侯和万国,实际上是由众多部族所构成的“邦邑”。笔者此处必须指出,极大多数中国古代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所借用的古代希腊“城邦”(city states)一词甚不妥当,容易引起错觉。古代希腊polis一词虽英译作“城邦”,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原著的较慎重英译往往作为community“(政治)社群”。公元前第5、4世纪的希腊城邦,除了雅典和科林斯(Corinth)外,商业都不发达,都是以农立国的。其首都的主要部分是宗教及政府建筑,所以全国连首都也不是具有复杂经济活动的“城市”。这种政治社群的最大特色是遵守法律,保持极严格的公民籍,所有公民都是成年男子,都有直接选举、参政、充陪审、服兵役的权利与义务。雅典丰富的碑刻资料证明,不但最高长官按期由公民选举,而且一般公民一生之中至少有一两次轮充官吏的机会[19]。雅典这种草根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精神、意识,与夏商周的家有世袭的邦邑(patrimony)制确有基本的不同。
商代武丁以后的大量卜辞也显示氏族邦邑林立的情况。已故丁山教授于1940年代中曾对甲骨骨面、骨臼、甲冉、背甲等部位非占卜的刻辞纪事做了原创性的考释和统计。这类卜辞纪事包括为商王侍夜之“妇”的“氏”名、王畿内外人都为王守夜氏族之名及其人数等等。这些纪事虽属片面性质,而氏族之可确定者已达二百左右。因此,丁山做了两个综述:(1)“殷商后半期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2)“商代所封建的氏族,都就其采地中心建筑城邑,也可名之曰‘城主政治’。”[20]此说高明之处在用“城主”而不用“城邦”一词,因为城邑及其郊野是“主”世袭私有的“产业”,“城主”就是诸侯,如果借用古代希腊城邦一词就与“城主政治”实际的宗教、政治、制度、意识内涵大相径庭了。
近年商周史研究方面可喜的成果之一是对有关商代姓、氏、宗族制度的一些错觉的澄清。其中最重要的是纠正了王国维著名的《殷周制度论》的看法——殷周制度最基本的不同是殷商没有西周式的宗法制度。实际上,武丁以后王位传子的原则已经确定,大宗、小宗之分已相当明显,类似西周的宗法制已经存在[21]。换言之,西周的宗法制对商代的姓、氏、宗族制不是革命性的改变,而是系统化、强化和大面积的推广与应用。
宗教方面,商王虽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风、云、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确已取得压倒的优势。自然神祇的祭祀有一定的季节或日期,而商王室和王室贵族的“周祭”——由五种祀典组成的,轮番周而复始地对各世代祖妣的祭祀系统——却是终年不断地排满了三十六旬,偶或还有必要排到三十七旬[22]。这是祖先——广义的“人”——已成为宗教体系重心的铁证。
此外需要一提的是商人邈远的始祖(帝)喾随着商部族力量的扩张和商王朝在中原威望的建立,已逐渐变成了人类的至上神。卜辞中称之曰“帝”,但商人也称之为“天”。据笔者年前的考证,海内外不少学人认为“帝”是商人的至上神,“天”是周人的至上神,“帝”与“天”对立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周族文化落后、羽毛未丰、臣服事殷的期间已把商族的宗教、祖宗、至上神全部引进。这正说明何以周代文献所述古代谱系里商周两族是同祖的[23]。
西周才开始有了文献,两周金文又可与文献不时互证,因此我们对周代宗教及氏族制度所知较史前和夏商两代更为深广。兹摘要分述如下。
(1)《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经,是指吉、凶、宾、军、嘉五类的礼,极大部分的祭祀都属于吉礼,所以最为重要。近年一篇根据西周金文极具功力之作,一方面指出西周二十种祭礼之中,有十七种祭名与商代一致,这说明《论语·为政》“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是大体正确的;但另方面证明西周祭祖礼的重点和精神与商代有重要的不同:西周王室特别注重“近祖”。金文中最重要的“禘”礼晚周皆释作“追远尊先”始祖之祭,事实上不免有儒家猜测成分,与西周史实不符。西周金文中除了康王祭文、武、成王三代以外,其余诸王所祭俱以祖考两代为对象,并无追祭三代者[24]。这种重心的转移反映西周王室对祖先崇拜的想法越来越“现实”。
(2)周王室和各级贵族祭祖的宗教仪节也反映同一趋势。《礼记·礼器》:“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尸”是受祭者的后嗣,在祭祀中扮演神(鬼,受祭者)的角色。由于周族的昭穆制,“尸”一般是受祭者的孙子。周初祭祀最主要的对象是文王,祭文王时嫡孙成王充“尸”。在全部仪节中,“尸”不但威仪棣棣地坐着受膜拜,并接受多道酒肉蔬谷的奉献,“尸”还随时都向与祭者招呼还礼,最后还通过专职通神司仪的“祝”,向子孙作以下这类嘏辞:“承致,多福无疆,于女(汝)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25]生性是浪漫诗人、艺术家,喜道家的超越、厌儒家的现实的闻一多先生,曾作以下的案语[26]: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质的存在。惟怕其不能“如在”,所以要设“尸”,以保证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实性。这态度可算执着到万分,实际到万分,也平庸到万分了。
究竟是平庸还是智慧,尚有待深究。从立尸之礼和闻先生的案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史上从来没有比古代华夏宗教更“人本”的了。
(3)讨论周代宗教,不能不涉及宗庙制度。晚周文献所述周代宗庙制度甚详。《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而《礼记·丧服小记》却说:“天子五庙。”征以西周诸王禘祀限于两代近祖,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制》之说可能代表战国儒家对古制的夸张。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很多的士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建造维修一庙。但对古制的夸张和整齐化并不影响我们对宗庙制度功用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周族远祖古公亶父初建都城之时,最早动工的建筑就是宫室和宗庙[27]。周族强大克殷前后所营建的几个京城和别都的设计,无一不以宗庙宫室为核心。开国的诸侯,始封的大夫,营建都城时亦无不如此。庙与寝前后接连,庙是祖先神灵之所居,寝是今王的经常住处。庙也称为室,既是祭祀系统的中枢,又是朝觐、聘、丧、射、献俘、赏锡臣僚、会合四方诸侯等重要典礼举行的场所。一切军国要政必告于庙。生者与逝者之间世代永存一种双向关系:生者经常以祭祀方式向祖先报恩,祖先经常对后代庇佑降福。人鬼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宗教所不能比拟的。
(4)周代宗庙制度,以至全部宗教、政治、社会体系,无一不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之上。周代宗庙制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克商以前的远祖公刘。《诗经·大雅·公刘》追述公刘率领部族迁居于豳,有“君之宗之”一语。《毛传》曰“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是正确的解释。但这雏形的大宗之制在克商以前颇有例外。武王克商以后,原自西土的周族不断向东发展,疆域和人民都有了革命性的扩张。但武王逝世后,成王幼,三监叛。各地区殷人势力仍很强大。在严峻的情势下,周族最高领袖周公急切需要一个对广土众民的高效统治网;组成每个商周贵族阶层统治网的基本单位是宗法氏族,而树立全域性宗法体制的先决条件是创建天子制度。虽然现存《尚书》自尧以降君主皆称天子,笔者近年的考证,肯定了天子之称始自成王。经过周公、召公周密的筹划,在周公“保文武受命”的第七年春,在刚刚营建完成的洛邑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多民族大集会,充大司仪的召公重申商王纣失德遭天罚,天命转移到成王。当这庄严仪式达到戏剧性的高峰时,召公才点出主题:“有王虽小,元子哉!”作为“天”之“元子”或嫡子,成王当然即是人间至尊的天子。
天子制度成立的意义,笔者曾作以下的分析[28]:(1)成王是承继祖德(广义包括周民族的德)才被皇天指定为新的“元子”,元子就是嫡子,从此王位(诸侯、大夫等同此)承继以嫡成为大纲大法。(2)天子为人间之至尊,其至尊的地位自此取得宗教及政治的双重意义。(3)天子制度之确定也就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确定。天子为天下之大宗,当然是所有姬姓诸侯之大宗,姬姓诸侯对天子而言都是小宗。小宗对大宗必须无条件地臣服。据《荀子·儒效》,周初封建诸侯七十有一,其中五十三国的君主都是姬姓。所以宗法制度具有对周王室统治自征服得来的,大大扩充的疆土与人民控制网的功用。(4)在各邦国之内,诸侯为大宗,大夫为小宗。按嫡庶而分,层层推展下去,这大、小宗制一直达到统治阶级最低“士”的层面。于是金字塔式的封建社会每层都由大宗控制小宗,这种控制都具有血缘、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的多重性。
而对于异姓之国的统御,早在七十多年前王国维就指出[29]:……异姓之国非宗法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
宗法制度的宗教体现就是宗庙制度。宗子既是总揽大权的宗法氏族长,又是主持祭祀的“宗庙主”。其余所有成员依长幼尊卑在宗法氏族中的“龛位”,也就是在宗庙祭祀系统里的位置。此外,宗法制度与族墓制度又是牢不可分的。生者既然聚族而居,逝者当然是聚族而葬;埋葬的位置照例是取决于生前在全族里辈分和等级的高下。
宗法制度虽是极高度发展的血缘组织,由于累世聚族居于采地,所以又具有顽强的地缘性。结合岐邑、周原、丰、镐等都城附近的考古与西周金文资料,“这些世族的聚落包括族长和族人、家臣居住的村落及其周围的土田、作坊和族墓地,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胞体,从本质上分析,非常类似史前社会的原始聚落。前者是由后者发展而来的,它是血缘胞体在商周社会更高的历史阶段上的再现”[30]。
这就无可避免地引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恩格斯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三大演进阶段——事实上政治人类学用不同的术语也得到类似的看法——却并不符合中国史前和有史早期的历史经验。结束本节之前,笔者认为对此理论问题有略加检讨的必要。
虽然当代西方一般政治人类学家讳言恩氏学说,笔者却深深感到比较后起的政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却与恩氏三阶段说大体上不谋而合。恩氏的“家庭”相当汉译的“原始氏族公社”,亦即人类学家所谓的,以纯血缘关系构成的、温暖亲切、几乎没有剥削的亲属制(kinship system)社会。恩氏“私有制”阶段大体相当人类学家所谓的非亲属制度的、开始具有明显政治性、剥削性的阶级社会,大体上相当恩氏的部落联盟阶段。恩氏与人类学家的“国家”并无基本的不同,都是强制性更高、比较更广土众民的政治实体。至于促成由第一到第二阶段间“量子式”跳跃的因素,政治人类学家认为是由于同一有限空间人口不断繁衍使得亲属制无法解决部落间的人事纠纷和利害冲突;换言之,亲属制已丧失其原有的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veness)。用汉译恩氏术语表达,这就是“原始氏族公社的瓦解”。尽管前者与后者术语及表达方式不同,这次跳跃的社会制度意涵是相同的:血缘的链环被政治性的地缘链环所代替[31]。
但在古代中国,血缘的链环始终未被政治性的地缘链环所代替。相反地,恩氏三大阶段是通过血缘氏族本身的地缘化、氏族内部族长的集权化、氏族功能的多样化和氏族内部及百百千千氏族之间权力名位的等级化等程序而完成的。武王克商之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姬姓宗法氏族大规模武装拓殖性的迁徙,也是氏族血缘和地缘性的重新结合与强化。与这种制度方面的发展大体平行的是祖先崇拜的演化。这种最高度发展的父系亲属制度和祖先崇拜是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此义在本文结语中将再扼要发挥。
注释
[6]杨希枚,《再论先秦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重新指出一般学人对先秦“姓族”“氏族”(clan or gens)二词仍混淆不清。姓族是血缘亲族团体,氏族是“邦国采邑之类的政治领域集团”。此说有其重要性,但西周有些氏族,虽是政治集团,却具浓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由于西周以前,特别是史前时期“姓族”、“氏族”很难分辨,更由于“氏族”和“氏族公社”这类名词通行已数十年之久,不能不继续应用。《辞海·氏族》条:“也叫‘氏族公社’,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公社制和社会基本单位,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初为母权制,约当新石器末期开始过渡为父权制。……”
[7]E.E. Evans-Pritchard,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11.
[8]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页6。
[9]征引自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同上书,页97,是原则性的概论,并不专指中原龙山文化。
[10]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1]闻一多,《说鱼》,《神话与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结语,页134—135;及《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页81—116。
[12]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13]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64本第3分(1993年12月),征引语在页622、623。
[14]任式楠,《中国史前玉器类型初析》,《中国考古学论丛》,页126—127。
[15]邵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说》,《中国考古学论丛》,页6、131。
[16]征引自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页100—102。
[17]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中国考古学论丛》,页68—70。
[18]周苏平,《夏代族邦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页131。
[19]根据大量碑刻研究古代雅典民主政制基层结构与运作最严谨的著作是:James S. Trail,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Attica: A Study of the Demes, Trittyes, and Phylai,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he Athenian Counc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J. Rhodes, The Athenian Bo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0]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全书,特别是页32、44、54。
[21]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特别是此文的前半,页296—310。
[22]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3]详见何炳棣,《“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1期)。
[24]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全文,特别是页497。
[25]《仪礼注疏》(台北《四库全书荟要》本)卷15,页958,郑玄注中所拟的嘏辞;因其辞义部分根据《诗经·小雅·楚茨》,而此诗《毛传》认为是刺幽王思古之作,可能与西周一般嘏辞同一情调。
[26]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诗与神话》,页149。
[27]“作庙翼翼”,《诗经·大雅·绵》。
[28]何炳棣,《原礼》,《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
[29]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上海古籍书店:《王国维遗书》,1983年重印本)卷1,页33。
[30]卢连成,《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代、西周都城形态的考察》,《中国考古学论丛》,页237。
[31]笔者近年撰文不时须声明文章是在完全缺乏汉译马、恩著作的条件下完成的。这对笔者造成很大的不便。西方政治人类学著作的数量已相当可观,此处仅提出两部:一般理论方面,Georges Balandier,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据笔者所知,这位法国学者可能是唯一政治人类家坦白承认恩格斯影响深远的;特别是页156—157。根据非洲及大洋洲近、现代较原始社会调查资料、可读性较高的著作是Eli Sagan, At the Dawn of Tyranny: The Origins of Individualism,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the State(New York: Knopf, 1993)。
- 0000
- 0001
- 0004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