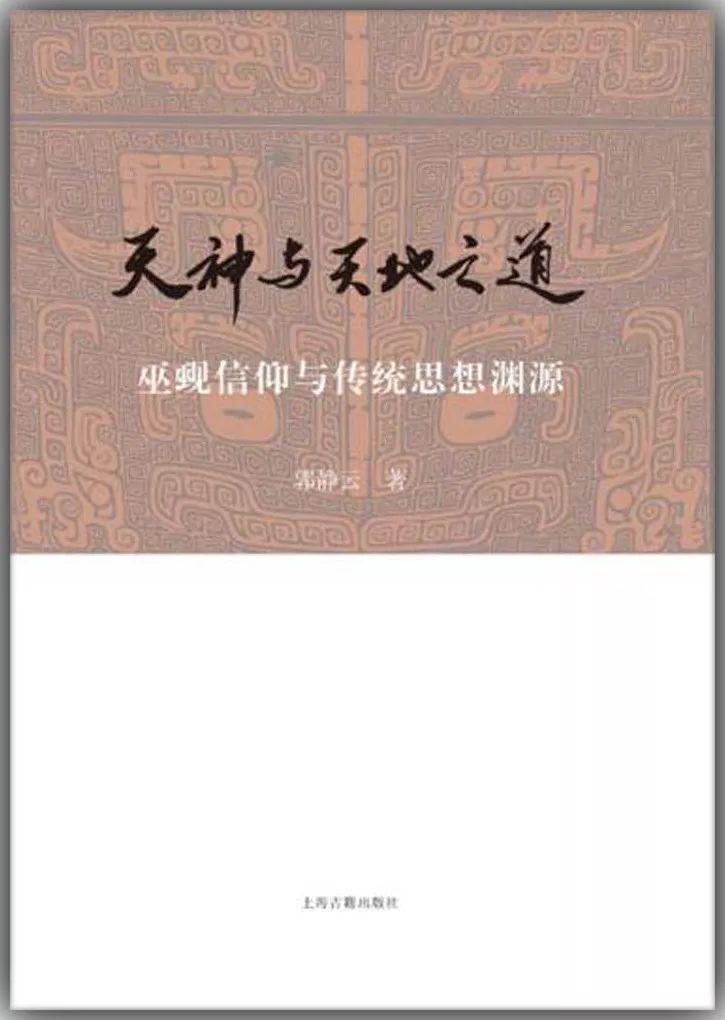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与古国风俗考——时代背景与考古新证
摘要:喜马拉雅丝绸之路(唐代丝绸之路“东道”)的开启是以一系列高原王国(吐谷浑、吐蕃、泥婆罗、大羊同)之间、高原王国与唐王朝之间的和亲为背景展开的。王玄策官方使团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往返印度,并对高原王国大羊同、小羊同有了深入的了解。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和浪卡子县汉晋墓葬的发掘提供了研究大羊同和小羊同丧葬习俗、文化交流的实物材料。唐代丝绸之路“东道”的凿通对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喜马拉雅地区仅通过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进行“物”交换的局面,贯通高原南北,成为连接中原与印度的主动脉,并成为官方使团经过的重要通道,实现了“人”的直接交流。
关键词:高原丝绸之路;大羊同;小羊同;象雄;王玄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唐时期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4BKG015)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的山脉河流多为东—西和西北—东南走向分布,在吐蕃时期以前,除了横断山区之外,高原交通与交流多是以东—西方向为主导。因此南—北方向纵贯整个高原的交通路线,注定是所有路线中最为困难和充满挑战的。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古代人群沿东—西方向的跨区域沟通和交流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已经开启,来自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岩画要素通过拉达克的狮泉河通道向东深入影响到藏西阿里地区。汉晋时期,汉文化沿河湟谷地向西延伸到青藏高原的东北缘,这一通道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来自遥远的中原汉地的丝绸、茶叶、漆器等物品,辗转输入到西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吐谷浑时期青藏高原北部地区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完全打通了,柴达木盆地周缘作为东西方连接纽带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北部的河西走廊,成就了该地区在古代历史上的初次繁荣。青藏高原的北部和西部这两个在地理上最接近丝绸之路主干道的区域,均表现出以东—西方向的文化交流为主导、并在发展程度上领先于高原其他地区的态势,这是青藏高原吐蕃之前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吐蕃时期纵贯南北方向通道——唐初文献称之为“东道”——的打通,毫无疑问是青藏高原古代人类活动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它打破和跨越了自然形成的多重高山峡谷屏障,并非简单地沿河流、山谷形成人群迁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与晚期沿东西方向打通横断山脉而形成茶马古道的情形非常类似。由于难度太大,它必须是由官方组织、投入大量的资力、并由多方共同合作才能够开通和维护。而一旦开通以后,其产生的影响必定是极为深刻的:一方面,“东道”为东亚的官方使节、僧侣和商队开辟了一条除以往的陆路和海路之外第三条通往南亚的通道,而且这条通道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另一方面,从整个人类的探索史来看,这也是首次由官方组织完成的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峡谷通道的壮举,是人类挑战极端恶劣环境、打通最难逾越的天然屏障以实现跨文明交流所创造的奇迹。
一、“和亲之路”的开启
纵贯高原南北的丝绸之路,以往习惯被称为“唐蕃古道”或“唐—蕃—尼古道”,这一称谓将重点放在了唐朝与吐蕃的沟通和交往上,实际上忽视了这条路线所发挥的连接东亚和南亚文明的作用。与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有所不同,穿越喜马拉雅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实际上是当时东亚和南亚文明互相慕求接触和互联互通的时代产物,是丝绸之路的两端及其经行区域多个统治集团的通力合作才得以实现的。
在公元640年前后,东亚和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对穿越喜马拉雅交通路线的开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缘起当是640年玄奘与摩伽陀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的会晤,玄奘“言太宗神武”,戒日王遂遣使通大唐。641年使节至长安,唐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戒日王复遣使者随入朝[1]。这是中印之间首次互通使节,但其具体路线缺载,无法确知双方是否穿越了青藏高原。但自此以后王玄策的三次衔命出使印度(643年、647年、658年)[2],都经青藏高原往返,并在第三次出使期间,在今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嘴留下著名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3]。
王玄策在二十年间数次往返印度,这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说明虽然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充满挑战,但相比“自古取道迂回,致成远阻”[4]的传统陆地丝绸之路,不能不说是一条直通南亚的捷径,而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成功得益于当时高原诸国之间及其与唐王朝之间所创造的睦邻友好的政治环境。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和南部的吐蕃分别与大唐通过和亲建立了甥舅关系,吐蕃与大羊同(象雄)、泥婆罗(尼泊尔)也分别以和亲政策加强了交往,因此纵贯高原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和亲之路”。
639年,吐谷浑国王诺曷钵亲自到长安迎亲,640年唐太宗令宗室女弘化公主嫁于诺曷钵,令淮阳郡王李道明和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持节送亲。弘化公主是唐朝外嫁少数民族、实行和亲政策的诸多公主之中的第一位,在高原上产生了一系列联动反应。在同一年,松赞干布派遣吐蕃大相禄东赞前往大唐求亲,于次年(641)迎娶了文成公主,李道宗持节送公主到吐蕃。与送亲队伍同行的很有可能有前述大唐派遣出使印度的云骑尉梁怀璥[5]。639年,也就是吐谷浑向唐朝求亲的同年,松赞干布迎娶了泥婆罗国王鸯输伐摩的女儿尺尊公主(布里库蒂)[6]。再加上在644年之前,松赞干布的妹妹萨玛嘎嫁于象雄王李迷夏,此后松赞干布又迎娶象雄王妃黎娣缅、弭药(党项)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等[7],到7世纪40年代初,青藏高原诸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交融、和合为一家的历史局面,从大唐经吐谷浑到达吐蕃和羊同,再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尼泊尔和北印度,必经之路上的几个政权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合作,打通高原通道的人为障碍已经不再存在了。643年,当玄奘完成取经伟业从北印度启程返回大唐之时,王玄策作为副使从长安踏上了出使北印度的旅程。可以想见,王玄策的使团在一开始便可能具备了安全和后勤上的充分保障,并在第二次出使中遇到突发危机时能够顺利获取吐蕃和尼泊尔的军事支持。
和亲之路使得自长安经吐蕃、尼泊尔到达北印度的路线全线贯通,此后唐蕃双方使节在长安和拉萨之间频繁往来,基本都经由这一通道。在634-842年的209年间,唐蕃使节交往共290余次,其中唐王朝派往吐蕃使节100余次,吐蕃使唐180余次[8]。这一路线的开辟也使得喜马拉雅地区诸王国与唐王朝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官方往来:641年,大羊同国“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9];646年,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一个王国——悉立,遣使至唐贡方物[10];同年,悉立国西南的邻国章求拔“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11];647年,毗邻的泥婆罗国向唐王朝“遣使献波稜菜浑提葱”[12];同年,“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等远夷十九国,并遣使朝贡”[13];651年,泥婆罗王“尸利那连陀罗遣使朝贡”[14]。
由于这一高原通道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和优势,大唐高僧多取此道赴印取法。根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太宗、高宗和武后三朝,计有60高僧沙门到印度求法,确定经陆路赴印的19人中,12人经青藏高原至印度或返回内地,包括玄照、慧轮、道生、玄太、道希、道方、末底僧诃、玄会等人。而取道西域和中亚地区往返印度的仅有6人[15]。
可见,玄奘与戒日王的会晤最终促成了中印之间的官方往来,而青藏高原诸国因和亲形成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这条通道得以贯通的前提和保障。玄奘通过传统的陆路经中亚最终到达印度,如果其所经行的路线被称为“丝绸之路”无疑问的话,王玄策等唐代使团和僧侣跨越高原诸国到达印度的通道,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被称为丝绸之路了。这一条高原通道可以说是传统陆地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延伸,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它的开拓和使用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王玄策与大、小羊同
道宣在《释迦方志》(成书于658年前后)中将途径青藏高原到达印度的通道称为“东道”,详细记载了沿途所经地点和具体线路:“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16]即经今天的天水、临洮、兰州、乐都、西宁、日月山、恰卜恰、温泉、黄河源,越巴颜喀拉山,由清水河镇至玉树,逾唐古拉山经那曲入藏,然后经日喀则、吉隆宗喀到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596-667)并未亲自游历过西域和吐蕃,《释迦方志》中对西域诸国的记载多来自于同时期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而《大唐西域记》中未见关于“东道”的记载,连两《唐书》及同时代的其他书中都未提及,《释迦方志》的《遗迹篇》中还提到王玄策和李义表之事,也不出于《大唐西域记》。因此当是依据王、李二人口述或从王玄策《中天竺行记》(今轶)来补充的,“东道”即为王玄策使印经行之具体路线。尤其是其中关于“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的记载,与“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的发现地点完全吻合。
大、小羊同国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腹心地带,是喜马拉雅北麓的重要古国。喜马拉雅通道的贯通,使唐人了解到它们的存在及其方位和风土人情。“大唐天竺使之铭”碑文显示其所在的吉隆,“界于小杨童(即羊同)之西”,而小羊同又位于吐蕃西南,可见其地理位置在逻些和吉隆之间,即今日喀则、江孜、定日一带。既然有小羊同,必定已知有大羊同国,故以大、小来加以区分。“大羊同”之名,同样最早出现于道宣的《遗迹篇》中。较之于对于同一国度的记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称之为“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即东女国也”[17],而道宣在参照玄奘的记载时,新增补一句“又即名大羊同国”,他大概是参考了当时王玄策的见闻和记述,将两者联系起来。
杜佑在8世纪后半期编纂的《通典》,对大羊同国有更加详细的描述:“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18]
对于一个地处喜马拉雅深处的遥远国度,如没有亲自游历考察过,对其疆域四至、风土物产,尤其是具体的丧葬习俗,很难了解到如此全面、详尽的程度。而纵观唐代杜佑所记羊同可知,能够亲自途径大羊同,并对其进行调查和记述的,非王玄策使团莫属。727年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也提及到“杨同”国,但未见有大小区分,也未记其详细情况[19]。由于慧超的返程路线不必经过羊同,因此可能是仅闻其名。王玄策658年所撰《东天竺行记》,宋代已散轶,但其个别章节存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等书,其体例多记载自唐朝至天竺路线所经诸国的风物人情。《通典》中这段关于大羊同的内容很有可能便是出自王玄策的行记。
但《通典》中关于大小羊同相对位置的记载出现偏差,东接吐蕃的大羊同无论如何是无法“西接小羊同”的。因为根据《释迦方志》和“大唐天竺使之铭”的记载,小羊同在吐蕃西南,因此有不少学者已经正确指出,“西接”当为“南接”之误,小羊同在吐蕃和大羊同之间。
三、羊同国风俗的考古实证
《通典》《唐会要》等书中关于大羊同国风土物产、丧葬习俗的记载,近些年来得到考古新资料的一一印证。自2010年以来,中外考古学者在西藏西部及周邻地区,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重要墓葬和遗址,这些墓地包括: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19]、曲踏墓地[20]、加嘎子墓地、皮央·东嘎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地的马拉里墓地[21];尼泊尔穆斯塘的萨木宗墓地[22]等。这些墓地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北麓的河谷地带,以象泉河及其支流为中心,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最东至尼泊尔穆斯塘地区,最西为北印度斯皮蒂地区。该地区海拔普遍较高,在3700米以上。墓葬年代跨度较大,最早为公元前2世纪,最晚可至公元5-6世纪,但其文化面貌具有较多的共性,包括:黄金丧葬面具较为流行;大部分墓葬为洞室墓,少数地点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多使用箱式木棺葬具,大部分为侧身屈肢葬式;多以羊、马、牛等动物殉葬;流行同样风格的铜质器皿、带柄铜镜、青铜短剑、铁质兵器和工具;饰花玛瑙珠、红玉髓、玻璃珠、贝饰等饰物较为丰富;在公元2世纪以后的墓葬中多出现汉地丝绸。从这些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遗物可以看出,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的南北麓河谷地带,至少自公元前2世纪起一直到公元5-6世纪,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保持着较多的共性和明显的连续性,彼此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和交流,非常接近于一个享有多元因素、具有个别地方类型的文化统一体。
这一文化统一体与文献记载中的大羊同国(藏文献象雄国)在地理位置上是比较吻合的。在时代上,由于唐初王玄策凿空喜马拉雅通道之前,内地对这一区域所知甚少,因此唐以前的汉文记载较为模糊,且混淆严重。但至少《北史》《隋书》中已经记录了葱岭和于阗之南存在“女国即羊同”,可知大羊同至少在5-6世纪已经是西藏西部的一个王国[23]。藏文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象雄国的记载,但其存续年代充满争议。上述考古发现中,年代与文献中大羊同国最为接近的是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萨木宗墓地,其碳十四年代分析为公元400-650年[24]。由前文分析可见,王玄策所经行的吉隆“界于小杨童之西”,而小羊同地处大羊同与吐蕃之间,因此可知吉隆以西地区为大羊同国。而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北与西藏仲巴县毗邻,地处吉隆以西且距离非常接近,当属王玄策时代“大羊同”之境,至少在文化面貌上与大羊同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
从萨木宗墓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在不少方面都印证了关于大羊同国丧葬习俗的记载,尤其是剔骨葬习俗。考古学者在海拔4000米的萨木宗墓地发掘了10座带有垂直墓道的洞室墓(图3),墓室深入岩层,地表无任何封土地标,由于地震或侵蚀导致崖面垮塌,墓洞才得以暴露,是为“藏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墓室内发现有箱式木棺,墓主人侧身屈肢蜷卧于棺内。在数具尸骨上发现有黄金面具(图4),面具上用红黑颜料勾画出眉眼口鼻,额部装饰有成排的彩色玻璃珠,背面以丝绸作衬底,覆盖包裹于尸骨面部,这毫无疑问便是文献中记载的“金鼻银齿”。尸骨周边也发现有大量珠饰。在萨木宗墓地出土的尸骨“76%带有确定无疑的刀痕,并且这些痕迹很明显是在死后产生的”,不是出自乱砍或猛击,很可能是在死后为制作干尸而剔除皮肉、分解尸体所留下的,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西藏实行天葬的开端[25],可见其埋葬之前对尸体进行了一系列洁身仪式和美化装饰。此外,墓室内随葬较多牛羊马骨,当为动物祭祀。动物骨骸之间蜷卧有儿童尸骨,不见葬具,应该为人殉现象。
从西藏西部及周邻地区的墓葬来看,二次葬虽很普遍,但剔骨习俗并不多见,目前仅在萨木宗墓地发现。很有可能当时唐人便是以穆斯塘周边地区所见的葬俗作为大羊同丧葬习俗的代表,也许正是因为它完全迥异于汉地,令人印象深刻,唐人才不吝笔墨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一考古发现也反过来印证了唐代文献记载的清晰度和可信性,为确定大羊同国的方位提供了有力佐证。
萨木宗墓地除了剔骨之外的诸多特征,在西喜马拉雅南北麓的其他墓地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墓地类似的黄金面具一共发现了5件(图5);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随葬遗物,大都与萨木宗墓地相同;人殉并不常见,但在3-4世纪的故如甲木墓地出现过数例;殉牲较为普遍,基本上存在于每座墓葬之中,动物多为羊、马、牛等。虽然这些墓葬的年代均早于萨木宗,但彼此之间的时序传承非常明显,可见这一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关于大羊同风土习俗的相关记载在西藏阿里地区的墓葬中能够得到更多印证。曲踏墓地II区(公元前2世纪)和加嘎子墓地(3-4世纪)均保留有墓主人的发辫,前者还见有较多毡子之类的服饰,可见确实为“辫发毡裘”。墓葬内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同时还发现一些青稞、粟、稻米等谷物种子。粟和稻米显然是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较低的区域输入的,青稞在当地仅有小规模的种植,因此其生业基本上以“畜牧为业”。此外,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西藏西部在吐蕃之前并没有发现文字,曲踏墓葬内壁发现有类似岩画的刻划图案,木棺上也发现有简单的拼接记号,但都没有出现文字。即便在整个青藏高原西部地区的早期岩画中,也从未见过可以确定为吐蕃时期之前的文字。这也与文献中“无文字”的记载相符。
关于小羊同的详细情况文献中缺乏记载,仅能根据其所在方位结合考古资料进行大致的推测。既然同名为羊同,大、小羊同国在族群和生活习俗上至少会存在一些共性。依前文分析,小羊同在吐蕃西南,大致为今日喀则、江孜与吉隆之间。这一地区由于考古工作开展太少,迄今为止尚未有吐蕃以前墓葬和遗址的相关报道,因此对其丧葬习俗无法给予准确的描述。但在东部临近的浪卡子地区,发现有两处吐蕃时期之前的墓葬,姑且可以作为参照。一处为查加沟墓地,墓葬地表无明显的封土,残存有砾石围成的梯形边框。墓葬形制为砌石边框,墓葬遗物种类有成套的黄金饰件、铜马具饰件、铁剑和箭镞、陶器、红玉髓珠饰、海贝(饰件)、丝织物、动物骨头等108件,其中黄金制品17件,包括马形饰牌、圆形额饰、管形发饰、耳饰、戒指等[26](图6、图7);另一处为多却乡墓地,墓葬使用木棺,墓主人为仰身直肢葬式,头部背后发现1件金管,可能为束发之用,额部有黄金制作的圆形饰,面部罩一层薄金片,颈部环绕好几排用黄金、珊瑚及玻璃等制作的装饰品,其中有十几件黄金制成的盘羊形饰牌。墓主人右侧腰部系挂一件青铜短剑[27]。查加沟墓地发掘者推测该墓葬年代为距今200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可晚至吐蕃时期[28],霍巍教授认为这两座墓葬相当于中原的汉晋时期,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大体相当的时期,考虑到墓葬形制特征、出土马形饰牌与鲜卑地区流行的马形饰牌非常相似等因素,此推断较为可取[29]。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来看,它们与西藏西部及其周边所发现的墓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地表无封土;使用木棺葬具;有较多的黄金制品;随葬青铜短剑、铁剑;发现丝织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多却乡墓葬的人头骨面部罩有一层金箔片,其功能似乎与西藏西部及周边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浪卡子地区处于我们所推测的小羊同的东端,穆斯塘地区处于其西端,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这些共性应该可以代表小羊同的丧葬习俗。但详细的情况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揭示。
喜马拉雅南北麓墓葬中发现不少黄金制品,说明这一区域黄金蕴藏丰富,比较流行,这在中外文献中都得以印证。玄奘《大唐西域记》:“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土黄金,故以名焉。”《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引王玄策《西国行传》:“从吐蕃国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国。云:从此驿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宝山。山中土石并是黄金,有人取者,即获殃咎。”[30]悉立在吐蕃西南,一般认为今亚东一带喜马拉雅山谷地区。向北九日行程,当靠近小羊同之境。10世纪的伊朗地理学著作《世界境域志》记载,“Rang-Rong(让绒)是吐蕃的一个省,与印度和中国相毗连。在吐蕃没有比这更穷的地方了。居民住在帐篷中,其财产为绵羊。吐蕃可汗向他们争取人头税以代地税。其地长为一月的路程,宽亦如之。据说其山上有金矿,山中发现金块,状如几个羊头拼在一起。不管是谁,如果收集到这种金子并将其带回家,死神就要降临,除非他把这金子送回(原)处”[31]。东西和南北各为一个月路程,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只有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了。且从叙述次序上看,Rang-Rong之后为博洛尔(巴尔蒂斯坦)和玛域(拉达克),依照本书惯例,可知三者地理位置上必相邻近,再加上其读音也基本吻合,因此Rang-Rong当为羊同或象雄(XangXung)无疑。本人认为这是汉藏文献之外关于羊同(象雄)国的唯一确切记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其中关于其地富含黄金、随意采掘会招致灾难的传说,与王玄策所记宝山黄金一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麦加斯梯尼的《印度志》和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等文献中也记载印度北部山区“蚂蚁金”的传说,采掘者一旦被发现便会被蚂蚁追击、杀死,这一传说的源出地被定于西藏西部和拉达克地区[32]。可见黄金在羊同国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功能,与丧葬面具的流行有一定关联。
四、王玄策“凿空”之前的汉文化因素
从文献记载来看,643年的王玄策使团应该是第一批出现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原人。405年,法显从中亚地区辗转到达了佛祖诞生地——蓝毗尼(今尼泊尔布德沃尔南部),该地向北正与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对应,两地间通过卡利干达克河谷相连,只有200公里之遥,这是当时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到达的距离喜马拉雅山中段最近的地方。而早在法显取经求法之前的公元2-3世纪,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丝绸、漆器等物品,已经从另一条通道输入到喜马拉雅山脉深处了,这就是自南疆至藏西的丝绸之路支线。
在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曲踏墓地II区以及尼泊尔穆斯塘的萨木宗墓地都出土了确定来自于中原汉地的丝绸。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和曲踏墓地II区三处墓地年代相当,约为公元2-4世纪,出土丝织品包括“王侯”文鸟兽纹织锦(图8)、几何纹织锦(图9)、黑色和红色方目纱、棕色绢等。大部分为平纹经锦和纱、绢,属于典型的汉地纺织工艺,产地应该是在中原内地。有一部分为几何纹平纹纬锦,根据纺织工艺特征推测可能为新疆本地所产。“王侯”文织锦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较多,一般被认为是中原官服作坊织造、赐予地方藩属王侯的标志性物品,是贡纳体系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类织锦在西藏阿里地区的高级贵族墓葬中出现,说明本地区对它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有一定的了解[33]。穆斯塘萨木宗墓地也出土有丝织物,这些丝织物主要为绢类平纹织物,经纬线光亮、未加捻,带有朱砂,是明显的中国丝绸(图10)[34]。从墓地所出的其他来自于印度次大陆的物品来看,当时丝织品很有可能通过卡利干达克河谷通道输入到南亚次大陆了。浪卡子查加沟墓地出土的丝织物虽未见详细分析鉴定,但应该也是中原汉地所产,从墓葬的整体文化特征来看,其来源渠道也可以追溯到西藏西部和新疆地区。
除了丝织品外,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的茶叶和漆器,应该也是来自于中原内地的物品。此外,马蹄形木梳、一字格铁剑、刻纹木牌、四足木案等器物,受到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强烈影响,一些器物带有浓厚的汉式风格。这些汉地物品和汉文化因素的出现,得益于藏西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它的一条支线从和田和叶城一带向南延伸,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到达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然后再沿印度河而上到达阿里地区。当然也不排除从和田地区通过桑株古道或克里雅古道直接通往高原的可能[35]。在吐蕃时期,这几条路线成为吐蕃进军中亚和和田的捷径,被称为“吐蕃—于阗道”。
除了来自遥远的中原汉地的文化因素,汉晋时期喜马拉雅北麓地区还汇聚了不少来自于南麓低海拔地区和印度次大陆的物产,如稻米、粟等谷物,铜器、木器、染色的毛织物等生活用品,以及玻璃珠、饰花玛瑙珠、贝饰等装饰品。它们的出现同样是经过喜马拉雅的河谷通道实现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穿越喜马拉雅丝绸之路的发展阶段和文化交流模式:汉晋时期中原地区的物产和文化因素经南疆地区输入、影响到喜马拉雅山北麓地带,这主要是通过东—西方向的狮泉河通道实现的,属于“物”的传播;吐蕃时期打通了沿南—北方向纵贯整个高原的“东道”,使中原人得以直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道到达印度次大陆,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诸王国也直接遣使通唐,实现了“人”的直接往来。
结语
本文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认识可以归纳如下:
一、喜马拉雅丝绸之路(即唐代丝绸之路之“东道”)的开启是以一系列高原王国之间(吐蕃-泥婆罗、吐蕃-大羊同)、及其与唐朝之间(唐-吐谷浑、唐-吐蕃)的和亲为时代背景的,睦邻友好的国际环境是王玄策可以多次顺利跨越青藏高原往返印度的重要原因。
二、唐代关于大、小羊同的区分及其风土习俗的详细记载可能是源自王玄策的行记。
三、从时空关系上看,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可以作为大羊同国丧葬习俗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与文献记载中的大羊同国实行剔骨葬、使用黄金葬面的丧葬习俗契合度极高;浪卡子县的两座汉晋时期墓葬可以考虑作为小羊同国丧葬习俗的代表,它们与藏西及周邻地区的同期墓葬有不少共性。
四、10世纪伊朗地理学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所载吐蕃的“最穷的一个省”——Rang-Rong,即为从属于吐蕃的羊同(象雄)国。其中关于私采黄金可招致殃咎的传说与王玄策行记中的记载吻合,也与西方和印度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喜马拉雅地区“蚂蚁金”传说存在关联。
五、在王玄策的官方使团凿通“东道”之前,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是通过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相连接,输入中原的丝绸、茶叶等,在公元3-5世纪的物质交流已经非常兴盛,是“物”的通道。“东道”在唐代成为纵贯高原南北、连接中原与印度的主动脉,最终实现了“人”的直接交流。
注释:
[1]欧阳修、宋祁等撰:《百衲本新唐书》卷一四六《天竺国》,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1554页。
[2]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年第A1期。
[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66册),1994年;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4]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33页。
[5]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年第A1期。
[6]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
[7]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三)》,黄颢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林冠群:《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10-245页。
[8]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续)》,《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
[9]王溥:《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70页。
[10]杜佑:《通典》卷一九○《边防·悉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78页。
[11]欧阳修、宋祁等撰:《百衲本新唐书》卷一四六《章求拔国》,第1554页。
[12][14]王溥:《唐会要》卷一○○《泥婆罗国》,第1789页。
[13]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页。
[15]张云、张钦:《唐代内地经吐蕃道与印度的佛教文化交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6]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5页。
[17]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页。
[18]杜佑:《通典》卷一九○《边防·大羊同》,第5177-5178页。
[19]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4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21]Bhatt, R. C., Kvamme, K. L., Nautiyal, V., Nautiyal, K. P., Juyal, S., Nautiyal, S. C., "Archa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High Mountain Cave Burials in the Uttarakhand Himalaya", in Indo-Kōko-Kenkyū – Studies in South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 2008-2009, vol. 30, pp. 1–16.
[22]Aldenderfer, M., "Variation in Mortuary Practice on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High Himalaya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 Vol. 1, Inaugural Issue, 2013, pp. 293-318; 迈克尔·芬克尔撰,刘珺译:《尼泊尔天穴探秘》,《华夏地理》2012年第10期。
[23]李延寿:《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女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5-3236页;魏征等撰:《隋书》卷八三《西域
传·女国》,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0-1851页。
[24]Aldenderfer, M. & Eng, J., "Death and Burial at Two Ancient High Altitude Communities of Nepal", In: G.Schug and S.Walimbe eds., A Companion to South AsianPrehistory: Archaeological and 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 New York: Wiley-Blackwell,2016.
[25]Aldenderfer, M. and Eng, J., "Death and Burial at Two Ancient High Altitude Communities of Nepal", In: G.Schug and S.Walimbe eds., A Companion to South AsianPrehistory: Archaeological and 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 New York: Wiley-Blackwell,2016.
[26]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
[27]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28]Amy Heller,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Orientations , 2003, (34)4, pp. 55-64;吕红亮:《西藏浪卡子出土金器的再认识》,《西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9]霍巍:《西藏新出土的早期黄金制品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
[30]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六三《园果篇第七十二·感应缘略引十二验》,北京:中华书局,
2003年,第1906页。
[31]佚名:《世界境域志》,王治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5-66页。
[32]布尔努瓦:《西藏的黄金与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62-86页。
[33]仝涛:《西藏西部的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2期。
[34]Margarita Gleba, Ina Vanden Berghe & Mark Aldenderfer, "Textiletechnology in Nepal in the 5th-7th Centuries CE: the Case of
Samdzong", STAR: Science &Technology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 2016, 2:1, pp.25-35, DOI: 10.1080/20548923.2015.1110421.
[35]殷晴:《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小甫:《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研究奖学金”资助考察报告》,《春史卞麟锡教授停年纪念论丛》,釜山: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05-321页。
(作者简介: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
- 0000
- 0000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