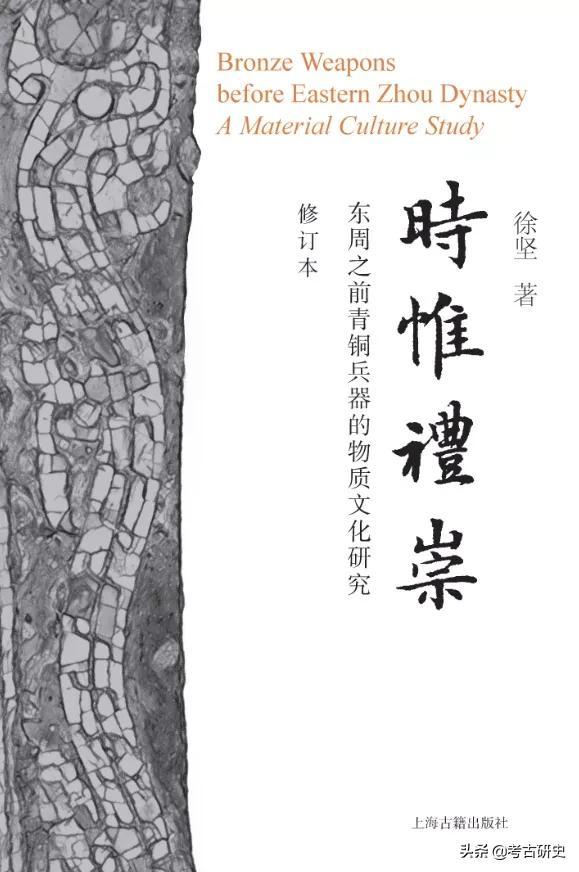颜海英: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
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夏鼐先生,曾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工作30余年,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但少有人知,夏鼐先生还是我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1934年他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于1935年9月进入伦敦大学,1936年开始专攻埃及学,1937—1940年期间,两度赴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和考察研究。在此期间,夏鼐先生师从著名的埃及学家格兰维尔(S.Glanville)、田野考古专家惠勒(M.Wheeler),由古埃及文字学的泰斗伽丁内尔(A.H.Gardiner)亲授象形文字,并得以利用当时最新考古资料从事研究,相继在埃及学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在当时已引起英国第一位埃及学教授、“埃及考古之父”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的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从事中国考古工作,但他始终关注并参与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本文将细述夏鼐先生与埃及学的这段曲折而深刻的因缘。
一、知难而进,选择埃及学
1934年,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并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不久又以优异成绩获得庚子赔款提供的出国奖学金,方向为考古学。1935年9月,进入伦敦大学,开始在科特奥德研究所师从叶兹教授学习中国美术史。从此时到1936年4月,夏鼐在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上,经过了反复调研、咨询、思考,最终形成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有史考古学为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一是选择埃及学为主攻方向。他给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要求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学系,改攻埃及学并延长留学年限,并陈述理由:“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①
这是一个知难而进的勇敢选择,反映了夏鼐在学术上的高远志向和超前眼光。与那些选择容易结业的专业、以获取洋学位为目标的留学生相比,夏鼐时刻没有忘记自己出国的初衷和原则:兼通世界学术,发扬中国学术,“师夷长技”。在清华读书期间,既已认识到“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在世界中的位置”,② 留学的目的,“不仅可得技术方面之知识,即所学之近东方面考古学知识,亦有利于将来返国后作比较研究也”。③因此,出国之前,夏鼐已明了自己的学习目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博物馆之技术,欧洲考古学方面之知识及人类学的背景,考察欧洲方面所保存的中国古物。④ 而导师傅斯年甚至建议他:范围须稍狭,择定一导师,少与中国人来往,最好不要研究中国问题。⑤
在这样的原则下,夏鼐很快认识到在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是个错误,并及时做了调整。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爱丁堡大学攻读史前考古;一是转往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攻读希腊罗马考古,或者埃及学。当时国内研究考古的学者以史前考古为其方向,已有李济、梁思永等。而有史考古则需要人拓荒。夏鼐认为,对中国考古学界而言,埃及考古比希腊罗马考古更有借鉴意义,而且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实力更强。英国第一个埃及学教授的职位,就是伦敦大学为埃及考古学巨匠皮特里破例设立的,这是埃及学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当然,对于学习有史考古学的困难,夏鼐有充分的认识:“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工夫阅读不可。”⑥
1936年4月,夏鼐,这位来自中华文明古国的学子,开始了与另一个古老文明——埃及的对话。此后的四年间,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他始终在埃及学的领域辛勤探索,并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二、师从名家,博采众长
回顾夏鼐在伦敦的学习生涯,给人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志向高远,识见超人,总是站在中国考古学的前沿思考和选择;再就是他的勤奋刻苦,博览群书。他在1938年日记的末尾曾经写道:“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尚且读过那么多书,其他年份更可想而知。粗略估算,他在1936—1937年间,每年都读书100种以上。在他当年阅过的长长书单中,大致包括三类书:埃及学及古代近东方面的专业书籍,考古学技术及理论方面的最新著作,人类学名著。⑦
夏鼐认为,要从事考古学,必须有人类学的根基,“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泰勒的‘均变论’(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⑧
除修习人类学课程外,夏鼐大量涉猎了人类学的重要著作。通论方面主要有:G.Elliot Smith,Essays on the Evolution of Man(埃里奥特·史密斯:《人类进化论》);A.C.Haddan,History of Anthropology(哈登:《人类学史》);R.R.Marett,Man in the Making: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马里埃特:《人类的形成——人类学入门》);R.H.Lowie,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T.K.Penniman,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lolgy(彭尼曼:《人类学一百年》);Alexander A.Goldenweiser,Early Civilization: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戈登威泽:《早期文明:人类学导论》);B.Freire- Marreco and J.L.Myres,eds.,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弗雷尔、迈尔斯:《关于人类学的札记和疑问》);Edward Burnett Tylor,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泰勒:《人类学:人与文明研究导论》);Roland B.Dixon,The Building of Culture(狄克逊:《文化的构筑》);E.P.Stibbe,An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斯蒂布:《体质人类学导论》)。
此外,他还对涉及原始文化的专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过E.Crawley,Mystic Rose(克劳利:《神秘的玫瑰》);E.Crawley,Oath,Curse and Blessing(克劳利:《发誓、诅咒和祈福》);Franz Boas,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博厄斯:《原始人的心理》);Edward Tylor,Primitive Culture(泰勒:《原始文化》);Sigmund Freud,Totem and Taboo(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在考古学理论与技术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夏鼐做到了难能可贵的两点:一是主动了解、吸取最新的学说和成果,除利用学校、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资源之外,他将奖学金的近乎一半用来购买书籍,大量阅读当时考古学界的最新著述。例如他敏锐地注意到“实验考古学”概念的出现,预见到该方法将会越来越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他系统地阅读了皮特里的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考古学的方法与目标》),Prehistoric Egypt(《史前时代的埃及》),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考古学七十年》),The Revolutions of Civilisation(《文明的革命》),The Arts and Crafts of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工艺美术》),Religion and Conscience in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宗教与道德》)等著作。皮特里的理论和方法对他影响非常深远。在埃及考古学发展史上,皮特里和莱斯纳在考古理论和方法上均卓有建树,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地层学、关注细节、统计学、选择性发掘等,都是后世埃及考古学者的典范。
此外,夏鼐非常注重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古代文明,在历史比较、文化比较的框架下,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西方学者的偏见。此外,强调理论意识、宏观视野和比较研究的眼光,以点带面、以小见大,了解东西方学者的差异,寻找互补之处。出国之前,他曾参加了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河南安阳西北岗商代王陵区的发掘。在英国学习期间,他每每结合自己的田野工作经验,以独到的视角思考和发问,提交的课堂论文经常得到导师的赞赏。在田野工作方法上,仅安阳“花土”(殷代大墓中发现的朱绘木雕印痕)问题,他就多次请教过不同的专家学者。
正因为有着卓于常人的见识、抱负、学养,夏鼐才得以在进入埃及学领域后,突飞猛进,成绩斐然。他的指导教师是皮特里的继任者格兰维尔,而教授他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是古埃及语权威伽丁内尔,其所著《埃及语法》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埃及学专业的主要教材。夏鼐自1936年9月21日正式开始学习象形文字,到1937年3月17日已经学完600页左右的中埃及语(Middle Egyptian)语法,做完了全部练习,并得到伽丁内尔的订正。此外,他还学习了僧侣体象形文字(Hieratic)、新埃及语(Late Egyptian)等。到1937年底,他已经译完了《辛努海的故事》、《胡夫与魔术师的故事》、《温纳蒙出使记》、《真理被遮蔽》、《奥赛里斯与塞特的争斗》、《荷鲁斯与塞特》等古埃及文作品,这是埃及学专业的学生至少需用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功课。在读《荷鲁斯与塞特》时,文中提到埃及人看不惯喝牛奶的外族人,夏鼐用“乳臭小儿”一语来解释,令伽丁内尔教授击节赞叹,让他写成一篇短文《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后发表于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埃及考古学杂志》1938年第24期)。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12月,夏鼐先后修完古埃及象形文字、近东上古史、埃及历史、埃及宗教史、埃及考古学、象形文字文献阅读以及上古美术史、工艺学、地质学、人体测量学、人类学等课程,还修过英语语音和德文,成绩优异。1937年12月,夏鼐通过了硕士学位的资格考试;1938年5月,开始计划博士学习;8月,再次获准公费延期。1939年7月,获得马格雷特·默里奖(Margaret Murray Prize)及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Douglas Murray Scholarship)。
从格兰维尔1937年2月8日写给清华大学推荐夏鼐延长留学期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夏鼐的肯定:
自去年10月以来,夏鼐先生一直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埃及学。他做得很好。极其勤奋、认真、严谨;就我看来,他对他的课程表现出全面的兴趣。
在通过资格考试后,他将以几乎全部精力撰写考古学性质的论文。论文题目尚未决定,因为我想先多了解一下他的考古工作。我知道夏鼐先生想在攻读埃及学的同时尽快取得田野工作的经验,我希望能在今秋或明春作此安排。这将大大提高他攻读埃及学的进益,增加其一般考古学的经验和训练。⑨
三、埃及考古与串珠研究
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4月初,夏鼐先后参加了埃及艾尔曼特(Armant)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Tell Duweir)遗址的发掘。此时他已经确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1938年10月,欧战爆发,伦敦大学考古学系停办,夏鼐本来准备回国,但导师格兰维尔教授设法安排他继续求学:先是争取让学校照常颁发夏鼐得到而未领的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42镑,又征得学校同意,让夏鼐在开罗工作一学期来代替缺少的一学期课程。这样,自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得以再赴埃及,进行了11个月的研究考察,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串珠研究”的准备工作。
夏鼐两次探访埃及并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其时正值埃及考古的转折期。在经历了抢劫者的时代,进入科学考古阶段之后,埃及考古以二战为分水岭,前后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二战前,埃及考古注重艺术史方面的内容,以实物为主,看重铭文,偏重于研究宗教和墓葬建筑;而二战后,则关注日常生活,更多地发掘城镇聚落,最重要的则是重视文物保护,主张多勘测少发掘。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埃及考察学会在埃及南部的发掘工作集中在3处:阿拜多斯、阿尔曼特和阿玛尔纳。1938年1月,夏鼐就是在阿尔曼特考古工作站工作。除负责陶片整理和测绘之外,他还详细记录了考古队的工作和管理情况,包括撒哈拉遗址的集体勘测。
随着勘察、发掘和分析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的方法,专业埃及学家也更加注意科学知识的充实,如生物人类学、地质学、遗传学和物理学。而科学家的参与,也给埃及学的研究带来了活力。如在开罗工作的化学家艾尔弗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在图坦卡蒙墓发现后不久,就出版了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古代埃及的材料与工业》)的第一版,对现存关于埃及材料和工艺品方面的资料做了很好的综述,该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被视为埃及科学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卢卡斯能够接触到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很多资料,有条件整理和研究19世纪中期以来出土的大批重要文物,进行数据、化学分析,其中包括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随葬品。在伦敦期间,夏鼐就阅读了《古代埃及的材料与工业》一书,在埃及期间,夏鼐与卢卡斯有频繁的交流,多次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初稿及其他文稿交给卢卡斯征求意见,而卢卡斯对夏鼐的研究评价极高,提出战后修订其名著《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时,将添加“串珠和串珠制造”部分,并采用夏鼐博士论文中的材料。
夏鼐选择古埃及串珠为其博士论文题目时,这个领域还很少有人涉及,而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博物馆又收藏了大批皮特里在埃及发掘到的串珠,没有人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在开罗近一年的时间里,夏鼐得以对国家博物馆所藏及其他来源的串珠进行对比研究,在选题上,已经站到了埃及学研究的前沿,具备利用第一手考古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便利条件,特别是他于1940年5月开始,与最主要的发掘者皮特里有了直接的书信交流,得以亲自询问各种细节问题,并把论文的前几章寄给皮特里。1940年9月皮特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细读了你的论文。其中最后4页主意极好。希望你回国途中能来耶路撒冷面晤叙谈”。这里所谓的“主意极好”是指夏鼐提议串珠分类,须先依材料归类,仿照皮特里Predynastic Pottery Corpus(《前王朝时期陶器集成》)之先例。
在进行串珠研究的过程中,夏鼐不仅吸取了皮特里研究方法中的材料分类法,而且尝试利用统计学整理自己所搜集的古代埃及串珠材料,先后阅读了King's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thods(金:《统计方法原理》),Petrie's Inductive Metrology(皮特里:《归纳的度量衡学》)等著作。
正因为夏鼐的研究从选题到方法都敢为人先,他的工作很快就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论文写作开始不久,开罗博物馆的布伦顿先生(Mr.Brunton)就请他鉴定阿尔曼特出土的串珠,后来夏鼐写成“Beads from Saharan sites at Armant”(《阿尔曼特撒哈拉诸遗址出土的串珠》)一文,被收入Cemeteries of ArmantⅡ(《阿尔曼特诸墓地》第2卷)中。
在开罗期间,夏鼐还写成了“Some Remarks on the Bekhen Stone”(《关于贝克汉岩的几点评述》)、《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几颗埃及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等文章,先后得以发表。其中《关于贝克汉岩的几点评述》是与埃及学家Alan Rowe(艾伦·罗威)进行商榷的文章,夏鼐读过艾伦·罗威关于贝克汉岩的一篇文章后,对其观点有不同意见,并且当面与之讨论,艾伦·罗威建议夏鼐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在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l' Egypte(《埃及古物研究年报》)上发表。夏鼐很快找到一份古埃及文字的新材料,证明贝克汉一词应译为“塔门”,而非艾伦·罗威所说的“祭坛”。文章写成后,经过与艾伦·罗威反复辩论,夏鼐删去“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is incorrect”(原译不正确),改轻语气,谓“Another interpretation may be given”(可以有另一译法)。此事说明夏鼐使用古埃及文字的考据功夫已经相当深厚。
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是在1940年回国以后,于1943年7月最后写完的,10月设法寄往英国。伦敦大学正式通过并颁发博士证书的时间是1946年7月。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博物馆,至今还保存着夏鼐先生当年亲手抄制的近2000张卡片(“Shiah Bead CorpusⅠ,Ⅱ”),把皮特里收藏品里的1760枚珠子,按形制、颜色、材料、文饰、出土地、时代、用途登记,并手绘线图。夏鼐先生家里,至今保存着他带回的资料卡片,以及论文副本。1995年,笔者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所托,翻译该论文导言第一章,在此过程中,得以亲眼目睹这份珍贵的手稿和资料卡片,编目严谨而有条理,写作思路清晰而缜密,英文流畅优美,可以看出夏鼐当年做学问的扎实功底。事过60多年,论文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有合适机会,当予以出版。
格兰维尔教授在1938年6月30日写给学院院长的信中称赞了夏鼐的天赋: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这与他很快就适应了考古学是一样的……从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考古经历来看,不只一两位考古学家证明他对不同类型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能掌握,并能融会贯通。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勤奋的和值得信赖的学生。⑩
诚如格兰维尔教授所预见的那样,夏鼐回国后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
四、再续前缘:夏鼐与中国的埃及学
在伦敦求学期间,夏鼐曾多次问及Sir 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收藏的埃及古物一部分,能否赠与中央博物院,据云已分配完尽。后来在埃及停留近一年多,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念头,常常在他脑海萦绕。
回国以后,夏鼐从事和主持中国考古工作,早年埃及学的训练对他有着很深的影响,而建立中国的埃及学,也是他的夙愿。1938年2月,夏鼐曾经考察吉萨的金字塔考古现场,与当时主持发掘的G.A.Reisner(赖斯纳)及S.W.Smith(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带他仔细参观了吉萨墓区,胡夫之母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的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墓于1925年发掘,随葬品保存很好。其后夏鼐认真读过赖斯纳所著的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yptian Tomb Down to the Accession of Cheops(《齐奥普斯登基前埃及墓葬的发展》),以及Tomb of 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之墓》)。1957年5月,夏鼐主持定陵发掘期间,又重新阅读《海泰斐丽丝之墓》,他发现该墓的复杂情况与定陵非常相似。
1956年3月,为执行中埃文化合作协定,经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提名,中国科学院邀请开罗大学埃及学专家艾哈迈德·费克里教授、亚历山大大学埃及学专家穆斯塔法·埃米尔教授,先后来华讲学。两位专家的授课讲稿被译成中文后,夏鼐亲自审阅译文并修正了其中的错误,费克里的《埃及古代史》和埃米尔的《埃及考古学》,很快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同时,夏鼐热情支持埃及学在中国的创立和建设。1978年末,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组织了部分世界古代史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座谈会,商讨古典文明史学科建设问题,夏鼐在会上介绍了他学习埃及学的经验,展示了他当年师从伽丁内尔学习古埃及文字所做的练习题,并勉励大家:学习世界古代史,一定要从掌握古文字入手。
1985年,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联名发表题为《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的文章,呼吁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同年,在三位教授的主持下,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二十几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等六所重点大学,教师则是从美国、德国和南斯拉夫聘请的专家,分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和赫梯学等专业。
1991年,笔者开始师从林志纯先生攻读埃及学博士时,林先生赠与一本夏鼐读过的法文埃及学著作,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夏鼐先生工整的题注。记得夏鼐日记中曾经提过,他读法文书籍最快时可以每天读80多页。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一直鼓励着笔者在埃及学的道路上前进。
2005年,经国家博物馆朱凤瀚先生指点,笔者发现了清末端方从埃及购买来的一批古埃及文物,包括彩绘木棺3具,石碑50多块。遥想当年夏鼐先生争取收藏埃及文物的心愿,殊多感慨。回首半个多世纪前夏鼐先生在埃及学领域的勇敢拓荒和辛勤耕耘,他无愧于中国“埃及学之父”的称号。
注释:
① 王世民:《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这封信是在夏鼐先生1936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发现的。(夏鼐先生数十年间的日记,现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和夏先生的子女共同整理并准备出版)后来夏鼐获准延长留学年限,并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
② 夏鼐1935年1月4日日记。
③ 夏鼐1935年3月15日日记。
④ 夏鼐1935年4月2日日记。
⑤ 夏鼐1935年6月11日日记。
⑥ 王世民:《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⑦ 参见夏鼐1938年日记。
⑧ 夏鼐1936年7月5日日记。
⑨ 费尔德(Edward Field)、汪涛:《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文物天地》1998年第6期。
⑩ 费尔德(Edward Field)、汪涛:《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文物天地》1998年第6期。
来源:《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