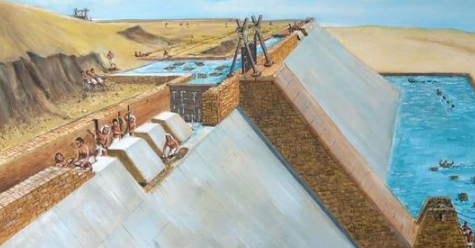中国考古百年 | 曹兵武:以文物为媒的“文化探索三部曲”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落后而又热闹的黄土高原小农村,来到80年代书声琅琅的岭南大都市里的中山大学康乐园学习考古,恍如一下子穿越了无数个世纪的历史。当时接触的第一个专业性概念就是“考古学文化”。业界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是: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质性人工遗存。老师在讲解完这个考古学的概念之后,接着就是从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直下历史时期,用一堆一堆的典型器物组合——最主要就是石器、陶器和铜器等,加上一个一个的陌生地名,给我们这些考古学新生讲解不同时空中作为人类进化表征的考古学文化的组合特征及其演变源流。
我曾经很纳闷,这些考古学的“文化”怎么就能代表整个人类文化呢?好在很快在我们这个考古学专业所在的人类学系的人类学概论课程就给出了答案: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超越人类肉身适应环境的超级复杂系统,仅获专业人员认可的定义就达200多个(美国文化学家克虏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性考察》一书,即收录有西方学界关于文化的160余个定义),其中物质文化是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因此考古学在西方往往被称为是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之一。其实早期人类的物质遗存能留存至今,不仅侥幸,而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相当简单、贫瘠,最早可以传达人类心意、记录人类行为的文字只有五六千年(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然而,认识人类及其文化,在早期除了其自身的化石遗存,再就是古人所能留下的一鳞半爪的遗迹和遗物了,这些考古遗存、器物组合(即所谓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极其宝贵的研究对象和文化遗产了,用考古学研究文化、研究人,就颇有管中窥豹、隔靴搔痒之感。
当然,从最广大时空范围内观察研究人类文化,考古学家从不缺乏雄心壮志,新考古学派将人定义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适应的动物,将文化定义为人类超肉体的适应方式,以人工制造物为代表,并试图从这些古人遗留的残缺不全的盆盆罐罐、竹木金石中,透视人的行为、社会、精神,寻找文化演进的动力学法则。1990年前后我也曾经为此一宏大理想而痴狂,加入向国内翻译引进介绍并实践新考古学的行列,在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指导下,筹划班村遗址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的实验。不过,我还是越来越感觉到,考古遗存背后的文化意义实在是太复杂了,认识人也太困难了,上百万年的长时段链条和考古学建基于物质性的叙事观察分析优势也未能让我们真正把握到多少人类文化的动力学法则,尽管借鉴了几乎所有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手段,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也仍然缺乏自然科学那种精确性和预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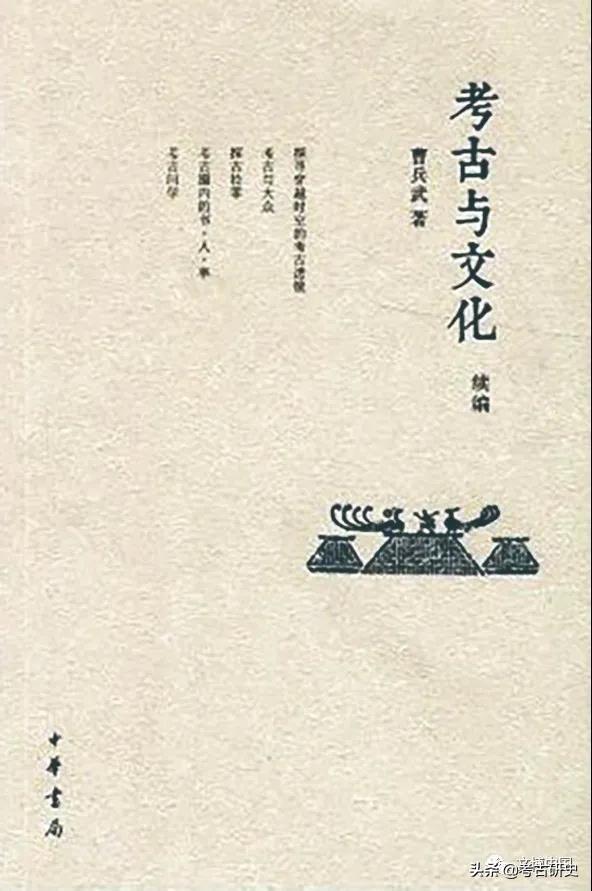
随着后来我离开考古一线出国访学,从事民间文物收藏和博物馆事业管理,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传播等工作,又接触到了古代遗存在考古学之外的一些文化与社会含义,认识到不仅过去的遗存如何揭示古人的文化是一大学术难题,在现代文明中如何处理它们以推动文化进步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是重大而棘手但又无法回避的复杂问题。作为考古遗存的人工创造物不仅曾经助力人类超越自身的局限,攀缘上自然金字塔的顶端,也通过文化实现了人与人的生存合作范围与秩序的拓展,构筑起复杂的文明社会,最终创造了一个自然之外的人文环境并栖息其中,人本身就是自然与文化双重演化的结果。因此,人的继续发展不仅需要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更需要文化自身的继承创新与不断完善。因此在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学术性小册子《考古与文化》时,我即试图将这些都归结为以一种以文物为对象、以文化为统领的整体性思考和探索,希望能够由物见人,比较系统地探索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传承发展的奥秘。

又是20余年过去了,总结我所涉猎的考古、文博管理、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播等不同领域之所得,渐渐积累起了一个小小的随笔性书系,我觉得大致上可以称之为一个以文物为媒的“文化探索三部曲”。其中《考古与文化》(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续编)侧重于从古代发现文化,源源不断地将以文物为载体的古代信息搬运到现代社会,融入我们的知识体系和历史记忆;《博物馆与文化》侧重于用文物作为符码来向现代社会展示、表达和沟通古往今来的文化信息及有关问题,文物不仅可以让我们重建过去,也是今天不同人、族群之间开展文化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文物与文化》则更多是关于在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场域中处理古代遗存及其作为一种现代职业存身之道的一些思考,即通常所说的文物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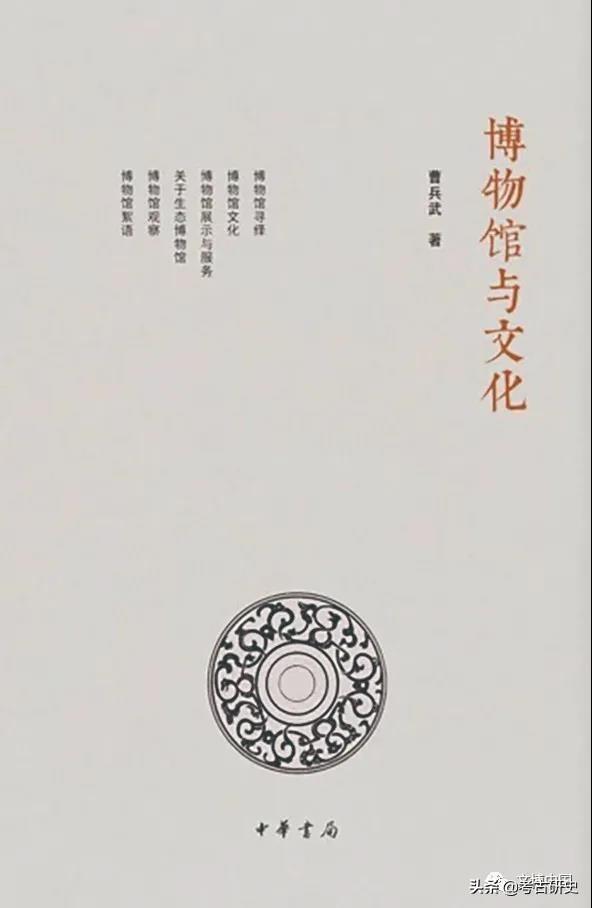
古人的文物遗存,穿越千万年进入了今人的视野,甚至在博物馆那样的文化殿堂里盛装与观众见面,在荧屏上如同明星一般与各色人等神交、对话,不仅延伸着我们的历史记忆,也重构着相互的情感认同和人文素质。即便经历了如此几个不同的领域与学科,我感觉我们从中所窥到的文化也仍然如同考古出土物一样,既丰富又零碎且缺乏系统性,在很多方面都尚未触及到古人的本真,以及利用文物中的信息与价值进行文化传承和建设等根本问题。所以,这些文章都基本上仍然是属于文博圈里的自言自语、自弹自唱,只是自己有些敝帚自珍而已。
不过,生在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我坚信这些寻找与探索的重大意义。人集中了大自然的一切精华,在揭示天地万物奥秘、利用和改造乃至创造环境的同时,过去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还应该怎样走下去?可以说这一直是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的时代天问。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区域性传统能够保持数千年根脉未断,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从人类打造了第一块石器开始,多少文化兴起又衰落,多少文明照亮过人类心中的希望又在人类自戕的灾难与血泊中如昙花般坠落。中华文明从驯化家畜、栽培小米(包括黍与粟)与大米开始,就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持续不断地辛勤耕耘,在整个农牧文明阶段基本上一直挺立潮头,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基本上一脉相承,且兼容并包,内修外拓,不断发展壮大,经过村落、部族、邦国、王朝、帝国,一路迈进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不计其数的发明创造和生存智慧,现在自身又处于与工业和信息文明的碰撞中跌跌撞撞急速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中途。因此,在中国从事考古文博是一种切身的幸运,也是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以自身民族的历史过程和宝贵经验对文物、文化遗产进行科学挖掘、认识和处理,不断回望来路,反省初心,校正目标与道路,在当下混乱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技术、社会以及价值观念探索中,显得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因此,我不揣冒昧,在一些编辑朋友鼓动下将相关文章结集出版,就教于方家。
人本同源,四海之内皆兄弟。无论古今中外,文物都折射着人类文化和历史脉络中的智慧之光,以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不能吃不能穿,却是联系过去、现在、未来的纽带,也是联系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考古、博物馆做的是打捞过去的遗珍、架起古往今来人类交往交流和相互理解之桥梁的工作。诚如总书记所说,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让更大更强的文明之光照亮我们的心灵和前行之路。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透过文物身上厚厚的蒙尘,在这个粗糙的三部曲之上再加上一本《文化与文明》,让文物与文化释放出更多的文明之光来。(《考古与文化》,文物出版社,1998年;《考古与文化(续编)》,中华书局,2012年;《文物与文化》,故宫出版社,2010年;《博物馆与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 0006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