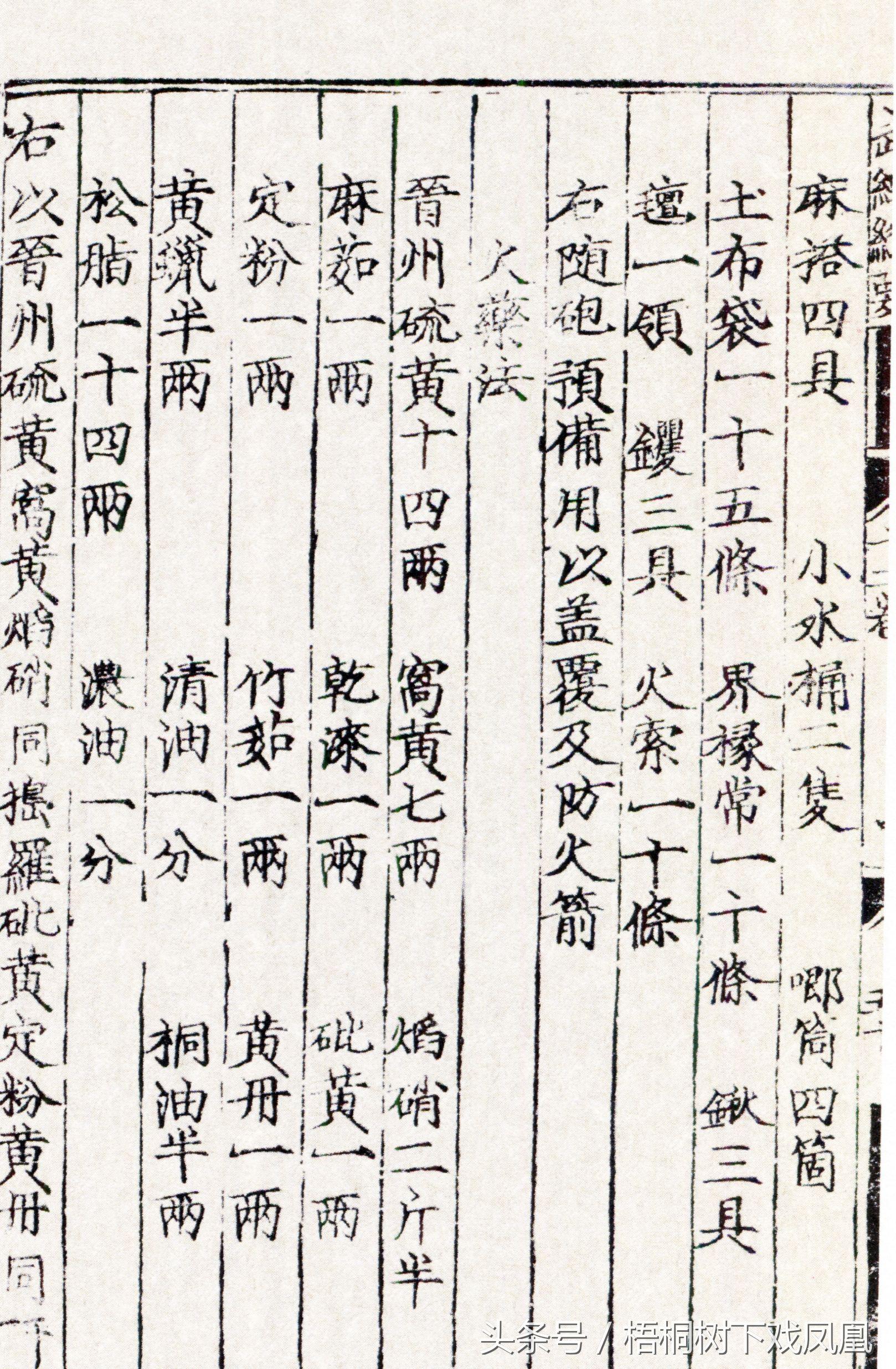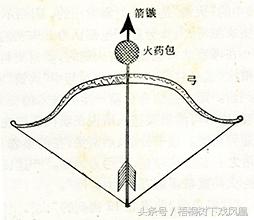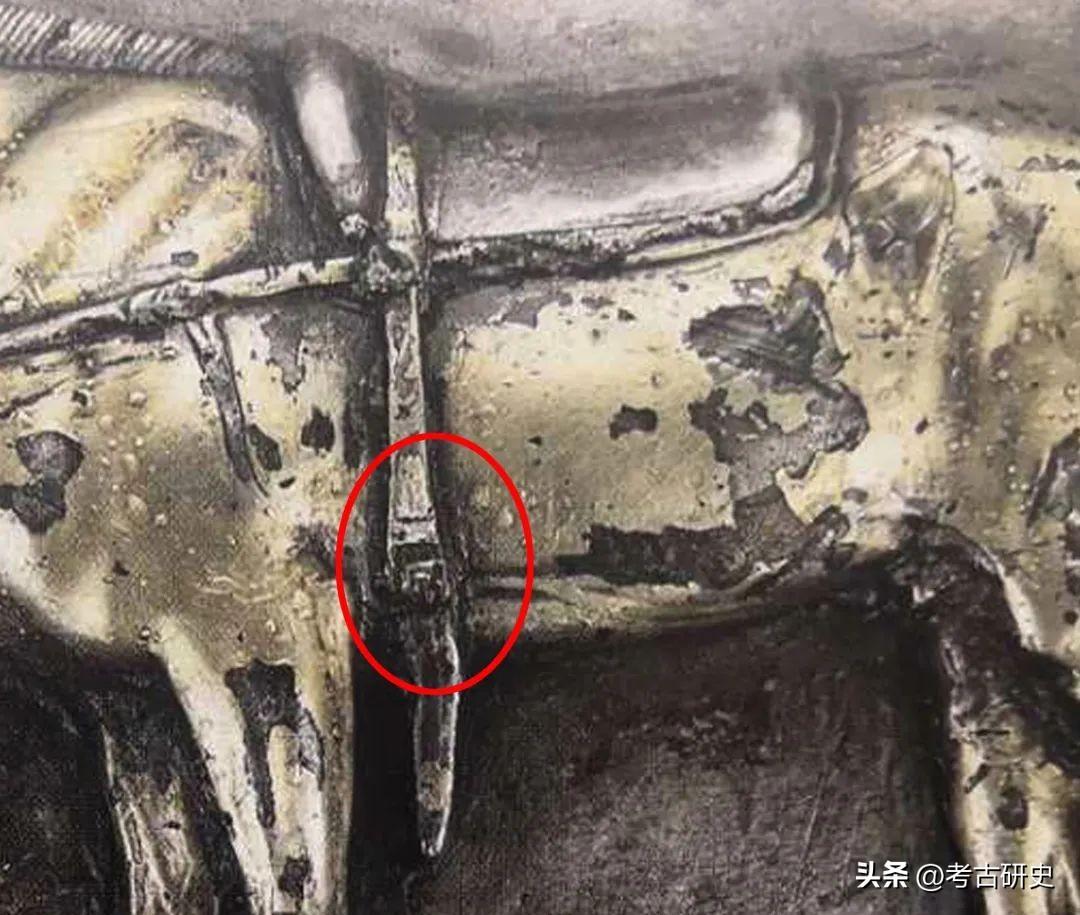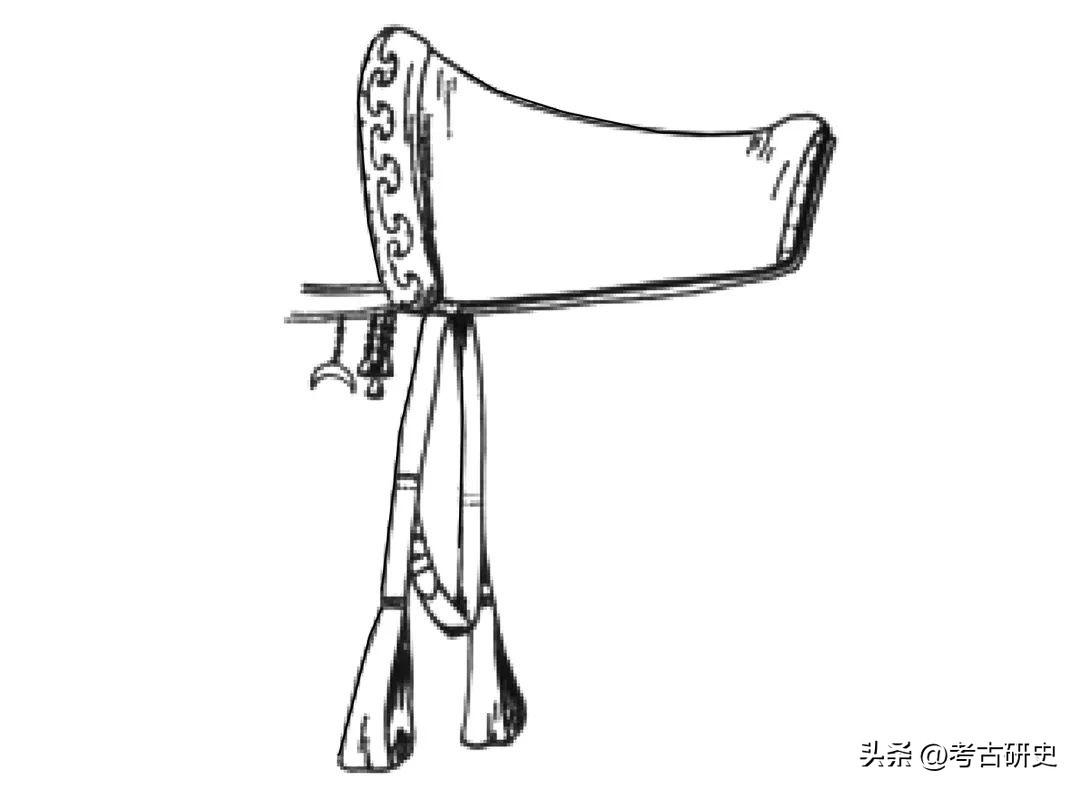郭静云:“三皇五帝”跟“六帝”是什么关系?
【编者按】本文原名《“三皇五帝”和“六帝”概念为哲学范畴的意义》(载于《史林》2017年第1期),感谢作者郭静云先生不吝赐稿。转载时省略了注释,若欲引用,请参看原文。
【摘要】本文分析“三皇五帝”和“六帝”概念的内在意义。笔者一方面并不否定三皇五帝的传说是从深古往事的种子长出来的,隐含着源自远古的文化记忆,但在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三皇五帝”这一结构始终不能代表古代历史,这是基于象数宇宙观而建构的帝国历史哲学,不宜将之视为历史叙述来读。此外,秦汉帝国以前流行的“六帝”概念与“三皇五帝”有源流关系。这些关系牵涉到象数思想中“尚六”与“尚三五”概念的传承及转变。
[关键词]历史哲学、三五、三才、五行、三皇五帝、六帝

一、前言
清代干嘉考据学流派梁玉绳先生《志疑》言:“孔子删《书》肇于唐、虞,系《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每祖述仲尼,则《本纪》称首不从《尚书》之昉二帝,即从《易》辞之叙五帝,庶为允当,而以黄帝、颛、喾、尧、舜为五,何耶?于是谓其略三皇者有之,谓其遗羲、农者有之,谓其缺少昊者有之。夫略三皇可也,缺少昊可也,而遗羲、农不可也。盖先儒举三皇之名不一,……凡斯众说,半归诬诞,总以年代悠远,莫由详定,……。殊不知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况皇、帝以前之荒邈乎?《列子‧杨朱篇》曰:『太古灭矣,孰志之哉?』《楚辞》屈平《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1]
历史传说从三皇五帝开始,近百年考古学研究,更加引起讨论考古文化与某一位皇或帝的关联性,如渭河流域半坡文化通常被说成“炎帝部落”,而在郑州附近发现大约距今5000年的西山城址被说成黄帝时代古城,陶寺遗址被视为尧都等等[2]。学者们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出发,又往前推三皇五帝断代工程,将《三皇本纪》、《五帝本纪》当作古史记载来读。
有关三皇五帝的讨论甚多,但无论是当真或伪,都将之当作历史叙述来讨论。笔者一方面并不以为三皇五帝所载的故事都是凭空而来,这些传说应该是从深古往事的种子长出来的,隐含着源自古的文化记忆,但在另一方笔者面认为,“三皇五帝”这一结构始终不能代表古代历史,这是基于象数宇宙观的帝国历史哲学。因此下文拟从这一新的角度来解析“三皇五帝”以及原有的“六帝”概念之所隐。
二、现代学界讨论中的“三皇五帝”问题
有关三皇五帝等古史英雄,在现代学界流行的看法大体可归类为以下四种:其一是认为曾经有过这些人物或者以为这些人的「氏族」曾经统治天下[3];其二是认为三皇是三大族团崇拜的祖先,而五帝是三皇族团灭后五族之名号[4];其三是认为这都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上古族群、部落的名称[5];其四则将这八个名字视为广泛的时代符号[6]。以上四类之外,还有不少很独特的说法,例如有些学者认为,三皇五帝都是蒙古高原、阿尔泰先民的祖先[7],或者假设他们与现代苗族有密切关系[8],等等。不过后面这些看法太过独特,基本上不为学界所关注的讨论,因此,笔者拟仅讨论前述四种说法。
在第一种说法中,学者们经常讨论八位统治者的关系如何,如张玉勤先生专门写文章,论证神农与炎帝不是同一个人,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两个不相干的人物[9]。神农与炎帝是否为同一个人,乃近百年在学界讨论得很热门的话题,但这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把炎帝和神农视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许顺湛先生则认为,太昊伏羲氏是指从伏羲到太昊一家的领袖或酋长,他们这一家“最少是一千多年,最多是五万七千多年”执政于天下;“神农氏发展了两千年或三千年才有了天下,说明白一点,才成了部落联盟的盟主。从文献记载推测,神农有天下之时,可能就是炎帝时代。炎帝属于神农系统末期,形成了一个很有成就、很有影响的大族团。”至于黄帝,许顺湛先生也将之当作具体的人物,把五帝都视为五个朝代的代表人物,即类似于开国之王的身份,并且计算这些「朝代」的年代,以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联接为一套历史体系。[10]这种“三皇五帝断代工程”亦有其他学者提出过讨论。以笔者浅见,这种论述方法勿庸说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秦汉之前没有大一统的“天下”和“朝代”,生活在东南西北不同环境中的族群,不可能组成一团,一元史概念是后世帝国意识形态的成果,符合秦汉帝国的政治目标,而不是表达历史真相。另外,三皇五帝的形象,是神话中的远古超人,是从文化记忆组合而具象化为英雄形象,那种以为三皇五帝代表具体人物的观点相当不合理;视为宗族或朝代也一样不合理,不存在几千年不亡的家族或王室,这不是实际人生所能有的经验。
第二种说法,则如顾颉刚先生闻名的论述:三皇五帝可能是中国境内不同族群的祖先,“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的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先算作了乙国的祖先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作了甲国的父亲……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实是一种极有利的政治作用。”[11]这种看法表面上合理,但如果深入反思先秦史的情况,则很容易产生很多疑问。例如,在中国多元的历史时空中,在哪一时代,什么地方“号召统一”?难道某人决定甲、乙国的祖先有父子关系,大家就接受?国家的合并是复杂而血腥的过程,有胜利者也有被毁灭者,可不是自愿结兄弟的故事。另外,在历史传说中,只有颛顼才被纪录为楚国的始祖,神农、黄帝、尧舜等并没有视为某个具体的国家的祖先,史料中好像也没有任何相关指标表达他们是全天下的圣王。对此问题,黄炘佳先生提出的想法是,炎帝为商族的始祖神,就是因为姓羌,所以为牧神(与神农不是同一始祖神),而黄帝是周族的始祖神。[12]但以笔者浅见,而这种讨论既无根据,亦无明确的思路,只能令人迷路。
第三种说法支持的人可能最多,其虽然好像有理性化神话的目的,但实际上只是进入另一种神话的环节,而起经常毫无根据地猜测这些“部落”怎么生存。如果将伏羲视为渔猎“部落”,而将神农视为农耕“部落”,我们如何具体指出这两个族群在哪里活动?在中国那么大的空间境域中,难道古代只有一个渔猎和一个农耕的“部落”?显然不是。难道中国境内所有的“渔猎部落”自称为伏羲?为什么用这两个字来指称“部落”?这到底是自称或是它称?我们知道殷商用“羌”字指称北方游牧民族,是典型的不分实际族群的他称,那在远古时代由谁把“渔猎部落”总称为“伏羲”?似乎不大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可见,以实在具体的“部落”来理解神话英雄,实际上与视为具体的人物的差异不大,甚至更加令人迷惑,恐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反而产生更多的疑问。有些学者用“族团”概念来取代“部落”概念,如迪拉娃尔‧吐尼亚孜先生认为:“华夏族是在三大部族集团的长期交流和战争中融合、同化而成的。……从这一过程来看,华夏族的血统不但混合了以三大部族集团为主的血统,而且也融合了其他部族的文化。由此,形成独特的华夏族历史文化,『三皇五帝』的传说和帝王谱系只是共同的华夏族历史文化的一个『浓缩性』文化符号而已。……华夏族源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部族联盟,从部族间的冲突、战争到融合……”[13]这种解释还是认为,自古以来一直有过以几家王室联盟而形成的大一统中国。这一观点,若从人类历史来思考,同样只能存疑。这些所谓三皇五帝的“族团”到底是指哪些远古社会?他们生活在哪里,怎么生活,族团为什么只有三个和五个,他们如何互斗?这“三个族团”、“五个族团”与商周时期无数大大小小的诸国有什么关系?前后如何联接而划出历史的蛛丝网络﹖这些问题之所以无法回答,就是因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与实际的历史不相符。
第四种说法,则如王震中先生把全中国历史分为伏羲时代、神农时代、黄帝时代、颛顼帝喾时代、尧舜禹时代等,并搭配与考古文化及社会型态。[14]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讨论,但是古史传说并非这样是以设定“符号”的方式而形成的,古人并不会有意作结构社会学而创造时代的象征符号,除非这些故事全部是后人伪造,才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笔者认为传说并非全部都是凭空而伪造,其中应该还是含有古人记忆的沙粒。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说法,实际上非常接近,都把三皇五帝当作某个具体的团体,时代或活动地域虽然不同(如经常说,神农部落在南、黄帝部落在北等),但却一直有天下统合的关联。由于学界还是有这种基础的“中国”观念,很多学者曾提出过类似“三皇五帝断代工程”,王先胜先生专门搜集并总结了几家“三皇五帝断代工程”的成果[15]。换言之,无论什么说法,在讨论远古史时,都缺乏对传说故事进行“分层”的分析,即很少考虑在故事中分辨不同时代的层面。我们手里毕竟只有战国以来的文献记录,难道从远古到战国甚至汉代,对遥远古代的历史故事的认识没有发生变化?古史的种子与后世的层面如何分辨?了解这种分辨难度的人,从一开始就会放弃对三皇五帝问题的讨论。笔者也非常理解这种担忧,原来也是一直希望避免讨论相关的话题和记载,但是随着经验的多年累积,逐渐看出历史文献中的多个不同层面,而稍微学会了采用不同层面的知识探赜索隐,方始思考古史传说所隐。如果对历史神话传说进行一套的分析,这将是一种庞大而难度极高的课题,并非一篇文章能够解决。本文尚不准备投入这种讨论,而是首先作一认识论及方法论的总体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三皇五帝”这一结构?为什么古代史书将远古的历史归纳为“三皇五帝”的结构来叙述?
三、三皇:文献的矛盾及其内在逻辑
班固《白虎通‧号》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也祝融。”将三皇定为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顺序如上,其文引《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接着加以说明:“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谓之祝融何?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属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谓祝融也。”[16]
以笔者浅见,这是很好的实例,可以显示“三皇”并不是自远古以来的传说记录,撰者对早期社会发展的前后演化关系并不知悉,而是依靠本身生活经验和汉代人观念来编撰传说,他。上述三皇的顺序里,燧人位列三皇中最后的皇,同时解释燧人的贡献是教民以燧取火和熟食。我们现代人经过考古学的发展已经知道,取火的方法是人类最早掌握的技术,旧石器时代的游猎人已会燧火,甚至智人之前的直立人已会敲石取火。人类已会用火加工肉食时,尚未定居、农耕,更加没有夫妇家庭的社会。在上述顺序里,伏羲为三皇间最早的皇,而对他贡献的描述,反而符合已非常稳定的农耕社会。这是因为在两汉观念中,人们生活一切以制度为基础,汉代意识形态认为,若没有社会制度就有不了一切,所以从两汉的观念出发,将教导人以伦常制度安排生活的伏羲定为最早的圣王,这种对历史的叙述方式所代表的,正好是两汉时代的社会观念。
《易‧系辞下》描述伏羲的贡献,呈现出另一种角度,强调他对自然界的知悉,并指出网鱼之始;而在伏羲之后,神农来教训农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7]我们从一方面可以疑虑:传说中了解鸟兽的人物不少,包括造文字的仓颉,舜帝的山林官伯益,如(《史记‧五帝本纪》:“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18])等;但从另一方面看,《系辞》所表达的先半定居为渔猎,而后发展耕地和交易的顺序,相当符合人类进化的实际情况。《系辞》这种纪录的准确性,是纯属偶然而巧合,亦或基于当时人对人类的了解或某种文化中留下的恍惚记忆?很可惜,这一点我们无法评估。
从伏羲、神农的神话来看,其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就是世界古代文明通见的原始“黄金时代”的理想。其中伏羲的形象是远始的崇高智慧的理想;而神农是终于到达养育厚载的理想,可以不再流浪,定居而从自己的土地获得养育。
实际上中国上古多元的神话中,不只有伏羲才符合作崇高智慧的理想,神话中有很多英雄表达这种形象,女娲、彭祖、黄帝、西王母、仓颉、舜、文王、老子等等,都是在不同的文献中代表着远古掌握崇高智慧的人物。可能是因为阴阳五行的思想在秦汉帝国变成为天下意识形态,还因为《易经》的影响力,而使其他智能老翁形象,在传说中变得次要。换言之,这种结果并不是古史传说留传所造成,而是帝国历史定型导致的结果。
如果单纯从伏羲传说来着手,我们恐怕没办法讨论这一神话的来源。各地都会有类似的传说:掌握崇高智慧的巫师,了解了禽兽鱼虫等等,并创造了影响天地人生之祈祷占卜的神秘系统。这种形象不带有任何特定地方的特色,只是从伏羲教导人们网鱼的说法,或许才会暗示一些较具体的含意,有助于排除部分地带。如果将伏羲与神农结合起来分析,假设两位历史英雄形象的来源代表同一个文化记忆,则因为人类从猎民转身为渔民和农民的历史,并没有人类认识燧火那么遥远,所以其故事背后或许真实隐藏了人类对新石器革命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从哪一文化和地区留下来,这并不是容易研考的问题。
若就燧人或祝融来说,教民取火的燧人也是难有确切来源的英雄,虽然很多人把燧人的故事联结为真实表达旧石器时代人们学会以燧取火的事情,但这种思路有过度将神秘传说现实化的嫌疑。循着这种逻辑,普罗米修斯也是旧石器时代的记忆所留下来的英雄,这种想法显然不妥。我们只可以推论,人类对火的崇拜可能源自人类之出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铜器和铁器时代的人类都有崇拜火以及相关的仪式活动,亦或用火祭来与昊天进行沟通。中国神话中的燧人,即是与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神话有同一种意象基因。这并不是遥远的旧石器早中期直立人或尼安德塔人所留下的「文化记忆」,反而是从较晚时代抽象出来的意象,是地球上人类共同的原型(archetype),不宜在历史研究中来讨论。
祝融也是以燧取火的火神,这或许是几个相类似的神话在多元的中国文化中混在一起的遗迹,是同等互补而合编出来的结果。燧人和祝融的神话都很笼统没有独特意义,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创造该神话的文化属性和特征,所以只能看作一个互补的合并的笼统的对象。
在上述三皇之间,可能只有神农的传说,才含有一些独特的征象,允许考虑创造其故事的文化属性,甚至也许可以大致上划出该神话形成的地域范围,但是一样不能视为“历史纪录”。这是含有很多历史层次的故事,沉淀了从最初文化记忆的源头到不同时代后裔的理解与诠释。
不过,在传世文献中,虽然普遍有“三皇”历史的叙述,但这些“三皇”的形象和名号并不相同。大致上可以说,伏羲与神农二皇都被列入三皇之内,但对第三者的身分则各有所言。如在《尚书‧序》和《帝王世纪》中,第三个皇是黄帝,《周礼‧春官‧外史》的郑玄注、《庄子‧天运》成玄英疏亦用此说[19];而高诱注《吕氏春秋‧用众》则将女娲当作第三皇[20]。司马贞《三皇本纪》将三皇定为伏羲、女娲、神农,并且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21]也就是说燧人是一个位在三皇之前的统治者,但却不列作“四皇”的结构。
由此可见,在秦汉以降历史思想的传统中,一定要安排一个远古存在“三皇”的结构,以伏羲和神农为不变之核心,有关第三者则有不同的说法,并将多余的排除在外,或者根本不被提及,或者不被视为统治者,或者将其排在三皇之前。无论如何,绝对要保留“三”之数。
四、五帝:文献的分歧及共同重点
有关五帝的问题,虽然有很多具体的记载,两千年来经学界讨论不休:何故五帝的统治者并不一致?同一本《史记》,在《五帝本纪》里把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列为五帝,是与《大戴礼记‧五帝德》相同[22];但同时在《孝武本纪》和《封禅书》里,五帝却又指青帝太昊(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轩辕、白帝少昊(少皞)、黑帝颛顼,是与《礼记‧月令》和郑玄注《周礼‧春官‧小宗伯》相同[23]。此外,还有《易‧系辞下》将包(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视为五帝[24]。孔安国《尚书序》言:“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将伏羲、神农、黄帝作为三皇,而将少昊、高阳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作为五帝。《帝王世纪》亦同。[25]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与“三皇”一样的趋势:对五帝的名号和叙述各有所言,但无论是指出哪些帝主,重点是要坚决地保留“五”之数。
五、三五结构在历史叙述中的意义
前文所引梁玉绳先生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三皇五帝是各家之言的传说,我们无法考证各家说法的来源及缘故。笔者想进一步思考,何以各家虽然采用不同的成员,却都一致采用三皇、五帝、三王、五伯(霸)的结构?王震中先生认为:“『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这种概念和古史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周秦以来人们对中国上古历史和社会变化的一种认识和表达”。[26]孟祥才先生认为“秦汉大一统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历史学家就以统一的理念,对已有文献记载或在口头上流传的神话传说进行加工整理……”[27]。笔者拟在此补充,不仅是因为有习惯性的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是因为要有目的性地强调,现有的大一统的结构是自古以来的事实,以远古来证明帝国存在的正确性。
不过,笔者进一步认为,“三皇五帝”历史结构,根本没有先秦历史的涵义,而是一贯而彻底地表达秦汉意识形态的榜样和模拟,即“三五”象数宇宙观的概念。刘俊男先生曾经已提出,三皇五帝概念源自“三正五行”。此观点准确,但是刘俊男先生认为这是自古以来的结构性的概念,甚至涉及到新石器时代某些信仰观念[28],这种理解笔者无法赞成,因为“三正五行”及与其搭配的“三皇五帝”概念,首先是基于政治需求,在帝国背景中创造出来的时空概念。
“三五”概念源自战国百家争鸣,如战国秦汉各家曾经通用过“三元”宇宙产生的概念,即《老子》的“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谷梁传》的“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出土文献中还有郭店楚墓出土楚简《太一》的“太一、水、天”为三元;又有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简《恒》的“恒、或、气”。具体表述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结构和内在意义都一致:三元观的重点是在表达“三为一体”的“创生”概念。“水”、“火”、“木”、“金”、“土”的“五行”结构,虽然尚未见于先秦出土文献的版本里,但应也差不多是同时定型,属于战国时期宇宙观念之一,将上述“五行”视为万物、时空造化的规律。如《孔子家语‧五帝》所言:“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29]
照着宇宙的规律以及遵守着“社会取法于天地”的概念,儒家(应该是子思子学派)伦理化“三五”宇宙观而提出社会伦理的“五行”和“三无五至”的概念。郭店楚墓竹书的《五行》所载的“五行”为“仁”、“义”、“礼”、“智”、“圣”;传世文献多见的“五行”为“仁”、“义”、“礼”、“智”、“信”[30];又有“庄”、“忠”、“敬”、“笃”、“勇”(《吕氏春秋‧孝行》)[31];“柔”、“刚”、“仁”、“信”、“勇”(《淮南子‧兵略》)[32]等其它“五行”的结构。虽然说法多样,但都固定地保留“五”之数。
子思子学派同时也提出“三亡(无)五至”的统治社会理念。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民之父母》表达君子要施行“五至”和“三亡(无)”“以皇于天下”。竹简整理者濮茅左先将竹简的“皇于天下”通假为《礼记‧孔子闲居》所用的“横于天下”(郑玄注“横,充也”)。[33]但是笔者浅见,楚简的“皇”字反而更直接的表达本义。“皇”是古代文献常见对君王的叹美辞,同时也为“煌”字的本字,如《诗‧周颂‧执竞》:“不显成康,上帝是皇。”意即上帝嘉美赞许周成王与康王。《诗‧周颂‧臣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东汉扬雄《法言•孝至》:“尧舜之道皇兮。”东汉蔡邕《独断》卷上:“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34]也就是说施行三无五至的君盛德煌煌,无所不照于天下。
《民之父母》所载的“五至”为“物”、“志”、“礼”、“乐”、“哀”,《礼记‧孔子闲居》所载为“志”、“诗”、“礼”、“乐”、“哀”,虽然可能有一些差异,未必要解释为完全相同的概念[35]。有关“三亡(无)”,《民之父母》载:“孔ニ(孔子)曰:『三亡(无)虖(呼),亡(无)圣(声)之乐,亡(无)(体)V之豊(礼),亡(无)备之(丧),君子以此皇于天下。奚[36]耳圣(声)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见之,不可VI(得)而见也;而(得)(气)塞于四海矣。此之胃(谓)三亡(无)。』”[37]《礼记‧孔子闲居》:亦言“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38]
儒者好像只是讨论统治理念,但在用三五概念时,有意表达这样的意思:即若到达三五的理想,则“皇于天下”、“塞于四海”等。这意味着,“三无五至”的统治方法乃通天通地、集于中而满四方、无所不及,此乃“三五”结构象征的重点。儒者特意用“三五”的象数概念,以强调上下四方无所不及并全部集合于中位君子的德性。总之,无论是在讨论天地、万物造化或者讨论社会君臣伦理,“三五”的象数是最基本的思想模式,不仅表达上下与四方,更加强调分而不离,结合于中。
统括时、空、意、物、天地与社会的“上下中(和)”和“五行”概念在战国时期还没有被当作一个模式完全通用,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直至吕不韦将阴阳五行思想基质,提升到天下、天地、人生观高度,以此编成作为大一统意识形态后,而汉帝国意识形态略作修正而继承之,并与“阴阳和”、“三才”等概念固定合为一体。从此以后,“三五”概念模式趋向定型并不断扩展其影响。
换言之,从战国思想起,“三五”表达一种以“上下中”、“四方、中”为基础的完整的宇宙人生造化观念和社会运行理想。但是不能说战国时代,此概念已占有绝对优势,只是因为到了汉代,“三五”概念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模式,所以从传世文献来看,好像一直是它占优势。汉代“三五”概念涉及到各种范围,如历法用“三五”一词表达月亮的周期,《礼记‧礼运》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39]《史记‧天官书论》,一方面用“三五”来分类天体,即三辰为日、月、恒星,五星为相应五行之行星;另一方面用“三五”表达历史周期,据司马贞《索隐》,“三五,谓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40]三十年为小周期,其后国家会有些变动,五百年为大周期,其后国家会面临很大的转变,甚至会灭国而再新兴。这种结构就是以当时尊尚的三、五两个数字为核心。养生学也用“三五”概念,以三田五脏来解释人身的生理。
至于三皇、五帝、三王、五伯(霸)的说法,以笔者浅见,最早“三皇、五帝”之句未必用来指出具体的帝王,更有可能是用来泛指理想中所有的远古首领,如《庄子‧天运》云:“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刘向《楚辞‧九叹‧思古》:“背三五之典刑(型)兮,绝《洪范》之辟纪。”王逸注:“言君施行,背三皇五帝之常典。”屈原《楚辞‧九章‧抽思》:“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虽然王逸注:“三王五伯”[41],但原文一样允许理解为三皇五帝,尤其是对三王五伯说法也不一致,各从其说[42]。这是因为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指出具体的三、五位统治者,其名字原本没有固定,是指皇、帝或王、伯也并不重要,这是一种广泛的表达方法,总体指出一切远古圣王的理想。
秦汉时,也继续广泛采“三皇五帝”的总合性的理想概念。但与此同时,从秦汉始,出现大一统的历史纪录。从此,古史因被用来作大一统的基础,在意识形态中,与天地人的基础一样遵循着“三五”的规律。从此在官方文献中,一定要把传说的英雄按照”三五”的结构来排。但在“三皇”和“五帝”的名号已大致固定的结构里,具体哪几位先君组成“三”,哪几位先君组成“五”,往往是次要的,因此并未固定下来,文献中的说法众多。在汉代历史思想中,“三五”的结构依然是关键所在,并且此结构始终离不开天地时空的“三五”象数概念。
若就“三皇”而言,明显可见其以“上下中”的意图为基础。如孔安国《书序》把“三皇”说为伏羲、神农、黄帝。其中神农为司农事之土神,这在其它文献中表达得很清楚,如《礼记‧月令》曰:“季夏之月……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郑玄注:“土神称曰神农者,以其主于稼穑。”《吕氏春秋‧季夏纪》载:“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高诱注:“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为神农。后世因名其官为神农。”[43]可见,在“三皇”结构里,神农相当于“地皇”。黄帝在“五行”的系统里相关于“中”,在“三”的系统里显然也是“中”,相当于“人皇”。而受龙图以作《易》、“幽赞于神明”[44]的伏羲圣人,在此结构中代表天,相当于“天皇”。是故,《春秋纬》等传自汉代的古书中,恰好有过按照“三才”安排“三皇”,“以羲、农、黄帝为天皇、地皇、人皇”[45]。
“五帝”结构最初的基础,依然离不开“五行”、“五方”的时空结构,这乃毋庸置疑,只是这一结构具体的组成会有几种不同的版本。除了上述几套说法之外,《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回》实际上也建构了一套历史五行概念:以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秦为“五行”之帝[46]。虽然《吕氏春秋》不叙述远古五帝之事,所列为“五帝”的五位统治者与《史记》不同,但其“五行”、“五方”的基础概念与《史记》伏羲、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是一致的。虽然《史记》里《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统治者与《史记》里“五方帝”的结构有差异,但《史记》却与《吕氏春秋》一样以五行的周旋来排历史朝代,只是改顺序而已,所以《五帝本纪》的五帝一样离不开“五行”、“五方”的时空结构。《史记》同一本书之内,可见两种五帝结构,以笔者浅见,这是“三五”概念系统与编撰叙述历史的目的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现在也可以了解,何故黄帝既记为三皇之一,亦记为五帝之一,因为他既按照“上下中”及“三才”的结构被连接于“中人”范畴,亦按照“五行”及“五方”的结构被连接于“中土”范畴。这实际上在汉代人的“三五”理念中并无矛盾;但是如果将此一概念进一步历史化,就会遇到明显的矛盾,这种情况很容易从秦汉文献有关三皇五帝的说法矛盾中看到。
各家文献中的“三皇”结构,固保留天皇伏羲、地皇神农上下二皇,但是因为从《吕氏春秋》以来,把黄帝安排在“五帝”的结构里,第三皇之名号各家不同。前文已指出,高诱注《吕氏春秋‧用众》第三者释为女娲;班固《白虎通‧号》释为火神祝融或燧人。无论是女娲、祝融或燧人,他们都不带有“中皇”的意思。《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载了全新结构:天皇、地皇、泰皇,这已经完全不符合“三才”概念,没有天地之间的“中”,反而在天地之上另创造了一个至上的泰皇。以笔者浅见,“三皇”结构模糊化的原因,是因为在三皇五帝具体化过程中,黄帝被纳入到“五帝”的结构里,所以“三皇”之“中皇”位置变空。或许因为如此,司马迁之时“三皇”结构已变得模糊,他干脆放弃编《三皇本纪》[47],直接从黄帝讲起。
有关为什么《史记》里没有《三皇本纪》,笔者另拟提出一个假设:文献所描述的伏羲、炎帝,都是原初时代始没有国家的社会,如《商君书‧更法》曰:“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淮南子‧泛论》曰:“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48]太史公需编撰大一统史,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帝国史书的目的,大一统的历史需要写以黄帝为源头。虽然司马迁放弃写三皇这一部分,但到了下一个大一统的唐帝国,司马贞补了《三皇本纪》,把一元史推到更早时代。不过,汉代的《史记》虽无《三皇本纪》,但其历史结构却完全符合当时的思想模式,一惯地离不开“三五”概念,即以三代的“三王”为“三”;同时,为了符合汉帝国的理念,黄帝到大禹之间一定要选择五位正统的「帝」,其他排在正统“五”的结构之外,并在五帝和三王之间不能有其它政权。基本上可以看出,《史记》所采取的结构,是在固然预定的模式与将原本多样叙述的故事合编为一元史的目的这二者之间,寻求折衷妥协的做法。
不过徐义华先生颇为准确地指出:“『伪造的古史系统』当中,『伪造』的主要是系统,而不是古史。所以,貌似『伪』的古史系统中包含有许多真实的史实。”[49]这些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三皇五帝”的系统是完全配合秦汉意识形态而建构,但是组成该系统的传说,则不全是后人的想象,能不能用“许多真实的史实”这样的说法和定义和描述,这还可以商榷,有多或少实难以斗量,但是这些故事却有上古文化的成份,只不过这些成份,均隐藏在最下面的地层,经过屡次的转传,早已成为难以辨识的文化密码。但是这些曲折而传世的故事组成“三五”的结构,显然不能代表古史,而只能代表汉帝国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
五、从六帝到三皇五帝:两种结构之相关性
我们两千余年传统的继承者,习惯性认为只有“五帝”概念,但是郭店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提及“六帝”的结构。“六帝”一词原本未见于文献中,但六帝的结构确实出现在东汉晚期的传世文献中。此问题从顾颉刚先生始有提及,他认为,自刘歆《三统历》中所载《世经》始,在五帝的结构抽入了少昊,由此成为“六帝”趋势。[50]周凤五先生认为,西汉末期“五帝”说中多出了少昊,这就是“六帝”概念之源头,五帝的结构在黄帝与颛顼间隔了少昊一代。[51]但是郭店楚墓随葬的文本,不可能受到汉末的影响,《唐虞之道》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新知识,揭示在战国时期,除了“五帝”之外另有“六帝”概念,并且很有可能的是,“六帝”概念早于“五帝”概念的存在。
《唐虞之道》第7—8简言:“孝,仁之免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日(皆)采此。”[52]笔者认为,在此“免”字的意思相当于《礼记‧内则》:“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郑玄注:“免,新生者。”)或《大戴礼记‧公符》:“推远稚免之幼志,崇积文武之宠德。”[53]即表达衍生、为源头的意思,此意思后来由“娩”字表达,“免”亦是“娩”的本字。在先秦儒家概念中“仁”的理念可能确实基于古老的“孝”观念,将家族的“孝”扩展到社会君民之间的关系。““字裘锡圭先生隶为“”或“”释为从“今”得声之与“含”字古音相近的“咸”字,或疑为“皆”字的异构[54];刘钊同等与第27简的“

”字,释为“皆”字的体[55]。笔者认为,该字宜隶为“

”及释为“皆”字的异体字,与郭店简时代接近的中山

王鼎“

”(皆)[56]字写法相同。此外笔者认为,“采”的意思犹如《书‧尧典》所言:“帝曰:『畴咨若予采?』”孔传:“采,事也。复求『谁能顺我事者?』”[57]也就是说,这段文字表达,孝是“仁”之源头,而禅(将帝王位非以父子继承,而选无血缘关系的贤人而让位)是“义”的至高表现;六帝的政事就如此。
邓建鹏先生曾经提出讨论“六帝”的问题,他发现,《左传•昭公四年》另有“六王”之说,其中两位是夏商建国王,四位是从西周王选出来的。此外,文献中还有“六天”、“六神”、“六宗”等很多以“六”为单位的概念,不过邓建鹏先生认为这些概念都与“六帝”不相干。根据他的研究,《唐虞之道》所代表的子思子古帝说以六纪数,将六位统治者视为符合伦理标准,其中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即与《史记•五帝本纪》相同,只是夏禹也被视为帝。[58]
黄君良先生则认为,《唐虞之道》中“六帝就是指唐、虞两代四祀的六位祖先。古六帝代表了中国古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具有伟大功德的名帝为后世所祭祀。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和舜六人都是治绩超卓,功德高尚的帝王,这一派的儒生构架古帝王体系为他们的政治学说建立坚实的论证支柱。”[59]学者们推论各自有自己的道理,但问题是没有一个文本描述六帝统治的历史。所以能否从古史复原的角度来分析“六帝”概念,还值得商榷。
郭店楚墓另有出土《六德》第一简曰:“可(何)胃(谓)六●=(德)?圣、智也,●=言去(仁)、宜(义)也,忠、信也。”[60]传世文献中亦有“六德”一词,如《书‧皋陶谟》:“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周礼》所记录的“六德”与郭店楚墓的《六德》篇虽有些出入,但基本的概念相近。徐少华先生认为,《六德》篇与《唐虞之道》有密切联系。[61]笔者赞同这一说法,“六德”是理想之德的伦理概念,而“六帝”即是“黄金时代”理想统治的形象。在此,“六”并不代表曾经具体在位统治者的记数,而用来作带有象征意义的数字。
邓建鹏先生指出:“《六德》与备『六帝』说的《唐虞之道》俱出一墓,似乎在纪数上昭示着某种一致性。另外,先秦典籍(尤以成书于战国中期前为甚)以六纪数较为流行。如『六师』、『六极』、『六府』、『六气』、『六言』、『六蔽』」、『六正』、『六志』、『六物』、『六畜』、『六事』、『六卿』等。随着战国后期五行说及五德终始说的盛行,以五纪数逐渐占据上风。『六帝』说随即被『五帝』说取代。这同时也说明先秦『六帝』说仅此一见的原因: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唐虞之道》,处于以六纪数向以五纪数转变时期。『六帝』说最后在古帝五行化的笼罩下,迅速完成了向『五帝』说的转变。”[62]
笔者认为,邓建鹏先生的论述基本准确,只是需要作一点补充。第一,战国中期不是“以六纪数向以五纪数转变时期」,而是在百家争鸣中以五或六纪数并存时期。后来《吕氏春秋》第一次建构以“五”为单位的宇宙意图,秦帝国却选择“六”为概念性的数。但是汉帝国意识形态则选择“三五”,因为汉帝国统治长久,在后世的观念中,“三五”的结构成为替意识的认同。第二,既然“五帝”能够取代“六帝”,两者不可视为“历史”,在历史中王室、朝代有多少就多少,不能按照象征性的数字而变得少或变得多,“六帝”和“三皇五帝”,同样都是结构化出来的、历史化的宇宙时空概念。第三,严格来说,最终不是“五”取代了“六”,而是“三五”取代了“六”,是因为“六”系立体的概念,而“五”只是平面概念,必须以“三”搭配,才能构成立体的结构,此问题以下说明。
在“三五”的结构里,“五帝”的“五”,藉由天下历史的时间,来表达四方与中的天下的空间结构,并以“三皇”的“三”搭配,藉由天下历史的时间,来表达上下与中的天地关联,且在“中”位,“三”和“五”的结构获得不可分离的结合,此位就是以黄帝来代表。而在“六帝”的结构里,“六”的象征意义应该是什么﹖《书‧舜典》: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63]笔者认为,远古“黄金时代的”六帝”概念与只次于上帝的“六宗”概念实密切相关,“六帝”乃是历史化的“六宗”之宗教概念。有关“六宗”之意思,孔颖达等《正义》载:“说六宗者多矣。欧阳及大小夏侯说《尚书》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谓天,下不谓地,旁不谓四方…………马融云:『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谓六也。……”孔安国《传》亦载:“马云:『天地四时也。』”[64]也就是说,“六”的象征意意为上下四方,此象征在“六帝”的概念里依然可用。并且因为四方相当于四时和四季,而上下相当于昼夜和死生的周旋,所以这一空间概念,同时也为时间概念。
如果“六帝”与“三皇五帝”两种概念进一步比较,容易发现其之间的关联,包含关键的共同性和关键的差异性。“三皇五帝”的“三皇”联结上下竖立的空间,而“五帝”则联结四方平面的空间,一起表达“上下四方”的皇帝,而在“六帝”概念里纵横“上下四方”的帝原本已都在一起。但是在“六帝”概念里,中位空虚,这其实是上帝中央虚空,而“三皇五帝”与“六帝”相反,双重强调“中位”在帝国历史的存在。所以“三皇五帝”概念将“六帝”概念内虚无之“中”,改成重实之“中”的形象。
六、结语
总之,“三皇五帝”所代表的,首先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帝国意识形态中的时空概念投射到帝国根源史的结果,藉由古史传说的重编,而构成理想的天下历史的时空体系。换言之,三皇和五帝的个别故事或许有源自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及传说的成份,但完整的”三皇五帝”观念及系统,首先代表的统一天下的思想理念,通过这一概念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汉帝国哲学理念,但不宜从了解上古历史的角度去认同它。
当然这一概念并不是汉代才形成,而有更早的源头,但其形成的过程表达“天下”概念的发展,以及统一天下施行步骤。历史演化与思想演化往往互相促进,在观念未形成之前,事情亦难以施行。把天下视为互补关联并系紧于中的上下四方,把天下的历史也认同为系紧于中的上下四方的整体,这种观念宣传成功,才有成功统一天下的坚固基础和可能性。这种观念被诸国人们认同的过程漫长曲折,所以“三皇五帝”概念显然并不是汉代才初出萌孽。可是秦汉统一天下之前,“三五”概念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同时存在的“尚六”概念的影响也相当大,“三五”概念占主导之后,“尚六”概念影响的痕迹也没有完全失传,因此文献中留下了很多以“六”为纪数的概念,其中《易》卦爻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
“六帝”也是“三皇五帝”占主导之前,与后者同时存在的概念,并且从意义上可以看出从“六”到“三五”的传承关系,而且可以从中看出二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六帝”为“上下四方”,“中”为大虚空(或许意味着崇高上帝的大虚),而“三皇五帝”的结构,实际上与“六帝”的结构一样以“上下四方”的时空概念为基础(文献有表达,三皇是伏羲为天皇、神农为帝皇、黄帝为中皇或人皇,至于五帝则则配五方)。但是在“三皇五帝”结构里,中位并不大虚,反而纵横两次被强调。从空间关系而言,就是因为黄帝的“中位”纵横两次被强调,所以“三皇五帝”原本并不是八位,而是以七位构成,黄帝既出现在三皇,亦出现在五帝的结构中,其位既代表“上下中”的“中”,亦代表“五方”的“中”。这一概念在历史宇宙观的理念里毫无矛盾,但是当这一象数结构被用来作历史记录的基础时,同一位皇帝不能代表两代,由此“三皇”的结构失去了“中皇”,这造成文献中关于三皇的纪录分歧甚多,而司马迁不录《三皇本纪》,直至唐代才有之。
- 0005
- 0000
- 0001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