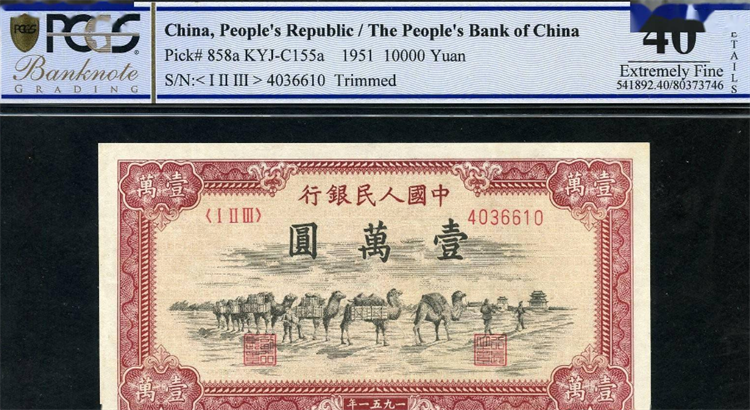郭静云:饕餮纹鼻形是用来强调饕餮神与天皇的连接
【编者按】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页107-113.,原文中有较多甲金文字因技术原因无法贴出,有兴趣者请直接看原文。

观察饕餮纹的结构,我们可注意到两条夔纹之间突显出来的鼻形。因此,笔者乃参考古代文明与鼻形相关的信仰,推论如下。
(1)甲骨文以鼻为象形意义的“自”字
甲骨文中鼻的象形字乃是“自”字。在甲骨文中“自”字的意思范围如下:
甲、鼻:
贞:有疾自,隹(唯)有蛇?
贞:有疾自,不隹(唯)有蛇? 《合集》11506[1]
《说文解字•自部•自》言:“自,鼻也,象鼻形。”[2]表达“鼻”为“自”字的本义。
乙、自从:
壬寅卜,贞:兴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合集》270
贞:〔兴〕方以羌自上甲用至下乙?
……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1
贞:勿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419
辛酉卜,贞:自今五日雨? 《合集》1086
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以下略] 《合集》21021
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下》:“自天子达于庶人。”[3]
在商代之后“自从”发展出“缘故”、“由于”等用义,如《易•需》:“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朱熹注:“自,由也。”[4]同时也发展出“始”、“自来”、“自出”、“原本”之义,如《韩非子•心度》:“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松皋圆《韩非子纂闻》云:“谓爱民之道,自此生也自……山曰:‘自,宜作首’。”[5]都是与“自从”相关的涵义。
丙、商王的自我自称:
王自飨? 《合集》5239、5240、5244-5246、6234、6394、39854
贞:(惟)王自往西? 《合集》6928
己未卜,争贞:勿隹(唯)王自从望乘呼…… 《合集》7528-7530
……河珏,(惟)王自正?十月 《合集》24951
庚戌,(惟)王自征刀方? 《合集》33035、33036
乙未卜贞勿隹(唯)王自征 合集39928?
贞:我勿伐合集39928? 《合集》33928
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用意,如《诗•小雅•节南山》:“不自为政,卒劳百姓。”[6]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原始社会中,这类独一的自称是与庶民相对的,仅限于表达“王的自我”,不具神权身份者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代名词。唯有神圣权力的国王才是独一的“自我”,而且被视为天王的体现。[7]
既然,在“自”字的意义中,鼻子系该字象形义所反映的本义,所以“自从”、“自来”、“缘故”、“原始”与王的“自我”都是衍生出来的涵义。据此可以推论,王“自我”的本义出于鼻子的形象,并含有“本始”之义。以笔者浅见,“自”字的这种意义表达了颇为关键的文化观点。呼吸,是表示人活着的重要生物性指标,故呼吸器官自然被当作人活着的标志:生命实始自呼吸。正因为如此,故古人一方面以鼻指出王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将鼻子视为一切事物的开始。从后世的用意来看,“自然”观念或许也源自古代“自”的概念。“自然”观念与“天然”有异,表达了非从天而来,而是从自己而来,以自己呼吸的元气体现由我亲自呼吸的生活。
不过,回到商代,“自”的涵义不仅表达这类生物概念或者呼气观。对古人而言,“自”并非指所有生物的自我,而是唯一之天子的自我。因此,古代“皇”字就是从“自”。《说文解字•王部•皇》言:“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8]
仔细参照甲骨文的“”、“”字形,可见有两个明显的鼻孔;至于上面三竖画的意义何在,将于下文再论。
(2)文化信仰中“自”与天皇观念的结合
观察古代礼器形状,可以发现,河姆渡、良渚、石家河龙山礼器上常见三叉形的上盖,如河姆渡陶钵上的刻纹(图九四:1)[9]、良渚墓葬中放在头部玉器的典型形状(图九四:3)、良渚璧和琮上的符号(图九四:2)[10]、石家河虎面饰[11]和龙山玉圭刻纹[12](图九四:4—7)等。基本上,笔者赞成冯时先生的意见,这些三叉形的上盖应为天盖的象征。[13]然而,上述几个例子的时代文化属性与商周不同,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商代观念。可是在商周礼器上,也常见有类似的上盖,且其正好与鼻形结合(比较图九四:7—9)。或许可以思考为,上盖符号从新石器时代起便存在于长江流域文化中,它表达与天上的关系,如收纳天上的神祕精华、旨命、恩惠等,这种思想奠基了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并影响到后期商周文明的精神文化[14];而从商周时期,再经过千余年的演化,继续见于汉代神祕造型中,如马王堆帛画双龙上的天盖形状亦如此(圖六五)。在这一大文化脉络中,商文明提出了独特的观念:把天盖与生物吸收天之气的呼吸器官作连接。
鼻形与天盖形状的结合,恰好符合“自”字的结构。商代玉质兽面除了两个角之外,中间也常有某种竖形,如殷墟墓葬出土兽面形饰(图九五:1-3)[15]。妇好墓出土的玉匙上蝉纹便有此种构图,其中间有鼻嘴,往上有抽象的两翼与中尾,此一结构,似石家河玉刻构图,又像甲骨文的“”或金文的“”(自)字形(图九五:4)[16]。这种结构与良渚的典型玉器颇为相似(图九四:10)[17]。江汉地区青铜早期石家河玉器中有这种形状,并且其传播的范围甚广,如青铜早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22墓,也出土了石家河类型的兽面玉饰(图九四:6)[18]。这种种现象表示,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前商文化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长江文化体系与殷商的天盖形状,或许有某种文化交流及传承关系,使“天盖”成为古代通用的观念。
其实,殷商人对“自”形的崇拜,以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最明显。由上所列的青铜器纹饰可见,饕餮构图的中心都有凸形的鼻子,在两条夔龙间形成大鼻状,并常以扉棱作为强调(图九四:8)。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收藏的亞丑方彝的彝盖耳上的符号(图九六:1)。此处通常有龙首纹或明纹(明纹的定义,详见下编第三章),但亞丑方彝盖耳上却以“自”字形符号()来代替。且此符号刻在礼器最高的地方,以表达其崇高的意义。在其他商周时期的器盖耳上,亦常见龙鼻的造型,如山西出土西周早期的方彝盖(图九六:2)等。
直至东周时期,仍可见双龙与大鼻形的构图。如曾侯乙铜镬鼎饰带,即为典型的双龙饕餮构图,在双龙间有独立的鼻形令牌形状,鼻下两个圆圈应是象征鼻孔,全图符合殷商时的饕餮鼻形(图九四:9)[19]。殷商时期的饕餮结构也常见有独立于夔龙外的鼻形(如参图五七;六三;七六:2;八二;八五;八八;八九:2;九二;九三:2;百零六:1;百四二;百四五:1;百四六;百六二;皕十七:2;皕卅三:4等)。
对照“自”的字形、字义以及礼器构图,笔者推论“”(、、、、、、)为呼吸器官的形状,加上天盖之类的象征,表达源头的概念。古代的“皇”字形可以补证此一观点。殷商皇爵铭文的“皇”字作“”[20],与饕餮纹的大鼻形状颇为相似;西周早期尊作“”[21]结构相同。另有殷商时期的皇鬲作“”[22];皇戈卣及皇戈尊作“”[23];亞皇卣作“”[24]、皇戈及皇钺作“”[25],为从五竖异体字。信阳罗山天湖商周墓里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铭文上有“”字,应也读为“皇”的意思,如十二号墓铜爵铭文为“皇己”;八号墓铜爵铭文为“辛皇”,而铜觚铭文为“乙皇”;六号墓铜鼎铭文为“皇父乙”;二十八号墓一件铜鼎铭文为“父辛皇”(图九六:3),而另两件鼎和爵只有“皇”一个字。[26]
西周早期作册大方鼎[27]、小臣鼎[28]、史兽鼎[29]、召器[30]、皇鼎[31]皆作“”;耳侯簋作“”[32];伯簋作“”[33];作册令簋作“”[34]。此外西周早中期的鼎作“”[35];农簋作“”[36]。西周中晚期多数铭文作“”字形。春秋早期秦公簋作“”[37];春秋晚期齐鲍氏孙□钟作“”[38];徐王义楚觯等铭文作“”[39]。战国早期齐陈曼簠[40]、陈侯因錞皆作“”。说文》小篆的“”形从“自”,亦反映了将“自”与“皇”字联系的概念。
上述分析启发我们,像鼻形的“自”字不仅用以表达天子的自我,也涉及皇天的源头,所以在礼器上的饕餮纹鼻形可能用来强调饕餮神与天皇的连接。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后引简作《合集》)。
[2]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136。
[3]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页193。
[4]参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页1366。
[5]参战国韩‧韩非著、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页813-814。
[6]竹添光鸿(日)撰,《毛诗会笺》,册六,卷十二,页五-六。
[7]细参陈炜湛,《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陈炜湛著:《甲骨文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77-82;郭静云,《论中西古代个人像艺术及其观念》,《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页275-280。
[8]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9下-10上。
[9]河姆渡遗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10]良渚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11]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79-80,图51;页94,图62。
[12]据台北故宫收藏,参邓淑苹,《再论神祖面纹玉器》,页49,图6.2:7;页46,图6.1:8。
[1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4]关于天盖思想的起源、演进与文化内涵,涉及一个庞大的主题,此处受主题和篇幅限制,笔者拟日后另以专文论述。
[15]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博物馆,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36、37;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页153,图七九。
[16]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页142,图五一。
[17]所谓“叉形器”,以笔者浅件应名为“翼形器”,是奠基钱塘江、长江下游深入传统的形状,盖形状的意思,笔者拟另文专门探讨。
[18]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硏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彩图IIM22:135;宋建忠,《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61、99。
[19]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据笔者自摄照片。
[20]《集成》器号7732,现藏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21]《集成》器号5908,现藏于北京故宫。
[22]《集成》器号443,藏处不明。
[23]《集成》器号4869、5582,藏处不明。
[24]《集成》器号5100,江西遂川县泉江镇洪门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遂川县博物馆。
[25]《集成》器号10670,河南安阳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集成》器号11724,现藏于北京故宫。
[26]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欧潭生,《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页173,图二二:1-16、20。
[27]《集成》器号2758-2761,河南洛阳市邙山马坡出土,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台北故宫、美国诺褔克赫美地基金会(汇编)。
[28]《集成》器号2581,现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
[29]《集成》器号2778,现藏于台北故宫。
[30]《集成》器号10360,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1]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参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保利藏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页55-56。
[32]《集成》器号3826,藏处不明。
[33]《集成》器号4073,藏处不明。
[34]《集成》器号4300-4301,河南洛阳西工区邙山镇马坡村出土,现藏于法国巴黎基美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 Paris, France)。
[35]《集成》器号2063,藏处不明。
[36]《集成》器号3575,现藏于台北故宫。
[37]《集成》器号4315,出土甘肃礼县红河乡西垂村王家东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8]《集成》器号142,藏处不明。
[39]《集成》器号6513,清光绪戊子(1888年)出土自江西樟树市义城镇临泉村,现藏于台北故宫。
[40]《集成》器号4595,现藏于台北故宫。
[41]《集成》器号4649,藏处不明。
- 0001
- 0001
- 0000
- 0004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