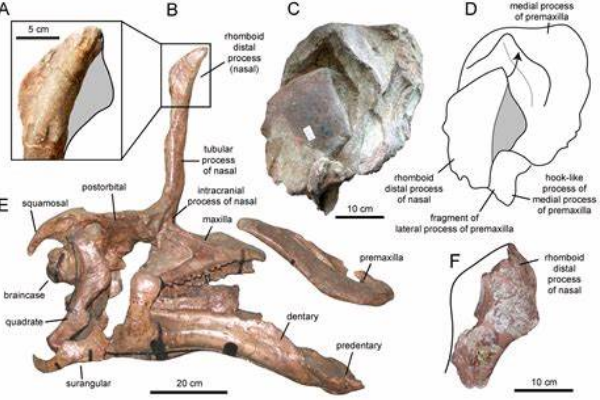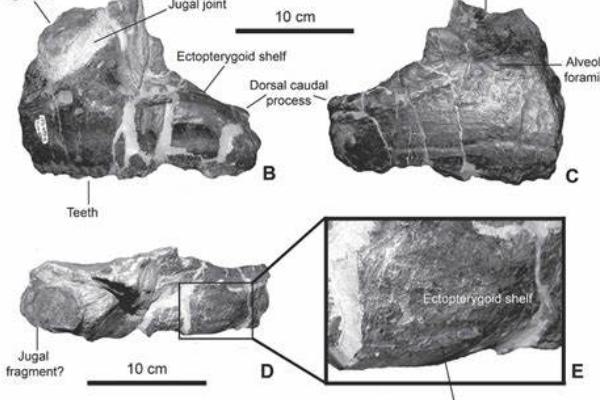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在陈寅恪的生平中,最为人熟知的事迹之一,是陈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因战争爆发而一再延期上任,战后又因眼疾不愈而不得不放弃该职位。由于资料有限,以往人们的了解一直主要是依据陈寅恪及他人的回忆。笔者1998年夏造访牛津大学期间,在图书馆及注册处职员协助下,阅读了1935年至1947年间牛津大学有关聘任汉学教授之档案文件,因而对牛津聘任陈寅恪一事之来龙去脉,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这批档案有牛津大学校方的正式文件和报告,也有包括陈寅恪本人在内的有关人士的来往书信,使我们可以用更接近当事人的眼光,考察陈寅恪个人对受聘一事的态度,以及牵涉其中的中外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角色。笔者对陈寅恪生平知之甚浅,对中国和西方汉学研究的认识亦相当有限,这里仅就在牛津所阅档案,辅以其他参考资料,胪列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一事之前因后果。

受聘牛津之缘起
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中文教授,与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 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简称UCC)的机构有直接的关系。早在1935年5月,由于牛 津大学原中文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 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学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中文教授之空缺[牛津大学档案CP/1,File 1(以下凡牛津大学档案均只标注档案号。又,本文所引牛津大学档 案原文全部为英文,由笔者译成中文)。],并在1936年3月就遴选中文教授事通过有关的大学规章中,列明遴选委员会的组成,除牛津大学有关方面人士外,特别留一席 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代表出任[注解:STATUTE Approved by Congregation on Tuesday, 3 March 1936, CP/1, File 1.]。大学中国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于1931年从庚子赔款中拨出20万英镑成立的,主要由英国汉学家和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组成。从1936年牛津大学颁布的遴选委员会组成看,尽管大学的代表可以从不同学科和学校行政的角度考虑,但最有资格从汉学的角度去考虑人选的,应该是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成员。
至1938年,牛津大学就聘请中文教授一事采取更具体行动。先是在1月决定中文教授的空缺 应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补,随后在5月委任了4名遴选委员,并按原议预留了一个席位由大 学中国委员会指派。在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档案中,最早出现陈寅恪的名字的一份文件,是 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Perceval Yetts,UCC成员之一)在1938年10月28日致 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一封信,信云[注解:文中所有整段的引文,皆出自牛津大学档案 CP/1 Chinese: Professorship of,不再一一注明。]:
我已同大学中国委员会的秘书谈过,得悉他昨天方才收到中英文化协会主席杭立武的电报, 转达陈(寅恪)教授申请剑桥教授职位事。
我们觉得电报应该发到下列地址:
Professor Chen Yinchieh
c/o Han Liwu
Board Trust
Chungking, CHINA
"Chen Yinchieh"的写法,是以往通讯中的写法,"Board Trust"是注册的电报地址。
请容许我冒昧建议,电报的措辞应该确定无疑地表明他已经被选定并正被邀请出任该职位。我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他申请剑桥职位已经落选,如果他以为这次也只是提出给予他一 个候选人资格,他大概不会愿意再冒另一次落选的险。
我是否还可以建议,如果薪金少于剑桥提供的1 000镑的话,电报应该清楚说明确实的数额,以免他以为也是1 000镑。当然,你会写明是"牛津",以免和剑桥之事混淆。
这封信使我们确切地知道,牛津大学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做出聘请陈寅恪出任中文 教授的决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协会是1933年由时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文化友好组织"[注解:《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 王萍访问,官曼莉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8页。]。至于剑桥大学聘请中文教授之事,胡适于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给傅斯年的信中已经提到"C 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n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Pelliot允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大概不成问题。"[注解:胡颂平编著《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5)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1639页。引文中的Monle应为Moule。] 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有一份杭立武于同年10月4日给大学中国委员会秘书的信,谈及陈寅恪申请剑桥一事:
我在上月收到你于7月21日发到汉口给我有关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信,很抱歉,我并不能够 通过你向剑桥大学提供有关陈寅恪(Chen Yinchieh)先生更详细的资料(他自己喜欢用的姓 名的罗马拼音是"Tchen Yinkoh")。我收到你的信后,立即发了一份电报给他(指陈寅恪,——译注),请他提供你所需的资料。不过,由于他任教的西南联合大学现正放假,他居处不定,直到10月2日之前,我们仍无法获取他的资料。我当天已经发了一个电报给你,电文如下:
"陈寅恪年47健康良好能以英语授课打算在剑桥逗留5年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国学者之一。"( 原文无断句——译注)
我希望这份电报能够及时到达你处,以供负责遴选教授的委员会考虑。很抱歉在该电报我未 能提供他的著作的详情。附上一封胡适为其他目的提交的保密推荐信,以供剑桥委员会参考 。
至于遴选委员希望了解有关T.K.Ch?u先生的资料,由于你未提供他的中文姓名给我,很抱 歉我不能辨认出他是何人。[注解:杭立武致A. G. Morkill信,1938 年10月4日,CP/1, File 1。]
这封由杭立武为陈寅恪申请剑桥事致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函件,出现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是 异乎寻常的。从杭立武的信可以看出,大学中国委员会在7月曾就剑桥大学聘请中文教授事 ,发信给中英文化协会,了解有关陈寅恪的情况。但杭立武9月才收到此信,了解过陈的情况后,10月2日才向大学中国委员会发出一个非常简短的电报,并于10月4日发出了这封信件。如果把该信和前引颜慈10月28日给牛津大学的信联系起来,可以推测,大学中国委员会把原来为剑桥大学了解的情况转到牛津,而牛津大学应该是在剑桥大学未聘请陈寅恪的情况下,根据大学中国委员会转来的这些材料和颜慈本人的介绍,很快就作出了聘请的决定。
1938年11月19日,颜慈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告知陈寅恪的通信地址[注解:颜慈致牛津大学注册长信,1938年11月19日,CP/1, File 1。],让牛津大学直接与陈联络。很显然,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中文教授,除了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影响外,在中国方面,当时参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后来陈寅恪周章曲折而未能成行起了左右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将留到下一节讨论。
在牛津的档案中,杭立武信后除附有胡适的信之外,还有一份是关于陈寅恪学术研究特点和 学术水平的介绍,内容如下:
陈寅恪(Chen Yinchieh)先生比较喜欢他的名字的罗马拼音作"Tchen YinKo h"。
1.候选人之履历:陈寅恪先生,江西义宁人,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英国、德国,1917年后 ,他继续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1925年,他被聘任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 和国立北京大学讲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自1929年以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 史组主任。
2.研究领域及方法:陈先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 有造诣。近年来,他致力于汉、中国和六朝的历史(原文是the history of Han, China,a nd Six Dynasties--译者按),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却相当深远,堪称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并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利用。
3.其贡献之重点: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甚为广泛,要达致最好的成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 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惟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 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先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先行者。以下是一些能够突显其贡献的重点:
a.陈先生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 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陈先生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展示出各种细微事实的联系,以解决大的历史问题。他的著作诸如《唐太宗的祖先》第一至第四,(这里估计是指《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等四篇论文--译者按)《约公元126- 536年间道教与沿海省份》(这应该是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译者按)是目前历 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他的方法和他的观点,都可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的楷模。
b.陈先生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利用藏、蒙、满文的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他 的成就,正如在他的《蒙古源流研究》等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西方汉学家难以超越的 。
c.陈先生比较梵文、藏文和汉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对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笔记,于准 确性方面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虽然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研究,但这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根本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以文本批判开始,如此,所引用的材料才属可信,并能得到合理的诠释。陈先生是中国可以这样做的最前沿的学者。他的见识,他对于细节的关注及其 严谨的态度为将来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成就也结合了西方和中国学者的优点。
4.学者的评价:中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对于陈先生的著述评价甚高。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 的中国学者。
笔者一时不能判断上文出自何人,但从文中有关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贡献以 及伯希和等中外学者对陈的评价等内容来看,应该是由对陈寅恪的学问有较全面了解的人 提供的。相形之下,胡适的信倒比较简单和含糊:
陈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 Ying ch'iuh Ch en(陈寅恪)"〕年约47,江西义宁人 ,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 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
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Baron A. von Stael Holstein)合作。
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 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译者按)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37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
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10年之久,该 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之一。
(签署)胡适(此处并无亲笔签名——译者按)
其实,在上述各方为牛津聘请陈寅恪事多次电函往来时,陈本人对于到牛津大学任教并不见 得有多大兴趣,他次年赴香港前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便表明了这一点[注解:陈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201页。]。他对去牛津任职事一度犹豫的态度,在颜慈1938年12月26日写给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 Veale的信中也得到证实:
中国大使发出一封信函,谓陈教授已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大学之聘任,我为能将此信之摘录 送交与你而松一口气。如此一来,亦必省却了遴选委员不少忧虑。我估计,遴选委员毋需再 次开会。四日前我在雪中摔伤了腿,因此有数周不能参加会议。
你会从大使的信函得悉,他将愿意代你与陈教授联络。[注解:颜慈致Veale信,1938年12月26日,CP/1, File 1。]
在陈寅恪致梅贻琦信中提到的郭复初,即颜慈信中提到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陈寅恪之应 聘牛津,很大程度上是郭泰祺劝说的结果。至1939年中,陈寅恪本人和牛津方面都为陈赴英 做好准备,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亦同意拨款100镑作为陈寅恪旅费之用[注解: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秘书致注册长信,1939年5月2日,CP/1, File 1。],陈 寅恪则于1939年6月动身离开昆明。
两度赴英受阻
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之后,先后两次赴香 港,准备动身前往英国。第一次是1939年夏由昆明到达香港,正准备转乘轮船赴英就任的时 候,却适逢欧战爆发不能成行,只好于9月返回昆明。次年夏天,陈再次赴港,"待赴英时 机。既难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注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8-119、126-127页。]人们一 般把陈寅恪不能成行的原因,简单归咎于欧洲战争的爆发造成交通中断。不过,尽管陈寅恪第一次不能成行的直接原因确实是欧战爆发,然而,从事隔一年,欧洲战火未息,陈仍再次决意起行这一事实看,欧战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尤其第二次滞留香港的原因,更似乎另有蹊跷。
牛津大学的档案显示,陈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战争受阻不能按时上任,曾于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原函未见,但这封信的原文在档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内容如下:
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 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 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注解:N ote on Negoti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1932-41, CP/1, File 2.]。
牛津大学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1939年9月,在陈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时,大学的监察委 员会已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允许陈寅恪延迟至1940年度第一个学期初就任[注解:eport from the Visitatorial Board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CP/1, File 1.]。此建议随即为大学当局通过。陈寅恪在1940年再次动身赴港,显然是根据牛津大学这一决定,准备在1940年度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在牛津大学有关的档案里,有一封相信是陈寅恪在1940年5月从昆明发给牛津大学的亲笔信件,内容如下:
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 院事宜。
可见陈寅恪此行并非如今人一般所说,是到港探亲,等待机会赴英,而是已有很明确的赴英 行程安排。但是陈寅恪抵达香港后,却没有按照原计划成行。他在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 函中很清楚地讲到了改变行程的原由,信云:
月涵吾兄先生左右:别来不觉月余,想起居佳胜。弟到港即接郭大使自英来电,因时局关系 欲弟再缓一年赴英,当即托英庚款会代复照办[注解: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函,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3页。]。
据此,陈寅恪1940年滞留香港乃根据郭泰祺的意思"照办",但牛津大学的档案却显示,当时牛津方面从郭泰祺那里所得到的信息,是陈寅恪本人希望再推迟一年上任。郭泰祺在1940年7月8日亲笔签名致牛津大学注册长Douglas Veale的信函中写道:
有关我6月17日的信函,我今天接获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电报如下:
"请告知牛津大学陈寅恪推迟到明年上任之意愿--杭立武"
请就上述之请求发信往昆明答复陈教授。
郭泰祺提到的"6月17日"的信函,在档案中未见,但档案里有一份材料,乃摘录自牛津大 学周议事会6月17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其中有云:
注册长接到指示,答复中国大使刚提出的查询,假若陈教授希望再次推延其上任的日期(见V ol.174,p.23),周议事会将提出一个议案,予他再度休假一年[注解:Acts?, 17 June 1940, Vol. 176, p. xxx, CP/1, File 1.]。
这个议案后来在1940年10月获得通过,据此,陈寅恪应在1941年第一学期到任[注解:?Acts?, 14 Oct. 1940, Vol. 177, p. ix, CP/1, File 1.]。
根据以上几段资料,可以做以下的判断:从1940年5月陈寅恪致牛津大学函,知道陈此次去 香港,是决定前往牛津上任,而不是去香港等候时机。就在陈寅恪动身赴港的时候,1940年 6月17日,郭泰祺致函牛津大学,虽然原函未见,但同日牛津大学周议事会发出的通告中提 到,郭泰祺刚刚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再次延迟上任日期事,由此可以知道郭泰祺在陈寅恪 已经动身的时候,曾向牛津大学查询陈寅恪是否可以推延上任。
牛津大学当局接到郭信之后 ,指示注册长答复郭泰祺,如果陈寅恪希望再次推延上任日期,牛津大学可以准予再延迟一 年,可见陈寅恪1940年再次推迟到牛津上任是郭泰祺提出来的。在1940年,从牛津大学的角 度去看,关于陈寅恪何时上任,战争似乎不是一个直接被考虑的因素。同年7月8日,郭泰祺 又致信牛津大学注册长,转达杭立武的电报,并请牛津直接答复陈,杭的电文原文是"Please inform Oxford Tschenyinkoh?s wish postponement another year-Hanlihwu",由于这是一份电报,用了省略的句子,不同的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微妙的差别,但杭立武用上"Tschenyinkoh?s wish"的说法,则很显然让牛津大学觉得他们正在转达陈寅恪的意愿。而当时郭提出要牛津大学直接致函到昆明答复陈寅恪,表明郭当时还不知道陈寅 恪动身的安排。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陈动身的准确日期,但从陈一到香港就收到郭电报看,陈动身日期很有可能是在7月8日以后,即使在7月8日之前,也不会早多少天。从陈寅恪8月24 日致梅贻琦信看,正当郭、杭向牛津大学转达陈寅恪欲再缓一年的"意愿"的同时,或者甚至是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陈却离开昆明到香港,准备去英国。而陈到达香港的时候,郭泰祺致电表示希望他"再缓一年赴英"。可见,郭在7月8日还希望牛津大学直接复信陈,以便在陈未离开昆明时搁置赴英行程,但随后得悉陈已到香港,便直接致电陈提出要他推迟行程。
从这些片断的资料看来,陈寅恪1940年未能赴英上任,牛津大学所得到的消息,是陈寅恪本 人的意愿[注解:在159页注⑤所引的文件中提到:"1940年夏天,陈寅恪教授再次 要求允许他再推迟一年就任他的教授职位",CP/1, File 2。],但陈寅恪得到的信息,则是郭泰祺的指示。从日程来看,在陈寅恪得到这样的信息甚至还没有离开昆明之前,郭、杭二人已经为陈寅恪推迟上任同牛津大学交涉,而这个时候,陈本人显然毫不知情,还按原计划离开昆明到了香港。可见,陈寅恪1940年再度赴英未果,很可能是郭、杭二人的刻意安排。
这一历史的真相和具体的细节如何,郭、杭二人当时有何特别考虑,在没有掌握更多资料的时候,难以做进一步的揣测。不过,了解一些郭、杭二人相关的资料,也许对进一步考虑这一看似偶然事件的意义有一定帮助。
身为驻英大使的郭泰祺,在此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他的大使身份外,似乎还由于他 和牛津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正如陈寅恪在致梅贻琦函中已经点破的,郭泰祺以中英合作为 理由力劝他接受牛津聘请,但所谓中英合作,实际上"即大使馆与牛津之关系"[注解:陈寅恪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函,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1页。]。据《郭泰祺先生行述》载:
当公(郭泰祺--引者)在使英任内时,与英国朝野均能深相结纳,博得对方之尊重,如保 守党之丘吉尔、艾登及巴特勒,工党之阿特里、贝文及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及各著名之大 学校长教授,新闻界之有力人物,无论左派右派,均有相当之友谊,英国牛津大学曾赠以荣 誉法学博士学位......[注解:《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8册,台北,199 3年,333页。]
郭泰祺是在1938年夏获得牛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注解:?Who?s Who in Ch ina,? Supplement to 5th edition,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40, p. 26.],就在郭获得这一荣誉不久,牛津大学决定聘任陈寅恪,郭显然在中 间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正是郭泰祺积极与英国朝野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郭为陈事所做 的努力,从郭泰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他在英国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至于杭立武,则 曾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也是中英文化协会的创办人,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 委派为蒋与英国驻华大使及丘吉尔驻华私人代表的联络员。1940年7月,英国曾应日本要求 ,将滇缅公路封闭,禁止军事资源运达中国,中英外交正处于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郭代表 中国政府向英提出书面抗议,并做外交交涉[注解: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 料汇编》10册,台北,1996年,4505-4509页。];杭立武则代表 蒋介石和丘吉尔交涉,争得滇缅公路重开[注解:《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 王萍访 问,官曼莉记录),19页。]。可见,郭 、杭二人均与英国政界、学界和文化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在陈寅恪和牛津大学之间所 扮演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转信人和传话人的角色,在陈寅恪滞留香港不能赴英的事情上, 也显然是最知情者。他们这种角色,也许令杭立武觉得有责任施以援手,于是出面与香港大 学商洽,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并为此事于1940年8月24日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注解: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前引书,202页。]。
从杭立武一函可见,陈寅恪之受聘于香港大学,实际上是杭一手促成的,连陈在香港大学的 薪金,似乎都是由杭立武的中英文化协会支付。上文曾引录的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 琦函中,也提到"近因滇越交通又阻,而飞机票价太高,内子复以病不能即旅行赴沪"," 几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注解:陈寅恪1940年8月24日致梅贻琦函,清华大学校史 研究室前引书,203页。]由此可见, 就陈寅恪的主观意愿而言,1940年 中赴英之意本已甚决[注解:陈流求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一文中也回忆陈寅恪先 生在滞留香港期间,"仍在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也可作为陈本 人没有放弃赴英打算的旁证。见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 育出版社,1994年,73页。],既接郭泰祺电告再缓一年,不得已搁置行程, 并欲尽快回国,滞港亦非所愿,寄籍香港大学实属不得已之举。就客观条件来说,此时距离 欧战爆发已经一年,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凡是涉及陈寅恪推迟上任的文件,都没有提及战 争期间交通中断的理由。从前引陈寅恪至梅贻琦和牛津大学的信可以看出,陈寅恪从离开昆 明到抵达香港,也没有考虑到交通中断的问题;倒是陈要从香港回昆明遇到了滇越交通受阻 问题。而且,回昆明旅费昂贵,陈私人财政非常拮据,而赴牛津上任则反而有旅费资助,返 回昆明 明显比赴英更为困难。今人常混淆了陈寅恪两次不能成行的原因,笼统地以为欧战爆发,交 通中断是陈寅恪未能赴英之障碍。其实,第二次滞港的原因虽不能说与战争无关,但直接的 原因似乎更多是各种人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至于真相如何,尚待专门研究者解答。
陈寅恪1940年被郭泰祺通知再缓一年赴英后,本来按照牛津大学当时的决定,应该在1941年 10月之前到任,然而,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得知,陈自1940年夏寄居香港,任 教香港大学,期间经历日军占领香港,到1942年5月5日才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6月 末抵桂林后,便在桂林留居年余,任教广西大学[注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 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6-131页。]。陈寅恪1941 年为何没有赴英,未见任何中文资料的记载,而在牛津大学的档案里,有一份在1941年4月2 8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刊载大学已经通过议案,容许陈寅恪延迟到任,直至当时的紧急状况 结束为止的消息[注解:?Acts,? 28 April 1941, Vol. 179, p. xii, CP/1, Fil e 1.]。到底牛津大学这次得悉陈寅恪不能到任,是如1939年般接到陈寅恪的 信函,还是像1940年那次通过郭泰祺和杭立武通报,档案中并没有任何直接材料显示,惟一 一份相关的文件是郭泰祺于1941年10月之前致牛津大学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原函未见,发 出日期亦不详,笔者在大学档案看见的,只是1941年10月21日牛津大学遴选委员会关于此份 电报的讨论记录,全文如下(郭泰祺电报原文无标点,标点为引者所加):
遴选委员就以下来自郭泰祺的电报做出讨论:
"请坦诚地给我意见,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们希望陈寅恪教授在明年秋季赴英,还是希望他 再缓一年,抑或是希望中止协议。据我了解,由于其健康不佳,他对此行并不热心,但十分 希望按照你们认为是最好的做法去做。
郭泰祺"
遴选委员会强烈反对陈寅恪教授辞职的建议,但同意他应该再缓一年到任。与此同时,应该 查询究竟健康不佳是否陈寅恪教授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注解:Electors to the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 21 October 1941, CP/1, File 2.]
虽然郭泰祺电报的发出日期不详,但可以推测,这份电报是在牛津大学于1941年4月第三次 通过批准陈寅恪再缓上任的决议后才发出的。首先,从档案的内容和排列看,牛津大学在获 悉陈寅恪再度不能上任和通过决议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份电报;其次,郭泰祺提出请牛 津大学考虑的三个可能性,之前在大学档案的文件中一直没有提及。从遴选委员会的强烈反 应看来,"中止协议"似乎从来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甚至怀疑"健康不佳"是否陈寅恪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不论这份电报何时发出,令人更感到疑惑的是,究竟陈寅恪对郭泰祺这份电报是否知情,其中所表述的包括其健康状况是否陈寅恪本人的意思,到底电报中提到的"目前的情况"和牛津大学的议案所提到的"目前的紧急状况"是否同一回事,战争是否造成陈寅恪第三次未能赴英的原因,这都是凭现有的材料不能判断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牛津大学这批档案中见到的是,陈寅恪从1939年接受牛津聘请,一直到1945年因医治眼疾无效正式提出请辞之前,从没有表示过放弃就任的意愿。相反,在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942年到访中国期间,陈寅恪曾与之会面,详细而具 体地商讨牛津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发展方向,甚至迟至1944年9月,还致函请修中诚代 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的学系发展方案[注解:Communications from the Genera l Board of the Faculties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 22 March 1945, pp.32-33,CP/1, File 2.]。
有关陈寅恪和修中诚的讨论,下文将做更详细的阐述,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郭泰祺可说是陈寅恪受聘于牛津的首议者,但郭、陈二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却一直背道而驰:先是郭泰祺力劝陈寅恪就任,陈寅恪但觉勉为其难;到陈寅恪决定赴英,郭又请其缓行;正当陈寅恪对赴牛津之兴趣未见有减,甚至越觉有所作为之际,郭泰祺却向牛津大学提出甚为极端的建议,字里行间有意让陈任教牛津一事无疾而 终。郭泰祺于1941年4月17日离英返国就任外交部长[注解: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 外交史料汇编》10册,4707页。],上引郭的最后一份电报很可能是他离英之后发出的,此后,郭便似乎没有再参与其事了。这些事态发展,到底是出于郭泰祺的某些外交或个人方面的考虑,抑或是陈本人的想法时有反复,还望日后发现更多材料,方能做出进一步判断。
学者的追求
以上的讨论表明,陈寅恪受聘于牛津一事,或许可以置于一个政治、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去理解。陈寅恪受聘牛津未果,作为一宗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仅是陈个人际遇,在事件背后,交织着当时中国外交官员的政治考虑和大学行政部门的财务考虑(关于后一点,限于篇幅,本文未展开讨论)。然而,中国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部门自可以有其政治和行政考虑,而身为学者的陈寅恪先生,一旦决定应聘牛津,一开始便是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陈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环境里,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从牛津档案的其他部分可见,陈和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最乐于花时间和精力的,始终是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1942年至1943年间,修中诚访问中国,其间专程到桂林和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相处了一个月,两人就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批档案保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政府和大学官僚许许多多非学术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映照出学者执着于学术追求的独立人格的光辉。
修中诚(1883-1956),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来华,在福建汀州传教18年,1929-1932年 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注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20页。],自1934年1月起,在牛津大学任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上一节提到的陈寅恪致梅贻琦信谓"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指的应该就是修中诚的研究兴趣,而当时陈寅恪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与文学方面"。可见,陈寅恪最初不十分愿意去牛津,很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修中诚不能配合,而修中诚原来对陈寅恪似乎也了解甚少。但是,当两位学者在中国见面,一起切磋学术,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他们不但互相了解了对方,并且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展现了对发展汉学研究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在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着两份至今读着还令人怦然心动的文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抱负,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陈寅恪不能到牛津赴任,对于中国以至西方的汉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因此,笔者不惮其详地将文件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一份文件是修中诚1943年11月29日从昆明发出致牛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的信[注解:修中诚19 43年11月29日至牛津大学校长函复本,CP/1,File 2。],信中写道:
(上略)
所谓我的许诺,是对陈教授--即我们选定的中文教授而言的。让我从头说起:多数对这次聘请感到有兴趣的人士,一定有一个印象,认为陈教授对于这次聘请是半心半意的,并且对于任教于牛津有被流放的感觉,因此似乎居留不会多于三或四年。我凭着对他深奥晦涩的专著的性质的印象,也曾经这样以为。我现在有一点我自以为很清楚的依据可以证实,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在此,我向你提出这些依据,希望你认真考虑。首先,我同陈寅恪教授相处了一个月,就我所专注研究的在语言中句法和文体的发展所反映出的逻辑意识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我们研究的中古前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代,西方汉学家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而陈教授是研究这一时代的大师。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教师,他很快可以看出一个人研究的途径和真正问题所在。我亦发现,他用英文陈述他的观点和进行讨论如同他用中文一样好。再者,他尖锐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悦的幽默感,使得所有的讨论生色不少。因此,对于我来说,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其次,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不但认识到西方研究在中国文化史的价值--很多学者也多多少少认识到这一点——我更肯定地确信,只有等到训练有素的西方人,以他们自己的观点,委身研究历史和哲学的材料,中国学者才有希望得到他们需求甚殷的启发,以重新发现新问题。其三,因此,由于牛津此次聘请为这样的发展开启了一条路子,这对于他便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因而愿意接受在西方从事研究。其四,故此,他所想到的并不是在三数年内可以做到什么,或者要促进什么和睦 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对于牛津给予他的荣耀,惟一一个应有的回报是一个实在的、至少为期5年的工作计划。因此,当他考虑到本科中文系学生的基础中文训练时,他觉得他的贡献不应该放在这方面。这类工作,若由一个英语助理承担,应更能胜任。他也希望他要承担的一般教学任务可以减至最少,比如说,每年只需任教一个课程。其五,由于(a)唐代(618-906)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具有关键的文化重要性,可与印度和希腊文化相媲美;(b)此时期尚未以现代方法系统地重新研究;(c)敦煌手稿对于了解此时期极有帮助;(d)此范畴之文献乃陈教授多年来专门研究的课题,因此应该在陈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的研究,包括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和就某些方面做专门著述。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他们的会面,不仅澄清了修中诚以及牛津大学方面原来对陈寅恪没有到 牛津上任的误解(前面已经提到,这一误解多少是郭泰祺造成的),更令修中诚了解到陈寅 恪的学术与人格。根据他们当面商谈所形成的共识,陈寅恪在1944年9月致函修中诚,授权 修代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中国研究学科发展的计划,该计划提交到东方研究学院,经由 东方研究学院议事会(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和总议事会(General B oard)通过的备忘录,再提交大学当局。下面是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注解:Communica tions from the General Board of the Faculties [For the Hebdomadal Council only ], CP/1, File 2.]:
高级中国研究计划东方研究学院
代理中文教授修中诚先生在访华期间,曾专程到桂林,与陈寅恪教授相处一月。以下的建议 出自他们就西方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欧洲和美洲的中国文化研究动态的讨论。这些论点来自 陈教授和修先生的看法:即思考一文化之历史非仅为该文化本身,也是将该文化视做人类文 明生活和思想的经验的一部分。陈教授请修先生代向大学表示敬意,对大学给予他的荣誉, 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诚盼在大学杰出学者的协助下,他能够对卓越研究和高等教育做出 贡献。陈教授授权修先生(参看1944年9月18日的信函)作为"向大学当局提交这个计划的 代言人"。
计划
A)该教授应负责将《旧唐书》(刘,220卷,10世纪)及新唐书(欧阳修,225卷,12世纪)以比较形式译成英文的工作,为确保该任务能够在5-6年内完成,应聘请5名专业的协作人为编辑及翻译,即除教授外,再加上2名华人、3名英国人及美国人。
B)为了提高唐史翻译的价值,应鼓励这5名翻译及其领导(即该教授)在从事主体工作的 同时,运用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利用敦煌手稿,撰写研究论著,阐明唐代文化;论著应 同时以英文及中文发表。
C)同时,出版社应该委任雷海宗(哈佛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清华硕士, 曾在巴黎和柏林读研究生)、孙毓棠(清华硕士,曾在日本读研究生)写一套3卷本约1500页并附所需地图及详细索引的中国历史。这套历史应用英文撰写,并以认真的历史学生为对象。上述作者应该征询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其成员有汤用彤(哈佛博士,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学家)、冯友兰(哥伦比亚博士,中国哲学史学家),连同其他专家包括RobertPayne(小说家及诗人,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陈教授、修中诚,以及出版社的一名代表。
D)大学应与出版社磋商,在大学及大学以外、英国及英国以外去寻求财政资源来应付该计划 的开销,即每年4 000镑,不少于5年,不多于6年。
该计划之论证
1.这是首次在牛津这样一所在西方学术世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聘请一位中国人担任教授。这 所大学有其独特的传统,应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英国的汉学研究水准,并适时地尽力产生一些 现已有可能把中国和西方的批判性学术结合起来进行创新研究的成果。
2.众所周知,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之一。在这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成就卓著,才华尽显。中国人对于佛教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并把这些成就带到了纯哲学的领域,政府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法律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一种以开放的态度去欣赏世界的精神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而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更达到顶峰。如果不明白唐代在散文和论说文的写作方面的发展,就不可能理解宋代理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哲学思想已达到一种新的睿智的整合和水平。
3.除了上述特色外,还有一点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的进步时代当中,唐朝是惟 一一个有着两套以传统方式撰写的官方历史的时代。由于这两套历史的原材料相若,而第二套则从不满第一套的观点出发而撰写,故此,进行严谨的比较的试验,实在大有可为。再者,专门研究历史方法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独特价值,向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史学可上溯至殷周时期,到《史记》(司马谈,司马迁,公元前2世纪)以其有条不紊的论述及广阔宽宏的眼界,更使中国史学达到惊人的成就,并成为后来各朝代写作二十四史的楷模。
4.尽管近期的出版著作也有从世界史的眼光出发撰写的,但有意无意地,这类著作都显示 出,对于这些博学的作者来说,惟一值得注意的历史是源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即使这些作者尝试把中国文化纳入,但不论对于精通中国历史的人,还是对于那些已经尽量利用可兹利用的史料的作者来说,结果都同样令人感到苦恼。这套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不是比提纲稍为详细一点的著作,在过去30年间,罕有以中文发表的批判性研究被西方学者翻译或评价。有见及此,美国学会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委托一个中美小组翻译班固的《汉书》,现在向大学和出版社提交的这个双重计划将会大大扩展该项译事及Dr Wittvogel摘译二十四史的工作(尚未完成)。此举将大大改善目前这种令研习历史、历史方法、宗教哲学、纯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学生不满的状况。并且,正如陈教授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的,中国历史研究在其自身的领域中所存在的弊病,正在于缺乏具有足够学识和资讯的西方批评。
其他考虑
1.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他现年50 。约30年前,他赴日本读书,为留学德国做准备。他在日本、德国、巴黎和哈佛都从事过专 门的研究工作,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正当他在北京与钢和泰合作的时候,战争 爆发,他们的工作因此中断。
2.由于过去30年中国学术圈在批判性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以及不少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熟 稔英语,这样,在会讲英语的中国历史学家和会看中文的西方历史学家之间,合作的大门, 正前所未有地打开。
这样一份计划,无须再做任何诠释,每一个熟悉后来中国历史学和英国汉学发展状况的学者,读了这份文件,都会为这一计划失去了实施的机会深感惋惜。当然,即使陈寅恪能够如愿到牛津上任,这份计划是否能够付诸实践还有很多未知数。事实上,在这批档案里,紧接着修中诚这份报告的,是数份来自大学出版社和东方研究学院的文件,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和所需的庞大经费提出质疑。由于实施该计划涉及牛津大学各方面对中国研究在认识上的分歧,更涉及学术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虑,这份计划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学的学术和行政部门通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直到1945年秋陈寅恪赴英国医治眼疾前夕,他对 赴任牛津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修中诚在一份于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他正在向大学提出一个由他和陈寅恪共同商拟的计划,陈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国 ,将有助于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一个新时代[注解:Report on the Academic Yea r 1944 to 1945 by E. R. Hughes, Reader in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CP/1, Fil e 2.]。可惜的是,虽然陈寅恪当年秋天就到达英国治疗眼疾,终因未能奏效,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聘任。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了一封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于1945年12月31日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件,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陈寅恪教授委托我转达以下事宜:陈教授请我感谢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医院留多久。事实上,他并不 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足以应付舟车劳顿,就会马上返回中国。故此,他不得不谢绝接受牛津大学中文教席的荣誉。他为把这个决定告知你而深感遗憾,并且希望你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觉得,只有尽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对大学,对各有关人士,以及对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注解:陈源致牛津大学校长Sir Richard Livingstone函,1945年12月31日,CP/1, File 2 。]
从这些通过第三者转达的话中,隐隐然可以感觉到陈寅恪先生为无情的命运捉弄而不能遂其 志的无奈。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辞职[注解:?Acts?, 21 Jan 1946, Vol. 193, p. xi, CP/1, File 3.]。在中英两国学术史上令中国学人惋惜不已的这段"姻缘",也就此终结了。
原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注释从略。
- 0000
- 0004
- 0000
- 0000
- 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