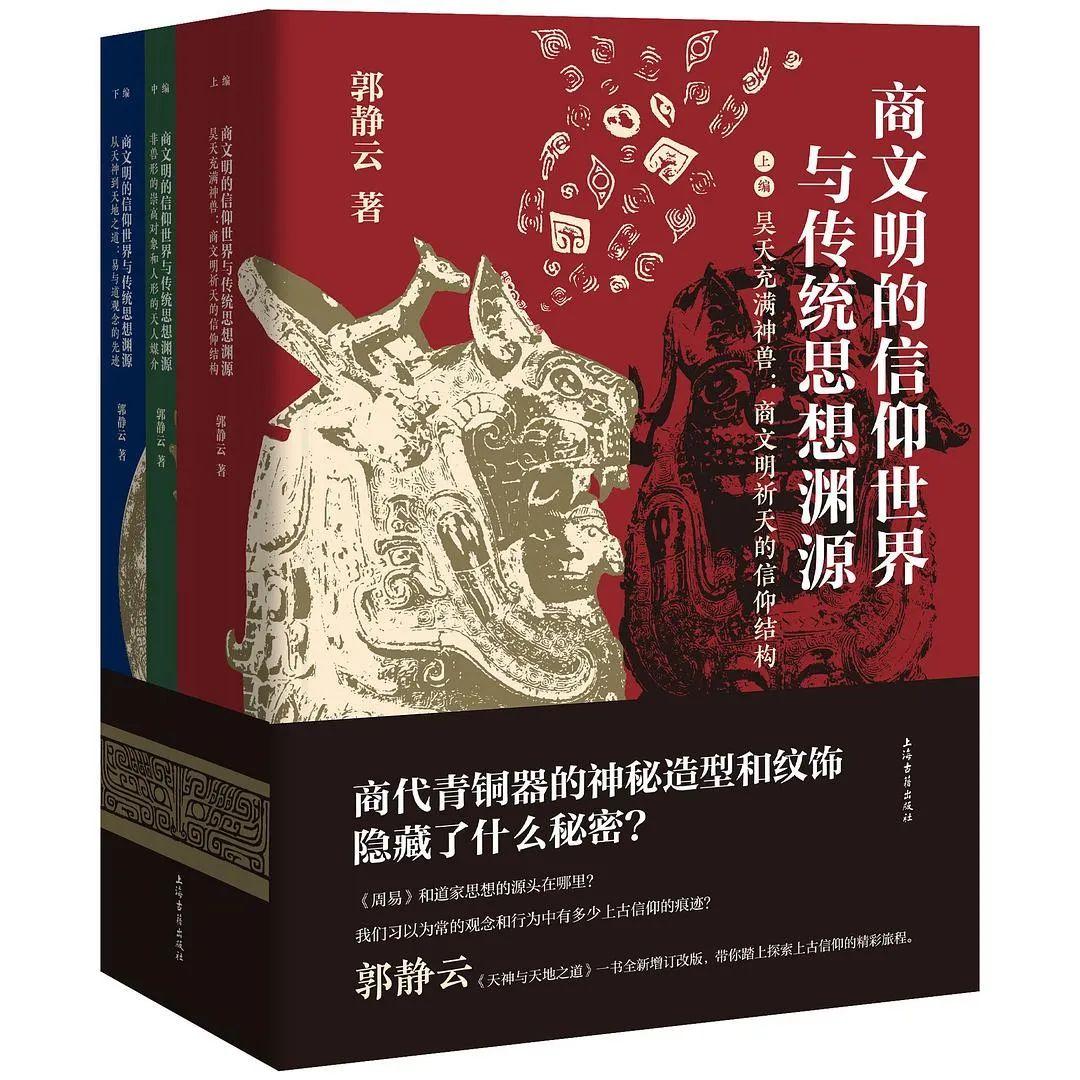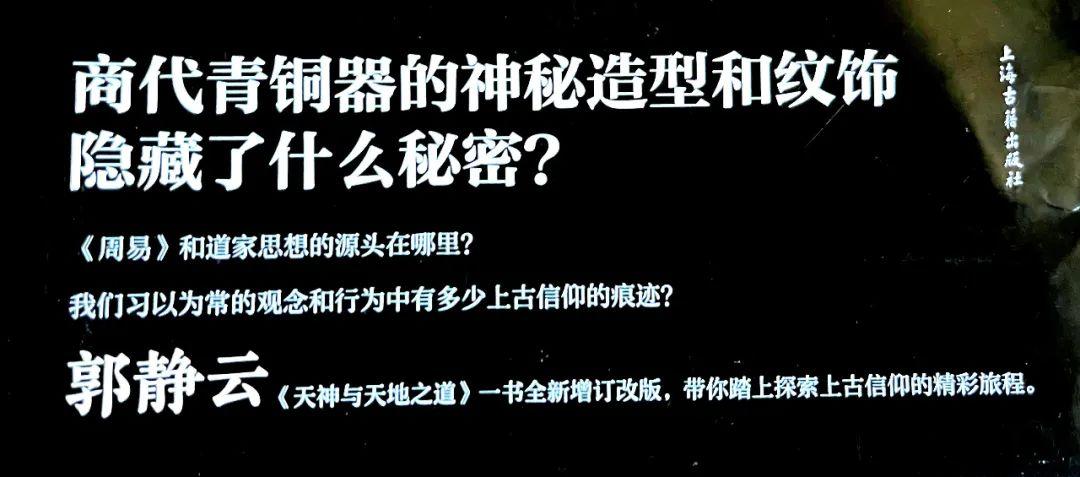许倬云:中原中心论令我不安
我参与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计划时,有一个同时进行的工作,就是酝酿有关“国史”的观念,即中国历史的观念,或者中国文化发展的观念,这跟我最近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有相当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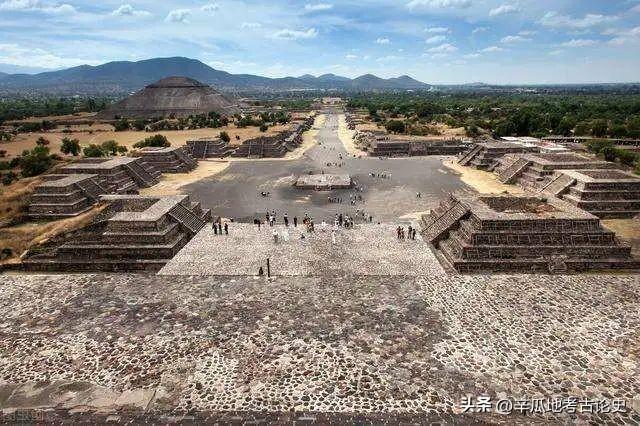
从1983年开始,我一直为中国古代文明系列的《西周史》做研究工作,做了两三年,看了很多考古材料,不单看周代,连商代也一起看,从几个同时代平行的大文化往上追,直到它们在新石器时代的源头。所以《西周史》花了我相当多时间,等于重新将新石器时代的相关资料整理了一遍。七〇年代后半期到八〇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考古学非常热闹,许多重要遗址陆续出土,当时美国介绍中国考古学就是两本书,一本是郑德坤写的,但出版得太早,新资料看得不多,不能算数,另一本就是张光直写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
张光直跟着大陆报道的方向走,就是“中原中心论”的框架。我看了、摸了那一大批材料后,发觉新出的材料又多又快,于是建议匹兹堡大学图书馆搜集中国的考古期刊,只要一出刊就用航空寄来美国,所以我看到的资料,平均比一般人快上两个月。
我看得愈多,愈觉得不是张光直说的那么回事。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很多,加以归纳,可以发现本来的小系统可以变成大系统,但不能用英文的evolutionary形容,因为evolutionary是分岔的,但这是聚合,所以我用中文的“演进”一词,就是这个道理。演进是小支流变成大支流,大支流再慢慢变成几个大的文化体系。
八〇年代初期,我脑子里已经隐然有个观念,中原文化绝对不是单一系统的演变,而是多系统互相交流、激荡,在这文化激荡中间,有毁灭的,有篡夺的,有合并的,有互相冲突终致两败俱伤的,通通都有。
1983、1984年,纽泽西的罗格斯大学请我去讲演,因为事后要编成一系列的学术论文集出版,我不能掉以轻心,得用心想想。我想了半天,拿考古的东西理到中国史上面来,忽然想起当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史叙论》,这篇叙论只是架构,并没有成书。任公才华盖世,念头很多,没成书的东西不算少,这是其中之一。

我十来岁时在重庆看《饮冰室文集》,脑袋里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到无锡辅仁念中学,老师讲课,我又拿出来翻了翻,虽然到台大之后就没有再看过,但内容已经深人脑袋。我找任公这篇东西,一找就找到了,用它当论文架构。我提出的主要观念是,梁任公的想法是要从一个中原的中原,到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我就根据这个理路讨论中国古代史,后来写《万古江河》也是同一理路的继续发展,把梁任公的叙论敷陈成一本大书。
我从考古学上得到一个感觉,任公的叙论只是开头,还需要后来的人加以完成。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跟其他研究同领域的德国人、法国人、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常常有一个辩论,亦即雅斯培所讲的文化系统都是单线的,他们认为,没有经过枢轴时代突破(Axial age break through)的文化,例如古代的亚述,近代的日本,都没有办法真正加入对话,因为它不是初创的,而是学习的。
雅斯培是德国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虽然他的历史知识不错,也有远见,但毕竟历史知识不是那么专精。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认为有几个古代文明,都有一次突破时期,将人类文化推进一个新的阶段,为人类在求生存之外,提出超越的观念。
他的理论曾在思想史与文化史方面引发相当多的讨论,但那些讨论都只限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大家都忽视了书中雅斯培对现代文明的想法,也就是现代的人类正在经历另一次突破。在这一现代的枢轴时代,以科技文化为基调,将有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涌现。我们几个人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研究的某一个系统本身绝对不是不变的,一定是在融合各种新生因素,而雅斯培讲的第二次突破目前正在进行中,此刻正出现世界文化,科技文明众流归大海。
受了这个观点启发以后,我回头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培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Arnold Toynbee)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于是我以任公先生这篇东西为指引,到罗格斯大学讲演,就是中国文化一路下来,挑战、回应、挑战、回应,不断扩大它的文化领域。我的《西周史》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包括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的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围扩展。
我写《西周史》时应用考古学,搞civilization analysis,讨论文化的变化,梁任公先生这篇大作就构成了我往后二十年的主要思考线索。我研究《汉代农业》时,对各个地区四周围的情形还没这么清楚,还是“全国一盘棋”,等到写《西周史》就不是一盘棋了,而是多盘棋的发展与交流,互相影响,甚至解释西周的封建经济是以藩屏周,每一个封国本身都是多元的配合。
从这个结果回头看,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比别的系统有发展的机会,不是因为地理条件强,也不是源流来得长,而是那几个扩大的系统都有很强的容纳精神,有容乃大,所以生命既长且久。
我目前最新的著作《万古江河》,以任公先生的《中国史叙论》做骨架,这是个大框架,我就在新石器时代上面多花点功夫,多想想。大概从1981、1982年开始,苏秉琦先生花了六年的时间,不断发展区系类型理论及古国演化系列理论,我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观念。苏先生是长辈,比石璋如先生小七岁,是济老跟我中间的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考古学家,1997年以88岁高龄过世。当时我到东北看考古,正回头准备到医院看他老人家,结果一个电话来,说苏先生过去了,竟然缘悭一面。
苏老先生早期文章都不在重要期刊上发表,那时候夏鼐掌握了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否决权,所以他只好在各地以讲演方式零碎发表,虽然我没有得到他的研究讯息,可是殊途同归。大概在1986、1987年,我得到他的几篇讲义,那时真是高兴,他老人家看到那么多东西,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居然如此符合。我后来对新石器时代的整理就是依傍苏先生的想法来做的,从此我也对处理历史时代的演变更有把握,更有自信,自认为我对国家观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无缘向苏秉琦与夏鼐当面请益,大陆开放后我很晚才去,光直老早就去了。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回到大陆,去了西安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的仓库里,看了几天新出土的文物,既激动又兴奋。
我每次到大陆,不到北京城,不到上海市,一下飞机就直奔偏远地区的遗址。张忠培陪我到几处遗址参观,成了知交。1997年.我跟他在香港主持了首次考古学会议之后,又连续办了两次,后来出版了三本论文集。
为什么我绕着中原四周围都看了,直到最近(2008年)才去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为我总认为应该先看四周,再看中原核心。最近西周出了五六个新东西,把西周的断代全颠覆掉了,所以当年我研究时,一开口就说我不断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我去看遗址时,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库房看陶片,书上写的、照片和图画,都不算数,你得拿在手上掂一下,掂出东西来,翻来覆去,看它小的洞洞,看它的质,我们叫看它的感觉,看多了就能看出感觉来了。你写都写不出来,你可以写出陶的质地,纹是粗或细,同样的斜纹在书上画出来是一模一样的,但你一看就晓得实物上的斜纹画得不同,是两个不同人画的,手指甲画出来的纹跟刀刻出来的纹也不一样,东西拿来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回事。看铜器也有感觉的说法,两个铜器一模一样,有经验的人一看就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说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变,那时候隔了个太平洋,我掌握资料当然不如大陆国内同仁完整。但当时我模模糊糊的至少隔离出一个东南,一个东北,一个北方。北方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少分割成四块,后来苏先生分割成六块,最后分成七块。
我在七〇年代晚期就跟光直讲过;“我总觉得中原中心论令我不安,I don’t like it。”我们来回讨论,他择善固执,直到书出第三版时,才终于承认中原中心论不如多元论妥适,全面据改。光直是很用心的人,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他觉得我搞历史专业,他搞考古专业,掌握的材料比我多。可是他忘了一点,他看到的是夏鼐系统的理论,别的理论没看见,而我看到的是世界上的理论,全世界文化的演变,因为我参加了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
八〇年代那一段对我而言是重新整顿自己,那时候我最高兴的就是理清楚仰韶文化、庙底沟那一系统,能够从关中一直拉到郑州,不断地发展,最后终于成为中原最根本的文化基础。在山东同时代的龙山文化,以及龙山前面那个系统,虽然和它一样强大,但是没办法和它对抗,至于河北那一系统,老早就被山东一系打败了,而东北系统和东南系统都无法发展下去。
长江系统是从大溪到石家河,也有它的发展方向。黄河边上的庙底沟和江汉接壤的石家河、屈家岭这一系之间,显然有互动。这个认知使得我后来能够解释战国文化的大变化,战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异锋突起,变得那么磅礴,终于替中国找上统一的局面,乃是江汉和黄河两套东西互相融合的结果。这个融合是儒和道的融合。前几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证实那时候的“道”,跟我们后来了解的“道”,不是一个事情。
我搞西周搞到今天,写了《西周史》,大陆上考古界以及历史界的朋友,每次发现新东西,就告诉我;“你的话又对了!”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本文摘选自《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许倬云口述,陈永发等访问、记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