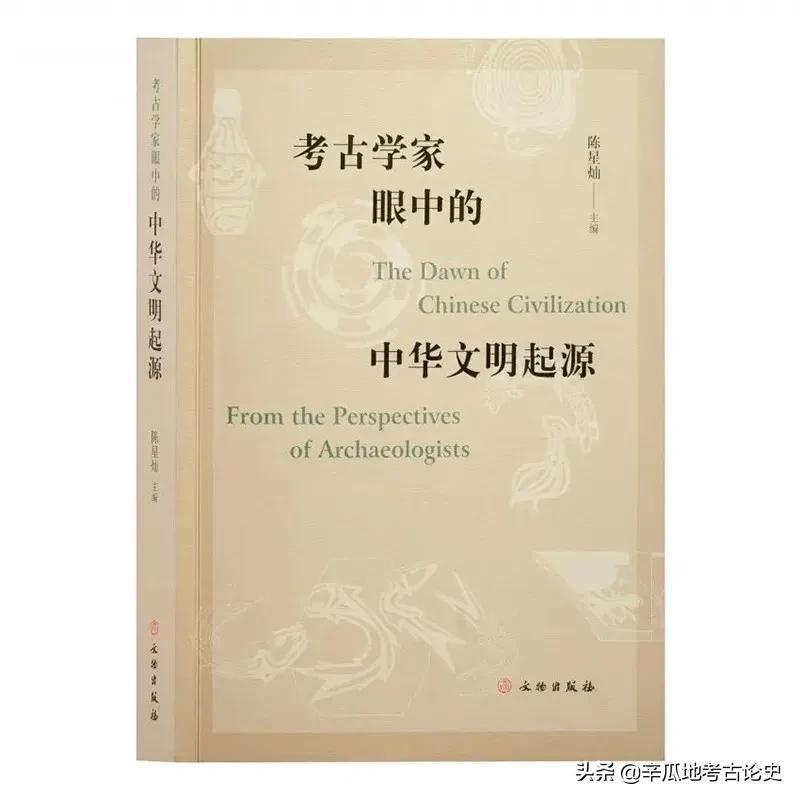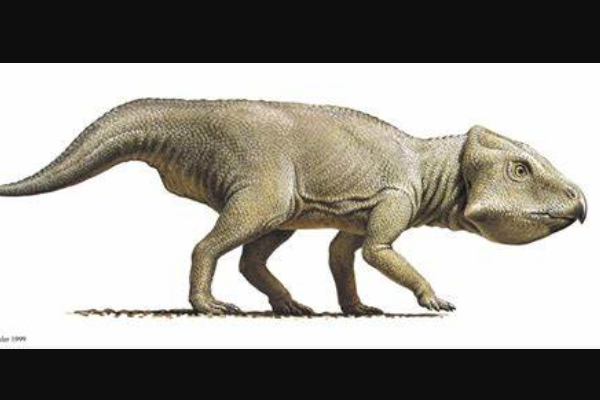荐书: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 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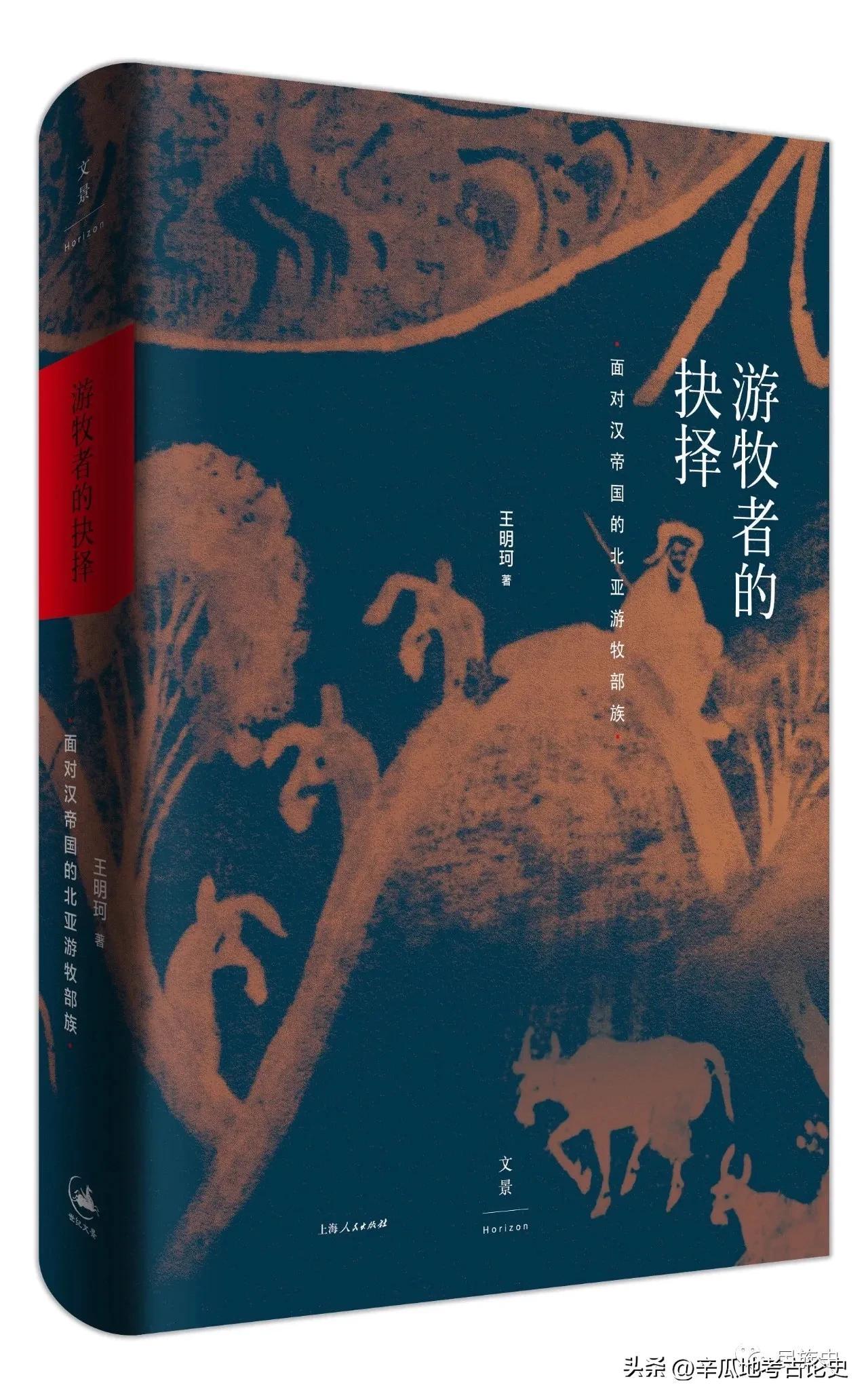
专家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 媒体评论
王先生绝非传统的书斋型学者,他的理论背后有着大量的田野调查作为支撑。——澎湃
他(王明珂)从“华夏边缘”出发,在田野和文献之间切换,横跨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透过常人习焉不察的现象揭示人类社会的本相,对大陆学术界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腾讯大家
序
多年来,王明珂先生屡次前去四川北部羌族地区调查,根据田野访谈与当地调查,提出具有卓见的报告,久已为同行钦佩。尤其他论述族群之间的关系时,常以“英雄”“兄弟”之类的故事,传达了隐喻的信息,王先生的报告,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也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
本书则是王明珂先生写作生涯中的又一新尝试。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陈述草原与高山两种游牧文化,列举中国北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形地势及其生态条件,决定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放牧经济与由此衍生的社会形态。因为这种差异,而有了两种牧业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王明珂先生的贡献,实已由田野报告,提升到比较研究的理论。他的造诣,又出现了一次跃升!
忝为王明珂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同事,我当然为王先生的学业精进十分欣喜!欣喜之余,也愿为本书陈述的许多现象,添上读后的感想,聊备本书的附语。
中国北方草原的族群,历史上即与其南方的中国农民,有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一次又一次,北族组织了强大的草原联盟,挑战南方的大帝国,而且还多次征服了中原的一部分,甚至两度君临中原。在这一类的斗争过程中,北族人口少,掌握的资源也不多,却不仅使中原疲于奔命,更能击败广土众民的中原帝国。在人类历史上,除中国的个案外,波斯帝国与印度也曾遭遇草原族群的冲击,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欧亚大陆的印欧语民族,一波又一波,侵入印度与欧洲各处,殖民建国,终于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种成分,也在欧洲发展了高加索族群的文化。
亚欧大草原游牧族群的动能如此强大,是不是意味游牧族群独具特色?我们不妨观察别处游牧族群的情形,作为比较。在非洲东部山谷的马赛人,他们牧养非洲牛,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马赛人的牧群里只有数十人的亲属团体,他们移动的范围并不大,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自古以来,未曾结合为大型的复杂组织,也未曾成为农耕族群严重的威胁。
阿拉伯的贝都因人,自古以来就在这一片干热的沙漠牧养羊群,沙漠中有水源之处,就有贝都因的部落,一个部落,也不过数十家,数百个部落,彼此独立,不相隶属,各有设克为其首领。贝都因人,能征善战,但也不过劫掠商旅,似乎未曾联合为部落联盟,像匈奴、蒙古那样,构成游牧帝国。阿拉伯人忽然崛起,是在穆罕默德的宗教力量,集合许多部落,才发展为强大的实力,从伊斯兰大帝国的兴起,可以获知“组织”是集合那些牧民的重要条件。
再以本书对山地牧民的情形观察说起,中国西部山地海拔高、纬度低,山顶、山坡与谷地之间,温度显著不同,牧养的牲口,冬季入谷避寒,春天开始,一点一点往山上移动,可以常年有足够的饲料。牧民只须在同一地点,上山下山,不必迁移,于是也可有农业补充牧业的不足。山地陡峭,没有广大的空间发展大型聚落,因此,山地牧业的居住形态,也是规模不大的小区,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大山里。这样的条件,不利于聚合为巨大的复杂社群。东汉的羌人,长久以来,只有地方豪强,没有大部落,更别谈国家形态的组织了,唐代吐蕃崛起,成为当时列强之一,其资源大部取于山下的青海大草原及天山南路的绿洲城市;吐蕃人力不足,还须掠取中国百姓驱赶入蕃。吐蕃维持帝国的力量有限;所以沙洲汉人地方势力张曹诸族可在河西割据,吐蕃竟不得不容忍其存在。
据以上所述,可以推知,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以至蒙古,能够常常聚合成大型帝国,应当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我以为,东方的牧业文化,应在新石器文化时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其北面边缘,已推到相当于日后长城一线,更往北去,温度雨量都已不利于农耕。于是,在今日内蒙古一带,农业只能勉强维持百姓生计,必须以采集和渔猎补充食粮之不足。饲养牲口不得不在较大的空间放牧,以就食于水草。这一初级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才有了远距离移动的游牧,谋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又因为驱车之便,长途贸易,更使资源与信息也可以传递流通。凡此条件,遂使大型复杂社会可能出现,草原大帝国,几乎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席卷大群牧民,以其骑射专长,崛起为强大的战斗体。他们不需有后勤补给,也不必顾虑兵员的补充。昨天征服的部落,就是明天进一步攻击的新兵。这种组织方式与骑马作战的速度,遂使草原上的牧民帝国,有其迅速崛起又迅速解散的发展过程。他们能征服南方农业文化的中国,并能入主中原的大帝国,但又消融于完全迥异的生态环境,最终被农业大帝国同化。
“五胡乱华”的鲜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是东北山地森林的以狩猎与初级农业维生的族群,在当地生态变化、生活艰困时,经过大约两代的长途跋涉,进入可能是今日呼伦贝尔的草原,又逐步南移到长城线,一路以其骑射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终于进入中原,建立了征服王朝,又以汉化消融于华夏文明。这一过程,契丹又重新走了一遍。但是,契丹并没有全部汉化,西辽一支迁入中亚,建立喀喇汗国,最后才消融于中亚的族群之中。后来的女真与蒙古,几乎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过程。满洲的经历稍为不同,他们在老家已以渔猎与农业建立了城邦,但是满洲征服中原,是结合了科尔沁蒙古的力量,而征服喀尔喀与准喀尔蒙古,则是结合了满洲的武力与该地的资源。
王明珂先生这本著作内容丰富,受他的启发,我联想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写入序文,也是我对王先生佳作的读后感。
许倬云 谨序
2008年11月1日
- 0001
- 0002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