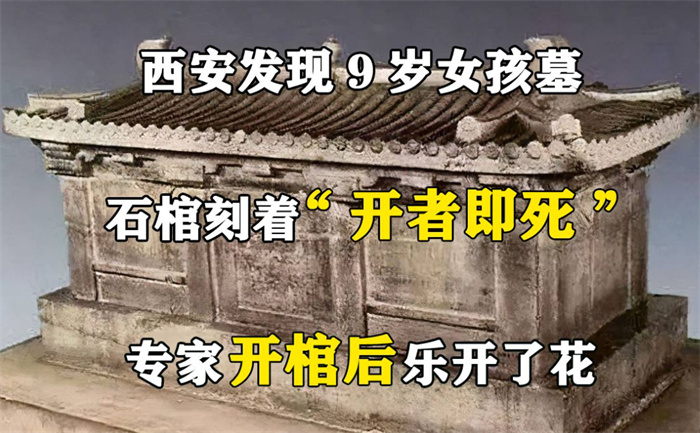曹斌:西学理论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自觉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应该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思考中国考古的现在和未来。提倡在考古学研究中贯彻田野精神,让考古材料重新说话。多手段分析发掘获得的“实验数据”,以实证主义的原则,置身本土文化以古人的视角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等。并率先讨论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

中国考古学源自西方近代考古学,与其他旧大陆的考古学一样,深受历史学影响。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出现,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成为美国考古学的主流。身处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中国考古学在90年代也曾掀起一场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之后,一方面新考古提倡的科学技术手段更加普遍地进入中国考古,促进了考古学的多学科合作和现代技术应用;另一方面,后过程考古学的理念和思想开始更多地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前者更多地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后者则为学术思想的影响,然均未能真正撼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也不能阻挡更多地中国考古学家对于中国考古学“特殊性”的个体思考和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探索。不可否认,中国考古学自夏鼐、苏秉琦、邹衡先生以来,西方考古学已谈不上对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整体冲击,但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亦需有自己的理论思考和探索,中国考古学研究也面临新时代的自觉。
01经典考古学到过程考古学的兴起
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初,正如前辈学者的教育背景一样,渊源在西方。李济和梁思永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前者博士毕业回国6年即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主持殷墟发掘并尝试对殷墟器物分类,后者1931年发现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奠定了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基础。夏鼐先生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从担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到辞世一直为国内考古学最具话语权的学界权威。留学归来学者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引领说明考古学为西来之物,初兴的中国考古学也基本是沿着西学的步调开始自己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工作一样,命名考古学文化,确定文化类型,建立年代序列。但是5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逐渐隔绝,6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停滞阶段,考古学虽在零星发掘,但学术研究相对沉寂。这一时期如果用一个流行的英译词概括,那可能是“断裂”。在70年代末学术研究全面恢复、高校重新招生之后,中国考古学理论基础依然是50年代之前汤普森“三期说”、蒙特留斯器物分类以及柴尔德文化历史研究等。但欣慰的是,中国考古学对于器物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独立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止,同时一位成长自北平考古研究院,土生土长的中国考古学家的思想在苏秉琦先生本人和学生的阐释下逐渐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西方学者并不都认同这样的思想就一定是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初到西方世界的中国考古从业者,多数情况下国外同行还是会微笑着问是不是研究“区系类型”,所以至少在西方考古学的眼中,用另一个流行的英译词汇,它已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但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相对沉寂和研究范式正在形成的时期,西方考古学却发生着巨大的变革。50年代一批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进入考古学界,在科学研究思潮,特别是1962年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专著《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下,美国考古学界掀起了“过程考古学”(“新考古学”后来修正为“过程考古学”)的革命。不可否认,过程考古学实证的态度以及通过科学手段考证“功能”的方式与我们自清代以来形成的考据学传统在理念上有着一定的互融性,而考古学科学化的提法也很符合我们试图将考古学发展为一门“硬学科”的愿望。因此过程考古学推崇的许多科学手段,特别是田野调查、发掘和记录的方法在我们与欧美学术交流频繁之后很快进入中国,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而中国形成的“航空考古”、“水下考古”也正是过程考古学理念的实践,特别是水下考古还形成了专业的研究人群,组建了国家级的考古机构。当然,在借鉴了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也杂糅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和学术观点后,过程考古学形成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建设,如基于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理论发展出的“功能学派”的器物、遗址功能分析,与自然学科结合的人类适应性研究等,理论有考古记录形成过程和与民族学方法结合产生的中程理论等。

02后过程考古的探索和思考
在“后现代”社会思潮大背景的影响下,西方考古学者开始检讨、甚至批评过程考古学中的某些问题之后,中国考古学也在稍晚时候某种程度上加入了“批评”的行列。我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初入大学第一次师生见面的场景。30个还不知道考古学是何物的懵懂新生挤在学院三层博物馆的陈列室,聆听正前方座椅上几位考古学教授的迎新谈话。当时谈话的内容基本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有两个场景至今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中国考古学新生见面会恒久的问题,“谁第一志愿填报了考古学?”,第二个既是谈到新考古学时几位教授的调侃。很显然,在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已经形成的年代,过程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式已很难真正撼动中国考古学。新考古的科学手段和多学科合作虽为中国考古学所欣赏,并实践于国家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但是新考古学“推演法”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中国考古学惯用的“归纳法”还是有着一定的抵牾。“推演法”于考古研究实践中常见的是一种研究者先构思观点,然后从一堆材料中选取支持自己构想的材料从而支撑自己观点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不存于旧大陆学术体系,只是这种预设前提然后选择材料论证支持自己观点的方法长期为中国学者所厌恶和摒弃。此外,新考古学对于考古学“科学”的理解也与中国考古学有着许多的不同。中国考古学数年基于严密的材料考证形成了“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风,借用“科学”手段最大的苦恼源自人文学科学术问题的不能“说死”,希望科学进入考古学能给予学术问题1 1=2的结论。但是新考古学演绎推理(沃森:“几分天资,加上演绎推理,再加一些新技术装备起来的跨学科队伍”)的结论让中国考古学意识到他们与传统的中国式“严谨”仍有距离,更不能替代层层严密的实证推论。所以这样的批评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同的是西方考古同行对于新考古学的批判将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带入到了新的阶段,国内则坚定并规范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且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了更加“务实”的时代。 科学可以很好的解释自然世界,但始终无法替代人类的思想,也还不能更好地阐释人类的思维。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人探索宇宙,有人为信仰而战,主观选择因人而异,并不划一。而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人和与人相关的学科,其中涉及的显然是人类思维(脑力)指导行为产生的现象和结果,必然不同于自然和动物世界。对于这样的研究,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手段必不可少,但究其本身而言,考古学可能并非自然科学。虽然在科学主导世界的时代,我小时候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考古学在50年代之后也一直为将考古学变为一门“硬科学”而努力,但西方的探索似乎说明两者的关系渐行渐远。在结束了近40余年的辩论之后,考古学不是自然科学在美国已是无需再争辩的话题。考古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先假设再推论,但是“科学”实践于考古时依然无法测量“误差”,而古代人类遗留的偶然、随机、片段这一基础材料问题也需予以考虑。所以首先,人之所是“人”而迥异于动物,就是人类主观意识的强大和人类的主动能动性,否则人类至今可能依然生活在树上。所以考古学对于人类遗留的研究显然不同于科学对于自然世界和动物群体的探索模式,首先需要理解人之所以为人所独具的观念和信仰世界。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将考古的探索回归人类主体的研究,去理解人类如何在思维驱动下从事相关活动并形成物质遗存;此外,人类的演进模式也不可能总是过程考古学立论基础之一的“均变论”,人类很多情况下会选择适应,但每一次大的跨越可能都是主动选择以及突变的结果。即便在人类充分进化的今天,选择和非均变的例子也随处可见。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揭示,由于人类的选择荷兰人的身高在近150年增长了20厘米一跃成为全球最高,而曾经作为世界最高人群的美国人平均身高却已明显低于北欧,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却是荷兰女性对于高个子对象的偏好和美国男性对于身高更低的女性生育对象选择的结果。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人类主动选择性导致的进化和发展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另一方面不同情景、不同时段的发展不可能匀速均变。所以,从人类“主体能动”研究出发的“后过程考古学”就有必要登上学术的舞台。 提到“后过程”可能在国内只有考古学家知晓,但是提到“后现代”却无人不知,其实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正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下发生的。在“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就像20世纪40年代初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瓦特·泰勒在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下,依然凭借唯一出版的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对传统考古学发起挑战一样,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以伊恩·霍德(Ian Hodder)为首的考古学家开始了“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建设。就在90年代西方考古学界的讨论更加自由,特别是美国考古学界的年轻考古学家可以平等“挑战”前辈学者之时,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对西方考古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国内考古学后过程视角的研究相对多见性别考古的探讨,但实际上后过程考古学的理念对于中国考古学家研究的影响已明显可见。例如中国考古学界经常提到的“contextual”词汇以及以之为代表的“背景考古学”的理念。此外,他们主张的社会变化同时受到背景(contextual)和文化特殊性(cultural particularity)制约,并非铁板一块匀速均变的观点亦非常重要。

03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反思
经过几十年的争辩,不同派别互相攻击的西方时代已经过去,甚至这样的讨论,西方学者们也都开始“淡漠”,曾经的过程考古学家也开始从事认知考古的研究,当代考古学即便能够划定派别的界限,可能也很难为自己定位。幸运的是,无论西方“新思潮”的兴衰,中国考古学从没有被任何一种范式统一过,也没有发生过互相的替代,而中国学者也一直不以学术研究的派别划分界限,或许也根本理不出复杂派别的头绪,有的只是研究时段差别造成的具体研究方法的些许不同。如果说中国考古学有一个“中国学派”,那么其实就是在传统考古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点以及中国传统学术的特长,不断吸收各种养分,以解决学术问题为出发点,在实证主义的前提下运用多种手段从事学术研究,并在内部之间形成了新石器范式、商周范式、历史时期范式以及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和共同发展。如果现在的中国考古学还沉浸于西方曾经的学派论争或者复古曾经被证明不太有效的理论方法,那么无疑是一种倒退,或者说停留在了以西学为尚的“殖民文化”学术体系中。中国考古应该做的是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思考中国考古的现在和未来。 传统考古学是否已经落后,其他学科或者现代性的研究才是前沿?上世纪20年代后半段,奥尔布赖特(Albright)的圣经“考古”第一次被世界考古学界抵触和“反感”,正是因为其丧失了考古学研究的特性,将考古学变为一种纯服务于历史学或者证明文本有效性、确定性的工具,而新考古学兴起之初,似乎又走向了唯科学技术和演绎假说的另一端。西方考古学曾经反思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中国考古学也曾被其他学科的课题和方法技术完全“吸引”。传统考古学的问题,例如编年序列、文化性质、文化谱系等问题逐渐沦为“下品”学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的课题和研究成为考古学的“上品”学术,这在一些期刊的发文选择和学界内部科研评价中的都有一定的体现。其实学术的研究本就不应有“上品”、“下品”之分,而应视提出的学术问题和解决的学术问题而定,只有解决了或者提出了学术问题的研究才能称为好的研究。而多数情况下经典的才是永恒的,盲目追赶或者穿凿附会时尚潮流的学术来的快可能去的更快。余英时先生说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但是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也应该贯彻踏实求真的传统,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理解中国的考古问题。未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应置身本土文化或者像生活在古代的古人一样解释世界,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思想和价值观等。同时将碎片化的考古材料、文本记录整合进“大历史”的范畴,通过整合研究使考古学成为复原逝去的古代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的一门学问。而中国考古学的源流,似乎也不必完全切断与传统金石学之间的联系,否则并不一定有助于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还有让之成为借鉴其他学科而成的杂合体的危险,从而影响了考古学的地位和未来发展。其实对于研究古代的学问,考古学才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学科之一。 即便现代学科有趋同之势,但是考古学和其他一些人文学科还是有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获取材料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理解考古学依然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考古学获取材料的方式都是考古学家发掘,发掘的对象为古代的物质遗留,是一批随机遗留下的客观资料。考古学科的这个基本特征,要求我们不断的去“做实验”和取得“实验数据”(考古发掘和整理过程相当于做实验和获取实验数据),通过“实验数据”论证、推理学术问题,所以考古学也是一个不断“修正”的学科。虽然考古发掘不能重复性作业(逻辑证伪),但是考古学是一个可以“前进式”证伪的学科,可以不断通过新的发掘(实验)和获取的考古材料(实验数据)去证真或证伪以前研究的学术。而全世界的考古学确实也都如此,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包括有着悠久传统的欧美考古学者也不断的走向世界各地去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推动考古学的进步。如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以付罗文教授为核心的团队长期在四川盆地和甘肃齐家坪进行调查和发掘工作,而我们的考古学家也开始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进行田野发掘工作。但如果考古学的研究不再重视田野工作,那么考古学就停滞和局限在了类似一些人文学科的阐释的范畴。此外,考古学的发掘仍是考古学者主观的选择,古代的遗留也是随机性的,不是古代社会的全部遗留,如果停滞考古发掘和不再获取新的“实验数据“,那么考古学还可能沦为一种循环论证和语言文字游戏的可能,从而丧失了考古学不断求真、前进式证伪的优势。而所谓对于古代社会的复原、对于古代历史真实的探求也只能是考古学家自己理解的古代社会和古代历史,不再是历史真实的追求。 说考古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好比说科学被实验数据牵着鼻子走,这样的观点并不能得到更多地认同。过去的考古学不是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而是被其他学科。如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商文化老观点的“新热”,完全是受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影响的结果。而考古学家不熟知的是,新的碳十四数据公布的是拟合后的二里头文化各期的绝对年代,而未公布全部碳样品测年的原始数据。应该说碳十四测年的数据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但在“整合”进入考古学研究领域的时候,通行的是贝叶斯统计分析,而该统计方法其实只是诸多统计分析方法的一种,其二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先验条件,借鉴哪位学者的分期意见作为先验条件,那么各期绝对年代的数据拟合结果自然会向该学术观点倾斜。这是一个考古学家放弃自身材料分析研究而被其他学科或者技术手段牵着鼻子走的典型例子。其实长久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倾向,以前是历史学、中间是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还有是政治学、认知科学的趋势,考古学的过去险些成为其他学科的牵线“木偶”,因为“弱小”而视别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更“进步”,甚至险些成为只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的学科。如果坚持考古学研究是“科学”模式,那么更要坚持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实验数据”,并用实验数据进行学术研究。考古学作为一门自己获取研究材料的学科,必须坚持从材料入手的原则,并在具体分析中遵循实证的原则。科学研究一直视“超数据量”的推论为不严谨的结论,那么中国考古学“一分材料说一份话”的推论模式可能也并不过时。
04结语
在地方性知识与人性、全球化的范式之间寻求共同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潮流之一,而“让资料说话”的口号,促使人类学者又一次进入田野以经验的态度收集多元化的文化资料。其实考古学的研究亦是如此,在经历了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两位代表人物90年代之后也走向田野贯彻田野精神。诚然,考古学的研究既是具体遗址的田野工作,也是远离田野的思考。但是当考古学的研究进入更复杂的层级之后,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趋势必然也是一股重新回归田野的潮流,与其“空谈”或者争论理论方法,不如回归本源“让考古学材料重新说话”。 考古学研究是对古代世界的探求,需要以古代人的观点看待古代世界,然后将物质的、象征性的东西转化为当代的语言表述出来。成为一级学科的中国考古学有条件也理应率先思考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而不是附属于某一个学科的考古学。此外,考古学作为与自然科学技术关系最密切的人文科学,未来要思考的不是哪些近代科学技术可以代替学者的研究,而应思考哪些考古研究是科学技术、人工智能做不到也不可能完成的,这才是可以永恒的学术研究。即我们要从事的不是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的研究,而是那些人工智能不能也不可能完成的研究。
注从略
本文发表于《齐鲁学刊》2020年4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