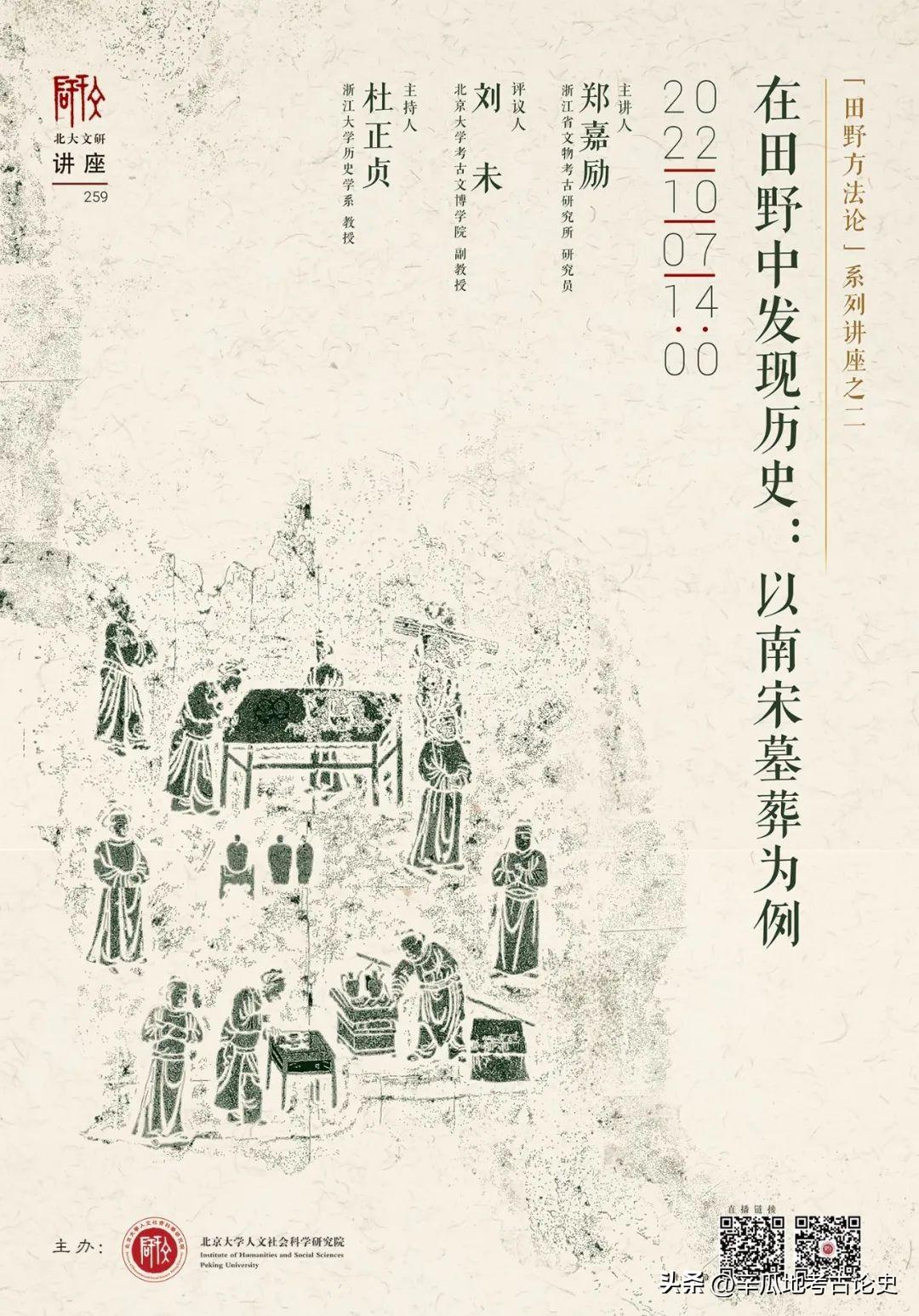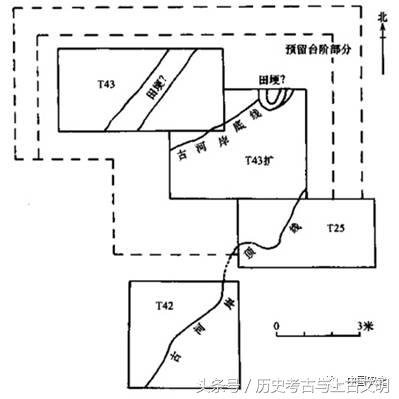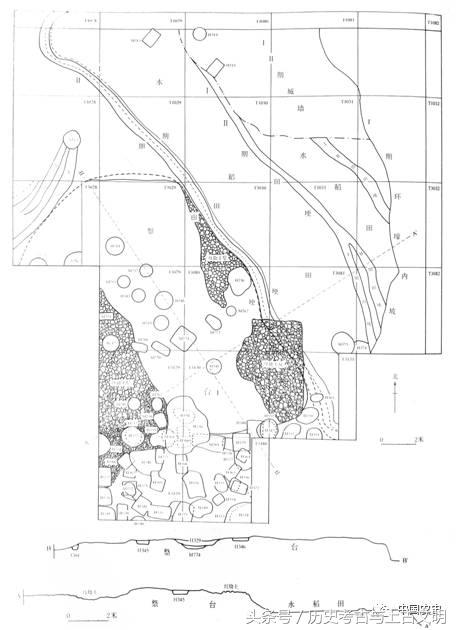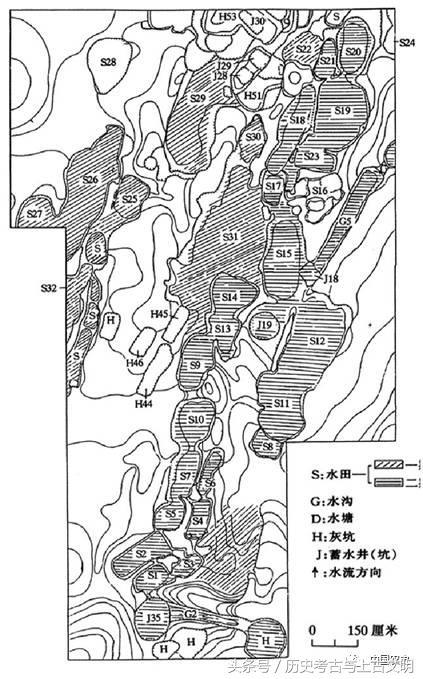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泛指我国西部的疆域,包括天山南部与北部地区、中央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印度诸国,及至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地区,这里包括三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三河: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笔者在论述西域文化时,基本上采用狭义西域的概念。

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相当密切,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的交流,与政治、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密不可分。早在商代,西域与中原就有了密切的联系。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好女墓中发现了750余件玉石雕刻品,据鉴定,玉雕材料为新疆和田玉。这说明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在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已存在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因此,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更为频繁,两地之间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公元前138年(前汉建元三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时13年之久。他的足迹抵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公元前119——前116年(元狩四年至元鼎元年),张骞再次通西域,到达乌孙。他遣副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张骞两次通使西域,揭开了中原与西域密切往来的辉煌篇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东汉时期,西域与中原屡受匈奴的骚扰。班超步张骞之后,两次出使西域,联络西域诸国,抗击匈奴,平定叛乱。班超的第二次出使西域,曾长期留居疏勒(现在新疆的喀什市),他在西域经营30年之久,与于阗、姑墨、莎车、龟兹(今库车)、焉耆、月氏、乌孙、康居等广为联系。他还曾派使臣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国)、条支(今阿拉伯)等国。他为维护西域的稳定、促进西域与中原汉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班超去世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也走上通往西域之路。
张骞及班超、班勇父子不畏艰险,多次率众奔赴西域。他们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行者。他们首次向中原传播了西域的知识: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生活、各种物产以及奇风异俗等。他们的西行见闻被记载在汉文的史书和典籍之中,成为国内外学者认识与研究西域问题最为宝贵的资料。
通过这些无畏使者们的努力,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开通了。从此,西域各地的使者、商贾来中原者络绎不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西域使者及商贾足迹遍及中原各地。而中原使者与商贾赴西域者也不在少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列传》)据此记载,中原赴西域的使者以每年十批、每批二三百人计算,那么,每年赴西域的汉使、商人可达二三千人之多,且在那里滞留多年。汉代中原与西域关系之密切,可从中窥见一斑。
驰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汉代之前业已开通。《汉书·西域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一位研究西域的西方学者说:“汉使所至,常能表现中国兵威及工业之盛。中国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丝绸为著。自是以后,希腊及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斯人’(Silk-Weaving Seres)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可知丝织品通商与中国关系之重大矣!”
汉代在经营西域方面,成就是空前的。汉朝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天山南北各地归附汉朝,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魏晋的统治者对西域地区也很重视。汉代末期,西域各地纷争迭起,东晋初太元七年(382),前秦苻坚平定了东方,欲进军西域。他任命吕光为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吕光率七万大军西征,抵达高昌、龟兹、焉耆等地,威震西域。后他护送龟兹佛教大师鸠摩罗什东归,其子复任西域大都护、镇西将军,镇守高昌郡。吕光父子为维护西域的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贡献。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西域与中原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大量西域人涌向中原,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西域商人到洛阳的人数剧增。《洛阳伽蓝记》对此有生动的描写:“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己。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许多人滞留不归,仅居住都城洛阳者就有一万多户。在中国历史上,西域人入住都城人数最多的当属北魏。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局面,征战不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涌向西域,高昌地区成为汉族移民的聚集之地。西域与中原人员的大规模互动,极大地促使两地的文化交流。加之魏晋统治者注重对于各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为隋唐多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代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亦功不可没。隋朝的统治者重视与少数民族建立联系,例如:一突厥部族的安全受到威胁,其头领沙钵略可汗向隋文帝告急求援,隋文帝立即派人领兵接应,并送去大量的衣物和粮食。沙钵略可汗很受感动,上表隋文帝宣称“永为藩附”。隋文帝亦颁诏书普告天下说:“往虽与积,犹是两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沙钵略可汗病死,隋文帝竟为此停朝三天,派人前往吊唁,赠送奠伊杂帛五千段。(《隋书·突厥传》)隋炀帝即位后,与东突厥大首领启民可汗关系友好。大业三年(607),隋炀帝率浩浩荡荡人马北巡,到达榆林郡,亲赴启民可汗的牙帐。隋炀帝一贯厚待启民可汗,据《资治通鉴》记载:“帝欲夸未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驮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两千(十)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场面之豪华、庄严,宴席之丰富,散乐演出之变幻莫测,令游牧的突厥人惊慕、喜悦。启民可汗仰慕中原文化,提出要改穿隋朝的冠带服饰。他还曾先后娶隋朝的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为妻,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隋炀帝有志于通西域,对西域之事甚为关注。当时西域商人多聚集于河西走廊的张掖,与汉人互市。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亲自西巡,抵达张掖。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三十余国使臣应邀来到张掖,拜见隋炀帝。在张掖举行的西域各国使者盛会,表明了隋炀帝对西域的高度重视。除此之外,隋炀帝经营西域还有三大功绩:一是势力抵达伊吾(现新疆哈密),并修建新城,号“新伊吾”,这里成为胡商与汉人互市之地;二是设立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新疆且末)、伊吾(今新疆哈密)三郡,实行了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度;三是隋炀帝在世时,掌管西域事物的裴矩撰写完成记载西域各地山川、险要和风俗的传世名著《西域图记》(三卷)。此书的问世,使世人对西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隋朝的统治虽不足40年,但是,隋文帝、隋炀帝有志于治理西域,重视发展与突厥可汗的友好关系,成就显著。
到了唐代,由于唐朝统治者采取开放政策,加强与各国各民族的往来,尤其重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唐朝文化充满了活力,呈现出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唐朝对于西域地区尤为重视,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朝经营西域最显赫的功绩之一,是统一西域,并在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西域设置了八个“都督府”、八个“州都督府”,在各属地设置了七十二个羁縻“州”,结束了西域长期存在的地方割据势力和连绵不断的征战局面。为了维护西域的稳定,唐朝在西域加强了军事力量,在西域设立了安西督护府,统领龟兹(现新疆库车)、于阗(现新疆和田)、疏勒(现新疆喀什)、碎叶四镇,管理西域驻军人数不等,多则上万,少则上千,安西四镇驻重兵,有时多达三万兵马。唐朝基本上完成了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形成了以伊州(现哈密)、西州(现吐鲁番)、庭州(现吉尔萨尔一带)为核心,以安西督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
丝绸之路畅通,西域的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唐朝都城长安,积极与唐开展贸易。其中有小型的民间贸易往来,也有由西域组成的上千人的贸易使团,他们带来西域丰富的特产,并将内地的丝绸、瓷器等物销往西域各地。当时的长安,有大量西域人居住,其中仅突厥人就近万家。而天宝初年,长安仅有三十余万户,也就是说,三十来户人家中,便有一户是突厥人。此外,还有西域各地的商人,长安的西域人口数目惊人,长安成为一座多民族的国际名城。
到了宋代,西域与内地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回鹘汗国与内地的贸易往来较之从前更为频繁,据《宋史·回鹘传》记载,仅乾德三年(961)一年,西州回鹘汗王就先后三次遣人入贡。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建隆二年(961)至天胜六年(1028)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回鹘汗王遣贡使四十余次,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百人,他们到开封,带来马匹、骆驼、玉器、药材等,带回的是丝绸、布匹、茶叶、瓷器和日用生活品。
建都于喀什噶尔与巴拉沙衮的喀喇汗朝,虽距内地路途遥远,但是,他们的使臣常常远道而至。尤其是从宋熙宁元年(1068)以后,其汗几乎是每隔一年或两年遣使一次,有时甚至一年内遣使两次。由此可看出宋代西域与内地关系之密切。
西域从汉代划入祖国版图之后,西域与中原的关系,历经魏晋时期的发展,隋唐时期的鼎盛,宋代密切的往来,千百年来从未间断过。因此,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
从汉代起,汉人开始大量入住西域,其中包括历代汉吏及其随从、汉族官兵及屯田战士、和亲的汉公主及庞大的随嫁人员、躲避战乱的汉族移民等等,汉族的文化通过他们带到了西域。加之,历代政权通过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和实施郡县制度,汉语曾作为重要的西域官方语言之一。因此,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新疆的考古中,发现大量汉锦、中原形制的铜镜、汉文木简以及中原的铜钱。汉锦在西域多处都有发现,例如,1995年在尼雅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色泽鲜艳的织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还发现了用汉锦缝制的胡袍。锦和其他丝绸在西域的大量出土,说明西域与中原关系之密切。此外,中原的凿井术、筑城术,在汉代也传入西域。
汉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强了与西域的密切联系。在西域古代民族中,倾慕汉文化、学习汉文化的人很多。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绛宾携夫人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9年)入朝,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在长安滞留一年。离开京都时,获汉宣帝所赠厚礼。之后,龟兹王绛宾又曾多次入朝。这位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钟家仪”。绛宾王去世后,其子又多次入朝,保持着与汉廷迁亲密的关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莎车王父子兄弟三代学习汉朝典章制度的故事。莎车王延曾作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教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莎车王延去世后,其子康继承王位。为抗击匈奴,康与河西大将军窦融取得联系,表明自己思慕汉之心。建武五年(30)他被汉朝廷立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他死后,其弟贤继承王位,贤多次遣使赴汉廷献贡物。由于“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骑、黄金、锦绣”。三代莎车王倾心汉文化,受到朝廷重用的例子表明,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文化的影响在西域与日俱增。
从魏晋到隋唐,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匈奴普遍采用了汉姓,单于姓刘,另有冯氏、薛氏、郝氏、白氏。刘渊在晋时建国称汉,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武兵法,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卷101刘元海传)
高昌(吐鲁番地区)在魏晋时设立郡县,高昌王均由汉人担任,居民中汉人也较多,因此,汉文化在高昌地区的影响极深。据《梁书·高昌传》记载,高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高昌传》云,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胡语”。从这一史料记载看,汉文的典籍在当时已成为汉族和当地民族儿童的教材。从19世纪开始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论语》残片。尤为珍贵的是,1969年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唐景龙四年(710)的《论语郑氏注》写本,书写人竟是一个年仅12岁名叫卜天寿的西域孩子。[7]《论语》是孔子与他的弟子们讲论、问答的记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一直被视为经典,并成为儿童必读的教材。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被奉为圣人,祭孔之俗在中原汉地延续至今。此俗也传到西域,西域人将绘制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画像悬于王室。
在古代西域,汉语与胡语(民族语言)是通用的。在各民族民众中,通汉语的人也很多。在楼兰古城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魏晋时期(220—420)的700多件汉文文书,有写在木简上的,也有写在纸上的。其中在罗布泊“海头”发现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信稿,说明焉耆王通汉文。在罗布泊还发现了生活于当地的羌女用汉文写的信函,文笔流畅,用词达意准确。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在和田策勒县的出土,说明汉文在西域通用,是一种官方语言。
到了隋唐时期,汉文化对于西域的影响更为深远。在西域,精通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旧唐书》曾记载一位世居安西、名叫哥舒翰的突厥突骑施部人,他“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别什八里(北庭,现新疆吉木萨尔一带)僧人古萨里是维吾尔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他精通古汉语,深谙中原文化,他将巨著《金光明经》和《玄奘传》(全名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从汉文译成回鹘语。
各国各民族的商人、学者、艺人、僧人,从西域涌进长安和洛阳,其中许多人成为永久居民,他们精通汉文化。在汉化的西域知识分子中,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姓氏。例如,来自于阗的王族尉迟姓氏,出过许多名人。尉迟敬德、尉迟宝琳父子、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他们与佛经翻译家智严(尉迟乐)可能是同时代的人。智严“自幼生居异域,长于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崇级”。智严是唐中宗时代的人,上溯四朝,应是唐初来长安的。尉迟姓氏是于阗的王族,朝廷很重视他们。唐玄宗还把宗室女嫁予尉迟胜。尉迟青擅长吹篥,其技冠绝古今。他居住在长安的常乐坊,后来升为将军。除于阗的尉迟姓氏之外,龟兹的白姓氏、疏勒的裴姓氏、昭武九姓中的安姓氏、康姓氏等,都是长安中有影响的大姓氏,名人辈出。他们的子孙后代居于长安,是汉化的西域胡人。如果说,汉代是开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那么,唐代则促进了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业绩是辉煌的。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西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亦对中原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汉代起,中原汉地便开始形成一股强烈的“西域胡文化”热。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自张骞通使西域后,大量西域商人涌入内地,在长安和洛阳,胡人、胡姬随处可见。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对胡姬有所描写:“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壚。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窕窕,一世良无所”。“胡姬”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李白的诗句中,如《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铵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河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另一首诗《前有樽酒行》云:“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壚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到了唐代,西域文化影响之所及,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宫廷贵人穿胡服,学胡俗,食胡饼,听胡音。西域的乐舞与绘画艺术,对盛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乐就占到五部:《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西域的乐舞不仅受到宫廷的垂青,也深受民众的喜爱。
当时的长安和洛阳,胡商、胡姬云集,胡舞、胡乐成为时尚。诗人元稹感叹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在《法曲》中这样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在王建的《凉州行》中有这样的诗句:“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胡乐在长安、洛阳之盛行,从上述诗中可看出。西域的舞蹈也是别具魅力,唐代的诗人对此有形象的描绘,例如,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一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不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西域的习俗渗透到唐王朝各个方面。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在长安和洛阳,窄袖、小腰身的胡服极为盛行,花蕊夫人的《宫词》云:“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裳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至于胡食,魏晋以来,已遍及中原。到了唐代,食胡食之风更盛。胡食有胡饼(炉饼)等。胡饼包括有肉馅饼和无馅饼两种,一般是用炉烤制的。胡食不仅进入宫廷,在民间流行更广。安史之乱,玄宗西幸,至咸阳集贤宫,无以果腹。杨国忠从集市上买来胡饼,给玄宗充饥。
《新唐书·承乾传》记载,唐太宗之子承乾好突厥语言、好着突厥服、喜好突厥俗语。他愿意住毡房,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番旗设穹庐,烹煮羊肉,抽佩刀割肉而食。他还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鼓乐声昼夜不绝。王宫贵族对于胡俗的偏好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交流,无论对于西域文化发展,或是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0000
- 0000
- 0001
- 0000
- 0000